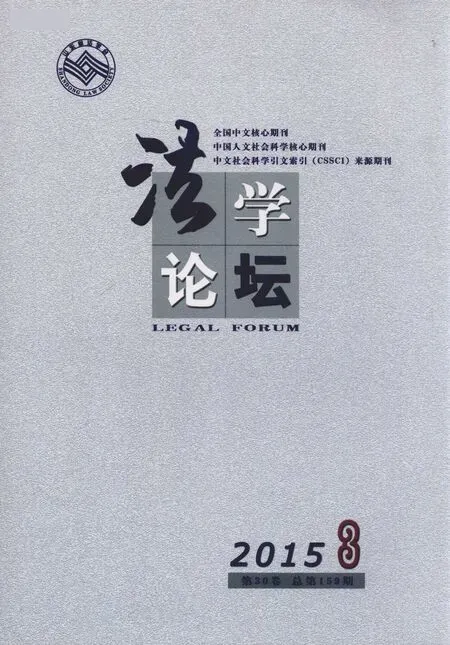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难问题实证研究
——以S省为例的分析
韩 旭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72)
【实证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难问题实证研究
——以S省为例的分析
韩 旭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72)
对S省五个市的实证研究发现,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权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会见难”、“阅卷难”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律师在行使辩护权的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难题:职权机关限制、剥夺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权的问题比较突出,阅卷权的实现面临一定的障碍,知情权和表达辩护意见权未受到应有重视,调查取证难问题依旧未改变,辩护权受到侵害后得不到检察机关的救济和保护。为破解律师辩护难题,建议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严格规范执法办案行为并为律师参与诉讼提供便利条件,建立侵犯律师辩护权利的程序性制裁规则及以审判为中心的权利救济机制,等等。
新刑诉法实施;律师辩护;权利保障;实证研究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新法针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权利救济难”等问题作了较大的制度调整和完善,旨在进一步加强对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中的作用。新法实施已近两年,修法的初衷是否已经实现,律师辩护中的“三难”问题和其他制约辩护权实现的问题是否已经得以解决,实践中律师辩护面临哪些新的困境?这些都是新法实施后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带领课题组成员自2014年7月开始先后到S省的Y市、L市、G市、N市、C市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访谈和问卷调查。先后召开律师、法官代表座谈会12场,访谈对象为当地主要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和中级法院、基层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包括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庭庭长),受访律师118人、法官66人。课题组共发放调查问卷515份,收回有效问卷498份,接受问卷的对象除Y市、L市、G市、N市接受课题组访谈的律师外,还有C市部分律师事务所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通过对上述实证调研资料的梳理分析,笔者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S省律师辩护权保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答。总的看法是,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S省律师辩护权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会见难”、“阅卷难”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律师对刑事诉讼推进的影响力增强,参与度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一些旧的问题还没有得以解决,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前者例如调查取证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难、获得权利救济难等传统难题依旧未改变,后者例如涉嫌贿赂犯罪案件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变得更加艰难,办案机关随意扩大“三类案件”的适用范围,公开或变相限制律师会见权,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辩护律师职能作用的发挥,影响了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的进程,应当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一、律师辩护“难”在哪里?
(一)职权机关限制、剥夺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权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涉嫌贿赂犯罪案件,律师会见权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曲意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则。例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45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一)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50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三)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为了限制律师会见,对上述规定作断章取义解释,将凡是涉嫌贿赂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案件均定性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而不考虑“犯罪情节恶劣”这一因素;对于“涉嫌贿赂数额在50万元以上”之中“涉嫌”二字的认识,办案人员通常也更愿意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要么是举报数额、要么是初查数额、要么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承认的数额,导致办案机关在涉嫌贿赂数额的理解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即便是对于贿赂数额达不到50万元的案件,也可以随意解释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从而限制律师会见;二是,办案机关任意扩大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案件”适用范围。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会见才应当取得办案机关的许可,除此以外的案件,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这“三证”即可直接会见。然而,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的办案机关将涉嫌敲诈勒索犯罪案件、非法经营犯罪案件、贪污犯罪案件、非法持有枪支犯罪案件等均以“三类案件”为名,给看守所打招呼,要求律师会见必须事先经办案机关批准,以此限制、剥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三是,看守所不及时安排会见或者附加限制性条件。有的看守所拖延至48小时即将届满时才安排会见;个别看守所违反律师凭“三证”会见的法律规定,要求律师会见必须事先进行预约;一些看守所在法律规定的“三证”之外附加其他条件,变相限制律师会见权,增加了律师会见的难度和成本;四是,一些看守所硬件设施不足,会见室数量较少,有的市级看守所会见室只有3个,且经常被办案机关占用,难以满足律师正常的会见需要,律师会见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律师可以凭“三证”直接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因会见程序简化、便捷,律师会见需求增多、会见频次上升,在律师会见窗口、会见室尚未增加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会见拥堵”,以致于一些地方看守所门口出现会见排队、黄牛倒号的现象。参见孙静:《看守所外有黄牛倒号》,载《北京青年报》2013年9月27日。五是,某些特殊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送看守所羁押时被隐去真实姓名,实行只有代号的秘密关押,辩护律师去看守所会见时因无法查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姓名导致会见权落空;六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因办案机关不通知家属和律师监视居住的地点,造成律师无法及时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有的案件律师在指定居所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办案机关派员在场进行监视、监听,律师与当事人之间自由、秘密交流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等等。
(二)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实现仍然面临一定的障碍
一是,律师复印案件材料,检察机关收费标准不统一,有的地方检察院存在滥收费问题。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检察院对律师复印材料收费普遍较高,低则每张0.5元,高则每张1元。个别检察院甚至将律师阅卷作为赢利创收的手段,例如,四川省宜宾县检察院对律师用手机拍照也要收取每页0.5元的费用,且不给任何票据,社会影响很坏;*参见杨璐:《四川宜宾检察院被曝拍照阅卷每张收五毛 不开票据》,载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140807/049776.htm2014年8月7日。二是,办案机关对律师阅卷方式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辩护人复制案卷材料可以采取复印、拍照等方式”,但是一些检察院对律师阅卷方式进行不当限制,甚至存在随意刁难律师的现象。有的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案卷材料,只允许律师查阅、拍照,而不允许复印;有的仅让复印,但不允许拍照。对于电子案卷材料,有的检察院不允许律师拷贝,这无疑增加了律师阅卷成本;三是,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与审查起诉部门对接不畅,律师联系或者预约阅卷花费时间较长,安排阅卷不及时,阅卷排队现象时有发生;四是,检察机关对阅卷范围进行限制。对于公安、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制作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虽然在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中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但有的检察院不随案移送,即使随案移送,有的检察院也不允许律师复制,导致律师在对讯问合法性提出异议、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时无法提供有力的线索或者证据。
(三)辩护律师的知情权和表达辩护意见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是,律师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的权利在实践中基本落空。《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但是,从课题组调研情况看,律师普遍反映他们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非常困难。对律师了解案情的要求,办案人员普遍不予合作,以各种理由敷衍推诿,有的要求律师去向自己的当事人了解案情,拒绝履行介绍案情的法定义务。在律师对基本案情尚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又何谈向办案机关提出和交换辩护意见呢?二是,办案机关普遍不履行案件移送情况的告知义务。《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时,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通过调研发现,办案机关对案件进度及其移送情况普遍不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当事人丧失由律师提供辩护的机会。一项关于“办案机关对案件移送情况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明,有70%的律师表示“办案单位一般不告知,全靠自己打听”;有26%的律师表示“有的案件会告知,大多数案件只能自己打听”。在访谈中,各地律师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及此问题,这是一个律师界反映强烈并深感困惑的共性问题;三是,辩护律师表达意见的权利未受到重视。《刑事诉讼法》虽然要求公安、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认真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做到兼听则明,但无论是侦查期间还是审查起诉环节,抑或是审查批捕过程中,公安、检察人员一般都不会主动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即便在律师提出要求时,办案人员通常也不会当面听取意见,而是采取变通方式,要求律师提交书面意见来代替当面的口头陈述,直接言词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并未得到贯彻实施,辩护效果大打折扣。
(四)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问题依旧未改变
在课题组设计的一项关于“您认为新《刑事诉讼法》所赋予律师的辩护权利,哪些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的问卷调查中,相对于会见权与阅卷权,只有4%的律师选择了“调查取证权”选项。在与律师的座谈中,律师们普遍反映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调查取证难问题并未得到改变,律师仍然视调查取证为畏途,不愿、不敢调查取证。有部分律师结合自己的办案实践,表达了对调查取证可能导致的刑事风险的担忧:对证人调查后,一旦证人推翻原来对侦查机关所作的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言,侦查机关便会对证人采取高压“措施”或者以伪证罪相威胁,迫使证人推翻对律师作出的有利证词,证人为了自保,不惜将翻证归责于律师的“教唆、引诱”,这无疑增加了律师调查取证的风险。在办案中,对“需要获取的辩护证据”,接受问卷的律师中,有72%的律师选择“申请法院、检察院代为调取”,只有28%的律师表示采取“自行调取”的方式。如果申请职权机关代为调查取证,有83%的律师表示“更希望向法院提出申请”。对于侦查阶段是否进行调查取证的问题,有近一半的受访律师表示“从不调查取证”,还有10%的律师认为侦查阶段律师不应该享有调查取证权。
(五)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新《刑事诉讼法》在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虽然作出了法律规定,但这种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已经落空,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现状仍未得到改变。访谈中,律师普遍反映,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往往得不到支持。有60%的律师表示“大多数案件法院不同意证人出庭作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证人出庭作证率与以前相比并没有明显提高。证人尤其是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不仅剥夺了被告人的对质权,审判程序的正当性受到质疑,而且为查明案件事实带来困难,不利于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六)律师辩护权受到侵害后得不到检察机关的有效救济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对公检法办案人员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律师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但是,从调研情况看,该条规定形同虚设,检察机关并未切实履行提供权利救济和权利保护的职责。在一项关于“您认为新《刑事诉讼法》所赋予律师的辩护权利,哪些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的问卷调查中,所有填写问卷的律师没有一人选择“辩护权受阻碍时,获得检察机关权利救济”这一选项。只有6%的律师认为“检察机关能够较好地保障辩护人的诉讼权利”。究其原因:一方面,控辩双方诉讼立场对立,存在角色冲突,让律师的诉讼对手即检察院提供权利救济确实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另一方面,律师担心申诉、控告会得罪办案机关,害怕今后在执业过程中受到公权力的职业报复,这在一些经济不甚发达、律师人数相对较少的地方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即使律师权利受到侵害,他们也不愿意向检察院寻求救济,律师对检察官表现出一种明显不信任的态度。
二、律师辩护难问题何以持续发生?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辩护权保障方面所暴露出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
(一)被割裂的法律共同体:盟友与天敌
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与警察、检察官、法官一样,在防范冤假错案、实现公平正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防范冤假错案角度而言,推而广之,从确保所有刑事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合理性、裁判可接受性而言,辩护律师都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量。”从根本上讲,他们追求的诉讼目的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律师在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中是通过辩护职能的发挥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作为“盟友”的各共同体成员间理应友好相处、平等对待,那么为什么公检法人员会“高人一等”,并对律师这位“盟友”处处设防、倍加警惕甚至于作为“天敌”对待呢?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随着律师制度和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律师服务的市场化,律师身份由“国家法律工作者”转变成“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成了不吃“皇粮”吃“私粮”的社会服务人员。律师头顶上的“国家性”光环逐渐暗淡,“社会性”、“当事人性”愈加凸显,律师职业因“国家性”而衍生的崇高性、神圣性、公共性不复存在,律师也由“公检法司是一家”变成了“公检法是一家”,律师被视为唯利是图的商人;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基本原则中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应当互相配合”,律师被排除在“配合主体”之外,成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而受到共同体的排斥。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反思冤假错案时所指出的那样:“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无论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出现的律师辩护“三难”问题,还是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出现的排斥、限制、剥夺律师辩护权的新问题,无不与此相关。
(二)被神话的权利保护者:浪漫天使与魔鬼梦魇
新《刑事诉讼法》在制度设计上将检察机关塑造成为一个法律天使,赋予其提供法律救济的职责,将律师权利交给这位天使保管。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大概与理论上承认检察官具有客观义务以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有关。然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又扮演着指控犯罪的原告角色,且在目前的绩效考评机制下,与案件处理结果具有某种利害关系,其公正性、中立性又如何得以保证?“如果原告就是法官,那么只有上帝才能充当辩护人。”*[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立法上的天真烂漫并未带来令人欣喜的结果。在现实中,当浪漫天使不但不能提供权利救济反而一次次地制造出辩护梦魇的时候,法律神话被打破,天使也就变成了魔鬼。立法上指望检察官为律师被侵害的权利提供救济,确实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更多地带有一种虚伪性,律师们对此并未抱有多少不切实际的幻想,课题组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朱朝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求检察官有效打击犯罪,以维护社会秩序之同时,复要求其应当保障人权,首先就人性而言,宛如对以打猎为生之猎人,要求其于打猎之余,不得滥杀野生动物一般,不是不可能,而是实期检察官会有良好成效,通常会流于伪善的钓鱼式查证,当然检察官也无法如无辜被告所期待的,成为一位热切忠实的人权辩护者。”*朱朝亮:《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之定位》,载《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15期。“无救济即无权利”,赋予律师再多的权利,如果缺乏有效的救济管道和手段,所有这些权利都是一纸空文。诚如陈瑞华教授所言:“最为重要的,不是增加辩护权的外延和规模,而是解决已有权利的救济机制的问题,使这些权利能够真正落实;如果不建立基本的救济机制,即便再次增加辩护权利,那也只是增加了‘书本上’的权利而已,对于辩护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并无实质意义。”*陈瑞华:《增列权利还是加强救济?——简论刑事审判前程序中的辩护问题》,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因此,救济权具有保障其他权利实现的功能,是权利背后的权利,是一项保障性权利,必须认真对待。
(三)被扭曲的一套技术规则:明规则与潜规则
无论是检察机关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会见许可还是看守所在“三证”之外附加其他会见手续,也无论是检察机关将当面听取意见方式变通为要求律师提交书面材料还是看守所在法定的48小时即将届满时才安排会见,均反映出办案人员普遍存在着通过恶意释法规避规则约束的心理,很多办案单位将自己一贯奉行的“土政策”、部门红头文件凌驾于法律之上,将法律虚化甚至架空法律,导致法律规则在实践中变形走样,法条规定与实际执行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例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6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通知看守所或者执行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和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但是,检察院办理的几乎每一起案件,在侦查终结前都不存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这一情况,从而也不存在“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又如,该《规则》第46条第3款规定:“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从调研情况看,检察机关大多是在侦查终结时才允许律师会见一次,在律师会见后很快就将案件移送起诉。不仅在会见的时间节点上控制在最后时刻,而且在会见次数上限定为一次。律师会见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发表意见的权利被变相剥夺,办案人员也“巧妙”地规避了“应当听取意见”的法定义务。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辩护律师反响强烈的贿赂犯罪案件“会见难”问题便由此产生。辩护权与侦查权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办案机关如此解释和执行刑事诉讼规则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制、剥夺律师会见权来扩张侦查权,从而保证其在信息资源方面的优势和垄断地位。
(四)被驱使的一群权力野马:利益驱动与惩罚冲动
在利益驱使下,权力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横行无忌,这直接戕害了律师正当的执业权利。利益表现为现实的直接利益与预期的隐形利益。为了获得现实的直接利益,办案机关对律师复制案卷材料不惜采取高收费、滥收费的做法。虽然这种做法加重了律师及其当事人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办案机关的执法公信力,但是其对律师辩护权利的影响远远小于办案机关在预期的隐性利益驱使下所造成的损害。预期的隐性利益以未来的评先、评优、经济奖励乃至职务晋升等形式体现出来,各办案机关通过执行内部的绩效考核制度将这种隐性利益正当化,并实现可预期性。然而,现行的绩效考核机制普遍以惩罚犯罪为导向,并通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各种“打击率”指标进行考评。考核机制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对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较之现行的法律规定,其对实际的司法运作状况的影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参见龙宗智主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保障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6页。在这根“指挥棒”的挥舞下,为了完成“打击”指标,办案人员普遍具有一种功利性的惩罚冲动。在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看来,无论是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还是调查取证权、表达意见权,都是在为有效完成打击任务增加困难、设置障碍,不仅影响惩罚犯罪的效率,而且可能会造成“漏网之鱼”。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办案机关会以各种所谓的理由千方百计限制律师的会见权,为什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会面临如此大的法律安全风险,为什么办案人员不愿向律师透露、介绍案情甚至存在隐匿、伪造证据材料的情况?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公安、检察机关普遍不告知辩护律师案件移送情况,为什么会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申请予以拒绝,对律师的辩护意见置若罔闻?更不难理解为什么非法证据难以被排除,律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难以获得支持?
三、律师辩护难题如何破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在“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部分提出:“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完善执业保障机制。”这为完善我国辩护制度和辩护权保障机制提出了任务,指明了方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意义。针对调研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结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提出改进和加强律师辩护权保障的若干意见和建议,以期破解实践中的辩护之难题。
(一)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以法律职业的同质性表现出来的共同体即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主要是以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些典型的法律职业为核心构成的职业群体。在西方存在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范畴,律师、法官和检察官都是法律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渊源、共同的背景、共同的伦理、共同的价值观及共同的法律语言、共同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参见程滔:《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在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尤其是法律解释的共同体。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不仅缺乏共同的职业伦理和价值观,而且法律语言、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各异。假如法律职业者不能形成一个团结的、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思维框架的集团,则法律界内部的沟通和交流就会变得困难重重,司法过程的配合与制约势必变成不配合、难制约,共同体与外界的交涉能力势必弱小。*参见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中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律师和检察官、法官对法律规则的认识分歧有关,各自都选择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去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则,不仅造成共同体内部相互指责、互不信任,而且破坏了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为此,必须着重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首先,消除偏见,端正对律师职业的认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法治工作队伍”概念,明确指出律师队伍是我国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认识到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实现公平正义、建设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包括检察官、律师在内所有法律人的共同责任和使命。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念,与广大律师一起,在诉讼中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相互尊重对方权利,相互尊重对方的诉讼行为,共同维护法治尊严、维护人民权益,提高司法公信力”;*曹建明:《着力构建新型健康良性互动检律关系》,载《检察日报》2014年12月9日。其次,大力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职业转换和沟通交流。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上述改革举措对于打破职业界分、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增强彼此尊重和认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推动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步骤。下一步应在中央层面通过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实现招录选拔、双向交流的规范化、常态化。同时,要建立健全业务研讨、学术交流、定期座谈、交叉培训等长效机制,进一步拓宽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的交流渠道,为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沟通交流搭建多元化、常态化的有效对话平台。
(二)严格规范执法办案行为并为律师参与诉讼提供便利条件
一是,针对广大律师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难”问题,检察机关应进一步明确“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标准,对“涉嫌贿赂数额在50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中的“涉嫌”、“犯罪情节恶劣”作出明确界定,以统一执法标准,防止办案机关随意扩大适用范围,限制律师的会见权;二是,大力推进办案机关诉讼卷宗电子化建设。各办案单位应将纸质卷宗扫描后制成电子文档,允许律师在阅卷时拷贝电子文档,以此降低阅卷成本,提高阅卷效率;三是,保障辩护律师知情权的实现。知情权包括两个方面,即侦查阶段了解案情的权利和诉讼中知悉案件移送情况的权利。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了解案情的要求,除了规定侦查机关不得拒绝外,还应对了解案情的方式、“案情”范围等事项作出规定,在知情权与侦查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诉讼中律师知悉案件移送情况的权利,*遗憾的是,《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性文件仅规定: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而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则未规定相应的告知义务。建立在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具体讲就是要实现诉讼流程公开,案件何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何时退回补充侦查、何时起诉到法院,这些程序性信息如果能够及时上网并实现网上查询功能,那么律师后一项知情权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就目前的技术条件而言,大多数办案机关经过技术层面的努力是可以做到的。*在201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律师界代表座谈会上,曹建明检察长在讲话中提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进一步深化以案件信息公开为核心的检务公开,构建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法律文书公开、辩护与代理预约、重要案件信息公开等四大平台。”这说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四大平台的建设将会使律师的知情权得到较好保障,律师参与诉讼也会更加方便。为了更好地满足辩护律师的知情权,还应当要求各办案单位对于每个诉讼阶段的终结性法律文书应及时送达参与该诉讼的律师。为体现对律师的尊重和对其辩护意见的重视,增强办案机关的责任感,应当对现行的诉讼文书格式进行修改,除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外,公安机关制作的起诉意见书、检察机关制作的起诉书也应当对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予以记载并对辩护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评析论理;四是,规范办案单位的收费行为,明确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严禁各办案单位收取工本费以外的费用,切实制止纠正律师复印案件材料过程中存在的乱收费问题。
(三)建立侵犯律师辩护权利的程序性制裁规则
公检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律师辩护权利后,不用受到程序制裁,也不必面临不利的后果,相反还会从侵权中获益。如此一来,侵犯律师辩护权利之风会屡禁不止甚至愈加盛行,办案人员会更加有恃无恐。由此可见,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一套侵犯律师辩护权利的程序性制裁规则。一是,对违法限制、剥夺律师会见权的,规定在限制、剥夺律师会见权期间办案机关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移送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制作的依据;二是,对检察机关剥夺律师阅卷权,导致律师未能依法查阅、复制案件材料的,该证据材料如果不利于被追诉人,不得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反之,推定辩护律师依据该材料所主张的事实成立;三是,对办案机关未依法履行案件移送情况告知义务的,法律应规定该移送行为无效,移送后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四是,对于依法应当听取律师辩护意见而未予以听取的诉讼事项,应明确规定办案机关不得作出相应的诉讼决定;五是,对于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如果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通知的,应规定该证人的庭外证言不具有证据能力,检察官不得在法庭上出示、宣读。若该证人是在审前程序中未曾作证的新证人,那么可以借鉴德国法律规定,辩护律师有权直接通知该证人到庭作证,法院不得予以拒绝。*《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20条第1项规定:“审判长拒绝传唤某人的申请时,被告人可以对该人员直接传唤。即使无先行的申请,被告人也有权直接传唤。”
(四)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权利救济机制
中国刑事诉讼最大的问题是整个程序进行中缺乏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尤其是审前程序中侦辩关系、控辩关系完全是一种行政化的单向构造或者线型构造,在辩护权问题上一旦发生争议,便缺乏一个提供权利救济和权利保护来维持诉讼秩序的权威机构,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职权机关的自觉和自律,而事实证明这种自觉和自律是靠不住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出现的律师辩护“三难”问题即是明证。针对这种情况,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检察救济制度,希望以此改变过去职权机关侵犯律师辩护权后投诉无门的问题。但是,根据我们的实证调研情况看,效果并不明显,检察机关在权利救济和权利保障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作为。不仅如此,许多侵犯律师辩护权利的行为恰恰来自检察机关。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问题不可谓不够重视,不仅专门出台了有关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文件,而且还开展了限制律师权利问题的集中整治活动。*继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之后,2006年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工作的通知》,直到最近曹建明检察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律师界代表座谈会上提出,要针对限制律师权利等突出司法“顽疾”,开展集中整治,健全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执业权利的保障机制,切实解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三难”问题。但是律师对检察机关的抱怨声并没有减少,职务犯罪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变得更加困难,实践中检察机关限制律师辩护权利的问题时有发生。出现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理论上的“检察官客观义务”被事实上的“当事人化”所消解;二是“法律监督机关”职能定位所应具备的公正性和客观理性被追诉犯罪这一重要诉讼职能的偏私性和冲动性所冲淡。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检察权屡遭质疑的原因所在。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检察救济”模式之所以在实践中难以为受侵害的辩护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原因也在于此。我国的“检察救济”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制度特例,一种权宜之计,所能提供的权利保护十分有限,而真正有效的救济机制则在于建立由独立的、中立的法院提供的“司法救济”。*参见韩旭:《检察官客观义务:从理论预设走向制度实践》,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一改革任务的提出将对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也为建立司法救济机制提供了契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打破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平起平坐”的诉讼格局,凸显审判权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司法“线型构造”向“等腰三角形”诉讼构造的转型,发挥审判权对侦查权、检察权的权力制约和对辩护权的权利救济功能,使审判权能够走出审判程序,走向审前程序,对包括侵犯律师辩护权在内的程序事项进行干预和处理。“在法律帝国里,法院是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美]德沃金:《法律帝国》 ,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当然,要建立法院主导的权利救济模式尚需要一个较漫长的过程和持之不懈的努力。在司法救济机制建立之前,应尽可能克服“检察救济”模式的弊端,最大限度发挥检察机关权利救济的功能。是否能够提供权利救济是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的试金石,因此,越是加强权利救济,就越要强调检察官客观义务。同时,应保障救济权主体履行职务的独立性,防止受到内外干预和影响。
除上述举措外,还应当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公检法机关目前实行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都是以“打击率”为导向,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这也是律师辩护权保障不力的原因所在。为此,应当改革“重打击、轻保障”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各办案机关应当将对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情况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当中,增加其权重,并通过各项具体的细化指标予以落实。对阻碍律师行使辩护权的行为给予负面评价,并加大处罚和追责的力度。
[责任编辑:谭 静]
Subject: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Lawyers' Difficulty in Defens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Criminal Procedural Law——Analysis on S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uthor & unit:HAN Xu(Law Institute,Sichuan Ac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engdu Sichuan 610072,China)
It is found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five cities in S Province that the level of lawyers' defense right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and problems like "difficulty in meeting the suspects" and "difficulty in reading the files" have been basically solved.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lying in the course of exercising the right to defense, lawyers still face a series of challenges, among which, the following are most prominent: 1) the authorities restrict or deprive the lawyers' right to meet the suspects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2)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read files faces certain obstacles; 3) the right to know and the right to express defense views have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4)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y in investigation is still unchanged; 5) remedy and protection are not provided by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when the right to defense is infringed.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y in lawyers' defens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must be taken in respect to lawyers' defense: 1) to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professional community of law; 2) to strictly regulate the behaviors of law enforcement and case handling and facilitate the lawyers' participation in litigation; 3) to establish procedural rules to sanction infringement of lawyers' right to defense; 4) to establish the right remedy mechanism that is centered around trial; and 5)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ystem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dex.
implementation of New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lawyers' defense; protection of rights; empirical research
2015-02-1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辩护问题实证研究》(12BFX058)的阶段性成果。
韩旭(1968-) ,男,河南南阳人,法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诉讼法与司法制度。
D925.2
A
1009-8003(2015)03-013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