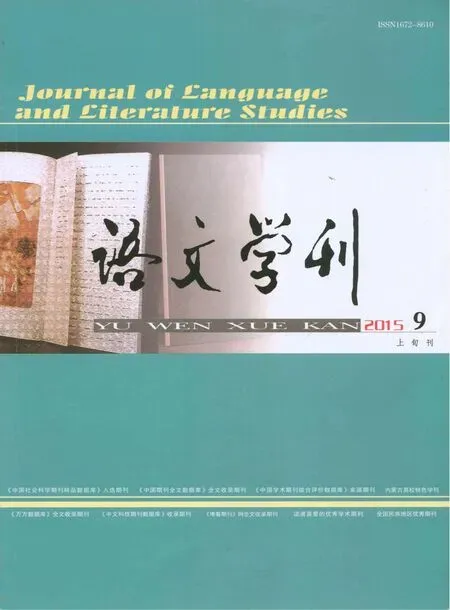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争鸣与思考
○ 魏行 袁芳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争鸣与思考
○ 魏行袁芳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摘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文章回顾了我国语言学界围绕任意性的争议,指出争议的根源在于对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误解——以语词与外在事物的指称关系取代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外在事物被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的原因:其一,语言符号的价值是由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不能以外在事物作为衡量的标尺;其二,语言符号是纯粹的心理实体,而外在事物属于客观存在,二者不具有同质性。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能指;所指
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这一概念时明确指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首要原则。在他看来,任意性原则是头等重要的,是整个语言系统建立的基础。然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在语言学界引发了很多争议。在我国,对任意性原则的质疑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任意性原则具有时代局限性,仅适用于语言的初创时期[1][2];二、任意性原则建立在印欧语的基础上,没有考虑到汉语的特点[2];三、语言符号的本质特征是象似性,主张用象似性取代任意性。[3][4]本文首先分析引发语言符号任意性争议的根源—以语词与外在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取代语言系统内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然后依据近年来索绪尔语言思想的研究成果[5][6][7][8][9][10][11][12][13],探讨索绪尔将外在事物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的原因,并简要论述这一做法对现代语言学所产生的影响。
一、语言符号的定义及其任意性原则
理清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定义,是正确理解任意性原则的前提。围绕任意性的争议多由对语言符号这一概念的误解所引起。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10]音响形象不是我们听到的具体声音,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或曰声音的心理表征)①。索绪尔特别强调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他举例说,我们不动嘴唇和舌头,就能自言自语;我们也可以在心里默念一首诗。这是因为语言中的词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音响形象。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是语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正如我们弹奏的乐器不属于音乐一样,声音本身并不属于语言。此外,书面文字也不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符号。我们听到的具体声音和看到的书面文字只是语言符号的实现形式(actualization)而已,它们本身并不等同于语言符号。在日常使用中,语言符号容易让人只想到音响形象而忘记了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概念。为了消除这一歧义,索绪尔引入了一套术语来表示这三个概念,用能指和所指分别指代音响形象和概念,用符号表示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的整体。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所包含的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语言符号是一种二元的心理实体。
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是任意性,主要是指构成符号的两大要素—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0]102要判定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还是必然的,只需判断语言符号的价值是外在赋予的还是内在固有的就可以了。若是外在赋予的,就是任意的关系,反之则是必然的关系。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自然联系的基础上,而是人为地赋予的,所以,这种关系是任意的(屠友祥 2013)。
二、对任意性原则的质疑
对索绪尔提出的任意性这一支配语言符号的首要原则,语言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在我国,对任意性原则的质疑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②:
首先,任意性原则有时代局限性;它仅适用于初民的语言,之后的语言就不再是任意的了。例如,许国璋先生指出“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有任意的,部落社会时期是约定俗成的,文明社会时期是立意的。如果说语言有任意性的话,那也只是限于原始时期,在此以后就不是任意的了。”[1]6-7胡壮麟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按照使用语言的形式,可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时期:即口述(orality)时期,读写(literacy)时期和超文本(hypertext)时期。人们对语言的定义在不同文明时期是不一样的。由于索绪尔的符号能指是音响形象,因此,“在讨论任意论时最理想的是拿这个理论来说明第一时期,即史前时期的口述语言”[2]97。此外,有学者认为语言符号一旦被社会群体公认和使用,就不再具有任意性了。持该观点的学者指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当然是就单个儿的符号最初产生的时候的情况来说的。如果一旦已经约定俗成,那就不是任意的了”[14]114;“这个被人……创始的符号,一经交换信息的社会群体公认 — 所谓‘约定俗成’— 和使用,它就不带有任意性。”[15]153
其次,语言符号是人类理性行为的结果,理据性是语言符号的根本特征,主张用理据性代替任意性。例如,许国璋先生指出,语言与事物的自然结合或自然联系可能性不大。“既然‘自然联系’不存在,当然只有‘人为的联系’,人为的联系即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是理性的联系,不是任意的联系。”[1]8胡壮麟先生指出,从逻辑上分析,符号不可能是自由决定的。“符号只有在使用者之间达成默契才具有符号的价值,也就是说,没有‘约定’,不成其为符号,‘约定’必然要求理性的选择。”[2]100此外,沈家煊先生也认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有理据的,主要体现在语言的结构上,如句法结构和人的经验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自然联系。[16]
再次,有学者指出能指与所指的主要关系是象似性,而不是任意性,主张用象似性取代任意性。持该观点的学者一方面从汉字的特点以及我国语言学研究传统出发,指出任意性适用于欧洲语言,对汉语而言,象似性更有说服力[2];另一方面,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指出在语言形式(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可论证的象似性关系,认为“象似性辩证说”优于“任意性支配说”[3][4]。
三、如何正确地理解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本节逐一评析针对任意性原则的质疑和批判,并进而探讨引发上述争议的根源。
(一)对任意性原则质疑的评析
首先,任意性原则是否具有时代局限性?该原则是否只适用于原始时期初民的语言?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其理由是初民之后的语言受到社会约定俗成的制约,披上了强制性的外衣。然而,约定俗成并非对任意性的否定。所谓约定俗成是指语言符号一旦被语言群体所公认,个人就不可能对它随意更改。然而,不能随意更改并不等于丧失了任意性。约定俗成之后的语言符号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任意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仍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二者的关系也还是人为地、外在地赋予的。[12][17]由此可见,语言的归约性并不构成任意性的对立面;相反,前者应视为后者的必然要求。正因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作为二者结合所产生的语言符号,势必要求同一语言群体内部成员普遍地接受;否则,不同成员间的语言交流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索绪尔有过精彩的论述:“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有别的规律;因为它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可能是任意的”。[10]111总之,约定俗称与任意性是相辅相成的,语言符号正是在任意性和约定俗称的双重作用下运作的。
其次,如何看待语言符号的理据性?理据性指的是能指与所指之所以能够结合构成符号是有理可据的,是可以论证的[2];而任意性旨在说明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不可论证的,即相对于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很明显,理据性与任意性是一对相反的概念。然而,对语言符号而言,理据性并不是对任意性的否定。相反,理据性应看做对任意性的约束。如果对任意性原则不加以限制,语言系统将会陷入混乱。但事实上,人的心智会设法给语言符号带来某种原则和秩序,这便是相对论证性的作用。[10]由于相对可论证性的存在,人类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这些语法规则对任意性施加限制,并把理据性引入语言系统。[13]索绪尔虽然强调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首要原则,但同时也注意到了语言符号的相对可论证性(即理据性)。他以复合词为例,说明了符号的相对可论证性。法语的vingt“二十”是不能论证的,而dix-neuf“十九”却是相对可论证的,因为它会使人想起它的构成要素(dix“十”, neuf“九”)以及跟它结构相似的数值(如dix-huit“十八”, vingt-neuf“二十九”等)。然而,尽管dix-neuf“十九”是相对可论证的,但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dix表示“十”neuf表示“九”,还是无法论证的,它们跟vingt“二十”一样,究其本质而言都是任意的。由此可见,语言的核心元素是任意的,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成分是相对有理据的。可以说,任意性是绝对的、根本的,理据性是相对的;相对的理据性不能推翻语言符号从根本上而言是任意的这一原则。总之,任意性与理据性相反相成,二者共存于语言系统之中。任意性使得人类的语言符号具有创造性,不必拘泥于能指与所指之间必须具有某种象似关系;而理据性使语言系统的运作有章可循,不会导致混乱。
再者,可否用文字(如汉字)的象似性取代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定义。有关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讨论应在索绪尔界定的语言符号体系内进行。根据本文第二节的论述,语言符号是由概念和音响形象联结而成的二元心理实体。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表现语言。“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10]47-48显而易见,文字并不属于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符号体系。此外,认为任意性原则只适合于史前时期的口述语言,不适用于读写时期和超文本时期,似乎有失偏颇。诚然,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符号指的是口说的词,不包括文字和图标。然而,文字和图标只是语言符号的实现形式,它们本身并不等同于语言符号。因此,不能以文字或图标特有的象似性否定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符号无论是采用口述语言,还是采用书面文字或超文本形式,充其量只是实现形式不同而已,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
退一步讲,即便是对于书面文字,象似性所能解释的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以汉字为例,象形字所占的比例比我们预期的低得多。据许国璋先生考证,即使在中国古代,一部收容量为9353字的《说文解字》所含的象形字也不过364字,占不到4%,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字的象形性是十分勉强的。[1]8总体而言,支配文字符号的也仍然是任意性。
总之,无论是归约性还是理据性或者象似性都不能构成对任意性原则的否定。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是任意的,这是制约语言符号的首要原则,也是准确把握语言符号乃至整个语言系统的出发点。
(二)引发争议的根源
根据上一节的分析不难看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之所以不断地受到置疑和非难,根源在于对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误解—以语词与外界事物之间的指称或对应关系取代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这两种关系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妨将前者称之为“指称观”,后者称为“任意观”。指称观本质上把语言系统当作一套分类命名集看待,认为语言符号与外界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照此逻辑,客观事物是第一位的、本原的,语言符号是第二位的、衍生的;语言符号的宗旨便是为外界事物提供相应的命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语言学家的首要任务便是寻找语词的理据、寻找语言符号与外界事物的联系。这种做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思想界都有着久远的传统。“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在讨论语言的‘任意性’的时候,中国过去的学问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就汉语的词与物之间的讨论还不时引起我们的遐思。”[1]9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统治语言学领域的主流观念便是“我们要理解语言,只能靠把我们使用的语词跟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无论语词代表的是我们内心的观念还是外界的客观事物)一一对应起来”。[5]220
然而,这一切在索绪尔看来是荒谬的。他认为语言符号所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不是外在事物的分类命名集或词与物的对应集,而是一套以任意性原则为基础的符号系统。对语言而言,并非客观世界事先提供了一系列物体或事件供人类去寻找相应的语词,而是人类为了满足交流思想之需而集体决定需要哪些言语上的区分。语言的系统性不能简单地从单个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中的物体或事件的对应关系来寻找解释;语言系统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该系统蕴含着语言符号的价值,而不是语言符号对外在事物的简单替代。[5]事实上,整个《普通语言学教程》都是在论证不要把语言混同于分类命名集。这种混同将语言符号与外在事物捆绑在了一起,成为理解语言系统性的最大障碍。
四、任意性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
依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一套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而任意性使得语言在全部符号体系中享有独特的地位。与其他符号不同,语言符号在选择它的能指方面是完全自由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妨碍我们把任何一个观念和任何一连串声音联结起来”[10]113。
作为一套符号系统,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autonomous)。所谓自治是指语言符号的意义和价值是由语言系统自身决定的,与外在事物无关。索绪尔曾拿经济学与语言学相比,阐明语言的自治性。两门学科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都涉及不同类事物之间的等价系统,只不过前者是劳动和工资,后者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然而,在经济学中,价值部分地建立在事物的自然关系基础上(例如一块地的价值和它的产量成正比),这种与事物的自然关系为价值提供了一个估算的基础,使得任何估价不可能是完全任意的。相反,在语言学中,由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二者的结合不是建立在自然联系的基础上,因此语言符号的价值不能以外在事物来衡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索绪尔主张将外在事物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
既然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并非以外在事物的自然联系为基础,语言符号的意义和价值不必也无需求助于外在事物。事实上,语言符号的价值来自于语言系统内部,由语言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各种关系所决定。在语言符号系统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各要素之间的差别;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概念差别构成的。[10]就语言符号的能指而言,音响形象在表达概念方面不存在谁比谁更合适的问题;关键在于使一个词区别于另一个词的声音上的差别,或者说,在于此音响形象不是彼音响形象这样的一种差异关系。同样,对于所指而言,起作用的是一个词与另一个词所表达的概念上的对立。单个语词不具有固定的意义,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与别的语词概念上的区别。道德性语词如“美德”与“邪恶”等其实自身并不具有道德性可言,现实世界中也不存在与上述语词对应的特定的道德现象。[11]这些道德性语词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能够表达其意义,完全是因为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关系。正是这种对立使它们获得了各自的价值。总之,语言符号的价值是由语言系统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不能以外在事物作为衡量语言符号价值的标尺。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排除外在事物的另一原因在于语言符号的两大构成要素—概念(所指)与音响形象(能指)—具有同质性,二者都属于纯粹的心理实体;而语言符号(确切地说,能指)与外界客观事物之间不具有同质性[12]:前者属于心理概念,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领域,后者属于客观实在,存在于外部世界。由于二者不具有同质性,我们难以对语言符号与外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做任何系统的研究。
综上,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使语言成为一个自治的系统;外在事物与语言符号不具有同质性,因而被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索绪尔将注意力集中于语言系统内部,集中于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关系,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使语言学从各种无关因素中剥离出来,从与外在事物的对应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7]
正如哥白尼指出了“地心说”的谬误从而为近代天文学铺平了道路一样,索绪尔揭去了笼罩在语言符号上方的词-物对应之假象,廓清了语言符号的本质,从而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研究。
任何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探讨必须首先明确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定义,并在其界定的范围内进行。作为二元的心理实体,语言符号所联结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二者的关系本质上是任意的。
无论是在语言符号的初创时期还是在今天,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都没有改变。语言符号不是对外在事物的命名,语言学也不是简单的分类命名集,语词与外在事物之间不存在指称或对应关系。以语词与外在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取代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违反了语言符号这一概念的初衷,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背道而驰。
【 注 释 】
①具体的声音是物理的,而音响形象是心理的,是听话人对具体的声音的心理印象。在索绪尔看来,人们发出的具体的声音属于个人行为,因人而异,不具有同质性(homogeneity),难以做系统的研究;而音响形象是听话人的心理表征,该表征为同一语言群体所共享,具有同质性,可以被语言学家研究。
②国内探讨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文献很多,本文只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不求面面俱到;涉及研究者的看法时,我们尽量引述作者的原话,力求客观。
【 参 考 文 献 】
[1]许国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之一[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3).
[2]胡壮麟.对语言象似性和任意性之争的反思[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3).
[3]王寅.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
[4]王寅.象似性辩证说优于任意性支配说[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5).
[5]Harris, R. & T. J. Taylor. 1997. Landmarks in Linguistic Thought: The Western Tradition from Socrates to Saussure[M].La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6]Joseph, J. E. 2006. The linguistic sign[C]//C. Sander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uss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9-75.
[7]马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哲学探索[J].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6).
[8]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M].于秀英,译.南京大学出社,2011.
[1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
[11]屠友祥.象棋之喻:语言符号的差异性与非历史性[J].文艺理论研究,2011(6).
[12]屠友祥.指称关系和任意关系、差异关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3).
[13]张绍杰.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4]胡明扬.语言和语言学[M].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
[15]陈原.社会语言学[M].商务印书馆,2000.
[16]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
[17]孙力平.应当如何理解语言符号的任意性[J].江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1).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5)09-0001-03
[作者简介]魏行,男,山东临沂人,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
袁芳,女,河北安平人,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句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