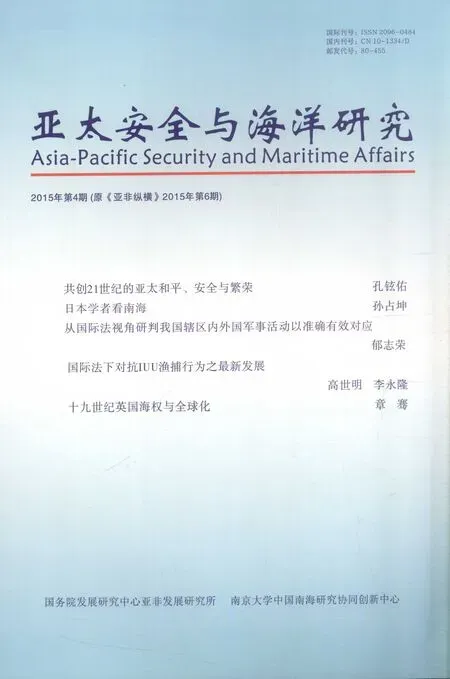外国学者对美国国务院九段线报告的评论*
外国学者对美国国务院九段线报告的评论*
苏拉·古普塔 莱昂纳多·伯纳德
*本文由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小奕博士翻译,由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法官校对。
[内容提要]2014年12月5日,美国国务院抛出了《海洋界限——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报告,公开了美国企图否认我南海九段线的官方立场,标志着美国正式在法律层面上介入南海争端。本文收集了美国和新加坡两位学者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九段线报告的“一正一反”两篇评论文章,现予以整理翻译,供有关学者及关心南海权益的人士参阅。
[关键词]南海 九段线 历史性权利 传统捕鱼权
一、苏拉·古普塔对美国国务院九段线立场之评析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引起了许多邻国和有关国家的担忧。中国对外宣称的立场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的主张)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这种措辞虽符合国际法,但却有失精准。近来中国提出对南沙群岛享有各种海域(full maritime zones)权利,但南海中各类构造的法律地位仍不明确,主张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相关海域”的界限也不清楚。
对于南海的权益主张国来说,这种做法可谓司空见惯。但与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不同的是,中国毫不犹豫地将其海洋权益主张推向极致,并予以施行,反对其他声索国在九段线内开展活动。中国这些执法行为似乎是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过度解释为基础的,只强调半闭海沿海国诸如捕鱼、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而不问其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中国有些权利主张甚至超出了《公约》的规定。由于中国政府从未颁布任何赋予九段线效力的法律或规章,中国学者到处搜集《公约》和习惯法中支持九段线的法理依据。围绕九段线的争论也日益加深(但平心而论,有些中国学者对九段线的论述是一贯的和准确的)。
2014年12月5日,美国国务院海洋、国际环境和科技事务司介入这一法理灰色区域,在其编制的《海洋界限》系列刊物中发表了对中国南海海洋权利主张的分析和评论。与早前在对台湾主张的报告中回避触及九段线的做法不同(台湾与中国大陆在九段线的立场上有重叠,但不完全相同),这份新的研究成果专门分析了九段线的合法性。过往的许多研究都试图论证:九段线即便合理,但也模糊不清,不足以作为在南海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基础;更有甚者,有的研究还得出九段线可能完全是非法的。美国国务院编制的报告综合采纳了这些思路,是一份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报告有些不得要领,当然也无法驳倒以下命题,即九段线最有力的法理依据:它是中国历史上形成和一直被承认的、在南海半闭海海域中行使的传统捕鱼权的地理界限。时至今日,该传统捕鱼权仍一如既往地在非专属和非排他的基础上行使。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对九段线做出三种解释:一是九段线代表线内岛屿、岛群的主权归属线;二是九段线代表国家海上边界线;三是九段线代表中国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线。报告对前两种情况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无懈可击,但对第三种情况的解释却令人生疑。
正如美国国务院报告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九段线在地图上有效地标明了中国主张主权的群岛范围。报告同时指出,对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主张必须源自陆地地物(land features),即高潮高地。至于哪些地物属于高潮地物,中国尚未明确。该报告还应进一步指出九段线最南端,即曾母暗沙南侧的一条线段的不合理性。曾母暗沙是水下地物,距离马来西亚海岸领海基点的最近距离只有60海里,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领土”,更不能被一个距离远超过200海里的国家据为领土。作为岛屿主权归属的地图示例,九段线最南端的这条线段应当划在曾母暗沙以北,而非以南。
美国国务院报告指出,九段线作为中国海洋边界外部界限的解释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这一结论无可厚非。在海洋划界案例中,作为一般原则,国际法庭通常不愿论及小型地物(small insular features)的准确地位,而是倾向于直接否定远离本国大陆而与相邻或相向国家的海岸投射(coastal projection)更为临近的岛屿(或岩礁)的海洋权利。正如南沙群岛的情形,不能使其他沿海国的海洋权利受到不公正的“切断”(cut-off)。按照《公约》的规定,海上边界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中国在南海所辖岛礁与邻国海岸之间的中间线。但是九段线不符合此要求,若作为国家边界,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尽管如此,九段线在中国国内地图中明确标识为“未定”国界,可以作为在国际上提出的临时界线。对于每个有领土争议的国家而言,包括南海的其他声索国,在谈判之前先在地图上单方面划定大大超过解决争端时的妥协方案的界限,这是各国的惯常做法。中国不必为这一做法而比其他声索国感到任何更多或更少的为难(no more or no less guilty),更何况中国已经明确地在地图上标注了九段线的临时性质(中国将九段线作为其海上执法界限,才是招致不满的根源)。在能够按照国际法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解决划界争端的情况下,如中国和越南在北部湾(Tonkin Gulf)划界的实践,或公平地分享潜在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如中国和日本在东海的渔业协定,仍然断言九段线是一条未定的、临时的、不能获得承认的单边国家海洋边界线(如美国国务院报告所言),这就言过其实了。
在九段线的第三种情况中,美国认为中国基于历史性权利在领海以外、但未超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海域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依据不足。这一观点是美国国务院报告中最可质疑的地方。美国国务院报告认为:中国接受《公约》中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效力,就等于放弃了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中的传统(或历史性)捕鱼权主张,即使半封闭海的情形也不能例外。此外,报告还援引1984年国际法院在缅因湾案(GulfofMaine)中的判决并断言,关于历史性使用(historic uses)的规定只存在于沿海国的领海之内。总而言之,《公约》创设专属性管辖权就意味着推翻了传统的权利。美国国务院报告的这一结论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在概念和法律逻辑上都存在缺陷。历史上形成并通过长期实践流传至今、在非专属或非排他基础上行使并得到半闭海区域内其他国家所接受的传统(捕鱼)权利,并不因《公约》而消亡,除非实体国际法(positive international law)明确撤销了这项权利。
在概念的层面上,美国国务院报告未能认识到半闭海中的捕鱼权和从事其他活动的权利可以以非专属的性质而行使。规范半闭海的《公约》第123条要求半闭海沿海国在养护、探勘和开发海洋生物资源时应开展合作。关于专属经济区的第62条同样也要求沿海国准许其他国家进入本国专属经济区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这两条通读的精神为在南海等半闭海中倾向于承认非专属和非排他性的传统捕鱼权指明了方向和依据。在缅因湾案之后的判例中,如扬马延岛(Jan Mayen)、厄立特里亚诉也门(Eritrea/Yemen)、卡塔尔诉巴林(Qatar/Bahrain)、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Barbados/Trinidad &Tobago)等案件都采用了这种观点,即认为长期存在的传统权利应受到国际法的尊重和保护。
美国国务院报告的另一个错误是,将传统或曰历史性权利与该权利的前身——“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制度(历史性水域通常由国家在海湾、海峡、河口和群岛水域中主张)混为一谈,从而将前项权利错误地限定在中国的内水。实际上,只要中国在非专属的基础上行使历史性权利,停止实施超出《公约》第123条授权的不合法活动,九段线作为中国在南海行使和实践传统或历史性捕鱼活动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界限,并不违反国际法。南海九段线距离其他沿海国的大陆和沿岸岛屿更近(24海里至75海里不等)的事实,并无碍于这一结论。例如,在东海,根据中日两国1997年缔结的《渔业协定》,由船旗国管辖的两国渔船在共同捕鱼区内允许抵达距离另一国海岸线52海里的海域作业。
当然,中国也有义务明确宣示九段线符合国际法的依据。不明确九段线的依据和范围,只是暗示历史性权利或历史性证据,如1998年《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以及2011年中国提交给联合国的照会,只会增加外界的疑虑,即中国企图借九段线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中非法划定大面积海域并开展威慑活动。
东盟的其他声索国可以通过优先推动《东盟—中国区域渔业协定》来测试中国的善意。这种协定类似于中国与其东北亚邻国,包括朝鲜所达成的双边协定。南海资源的共同开发遥遥无期,谈判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也遥不可及。相比之下,区域性的渔业协定却是指日可待的务实方案,它可以促成各声索国搁置管辖权争议的良性互动,并成为一条寻求解决南海更为棘手的其他挑战的可行途径。
二、莱昂纳多·伯纳德对苏拉·古普塔一文的评论
莱昂纳多·伯纳德对苏拉·古普塔《关于中国、美国国务院对南海九段线立场之评析》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一些质疑。他认为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未能分析到九段线存在着以下的可能性:“九段线是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且一直被承认的、在南海半闭海海域中行使的传统捕鱼权的地理界限;这一传统捕鱼权迄今仍在非专属和非排他的基础上行使。”以古普塔之见,这一论点是九段线最有力的法理依据。然而,古普塔忽略了相关的事实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中某些精巧的规定,因而得出了中国在九段线内拥有历史性捕鱼权的错误结论。
古普塔认为,国际法中的传统性/历史性捕鱼权有以下几个要件:一是历史上形成,通过长期使用(long-usage)的方式流传至今;二是在非专属或非排他的基础上行使;三是本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在实践中予以接受。然而本案中的事实和法律并不符合以上要素,因而古普塔的分析和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第一个因素,古普塔指出美国国务院报告将历史性/传统权利与“历史性水域”混为一谈,从而将前项权利错误地限定在中国的内水。实际上,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对历史性权利和历史性水域两个概念做出了区分;并解释道,与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水域是与内水地位相同的水域,具有领土主权)不同,历史性权利是指在海域中尚未形成主权、层级较低的一系列权利。在此基础上,该报告得出结论,中国尚未对九段线内水域明确地提出历史性水域或历史性权利的主张。鉴此,古普塔提出的中国可以继续在非专属的基础上行使捕鱼权的观点与本议题无关。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并未提出这类主张;其二,中国的行为表明,中国并不承认其他沿海国对九段线内拥有资源的权利。
即使中国对九段线内的历史性捕鱼权提出了主张,该主张也被《公约》中的专属经济区制度所取代。在专属经济区条款的谈判过程中,非沿海国提出的传统/历史性捕鱼权主张因与专属经济区制度冲突而未被采纳。根据《公约》规定,领海之外的捕鱼自由,包括历史性捕鱼权或公海捕鱼权,都被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所享有的主权权利所取代。
古普塔提到《公约》第62条要求沿海国准许其他国家进入本国专属经济区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但忽略了这种准入是由沿海国在决定了可捕量并考虑到沿海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而赋予的。第62条并没有规定沿海国应当承认他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传统捕鱼权。相反,它规定沿海国在准许其他国家进入其专属经济区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时,除其他因素外,还应当考虑到“尽量减轻其国民惯常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需要”。
关于第二个因素,古普塔认为如果把《公约》的第123条和第62条放在一起阅读理解,可以得出这两条的规定为在半闭海(如南海)中非专属地行使传统捕鱼权提供了依据。这种对条款的扩大解释是与《公约》精神不符的。原因有二:一是第123条并没有为沿海国创设专属经济区制度之外的新权利,也未允许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之外的半闭海中提出传统捕鱼权主张;二是第123条中规定的沿海国在行使权利时的合作义务也仅限于行使《公约》所规定的权利。
关于第三个因素,即便承认中国在南海一直在行使非专属性的传统捕鱼权,这项权利的确立还需要本地区的其他国家通过实践予以接受,而古普塔的说理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没有证据表明,南海的任何其他沿海国接受中国在九段线内水域拥有传统捕鱼权,无论这项权利是否具有非专属性。
有趣的是,古普塔在论述中引用了1997年的《中日渔业协定》,这一协定恰恰证明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是如何取代历史性捕鱼权的。《公约》缔结后,中国渔民在日本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不再享有合法的捕鱼权,尽管这项权利在历史上一直由中国渔民享有。1997年的《中日渔业协定》在两国主张的专属经济区的重叠区域设立了共同捕鱼区,准许中国渔民在日本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以传统捕鱼权为由继续捕鱼。这一《协定》的签订表明,单方面主张的历史性捕鱼权不能取代《公约》中专属经济区主张,除非相关国家同意并承认这一历史性权利。
除此之外,古普塔引用的所有案例也表明,这种传统捕鱼权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才能被接受。在扬马延岛案中,挪威和格陵兰都承认两国渔民在争议水域的传统捕鱼权。在厄立特里亚诉也门案中,也门也承认厄立特里亚渔民在其周边海域的传统捕鱼权。同理,正是由于缺少这种承认,国际法院拒绝了巴巴多斯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专属经济区中的历史性捕鱼权主张。
综上所述,美国国务院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即中国没有明确提出九段线内的历史性捕鱼权主张。即使中国提出了这一主张,也经不起国际法的检验。此外,南海的其他沿海国也并未接受中国的历史性捕鱼权主张,未来也不可能会接受。
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已经接受每个沿海国都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现状。而中国却又在南海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中继续主张历史性权利,这似乎是在有选择性地适用《公约》。如果允许一国以存在先于《公约》的权利主张为由随意减损《公约》的规定,那么《公约》的宗旨和目标以及整个专属经济区制度都会遭到破坏。因此,中国若想避免南海权利主张产生更多误解,则有必要澄清九段线地图的含义,并使其符合《公约》的规定。
三、苏拉·古普塔对莱昂纳多·伯纳德的回应
感谢莱昂纳多·伯纳德的热情评论。他的这一评论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所帮助,我在此表示感谢。下面我按照由主到次的顺序分别进行回应。
伯纳德评论中最核心的观点是:海域中的传统权利主张,如历史性捕鱼权,已经被《公约》中的专属经济区制度所取代;这类传统权利现由《公约》具体规范。这一论点是错误的。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厄立特里亚诉也门海洋划界案中,仲裁员一致裁定,即使当事方对各岛屿或陆地地物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一主权不仅无害于,反而在本质上巩固了该水域中的传统捕鱼权制度。这一制度不是随着《公约》创设的海域制度而产生的,而是在每个缔约国领海以外的水域中一直存在的。”实际上,从远古时代以来两国对这些水域的共同使用,“足以通过历史性巩固的过程为当事国创设某种‘历史性权利’”。
厄立特里亚诉也门案是关于红海当事国之间的历史性权利的案件。红海是拥有重要海上航线的半闭海,情况与南海类似。此外,扬马延岛案、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的判决也有相关论述。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其次,伯纳德批评我忽略了如下事实:即使中国在九段线内非专属地行使了传统捕鱼权,这项权利也只有在得到了区域内其他国家实际接受后才能成立。他认为这一条件并未得到满足。伯纳德先生的这一指责并不符合南海捕鱼活动的实际情况。除了原则上遵守领海界限以外,中国和其他南海沿海国的渔船自远古以来一直在这片水域捕鱼。中国在南海北半部实施的渔业和养护规范,尽管受到非议,但仍在实践中得到了遵守。当然,伯纳德先生正确地指出,其他沿海国并未正式接受(按照其利益也不应接受)九段线作为中国的历史性权利线,中国也确实尚未提出这一主张。但我认为,如果中国提出了这一主张,那么它在原则上是符合国际法的。
最后,伯纳德先生也正确地指出,美国国务院报告确已对“历史性权利”和“历史性水域”做出区分。但伯纳德先生和美国国务院报告未能指出或承认的是,历史性权利与历史性水域的主张是不同的。历史性权利一是可以存在于半闭海沿海国领海以外的水域(厄立特里亚诉也门案中的情形);二是可以在非专属的基础上行使(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伯纳德先生和美国国务院报告将传统捕鱼权仅仅限定在沿海国领海内的解释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十分错误的。
[修回日期:2015年11月03日]
[责任编辑:王婷婷]
[收稿日期:2015年09月20日]
[作者简介]苏拉·古普塔(Sourabh Gupta),美国塞缪尔国际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员;莱昂纳多·伯纳德(Leonardo Bernard),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