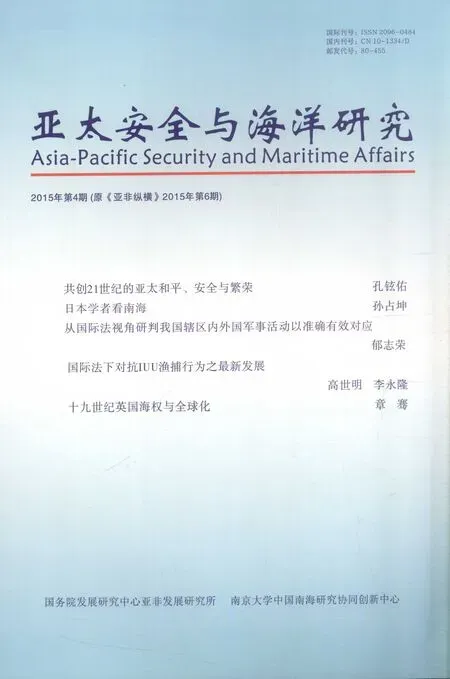十九世纪英国海权与全球化
十九世纪英国海权与全球化
章骞
[内容提要]十九世纪初开始,英国不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成为了一个当时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强大国家。当时的大海为英国所主宰,但是英国推行了一种以自由贸易政策为基础的新型海权,这种海权是和以往的零和博弈型的海权模式性格迥异,开启了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潮流。这个潮流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是也给世人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本文力求对这种新型的海权特征进行分析,并阐明这样的海权给全球化模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对于当时的这种全球化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目前的启迪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海权全球化英国海军自由贸易维多利亚时代
“全球化”这一个概念在当前正在被广为使用,澳大利亚学者沃特斯甚至说:“全球化……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M. Waters, Globalization,London: Routledge,1995, p1.那么什么是“全球化”呢?这样的社会到底会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所谓的“全球化”指的是由于世界观、产品、理念以及各种文化因素的交流之中,所导致的一种国际一体化的过程。*维基百科引自 Albrow, Martin and Elizabeth King (eds.).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London: Sage, 1990。随着交通、通讯等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原有的国家和地域的境界线愈发被跨越,各种扩大为地球规模的变化已经层出不穷。这个概念已经和原来依然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跨国行为的“国际化”相比,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
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大门被叩响,对于这样前景,有的人对此满怀期望,而有的则充满悲观。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英国的海权形成一支君临全球的力量之时,这样的时代也曾经到来过,但是这段繁荣发展的时期维持了大约一个世纪,随后步入的却是充满战火的二十世纪。当我们回顾这一段时代的成败得失,也许会对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机遇和挑战作出更好的对应。
一、日不落帝国时代的英国海权
在十九世纪初期,当英国战胜法国,其力量发展到顶峰时期的时候,这种“全球化”的局面也曾经一度来临。当时,英国不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成为了一个当时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强大国家。其殖民地遍及全球,形成了一个号称“日不落”的大帝国。而世界上的海洋则化作了英国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通衢大道,强大的英国海军,自然也成为了这些交通线的安全保障。根据最为乐观的估算,到1815年为止,英国海军中战列舰便拥有218艘,巡航舰为309艘,巡逻炮舰(Sloop-of-War)以下的小型舰艇则有261艘之多。*L.Sondhaus, Naval Warfare, 1815-1914, London: Routledge, 2001, p.2.
在此时,法国、西班牙以及荷兰等曾经参与争夺海权的各国,不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海军实力方面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而望尘莫及,无论是国际政治也好,国际经济也好,都明显地以英国压倒性的优势为前提进行运转,这个以英国强有力的主导力而维持的和平时期,被称作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inica)”时代。这一时期从十九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初叶为止,大约延续了一个世纪,堪称是不列颠的世纪。这个世纪中给人们带来双重的印象:首先是在皇家海军有效而稳固地监管下,世界上处于长期的和平稳定;同时,其他诸国,也都不同程度地依赖这个无比强大的国家。依靠遍及四海的海上贸易,全球经济开始呈现出一体的迹象,露出了全球化的端倪。
而这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却是一个与过去的主宰者相比完全不同的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帝国所控制大海的方式也和以往以攫取土地,进而获取资源为目的的所谓“欧洲大陆型国家”海洋控制方式完全不相同。
这种不同之处,英国拥有的这种海上主宰权具有更为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甚至于一旦这种主导权由于种种原因衰退之后,依然能够使得自己在稳定中得到顺利转型,不至于在剧变的波涛中颠覆。
英国的这种依托海上贸易,通过海上力量而形成的国家发展模式曾经为一位美国海军军官与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所倾倒。他将其当作了国家发展的理想状态,并创作了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通常又被简称为《海权论》一书。于是,“海权”一词开始被世人所广泛认识。而什么是海权,人们却往往认识比较模糊。
“海权(Sea Power)”这一术语,有时也被翻译为“海上力量”。但是马汉在其论著里,往往都只是使用历史案例进行说明,却避免给予明确的定义。在其说明的过程中,“海权”这个词汇往往被他赋予两种主要的含义,前一种仿佛表示通过海军的优势控制海洋,而后一种则当为拓展海上商贸、攫取海外领地、获得外国市场特权而造就国家富裕和强盛的合力。在其代表作中,前一种含义可以被形容为“拥有占压倒性的海上力量,才能将敌人的旗帜逐出海洋,或者只允许他们象海上的丧家犬一样出现。”*马汉著,冬初阳译:《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而后者则简单明快地表达为“扩大生产、海运、殖民地——一言以蔽之,就是扩大海权。”*马汉著,冬初阳译:《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马汉在他的著作中,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海洋这个世界共有的通衢大道之支配,是如何对其兴衰具有密切的关系,用充分的史料进行了阐述,同时还系统化地分析出了其中的成败得失。他特别强调的是,在他的时代中称雄世界七大洋,具有空前繁荣的经济实力和空前强盛的军事力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是如何把握海权,从一个自然资源并不充分的岛国成为世界帝国的过程进行了近乎理想化的解析。这一切,事实上给了当时的一些新兴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并指出了一条发展的途径。
这条途径就是,将国内的生产、海外贸易以及殖民地作为基础,而若要使之得到最大限度的畅通,则必须发展海上力量,保障海上安全。
由此也可以看出,马汉所指的海权是带有军事和经济双重意义的,而事实上,在近代以后,一个国家若要通过海上通道维护与他国的贸易,也必须有维护这个海上通道得以自由使用的秩序之能力,而这个能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还离不开国际政治范畴内的外交和经济协作,乃至可以使用的一切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海权”又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术语。
英国富有盛誉的海军历史学家,海军上将里奇蒙爵士(Sir Herbert William Richmond)曾经对于海权尝试进行剖析,他当时的叙述堪称是海权的一个工作定义:
“海权乃是一种国家力量之形式,此般力量可使其所有者令其军队以及商业穿过那些位于本国或者盟国之领土以及那些在战时需要达到的领土之间那广袤的海洋之同时,亦能令其所有者阻止其敌方达到同等目的。”*P.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Lane, 1976, p.2.
世界海权的格局随着国际舞台的变化而时常改变其特性,不过,比较重视海上对抗的时期,海权和制海权的概念常常会混同,到了后冷战时代,由于企图打破海上秩序之力量的消亡,海权已经比以往更多地从排他式的争夺,向着带有竞争和合作共存的崭新格局演化。国内有学者对于这种新时代的海权下了这样的定义:
“后冷战时代的海权,是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军事信息化的时代,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科技、文化等多种途径和手段对海洋进行控制、利用、管理和开发的一种综合能力。”*杨震、周云亨:《论新军事变革与后冷战时代的海权》,《太平洋学报》,2012 年第7 期,第62页。
当然,海权如果脱离了陆地是没有意义的。英国海上战略泰斗朱利安·科贝特爵士(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反对将海军战略看作一个独立实体,而指出必须将其作为整个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来看待,因为他认为人毕竟是居住在陆地而不是海上的。海权重要的不是海上发生了什么,而是海上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影响陆上事件的结局,所以他告诫道:
“近年来,全世界对海权的功效受到了如此深刻的冲击,以至于我们会倾向于遗忘掉海权本身在解决大陆强国的战争中是多么无能为力,实施海上行动又是多么耗时巨大,除非它能够与军事和外交压力良好地进行协同。”*G.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nd Ed.,Abingdon: Routledge, 2009,p.58.
正是由于海权这个术语过于广义,即便有一支不大的海上力量也照样拥有其相应的海权。所以,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Michael Kennedy)还使用了“海上主宰(Naval Mastery)”这一术语来对制海权,尤其是全球意义的制海权进行了界定:
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业已充分发展,雄踞于任何对手之上,而且那种主宰权已经或者能够远远超出其本土水域得以行使,其结果便是,若无这个国家最起码的默许,其他那些较小的国家便极难从事海上行动或者贸易。*P.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Lane, 1976, p.9.
本文所叙述的十九世纪英国,便拥有了这种空前的海上主宰力,在这种海上主宰之下,英国形成了它那具有强烈特性的海权。
二、19世纪发自英国的全球化浪潮
英国在当时毫无疑问可谓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不管在商业、运输、保险以及金融领域的优势不但极为明显,而且其发展还方兴未艾。构成这个“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之时代基础,便是英国依托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产业革命,在这场产业革命中,其生产力得到了飞跃般的发展,从而由原先“商店店主的国度”转变成为了担任起“世界工场”,进而又成为“世界的银行”之角色。
在1860年前后,联合王国达到了其极盛时期,它生产了全世界铁的53%、煤和褐煤的50%,并且消费了全球原棉产量的几乎一半。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却几乎相当于世界的40%到50%,欧洲的55%到60%;在1860年,它的煤、褐煤与石油等现代能源消费量是美国或普鲁士/德意志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它单独占有全世界商业份额的1/5,占有制成品贸易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扬着大不列颠的旗帜,而且所占的比率正在日益增加。当时的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曾在1865年的《煤炭问题》上绘声绘色地刻画出了当时大英帝国的盛况: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P.M.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 Unwin Human, 1988,p.151-152.
正是由于拥有这样发达的工业实力,英国的产品广销全球,与此同时,为了开拓新的市场、开发新的资源,以伦敦为中心的金融界也广泛展开了投资以及融资业务。英国在1847年通过海外投资便获得了1050万英镑的金利,而到了1887年更是攀升至8000万英镑。在1875年,英国进行的海外投资总额高达10亿英镑之多。*P.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Lane, 1976, p.151.由于外国通过伦敦的金融市场得到的资金,从英国的角度看也就是向海外进行的投资中,大多数都是用于购买英国生产的工业制品,这样从世界各地黄金大量流入伦敦,于是,英镑也成为了世界上最有信用的货币而君临全球。此外,英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支配着全球的商品流通,故而保险行业也聚集在伦敦,可谓是只要一个环节占据了先机,而其他相关环节也相应地获得了同样的益处,就是在这个复杂的关系构成之下,英国经济在全世界取得了不可动摇的优势。
在这种优势之下,一股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开始冲击整个世界。从世界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根源是来自大航海时代。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兴起,欧洲各国开始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正是海洋不再成为天堑而化作人类共有的通衢之路,人类的交往开始呈现出亘古未有的活跃场面。只有拥有了海洋这一载体之后,全球化才成为可能。通过全球航线的拓展以及殖民地的建立,欧洲的政治以及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开始萌生、物资流通的“全球化”航路也开始不断拓展。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萌芽。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世界海洋形成了英国的主宰,同时英国又开启了自由贸易的大门,随着近代化国民国家的形成,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全球化浪潮终于形成了。
英国之所以能够引领这一浪潮,从英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相对而言可谓是英国政策的核心所在。英国王室缺乏哈布斯堡或者波旁王朝般的神圣地位,其传统的贵族力量也在玫瑰战争等内乱中耗尽,新生贵族力量主要依靠商业阶层而不是军事集团组成。这与欧洲大陆列强往往不将经济问题放在外交政策中形成了对比。其原因离不开英国地理的优势,因为英吉利海峡给英国提供了天然屏障,英国可以置身于欧洲大陆列强争斗之外。
而欧洲大陆国家则通常被贪婪而强大的对手所包围,随时被迫与对手形成战还是和的关系,因此欧洲大陆国家不得不从军事角度优先考虑外交政策。而置身于大陆之外的英国则可以在悠然地看着“瓶中蝎子互相厮斗”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营造海上力量,只要用足够的海军将蝎子瓶口堵上,不让蝎子们爬出,同时,还保持一定的干预大陆能力,确保不让某个强壮的蝎子吞噬其他蝎子,并打破瓶盖而出,便能确保国家安泰无虞。*W. 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英国最为担心的,便是大陆国家有朝一日形成一支能够侵略英国,或者破坏英国海上经济体系的海上力量。
这也是英国能够奉行与其他欧洲列强不同的战略,可以通过建立全球贸易体系来促进自己的繁荣和发展的原因所在。英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得以成为了可以影响欧洲列强态度,改变欧洲大陆力量平衡的巨大砝码。然而真正对英国的海上主宰权乃至整个世界秩序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商业交换体系,也就是自由贸易政策的采用。
在十九世纪以前,各国一般采用的是通过官方特许垄断以及国家权力强行介入的所谓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强调积累金银货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这些国家的财富基本上都集中到了君王手中,他们经常操纵这个经济制度,使得经济为军事利益服务。这样的经济关系成了执行和加强王朝权力的工具,依靠这个经济体系,这些王朝得以建立强有力的军事机器。*弗里登著,杨宇光译:《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同时,重商主义者还认为国家间关系属于“零和”博弈。即财富是一定的,己方得到相对更多的财富必须建立在与其他国家相应等额损失的基础上,他们强调通过垄断和国家权力来增加财富。所以一个国家要改变或提交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必须掠夺别国的财富。强调政治决定经济也成了该学派的基本特征。
英国自身最早也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并通过这个方法迅速使得本国的工业以及海运业得到了保护,从而得到了培育和成长。然而,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之后,原有重商主义思想下实施的关税保护政策,反而成为了英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一方面,这阻碍了英国以廉价的工业品打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一旦采用关税保护政策,其他欧洲国家也必然会提高关税来针锋相对,这自然不便于英国产品的顺利流通。在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便开始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于限制进口、奖励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进行了逐条批判分析,并指出,给予经济活动包括对外贸易以充分的自由,是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条件。*张云宜:《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自由贸易运动》,《史学月刊》1984年第四期,第87页。
在这种形势下,自十九世纪初叶起, 英国逐渐开始放开工业保护制度,允许工商业自由发展,实行低关税乃至零关税的自由贸易政策。1838年,英国曼彻斯特实业家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布赖特(John Bright)组成“反谷物法联盟”,寻求撤销维持谷物的价格而致使劳动力成本高涨的《谷物法》。经过长年的争取,在1846年,英国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2nd Baronet)的内阁终于宣布废除了《谷物法》。这可以说是英国开始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一个标志。三年后,贸易保护的另一个重要象征《航海条约》也被废除,这样航海贸易的枷锁被打破。除了废除了这些法令,英国对于殖民地也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态度。这样,在1840年代末和1850年代初英国基本完成了这个贸易政策的转变,成为一个执行自由贸易并逐渐将其向全世界推广的国家。在这场转变之下,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这个曾经被《泰晤士报》评论为“在人类历史上它完成了任何一个公司从未肩负过,和在今后的历史中可能也不会肩负的任务。”*The Times 1874.1.2.这样的垄断性特权公司便首先于1854年被解除行政权力,最终于1874年6月1日被解散。整个印度以英属印度帝国的形式成为了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
自由贸易政策不仅仅使得英国的经济发生了飞速的发展,而且科布登以及布赖特等自由贸易信奉者还宣称,自由贸易还具有化解国际矛盾、确保国际善意、防止发生战争的功效。在这种浪潮面前,包括重商主义最为极端的信奉者法国也开始向科布登的学说转变,世界贸易仅1850年就增长了80%,虽然最大的赢家自然是英国,但是让以往的重商主义者们不解的是,其他国家、公司以及个人都成了这种自由贸易秩序下的获益者。*P.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Lane, 1976, p.152.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不列颠主导下的海权释放出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异彩。
三、英国的海权与全球化
马汉将海权的基本特征总结为“贸易、殖民地和海军”。由于贸易这一角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之后,那么其他两个角自然而然地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在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的贸易主要是由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进行的,而海军的任务则主要是对这些贸易航线进行直接的保护。然而一旦展开了自由贸易之后,“整个世界都展现在你的面前”。贸易的对象不再是仅限于殖民地,反倒是与外国所展开的在形式上的对等贸易成了主流。这样,殖民地的重要性相对而言有所下降。1812年到1914年之间有差不多七成的移民,1800年到1900年有六成以上的出口,八成以上的进口是来自殖民地以外的区域之间的。*P.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Lane, 1976, p.154.按照英国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的话说,对于殖民地进行管理和防卫的费用完全是套在英国纳税人脖子上的重负。
于是,这一阶段英国对于殖民地的发展战略不再着力于对大片区域的占领,而是精心挑选具有优越地理位置,在国际海上交通线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地。由于英国维持了连接世界几乎所有区域的贸易,因此,从英国伸向全世界的航线连接着英国本土以及殖民地的港口,都成为了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而这些战略要地,自然也成了这些生命线的“枢纽”。
除了控制海上贸易线的“枢纽”,这些基地还具有别的重要意义。当时英国海军已经基本完成了风帆时代向蒸汽时代的过渡,不过与风帆船舰相比,蒸汽船舰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燃料的消耗,若无煤炭就无法航行,这个问题在风帆时代是不存在的。进入蒸汽时代之后,煤炭在某种意义下,也就成了制约舰船行动的一副枷锁。因此,英国海军为了能够在世界的海洋上行动,便必须在世界各地布置相当一些拥有贮煤站的港口作为行动据点。因而连接大英帝国海上生命线的那些港口中都设有贮煤站,以作为蒸汽舰船行动的据点。而这其中的若干重要的据点内,则派遣军舰长期驻守,并设有船坞等修造设施。
在当时,还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如同英国那样密集的贮煤站网络,因此一旦爆发战事,与英国为敌的那一方便自然失去了赖以支持长期航海的煤炭补给,而被作为英国海军基地的港湾所包围,不但其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还在战略上陷入致命的被动态势。
英国海军当时在选择那些设有贮煤站的主要港湾之时,这些港湾周围资源或者产业如何并不是最优先的考虑因素,港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才是建港最大的目的。因此,从十九世纪以后而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区域中,为了建设贮煤港的获取的便占了比较多的比例。
为了保护这些分布于全世界的贮煤港以及舰船维修设施,其周围开始建造要塞炮台,屯驻陆军,一旦出现战事,就依靠这些力量坚守,直到周围基地甚至本土的援兵到达。这些要塞炮台以及舰船维修设施还不断地进行扩充改善,随着技术的进步,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其中大多数也发展成为了英国皇家海军外遣舰队的常驻基地。
为了更快地进行通信联络,英国在1843年起就开始进行试验,成功地建成了一条跨越泰晤士河的通讯电缆。而后这样的电缆首先越过英吉利海峡,而后又跨过大西洋,进而开始连接遍布世界的基地。到1880年,世界海底电缆的总长约156105公里,将英国和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非洲连接了起来。从孟买到伦敦的消息可以以每个词4先令的成本隔日到达。电报被称为了“世界的电力神经系统”。*N. 弗格森著,雨珂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年版,第147-148页。然而,在十九世纪,由于海底电缆价格昂贵,敷设困难,加上英国控制了用于海底电缆绝缘层的古塔波胶生产行业,因此海底电缆的主导权都掌握在英国的手中。在1896年,全世界拥有的30艘海底电缆敷设船中,有24艘是属于英国的。1892年英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海底电缆的三分之二,而即便到了1923年,英国依然占据着42.7%。*D.R. Headrick & P.Griset, Submarine telegraph cables: business and politics, 1838-1939,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5(3), pp.543-578.在这样技术力量的支持下,英国还能够窃听他国的重要电报,或者故意迟滞电报的发送,在外交上也横加利用这种新技术。
随着海底电缆网络的完成,英国以及广大的海外基地真正地连成一个有机体,这样,世界上不管什么角落一旦出现纷乱,只要与英国的利益相关,英国军舰便能迅速到达。
除了英国早期以及拿破仑战争胜利后获得的马耳他、爱奥尼亚群岛、直布罗陀、冈比亚、开普敦、毛里求斯、锡兰、巴哈马以及圣卢西亚等地之外,英国又占领了新加坡,从西面控制了进入中国南海的门户;攫取福克兰群岛以俯瞰通往合恩角的航路;夺得亚丁以扼守红海的南大门。此后英国还先后将香港、拉各斯、斐济、塞浦路斯、亚历山大港、蒙巴萨、桑给巴尔等基地收入囊中。
英国对于这些“枢纽”的占领,或者是在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地区建立英国控制的商业中心,或者是抢占交通要点,而且也可以将占领的附加费用和领土防守的保护责任降到最低点。这些基地的获取和更具有“大陆”风格的欧洲君主国领土扩张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殖民地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随着而发生变化的,便是英国皇家海军战略和使命。皇家海军开始从本土附近逐渐向全球展开,其任务也成了保卫那些使得自由贸易成为可能的和平,以及维护那种对于英国而言所希望的特定秩序。于是平时军舰的部署以及行动也成了外交活动的重要环节,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诸如展示国旗、在必要之时甚至驱使武力来推进外交谈判。“炮舰外交”这样的词汇也应运而生,海军行使炮舰外交的职能,也便成了英国在十九世纪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英国海军更多执行的,套用一个较时髦的概念,那便是一种“非战争军事行动(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1815年以后,英国事实上成了一个在海上占有绝对主导权的国家,然而当时英国的国防开支仅仅是国家收入的2%到3%之间,分摊到每个英国国民头上甚至不足一个英镑。*P.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 Lane, 1976, p.150.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当时法国新败,西班牙和荷兰的海军也早已一蹶不振,英国海军具有无可辩驳的优势有关。同时,从客观上而言,由于英国不失时机地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方针,正如科布登所宣称的那样,自由贸易是人类普遍愿望和理想的和谐化,是避免发生战争的良方。因此,英国海军尽管拥有遍布全球的海洋优势,但是其潜在对手还是认为自己受益于这个新的国际秩序,并没有真正花费精力和时间对英国的海上地位进行挑战。
伴随着自由贸易的转型,英国还广泛接受了为国际法与海洋法的鼻祖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所提出并力主的“公海自由(Mare Liberum)”这个口号,以便于对世界的海洋最大限度地广泛加以利用,这也构成了保障英国商船之自由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在这个时代中,沿岸国家对于自己主权的行使,英国则最大限度地加以限制。比如,领海三海里这一惯例,是由于过去的大炮射程大约在三海里而来。而当时尽管火炮的射程由于技术的进步已经大大增加,但是英国还是坚持领海仅有三海里这一原则。这样,“公海自由”尽管堪称为掌控大海的英国之自由,但客观上也给了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为了进一步鼓励所有人利用海洋,英国海军还承担了绘制海图的任务,这是一项艰巨无比的工作,通过一支又一支测量船队在全世界未知的海域测量海岸线和探测水深,费尽千辛万苦,历时十余年,绘制出的高质量航海图,最后却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向全世界的海员销售,彻底改变了原先对于测绘严格保密的自私政策,尽力扩大贸易量并有助于减低航海事故。*P.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Lane, 1976, p.158.
此外,对于自由贸易而言,公海海路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以英国海军为中心,在地中海广泛进行了扫荡海盗的行动,而后,这样一种大规模消灭海盗的活动逐渐扩展到全世界范围,曾经猖獗了几个世纪的海盗行为由此急速地减少,这对于营造一个安全的航海环境,促进全球范围的贸易活动,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1856年颁布的《巴黎宣言》之中,又将欧洲各国自古以来的一种传统作战手段,也就是由公权特许授予的私掠行为予以了废止。这样事实上等同于海盗行为的私掠船也失去了合法地位。
十九世纪中,英国海军另一项重要活动便是彻底地取缔奴隶贸易。早在1807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便通过了禁止在非洲或从非洲到任何其他地方的运输过程中,以任何方式买卖奴隶的法案,并腾出作战用的军舰前往西非查禁贩奴船只,甚至袭取自己盟国葡萄牙的贩奴港拉各斯等作为禁奴行动的巡逻基地。而后又宣布了奴隶贸易是等同于海盗的行为,并于1833年正式立法在所有英属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度。仅仅1840年一年,就至少有425艘贩奴船在西非海岸遭到英国海军的拦截,并被押往塞拉利昂,将这些奴隶贩子悉数进行严惩。*N. 弗格森著,雨珂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从1807年开始的大约50年期间,英国海军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几乎不间断的行动以取缔奴隶贸易,在其过程中,甚至不顾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抗议而强行地加以实施。
为了打击海盗和取缔奴隶贸易,英国海军在全球各个海域展开行动,对于世界各国而言,由此获得了一个更为良性的海上贸易环境,对于推动全球贸易的顺利进行有着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当然,与此同时也会在有形或无形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使得伦敦的意志迅速地在皇家海军的行动中得以体现。比如,英国仅仅派遣了一艘炮舰,便使得奴隶贸易的大国巴西在1850年9月效仿英国也通过了自己的废奴法案。如此,皇家海军扮演起了“世界警察”的角色,时而还强行迫使对手交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据点,展开炮舰外交,在扩大国际贸易的同时,使得英国获得了巨额的利益。
当时英国政策的核心,便是扩大世界市场、确保原材料资源、开拓海外投资地区。因此对于其他欧洲各国,英国设法保持其均衡;而对于一些被其他列强压迫的民族,英国则鼓动甚至支持其独立;而在亚洲和非洲,英国则夺取殖民地作为其开拓市场的据点。这一政策从1820年代开始展露,在1830年代,辉格党的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担任外相和首相,雄踞英国政坛核心的三十年期间,这一政策的实施成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而支持这一政策的,自然就是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往英国舰艇主要集中于本土、地中海以及波罗的海水域,而拿破仑战争以后,外遣舰艇也逐步增加,英国海军的外遣舰在1792年为54艘,1817年为63艘,而到了1836年骤然增至104艘,1848年则达到了129艘。1848年时英国海军的配置大约如下:
本土水域35艘,地中海水域31艘,西非海域27艘,西印度群岛海域10艘,南美海域14艘,太平洋海域12艘,开普敦水域10艘,东印度、中国海域25艘。*P.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 Lane, 1976, pp.170-171.
如此大量的外遣舰艇,自然导致了海军力量的膨胀,现役官兵人数到1847年也达到了45000人,这大约是皇家海军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1817到1820年最低谷时期官兵人数的两倍。同时,海军的预算也超过了800万英镑,又回到了拿破仑战争时的水平。*P.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Lane, 1976, p.172.到了1850年代,英国海军在世界各个海域都保持了优势,在任何地区都能为强制推行的英国政策提供坚强的实力后盾,这也可称为“不列颠治下和平”的巅顶时期。
虽然自由贸易并未象科布登所宣称的那样给英国和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但确实也可谓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英国力图将本国卓有成效的法治体系推广到全世界,在某种程度下打破了权力政治与重商主义的“丛林法规”,给英国和整个世界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并带来了几乎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在“不列颠治下和平”下的国际秩序中,英国主导的新海权是一种以贸易目的而不是军事目的为主导的。对于英国而言,维护这个基于自由贸易的秩序才是能够带来国益的关键。正是由于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尽管份额有多寡,但是具有共赢的特性,因此出现的对手只要是同样倡导自由贸易的,只要也是以贸易目的而非军事目的为主导的,英国可能根据当时形势与损益而进行妥协甚至退让。然而,一旦这种秩序本身受到了挑战,那么英国将会以炽烈的造舰竞赛来加以对应,以守住这个海上贸易的础石。
以当年的标准来看,十九世纪英国主宰下的海上秩序在许多方面已经具有了一些当今所谓的“全球化”色彩了。*引自G.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nd Ed., Abingdon: Routledge, 2009, p.4。这种秩序在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以及相对而言的和平之同时,事实上还是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以及潜藏着诸多的危机。比如,由于当年英国主宰下的国际秩序有赖于畅通无阻的海洋航运,正如马汉在1902年出版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作了如下的预言:
“随着交通速度的大幅提高,国家之间的利益紧紧交织在一起,直至形成了与往昔相比庞大得多的体系,它相当活跃却又极度敏感。”*G.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nd Ed., Abingdon: Routledge, 2009, p.3.
要建立在海上贸易基础上的体系仅仅一个国家进行维护是极其困难的。当时的这种全球化事实上远非真正意义的全球化,因为在这个经济运作过程之中,诸多殖民地、前近代国家仿佛是置身于这个全球化之外,远远没有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恩惠。
随着欧洲大陆列强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下积累了足够的国力,英国治下的大海成为了它们企图占据的目标。马汉思想中提到的那些关于海上力量应该在守护有赖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国际贸易体系上发挥作用几乎被无视,而《海权论》中提及的海上优势以及海上战斗方面则吸引了大多数海权挑战者们的注意。在不断出现的各种挑战面前,英国开始对于维护海上秩序感到力不从心,原本散布于全球各地的各大舰队又开始集中在北海,准备迎击传统的挑战。保罗·肯尼迪论述道:“只有当信心和国际善意都消失时,才会有老旧传统再次现身的状况。”*P.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Lane, 1976, p.175.自由贸易带给全人类繁荣、确保国际善意与防止战争的功效和人类失之交臂。恰如1910年诺曼·安吉尔(Sir Ralph Norman Angell)在他那本著作《巨大幻影(Grand Illusion)》中描绘的理想之图,宣称国际经济依赖要么会阻止战争的爆发,要么会使它提前结束的*基根著,张质文译:《一战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遗憾的是,善良的人们忽视了人类内心深处潜藏的贪婪、邪恶、愚昧以及野蛮。
从英国主宰海上秩序以来近乎一个世纪,国际间的经济协作与和平曾经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繁荣,这种繁荣也一度促进过国家民族之间的协作。但是由于人类未能把握好这个机遇,一旦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从而导致的经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战争便进一步加深了国际经济危机,全世界的经济便开始螺旋下降,并从起初和缓下降迅速加剧,使得任何阻止经济下降的所有尝试都告失败。*弗里登著,杨宇光译:《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于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所带来的第一次近代全球化浪潮,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数不清的动乱下落花流水而去。
结论
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海权模式,而在这种海权所建立的秩序下,十九世纪的世界曾经跨入了一次全球化的门槛。然而,这次全球化的发展未能解决经济的均衡发展问题,人类文明不但错失了和平发展的机遇,而且还引起了二十世纪的诸多战乱。对于这次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切,目前还是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赞否两派。但是我们应该可以认识到的是,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是不争的事实,而所有对此持反对态度的,基本上是将矛头指向由此带来的发展不均衡。事实上,著名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aul Polanyi)曾指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市场经济甚至到达了一种最高潮时期,而当时缺少的则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制约,缺少的是一种全球化体系下的国际秩序。因此,如果由此来全盘否定自由贸易,否定全球化的推行,并声称要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状态则是绝对片面的而且是愚蠢的。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世界经济又一次来到了全球化世界的门槛之前。在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海上格局和国际关系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当年英国主宰下的海权相比,现阶段的海权已经更多地由排他式的争夺,向着带有竞争和合作共存的崭新形态进行着转化,马汉的这些预言也开始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应验。
而这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尽管由一系列主权国家构成,但受到跨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影响,国家的绝对主权已经逐渐被削弱,人们的关注重点逐渐从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地向这个体系本身转移。而在这个体系下,人们策划的战略,也愈发转为服务于整个世界体系,而不是服务于常规的、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体制。
而且,由于贸易和商业导致了赢家和输家变化不定,因此,这也要求人们对外交、经济、社会以及军事政策进行积极主动、持续不断并小心翼翼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必须塑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才能更好地对这个体系进行保护。
最后,由于地球的百分之七十一为海洋所覆盖,因此,全球化对于畅通无阻的海洋航运有着绝对的依赖。
而在这一新的时代,马汉在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海权这一概念,早已成为太空、航空和信息等多种复合科技的产儿。而以往排他性海上霸权逐渐让位于功能更复杂和更国际化的当代海权观念。这一当代海权观念新颖和核心的特点是,海上力量已无力追求单极的全球霸权与秩序,相对于日益崛起的太空和空天复合力量,海权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即使对于拥有绝对海军优势的国家,在国际政策中,单纯利用海权优势也不可能达成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即使有能力轻易获得海上战争的胜利,其外交、经济和其他代价,也是其决定行动时不得不再三考量的因素。这也是与当代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急遽整合趋势一致的。
对于如何构筑这个新时代的海权模式,一百多年前英国在自由贸易模式下形成的海权模式作了诸多的尝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并给予我们以诸多的启迪。
当然,这种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和一百多年前一样,依然是一种非常敏感和脆弱的体系,这个体系面临的诸多威胁的形式,也都是和海洋有关,或者会产生重大的海洋性影响的。不过,和当年不列颠称雄海洋的时代有所不同的是,目前虽然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英国当年的角色,但是美国始终没有能够达到英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那种海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维护目前海上秩序的力量,仅仅依靠一国之力是无法完成的,这需要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下,依靠各个主要海军的通力协作。
对于这种全球化的经济秩序,最为直接的威胁便是从某种意义而言同样“全球化”了的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诸如海盗和对于武器、人口以及毒品的走私等跨国犯罪。而从更为长远的视角看,环境恶化以及对海洋资源的系统性掠夺还具有更为严重的威胁性。当人们意识到总体海上安全向着全球化海上贸易体系进行有效集中之后,保护海上良好秩序而维护海上总体安全也将成为人类的共识。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将造福于全体人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将会发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良好、持续以及建设性的关系才是取得共赢的关键,这种海上共识的维护,将通过多国联合行动的形式,更为积极有效地得到展开。这一点,不久前多次展开的亚丁湾联合打击海盗的行动,便是后冷战时期海上军事行动的典型性代表。因此,在这个意义下,全球化时代海军的主要任务,已经逐渐从我们比较熟知的与对方海军进行大规模对抗,变成了维护海上安全,打击破坏经济秩序的力量,诸如驱逐海盗,打击海上恐怖主义等内容。而不管在什么时代,陆地总是大多数海上混乱的根源,要从根本上维护海上秩序,如何从海上出击而消除这些祸害也将成为新时代海军最为经常需要完成的任务。这样的行动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追求快速,时而远离本土,也可能以多国形式实施。这种小规模、低烈度的行动会成为新时代海上力量运用的典型。
在这个时代中,海军对于海洋,如何加以控制依然是一个不变的课题,但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控制海洋为己所用,更多的倾向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利用海洋这一点,当然破坏这个体系的势力除外。因此,新时代的海上控制将更加具有监督和管理的意义。正如在2005年到2007年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迈克尔·穆伦(Michael Glenn“Mike”Mullen)在其任期中的2006年指出的那样:
“尽管旧的海上战略聚焦于海上控制,但是新的海上战略必须认识到,当海洋处于一国独占之下时,诸国兴起的经济大潮是不会出现的,只有当海洋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安全又自由之时,它才会涌现而出。”*G.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nd Ed.,Abingdon: Routledge, 2009, p.8.
当然,由于传统意义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还未完全得以解决,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传统意义的海上冲突和对抗还将长期存在,有时候也不排除可能出现激烈冲突的可能。而且,贫富不均给全球化带来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便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年英国的海权体系可以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思考,我们从中也能够汲取更多的历史教训。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全球化的大门展示在人类面前之时,便说明人类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急遽变化而带来的危机。也许回顾当年英国的海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对于后人而言还会有相当启迪的。
[修回日期:2015年11月05日]
[责任编辑:王婷婷]
[收稿日期:2015年10月25日]
[作者简介]章骞,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海洋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