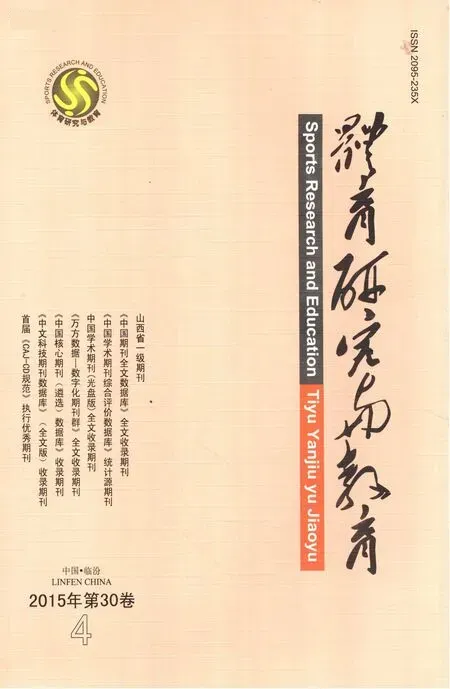谈孔祥熙与中国近代体育事业
吴 强
随着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亿万普通大众心中的奥运记忆又被再次唤醒。七年前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一圆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也使中国竞技体育成绩和群众运动普及程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比赛之外也对奥运历史、奥运精神、奥运文化以及奥运与中国之间的脉络联结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中国百年奥运的历史长河中,较之享有“中国奥运之父”美誉的民国著名外交家王正廷和“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作为继王正廷之后的第二位中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曾担任国民党政府多个要职的孔祥熙与奥运之间的互动及其对中国近代体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却长期湮没不彰。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外号“哈哈孔”的孔祥熙留给后人更多的还是其家世显赫、资财丰厚与子女作风的飞扬跋扈。鉴于此,笔者在参考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对孔祥熙的体育事功略作概述。
1 孔祥熙与体育结缘的时代背景
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号子渊,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系孔子第75世孙。在外人眼中,孔祥熙“生得脸型俊美,手指纤长,言谈举止儒雅大气”[1]。祖父孔庆麟为传统票号商人,家资雄厚,但至其父孔繁慈时已渐趋中落,转以塾师为业。孔祥熙从小跟随父亲在私塾中学习,因此有着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底,而母亲庞氏则在孔祥熙六岁时不幸病逝。生活于中国僻塞内陆小城的孔祥熙之所以在此后的生命中会和体育结下不解之缘,不得不提及来自三个方面的因素。这其中既有政府政策影响下的外部客观环境和时代思潮的双重推动,也与孔祥熙自身成长经历有着莫大关联,诸多因素的巧合共同将孔祥熙推向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前台,可谓因缘际会!
西方体育思想和主要运动项目近代以来的先后东传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体育观——从过去将体育视作较为单纯的游戏和娱乐转变升格为国家民族乃至种族盛衰的象征,这是理解孔祥熙体育情结的重要时代前提。
鸦片战争以降,国门洞开,各种西方学说以强劲力道冲击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国人在新奇、惊叹之余也渐渐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与落后。在东传的诸多西学科目中,既有数学、物理学(时称格致学或格物学)、化学这样颇有深度的理论科学,也有地质、矿物、农桑、兵工等实用性技术。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西人来华,其超出中国人认知视界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习惯也被带入中国,并随着他们在中国居住地的一步步扩大和深入而被更多人所熟知、了解并接受,这其中也包括体育。时人不仅已经开始意识到体育对个人体魄和身心的重要性,如蔡元培所言——“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2],而且把它与国族命运相联,赋予其更为丰富的社会思想内涵。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体育的接纳不仅是对篮球、足球、游泳、田径等运动项目的学习,而且一定程度上也认可了透过体育比赛中的胜负输赢能够展现个人和国家综合实力这一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强权”逻辑。“即体育不仅有军事上的强兵作用,更有在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上的强种、强国作用”[3]。
此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所确立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体育则被执政者视为能够有效提升新政府统治合法性、凝聚全国民气、贯彻领袖意志、有利于稳固统治的工具。其后,1929年国民党三大颁布的《教育方针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教育应“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具体实施共含八项细则,其中一项即是“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国民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发展体育之目的,固在增进民族之体力,尤须以锻炼强健之精神,养成规律之习惯为主要任务”[4]。1931和1932年更进一步颁布《国民体育法》、《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强化党国体制对体育的领导和统驭。
除了时代诱因和政府政策因素这两者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所办的教会学校对体育的普遍重视也是成因之一。孔祥熙所受的教会学校教育及其在美国留学的经历都使他切身体认到体育的重要性和在学校教育中所扮演的无可替代作用。这一直观感受对于孔祥熙来说相较上述时代因素更为直接。
中国传统私塾和书院在教育内容上以读背记诵为主,重点在于培养儒家式士大夫。与之相比,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已不再固守早期教会学校的单一传教目的,而是转向作育熟知中西文化的“通才”、引领风潮。“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5]。在课程和教学方法上,教会学校重实证、讲实验、强调学生的实际参与和动手能力,同时也有诸多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而体育活动在其中就占据重要位置,如抢球、夺旗、棒球、足球和各种游戏性赛跑项目。[6]这些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仅愉悦了学生身心,而且也使教会学校的体育竞技水平位居当时全国学校体育的前列。
与民国政坛上的其他文人相比,孔祥熙自幼受洗入教,先在太谷当地的教会学校就读,后被保送至北京附近的通州潞河书院深造,接受的是完整教会教育,英文好,与校中担任教师的国外人士有着密切接触,对西方教育方式和思维观念自不陌生。1901年更因义和团运动期间协助办理太谷教案而被保送至美国留学,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研究院完成学业,直至1907年回国。如果说此前在国内教会学校孔祥熙还是间接感受体育的话,那么,长达六年的美国大学生活则是他置身于西方文化的浸润中对体育感同身受的体验。
2 发展学校体育、引入近代体育
孔祥熙1907年留美归来,回到老家太谷,在母校欧柏林大学的支持下创办铭贤学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农业大学),旨在纪念山西义和团运动期间的部分欧柏林死难校友,其英文校名为“Oberlin Shansi Memorial School”(“欧柏林山西纪念学校”),有”铭记为传教而殉难的诸位先贤“之意。铭贤初为小学,后陆续开设中学和大学,办学重点在于现代农业科技研究和农作物改良工作,成为当时国内重要的农业研究基地之一。“堪称当时实业教育的典范”[7],被誉为“三晋学府、私校典范”,并受到蔡元培、张学良的题词嘉勉,吸引了包括陈衡哲、蒋梦麟、潘光旦等一流学人和教育家的参观考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是在主政铭贤期间,孔祥熙开始将他的体育理念作为整体办学思想的一部分而付诸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虽然并非职业教育家,也不是教育学科班出身,孔祥熙却充分意识到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教育是立国之本,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全视教育的成败为转移。故本人自留学美国后,即本办学救国的志愿,追随教育界同仁之后,努力提倡教育。”[8]掌校期间,孔祥熙在提倡包容、开放的前提下将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树为整个铭贤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轴,传授知识与建构学生整全人格并举,“人的每一部分都彼此关联、相互影响,是不可分割的”[9],这其实也是基督教“四全”(全备、全人、全面、全盘)式教育的体现。同时,孔祥熙在办学中极力倡导中西汇通、援西入中,有机结合两方长处而不可偏废其一。进而言之,孔祥熙不是单纯就体育论体育,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将体育置于更大范围的教育框架下,探索其对学生成长和民族发展所具有的功用,体现了当时“以体育人”和“体育救国”这两大思潮。在他看来,体育与教育紧密不可分,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失去教育作为支撑,也将大为弱化体育中“育”的成分,这样,体育也就与好勇斗狠、机械蛮力没有区别了。因此,发展学校体育不仅有助于健全人才的培养,而且也是兴办社会体育的典范。在这一点上,孔祥熙与著名体育家马约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颇为相似。
具体来说,在铭贤学校的课程设置上,除了文化科目外,创校之初就已开设体育课。内容以田径、球类和游戏为主,另在训导处下设有体育卫生部,孔祥熙还亲任体育教员。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学校一方面充实体育教学设施,兴建了250米田径场和篮、排球场等;另一方面不惜重金延聘诸多术有专长的教学人才担任体育教师,中国近代著名武术家、形意拳一代宗师布学宽先生就曾担任铭贤武术教员,以推进武术在青年学生中的普及程度,部分美籍教员则向学生讲授田径、篮球和排球等课程,通过提供器材,引进和推动了篮、排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此外孔祥熙还利用在外省旅行之机,到京、津、沪等地的学校招揽体育人才入晋,这批受过现代体育教育的教师在引入近代体育,扩大新式体育在山西的影响力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孔祥熙的重视和提倡下,铭贤的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一向都开展得很好。学校成立了全校性的体育会,组织了篮球队、排球队、体操队、田径队、国术队和棒锤班等各种专项运动队。这些队伍的组成不分班级和师生,一律根据个人兴趣和爱好自由选择,裁判术语也都是英语。由于训练刻苦,水平较高,这些运动队不仅在校内经常进行对抗性比赛,而且多次参加华北地区和山西全省的运动会,并取得佳绩。在1915年4月的山西第一届省运会上,铭贤分别夺得跳远、跳高、铅球、400米跑和200米跑等项目的冠亚军,轰动全省,此后又多次在全省和华北运动会上夺魁。因为铭贤学校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直接受到西方的影响,体育活动非常活跃,竞技运动成绩显赫”,因而“大大扩大了铭贤的声誉”[10]。
3 入选国际奥委会、支持国家体育
囿于平台所限,孔祥熙主政铭贤期间重视和发展学校体育所产生的影响力远不及他后来登上政坛高位后对中国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推动和资助,其个人也入选国际奥委会,成为第二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得以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
3.1 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奥林匹克运动早在1900年就已传入中国,当年7月于上海出版的《中西教会报》上就曾刊载过关于法国巴黎召开第二届奥运会的消息。[11]1903年,清政府外务部已有专门奏章提请派遣专人参加于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第三届奥运会,但此次与会并非正式参赛,而仅仅是以考察1904年同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名义作了一下局外参观。直到王正廷当选为国际奥委会首位来自中国的委员之后,中国才在1924年派出三名运动员赴法国参加第八届奥运会的表演赛。1924年,中国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英文全称为“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并于 1931 年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12]
出身外交系统,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王正廷敏锐觉察到奥运会的国际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参与奥运会不仅对推动本国体育事业发展功莫大焉,而且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国际能见度。出此爱国情怀,根据奥林匹克章程,王正廷运用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影响力,分别于1939年和1947年两次向国际奥委会推荐孔祥熙、董守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正是在王正廷的力挺之下,孔祥熙得以成为继他之后第二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政经之外又获得一个受人瞩目的高平台。孔祥熙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也一直保留至他1947年前往美国做寓公后,1955年才正式辞任。
王正廷之所以力荐孔祥熙而不是其他人,既有他们之间的私谊起作用,如都为基督徒、留美同学、耶鲁校友,同属一个兄弟会,回国后都曾担任过基督教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董事。王正廷当青岛督办时,孔祥熙则担任其实业处长兼电讯局长等。但比个人交好更为重要的还是在于王正廷从大局出发,认识到要开展“体协”的各项工作和推动奥运会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必须得要有一个身居要职,较为熟悉国际事务,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高层有一定话语权和活动能力——特别是在筹款方面,同时也能够和自己相互配合、彼此了解之人,而孔祥熙在王正廷交友圈中恰恰具备了这些条件。因此,推荐孔祥熙进入国际奥委员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了。他在和董守义交谈时坦承:“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依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能向政府说话的人,有找钱能力的人才行。”[13]
3.2 支持和资助国家体育
民国时期的体育事业受制于深处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不论举办全国性运动会,还是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资金的短绌都是首要难题。同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就曾忆及这一窘境,“没有固定的经费,根本谈不到什么事业费,更谈不到什么体育事业的财务计划,就连平常维持几个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很困难,所以一遇到某项大的开支,筹款就成了很大的问题”[14]。
也正是在这方面,孔祥熙给予全力协助。1933年,已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作为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名誉顾问为大会题词“锻炼图强”。两年后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开幕致辞中鼓励运动员要“强健体魄”。1936年,受“体协”邀请,孔祥熙为《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一书题词“提倡体育,角逐群雄,自强不息,计日程功”。
1930年,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当时“体协”经费十分困难,连运动员最为基本的参赛物资都无法保障,孔祥熙见此情形后,批准了“体协”补助200英镑的请求,使得中国运动员最终能够顺利成行。1936年,第十一届夏季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办,中国代表团的所需经费预算高达220 000元。这时已是抗战前夕,国民党政府财政拮据,收入有限,但孔祥熙还是在压力之下划拨了170 000元(其余50 000元则向社会各界募捐)供其使用。1943年,“体协”因经费紧张、运转困难,孔祥熙特批法币20 000元以维持其日常工作。1948年,王正廷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结束后,因回国路费告罄,孔祥熙特汇美金3 000元以解燃眉之急。
4 对孔祥熙参与体育事业的评价
列宁和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论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5]“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社会”[16]而孤立的以某一标准衡量。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绝非以单一面相存世,后世在对其进行评价时既要看到其一生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样态,也需分辨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人的具体作为及其影响,实事求是、就事论事。
时过境迁、斯人已逝!综上所述可见,孔祥熙在那个时代属于较早一批有机会能够亲身前往美国学习和体验西方文化的探路者,在回国时则将他们所感受到的西方体育观带回国内,并通过发展学校体育积极践行,使体育成为启蒙大众、塑造新民的重要方式。就此而言,孔祥熙在一定程度上堪称时代的先觉者。从1928年南下广东担任省财政厅长至1944年在一片国人骂声中去职下台,孔祥熙在民国政坛屹立将近30年,虽然曾经担任过包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在内的多个重要职务,掌管国家财金命脉,但当时的中国却是一个连年战祸、军阀割据,且遭受日寇侵略长达十四年的贫弱之邦,也无所谓国际地位可言,体育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体系和国家投资等等都十分落后,根本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对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尽其所能给予支持和资助。单凭这一点,无论从他个人角度还是从国家民族角度来说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毕竟他无法超越时代,更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外在客观环境。他自身的局限性其实本质上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缩影。
孔祥熙深受近代欧美体育思想的影响,1907年留美回国创办铭贤学校后,孔祥熙在其掌校期间极为强调体育对增强学生体质、锤炼青年一代人格所能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不仅局限于铭贤学校一隅,他还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提倡新式体育项目、倡办运动会,由此推动了山西近代体育的进程。之后,走上政坛的孔祥熙还较好运用了自身政治能量为全国体育运动提供必要支持,特别是在中国代表团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一事上慷慨解囊。正是由于这些骄人功绩,他本人也入选国际奥委会,成为继王正廷之后第二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1] 麦美德.费起鹤及孔祥熙[M].郭晓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2] 蔡元培.体育为修己之本[J].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3] 崔乐泉,罗时铭.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王凤喈.中国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
[5]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6] 王华倬.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 杨常伟.孔祥熙与近代中国农业科技改良——以山西铭贤学校的农业科技改良实证考查[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4):88.
[8] 孔祥熙.孔庸之(祥熙)先生演讲集[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9] 区应毓.教育理念与基督教教育观[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10] 山西农业大学体育教学部.山西农业大学百年体育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11] 罗时铭.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时间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4(12):67.
[12] 格吉诺夫·瓦西尔,董进霞.奥运会的起源与发展——解读奥林匹克运动会[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
[13]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J].文史资料出版社.奥运会与中国[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14] 董守义.中国与远东运动会[J].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二辑)[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7.
[15]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6] 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