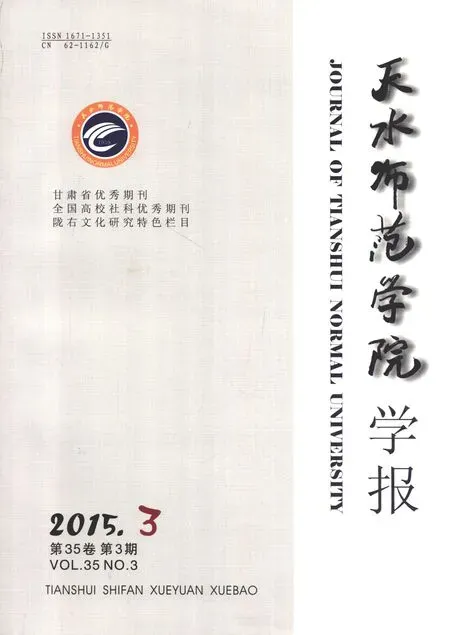何处是归程——宋元之际同题诗的新主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51(2015)03-0030-04
收稿日期:2015-03-28
作者简介:乔俊梅(1991-),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同题诗指的是两人或两人以上所作的同一题目的诗歌,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由来已久。早在汉代就有柏梁台联诗,魏晋以来的同题诗创作气象蓬勃,邺下文人因领导者的倡导而广泛创作同题诗,比如曹植等人的《宴会诗》、王粲等人的《斗鸡诗》;唐朝诗歌唱和高涨,屡见同题。有宋一代同题诗得到了继续发展,尤其在南宋涌现出不少诗社,为某一主题的发起而集体同题创作提供了便利。宋元之际的同题诗深受政局变化的影响,表现出新的风貌。历来对宋元之际的文学关注多侧重在遗民词上面,诗歌方面则多倾向于个别作家或者某一群体的研究,比如月泉吟社诗就受到很大关注,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尽管易代之际为集体唱和带来诸多不便,但此时期却仍有数量可观的同题诗出现,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思考。究其诗作就会发现,《送水云归吴》《题汪水云诗卷》《游洞宵宫》《大涤洞天留题》和《春日田园杂兴》等同题诗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宋遗民在精神上的追寻和寄托,表达出他们特殊的心理诉求。反观之,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求仙问道:城郭身今化鹤归
汪元量(号水云)是由宋入元比较典型的人物,尤其是他随三宫北上后,时隔十二载“乞得黄冠还故乡”的特殊身世遭际,成为其诗歌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不少诗人创作的题材之一,同题诗《送水云归吴》和《题汪水云诗卷》就是如此。
“北师有严程,挽我投燕京。挟此万卷书,明发万里行。出门隔山岳,未知死与生。三宫锦帆张,粉阵吹鸾笙。遗氓拜路傍,号哭皆失声。吴山何青青,吴水何泠泠。山水岂有极,天地终无情。回首叫重华,苍梧云正横。”(汪元量《北征》)
汪元量的这首诗真实地再现了德祐二年(1276)三宫北上的历史。“(元量)以善琴事谢后、王昭仪。” [1]1887这次北上的宫嫔中就有谢后、王昭仪。汪元量陪三宫北上后,虽然深受新朝器重,但是入元十二年后,他再三请求并且如愿南归,此事在南宋宫人的14首同题诗《送水云归吴》中亦有所述。
王清惠(即王昭仪)在《送水云归吴》序说:“水云留金台一纪,琴书相与无虚日。秋风天际,束书告行,此怀怆然,定知夜梦先过黄河也。一时同人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分韵赋诗为赠。他时海上相逢,当各说神仙人语,又岂以世间声律为拘拘耶。” [2]44058王昭仪记述了这组同题诗的创作背景,尤其“束书告行”点出了汪氏南归一事。“一纪”就是十二年,在《国语·晋语四》:“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纪,可以远矣’。注:蓄,养也。十二年岁星一周为一纪。” [3]321此外,王昭仪还有诗《李陵台和水云韵》写道:“客路八千里,乡心十二时”,这十二时的乡心想来也是众位北上宫人的乡心。度宗时其他北上的宫人何凤仪、黄慧真、郑惠真等人所赋诗《送水云归吴》亦皆是一曲曲啼血的盼归词。如“十年燕客身如病,一曲剡溪心不竞”(何凤仪《送水云归吴》)、“寒上砧声响似雷,怜君骑马望南回”(叶慧静《送水云归吴》)、“琵琶拨尽昭君泣,芦叶吹残蔡琰啼”(郑惠真《送水云归吴》)等都表达背离故国的悲苦,甚至嘤嘤啜泣后还有铿锵真切地叮嘱“君今得旨归故乡,反锁衡门勿轻出”(方妙静《送水云归吴》)。
总的来说,这十四位宫人的同题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入元后宋宫人们的内心世界:江南江北路茫茫的怀念和虽有归心却无法左右现实的无奈和悲凉,尤其是借昭君和蔡琰的典故表达了政局变乱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和苦楚。
汪元量南归后,出现了同题诗《题汪水云诗卷》。以这一题目作诗的诗人包括孙鼎、彭淼、萧豳、刘渊等,他们都是宋遗民。这些诗不同于一般的作品题词,有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在内容上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揭示了汪元量顺利南归的事实。比如彭淼“万里归来旧布衣,笳声不断转桐丝”、萧壎“辽鹤归来世已殊,忽悲身晚及塘蒲”、戴仁杰“今日相逢又相别,新诗满橐不论钱”、刘震祖“剑吼洞庭朱顶急,归来城郭问云仍”、兜率长老“穷发归来脱孟劳,何嗟澹与泊相遭”、永秀“黄冠氅服今谁识,前宋遗贤有此儒”、杨学问“握手论心不记年,重逢仍似地行仙”、萧灼“十年归来两鬓霜,袖有诗史继草堂”、祖惟和“北去南来策蹇驴,偶然过我古玄都”等等,这些诗歌几乎都或明或暗地说出了这部诗卷主人的归来。对于汪元量以“黄道师”归吴的头衔,有人在诗中很坦率地说道:“黄金好铸钟子期,知君不是黄冠师”。(萧灼《题汪水云诗卷》)
其二,将汪元量比作南北朝时期的庾信。因为身世遭际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汪元量和庾信都是被迫由南入北,并且深受北国器重。比如彭淼“十年秋入肩吾鬓,四海人传云叟诗”、萧壎“剡曲祗今书贺监,稽山在昔庾肩吾”、秦嗣彭“庾郎谩有江南赋,得似先生醉后歌”等等。这些宋遗民把归来的汪氏和庾信对比,更突出的是前后历时相通的故国之思。
其三,汪元量是他们心目中的知音。这些为汪氏诗卷题诗的遗老们很多都有知音难得,知音归来的感慨。罗绮“知音向近西湖上,却不当初早理弦”、祝从龙“竹杖芒鞋短后衣,抱琴何处觅钟期。百年烂醉乌程酒,千首新吟晋宋诗”、萧灼“黄金好铸钟子期,知君不是黄冠师”、严日益“世间未必无子期,至音元不求人知”、张嵩老“会心又见钟子期,识操又遇韩昌黎”等等,他们都深切地表达了与汪元量互为知音的欣喜和感动。
为什么一个在元朝生活了十年之久的人归来后仍能得到这样热情的接纳?从这组同题诗中还是可以得出一些答案的。彭淼有“四海人传云叟诗”的说法,说明了水云诗的流传范围之广。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水云诗的受众广泛,至少《题汪水云诗卷》的作者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作品能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水云诗能够满足读者的需要。而这批同题诗不仅讲出了水云诗卷的内容,并道出水云诗堪比杜诗为人们广泛推崇。
从杜诗在历代的接受情况来看,“千家注杜”足以说明宋人对杜诗的推重。宋遗民认为汪元量堪与杜甫比肩,可见他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王祖弼“我辈恨生南渡后,道人啸出北征诗”、曾顺孙“琴音不忍移南操,诗卷犹能续北征”、萧灼“十年归来两鬓霜,袖有诗史继草堂”。汪元量作的一首和杜甫同题的《北征》被反复赞颂,其真正的动人之处当在于:他也真切地表达了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的流离失所等不幸,和杜诗一样具有史诗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汪元量和杜甫一样,前期成长在一个礼乐盛行的时代,深受正统文化的熏陶。但是战乱使得这一切遭到极度破坏,对他们的内心产生了强烈冲击。元代大儒郝经在他的诗歌《巴陵女子行》序言里说:“宋有天下,文治三百年,其德泽庞厚,膏于肌肤,藏于骨髓。民知以义为守,不为偷生一时计。其培植也厚,故其持藉也坚。乃知以义为国者,人必以义归之” [4]33而那些作诗送别汪水云南归的宫人和为汪元量诗卷题诗的遗民们,他们在礼乐极盛的宋代生活过,又见证了异族入侵,礼乐崩坏,这种遭遇才会让他们有“把君丙子集,读罢泪潸然”(萧炎丑《题汪水云诗卷》)的共鸣,诗歌无疑已经变成了遗民情感交流和心理慰藉的重要媒介。与其说是他们声通气应地表达对汪氏诗卷的认可,不如说是在诗歌的王国里他们找到了自己情感的归属。
汪元量以黄道师南归的背景之一就是全真教在当时的盛行,汪氏的这个选择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道教认为山是神仙所居住的处所。《说文解字》:“仙,人在山上,从人从山。” [6]167唐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终宋一朝,道教一直都备受重视,尤其是宋徽宗大建宫观,册封神仙,编修道藏。《宋史》记载徽宗时期“九月辛卯朔……令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 [5]396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人本身对于道教就有一定程度的认可。道教在元代被推崇的表现同样是大修宫观,曾经在宋朝就已经辉煌一时的洞宵宫更是屡经扩建。大涤山自汉代就是道教宫观选址,历朝都有修整,在宋元两代亦是如此。
生活在宋末的一批诗人们留下两组同题诗:《游洞宵宫》《大涤洞天留题》。尽管这些诗人生平遭际许多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他们的作品却记录了他们在大涤山,这座道家神山上的无尽情思。
洞宵宫在大涤山的中峰,这两组同题诗都是游大涤山所作。身处此地的众位诗人为后人留下的既有“山锁清溪溪锁峰,溪光山色两怡融”(《黄常吉《游洞宵宫》)的秀美,还有“一朵云根生老涧,千寻天柱压群峰”(张巽《游洞霄宫》)的宏伟。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置身于此,面对此景,他们有对道家平和无为,得道求仙的无限向往:“此地隐居皆胜士,道骨仙风绝尘滓”(聂兼善《游洞宵》)、“我到此间无别事,烧香直欲达诸天”(彭挥《游洞天》)、“山茗已堪回短梦,金丹要可得长年。是中着语真难事,今古舂容几大篇”(吕奫《大涤洞天留题》)、“凡心洗涤今无妄,仙迹微茫要指南……抱琴携子盟泉石,终老山阿我亦甘”(高攀《大涤洞天留题》)。有的表达了“俗累”难却的纠结心境,坦言“道念岂不定,俗累良未休”(黄常吉《游洞霄》)、“何时罢脱功名去,始悟人间万事非”(馀杭令《游洞宵》)。
从汪元量个人以“黄道师”南归到宋末风云变幻之际广大不为后人知的群体对道家宫观的咏叹,这些同题诗不但满足了当时生活在相对集中范围内人群的情感交流需要,而且比较集中地揭示了当时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宫人日夜思归不得之无奈,江湖人士浪迹天涯诗酒唱和寻找感情寄托的落寞,还有试图走向无为清静世界以求让自己身心得以安宁的求道之路,他们的同题诗创作可以说是那些落寞的文人寻找心灵归途的记录。
二、田园之寻:芹塘泥滑燕归忙
与其他遁世求道的遗民不同,还有一批遗民在新朝用“回归田园”的方式来接受亡国的事实,这就是月泉吟社的诗人们,即《春日田园杂兴》的创作者们:
至元二十四年,宋义务令浦阳吴渭字清翁,号潜斋,约诸乡遗老为月泉吟社,预于小春月望命题,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终结局。诸乡吟社用好纸楷书,明书州里姓号,如期来浦江交卷,俟评校毕,三月三日揭晓,赏随诗册分送。因用范石湖故事,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延谢翱皋羽、方凤景山、吴思齐子善,相与甲乙评骘。计收卷二千七百三十五,取中二百八十,刻诗六十名。 [7] 55-56
这段话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诗社的成立和此次《春日田园杂兴》征稿、评选、奖赏的大概。能在短短几个月收到两千七百多首诗,足以见得这次征诗的响应者之多,尽管其中不乏有人投递一首以上诗歌,但是仍然不能否认此次征稿的成功。
这次有组织有主题的诗歌创作,因为题目与田园相关,故而在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人物就是陶潜。比如梁相“彭泽归来惟种柳,石湖老去最能诗”、杨本然“栗里久无彭泽赋,松江仅有石湖诗”、全璧“晋氏衣冠门外柳,豳人风俗屋边桑”、吕文老“浩兴归来吟不尽,陶诗和后和豳诗”、高镕“已学渊明早赋归,东风吹醒梦中非”、胡南“渊明千古立,伫立此时心”等不胜枚举。因此有人说“以春日田园命题,取靖节‘田园将芜胡不归’之意”, [8]335这也是不无道理的。与陶氏一样备受青睐的就是不肯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如九山人“种秫已非彭泽县,采薇何必首阳山”、何鸣凤“何许蕨薇君欲来,饥眠堪羡华山高”等。
这些创作者们有的在入元后坚决不仕新朝,如全璧、何鸣凤就是如此。他们不仅是用浅斟低唱来赞扬忠于故国的前人,而且身体力行效仿前朝的“守节”之士。南宋理学思想盛行,统治阶级已意识到,理学家那种以正心诚意为主旨的道德哲学,可用来教化世道人心,使士大夫中的达者克己奉公,不滥用权柄;穷者安于贫困,乐天知命,以维系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团结和皇权的巩固。出于这种道德政治的需要,这个时期的理学家既希望诗人和作家成为卫道立说的圣贤君子,也要求文学作品有补于教化。 [9]261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面对家国颠覆的文人们,在奔走呼号舍身成仁的另一战线就是用诗来捍卫自己的节气。这就使得《春日田园杂兴》这个看似在抒写田园情怀的诗题,却表达出用意深广的政治内容。
深读这些遗民的诗歌就会发现,其实在诗人们的内心深处也有着对陶潜全身心回归田园的欣羡。陶潜几仕几隐,最终回归自然,不问俗累。而此时,这些遗民们既不能全身心回归自然,又不能卷土重来复兴故国,只能借诗歌来互吐衷肠。他们有无法彻底放下朝市全心回归的苦闷,就在作品中表达对陶潜超脱境界的无限向往。姜霖“麦陇风微牛睡稳,芹塘泥滑燕归忙”、高镕“篇诗那可形容尽,何似忘言对夕晖”、东必曾“日长虽有荷鉏倦,薄暮归来常醉吟”、俞自得“物态满前看不足,等闲吟咏对斜晖”、王进之“满眼春愁禁不得,数声啼鸟在斜阳”等等都构设了和陶潜田园生活相似的画面,然事实是落暮斜晖正归时的无归处,心灵的无法回归成为此时期文士的最大痛楚。“世数有变革,田园无古今”(胡南《春日田园杂兴》),他们说历代都有田园,从表面上看似乎已经接受了世事沧桑变化的常理。实际是把“田园”变成一种象征一种理想,成为那些落寞的文人们面对已成定局的家国破坏所架构起来的可以守护自己心灵的家园。“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漫长的回归就是这一批落失意文人关于仕隐的斗争,关于归于何处的探求。
总之,同题诗《春日田园杂兴》除了在内容上反映宋遗民求回归的自我心灵救赎的历程,还在更丰富的情感表达上折射了南宋礼乐教化的结果。这种正统的儒家思想熏陶使得民众在面对家国变乱的情况下,除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激烈反抗之外,还多了一些儒家的中和。
三、结语
同题诗作为一种在时间、空间上相对集中的群体所作的诗歌出现,是一种集体活动的产物。而宋元之际的遗民所作的这些为数众多的同题诗,成为观照其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宋一代文士生活环境宽松,思想开放,各家学说均有一席之地。所以,南宋的文士们既能践行儒家的积极处世精神,又能吸收道家的潜退出世之道,这就使得他们在历史转关之际多一些生存的智慧。
但是,他们深受儒家“义、节”思想的影响,在遗民诗人们的部分同题诗创作中表现出的两种心态:遁世求道与归田守节,其实都是在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捍卫他们心中的高义大节。从汪氏的南归到一大批文人在道家宫观的浅斟低唱,无论是真心向道,还是想暂且在大涤山中寻得心灵的一份清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在他人看来无为出世的方式;而入元不仕的一些文人们在吴渭的领导下积极创作出来的同题诗《春日田园杂兴》,表达的也是一种“回归”的渴望,这种渴望之中既有对旧朝的怀念,更多了一些无法回归自然,求静不得的躁动。他们将这种复杂的情感付诸于诗互相倾诉交流,使得诗歌成为他们走向心灵桃花源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