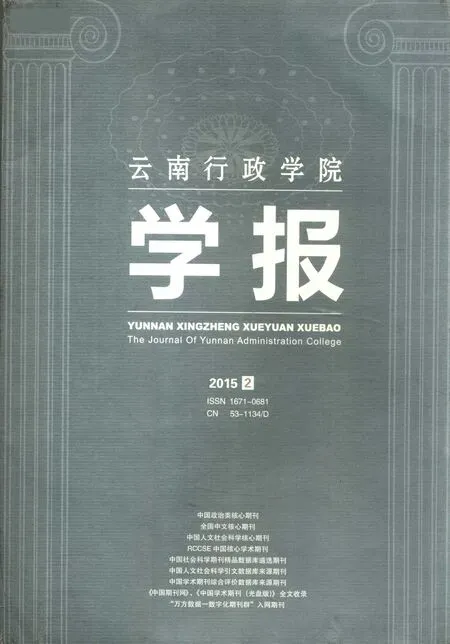托克维尔的帝国思想探析
段德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托克维尔的帝国思想探析
段德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托克维尔一方面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另一方面他非常热心地支持当时法国在海外——特别是北非阿尔及利亚地区——的殖民和扩张政策,这一“矛盾”即所谓托克维尔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近年来托克维尔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之一,主流的以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为代表的“自由帝国主义”论者认为,托克维尔的帝国立场在最终的意义上与其严肃的政治理论不相契合。这一解释角度具有很大的缺陷。事实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托克维尔自身的思想中,自由和帝国二者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矛盾,而这二者的结合更应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托克维尔的自由概念,而不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托克维尔;自由;帝国;共和主义
一、引论
随着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各种类型的文字—书信、国会报告、笔记等在《托克维尔全集》中的不断完善,托克维尔作为法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坚定支持者的形象逐渐明晰,学界对此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在于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托克维尔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另一方面他又是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事实上,在写作其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之时,托克维尔已表现出对法国在北非的占领和殖民统治的强烈兴趣。1833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如何使法国获得好的殖民地”的文章。1837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阐发其关于巩固法国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地区殖民统治的观点。在1841年和1846年,他两次亲身探访法国占领下的阿尔及利亚地区,留下了许多笔记并撰写了长篇严肃的文章。在这些文字中,托克维尔详细探讨了法国在北非的存在为何应该得到加强,以及如何得到加强。①托克维尔关于帝国和殖民地的文字主要收集在法文(1962 Gallimard edition of Oeuvres Complètes,volume 3,part 1&the 1958 edition Oeuvres Complètes,volume 5,part 2)在此基础上,詹妮弗·皮茨编辑和翻译了许多重要的托克维尔关于帝国和殖民地的文字,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ed.&trans.,Jennifer Pitts,Baltimore&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托克维尔说:“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在非洲海岸竖立起一座象征着我们国家光荣的丰碑。”[2](P24)然而,有意思的是,托克维尔同时又以一个为自由辩护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而闻名。此一自由与帝国的对勘,我们称之为托克维尔的“阿尔及利亚问题”。
托克维尔研究领域已经有一些对此问题的探讨。例如,在《托克维尔论阿尔及利亚》一文中,梅尔文·里希特(Melvin Richter)梳理了托克维尔与当时法国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关系,在比较了他的帝国立场与其在《论美国民主》一书中的观点以后,里希特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在里希特看来,托克维尔很遗憾地未能将其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社会学视角充分运用到关于帝国和殖民的分析上。他甚至因此宣称,“托克维尔值得被称赞的时代已过去了。”[3](P362)托克维尔专家、英文版《托克维尔论帝国和奴隶制问题》(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文集的编译者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的观点则更为温和,她将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立场放在一个所谓不断进化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中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和判断往往与其所处时代和国家的特定境况有关[4](P1—3)。与皮茨类似,希瑞·威尔奇(Cheryl Welch)也将托克维尔放在自由主义的传统语境中,但她的基本论点是:同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托克维尔必须面对他自身思想中的矛盾,为了避免道德上的困境,他有意地选择种种修辞手段为其帝国立场辩护。威尔奇认为,托克维尔的这种做法在当今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仍然存在[5](P235—264)。
以上这些关于托克维尔“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分析虽然各不相同①关于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David Clinton,Tocqueville,Lieber,and Bagehot:Liberalism Confronts the Worl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Margaret Kohn,“Empire's Law:Alexis de Tocqueville on Colonialism and the State of Exception,”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1(2),2008,pp.255—278.Roger Boesche,Tocqueville's Road Map:Methodology,Liberalism,Revolution,and Despotism,Lanham:Lexington books,2006.,但在一点上是一致的:托克维尔被当作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的一员,这一传统秉持的基本原则包括自由、平等、人权以及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等等。从这一角度看,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立场只能是对其自身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背叛。本文将质疑这一分析视角。首先,本文将给出以皮茨为代表的“自由帝国主义”式分析。其次,本文将指出这一分析视角的错谬之处,以为引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作辅垫。再次,本文将指出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立场与其思想中的共和主义成份有着密切联系。事实上,自由与帝国在托克维尔思想中的真实距离比人们想象的要近得多。
二、自由帝国主义视角
理解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问题或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其自由的概念。只有在特定的对托克维尔自由概念的理解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自由和帝国这一对关系在其思想中是如何共存的。本文这一部分试图给出皮茨提供的“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t)视角,以为我们讨论托克维尔的阿尔及利亚问题提供一个理论背景。
皮茨所问的问题大致与里希特相同,即为什么奉自由为神圣价值的托克维尔会转向帝国、征服和殖民?里希特将这一现象归为托克维尔的“盲点”(blindness),意即出于某些不得而知的原因,他未能一以贯之地运用他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但皮茨却将该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理论背景中,从而使其更为复杂和有趣。皮茨首先指出,托克维尔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例子。事实上,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中,曾经存在一个“转向帝国”的浪潮,而托克维尔只不过是这一浪潮的一部分。在皮茨看来,这一事实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例如,与托克维尔一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即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同是又是帝国主义的支持者。除了亲身参与英国对外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在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以外,密尔还有大量文字为英帝国在海外的统治辩护。值得注意的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辩护的基础看上去极为“反自由”(anti—liberal)。在《论自由》中,密尔说:“在与野蛮人打交道时,专制主义是一个合法的统治形式,前提是这一统治的目的应在于促进他们的进步,以及统治的手段事实上能达成这一目的。”[6](P48)在《论代议制政府》中,他说:“落后人类的一个共同且迅速成为普世性的境况是,他们要么处在更先进人类的直接统治之下,要么生活在其完全的政治优势之下。”[7](P314)
根据皮茨的论述,尚有许多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在这方面与托克维尔和密尔大致相同,如鲁瓦耶—科拉尔(Pierre Paul Royer—Collard)和基佐(Fran.ois Guizot)等。这些思想家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阵营,同时又支持帝国主义政策。皮茨将他们与前一时代———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家相对比,发现了这样一个转变的模式:
在1870年代左右,对特定的帝国主义行为和无限止的扩张计划的怀疑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共识。然而,仅仅五十年之后,我们就很难看到有重要思想家批评欧洲帝国主义。的确,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包括托克维尔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是热心的帝国主义者[8](P296)。
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Turning to Empire: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France and Britain)一书中,皮茨指出十八、十九世纪文化和政治氛围的变化主导了人们对欧洲以外人民及其文化的态度。随着欧洲人对自身文化的信息逐渐加强,他们对欧洲以外的文化和人民的态度也从包容—甚至某种程度的仰慕—转向批评和排斥。皮茨所说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从反帝国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大转变”即与此密切相关。斯密(Adam Smith)、伯克(Edmund Burke)、边沁、密尔父子、托克维尔、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等人都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普世主义者”,都相信人的普遍平等和大致相同的道德能力,但他们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却表现得并不一样,它或许会是一种包容和多元的普世主义,又或许会是带有强烈进步主义色彩的普世主义。
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所造成的“压力”和“焦虑”与个体思想家的关系中,皮茨认为,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最终能够得到准确的理解。皮茨正确地指出,托克维尔一生的理论思考所围绕的一个核心要点是自由。托克维尔认为,他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包括法国—自由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个人从公共领域中的撤退,现代的个人主义在物质主义的伴随下蚕食着自由赖以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如果不存在一个有活力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现代社会将面临着新的专制主义的危险。皮茨的这一描述大致可靠,但问题在于,她将托克维尔对政治共同体的敏感性看作一种负面的、消极的因素,这一因素影响着托克维尔,使民族主义甚或帝国主义的态度渗透进他的思想,使其自由主义带上了“污点”。
应该指出的是,如皮茨所说,托克维尔对法国帝国扩张和殖民计划的支持确实与他对国家荣誉的热爱有关。对外征服可以使法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使其国民感到“光荣”,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使他们能够更有动力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分享国家的荣誉和命运。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皮茨认为,托克维尔越过了红线,对国家荣誉的向往导致其对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关键的一步使得托克维尔与其自身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原则不相符合。这一判断直接导致皮茨对托克维尔的帝国情结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称托克维尔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幼稚,最明显的一点是他将真正的公民美德与夸张的民族情绪混为一谈。皮茨说,在这方面“托克维尔经常被一厢情愿而非仔细的社会学分析所引领。”[4](P194)事实上,皮茨并不是第一个作这样批评的人,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密尔曾给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判断。在回复托克维尔的一封信中,密尔说:最愚蠢和无知的人也很清楚地知道一个国家在外国人眼中的真正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大声的、喧闹的对此重要性的宣称,这一宣称的效果只能是带着愤怒的软弱的表现。一个国家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其工业、教育、道德以及良好的治理①。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皮茨和密尔在谴责托克维尔向帝国和国家荣誉的转折时都援引了自由主义的观念和价值。从而,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显得没有那么真诚和纯正。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视角具有很大的缺陷。
三、托克维尔帝国立场的再考察
皮茨对托克维尔帝国主义问题的解释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对托克维尔帝国主义倾向的心理分析大大降低了与有关帝国的文字在他的整体著作和思想中的重要性。皮茨的论述视角暗示,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可能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下真诚而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帝国立场。为了理解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同一个思想家那里“不可能”的互相揉合,我们最终需要一个心理学的解释。正是因为这一点,托克维尔关于帝国主义的文字在他的整体著作只能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它们也不会对我们理解托克维尔的思想——特别是其自由概念——有多大作用。皮茨提出的一个依据是托克维尔从未详细而准确地解释国家荣誉是如何转化为公民美德的。然而,正如本文接下来将要指出的,托克维尔自己未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显然也无法从这一点判断有关帝国主义的文字在托克维尔那里有多重要。
有意思的是,当皮茨在讨论托克维尔所可能感受到的“压力”和“焦虑”时,她自己也未能解释这一心理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尽管她对历史情境的描述很可能是对的,而且这种描述对我们理解托克维尔也有意义,但她未能清楚地告诉我们托克维尔思想中哪些部分是受到历史情境的影响,哪些部分没有。事实上,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能够直接证据证实皮茨所指出的“压力”和“焦虑”。他关于法国对外征服和帝国统治的文字与其《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样真诚而严肃,在时间上这两部分文字几乎同步。可以说,在帝国这一话题上他花了与其他著作不相上下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更好地了解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和民情,他阅读了《古兰经》等伊斯兰教文献,浏览了大量政府公文,通过私人关系长期保持对阿尔及利亚当地局势的了解,甚至考虑过与他的表兄弟克尔郭来(Louis de Kergoly)在那里购买一块土地做殖民者。[2](pxii)他的两封《阿尔及利亚之信》(Deux Lettres sur L'Algérie,1837)写于《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出版之间。1839年他当选国会议员,阿尔及利亚问题在其政治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也才有我们今天在《托克维尔全集》中看到的写于1841年的《论阿尔及利亚》(Travail sur L'Algérie)和1847年提交给国会的两篇关于阿尔及利亚民事和军事状况的长篇报告(Rapports sur L'Algérie)。
以上这些以及许多我们在此尚未列出的文字理所应当被看作托克维尔思想发展的一部分,应该与其他更“正式”的著作一样值得我们了解和研究,它们必须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其他更“正式”著作中所不能告诉我们的东西。
其次,由于自由帝国主义视角将托克维尔对政治共同体的强调看作一个错误,它大大低估了这一点在托克维尔自由概念中的地位。皮茨认为,总体而言,托克维尔与密尔一样应该被归入自由帝国主义思想家的行列,因而他不应该如此强调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对外征服和殖民统治这一话题上。换而言之,在皮茨的视角中,托克维尔对政治共同体的强调与她所理解的托克维尔的自由的概念是背道而驰的。本文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解释此理解的错误之处,但在此,我们只需要指出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在事实上与皮茨的描述有很大出入即可。
由于对共同体价值的强调,托克维尔事实上更愿意揭示欧洲国家在与其他文化接触时所产生的“暴力”。这种暴力不仅包括直接的物理意义上的暴力,如他在《论阿尔及利亚》中所说,“我们现在在战争中比阿拉伯人更加野蛮”,[2](P70)还包括不可见、但程度甚至更严重的暴力。托克维尔在很多地方都描述过后一种暴力,它存在于欧洲国家殖民统治的权力结构之中,而且往往以文明和启蒙为名。在1847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托克维尔说:仅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接触便导致前者对后者的压迫和贬低,文明人并不一定自觉地想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并不自知这一点。对欧洲人来说作为自由和财产的保证的行政法规和正义原则对野蛮人来说不啻于难以忍受的压迫[2](P144)。
这一评论与托克维尔先前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结尾处“居住在美国的三个种族”一章中所作的观察遥相呼应,在这里他用更多的笔墨分析了为什么欧洲殖民者所谓的自由社会对黑人和当地印度安人来说不亚于监狱。密尔为英帝国扩张政策辩护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帝国能为欧洲以外的人民带来文明和进步,而托克维尔的观察正好相反。托克维尔说:“你可以使轩人获得自由,但你无法使欧洲人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9](P398)在美国印地安人身上,这种权力支配的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欧洲人的存在成功使原本自由的印第安人低等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托克维尔在其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展示了某种程度的来自欧洲的文化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从来没有达到用“文明程度”来合法化帝国统治的程度。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一个将殖民统治看作欧洲人向外传播文明的途径的意识形态—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那里被广为接受,启蒙思想家如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认为欧洲以外的人在文化上较欧洲人更为低级,因此欧洲人有某种“责任”使他们在文明进阶的序列上取得进步[10](P269)。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对外扩张、帝国统治、甚至某些暴力的行为都在长远意义上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皮茨未能区分自由帝国主义思想家内部的这些重要的分歧。一方面,托克维尔不相信一个所谓“高级”的文明能“提升”所谓“低级”的文明;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绝对的普世主义与人的境况不相符合。他曾经严厉批评种族主义知识分子戈必诺(Arthur de Gobineau)①Melvin Richter,“Tocqueville on Algeria,”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25(3),1963,p.384.的观点,称其理论的实践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的重大挫折,如果不是彻底消失的话”[11](P298)。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对殖民地人民的共同体生活和文化存在有高度的敏感和同情心,这与皮茨对自由帝国主义的一般性描述有很大出入。那么,如果不是自由帝国主义的话,托克维尔支持帝国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答案应该在托克维尔自已的文字—而非某种潜藏的心理因素—中寻找。托克维尔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只不过这些表述在皮茨的分析中并没有获得重视。在1841年《论阿尔及利亚》一文的开头,托克维尔说道:我不认为法国可以认真地考虑离开阿尔及利亚。在世界的眼中,这一放弃将是我们的衰落的清晰表现。……如果法国从一个只有地域的自然阻力和些许野蛮部落反抗的事业中退出,在世人的眼中这将会是屈服于其无能和缺乏勇气。轻易地放弃已经获得的,选择平和地从原先的疆界退出,任何这样做的人无异于宣布其伟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从此明确地进入衰落时期[2](P59)。
皮茨与密尔都未能看出托克维尔在这里实际上更为现实考虑,而非为浪漫情绪左右。他们都强调托克维尔将军事荣誉与公民美德相关联时的“幼稚”,但他们未能意识到他将重点放在了别处。托克维尔关于帝国主义的文字大部分是关于海外殖民地的巩固如何能够增进法国的国家实力和地位,他非常清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现实的实力的话便很难有真正的荣耀。在这里,托克维尔展现的是一种典型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逻辑和政治家(statesman)式的思考。他说:“如果我们能将非洲海岸牢固并和平地控制在我们手中的话,我们在世界一般事务中的影响将会大大加强。”[2](P60)在十九世纪所谓“新帝国主义”时代中,欧洲国家之间对海外领地的争夺异常激烈,它们往往面临着两种可能性:参与到这场争夺中并尽力增强实力,或者被其他欧洲强国排挤出去。托克维尔非常了解这一情形,他也明确地表明,如果法国退出争夺,那么它将会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且他也很清楚这对非洲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说:“我很明白,非洲从此进入了文明世界的运动之中,并将永难离开。”[2](P61)
在《论阿尔及利亚》中,托克维尔列举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将有益于法国的两种方式。首先,法国将获得米尔斯克比尔港(port of Mers—el—kebir),该港位于迦太基对面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形成的海峡之首端。“这一地理位置明显扼制地中海的出口和入口,”从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法国可以获得第二个战略要地是阿尔及尔,在完成其基础建设后,这里有潜力成为非常重要的军事和商业港口。托克维尔说:“这两个地方在我们时代的政治海洋(指地中海—笔者注)之上,位于法国海岸对面,形成互相支持之势,它们将无疑大大增强法国国力。”托克维尔接着评论道,“同样确定的是,……如果这些地方不在我们手里,它们必将落入别的欧洲国家手里。”[2](P60)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托克维尔支持帝国主义的真实动机在于维持国际层面的权力平衡②另外,在其《回忆录》中,托克维尔还对1849年“东方问题”危机作出评论:当奥托曼帝国崩溃时,俄国从中获利即相当于法国受损,因为它将大大改变国家间权力的平衡。因此,“如果他们(俄国人)在本质上是想染指奥托曼帝国的领土,那么他们肯定是在要求一场全面的战争,因为我们虽然在最终的意义上是想要和平的,但我们绝不应在没拔过剑的情况任由康斯坦丁堡陷落。”Tocqueville,Recollections,trans.,George Lawrence,ed.,J.P.Mayer&A.P.Kerr,Garden city,N.Y.:Doubleday&Company,Inc.,1971,p.324.。作为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思想家,他认为法国应该成为一个强大但温和、负责任的帝国主义国家,否则的话它必将被其他欧洲强国排挤出有影响力的圈子之外,失去制衡其他强权的能力。而一旦此危险不再那么紧迫,法国并非不可以放弃阿尔及利亚。但在当时,在“(法国)好像正在沦为第二等级的国家,任由欧洲事务的控制权落入其他国家之手时”,它不能这么做。[2](P59)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法国的确放弃了阿尔及利亚,但这时殖民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这一“放弃”还是导致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结束,其原因不禁使人回想起托克维尔。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65年以类似托克维尔的口吻说道:“事实上,可以说第四共和国不是缺乏保卫阿尔及利亚的能力,而是缺乏放弃它的能力。法国需要一个足够强的政府以承担起‘放弃的英雄主义'。”[12](P1)
四、托克维尔和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将前一部分的内容看作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的“另一面”,这也是皮茨所未能看到的一面。通过将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与其帝国主义相对立,皮茨排除了托克维尔可能前后一致地同时支持这二者的可能性。这里仍有待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托克维尔是否符合皮茨所描述的那个“自由主义”?换句话说,我们仍需考察已被皮茨排除了的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与其自由观念之间存在“理论联系”的可能性。
皮茨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所有人都从自然那里获得指导其自身行为的智力,他们在只涉及其身的所有事务上不应该受他人的干涉,应该有权以其自身的意志规划其未来。”这一关于个人自由的观念显然与皮茨对自由主义传统的看法有关。个人“在只涉及其身的所有事务上不应该受他人的干涉”的原则与密尔著名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类似[6](P48);它也可以被追溯到洛克(John Locke)关于财产权先于国家,国家乃经由个人建立以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之设施的思想;它还可以使们想起霍布斯关于国家作为一个工具,其唯一的目的是保存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论述[13](P223)。在这一传统中,国家的角色被限制在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利益,任何对此目的的超越都被认为是危险的。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难免导致某种形式的普世主义,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人”是没有国界限制的。从这一角度看,皮茨认为托克维尔与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没有太大区别。皮茨引用威尔希的话来为自由主义作一简单的定义:
自由主义包含对某些个人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等)的承诺,对重商主义国家政策的反对,对王权——如果不是王制政府的话——的反对,以及社会同情心的包容性[4](P3)。
本文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托克维尔与这一自由主义传统的关系。事实上,托克维尔并没有将国家看作服务于个人利益的人造工具。相反,他给予了国家很多远超出“工具”以外的正面价值,这一点很清楚地体现在他对法国国家荣誉的强调中。在他关于帝国和殖民地的文字中,国家的“荣誉”和“伟大”是一个经常的话题。在前文提到的托克维尔给密尔的信中,他说:亲爱的密尔,我无需告诉你,威胁着如我们一般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最大病症是民情的逐渐衰弱、心性的堕落、品味的平庸化……。我们不能让这一民族轻易地养成牺牲他们认为崇高的事业以获取安逸、放弃伟大的事物而安于庸碌的习惯;这样做是不健康的:允许一个民族认为她在世界上的位置比现在更低,她要从祖先为其安排的位置上衰落下来,但她可以从建造铁路、和平地获取繁荣—不管这种和平是在什么条件下取得的—以及私人个体的福利中找到安慰[11](P150—151)。
显然,密尔并没有被他的朋友对国家荣誉的强调所打动,他认为工业、教育、道德和良好的治理要重要得多。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不那么愉快的通信似乎在曾是朋友关系的两人之间创造了一个难以弥合的鸿沟,他们的友谊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状态[14](P217—234)。
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对伟大和荣誉的热心与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倾向于将自由看作不同群体之间斗争的结果,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一种需要争取来的特权,而这种“争取”很多时候要通过战争来进行。这在马基雅维利那表现得很明显:在共和国内部,自由依赖于内部权力的互相冲突和制衡;对外,自由需要通过战争来保持共和国的地位和权力,防止共和国被他国征服从而跌入被奴役的境地。而这一机制不可避免地需要其公民具有充分的公共美德、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以及一定程度的国家荣誉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托克维尔更符合这一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而非现代自由主义传统。他和密尔之间的分隔也比许多评论家估计得要大,后者比前者要“现代”许多。
与此相关联,与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的是,托克维尔为权力本身也赋予了一些正面价值。我们在前文提到托克维尔支持帝国的主要原因是它能加强法国的国家力量,尤其是在与其他欧洲强国竞争之时。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是古典共和主义关于自由的永恒话题,也是托克维尔自由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对国家的权力和荣誉的强调相似,他曾激烈地批评七月王朝在处理对外事务时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习气。在其《回忆录》中,他说:资产阶级不仅成为社会的唯一指导者,而且是社会的培育者。……紧接着,政治激情遭遇了谷底,像是一种普遍性的萎缩,而与此同时公共财富却迅速增长。中产阶级特有的精神成为政府的一般精神,它支配着外交政策以及国内事务,……与人民或贵族的精神相结合,这种精神可能会创造奇迹,但仅其自身却只能创造一个没有美德和崇高感的政府。
以上这些例证皆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即托克维尔与传统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如何在现代民主社会实现和保存自由是托克维尔政治思考的核心主题。与身份不平等的贵族社会相比,现代民主社会中个人从传统社会组织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平等的个体。但同时,随着贵族阶层的消失和传统有机社会组织的瓦解,社会逐渐原子化,个人尽管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又是孤立和软弱的。托克维尔说,这样的社会很容易产生过度集中的权力,这种集中化的权力又很容易导致专制主义。在缺乏中间阶层以及积极的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国家往往成为社会的主人和庇护者,个人成为依赖于国家而存在的平庸的、软弱的原子式的个体,这一状况被托克维尔称为“新专制主义”[9](P867—872)。
因此,托克维尔说,人们只有参与到政治中去才能获得自由。通过这种参与,个人得以与其他人建立起联系,从而为其共同的命运而坚守。这种自由与政治参与及某种程度的自治之间关联非常典型地来自于共和主义的传统①从共和主义对托克维尔进行解读的文献,可参见Sheldon Wolin,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lds: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Bruce James Smith,Politics and Remembrance:Republican Themes in Machiavelli,Burke and Tocquevil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正因为此,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持续性地批评现代社会中的非政治化倾向,个人只关注其私人事务而不顾公共利益,决定共同体命运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机构手中,等等。托克维尔认为,与贵族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很容易被平庸的个人及其物质欲求所淹没,而某种程度的爱国主义则可以说是某种古代贵族精神在现代社会的代替品。[9](P268—270)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对政治共同体的情感联系需要明智的政治领导和恰当的政治体制来帮助维系。托克维尔举例说,美国的联邦体系通过“结合小共和国和大国家的优点”来完成这一点,各个自治的州相当于是一些小共和国,它们使得人们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可以培育出互相关联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这种共和精神,即一个自由民族的这种风气和习惯,就是这样先在各州产生和发展起来,而后又顺利地通行于全国。”[9](P182)而当时的法国人则严重缺乏政治生活和自治的习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法国可能是欧洲国家中政治生活最为缺乏的国家。[23](P109)
另一方面,避免现代社会中的集权主义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权力的互相制衡。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说:“我认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9](P289)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社会尤其需要一些所谓“中间组织”来聚集个人,形成一些能够与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形成制衡的局面,从而使自由得以保存,这正是他极力赞赏美国自由结社和地方自治精神的原因所在。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可以说继承了孟德斯鸠关于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思想。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托克维尔将此权力制衡的原则运用在了国际层面上。一国人民的自由不仅依赖于其国内状况,而且与国际状况有关。在小共和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中,托克维尔认为,虽然小共和国更容易培育出积极的公民精神,但大国可以保证其不受其他国家支配。“小国往往贫弱,不是因为它小,而是因为它弱。大国之所以繁荣,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强。”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从来没有为权力而支持权力。他说:“如果只有小国而无大国,人类无疑会更加自由和幸福。但是,不可能没有大国。”[9](P181)因此,托克维尔秉持的是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正如前文所述,这正是他支持帝国扩张的核心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在《托克维尔、列贝尔和白芝浩:自由主义面对世界》一书中,大卫·克林顿(David Clinton)用托克维尔的帝国立场来说明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何理解国际政治,他正确地指出了托克维尔对国家及其荣誉的重视,国家为了保证公民对其的忠诚和情感上的向心力,因而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但很成问题的是,他认为托克维尔所强调的“公民美德”指向一种“更高级”的道德。在托克维尔那里,政治和道德有很清楚界限,这一点显然并没有为克林顿所重视。我们当然可以选择相信托克维尔原意促进国际社会中的“道德责任”以及“自由和有荣誉感的行为准则”,但他所强调的权力之间的制衡并不一定能被归入道德话语中,甚至不可避免地包含强制和暴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既不是虚伪地以普世性价值自证合法性的“自由帝国主义”,也不是毫无原则地将本民族的重要性抬高到所有其他民族之上的自我迷惑的民族主义。我们在其对帝国的辩护中找到的最主要是“国家理由”(Raison d'Etat)这一共和主义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共和主义式的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强大并不矛盾。用邓肯·贝尔(Duncan Bell)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共和主义式的帝国主义”(republican imperialism)[16](P178)。
五、结语
托克维尔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热心支持似乎在托克维尔的研究领域创造了相当大程度的疑惑甚至愤怒,如同我们突然在一个自由主义的、和平和人道的托克维尔身上发现了“另一个”不道德的、暴力的和帝国主义倾向的托克维尔。然而,我们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考察托克维尔“另一面”,他可能并不如我们一般预设的那样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自由概念也并不一定与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自由概念那样与国家的权力和荣誉相冲突。当皮茨评论说托克维尔思想中的这一矛盾不可能有一个理论上的解决办法时,她暗示的是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多少为其自由主义思想涂上了污点,她也因此倾向于用一种非理性的民族情绪来解决这一矛盾。但显然,在这样的解释中,托克维尔对自由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洞见便被掩没,而这一洞见却是其整体政治思想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1]Alexis de Tocqueville.Oeuvres Complètes[M].Paris:Gallimard,1962.
[2]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M]. Ed.&trans.,Jennifer Pitts.Baltimore&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3]Melvin Richter.“Tocqueville on Algeria”[J].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25,No.3,1963.
[4]Jennifer Pitts.A Turn to Empire: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M].Princeton&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5]Cheryl B.Welch.“Colonial Violence and the Rhetoric of Evasion:Tocqueville on Algeria”[J].Political Theory,Vol. 31,No.2,2003.
[6]John Stuart Mill.The Spirit of the Age,On Liberty,The Subjection of Women[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1996.
[7]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and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M].Ed.,R.B.McCallum.Oxford:Basil Backwell,1946.
[8]Jennifer Pitts.“Empire and Democracy:Tocqueville and the Algeria Question”[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8,No.3,2000.
[9]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0]Marquis de Condorcet.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Historique de l'Esprit Humain[M].Paris:GF Flammarion,1988.
[11]Alexis de Tocqueville.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M].Trans.,JamesToupin&RogerBoesche.Ed.,Roger Boesche.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12]Raymond Aron.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M].Paris:?Gallimard,1965.
[13]Thomas Hobbes.Leviathan[M].London:Penguin Books,1985.
[14]H.O.Pappe.“Mill and Tocqueville”[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25,No.2,1964.
[1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6]Duncan Bell.“Republican Imperialism:J.A.Froude and the Virtue of Empire”[J].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XXX,No.1,2009.
(责任编辑刘强)
D066
A
1671-0681(2015)02-0004-08
段德敏,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讲师,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系社会与政治哲学中心研究员,博士学位。
2014-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