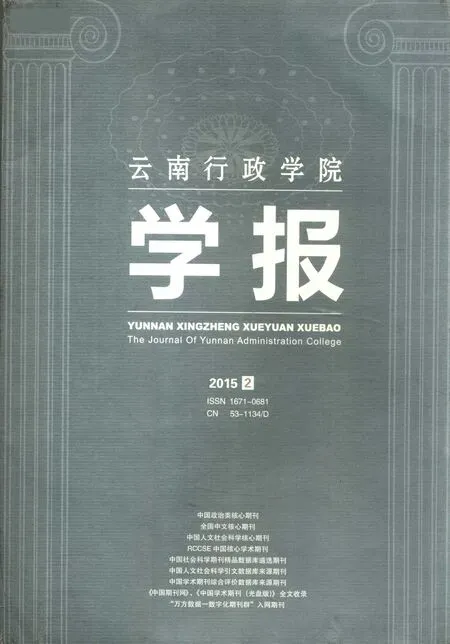“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马光选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科社教研部,云南 昆明, 650111)
当各种社会风险来临的时候,在个体自身不足以应对的情势下,我们往往寄希望于寻求到国家和政府的保护与庇佑而获取安全,但却发现一些奇怪的事实: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恰恰是大规模现代化战争的频发过程,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期恰好与现代国家的生发和成长期重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在现代国家的主持下被创造出来,并应用于人类社会,比如在现代国家我们拥有了足以杀死整个人类几十次的核武器装备;恐怖袭击、社会冲突、食品安全风险和环境污染等其他风险类型也都是在现代国家阶段大量生发出来,于是贝克等人更为直接地将现代国家高速发展的这一历史阶段命名为“风险社会”。
我们会发现国家的介入,不但没有使社会风险减少,反而使社会风险越来越多,那么这种现代国家与“风险社会”重叠出现是历史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现代国家在风险的治理与风险制造中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呢?其实,在人类面对利益生产和分配领域的“社会失灵”时,也曾经寻求过政府和国家的介入,但是却意外陷入了“政府失灵”的泥潭难以自拔,并造成国家在利益领域的治理悖论——“诺斯悖论”的产生。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现代国家与“风险社会”重叠的奇怪现象解读为:在风险治理领域也同样存在一种“政府失灵”和国家治理悖论。这些都将是本文意图深入探讨的命题。
下面我们将尝试从风险政治学的视角出发,以风险权势理论为分析框架,以风险分配正义原理为阐释工具展开剖析。
一、社会失灵与国家救赎
现有国家理论中盛行着一种“工具论”,认为国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社会自身存在着一种不完善的“社会失灵”状况,无法自我维持,所以需要国家的介入,以弥补这种不完善。反之,如果当社会能够完全自我治理的情况下,则国家的存在就成了累赘,也就是说国家自身并没有天然存在的价值,其之所以必要只在于其能对社会进行救赎。
从国家所能承担救赎职能的强度,可以将之划分为全面救赎、有限救赎、最弱意义救赎和暴力救赎等四种类型:
(一)全面救赎论
持论者认为人类社会混乱不堪,完全无法自我维持,针对这种“社会失灵”状况需要国家和政府出面维护社会秩序。正是因为人类自身秩序维护能力的匮乏,所以要将所有权力上交给国家和政府,从而形成一个无所不能,包打一切的全能政府。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其中典型。他认为首先存在一个“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危险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总想着“用武力或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1]而国家要阻止这种“人与人的战争”,就要存在“这种东西便是使大家畏服、并指导其行动以谋求共同利益的共同权力 ”[1],也就是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对社会不完善状态进行改进和救赎。
表面上霍布斯在看到对社会“国家救赎”的一面的同时,也看到了“国家失灵”的一面,但是,他认为抱怨主权者侵害自己的人,都是在抱怨自己,因为是自己将所有权力授权给了国家,这在实质上演变为在为政府绝对权力辩护。他没有看到,如果君主的权力失去监督,那么权力膨胀、权力滥用势必发生,国家权力会成长为一个人造的危害源头,同样也会对社会造成新的威胁。所以霍布斯意图通过“国家救赎”来拯救“社会失灵”的设想注定造成更为严重的“国家失灵”和“社会失灵”,人们在趋利避害的行动追求之后,却意外地面临更大的危害。
(二)有限救赎论
持论者如约翰·洛克等对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的预设并不像霍布斯那样不堪,他们认为先天存在的自然法是人们自觉遵守的、并无明文记述的理性规则,它可以约束人们不去侵害其他社会成员,但是人类社会也是存在一定缺陷,无确定性的规则来调节人们之间产生的纠纷,因此需要政府出面进行调节,以克服这些缺陷。洛克第一取向是“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2],并非霍布斯所关注的生存和和平问题。从洛克的国家观开始已经可以看到其对“政府失灵”甚至是“政府暴政”有了一定的觉察,但是他对暴政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暴政便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力,不是为了处在这种权力之下的人们谋福利,而是为了获取他自己私人的单独利益”[2],仅仅把暴政理解为“利益”的独占和国家权力公共性的丧失方面,并没有理解其“风险”的一面。
不得不说,洛克比霍布斯进步了很多,他至少对政府有一定的警惕,将政府也约束在与民众共同缔结的契约之下,这就有利于提醒人们防范政府的危害性行为。
(三)最弱意义救赎
诺齐克等人在个人权利优先原则之下,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超出纯粹保护个人基本权利范围以外的活动程度,通常要求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得到允准”[3],国家是“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较有限功能的国家”[4]。也就是说,面对社会失灵,国家的救赎职能只能像“守夜人”一样,实施消极的“防御性”职能,而不能主动出击干预社会生活。
这种观点主要是在与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观进行对话,似乎在最大程度上提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意见,但是其指向仍然是针对正面价值——权利和利益,而对社会的负面价值——风险问题缺乏必要的认知。不过这也不能过度的苛求诺齐克等人,因为他们的关注点是放在对新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导致的利益方面的“政府失灵”上面,风险领域中的“政府失灵”问题自然不会在其关注范围之内。
(四)暴力救赎论
新制度主义的国家观则更为直接地认为,政府的所有职能都在于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不管是契约履行,保护产权,货币供给还是安全提供,都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促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国家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为统治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个所有权结构;另一个目标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内降低交易费用,以便促进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5],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国家的经济理性,租金最大化诉求往往会掩盖社会产出最大化诉求,导致社会产出被抑制,第一次最为彻底的揭示了国家在面对利益领域的“社会失灵”时矛盾及其冲突的根源。
新制度主义国家观已经认识到利益领域的“国家失灵”问题,并深刻揭露出其中的本质规律——“诺斯悖论”的存在,“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5]。不仅如此,更为值得称道的是,与前面几种观点完全不同的是,新制度主义者对政府在风险领域的社会失灵已经开始有所觉察,诺思认为国家的这种制度安排的特点是它在暴力方面体现出的比较优势:第一,国家是对付非法暴力的合法暴力,这种合法性体现在对社会成员利益的捍卫和对别人侵害行为的抵御。第二,国家这种制度安排只有在能够促进社会利益优化,并且比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时,才被采用。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继续对这种国家合法暴力所形成的“合法危害能力”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危害进行认知,并对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本质规律展开探究,从而也就对国家在风险治理领域的治理悖论无法觉察。
可以看出,不管是现有是哪一种国家理论,无疑都认为国家可以有效地对利益生产和分配领域的“社会失灵”进行一定的救赎,也都认为国家在利益领域确实存在“政府失灵”的内在矛盾规律和治理悖论,但是却对国家在“风险”领域也存在失灵可能的本质规律缺乏深入思考。
二、风险矛盾与风险悖论
风险作为一种负面价值,其生产和分配过程和作为正面价值的利益完全不一样,所以不管是利益生产领域的“市场失灵”和利益分配领域的“社会失灵”,都无法直接应用到风险领域。那么对风险领域中的各种失灵现象的该如何认知和阐释呢?国家在风险治理领域的失灵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其背后是什么样的规律在起支配作用?本文认为国家在风险治理中出现“国家失灵”,进而导致“风险悖论”的产生,是与国家在风险治理方面内在的四对矛盾息息相关。
现有国家理论中,国家是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保护着国民的安全,但是这种安全是靠国家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实现的,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已。现代国家为了保证国民不受侵害,通过强大的暴力垄断能力,将民众和其他组织手中拥有的暴力手段进行集中,实现社会层面暴力的空白化,也就使自己成为领土范围内最为强大的暴力拥有者,可以实施对整个社会其他暴力行为的威慑和打击。而现有研究没有觉察到的是,国家不仅仅实现着对国内暴力的垄断,更是在知识领域和财富领域等都拥有着绝对优势,这样以来,国家不仅仅是吉登斯意义上的“权力的集装箱”或者“暴力集装箱”,也成为风险政治学意义上“风险的集装箱”,即成为最强势的风险制造者和分配者,对此下文将会具体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一)风险矛盾
国家之所以成为“风险集装箱”是与国家在风险治理方面内在的四大矛盾相关:
1.国家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与民众低下的自我保护能力之间的矛盾。国家因为具有强大的风险制造、施加和分配能力,在国民风险制造和分配能力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对国家的约束和制约能力匮乏。这种风险制造能力失衡的情势下,当国家将矛头朝向国民的时候,面对强势的国家,国民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从而使民众陷入一种高度风险状态。具体而言,现代国家制度之下,暴力的垄断,财富权利的界定和知识的生产与评价方面,国家都拥有极强的建构和自主能力,这就使得现代国家拥有更多的“合法危害能力”,任何国家对民众的危害行为都可能经过现代国家以国家名义合法化,而任何民众给国家施加风险的行为或者维护自身安全行为都可以被以非法名义打击,民众在“非法”与“合法”的夹缝中饱尝风险折磨。
2.风险事件的突发性与国家保护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以暴力风险为例,国家作为安全供给者,其供给能力的提升是需要一定的资源和技术作为支撑,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为条件。面对外来侵略,如果组织得当,保障有力,国家可能取得胜利而保护国民安全。但是在和平环境下,面对恐怖主义和犯罪行为,他们就捉襟见肘了,和战争状态不一样的是,战争是“明刀明枪”,有备战的时间和明确的作战对象,但是恐怖主义等危险行为则具有高度隐秘性和突发性,以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的反应能力很难对此做出有效预警和及时反应,即使能做出反应,也往往具有滞后性,存在一定的空档期。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垄断暴力的情况下,形成社会层面的“暴力真空”状态,在国家救援无法及时跟进的情势下,当“手无寸铁”的民众,独自面对风险侵害时,只能“坐以待毙”。所以不管是美国 911事件,新疆 7·15事件,西藏 3·24事件,还是昆明3·01事件中,我们会发现在国家无法预警的情势下,暴力事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突然发生,国家机器的救援没能及时到场,而民众由于缺乏必要的应对能力,只能任人宰割。
3.风险治理方式的专业性与风险特征的综合性之间的矛盾。由于现代化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制度的存在,国家在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有限的情势下,在综合性风险认知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比如食品安全风险,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等风险方面,对风险的治理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才能完成,但是现代国家在治理机构设置上却只是体现了专业性,而没有体现出综合性,公共安全归公安部门治理,食品安全是食品药品检疫检验部门管理,环境问题是环保部门负责。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部门式治理方式就很难对综合性的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当然也可能会有联合执法的可能,但仅仅是各部门之间有序协调已经是个问题,联合执法的成效就更难被寄予厚望。
4.风险治理手段的集中性与风险分布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风险散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各个层面,但风险治理的权力却收归于国家手里,比如就地震的预测而言,现代国家并不比街头算卦者高明多少。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不管民间是否拥有比国家更为强的预测能力,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个人或组织发布相关信息,即便是地震发生后的救援,也需要国家的批准,其他社会救援力量才能进入现场。其他类型风险的判定和治理标准也往往是国家制定的标准为准,比如水污染指标,空气污染指标等等。这样以来,一方面,仅以国家之力在面对如此众多的风险时往往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国家却保持着对风险治理的垄断而不许其他力量插手,这就很容易造成当风险事件发生时,国家即使再尽力,民众依然不信任不买账局面的出现。
(二)风险悖论
受这四对矛盾的驱动,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过程中就演变为双重相悖角色:国家既是安全的供给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这种风险治理悖论的存在,在实践层面就体现为政府的风险治理能力的低下,甚至是国家对民众的“合法伤害”的增加,于是就出现了开篇提到的大大超出了人们对国家角色期待的情况:我们面对风险时,本来希望国家能提供安全感,但是却发现,当风险真正来临时,我们赖以依靠的国家失灵了,更为严重的是国家甚至沦为风险的制造者,这恐怕是任何社会成员都始料未及的局面。当然,这也是现代化发展到反思性阶段的必然结果,反思性现代化使得原来在现代化第一阶段出现的各种事物具有了更强的反思性,即不但对事物积极的一面有所认知,对事物消极的一面也有所体认,从而使得现代化发展更为全面。
三、风险悖论与风险政治
在利益领域,“市场失灵”被认为是“看不见的手”失灵,“政府失灵”被看作是“看得见的手”失灵;在风险领域,“社会失灵”被看作是“人与人的战争”状态,“政府失灵”可以被认为是“人与国家的战争”状态。这种“人与国家的战争”状态具体表现为“风险悖论”,即国家既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风险悖论的产生与风险矛盾息息相关,但是从根本上而言,风险矛盾和风险悖论都受风险权势的运行规律制约和支配。
(一)现代国家与风险权势
风险政治学认为,任何风险的产生都是风险强势群体运用风险权势制造和分配风险的政治过程,风险一旦被强势群体制造出来,就有可能被分配给风险弱势群体承受,从而造成风险分配不公现象的产生[6]。风险强势群体之所以具备强大的风险制造和分配能力,就在于其能够综合运用强制性风险权势、知识性风险权势和财富性风险权势等三种风险权势进行风险造势[7],现代国家作为现代社会中最为强大的风险权势主体,也就最多地拥有这三种风险权势,由此可见,不管是吉登斯的“权力集装箱”理论,还是诺斯的“暴力潜能”理论,都只是认识到了强制性风险权势的存在,而没有意识到其它风险权势的存在。实际上,从风险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是多种“风险权势的集装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个人或组织面对强大的国家体时,“人与国家的战争状态”才可能出现。
(二)风险权势与权势规律
风险权势的运行逻辑分为两种,一种是倾向性逻辑,其运行结果是风险分配的不正义;另一种是对称性逻辑,其运行结果是风险分配的公平正义[8]。正是因为现代国家成长为一个包罗多种风险权势风险集成体,在风险权势运行规律的支配下,现代国家就成为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风险制造者和分配者。在不同的风险权势主体间,由于势差的存在,强势群体总是倾向于将风险制造和分配给风险弱势群体,就造成风险权势按照倾向性逻辑运行,造成风险分配结果的不公平。但是,这种不公平的风险分配结构的存在缺乏稳定性,其总是趋向于向公平结构去发展和演变,这也就要求风险权势的运行逻辑由倾向性逻辑想对称性逻辑转变[9]。
现代国家风险治理悖论的产生,在最为根本层面是风险权势的倾向性运行逻辑的外化表征。现代国家作为最强大的风险权势综合主体,其拥有的强大风险权势和风险能力,使得其他任何风险主体都成为其风险客体。所以在表面上,现代国家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安全依靠,但是在更多时候,我们往往不但无法获益甚至深受其害。至此,现代国家就从神坛上走了下来,成为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这就可以从最为根本的层面来解答开篇提到的奇怪现象何以产生的缘由。但是倾向性逻辑具有的不正义性使得风险的分配结果不公平,这就要求我们实现风险权势逻辑向对称化逻辑转变,以便实现风险治理领域的公平正义,而其最为直接的方式是实现风险治理方式的转型。
(三)风险治理与治理转型
现代国家“风险治理悖论”的存在警示我们,国家是靠不住的,甚至是需要警惕和提防的。在风险治理方面,现代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同时也是最大的风险综合主体,这就要求我们的风险治理理念实现三个转型:专业性治理方式——综合性治理方式;代理性治理方式——自主性治理方式;集中性治理方式——分散性治理方式,以化解上面提到的四对风险矛盾。而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型根本上体现的是风险权势运行方式由倾向性方式向对称化方式的转变,意图在于实现风险治理的信息对称,结构对称和行为对称,从而提升风险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实现风险分配的正义与公平。
1.专业性治理方式——综合性治理方式。为了化解治理方式的专业化与风险特征的综合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风险治理方式由专业性治理和综合性治理转变。专业化治理是现代化社会大分工的一部分,正如前面分析过的那样,这种单一的专业化手段去解决综合性风险时会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我们看到当前的风险治理中大量的都是专业化治理,比如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诸多现代风险面前,就需要综合运用多种风险治理手段才能凑效;为了国家领土内的安全,对暴力手段的专业化控制就是其专业化治理的典型方式,当这种方式已然不能满足风险治理的需求时,就需要将实现专业化治理思维向综合性治理思维的转变。
2.代理性治理方式——自主性治理方式。为了克服风险生发的突发性与风险治理的滞后性之间矛盾,国家强大的风险制造能力与民众低下的自我保护能力之间的矛盾,有必要实现风险治理方式从代理性治理向自主性治理转型。就像在经济上回到“自给自足”方式一样,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安全负起责任,而不是将之交给其他专业性组织进行代理,因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现代国家主导的风险治理存在信息不对称,结构不对称和行为不对称等缺陷,其主导的代理性风险治理方式都可能存在滞后性和间接性,而风险事件的突发性和直接性特征都要求风险的承受者和治理者能保持信息对称、结构对称和行为对称,从而能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对风险事件做出回应,甚至能够提预警和提前预防,使风险消失于未发之时。
3.集中性治理方式——分散性治理方式。为了化解国家治理手段集中性与风险分布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风险治理方式由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现代国家通过强大的风险权势能力,将各类风险治理权力集中于自身,但是风险的分布并不会因国家风险权势的集中而集中,风险散布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以隐秘而突发的方式爆发出来,这就使得现有的集中化治理方式难以凑效,从而导致现代国家主导的风险治理成效难以令人满意。所以针对风险分布的分散化特征,风险治理方式在实现综合化和自主化的同时,也有必要走向分散化,以满足风险治理实践的需要,提高风险治理成效。
四、结语
总之,当人类社会面临风险的时候,现代国家可以承担起治理风险的部分职能,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将这一任务交给国家。因为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现代国家在面对风险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会成为风险的制造者。正是因为这一风险治理悖论的存在,基于为整个人类社会整体安全考虑,我们需要改变目前的风险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在国家的专业性治理方式、代理性治理方式和集中性治理方式无法满足需要的情况下,积极实现风险治理向综合性治理方式、自主性治理方式和分散性治理方式转变,从而满足日益严峻的风险治理实践的需要,同时也为实现风险治理领域的公平和正义而努力。
[1]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1.
[2]洛克.政府论(下卷)[M].商务印书馆,1983:52.
[3]彼彻姆.哲学的伦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44.
[4]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53.
[5]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1.
[6]项继权,马光选.政治风险与风险政治———风险的政治学研究传统及新范式建构[J].深圳大学学报,2012 ,(6):65-66 .
[7]项继权,马光选.风险政治学:研究视角与范式变迁[J].探索,2013,(4):54.
[8]项继权,马光选. 风险分配的制度正义[J].2013,(4):39.
[9]马光选,项继权.政治学视野中的风险研究传统及新范式探索[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4):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