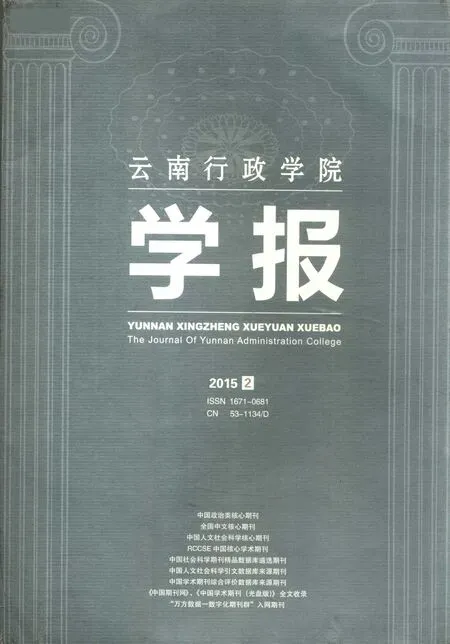西方生态民主主义中的三种论证策略及其限度
郝炜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西方生态民主主义中的三种论证策略及其限度
郝炜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在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环境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生态民主主义一方面认为环境与民主不存在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又试图构建环境与民主之间的桥梁,因而论证环境与民主的正向关系成为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为了达致这一目的,生态民主主义采取了三种策略,即比较优势策略、实用主义策略和内在兼容策略,但这些策略都未能有效地完成其使命。
生态政治;西方民主;多元价值;权利
一、问题的提出
民主能否应对环境挑战是当代生态政治理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生态权威主义和生态民主主义的分野,前者认为在环境问题面前民主制度本身无法承担改善的功能,非人类的自然利益与代际利益无法在民主体制中得到表达,个人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忽略环境利益,利益集团也有可能阻碍环境立法等等,以致R.赫尔布隆纳和W.奥弗尔斯强调在可怕的环境危机面前只有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是权威性的政府才能让人们接受应对措施。而且现实中应对环境问题最好的几个国家如“芬兰、德国、日本、挪威和瑞典都是强势政府,而作为主动推进生态现代化的一种结果,它们会变得更加强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生态权威主义质疑的只是工具意义上的民主,他们的所谓权威性政府、强势政府依然处于民主框架之中,他们的反民主面孔不是由权威这样的字眼装饰起来———因为民主政治也承认权威,而是由环境问题这一所谓“没有真正选择特征的绝对命令(imperative)”所决定的——因为在急迫的环境问题上结果优先于程序,所以安德鲁·多布森认为将R.赫尔布隆纳和W.奥弗尔斯视为生态权威主义者是“把反自由因素与反民主因素混淆了”,环境问题的绝对命令在多布森看来与自由主义的价值存在着矛盾,“自由主义者抗拒被告知思考什么和做什么。更为技术地,他们将他们感知的偏好视为其利益的精确指标,而且他们会说国家影响个人品味和偏好的企图缺乏根据”,自由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的张力体现了国家权威与个人自治之间的冲突,生态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侵犯了个人“生活中的发展和追求自身道德目标的自由”。因此,生态权威主义并不反对民主,或者说并不是真正情愿诉诸权威主义,而只是认为以代议制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民主不能有效应对环境危机,从而试图将权威主义嵌入自由主义民主之中。
与生态权威主义相反,生态民主主义认为尽管当前的民主模式可能无法有效应对环境挑战,然而不能就此得出权威主义的结论,仍然应当坚持采用民主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需要论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而不是要不要民主。尽管大多数的生态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与环境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如泰伦斯·鲍尔所指出:“对自然环境的承诺与对民主的承诺在逻辑和概念上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人能够是‘绿色的'却同时以哲学的或战略的理由反对民主。反之,一个人当然也能够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而无需非常同情——如果有的话——自然环境和自然的种种生物。”然而他们坚信环境危机不是摧毁民主的飓风,却是增进民主的契机。
在西方政治文化里,对于民主的反思和批判一直是一项重要内容,而且西方的民主理论作为一种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本身充满着分歧,民主理论家们也从来都不认为哪一种民主是完美的,民主与环境之间的张力只不过是为反思民主提供了一种新的论据而已。所以,在西方语境中,生态权威主义和生态民主主义都是通过环境问题透视民主的方式,所不同的是只有生态民主主义试图打通环境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就目前而言,这种努力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论证策略。
二、比较优势策略
比较优势策略的逻辑在于论证应对环境挑战的民主制度优于非民主制度。这一策略巧妙地将环境与民主之间的张力转化为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对抗,只要成功论证在环境挑战面前民主制度能够比非民主制度做得更好,就能为选择民主提供理由。这一论证策略看似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从论证逻辑上看,这一策略存在着诸多漏洞。
首先,应当说比较优势策略比较明确地指出了民主本身具备的一些成功之处,相对而言,民主在个人权利、市场经济、信息公开和政治开明等方面的确有所进步,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制度安排,民主似乎都能够发挥一种示范效应,以至于“那些在其他哲学观点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人都同样颂扬它。”[1](P1)但是证明民主具有相对进步性并不意味着民主能够成功应对环境挑战,意识形态上的胜利不能代表应对环境问题的实践上的胜利,制度安排的相对合理也并不意味着必然能够有效应对环境问题,因为在环境危机面前,生态权威主义也可以表现出生态民主所不具备的好处。因此,比较优势策略只能够支持作为一种修辞的民主,而不具有论证的方法论意义。
其次,比较优势策略仅仅着眼于民主本身相对的价值优势层面,而不能深究民主制度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表明在环境危机面前民主比非民主做得相对较好,而未能看到环境危机带给民主的巨大挑战,因而其视野是回溯的而非展望的,其比较是横向的而非纵向的。事实上,正如马努斯·I.米德拉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假定民主与环境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存在着深层次的困难。”[2](P344)比较优势策略的论证忽略了实际决策过程中立法机构与执行机构的粗糙,企业和环境团体之间的争斗导致的环境决策的真空,作为预算约束的结果民主可能更重视大部分选民的经济生计(economic sustenance)而非环境命令(environmental imperatives)。此外,民主国家中潜在的如富人和穷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以及环境议题全球化所呈现出的困难都与比较优势策略的民主理想有所差距。[2](P344-345)
最后,两篇文章都通过实证方法测量了民主层次(level of deomcracy)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水污染、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等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努斯·I.米德拉斯基的结论却是“森林砍伐、二氧化碳排放和水土流失显示出民主与环境保护之间值得注意的负向关系。”[2](P358)而李全和拉斐尔·鲁文尼的结论却是“较高层次的民主导致较少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较少的人均氮氧化物排放,较少的水源有机物污染、较低的森林砍伐率,以及较少的土地退化。”但后者同时指出这种结果的出现是因为民主国家能够更好地减少直接使环境退化的人类的活动的范围,而且民主化会由于国民收入的影响而可能促进环境退化[2](P953)。所以二者的结论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总之,比较优势策略在学理上是失败的,它既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结论,也无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正如J.唐纳德·穆恩的评论:这种论证“不能说明自由民主能够应对短缺。它们所能说明的只是相信另有他者的那些通常先进的理由无法经受严格的审查。”[3](P399)
三、实用主义策略
实用主义策略论证的前提是将民主视为一种操作手段,它依赖于真实存在的权力、机构和制度安排,而将环境问题视为一项公共事务,它首先要转化为一种政策议题,继而成为一种公共政策,然后交由政府执行,最终产生绿色政策结果。实用主义策略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这一过程更加民主化。正如约翰·德雷泽克指出行动中的民主实用主义“不是要把问题解决从行政机构中移走并把它交给代议制制度诸如立法机关;相反,这是一个使行政机构本身更加民主的问题”[4](P114)。她进一步列举了民主实用主义的六种政策工具,即公众咨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政策对话、非专业公民审议、公众质询以及知情权立法[4](P115-122)。这些政策工具的直接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政府机构内外互动的民主行政模式,旨在通过民主的方式使政策制定获得合法性,而并未着眼于环境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其基本的政治框架依然是行政国家。因此她评论说:“资本主义民主制框架下的政治,很少是关于无私的和有公德心的难题解决,其中许多不同的观点得到同等程度的尊重和对待。”[4](P131)所以,无论从动机还是能力方面看,当前存在的民主在现实操作中往往为利益集团所操纵而沦为达尔(R·Dahl)所说的“多头政体”,作为其构成主体的多元体即各种类政府组织、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是现实民主的主角,并非自由主义眼中的个人,多头政体的固化政治不平等、扭曲公民意识、歪曲公共议程和让渡最终控制等弊端使得这一现实存在的民主偏离了民主理想[5](P33-44)。因此,如果实用主义策略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的话,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退回到与生态权威主义的较量当中,从而重蹈比较优势策略的失败。
实用主义策略的出路在于回答何种民主或当前的民主如何改进方能应对环境挑战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既要求检视当前的自由主义民主与环境危机之间的张力,以要求论证如何改进或重塑自由主义民主。西方理论界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可谓汗牛充栋,实用主义策略的论证在这一方面并未添加任何新的理论内容,更多的意义在于从环境与民主的关系角度重申或强化了业已存在的论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民主的直接性和间接性的争论。众所周知,当代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民主是以代议制为基本内容的,撇开对代议制民主的卢梭式评论,自由主义民主在生态主义者看来首先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德雷泽克指出横亘两千五百年并出现在许多变体之中的民主与其立足的自由主义没有别的东西,唯有人类中心主义。在这一前提下,她指出:“自由主义民主的成员当然可能选择颁布环境保护的积极措施,例如通过保证自然客体的合法权利。那些客体的守护者可能进而提出政治和法律体系上的要求。但是自然客体的任何这种地位都可能简单地使自然降级为另一套价值,并通过将它们分配到可识别的自然客体以分解和孤立这些利益,从而忽略它们固有的生态的(内在联系的)特征。”[6](P147)在这里自由主义民主遭遇到来自生态主义的政治伦理深度的质疑,并进而带来代议制民主在操作上的人类中心主义难题,即利益表达和讨价还价的主体都是具有表达能力的人类,而且就算是人类也存在代际表达的难题,即未出生的下一代也无法参与到民主过程中来,而且当代的人类也无法获知未来人类的偏好。
对此,泰伦斯·鲍尔的回应饶有趣味,他首先给出了对利益的理解,即“如果X对于A的运行和/或兴旺是必需的和/或有帮助的,那么X就属于A的利益。”就像人体的运行需要锌一样,这种需要和利益不依赖于主观认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我的无知不能妨碍我拥有利益”,因此“对于我们将利益归于A来说,A无需是活着的和在场的”。所以对于非人类的动物以及后代,他说:“我们未必能有一种积极的或‘厚重的'责任去帮助他们;但至少我们有一种消极的或‘单薄的'责任去避免伤害他们。”[7](P137-138)如此一来,民主渡过了人类中心主义谴责的第一关,那么民主又如何应对操作上的难题呢?鲍尔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受到影响的非人类自然与人类后代无法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聚集起来就共同事务进行讨论、辩论和决定,那么绿色民主(green democracy)或生物民主(biocracy)就不可能是直接的或参与的,而应是间接的和代表的。由于需要和利益是客观的,其载体不需要出席,所以“此类生物和实体的利益理所当然地必须由具有声音和代理机构的人类来代表”[7](P140)。当然,作为代理机构的人类必须通过注意身体语言和其他非语言线索来“倾听(listening for)”来达到与非人类的自然实体和人类后代的沟通,这就要求包括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在内的某种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的方式,从而实现一种生物民主的公民品格,即“对更大和更包容的生物共同体的贡献的而非索取的”公民品格[7](P143)。实用主义策略对自由主义民主的重新理论化,或者说努力探索民主的变体,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具有新鲜感,绿色民主、生物民主之类的概念也使得民主理论变得更为复杂。
实用主义策略大都站在比较优势策略的肩膀之上,坚持应对环境危机的民主途径,无论是通过行政机构的民主化以达到环境立法的结果,还是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的重新阐释以达到对民主的再理论化,从而顺应环境要求,都认为民主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力工具,事实上,这两种进路在多布森看来是属于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与生态主义(ecologism)的区别,他指出:“环境主义主张对于环境问题的管理性方法,坚信环境问题无需现存价值或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改变就能够解决。生态主义主张一个可持续的和完满的存在以我们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激进变迁为先决条件。所以政府的部长们不会由于将他们的豪华轿车换成混合动力车就摇身一变为政治生态主义者。”[8](P2-3)因此,环境主义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策略往往容易与产生生态权威主义的论证相似的理路,也就是德雷泽克所评论的那样,民主实用主义常常是“行政理性主义的危机的补救”[4](P114)。最后,这一民主被“理解为一种为了受影响者的民主,而不是由受影响者构成的民主。”[9](P2)其次,实用主义策略的第二种进路,即寻求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改造,或者按多布森的提法即生态主义的理路,其最终依靠的路径往往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造,这种策略最后必然诉诸卢梭式的人性改造,而这一方式常被视为一种内含“最高立法者”要素的极权主义暗示[8](P102)。
总之,实用主义策略也未能在环境与民主之间搭建起一座安全的桥梁。
四、内在兼容策略
内在兼容策略侧重于从价值层面进行推导,力图挖掘民主与环境二者的内在相容性,与上述两种策略不同,内在兼容策略更多地关注到民主与环境的价值要求,从而使二者在本质上充分兼容,而不是停留在一种权宜之计或工具理性的层次。当然,正因为如此,内在兼容策略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理论难度,这不仅要像多布森所指出的那样,对生态主义的所有可能类型和民主的所有可能类型之间进行系统性评估[8](P113),而且要尽可能详细地分别罗列出环境价值与民主价值,并对这些价值之间的兼容性进行论证,这显然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不可能终结的任务。但是,幸运的是,内在兼容策略作为一种论证逻辑总是成立的,因而从部分已有论证中窥其一斑尚属可能。
其中,迈克尔·萨沃德的观点旗帜鲜明,他认为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是“民主的逻辑要求”,同时又是“在民主和竞争的价值之间进行合理权衡的基础”[10](P77-78)。就环境主义为何是民主的逻辑要求这一问题,他首先对民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民主的最佳定义是:在政府行为和关于那些行为的公民意愿的同等权重的表达之间应有必要的一致。”[10](P80)而民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赖于基本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结社和信仰等方面的基本自由、选举和担任公职的平等权利、信息自由、充分的上诉和救济机制、充分获知特定政策程序和结果的权利、充分的教育和卫生保健(health care rights)的权利,等等。在这里,最为直接地与环境危机相关联的正是卫生保健权,如果民主充分地遵循回应性原则,那么民主就必须对公民的卫生保健权给予充分的尊重。而卫生保健权属于一种积极权利,它要求民主采取一种预防性原则,因此,“一贯的民主主义者将会防止对公民的环境危害,并会承认一种绿色民主权利之类的事物。那种认为民主是一种手段而环境主义是一种结果的理念瓦解了;环境目标成为以民主手段达致民主结果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0](P85)当然,通过权利打通民主与环境价值兼容性的尝试首先避免了将权利变成一种修辞,将形而上的权利话语具体化为可被感知的权利行为,从而赋予公民更多的角色。其次,这一尝试能够为更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权利进入宪法开启了大门,这一点至关重要。萨沃德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个困扰着内在兼容策略的难题,即前面提到的生态主义的绿色命令与民主之间的冲突,或者说绿色命令的不容选择性与民主的妥协性之间的矛盾,对此,萨沃德认为民主在许多情况下都在处理着绝对命令,这些绝对命令来自经济、政治、社会、地理和宗教等等不同的领域,正是这些绝对命令使得民主拥有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能够使这些不同的绝对命令和谐共生[3](P64-65)。更进一步,既然这里存在着一个价值体系,那么多元价值之间必然充满着竞争,即哪些价值具有优先性,整体主义并不能回答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提出恰恰是因为事实上民主主义者往往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优先价值,所以由此看来民主与环境价值之间也必然存在着竞争,而不是天然的相容。因此萨沃德认为由于民主遵循回应性原则,回应性原则必然要求对其它价值的要求给予充分地尊重,这样,包括环境价值在内的其他价值就成为民主的限制性因素,一个政府越是民主,其他价值就越有可能产生结果。所以,在多元价值体系中,民主价值实际上被其他价值稀释了[10](P89-90)。由此可见,萨沃德的逻辑是将民主理解为回应性原则,而且有一种民主权利是充分的卫生保健权,并且在这一权利内部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环境问题,而民主本身并非社会中的第一美德,但它能够意识到需要被充分而明确地证明为正当的民主目标,所以他的结论是民主主义者一定是环境主义者。
但是,罗宾·艾克斯利却认为那种认为生态中心价值和民主能够通过自治原则的扩展和包含生态利益的权利话语联系起来的观念,即从自治到权利再到生态基础上的民主的推进存在着诸多障碍。自由主义的自治观念意味着人类选择自身命运的权利,这一观念假设个人是其自身偏好的唯一判断者,而民主能够将这些偏好进行归纳,但是这种权利观念无法成功扩展到非人类的自然身上,而只能根据密尔的“免于伤害的自由”进行转化,从而使民主建立在一种功利主义而非义务论的哲学基础之上。这使得生态中心主义的民主将招募更多的支持者,包括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环境运动,绿党以及诸如科学家和官僚的知识型社群的成员,但也因此而遭到更多的质疑[12](P167-194)。
由此可见,内在兼容策略要比前述两种策略更为有力,但也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这不仅关涉到穷尽民主价值和环境价值内容的难题,而且还陷入了价值多元主义这一现实和理论的困境,个人利益通过诉诸洛克的明白同意或默认同意以及多数同意或一致同意,都无法为政治正当性提供有效论证,这种有效论证同样也无法从功利主义对个人幸福的计算而实现,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片面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义务,那么人们将难以形成共识,社会就无法实现有效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会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只有强调权利的同时肯定个人对他人和社会负有义务才有可能使多元化的利益达成妥协,从而实现共赢。所以,内在兼容策略事实上选择了一条更为坎坷的道路,但要想在环境与民主之间建构起可靠的桥梁,这是一条无法回避必由之路,这也是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的创新之路。
[1]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Manus I.Midlarsky.Democracy and the Environment:An Empirical Assessment[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35,No.3,1998:341-361.
[3]J.Donald Moon.Can Liberal Democracy Cope with Scarcity?[J].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4,No. 3,1983:385-400.
[4]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M].蔺雪春,郭晨星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5]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M].周军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6]John S.Dryzek.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Liberals,Critics,Contestati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7]Terence Ball.Democracy[A].In Andrew Dobson and Robyn Eckersley(eds).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 131-147.
[8]Andrew Dobson.Green political thought(4th ed.)[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2007.
[9]罗宾·艾克斯利.生态民主的挑战性意蕴[J].郇庆治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14.
[10]Michael Saward.Must Democrats Be Environmentalists?[A]. In Brian Doherty and Marius de Geus(eds.).Democracy and Green Political Thought[C].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6.pp.77-94.
[11]Michael Saward.Green democracy?[A],In Andrew Dobson and Paul Lucardie(eds.).The Politics of Nature:Explorations in Green Political Theory[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p.63-80.
[12]Robyn Eckerley.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Rights of Nature:The Struggle for Inclusion[A].In Freya Mathews(ed.). Ecology and Democracy[C].London and Portland:Frank Cass,1996.pp.167-194.
(责任编辑刘强)
D082
A
1671-0681(2015)02-0012-05
郝炜(1982-),男,山西五台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12级博士,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2014-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