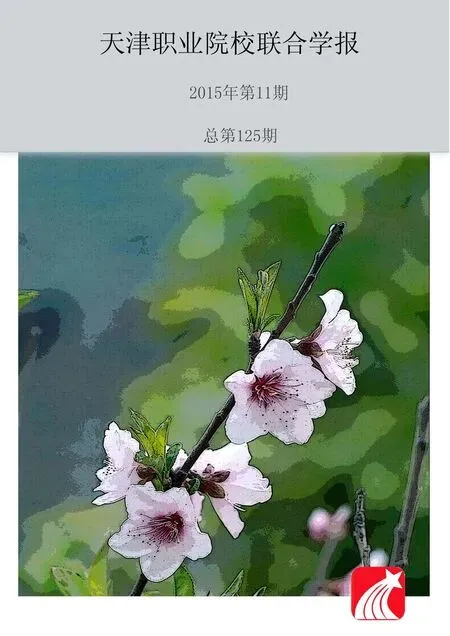论萧红《生死场》中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挣扎
王 远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天津 300350)
论萧红《生死场》中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挣扎
王 远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天津 300350)
萧红在《生死场》中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并通过对书中四位重点人物——王婆、赵三、金枝、二里半思想中民族意识的觉醒,指出穷苦农民传统意识中愚昧、落后的思想根源,以及在外族入侵的危难关头,普通民众思想中民族意识的一步步萌发,直至由个体民族意识的觉醒发展到群体民族意识的升华。
萧红;生死场;民族意识
著名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自诞生以来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一度在上海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鲁迅先生那句“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著名论断更为后世的研究者定下了评论的基调。在胡风的建议下小说将原名《麦场》改为《生死场》,使原有田园般的名称得到升华,更加切入作品所要表现的内核,同时在后记中他还强调了农民在民族战争中的觉醒和反抗,从而直接肯定了小说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死场》中第一次出现的民族意识可谓前所未有。民族意识兴起于二十世纪,在此之前,古代中国没有民族的概念,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 在“天下”观念的作用下,“中国”指的是王朝或文化,而不是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国家”指的其实是朝代,“亡国”真正的含义更多意味着“改朝换代”。直至十九世纪末,随着西方国家与中国的频繁接触,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逐渐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民族问题”开始成为历史要求,并且是以民族危机的方式提到日程上来。甚至直到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仍没有打破种族界限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鞑虏”是历史上中原人对北部少数民族的蔑称,他在这里仍利用了人们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激发民众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但后来的新三民主义,对民族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打响侵华战争的炮音,“中华民族”作为完整概念的民族意识得到强化,并空前高涨。
萧红作为东北沦陷区的作家对此有着切肤之痛,对国家存亡、民族危难的体验最为深刻。因此,在《生死场》中萧红凭借其女性特有的敏感体验,挺身代表、倾诉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异族入侵之际,广大农民民族意识由淡漠到觉醒的转变,以及由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的觉醒。
一、异族入侵之初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
作品中,特别是第十一回以后,作家只用了一句“静穆的村庄失去了心的平衡”来表述沦陷后人们心中的那份不安与躁动,并没有直接描写人们的正面反抗,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变化,表现出人们思想里越来越浓烈的民族情感和意识的萌发,这或许正是女性作家的特别之处:注意从个人的感受来分析民族意识的产生及其变化,从心理学和个体与群体心态及其互动的角度来研究民族意识与行为。
在侵略者最初到来的日子里,质朴的农民似乎也并没有想到反抗。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面对乡村一副破败的景象:秃田、残屋、弹坑和逐渐多起来的寡妇,他们有的只是愤恨和抱怨,抱怨“如今连个鸡毛也不能留,连个‘啼明’的公鸡也不让留下”,抱怨“今日的日子还不如昨日”。甚至在日本兵和中国警察进村捉女人的事情上也依然表现出惯有的麻木与冷漠,“王婆以为又是假装搜查到村中捉女人,于是她不想到什么恶劣的事情上去”,竟能够“安然地睡了”。
他们依旧按照他们习惯了的思维模式去思考、去生活。在自身家族利益没有受到侵害的时候,从不去想接下来的事情,甚至于带着几分“看客”的心理。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捉人的人中还有很多是中国人。
他们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在遭受外族的侵略,反倒为虎作伥,甘为走狗。这也正是中国人另一种奴性的体现。在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面前不团结,而是为了自身的那点儿既得利益甘愿屈身为奴,极尽谄媚之能事。
他们不为自己的同胞遭受的苦难和屈辱而感到痛惜、愤慨,反而从中收获乐趣“中国人都笑了!日本人也瞎笑……”他们一面讨好比自己强大的人,一面欺压比自己弱小的人,以保持自己在这个阶层中的地位。
但日本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农民的侵害,而是继续用“毒手努力毒化”着他们。他们四处宣传“王道”,甚至打出恢复“大清国”的旗号,以此减轻他们在统治异族过程中的阻力,要他们继续做日本人的 “忠臣、孝子、节妇”,妄图用这种套在人们头顶上几千年来的紧箍咒继续禁锢人们的思想,并打着为乡民清除匪害的旗号到处捉人。善良、老实的农民意想不到的——“女人”并且是“学生”——居然也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渐渐地,处于高压政策下的人们开始觉悟了,他们感到周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与日寇抗衡。随着日寇侵华的深入,这股“正相反的势力也增长着。”
二、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互动
根据思维认知的发展规律,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总是有先有后。一个事物的出现,不可能同时引起所有人的反应。同理,人们心底里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是有先有后。在《生死场》中萧红也为我们分别刻画了这样几组不同的人物,通过他们思想中民族意识的先后觉醒,体现出普通百姓心中那颗反抗外敌入侵、保卫自己家园的赤子之心。
1.王婆是《生死场》中一位比较独特的女性形象,她不同于普通的村妇,有胆有识,有一定的行动自主权,算是女人中比较有自主思想的一位,她在不堪忍受丈夫虐待的情况下,毅然带着两位年幼的孩子改嫁;她会使枪,这让有几分见识的赵三都感到惊讶又佩服;她还可以参与“他们男人”的事情。甚至在赵三组织镰刀会失败之后带有辱蔑性地说出“狗,到底不是狼。”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她的丈夫——赵三,更果敢更有主见。
她并不怕死,甚至因为儿子被杀而服毒。“死过一回”的王婆,再活过来时对很多事情都看淡了,经常自己一个人到河边钓鱼,似乎对很多从前她热衷的事情也不太上心。直到得知自己的女儿为了抗击日本人而死时,终于感受到了那种穿透肺腑的疼痛,这种切身的感觉使她不再是麻木,她一遍遍地追问黑胡子的人,自己女儿的死因。她被自己的女儿激励着,她(感觉到)“日本兵的刺刀会刺痛了自己。她好像觉得自己的遭遇要和女儿一样似的。”而这种疼痛也终于使她开始有了反抗的意识甚至是策略,她不再“把一些别人带来的小本子放在厨房里。有时她竟任意丢在席子下面……”她彻底地接受了抗战的思想。在得知女儿牺牲的消息后,她没有像北村的寡妇似的找人去拼命,更没有像得知儿子死讯后服毒自尽,而是接过女儿生前曾为抗击日寇所使用过的一支发亮的小枪。
这些行动上的变化都代表着王婆反抗思想的日益成熟,活着的意义不再是整日的麻木和漫无目的的空虚,而是有了更积极的意义。她甚至不再寄希望于男人身上,“那老头子说不定和小孩子似的”。
2.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是赵三。赵三此时的胡子不但白了而且稀疏,他不复壮年时的英勇,只能够依靠回忆年轻时的无畏往事来激起自己的意志,他借着酒劲儿漫无目的地散步到坟地,无话坐在那些死去的年轻时的伙伴中间,“蓦然念起那些死去的英勇的伙伴!留下活着的老的,只有悲愤而不能走险了”。此刻我们可以从中深刻地体会到他灵魂深处的无奈与痛苦。
当李青山再次召集人们商讨如何探寻活着的出路时,赵三革命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了,虽不能亲自走上战场,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的冷漠,而是鼓励自己的儿子和周围的年轻人去投身革命“你们年轻人应该有些胆量”“我老了,你们还年轻,你们去救国吧!”,他不断地向邻人们宣传“亡国,救国,义勇军,革命军”,并整日为自己的宣传成果而激动兴奋着。此处,作家并没有刻画如《八月的村庄》里铁鹰队长、陈柱这样一类的英雄人物。在那个“英雄”与“凡人”并存的时代里,萧红更侧重于对“凡人”的描写,通过对小人物的刻画更加真实地显现出普通民众对待重大历史事件时的态度。
一辈子敢当奴仆的老赵三在大敌当前,涉及到自身与国家的生死存亡之际,毅然地选择了为后者而牺牲:“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此时,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赵三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从前他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死了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一贯无知而愚昧的农民,一生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半步的寻常百姓,在民族危难之时,终于有了国家、民族的意识。
3.金枝是中国传统封建“夫权”统治下逆来顺受的角色体现,思想单纯,如果不是被外敌入侵打破了原有的生活轨迹,她也将会像周边生活的农村妇女一样,过上周而复始的普通生活。
原本自由恋爱的金枝,在传统礼教下饱受母亲和周围人群的非议,婚后也没有得到丈夫真正的爱,在遭遇了丈夫的抛弃、失女之痛后,金枝备受痛苦的折磨。此刻无依无靠的她,只好到城里去打工赚钱,缝缝补补,勉强维持生活。
但,就连这最基本的生存要求都要付出巨大代价。遭受凌辱后的金枝精神上受到巨大伤害,一气之下又返回家乡。她的母亲却是个见钱眼开的人,为她挣来钱而高兴,却不管她在城里所受的屈辱,劝她明天赶紧还回城里别误了挣钱的时间,简直就把她当做了赚钱的工具,从不考虑她的人格、尊严和个人的愿望。于是金枝失望了,但是已挨过蛇咬的她不敢外出,怕遇上更残忍无耻的小鬼子。走投无路的金枝本想远离尘世,出家当尼姑,然而,尼姑庵也早已经荒废,出家对于她都成了奢望。对生活彻底的绝望,终于迫使她在思想上有了觉醒,说出“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又说出“我恨中国人呢!”这样有见地的话。
就连一向有着男人一般见识的王婆也感到自己的学识不如金枝了。“从前恨男人”说明金枝作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现在恨小日本子”是在民族对抗中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最后的“我恨中国人”,是终于寻到了造成这一切恶果的根源——国人自身本体上的缺陷才导致了这一切苦难的发生,并由此产生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是作者通过金枝的口吻,表达出的对于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恨。民族意识通过金枝的切身体悟,经历了一个从朦胧到觉醒,从低级到高级的渐变过程。
4.二里半是觉醒最慢的一个。在村里所有人,包括寡妇们都在宣誓抗日的关键时刻,他不但没有盟誓,心里还时时刻刻惦念着那只老得不成样的山羊,并最终找来只公鸡换回了自己的山羊。并且对于亡国,他也没有表现出伤心的成分,为此老赵三用眼睛骂他:“你个老跛脚的东西,你,你不想活吗?……”但是,想在战争的洪流中苟且偷生的二里半不知道“危巢之下安有完卵”。终于在失妻丧子之后,这个头脑最顽固、曾经被所有人鄙视的人在失去了精神家园后也终于觉醒,依然拖着不健全的腿,跟着李青山加入了革命的队伍。临行前,他要亲手杀掉象征着他全部个人意识的山羊使自己再无牵挂。并且在路过老赵三的时候还说出:“你在这里坐着,我看你快要朽在这根木头上……”从中不难看出他革命的决心。这样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最后也被裹夹在历史的洪流中,使自己的命运连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他没有消沉而是选择了觉醒。维护民族的生存,即是维护个人的生存。普通的百姓虽不会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但他们却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的真谛。
个体意识的觉醒影响着群体意识的觉醒,群体意识的觉醒又反过来反应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平日里如行尸走肉般苟活的人们在此时不但表现出战争的决心,更表现出与敌人周旋的智慧。他们不再计较一己之私,而是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强大的敌人。平儿在素不相识的老乡家里被掩护起来躲过日本兵的追捕。李青山信任“革命军”有用,不再盲目地追随“红胡子”,并且认识到“(革命军)不胡乱干事,他们有纪律……”而不是开始时认为的那样“我才真知道人民革命军真是不行,要干人民革命军那就必得倒霉,他们尽是些‘洋学生’,上马还得用人抬上去……”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感觉到此时普通民众对革命的认识通过战争的洗礼,也由最初的蛮干转化为有组织、有纪律,同时更有效的抵抗。
此时的民族意识已经不止是民族成员的个体意识,而是在民族成员中具有普遍性或代表性的群体意识。虽然民族意识对民族社会存在的反映和认识是通过民族成员个体实现的,并通过民族成员个体具体反映和表现出来的,但单一个体的认识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民族意识。只有当这种认识上升为大多数人的认识,或者代表广泛具有和流行的趋向时才能称作民族意识。
[1]葛浩文.萧红评传[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2]郝庆军.论萧红小说的死亡主题[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02).
[3]季红真.萧红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4]姜志军.萧红《生死场》艺术手法新探[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02).
[5]李茂增,温华.战争叙事与民族国家想象[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04).
[6]李向辉.“生死场”的现代书写——萧红新论[D].兰州:兰州大学,2007.
[7]李宇梁.民族意识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D].湖南大学,2010.
[8]周鹏飞.萧红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Discussion on Awakening and Struggl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Xiao Hong’sTheFieldofLifeandDeath
WANG Yuan
(TianjinCollegeofCommerce,Tianjin, 300350)
InTheFieldofLifeandDeath, Xiao Hong showed strong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by telling the four key figures’ aw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cluding Mother Wang, Chao San, Golden Bough and Two-and-a-half Li, Xiao Hong pointed out ignorant and backward ideological origin in poor presents’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S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germinated gradually in the thought of common people at the critical moment of foreign invasion and then the awakening of individual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volved into the sublimation of group national consciousness.
Xiao Hong;TheFieldofLifeandDeat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2015-09-27
王远(1980-),女,天津市人,天津商务职业学院编辑。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方面的研究。
I207.42
A
1673-582X(2015)11-0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