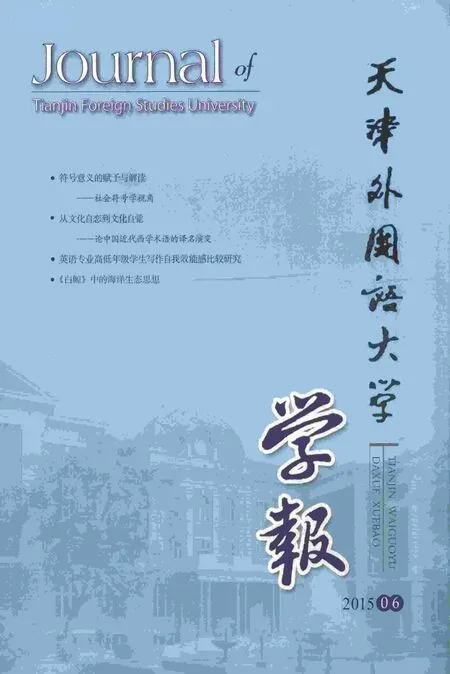《白鲸》中的海洋生态思想
左金梅,秦瑾晖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文学的生态批评逐渐成为显学,“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的发展是其产生的直接动因”(陈小红,2013:1)。生态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梭罗等生态作家的作品“在生态文化预警中展示人与自然重新融为一体的‘远景’,力求回归自然以逃避未来生态灾难和人类毁灭”(王岳川,2009:136)。而卡森等深受生态环境恶化之苦的作家则举起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大旗,“把刻不容缓的环境危机摆在世人面前的同时,还革命性地把反对‘征服自然’观念植根在每一个读者的心灵深处”(刘玉,2005 :155)。
著名文学评论家D. H.劳伦斯曾将《白鲸》誉为“无人能及的海上史诗”(劳伦斯,2006:161),它不仅是一部完整的海洋百科全书,更是一部宏伟的海洋生态预言。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白鲸》已初见规模,其中以对主人公之一埃哈伯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沙文主义的探讨最为集中。20世纪后半期以来,海上运输、过度捕捞等人类活动严重威胁着海洋环境,海洋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面对危机,保护海洋迫在眉睫。以海为主题的文学经典作品《白鲸》蕴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态思想,亟待被挖掘。本文拟借用生态批评,从复杂而平衡的海洋生态世界、海洋的生态警示以及海洋生态意识的觉醒三个方面分析这部作品,以期解读作者所意在传达的海洋生态思想。
二、复杂而平衡的海洋生态世界
在《白鲸》中梅尔维尔用众多无关于叙事的描述展示着海洋的不同侧面,这些描述因为海洋的生态主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复杂、神秘却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的海洋生态世界。海洋自我构建了一套完整、复杂的体系,鲸的分类是这个体系的一个缩影。第三十二章中梅尔维尔阐述了许多前人对鲸的分类,但漏洞百出。那些动物学和解剖学的泰斗们认为:“在深不可测的海洋中不宜从事我们的研究”,而将对鲸的分类看作“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梅尔维尔,2001:149)。梅尔维尔也在书中尝试着对鲸进行了分类,把对鲸的描写分为三卷,下分为章,每章又详细阐述鲸的别名、生存海域、商业价值以及渔人口耳相传的鲸的故事。作者自嘲说:“上帝不让我完成任何工作,这整部作品不过是一堆草稿——不,不过是草稿的草稿”(同上:160),鲸的分类之艰巨略见一斑。鲸是复杂的海洋生态的一环,对神秘的鲸的探寻是人类探寻神秘海洋的一步。
复杂而平衡的海洋生态世界体现在人类对鲸的描述中,书中描述了许多人类对鲸的可笑猜测。第五十五章中谈到了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稀奇古怪想象出来的鲸画像”(同上:282),还有众多画家们对鲸的错误描绘,如古苏格兰的西鲍尔德笔下的《鲸导言》和旧时《圣经》中的插画。就连自诩是科学画像的也非常可笑,白鲸就像“砍去了四条腿的母猪”,甚至像“半鹰半马的有翅怪物”(同上:284)。“我们可以从生物学角度认识鲸的一切细节,但我们仍不能真正认识这个造物的奇迹,自然对人永远是个谜。”(项伟谊,2000:75)对于前人来说,技术手段的匮乏使他们对鲸的描述还充满着想象,但这些描述已经在读者的心中勾勒了一个广袤不可测的海洋。那里孕育着不可计数的生命,变幻莫测又包罗万象,不断新陈代谢,有着自我的生态平衡。
作者通过叙述众多其他海洋生物,向读者展现一个复杂而平衡的海洋生态世界。它们互为食物,海洋由此才得以新陈代谢,维持自身的动态平衡。第五十九章中就描写了作为抹香鲸主要食物来源之一的鱿鱼。从桅顶上看,鱿鱼似是“怪异的鬼魅”(梅尔维尔,2001:298),而在大海中它只是鲸的一顿丰盛晚餐。“大海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孕育无数生命的巨大的有机体,它可以靠化能合成和光合合成两种方式制造有机物,从浅海到万米深海都形成繁荣的食物链。”(钟燕,2005:24)鱿鱼和鲸鱼都是这食物链上的一环,这条复杂的食物链环环相扣、和谐平衡。第六十六章中又描写了吞食鲸尸体的鲨鱼。但凡捕鲸船杀死的鲸周围都会迅速聚集起鲨鱼,水手们要用长捕鲸铲不停地赶杀它们,否则很短的时间内鲸鱼就会被鲨鱼吃完。即使鲨鱼如秃鹫般咬食尸体,实际却是海洋的清道夫,维持着海洋的清洁,这也是海洋处于动态平衡的体现。
复杂的海洋生态世界在平衡中运转着,鲸和其他海洋生物依赖大海生存,也相互依存,海洋也由此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并保持着动态的平衡。对于这个有机的生态世界,谁妄图打破这个平衡,谁就注定要受到大海严厉的惩罚。
三、海洋的生态警示
《白鲸》是一部伟大的生态预言,书中多处警示人类,如若侵犯海洋生态,必将遭受海洋的严惩。忽视这些警示,人类将错失自救的良机,死在自己制造的生态陷阱中;而关注这些警示,在危机前悬崖勒马,方能够逃脱自取灭亡的命运。埃哈伯就是忽视生态警示的人类代表,对于梅布尔神父讲述的约拿故事、莫比·迪克惨白的颜色等,埃哈伯均不以为意,他的狂妄已经蒙蔽了他的双眸。人类有着和他一样的狂妄,以为借助技术的进步就可以对大自然为所欲为。不顾海洋的承受能力而快速推进的工业是人类自己编织的网住自身的网。“不管幼稚的人如何大言不惭地谈他的科学技术,不管在一个称心如意的未来,科学技术可能如何发扬光大;而海洋始终将侮辱杀戮人类,粉碎人类所能制造的具有气派最为坚固的船只,直到末日来临。”(梅尔维尔,2001:296)埃哈伯的命运是人类命运的一个缩影,对其命运的警示就是对人类的警告,他的灭亡就是海洋向人类发出的生态警示。
《白鲸》的海洋生态警示表现在丰富的宗教思想与海洋生态的密切联系上。梅尔维尔赋予宗教全新的含义,用宗教暗示埃哈伯的悲剧命运。在小说开始前的摘录中多次引用 《圣经》。先是《创世记》中的一句话:“上帝造就出一头头大鲸”(梅尔维尔,2001:3)道出了白鲸在小说中将扮演的角色。在这里鲸就是上帝的化身,对鲸的侵犯就是对上帝的不敬。上帝创造了一个生态平衡的、和谐的海洋,鲸在其中自由地生存,替上帝管理、保护着海洋,如若有人侵犯海洋的生态平衡,上帝就会命令大鲸取其性命。《约拿书》中有云:“耶和华已安排了一头大鲸把约拿吞下”(同上),这也是约拿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第二次是小说第九章梅布尔神父借用约拿的故事预言埃哈伯注定命丧大海。约拿违抗上帝并妄图从海上逃跑,他以为一艘人造的船就可以将他带到不受上帝统治的国土中去,但上帝降下狂风暴雨,以摧枯拉朽之势袭击了约拿的航船,最后约拿葬身鲸腹,换来整个航船的安全。“约拿在最后的关头及时服从上帝的意愿从而挽救了船只,平息了风暴。亚哈固执己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船员身上,导致他自己和除以实玛利之外的裴廓德号船员皆遭灭顶之灾。”(孙筱珍,2003:25)上帝借鲸来处罚罪人约拿,暗示着海洋也借鲸来处罚侵犯海洋生态的埃哈伯。约拿的故事蕴含着梅尔维尔的深层生态警示,即如果人类如埃哈伯一般固执己见,忽视现实的警示,妄图控制海洋,肆意破坏海洋生态,就是自掘坟墓。
《白鲸》中莫比·迪克的白色让人惧怕,是海洋生态警示的色彩。在以往的宗教描述中,白色是纯洁和无罪的象征,基督教的教士们都身着白麻布长袍圣衣。白色也赋予自然界许多物质以纯净的美,如珍珠。白色还可以是“一切令人感动的高贵的颜色”(梅尔维尔,2001:207),新娘洁白的婚纱是贞洁的象征,老人的银丝白发是慈祥的象征,法官身着白色貂皮袍子象征着正义与威严,希腊神话中雪白的公牛也被视作伟大的主神朱庇特的化身。但书中的白色代表的是令人惧怕的力量。海上“鬼怪似的狂风”会掀起“滔天白浪”,死者的容貌也是“骇人的苍白色”(同上:208)。书中出现的其他白色海洋生物,如白鲨、北极熊等都是野蛮的,还有有着白森森牙的猛虎及似幽灵般盘旋在海面的白色信天翁。白色在 《白鲸》中代表死亡,在莫比·迪克夺走埃哈伯左腿的时候,这条“患有白化病的巨兽”(同上:197)就已经警告埃哈伯海洋神圣不可侵犯。白鲸之白实际为了表达海洋生态环境是纯洁的、无罪的,海洋可以很慈悲、温柔,但是一旦受到威胁或者侵犯,就将变得狂怒,把人类扔进毁灭的深渊。白色也表现了大海的两重性,“一会儿水波不兴,平滑如镜,笼罩着田园式的宁静,引人遐想;一会儿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大海母亲用‘白鲸’之类的丰富资源养育着人类,但面对人类对它残酷、疯狂的蹂躏,却以大而无比的力量将征服者吞噬。”(陈爱华,2004:92)
《白鲸》的海洋生态警示还表现在埃哈伯与莫比·迪克的殊死搏斗中,莫比·迪克的从容与埃哈伯的丑态百出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海洋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莫比·迪克“动作迅疾,气势非凡,同时却又显得从容不迫,温文儒雅”(梅尔维尔,2001:557),海面上一片“撩人的宁静”(同上:558)。而当它抬起尾巴拍打海面,埃哈伯就被这“旁若无人地搅起的巨浪闷得几乎闭过气去”(同上:560),只能在水中任由摆布。当他中途终于被救起,就像“一个被象群践踏过的人”(同上:561),动弹不得,喉咙里发出凄惨的哀嚎。而莫比·迪克则像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冲锋陷阵的好手,机动灵活”(同上:568)。它亲自为埃哈伯制造了预言中夺人性命的三架柩车的其中两架,第一架是预言者费达拉“那个袄教徒的伤残的身子”(同上:578),第二架是被拍得粉碎的埃哈伯的木船,第三架则是大海本身。“那只孤零零的小艇连同所有它的水手,每一支漂着的桨,每一根长矛杆,都像陀螺似的打起转来,活的死的,全都转成一个涡流,把披谷德号的最小的碎木片也卷了进去,不见了。”(同上:584)大海就这样吞没了一切,而“那片大的无边无际的尸布似的海洋依然像它在五千年前那样滚滚向前”(同上:585),在平衡中继续发展。小说旨在表明“人虽然可以观察世界、或对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量;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不能左右或征服自然。人只要不冒失地自取灭亡,大自然便乐于让他平静地生活。”(李一燮、常耀信,1991:240)
《白鲸》的海洋生态警示也表现在埃哈伯的惨死上。埃哈伯与白鲸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的殊死搏斗实际是人类与海洋之间的斗争。梅尔维尔娴熟地运用象征手法,向人类发出海洋生态警示。狂妄自大的埃哈伯象征着借一艘航船就妄图控制海洋的人类,而白鲸则象征广袤无垠的海洋。书中对捕鲸业详尽的描述实际是人类对工业化的狂热追求。埃哈伯带着水手们疯狂地追杀白鲸,试图“通过战胜最了不起的鲸鱼来证明自己的最了不起”(王诺,2003:148)。当埃哈伯把最后一支鱼叉插进白鲸身体,白鲸痛苦地逃入水中时,鱼叉上系着的绳索绕在了埃哈伯的脖子上,导致他被绳索绞死。“亚哈不是死于白鲸之手,而是死于人类工业文明锻造的绳索之下”(徐明、李欣,2006:115),就如同人类自身。这一段描写是全书情绪的迸发点,也是梅尔维尔为人类敲响的生态警钟。梅尔维尔借此阐释了当今海洋生态危机的根源,即人类疯狂地向海洋索取,不顾海洋的承载能力,也告诫人类疯狂发展的工业实际是人类套在自己身上的死亡枷锁,这种对海洋无所顾忌的态度最终必将使人类死在自己设立的陷阱中。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1973:517)
四、海洋生态意识的觉醒
海洋是美丽而壮阔的,以实玛利实际是梅尔维尔的化身,梅尔维尔借以实玛利之口多次表达了对海洋无限的赞美和热爱。以实玛利是埃哈伯的航船上唯一没有被大海夺去生命的水手,他的死里逃生绝非偶然,是他对海洋从头至尾深切的敬畏让他得以幸免遇难。《白鲸》中的海洋生态意识觉醒首先表现在以实玛利最初的出海动机上,与埃哈伯的动机完全不同,也必然与后者有不同的命运。开篇他表达了自己对当前陆上生活的厌恶之情。“19世纪,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人类的全部陆地活动,陆地文明已异化得使他不能把它再看作家园,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张慧诚、杨眉,2007:108)他感到“眼里有些发朦”,“肺部过分敏感”,甚至想“用手枪子弹了结此生”(梅尔维尔,2001:22),他必须要逃到海上去,在海上做一名普通的水手。他认为,人类自诞生就或多或少、或先或后产生“向往海洋的情感”,人类自古就热爱、崇敬海洋,当人类远离陆地之时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激动”,“古代波斯人把海奉为神明,希腊人也专门设一位海神”(同上:24)。对于出海埃哈伯内心满是复仇的怒火和征服的欲望,他的旅程是为了追捕莫比·迪克而开始的,扬言“要追它到好望角,到霍恩角,到挪威的大漩涡,不追到地狱之火跟前我决不罢休”(同上:179)。以实玛利却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对鲸的好奇,那头凶猛异常而又神秘莫测的怪物“叫人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其次是那“浩渺无际、远在天边”的大海,“几乎每一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只要心灵同样强壮健全,到了某一个时候,便会如痴如醉的向往到海上去”(同上:27)。
以实玛利在担任瞭望手的过程中,对海的观察让他更懂得敬畏海洋,海洋生态意识逐渐确立。瞭望手是一个苦差事,枯燥、单调,但对于以实玛利来说,这是一件美差,他很享受欣赏大海的过程,喜欢看着大海沉思。在桅顶本该努力寻找鲸的踪迹,但以实玛利心胸间萦绕着的是“整个宇宙的问题”(同上:174),他脚下神秘的海洋是 “人与自然中无所不在的深蓝无底的灵魂的视觉的形象”,成了“自己捉摸不到的种种奇怪、隐约可见、一滑而过的美的事物”(同上:175)。第三十七和三十八两章的篇幅都是描写以实玛利观察到的海上日落与暮色。在桅顶瞭望海洋是与海洋在思想上交流的过程,是与宇宙进行灵魂上对话的过程。以实玛利描述说他的精神在此时仿佛逐渐“退落到它的来处,消溶在时空之中”,成为了“全世界每一处海岸的一部分”(同上:176)。在这高高的桅顶上,“除了那轻轻摇晃着的船所赋予你的摇动的生命以外,没有其他生命,而船的生命是大海赋予的,大海的生命又是上帝不可思议的潮汐赋予的”(同上)。人的生命就这样与大海紧密联合在一起,对白鲸的海上追逐成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对海洋的深情赞美和敬畏之情也在以实玛利的心中扎根。
伴随着海洋生态意识在以实玛利心中发芽,他拥有了不同于其他水手的发现海洋生态之美的眼睛,用满含慈爱的口吻讲述着在海上观察到的美丽故事。第八十七章描述了母鲸奶幼鲸的情形,幼鲸在吮吸母奶的时候总是抬眼安详地望着世界,似乎此时此刻“同时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他一边吸着生命的养料,一边仿佛回想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往事,从中汲取精神的养料”,而我们在幼鲸初生的眼中只是“一撮海藻而已”(同上:403)。在以实玛利眼中,“大鲸是海洋里的居民,与人类社会一样,有着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及各种美好的情感。它们是力量、优美与智慧的完美结合体,是人类敬畏的对象、学习的榜样,在其幻想中,大鲸甚至戴上了神性的光环”(易建红,2012:50)。观察鲸的出生、成长和生存使以实玛利学会敬畏生命与海洋生态平衡,这种生态平衡之美启迪了他对生命本质和生存意义的思索。
海洋生态意识的觉醒表现在以实玛利对海洋的感恩之情上。他是小说中唯一感激海洋的哺育,并懂得人类应当与海洋和谐相处的水手。海洋在以实玛利眼中才是生命的故土,“生于大地,受的却是海洋的哺育,虽说山陵与溪谷抚育了我,你的滔天白浪啊,却是我非亲生的兄弟”(梅尔维尔,2001:509)。“白鲸是自然界的灵魂,杀灭它就等于消灭人类自身。毕竟,人类是无法离开自然而生存的”(央泉,2014:115)。海洋是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哺育人类,是人类依附的对象,人类无法离开海洋而生存。对于海洋的馈赠,人类应当充满感激与敬畏。但以埃哈伯为代表的人类不仅对海洋心无感激,还成了以征服海洋为荣的偏执狂。埃哈伯的死是人类的悲剧,但却并不悲壮,因为这是人类狂妄自大、愚昧无知的恶果。以实玛利与埃哈伯海洋生态观点的分歧也凸显出来,后者意欲彻头彻尾地征服海洋,而前者则学会顺从海洋,并把海洋当作自己的兄弟去和谐相处;后者以悲剧收场,前者幸免于难。现实的人类应作何选择不言自明。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使人类学会思考该如何生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而《白鲸》中的海洋生态思想使人类开始思考应该如何与海洋和谐共存,这是海洋生态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人类同样无法回避的抉择。以实玛利为人类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作者通过结局的安排,“认同了以实玛利的选择——人不能将自己等同于上帝”(同上:117),尊重海洋,敬畏一切海洋生命,才是人类命运的终极式救赎。
五、结语
《白鲸》成功预言了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海洋生态困境,对人类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分析。如果说梭罗带领人类走向荒野,那梅尔维尔就带领人类走向了海洋。虽然埃哈伯展示了他作为人类的智慧和尊严,但他也是人类贪婪和欲望的化身。白鲸则代指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生态环境,在人类妄图把白鲸赶尽杀绝之时,人类也把自己逼向了生态危机的边缘。实际上,“作为唯一有理性的动物,人类应该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当做最高利益和终极目的,承担起应尽的生态责任。热爱海洋就是热爱人类自身,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未来,这是大海的启示。”(易建红,2012:52)。作为海洋文学经典和生态文学力作,《白鲸》不仅讲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更发起了保护海洋生态的呼吁,呼吁人类敬畏海洋,合理开发海洋,主动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建设一个人与海洋能和谐相处的世界。
[1] 陈爱华. 2004.美国十九世纪主要作家笔下的人与自然[J].山东外语教学 , (3): 90-94.
[2] 陈小红. 2013. 什么是文学的生态批评[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 D. H. 劳伦斯. 2006.劳伦斯论美国名著[M].黑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4] 李一燮,常耀信. 1991. 美国文学选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5] 刘玉. 2005.美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 (1): 154-159.
[6] 马克思,恩格斯.197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7] 梅尔维尔. 2001.白鲸[M].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8] 孙筱珍. 2003.《白鲸》的宗教意义透视[J].外国文学研究,(4): 24-27.
[9] 王诺. 2003.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0] 王岳川. 2009.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 (2): 130-142.
[11] 徐明,李欣. 2006.论《白鲸》的生态意识[J].东北师大学报, (6): 112-116.
[12] 项伟谊. 2000.求索于海上:《白鲸》与西方文明[J].国外文学, (3): 73-78.
[13] 易建红. 2012.人·大海·启示——以《白鲸》、《海狼》和《老人与海》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6): 48-53.
[14] 央泉. 2014.英雄还是恶魔:《白鲸》主人公埃哈伯形象新解[J].外国文学研究, (3): 110-118.
[15] 张慧诚,杨眉. 2007.涉过历练生命的深水之旅——解读麦尔维尔小说《白鲸》[J].兰州大学学报, (5): 106-108.
[16] 钟燕. 2005.蓝色批评:生态批评的新视野[J].国外文学, (3): 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