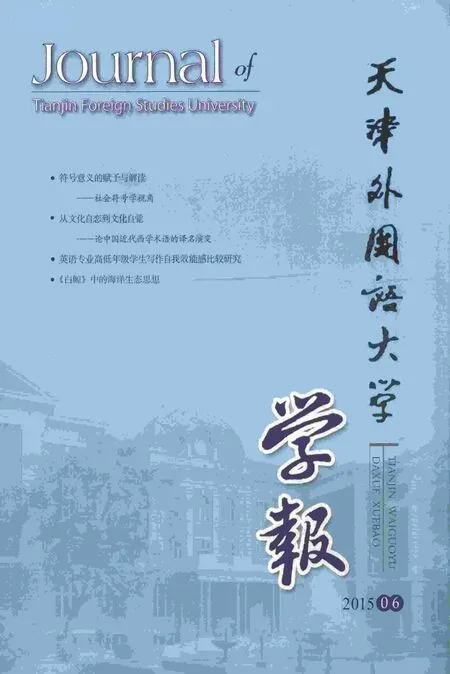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界定、取向与外延
毛延生,郝桂冠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一、引言
随着认知科学的不断推进,认知语言学家逐渐意识到:在语言的具体使用过程中,人们除了要考察认知元素之外,还必须关注社会元素。例如,Lakoff(2001)在一次访谈中首次提出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概念,进而强调社会因素可能比认知因素更重要(朱海燕、刘懿娴,2011:142)。随着 Croft(2000)的语言社会进化观、Harder(2003)的语言社会功能背景论以及Sinha(2007)的语言后生系统观的问世,这些似乎都在昭示认知语言学研究必须接受社会因素的全面介入方能彰显语言使用机制的全景图。刘宇红和吴倩(2005)从六个基本特征出发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随着《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变体、文化模式和社会制度》(Geeraerts& Kristiansen,2010)的出版,认知语言学正式将社会因素纳入到研究视野中来,这可以看作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诞生之作。在这本论文集中,作者们不但厘清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范畴、应用领域和研究特点,而且还为该学科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在2010年,Geeraerts等编辑了上一本论文集的续篇《认知社会语言学新进展》,收录的10篇文章均选自在波兰克拉科夫举办的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论文,标志着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正在不断完善并走向具体化。那么,经历起步性发展之后的认知社会语言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又是如何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整合于一体?本文拟结合当下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最新文献,试图廓清其基本概念、研究取向和应用外延等基本问题。
二、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概念界定
认知社会语言学综合了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取向和社会语言学的社会取向,关注认知的社会文化语境制约性,把认知体验的生理和物理环境拓展到社会文化语境,把语言及其背后认知的普遍性研究转向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语言(变体)与认知的普适性研究,因而可以看作认知语言学体验理论发展的里程碑(Bernárdez,2008)。王天翼和王寅(2012)在引进认知社会语言学时对其这样定位: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以“语言意义”为中心,以“实际用法”为取向,从语言的社会性和认知性角度深入研究语言变异、社团方言、文化模型、意识形态、双语对比、语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认知语言学的首字母大写,是因为在认知社会语言学中,认知语言学作为具体的理论研究范式出现,而社会语言学主要指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域”(Geeraerts et al.,2010:2),具体原因有二:
首先,认知语言学基于应用的本质及其自身显著的语义视角使其必然要关注语言中的社会因素。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内部认为其自身是对语言用法的研究,而大量的基于语言用法的语言研究认为“基于用法的语言学之核心在于语言使用和语言系统之间的方言关系,也就是以语言的实际应用为前提”(Langacker,1999:i-iv)。所以认知语言学要想证明自己是基于用法的研究,就不可避免的要转向社会语言学语料,进而真实地反映社会因素对于语言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意义的关注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Geeraerts,2006:1-10),但意义并非孤立的,而是动态的,它在人们互动过程中得以产生和传播,因此这种互动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结构。虽然文化和社会模式已经作为一个新的语言模式在认知语言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Holland & Quinn,1987:10-21),但尚没有一个通用的以社会和文化为导向的实验方法。由此可见,“认知语言学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就,就需要走出大脑,纳入语言的社会属性”(曹燕萍等,2011)。
其次,由于社会语言学长久以来忽略语言变体,而这恰好与心理学和感知方言学等研究领域毗邻,所以社会语言学可能会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引入方面获益匪浅(Gries,2013)。例如,认知研究中的心理语言学实证方法长期应用F-ratios和F1/f2数据以确保实证结果在跨学科中均有信度。但这种方法不易于应用到其他数据设计中,并且无法处理缺失数据或解决数据语言学中经常出现的不均衡设计问题(Baayen,2008:7)。许多年来,变项规则分析法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的主导方法。然而,这一方法在许多方面都有缺陷:笨拙的互动处理,不能包容不带因子的连续共变体及其缺失信息,不能处理重复测量数据点和共线预测等。Gries(2013)认为,认知语言学尤其是心理语言学是解决这一方法论问题的有益补充,即可以应用包括心理学和数据库语言学中的范例模型和新方法论工具,如混合效应、启动效应、逻辑回环等方法,推动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三、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取向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认知社会语言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取向:第一,以言语变异为研究对象;第二,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与社会语言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
1 研究对象
虽然言语变体本身无法单独构成理论,只被看作是划分语言异质性范畴的工具,但却被认定是语言研究领域各分支学科的普遍追求。过去的语言变体研究常常关注形式,常常忽略更加重要的意义研究。尤其是在Long(1988:4-10)对“形式”和“意义”进行了区分之后,意义研究逐渐被提上了日程。一方面,认知过程的开始就是由于学习者意识到有特定意义的存在;另一方面,按Geeraerts等(2010:7)的说法,社会语言变体指表达同一语言功能或者实现同一语言因素的一系列不同选择方式,并且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具有社会和语体意义,这些意义的产生与语言外因素密切相关。所以,语言变异研究对于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来说都具有全新的价值。虽然社会语言学和认知社会语言学都以语言变异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侧重点却不尽相同:前者主要关注语言变异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凸显其社会性;而后者主要从认知角度来考察,强调其认知性(苏晓军,2009)。因此,传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对于语言的内部变异和交际变异关注不够,而社会语言学忽视语言变异的认知根源必然影响其研究深度,所以二者在语言变异解释维度上的有机整合有助于语言研究获得纵深维度的发展。
就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次级范畴:语言行为、语言态度及语言演变(Geeraerts,2005:163-189),语言行为就是在实际使用中被社会化了的语言结构变体,其中往往涉及不同文化模式在同一语言社区内的竞争。如 Wolf 和 Polzenhagen(2009:2-5)对英语的英美变体和非洲变体进行了对比分析,强调了西方个体主义文化模式和非洲集体主义文化模式在同一语言社区内存在冲突。又如,关注不同文化模式和社会政治体制在同一语言社区内差异以及语言政策的文化模式时,就属于语言行为的研究范畴。语言态度是指交际中的说话者如何评估和感知语言变体。Geeraerts(2005:163-189)认为,语言态度是一种范畴形式,认知语言学中描述范畴的方法,如原型理论、概念隐喻和文化模式可以应用到语言态度的研究中。语言演变研究关注的是语言的变异,即语言的社会意义是如何传递以及触发变异。目前来讲,认知社会语言学主要关注的是语言演变研究,尤其是词汇和语义变异的分析,前面两个范畴尚待进一步拓展。
2 研究范式
将认知语言学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是该研究的基本特征。理论和数据支撑问题代表了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在语言学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Schwarz-Friesel,2012)。社会语言学经常遭到没有统一研究理论的诟病,而认知语言学一向重视理论而忽视方法。因此,认知语言学自下而上的理论框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语言变异这种社会现象的理解,反过来,对社会语言学维度的更多关注也可以进一步推动认知语言学向纵深发展。
认知社会语言学重视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语料库研究。要真正解释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的变异问题,就必然要用到社会语言学中的多原变量统计方法,如变项规则分析法。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变体、文化模式和社会制度》一书中,作者单独拿出一个独立的章节来突出和强调实证研究,尤其是语料库的多元变量分析。当然,在语料库的基础上,还可以辅之以问卷、测试等形式。在《认知社会语言学新发展》一书中又涉及了处理多维语言变异和区分概念性变异与社会性变异的一些前沿语料库技术(诸如多元回归树、混合情感启动和逻辑回环等),同时辅以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设计、调查和问卷等传统方法。由此可见,随着新学科的推进,认知社会语言学在方法上的推演也将会是一个飞跃,并为其他学科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范式。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优势还在于它将最终目标设定为通过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各种理论进行语言分析来锁定语料中所蕴含的特定文化模式。因为在以数据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中,数据只能用来进行描述、提供实际、客观的真实交际数据。如果不根据一定的理论框架进行后续的阐释和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Kristiansen和 Dirven(2006:71)基于概念转喻理论将两者联系起来并指出:语言主要是语音不仅是方言的体现,而且是社会意义的标识,它会唤起相应的概念语义,通过转喻与不同的语言类型范畴相连,然后这种语言范畴再通过转喻进一步与不同的社会范畴相连,这时就会使听话者对说话人所属群体的特征、意识形态、价值和社会阶层等知识有进一步的判断,从而建立了语音的社会意义功能。这就是language stands for identities在转喻理论中的具体应用。认知语言学致力于在普遍认知原则的指导下,从最基本的认知系统和认知能力来研究语言结构(Nerlich &Clarke,2007:590),发现各种语言事实背后的系统性和普遍性。但隐喻不仅具有普遍性,它还能够解释不同文化的认知特征,如Ning Yu (1996:11-15)以汉语中空间隐喻为例,解释了概念隐喻的相对性,即隐喻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模式,表明不同社会中的语言有其独特的文化认知模式。
四、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应用外延
认知语言学基本理论在社会语言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言语变异的理论研究、语言与认知文化模式研究、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研究。分别对应上文提到的语言演变、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由于认知社会语言学当下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在语言演变研究维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下面我们主要就语言演变(语言变异)方面进行梳理并加以实证分析,以厘清认知社会语言学国外研究的应用外延。
1 结构变异
Langacker(1999:21)指出,要研究概念和语法结构的动态性就必然要研究话语和社会交互的动态性,而这一点在以往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必须扩大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以涵盖话语和社会交互等领域。认知社会语言学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将社会语言学的语用和语境因素带入了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认知研究当中,比如将实际使用中语法结构变化的解释加入语境因素,就可以使原本的认知语法描述解释更加丰富。其中代表人物Schönefeld (2013)对语料库中真实语域下的go un-V-en语法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语域对语法的形式以及语法结构的准确应用有着重要影响。具体来说,不同的语域对语法的结构有着不同的吸引度和排斥度。这一结论表明,语法结构与语境有密切关系,因此认知社会语言学将改变以往只从认知角度关注语言中语法研究的传统应用取向,而是对于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采取兼收并蓄的平衡态度。
2 词义变异
自认知社会语言学诞生以来,词汇和词义变异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Geeraerts等(2010:5)指出,语言既是社会事实,也是认知事实。据此,认知社会语言学仅从社会角度论述语言是不完整的,而认知分析却是认知语言学的强项,且认为一切社会现象必须经由人的主观认知加工后,才能与语言发生联系。Geeraerts 和 Speelman(2010 :23-24)率先对方言中词汇变异(社会语言学范畴)的概念特征(认知理论)进行了研究。他们设想词汇方言变异不仅由地理和社会等级引起,词汇本身的认知概念也可能造成词汇的方言变异。像概念歧义和概念沉默等非传统的语义特征,也可能对词汇变异产生影响。在对大型的德语方言变体数据库进行了数据分析之后,Geeraerts 和 Speelman(2010)应用多元回归树分析法对歧义、沉默和负影响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得出非正字法的概念特征,如概念歧义和概念沉默等对词汇的异质性影响很大。这说明单从地理或社会因素解释词汇变异往往过于狭隘,认知视角对词汇和语义的阐释同样也不容忽视。过去对方言变体的研究几乎都是通过社会因素进行解释,而概念本身在方言变体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却无从知晓。所以,社会语言学无法彻底说明的词汇变异现象可以通过认知语言学的介入而更有说服力,语义阻尼研究就是很好的实例(Steels,2000)。
Sharifian(2010)运用词汇—联想—解释法讨论了澳洲学校盎格鲁白人学生和土著学生在使用一个表征相同的英语单词home时有不同所指的原因。结果发现,两个文化组群有着不同的但却同时具有相关交叉的概念系统,交叉的概念系统体现在他们有着共同的词汇表征,而不同的概念系统体现在语言上就是产生了土著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也就是说,在表层特征相同的情况下,导致其在不同群体眼中产生不同所指的原因是由于不同文化模式对概念化的影响。作者指出,正是由于两类学生在不同的现实生活环境中的认知体验不同,才导致了他们表面上使用着相同的词汇却有不同的所指,即进一步说明了词义的变异不仅是社会语言学中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同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模式也会造成同一社区内词汇的变异。
3 语言变异的态度问题
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很多学科的注意,如语言学、社会学、交际学等。如今,认知社会语言学也开始关注语言态度问题。对语言变体态度的研究与前两节的主题有所不同,它关注的是词汇的范畴化、感知、态度以及习得等问题。具体来说,它关注的是词汇意识的习得对不同词汇变体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一种具体词汇变体的不同态度。为了与认知社会语言学框架相一致,并在原则上与其关注的方言意识和态度变体相一致,Speelman和Geeraerts(2010:23-40)应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情感启动方法来检验德语中的认知表征和内部语言变体的社会意义。具体来讲,作者使用了听者效应实验,在这里参与者会对情感目标刺激作出快速反映,然后记录下实验者的语言产出。此实验能够测试出德语使用者在听到标准语和区域变体时的态度反应是一种自动的反应,与语义无关,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这说明听觉情感启动实验可以当作一种自动测量语言态度的新工具。因此,在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检测和评估这种语言态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最新的研究中也相应的引入了如多远回归树,尤其是混合效应模式等认知语言学尤其是心理语言学中的范式。以上诸多努力,可以看作是认知社会语言学在方法论上的进步,也就是说其研究范式已经不局限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认知社会语言学中的认知语言学也可以提供相应的研究方法。由此可见,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结合将是多角度的跨学科研究。
五、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综上所述,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从最初的只是关注单一维度的语言理据,发展到寻求多种语言理据来揭示语言使用机制的探讨,其具体的研究范式以及应用外延也在不断丰实。我们认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不仅仅在于证明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结合是可行的,更重要的是要找出针对不同的语言事实,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更有效。下面我们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理论框架、研究范式、语料/数据收集方式等方面对未来研究的趋势作一展望,并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拓宽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认知语言学最初的研究主要围绕范畴化、原型理论、概念化、构式、概念合成等问题展开并且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近年来,这些方面仍然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话题,但其涉及范围有了较大的拓展,研究的主题得到了深化,比如在一些传统的语言学领域有所涉猎,如在音位学、词法形态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束定芳,2012)。在未来的研究中,认知社会语言学可以从传统的语言学领域和新兴的语言学领域继续拓展其研究范围。
第二,寻求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式的灵活性与多样化。语言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从定性和定量的多视角研究与考察,语言研究的多元化要求研究方式的多元化。当前的语言学研究应同时努力加强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充分运用多种方法是未来语言研究的总趋势(Tashakkori & Teddlie,1998:1-10)。认知社会语言学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学范畴,应在未来的研究中迎合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寻求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式的灵活性与多样化(李怡、王建华,2013)。
第三,借鉴 、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研究框架。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创立本身就是建立在借助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认知语言学从一开始就是跨学科的研究。目前国外研究者已经能够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和实验手段对语言认知进行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借助神经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研究语言问题(辛斌、李曙光,2006)。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一些重要理论、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也逐渐引起了相关学科学者的兴趣,并由此派生了许多新的学科诸如认知二语习得研究、认知诗学、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文化学等具有跨学科和多学科性质的新兴研究领域(束定芳,2012)。这些理应成为认知社会语言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第四,扩大实证性选择范围,探讨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性证据。对任何科学研究来说,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桂诗春,1994)。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另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以及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反思。早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主要采用内省法。近十年来,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认知语言学研究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实证研究中,语料库研究方法、心理实验法、ERP(事件相关电位)和FMIR(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神经实验法、音像资料法等研究方法成为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研究中运用得较多的几种方法(束定芳,2012)。此外,认知社会语言学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应该更加的丰富且多元,例如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学习者都应成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
第五,重视语料收集与评估方式的多样化,并尽量确保语料的真实性。语料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至关重要。为提高语料的信度和效度,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方法的取向,将自然语料和引发式语料相结合,互为补充并互为佐证,这是一种趋势(李怡、王建华,2013)。但是对于选择研究方法的标准,我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人员应该采用能够收集到他们所需信息的方法,尽量确保语料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多样化收集和评估。
六、结语
随着认知科学领域,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研究对于社会语言变体的关注日渐提升,认知社会语言学开始了自身属性界定、研究取向以及研究外延的深入探索。一方面,这一研究取向较为珍视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探讨语言使用背后的语用理据,并将其纳入自身认知语言学解释范式的效度检验当中;另一方面,借助认知语言学的深度视角,重新审视语言变体的形成动因,进而从具体实例出发尽量整合微观与宏观研究,从而实现社会语言学的自我范式更新。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在国内才刚刚起步,针对汉语语料展开的实证性研究十分短缺。国内语言研究者应该适当借鉴和吸收国外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成果,探讨汉语使用机制的特点,这也可以为汉语普及教育提供夯实的参考。
[1] Baayen, R. 2008. Analyzing Linguistic Data: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Us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Bernárdez, E. 2008. Collective Cognition and Individual Activity: Vari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A]. In R. M. Frank et al. (eds.)Body, Language, and Mind (Vol.2): Sociocultural Situatedness[C].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3] Geeraerts, D. 2006. A Rough Guide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A]. In D. Geeraerts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C].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4] Geeraerts, D. 2005.Lectal Variation and Empirical Data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A]. In F. J. Ruize et al.(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nal Dyna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5] Geeraerts, D. & D. Speelman. 2010. Heterodox Concept Features and Onomasiological Heterogeneity in Dialects[A]. In Geeraerts,D.et al. (eds.) 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C].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6] Geeraerts, D., G. Kristiansen & Y. Peirsman. 2010. 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7] Gries, S. 2013.Sources of Variability Relevant to the Cognitive Sociolinguist, and Corpus as well as Psycholinguistic Methods and Notions to Handle Them[J]. Journal of Pragmatics, (52): 5-16.
[8] Holland, D. & N. Quinn. 1987.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Kristiansen, G & R. Dirven.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0] Langacker, R.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1] Long, M. 1988. Focus on Form[A]. Bellagio, the European-North-American Symposium on Needed Research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2] Nerlich, B. & D. Clarke. 2007.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A].In D. Geeraerts & C. Hubert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Pires De Oliveira, R. 2001. Language and Ideology: An Interview with George Lakoff [A]. In R. Dirven, B. Hawkins & E.Sandikcioglu (eds.) Language and Ideology(Vol.I): Theoretical Cognitive Approache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4] Schönefeld, D. 2013. It is quite Common for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to go Untested. A Register-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go un-V-en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52): 17-33.
[15] Schwarz-Friesel, M. 2012. On the Status of External Evidence in the Theori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mpatibility Problems or Signs of Stagnation in the Field? Or: Why do Some Linguists Behave like Fodor’s Input Systems?[J]. Language Sciences, (34): 651-655.
[16] Sharifian, F. 2010. Cultural Conceptualization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Aboriginal and non-Aboriginal Australian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49): 33-57.
[17] Steels, L. 2000. Language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M]. Berlin: Springer-Verlag.
[18] Tashakkori, A. & C. Teddlie. 1998.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 Wolf, H. G. & F. Polzenhagen. 2009. World Englishes: A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 Yu, N. 1996.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M]. Amsterdam: John Benji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1] 曹燕萍等. 2011.认知语言学内部转向——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兴起[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125-131.
[22] 桂诗春. 1994. 语言使用的研究方法[J]. 现代外语, (3): 1-8.
[23] 李怡, 王建华. 2013. 跨文化语用研究语料收集方法[J]. 绍兴文理学院, (3): 92-98.
[24] 束定芳. 2012.近10年来国外认知语言学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J]. 外语研究, (1): 36-44.
[25] 苏晓军. 2009.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J]. 外国语, (5): 47-51.
[26] 辛斌, 李曙光. 2006. 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应用及跨学科研究[J]. 外语研究, (5): 1-5.
[27] 王天翼, 王寅. 2012.认知社会语言学[J]. 中国外语, (2): 44-53.
[28] 朱海燕, 刘懿娴. 2011.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新接口——《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变体、文化模式、社会制度》评介[J].外国语文 , (1): 14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