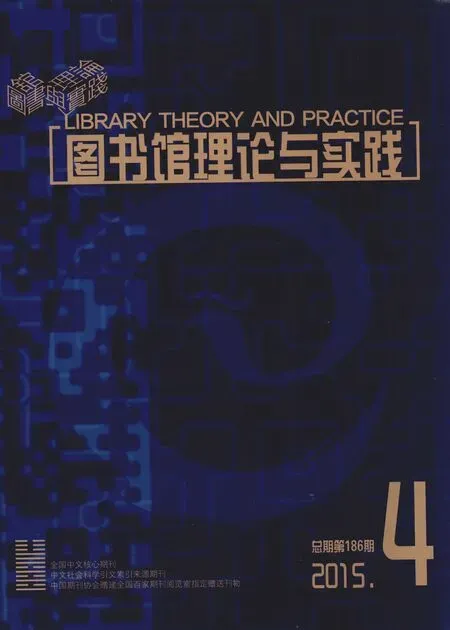唐代以来主要官私书录中的佛道之争
●罗 凌(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唐代以来主要官私书录中的佛道之争
●罗凌(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关键词]官私书录;道教文献;佛教文献;佛道之争
[摘要]唐代以来佛教与道教既相互融摄又相互论争,从文献学角度观照,佛道之争主要体现为各自建构严密的理论经典体系以及著文论辩问难两个层面。选取《隋书·经籍志》等十部官私书录,从佛、道文献类目名称与层级的区别、编排的次序先后、著录规模的大小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唐代以来书录中的佛道之争,各自有其历史阶段性,总体呈现这样的轨迹:道教文献由唐初书录的推尊地位,逐渐在类目层级和子部序位两方面呈下滑趋势,而佛教文献由唐初书录类目中的最末位置,在类目层级和子部序位方面渐次上升,个中先道后佛的观念持续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时才真正扭转过来,同时,佛、道文献的著录规模皆受到挤压,将佛、道文献纳入儒家文化体系的意图与佛、道文献的特殊性存在直接冲突。
佛教与道教能够相互融摄,但在信仰和义理层面又各有特质,为了宣扬正信、争取宗教的正统地位以及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衍生出佛道之争。佛道之争,从文献学角度观照,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则体现为佛教、道教各自建构严密的理论经典体系;一则体现为不同宗教集团相互指斥正邪,并著文往返论辩问难。卿希泰先生指出:“佛、道二教的发展,使它们为争宗教传播阵地和思想控制权的斗争随之日益激化。”[1]东汉魏晋时期,已开佛道论衡的先声,有东汉僧人摄摩腾与道士论难,西晋道士王浮著《老子化
胡经》、东晋孙绰著《喻道论》等。随着佛教、道教的广泛传播,其论衡愈演愈烈,如南北朝时期顾欢著《夷夏论》、明僧绍著《正二教论》等。
佛道之争全方位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包括书录的编纂。陈麦青先生认为“魏晋至唐初佛、道两教发展、消长的情形,从当时一些目录书中对佛、道经典的著录、安排等以及同时一些佛、道专门目录的修撰情况中,也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反映”。[2]唐初已经确定了儒家的主体思想地位,随后佛教、道教从发展的巅峰阶段渐次衰微凌夷。然而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的编纂则呈反向——日趋繁荣,唐代以后文献总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趋势。书录编纂能够体现出时代的思想潮流,故而主要官私书录著录佛教和道教文献的方式以及具体形态,也反映出不同时代书录中的佛道之争。荀勖《中经新簿》是最早著录佛教文献的书录,至于著录道教文献,王宗昱先生以为:“道教经典被收入目录学体系是后于佛教的,大约是受到了官方对佛经编纂的影响。”[3]唐以后三教融合的观点逐渐形成重要的格局,目录专书如何著录佛、道文献,佛、道文献在官私书录中处于何种地位,能否反映出佛、道两教的实际发展情形。本文将从目录学角度考察唐代以来主要书录著录佛、道文献的具体情况,试就三教融合背景下官私书录中呈现的佛道之争予以辨析。鉴于唐代以来官私书录太为驳杂,故范围有所限定,一方面考量其时代的代表性,一方面注重其在目录学史中的学术性,仅选取《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十部书录进行统计分析。
一、类目名称与层级的区别
分类是目录的灵魂,一部书目的编纂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类,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佛教类文献和道教类文献,唐以来书录中的类目名称并不一致,尤其是道教类文献,经常与“道家类”混为一体,其间有一个类例不分到类例明晰的过程。
唐以来十种主要官私书录中,佛教文献有四种类目名称:其一谓“佛经”类,仅仅在《隋书·经籍志》这样使用。以“佛经”作为类目名称统称佛教文献,这里的所谓“经”,并非佛教经律论的经,而是指向佛教文献的更加宽泛的义项。其二谓“释书类”,强调释家对文献的统领,北宋官修书录《崇文总目》置之于子部第二十类,随后私家书录《郡斋读书志》和《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个类目名称,《郡斋读书志》在子部第十八类,而《文献通考》在第二十类。其三谓“释家类”,以“释家”统之,因为是书目类名,故类目名称亦明晰。《通志·艺文略》子类第三、《明史·艺文志》子部第十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第十三的类目统一采用“释家类”。其四谓“释氏类”,与“释家类”名称近似,《直斋书录解题》子部第十一类即是。比较特殊的是《旧唐书》和《新唐书》,没有给佛教文献设置专门类目,而是泛泛归之于“道家类”中,与老学、庄学、道教文献汇编,从目录分类学角度看,不能不说是个缺陷。
道教文献的类目名称同样复杂,一则为《隋书·经籍志》集部之后所附“道经”类,著录道教文献。二则没有为道教文献设置专门的类目,而是笼统将老学、庄学文献和道教文献汇编为“道家类”一目,如《旧唐书》《新唐书》《通志·艺文略》《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其中,分类最为精致细微的是《通志·艺文略》,其“道家类”相当庞杂,细分为“老子、庄子、诸子、阴符经、黄庭经、参同契、目录、传、记、论、书、经、科仪、符、吐纳、胎息、内视、导引、辟谷、内丹、外丹、金石药、服饵、房中、修养”等二十五个三级类目,[4]“阴符经”类之后的二十二个类目实际是对道教文献的再一次分类。三则为“道书类”,《崇文总目》在子部第二类“道家类”著录老庄道家文献,而第十九类“道书类”则著录道教文献,这个类目名称更加名副其实。四则为“神仙类”,从《郡斋读书志》开始,为与老庄之道学增加区别度,将道教文献类目专门设定为“神仙类”,随后的《直斋书录解题》和《文献通考》都继承了这样的类目设置。
作为宗教文献,在目录分类体系中,佛教文献与道教文献应该归属于同一个层级,如《隋书·经籍志》就统一将“道经”类和“佛经”类分别附录于集部之后,虽不能与以儒学为中心内容的经史子集四部相提并论,不能算作《隋志》四分法系统中的一种,但这种设置也强调了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的同等重要性,它们是仅次于四部而可以独立分类的宗教文献,故尽管是附录,“道经”类和“佛经”类则相当于一级类目。
而大部分书录则将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著录在子部之下的二级类目甚至三级类目中,类目层级越低,表明对其重视程度越少。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各自设置类目同属于子部下二级类目的书录有《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同属
于子部“道家”类下三级类目的书录有《旧唐书》和《新唐书》,其将“道、释诸说”与“老子”、“庄子”类文献并而列之。
如果是科学的类目设置,则不应该将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著录为不对等的层级。然而不同的书录中,还是存在佛教文献与道教文献并非同等层级的情况。如《通志·艺文略》《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其佛教文献的类目名称为“释家类”,属于子部下二级类目,但与之相对应的二级类目“道家类”,实际上还可以细分为老学、庄学以及道教文献等三个三级类目。佛、道文献分属于不同层级的类目中,个中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出编纂者的分类思想,同时也映现出对于佛、道文献不同的定位。从这个角度看,《通志·艺文略》《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南宋及以后的书录对于佛教文献,应该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被归入子部下的二级类目成为唐代以来书录编纂形式的主流,但将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置于不同层级的类目,又反映出佛、道文献在书录中的层级之争。
二、编排的次序之争
现存唐以来主要官私书录子部二级类目的编排中,儒家从始至终被理所当然地著录在首位,充分体现出尊儒视域下对于儒家文献的尊重态度。但是儒家文献之后,其他诸家文献应该如何排列,佛教文献与道教文献各自居于何种位置,子部虽说能够自成一个学术体系,不同时代目录学家的学术思想仍存在差异性,故在编次诸家文献时建构有自己的义例,不同的义例反映出不同的目录分类学思想和学术主张。尤其本文关注的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还存在一个编排的次序先后之争。佛教文献和道教文献的编排次序,并非一个简单的孰先孰后的问题,毋庸讳言,编排的次序不同,反映出不同的受重视程度。
对于佛、道文献,《隋书》云:“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托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5]其著录编排较为简单,四部之后首先附录“道经”类,随后是“佛经”类。陈麦青先生认为:“《隋书·经籍志》的体例、类目安排等,一般都遵《七录》之制。然而在佛、道两类的排列上,却将《七录》的‘佛前道后’换成了‘道前佛后’,这恐怕非信手为之。”[2]《隋书》采取先道后佛的著录顺序,有唐初统治者将道教改造成为皇室宗教的时代思想渊源。
《旧唐书》和《新唐书》子部共分十七类,但并没有为佛、道文献专门立目,而是笼而统之归置于“道家类”中。“道家类”编排在“儒家类”之后,居子部第二位。其包罗文献门类甚多,首先著录老、庄之道学文献,然后是道教文献,佛教文献则忝陪末座,继承了《隋志》先道后佛的编排次序。
《崇文总目》子部分出二十类,值得称道的是,它区分了道家和佛、道二教文献,其中第二类是“道家类”,第十九和第二十类是“道书类”、“释书类”,宗教文献被置放在末尾,其中道教文献仍然居前。
《通志》诸子类下共分十一个二级类目,分别是儒术、道家、释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道教文献则没有二级类目,而是归并在“道家”类中,其类目相当庞杂,具体细分为“老子、庄子、诸子、阴符经、黄庭经”等二十五个三级类目,“阴符经”之后的三级类目多与道教文献有关。比较令人瞩目的是,佛教文献有独立的“释家类”二级类目,而且编次在子部第三位,远远高于其他名家、法家等的位次。“释家”类下的三级类目亦极精细,分为“传记、塔寺、论议、诠述、章钞、仪律、目录、音义、颂赞、语录”[4]等十种。郑樵实际上将道教文献编排在佛教文献之前,可惜没有专门为道教文献立目。但是,其将道、佛宗教文献在子部的序位大大提前,分别居于仅次于“儒术类”之后的第二、三位,充分体现出郑氏对佛、道文献的重视。
私家书录《郡斋读书志》的子类分儒家、道家、法家等十八类,其中道教文献和佛教文献分别著录在第十七、十八位,分别是“神仙类”、“释书类”,其佛、道文献的位次,受《崇文总目》影响甚巨。
《直斋书录解题》子部分二十个子目,道教文献和佛教文献分别著录在第十“神仙类”、十一“释氏类”。陈振孙摆脱了《隋志》《崇文总目》以及《郡斋读书志》等书录将宗教文献编排在某个类目末尾的传统思维,但是也没有郑樵提升佛、道文献位次的勇气,故而走了中庸路线,道、佛文献编排在第十、十一位,虽不如儒墨名法等传统子家显眼,但毕竟如兵书类、历象类、阴阳家类、类书类等九个类目都被甩在身后。
《文献通考》的子部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农家、阴旧家、
天文、历谱、五行、占筮、形法、兵书、医家、房中、神仙、释书、类书、杂艺术等二十二类。其中,道教文献居于第十九位,佛教文献居于第二十位,道、佛文献仅仅领先于“类书、杂艺术”两类文献,或可以说明马端临对宗教文献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够。
《明史·艺文志》子类分作十二类:除了“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十家之外,“十一曰道家类,十二曰释家类。”[6]其因袭《旧唐书》等的著录体例,将庄老之道学与道教文献混为一团,并没有为道教文献设置专门的子目。同时,在位次方面,宗教文献忝陪末座,再次回到《隋志》《崇文总目》以及《郡斋读书志》等书录编排宗教文献于子部末尾的传统。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有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十四类,佛、道文献仍然编排在末席。但是其具体序次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先佛后道。唐代以来重要官私书录一直持守着的先道后佛的文献编排传统,直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才最终被颠覆。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纪昀云:“诸志皆道先於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於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以释先於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7]按照纪昀的说法,并非他故意立异,只是回复到《魏书》《七录》等书目更古老的传统而已,也表现出纪昀等四库馆臣对于佛教文献的重视程度。
通过上面的梳理,唐以来主要官私书录的绝大多数将道教文献著录在佛教文献之前,而《四库全书总目》是唯一一部将佛教文献著录在道教文献之前的书录。但是道教文献和佛教文献在整个子部的排序,并无一定之规。为佛教文献设置单独二级类目并著录佛教文献最靠前的书录是《通志·艺文略》,编次在第三位,而编次佛教文献在最末的书录则有《隋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明史·艺文志》。道教文献因为与老庄道家的渊源,经常性被著录在子部“道家”类中,《旧唐书》《新唐书》《通志》等书录将“道家”类文献归置于子部第二位,但是往后的书录,“道家类”文献的编排渐次后移,《明史·艺文志》著录为倒数第二家,而《四库全书总目》则干脆将其著录在最后。可见,唐代以来书录中的佛道之争,不论是子部中的位次变化,还是编排中的先道后佛或先佛后道的次序,各自有其历史阶段性。总体的规律性则呈现出这样的轨迹:道教文献由唐初书录的推尊地位,逐渐在类目层级和子部序位两方面均呈下滑趋势,而佛教文献由唐初书录的最末位置,在类目层级和子部序位方面渐次上升,清代四库馆臣则最后完成了先佛后道这种转换。
三、著录规模的大小之争
书录的核心范畴是著录的内容,内容的多少以及质量的高低与著录范围的大小息息相关。如何取精用弘,著录的范围应该怎样控制,达到怎样的著录规模,都是书录编纂必须面对的问题。
因为唐以来主要书录编纂中始终贯穿着以儒家文献为核心的指导思想,故而官私书录不大可能出现既重视佛教文献又重视道教文献的情形,排除掉这一点,可以分别出这样三种情形:一则佛、道并轻,这是最主要的著录佛、道文献的方式,有《旧唐志》《新唐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书录。《旧唐志》道家类中所录“右道家一百二十五部,老子六十一家,庄子十七家,道、释诸说四十七家,凡九百六十卷”。[8]其中,附录有“释家类”文献22种178卷,道教文献则有25部355卷,道教文献和佛教文献所占比例都较小,根本不能反映出当时宗教文献的大致面貌。《新唐志》子部“道家类”一百三十七家,一百七十四部。前列老庄之道学文献,随后是道教文献:“凡神仙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失姓名十三家,自《道藏音义》以下不著录六十二家,二百六十五卷。”最后编排佛教文献:“凡释氏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失姓名一家,玄琬以下不著录七十四家,九百四十一卷。”[9]基本上沿袭了《旧唐志》的著录规模。《郡斋读书志》著录《四十二章经》《林间录》等53部佛教经论、僧传、灯录等,而“神仙类”则著录道教文献《度人经》等60部。[10]《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神仙类”文献55部,著录“释氏类”文献31部。[11]《文献通考》著录“神仙类”道教文献101部,著录佛教文献83部。[12]道教文献与佛教文献的著录规模都较小,可谓并轻。
一则重道轻佛,这方面有《崇文总目》《通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录。《崇文总目》卷九著录道教文献,共分九个部分,从“‘道书一’共五十五部计一百四卷”到“‘道书九’共六十部计一百六卷”,总计525部972卷。其卷十著录“释书类”文献,分作三部分:“‘释书上’共五十七部计三百三十六卷”;“‘释书中’共五十四部计八十九卷”;“‘释书下’共二十七部计二百二卷”,[13]共141部627卷,道
教文献的部数是佛教文献的近四倍。而《通志》著录道教文献规模:“凡道类二十五种,一千三百二十三部,三千七百六卷。”著录佛教文献规模:“凡释类十种,三百三十四部,一千七百七十七卷。”[4]又,《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范围则为:“右释家类十三部,三百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存目“十二部,一百一十七卷”。“右道家类四十四部,四百三十二卷。”存目“一百部,四百六十四卷”。[7]部数和卷数,道教文献都占据绝对优势,明显是重道轻佛。
一则重佛轻道,这方面有《隋志》和《明史·艺文志》等书录。《隋志》所附录道教、佛教文献共十五类。其中,道经“经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饵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录十七部,一百三卷”。合计四类377部,1216卷。佛经有“大乘经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小乘经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杂经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杂疑经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杂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大乘论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小乘论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杂论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记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合计十一类1950部,6198卷。[5]道教文献和佛教文献总计2327部、7414卷,个中道教文献的部数仅占16%,而佛教文献部数占84%;卷数方面,道教文献占近20%,而佛教文献占80%。故在著录范围方面,佛教文献具有压倒性优势。《明史·艺文志》著录如右:“道家类五十六部,二百六十七卷。”“释家类一百十五部,六百四十五卷。”[6]《明史·艺文志》著录佛、道文献的规模都受到限制,相对而言,佛教文献占据优势。
在儒家思想为绝对主导的传统背景下,佛、道两教难免受儒家思想的支配和控制。书录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离不开其所处历史时期政治思想和学术风气的影响,故而唐以来的官私书目编制也被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隋志》记载南齐王俭《七志》“其佛、道附见”,陈麦青先生认为:“道经在目录书中已和佛经并列著录,这表明当时道教经典已有和佛教经典并驾齐驱、相互抗衡之势了。”[2]但是唐代以来的主要官私书录著录佛教、道教文献,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则对于佛教、道教文献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整体上都没有反映宗教文献的特征;二则道教文献的规模无法与佛教文献相较,但因为本土宗教的优势,排序多靠前,存在先道后佛的观念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才真正扭转过来;三则著录范围的随意性太大,著录规模受到挤压,官私书录将宗教文献纳入儒家文化体系的意图与宗教文献的特殊性存在直接冲突。
[参考文献]
[1]卿希泰.中国道教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487.
[2]陈麦青.魏晋至唐初目录书中的佛、道两教[J].复旦学报,1991(1),86-87,90.
[3]王宗昱.官方目录学中的道书[J].北京社会科学,2000(4):44.
[4](宋)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605,1597,1640,1649.
[5](唐)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99.
[6](明)张廷玉,等.明史·艺文志卷三[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3,57,59.
[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5:1236, 1239,1241,1254.
[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30.
[9](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24.
[10](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37-800.
[11](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45-359.
[1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十一至五十四[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1161-1255.
[13](宋)王尧臣等撰,钱东垣辑.崇文总目卷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65-324.
[收稿日期]2014-09-29 [责任编辑]李金瓯
[作者简介]罗凌(1974-),男,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文章编号]1005-8214(2015)04-0062-05
[文献标志码]E
[中图分类号]G25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