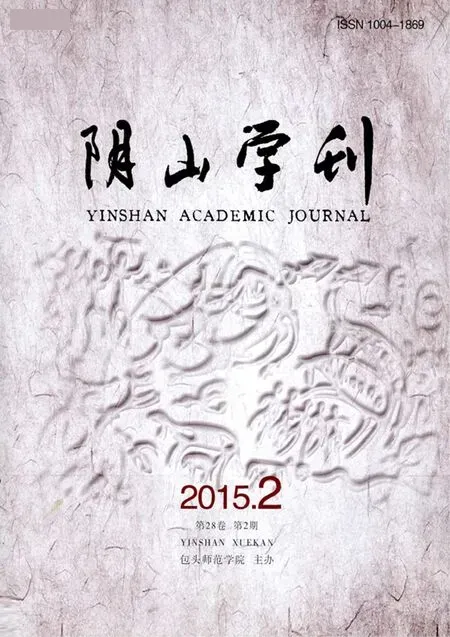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之“势”内涵辨析*
运 丽 君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之“势”内涵辨析*
运 丽 君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势”之内涵是“龙学”研究的一大悬疑,诸家各有阐发。诸多时贤将黄侃“法度”说与范文澜“标准”说归为同辙,二者其实不同。《定势》之“势”应指文体的基本格调。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势;文体基调
罗宗强先生认为:“刘勰理论的又一独具成就,是为中国文论提出了‘势’命题”。但他同时坦承:“势”,“是刘勰理论中最吸引人而又最飘忽空灵、最捉摸不定、难以把握的一个范畴。”[1](P350)
对此,“龙学”研究者可谓心有戚戚。由于刘勰以“图(描绘)风势”之法写作《定势》,“势之为训隐矣”[2](P110),从古迄今,对“势”内涵的理解说者纷纭,歧见颇多。
一、“势”内涵诸家释义
明清之际注家对《定势》之“势”已有关注,但多为漫评式,重在阐发研治印象、感悟。如明代曹学佺以为“势主风,为激水曲湍自然之态”[3](P218)。清代纪昀认为文各有自然之势,“行乎其不得不行,转也;止乎其不得不止,安也。”[4](P98)曹、纪二人对“势”不作正面阐发,像刘勰一样寓义于譬喻中,释义较为模糊。
近代黄侃探本索源,从文字考证上求解“势”之内涵,释为“法度”。《文心雕龙札记》引《考工记》、《说文》、《上林赋》作详细考训,指出:“势当为槷,槷者臬之假借。”“臬,射埻的也。”又因“臬”“本为射的,以其端正有法度,则引申为凡法度之称。”但究竟是什么方面的法度,黄侃语焉不详。且黄侃单纯从字义训诂上考求“势”的内涵,释为“法度”,这种脱离《定势》篇具体文本、语境解决问题的思路受到许多“龙学”研究者的置疑。刘永济认为,黄侃训释“虽合雅诂,非舍人之旨”[5](P212)。寇效信也认为这样的解释“辗转互证,迂曲难通”。寇效信并详细考证了《考工记》中“势”的含义以证黄侃释“势”之不确(寇效信《文心雕龙之“势”的辨析与探源》),其论证较令人信服。
进入现代,刘永济结合情、体、势三者关系论“势”,提出“体态”说。《文心雕龙校释》说:“势者,姿也。姿势为联语,或称姿态;体势,犹言体态也。”“体态”说确实较符合《定势》篇中论“势”的大量设比。但“体态”究竟为何?在古今写作理论乃至文论中都没有这样的术语。显然,“体态”这一词语概括有欠科学、周密。但它确实启迪学者们深入探析。
当代对《定势》篇的研究成果甚丰。目前,持论较多者认为“势”是“文体风格”。王元化、王运熙、张长青、张会恩、穆克宏等皆持此论。[6](P122)如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说:“刘勰提出体势这一概念,正是与体性相对。体性指的是风格的主观因素,体势则指的是风格的客观因素。”
当代第二种较为集中的观点是释“势”为“趋势”、“趋向”。如寇效信先生否认“势”是文体风格,但又指认“势”是“形成一定的文体风格的必然趋势”[7](P233)。詹锳先生认为“势”,“指的是作品的风格倾向,这种趋势变化无定。”“所谓‘定势’,就是要选定主导的风格倾向”[8](P62)。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把《定势》归入《文心雕龙》“风格论”的范围。
第三种观点是内在特点、客观规律说。如张少康先生认为“势”是作品本身的“客观规律性”[9](P117)。牟世金先生指认“势”是“随文体的要求而形成的特点”[10](P22~23)。郁沅先生说:“‘势’是特定内容在一定文体中的规律性表现方式”[11](P235)。
四是语调辞气说,语势说。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指出:“势是作品所表现的语言姿态,即语调辞气。本篇论述决定作品语言姿态的条件,所以叫《定势》。”童庆炳先生认为:“《定势》篇所讲的‘势’,是指语势,即《通变》篇所说的‘文辞气力’之‘势’”[12](P12~13)。
五是文体基调说。林杉先生在对诸家观点进行梳理和辨析后,以《定势》篇原文为本依,提出刘勰要定的“势”“是各种不同类型文体的基本格调。”[13](P149)
此外,还有把“势”释为“文体修辞方法”[14](P223),释为“气势、局势”[15](P52),或释为“机变”性[16](P250)等等。以上所有论证,或考据训诂,沿波讨源,或辗转互证,旁征博引,都能从《定势》篇找到一定的依据,有相通之处,却又很难达到共识。“势”的内涵究竟为何?至今悬疑未果。
二、“势者,标准也”——范文澜释“势”
范文澜是重要的《文心雕龙》学者,曾在南开大学等讲授《文心雕龙》。他著述的《文心雕龙注》(前身为《文心雕龙讲疏》),校勘细致、征引详赡、抉幽阐微、论理深富,被誉为“龙学”的奠基之作。“范注”因“文心为论文之书,更贵探求作意,究极微旨”[17](P34),对《文心》中的许多理论范畴抉幽阐微,征证考据,多所发明。同样,“范注”对《定势》之“势”范畴也作了深入探究、阐发。
范文澜紧紧立足于《定势》原文求解“势”的内涵。《文心雕龙注·定势》通俗而又确切地解释说:“文各有体,即体成势。章表奏议,不得杂以嘲弄,符册檄移,不得空谈风月,即所谓势也。”“文各有体”之“体”,指文体、体式,具体指“章表奏议”等文体。“不得”一词,强调“势”的文体规定性,“章表奏议”类文体取“势”的客观规定性就是“不得杂以嘲弄”。换言之,范注认为“不得杂以嘲弄”就是“章表奏议”类文体的“体势”规定或言标准。是故,范注以“标准”释“势”。《文心雕龙注·定势》说:“势者,标准也,审察题旨,知当用何种体制作标准。”指出“势”是文体体制“标准”。
刘勰在《定势》篇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准的乎”、“羽仪乎”、“楷式于”、“师范于”等即“以……为标准”、“以……准则”之意,与范注的“标准”一语正是同义。 刘勰与范注一正一反立论,其意是相通的、一致的,指出“势”是文体体制规范或言标准。
范注认为,这种体制标准是文体相对稳定的一种美学性能,是文体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他在注释《定势》篇“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句时说:“天圆则势自转动,地方则势自安静,天地至大,尚不能违自然之势,文章体势,亦如斯而已。”指出刘勰以自然之势为喻的目的,是阐明体之有势,实出自然,体势之异出于自然,体势有定,本于自然之理。故范注指出“势有一定”,其意是说每种文体有与其相应的特定的“体势”,“势”是“体”一种内在规定性要素,“体”不同“势”自不同,“势”受“体”的支配、制约,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客观规定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基于此,《文心雕龙注·定势》开篇批判了两种“体势”说,曰:“所谓势者,既非故作慷慨,叫嚣示雄,亦非强事低回,舒缓取姿。”这里明确指出,“势”不是写作主体表现于文章中的气势、文势,亦非写作主体主观上的“强事低回,舒缓取姿”,即“势”不是作者主体风格,在“体势”问题上,客观因素应为主宰,体势首先得顺应文体自身的客观要求。故范注说:“此篇与体性篇参阅,始悟定势之旨”。《体性》篇专论作家主体风格,而刘勰一向视“一意两出”为“义之骈枝”(《镕裁》),当然不会在《定势》篇再论写作主体风格。
范注的上述阐发是完全符合《定势》原文的。刘勰以物作比来阐明文体之“势”。《定势》说:“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刘勰在这段话中强调了“势”的两个特点:
一是说不同的“体”具有不同的“势”,“势”生于体并受体支配、制约。涧体曲折,涧水相应受体的制约形成了曲折回旋之“势”,受圆体的规束,相应形成了转动的“势”态,方体,其势“自安”,“槁木”,其势“无阴”。文体与其 “势”的关系也和自然之体、势一样,具有“势不自成,即体而成”、受体规范的特点。黄侃说:“离体立势,虽玄宰哲匠有所不能也。”[2](P110)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势由体定,不同的文体必然具有各自相应的、不同的“势”。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郭鹏先生说“定势”之“定”具有“辨体”的意味。[18](P228)
二是说,“势”是“体”与生俱来的,二者在生成上是共时性的,势定难违。
圆形物体易于滚动,当物形为圆时,“滚动”的自然之势同时已为圆形物所具备,“槁木无阴”,当树木枯槁时,“无阴”之势同时生成。“文章体势,如斯而已”。故《定势》赞曰:“形生势成,始末相承”,就是强调“势”在文体产生时已同时自然地生成了。有的研究者认为“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是说“由情而体,由体而势,是文学作品形成的自然程序”[19](P23~24),这种理解是欠妥的。“形”和“势”在生成上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共时性。这一点验之于实践信而不爽。从文体的生成看,一种文体从适应表现特定社会生活的需求产生,到经过漫长的、约定俗成的发展逐步稳固定型,“势”作为文体必不可少的内在要素,和文体同时生成。如萧统说:“美终而诔发”(《文选序》)。为了褒美死者,产生了诔这一文体。“诔体”顺应表达“哀情”的要求产生后,“暧乎若可觌”、“凄焉如可伤”的“体势”规范在表达的过程中同时生成并约定俗成下来。其次,从具体文章的生成看,在文章创作这个“因内而符外”、化无形为有形的过程中,“形生势成”是共时性的,不存在谁先谁后、谁为始谁为末的问题。故在这段比喻中,刘勰语意的重心在 “自然”一语上。刘勰反复以“自然”一语来规束“势”的生成原理,屡用“自转”、“自安”、“自然之趣”、“自然之势”,就是要强调“势”生成的自然、自为性与规律性。刘勰指出,圆体的“自转”之势,方体的“自安”之势,都是即“体”而生、“体”与生俱来的,是自然的、不得不然的趋势。说明“势”不是人为强加的,它是事物本身运动的必然趋势与客观规律。冠效信说:在“任自然这一点上”,刘勰是要“说明‘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和趋势”。[7](P156)其意正是强调“势”的客观规定性。黄侃亦言:“为文定势,一切率乎文体之自然,而不可横杂以成见也。惟彦和深明势之随体,故一篇之中,数言自然。”[2](P13~14)“体势”既然是文体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随体自然而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势定难违,特定的体有其相应的确定的“势”,这是恒定的,是不以写作主体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故“势”不是“无定而有定”的,它本身是确定的,无需另外再定。故此,范注“势有一定”的理解是完全符合刘勰原意的。这与黄侃“彼标其篇曰《定势》,而篇中所言,则皆言势之无定”的说法迥然不同[2](P110)。
在“定势”的具体原则和操作方法上,刘勰在《定势》篇提出“即体成势”,后又以“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等二十多种文体的体势标准为例,再次提出“循体而成势”,对此,范注阐释为“体势相因”。范注曰:“体势相因,即文非最休,亦可以无大过矣。”即指出,“体势相因”乃是文体写作的最基本要求,只有依据写作体裁表现出与“体”相应的“势”,才不会出现“失体”现象。是故,范文澜在注释“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句时说:“此以绘事喻文势也。势之不得离体,犹善画马者不得画犬如马”。其意是说:马的形体特征是一定的,如“体”,故有画法上的基本规范,如“势”;倘若违反了画马的基本规范,用画犬的方法体现,其“势”与“体”不相吻合,马也就不成其为马,也就“失体成怪”了。因此,范注强调,在“体势”的表现上,要“体势相因”,“文辞虽贵通变,而势之大本不可背离”。“势之大本”,指文体对“体势”最基本的要求,概相当于刘勰所说的“总一之势”,要求写作者从宏观上、总体上遵守各类文体的体势规范,写出合体的文章。
从上引范注阐述可见,范注指出“势”是文体体制方面的“标准”,是受体支配的,特定的“体”有与之相应的“势”,这是文体自然生成的,是客观、恒定的,写作时必须做到“体势相因”,才不会因“讹势”而“失体”。这些阐述不仅和《定势》原文紧密契合,而且范注释“势”为文体体制的“标准”是有所指的,这与黄侃抽象地释“势”为“法度”完全不同。但“势”究竟是文体体制方面的什么标准,惜范注言犹未尽,融而未明。
三、“势”是文体的基本格调
刘勰说:“将核其论,必征言也”(《征圣》),“势”的内涵为何,必须以《定势》篇和《文心》原文为本依来求解、印证。
其实,除了形象的比喻外,《定势》篇有一段较为关键的话说明什么是“势”: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在这段话中,刘勰以归类的方式指出所例各类文体基本的体势标准。如“章表奏议”类文体体势标准是“典雅”。那么,刘勰用“典雅”和“清丽”是表明“章表奏议”与“赋颂歌诗”类文体什么规定性要素呢?张灯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好,要想准确解释“势”,除了势字本身的训释外,还应看“在其创作论中应属何种概念范畴”[20](P54)。我国写作理论中的范畴、术语是传承发展的,我们用范文澜的“标准”或当代学者的“内在特点”、“规律性表现方式”来释“势”,与古今写作理论概念、术语并不对接,也不准确。那么,“势”是当代诸多学者所言“文体风格”吗?研究《文心雕龙》必须注意到一点,刘勰对《文心雕龙》中理论范畴的概括和命名,往往赋予其独特而各自不能取代的内容和深义,而如果把“体性”之“体”与“定势”之“势”都解作“风格”,就值得考虑了。故郁沅先生在将《体性》中的“八体”与《定势》中的“六类”(典雅、清丽、明断等)进行精细的比对、严格的推理论证后指出:“《体性》篇中的‘体’这一风格概念,既指主体风格,也指文体风格。”故他指出:“既然‘体’已经包括了文体风格”,刘勰就没有必要“再另立一个‘势’来指文体风格了”[11](P229)。他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涂光社先生在《文心雕龙·定势论浅说》中也表示反对:“倘将含有风格因素的术语,如像《文心》中的‘体’、‘体势’、‘势’统统不加区别地释为风格,至少是忽略了它们各自不能取代的特点,这样做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21](P1112)石家宜先生结合《定势》篇的主旨及《文心》的理论体系等问题驳斥“文体风格”说,他认为《定势》篇的主旨并非“讨论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如果把《定势》篇仅仅看成是论述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那就很有可能掩盖了刘勰以‘定势’命篇的更深一层的用意。”[16](P243)这些意见是非常有见地的。“文体风格”说的思路虽然大体可行,但用“文体风格”概括“势”的内涵,这一提法是不妥当的。其实,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范文澜先生屡言:《文心雕龙》是一部“作文法则”[22](P213)。从写作理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被时贤划归于“创作论”部分的《定势》篇,所谓“势”是指文体的基本格调。
文体的基本格调概指写作一类文体时应有的态度、情调、韵味、情绪等融合后体现出来的一种总的共同性。它是文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顺应文体表现内容的需求而自然生成、并逐渐稳固下来的审美定式,是基于共同文化、审美心理之上的传统规范。因此,《定势》篇一开始便以“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势也”为例,说明“形生势成”、“体以定势”、势定难违的道理。每种文体都有其相应的基本格调,如“赋颂歌诗”类文体的基本格调就是“清丽”,尽管因写作主体“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特点,但总的基调是无法更改的,刘勰提出写作必须符合“总一之势”,范注曰:“总一,犹言一体,雅体不得杂以郑声也”。又曰:“文辞虽贵通变,而势之大本不可背离”,其意是说写作主体在创作中可以发扬个性风格,但不可违背文体的基本格调。文体的基本格调对写作该类文体所有作品具有普遍的统摄、规范作用。故刘勰说:“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典雅”与“艳逸”是“经”和“骚”两类文体固有的基本格调,所以模仿它们写成的文章也会获得与其相同的文体基调。但不同类型的文体,基本格调不同,这是文体经过长期发展积淀而成的审美规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是“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的,即强调“势”所具有的辨体的严格性。刘勰非常重视在“杂体”中进行“铨别”,以防因“讹势”而造成“失体成怪”。范注曰:“功在铨别,即所谓定势”,指出“铨别”的关键是“定势”,道出了刘勰以“定势”命篇意在强调写作中通过铨别体势来辨体、定体的创作意图。是故,刘勰提出写作要“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因情立体”,即从所要表现的情感、思想出发,来选择、确立相应的文章体制。如“悲悼之情”与“祝贺之意”有别,必然要选择不同的文体去承载。“即体成势”是说,特定的文体必须表现与之相应的体势。如祝贺类文体的基本格调是“修辞立诚”(《祝盟》)、喜庆、热烈,如果写得悲伤、凄苦则“失体成怪”了。故当不同的“情”选择与之相应的“体”去承载时,不同的文体应表现出相应的体势,曰“循体成势”、“随变立功”。“随变”二字,并不是随意变换文势,而是说应随着文体不同表现与之相应的体势。
此外,范文澜虽未明确阐释“势”的内涵,但从范注对“讹势”的论述上,其实可以看出“势”的内涵所指。
范文澜在注释《定势》篇“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句时说:“彦和非谓文不当新奇,但须不失正理耳。上文云‘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羽仪乎清丽’,言文章措辞,势有一定,若颠倒文句,穿凿失正,此齐梁辞人好巧取新之病也。……世之作者,或捃摭古籍艰晦之字,以自饰其浅陋,或弃当世通用之语,而多杂诡怪不适之文,此盖采讹势而成怪体耳。”
范注认为,每种文体的体势有一定审美规范,即“势有一定”,如“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典雅”就是“章表奏议”类文体规范的“体势”,是故写文章措辞造句,应受该类文体体势支配、为表现体势服务,此即刘勰所言“宫商朱紫,随势各配”。而齐梁时代的作者,或“颠倒文句”,或“弃当世通用之语”而“捃摭古籍艰晦之字”,或“多杂诡怪不适之文”,选词造句一味“好巧取新”,违反了文体体势规范,造成了“讹势”,进而导致“怪体”。
范文澜在注释《通变》篇“宋初讹而新”句时又征引孙德谦《六朝丽指》所言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孙德谦曰:“文心通变篇宋初讹而新。谓之讹者,未有解也。及定势篇则释之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观此,则讹之为用,在取新奇也。”“讹势”有何危害呢?范注引孙德谦进一步指出:“诡更文体”。为此,他特意例举江文通为萧拜太尉扬州牧表“若殒若殡”句所用“殡”字之误,说明“章表之体,理宜谨重”,而“殡”字之用,则“惟务新奇,讹谬若此也”。可见,孙德谦之所以认为“殡”字用得有误,是因为它破坏、违反了“章表”体“谨重”的“体势”写作规范,造成了“讹势”,进而“诡更文体”。而孙德清所言的“谨重”意同于刘勰所言“典雅”,正是指“章表”类文体的基本格调。
再次,文体的基本格调是从内容、结构、取事、用辞等多方面综合体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性的审美感受。它作为文体本身固有的内在要求和审美规范,也对作品构成的方方面面进行约束和规范。范注说:“势者,标准也。……标准既定,则意有取舍,辞有简择。”指出“意”、“辞”都受到“势”的约束。刘勰说:“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就是从“意”与“辞”两方面谈与“势”的关系。《定势》篇说:“宫商朱紫,随势各配”。也道出了“势”与文辞之间的关系。文辞受文体基调的支配、制约,为烘托、表现特定的文体基调服务。刘勰批评“尚势不取悦泽”的做法,提出“势实须泽”的观点。范注曰:“悦泽为润色。势实须泽,犹言文之体式虽合,而辞句之润色,所以助成文体,安可忽乎。”指出写作者应以妥帖、生动的言辞鲜明的表达出文章的基本格调,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合体,使表意更鲜明。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更通俗地以“营造”为喻说明这个道理。他举例说,为了表肃敬之情,所以选择营造宗庙之作,此好比“因情立体”。宗庙的基本格调是庄严肃穆,故宗庙的结构规模,“宜极庄严宏丽之致”,“宗庙之中,大而一楹一柱,小而一户一牖”,都应与宗庙“庄严肃穆”的基本格调相合,“绣闳香帏”、“茅茨土阶”都不庄严敬重,所以皆不可施。这样“使人入其中者,一望而生恪恭寅畏之心”,最终能完美地达到表肃敬之情的目的。刘释也是强调文体体势应与作品的内容表现、情感抒发、谋篇布局、遣词造语等保持一致、和谐、统一和完整,并通过这些因素综合体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心雕龙注·定势》说:“本书上篇列举文章多体,而每体必敷理以举统,即论每体应取之势。”《文心雕龙注·总术》强调:“审定体势,上篇所论是也。”揭示了《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主要目的是“审定体势”。而详察“论文叙笔”之“敷理以举统”中所论各种文体之“大体”,其主要内容确实在于规范文体的基调特色与写作要求。如写作“诗”体,要求“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写作“赋”体:“义必明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诠赋》);“驳议”写作:“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事以明核为美”(《议对》);写作“论”体:“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论说》);写作“连珠”体要“义明”、“辞净”、“事圆”(《杂文》);“颂”体应写得“义必纯美”、“辞必清铄”(《颂赞》);写作“盟”体要“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祝盟》);写作“铭”体“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铭箴》),以此达到“体贵宏润”的“总一之势”,等等。从上述所举文体所规定的成体规范看来,“雅润”、“清丽”、“明雅”、“清铄”、“确切”、“宏润”、“辨洁”、“明核”等各体的“大体”、“大要”,与《定势》篇列举的“典雅”、“清丽”、“弘深”等体势要求具有质的相同性,就是指文体的基本格调,且是从义、辞等多方面规约的。《定势》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章表》说:“章以造阙,风矩应明”;“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其意是说,一则,章是上呈朝廷的,风姿和矩式应当明朗;二则,章要以典谟为范式,其体制应光彩显耀重于文饰;三则,章类文体内容的表达要既精要又不疏略,既明显而又不肤浅。此即从风姿、矩式、修辞、内容表达等各个方面对“章”类文体基本格调的表达提出约束、规范,其总的要求正是“典雅”。
综上所述,范注以文体“标准”一词阐释“势”的内涵,虽所指不够明确,但依据《定势》原文所述及范注对《定势》篇的阐释,笔者认为,“势”就是指文体的基本格调。刘勰写作《定势》的目的,是针对当时“讹势”、“失体成怪”的文弊,提出“势”这个范畴,确定“循体成势”等原则为补偏救弊的药方,以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体势”讹变,抵制当时“逐奇失正”的讹滥文风。
[1]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钟惺.五家言序[M].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总目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纪晓岚.纪晓岚评文心雕龙[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5]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寇效信.释“体势”[A].《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学刊(1)[C].济南:齐鲁书社,1983.
[8]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1987.
[10]牟世金.刘勰论“图风势”[J].文学遗产,1981,(2).
[11]郁沅.《文心雕龙·定势》诸家研究之评议[A].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12]童庆炳.文心雕龙“循体成势”说[J].河北学刊,2008,(3).
[13]林杉.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
[14]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5]陆侃如,牟世金.刘勰和《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16]石家宜.《文心雕龙》系统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8]郭鹏.《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和历史渊源[M].济南:齐鲁书社,2004.
[19]吴建民.《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2004,(2).
[20]张灯.《文心雕龙·定势》疑义辨析举隅十条[J].贵州社会科学,1994,(4).
[21]涂光社.《文心雕龙·定势》论浅说[A].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2]范文兰.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责任编辑 王 宇〕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Shi”In Fan Wenlan’s “The Annotation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YUN Li-jun
(School of Libral Arts,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014030)
The connotation of “Shi” is a big suspense of the research of “Dragon Study” on which many researchers have comments. Researchers tend to classify the “Moral Standard” of Huang Kan with Fan Wenlan’s “Standard”; however the two are in fact different.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conclusion that “Shi” of “Ding Shi” refers to the basic essay style.
Fan Wenlan; “The Annotation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Shi”; Basic essay style
2014-09-10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文心雕龙》范注中的‘文术论’研究”(NJSY11157)部分研究成果。
运丽君(1975-),女,内蒙古巴彦淖尔人,硕士,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创作理论和写作研究。
I044
A
1004-1869(2015)02-0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