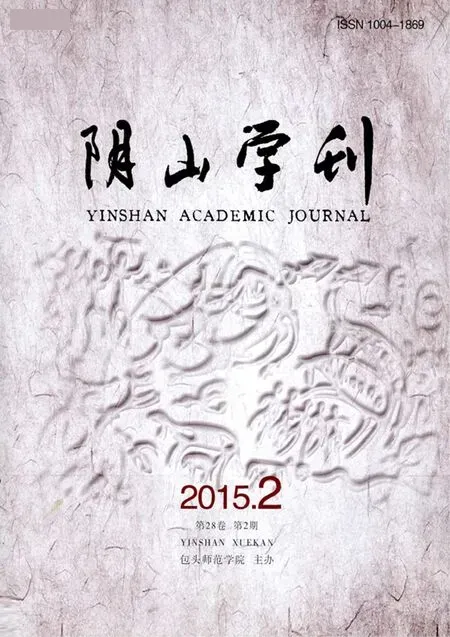庄子语境中的“德”“形”之辨*
王 传 林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庄子语境中的“德”“形”之辨*
王 传 林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在庄子的哲学语境下,“德”不仅具有形上性与内在性,而且也具有形下性与实践性;相对而言,“形”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形上性,但更多的还是形下性与外在性的。在“德”与“形”的价值判断上,庄子看重的是内在之德,而非外在之形。庄子以游心于德和为基点,以德兼于道为理路,以辨德之本末,以论德之立修,以别德形关系;不仅表达了他对当时之世的不满与批判,而且也揭露了当时世人的伪善与狡诈。一言以蔽之,庄子视域中的“德”“形”关系与价值取向是:一、形残而德可全;德全胜于形全;才全而德不形;二、重“德”不重“形”;重内不重外;重自然与无为,不重雕饰与有为。
庄子;德;形;意涵;特性;逻辑关系
商周之际,“德”作为重要的伦理范式已经被论及,一度被提升“以德配天”的形上高度与“敬德保民”的政治高度,甚至成为新旧王朝政权更迭的合法性之凭藉。相对而言,“形”作为哲学范畴虽早已有论,但是其在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传播与影响较之“德”还是要逊色的多。春秋之际,自老子与孔子始,道家与儒家对“德”的定义就已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时至战国,这一点在庄子的道德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庄子沿着老子的理路不仅拓展了“德”的意涵,而且提出了有别于当世诸子的论见。
在庄子的哲学语境下,“德”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形上性与内在性,而且也具有形下性与实践性;相对而言,“形”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形上性,但更多的还是形下性与外在性的。在“德”与“形”之间,庄子看重的是内在之德,而非外在之形。究而言之,“德”与“形”在庄子那里到底有哪些区别与联系,二者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内在张力?在此,本文以《庄子》内篇为据兼涉外杂诸篇,且对庄子道德哲学语境下的“德”“形”之意涵、特性及其逻辑关系略加缕析。
一、“德”之意涵及特性
纵览《庄子》,“德”字频现。庄子尝云:“德者,成和之修也”(《庄子·德充符》[1](P214~215),以下只注篇名),“夫德,和也;道,理也”(《缮性》),“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天地》),“物得以生,谓之德”(同上),“通于天地者,德也”(同上),“调而应之,德也”(《知北游》)等。概之,所谓“德”,可从内外谓之:内化于心,可以情感或信念谓之;外化于行,可以本性、品德或德行谓之。从哲学理路上看,庄子以“道”为本体建构出道德形而上学,以“德兼于道”(《天地》)的路径推衍出其道德哲学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向度。庄子认为“自本自根”(《大宗师》)的“道”是生成万物的神秘始基,同时庄子将“德”置于“道”之下并从形而上的高度赋予“德”以深刻意涵。在庄子的哲学视域中,天地先“我”而生,当“我”置于天地之维度中时,则“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我”在天地之时空中体认万物与大道,并在精神层面与之“为一”——“通于天地”、“复通于一”。因此,我们认为:在庄子的道德哲学语境中,由“道”而衍的“德”蕴含着丰富的意涵及特性。
(一)“德”之形上意涵及特性。由天至道,由道至德;正是在肯定了“我”在天地中的存在性与道德性的同时,庄子从道德形而上学的高度提出了“德”。庄子认为,“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天地》)。简言之,庄子所言的“天”不仅具有至上性,而且具有道德性;由天至人,其逻辑理路与价值向度是:由天至道,由道至德,由德至义……由天道贯通人事的价值向度次第展开。由德而类,推而论之;庄子分别阐述了“天德”、“至德”与“玄德”。
何谓天德?简言之,即指天的至善性与圆满性。庄子曾借舜之口以隐喻的方式论述说:“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天道》)。进而,庄子提出圣人之生死也应该随天行、合天德,他说:“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惔,乃合天德”(《刻意》)。由上观之,在庄子的哲学语境下,无论是“我”还是“圣人”,对“道”虽可体认,但却无法定义;无论是“我”还是“圣人”,都应该“循天之理”、“以合天德”。
何谓至德?在庄子那里,“德”作为形而上的存在是有不同层次的,其中,“至德”为上。诚如《德充符》篇所言无假、守宗、保始,皆德之和也;惟德之和,乃是至德。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庄子对“至德之世”进行了理想化的论述并传达出心向往之的憧憬之情,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马蹄》);“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同上);“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在庄子看来,儒墨所言的仁义的出现是因为道德有失,而且庄子认为儒墨所言的仁义是对人们淳朴本性的伤害。他说:“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
何谓玄德?在道家哲学思想中,老子率先对“玄德”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万物没有不遵从道而贵德的;他说:“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2](P204)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十章)进一步阐释说:“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3](P24)质言之,庄子对“玄德”又有哪些拓展呢?在庄子那里,“道”以客观性存于外,而“德”不仅仅具有外在客观性与形上性,而且又有内在的实存性与感受性;例如庄子认为“物得以生,谓之德”(《天地》)。同时,庄子认为“德”与“心”相关,而且“我”能够“游心于德之和”(《德充符》)。在老子“玄德”思想的基础上,庄子曾论述说:“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天地》)。在庄子看来,所谓“玄德”,其表象仿佛“若愚若昏”,其实质与天地相合,其性状至纯而且葆有自然之初态,其境界至高而且玄远;亦如老子所言:“玄德深远,与物反,然后乃至大顺”[2](P266);尽管如此,但是“我”之“心”却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
总的来看,在庄子那里,内在之德属于内在直观之定在,外在之德则属于经验直观之定在;同时,内在之德具有单纯性,外在之德具有多样性。当然,庄子在很大程度上对外在之德持否定态度,对内在之德持肯定态度。道德主体如何能够内在地直观自己,如何能够从内在直观中抽绎出“天德”、“至德”与“玄德”?庄子并没有沿着老子提出的“玄览”、“玄同”的逻辑理路论证下去,而是通过大量的喻证与寓言予以诗意化的描述;例如他说:“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秋水》);“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马蹄》);等。同时,庄子提出可以通过道德个体的外感官与内感官即外在直观与内在直观去体认“德”,他说:“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外物》)。庄子由内及外地体认“德”的存在,将其推展到社会与政治层面完成了向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转进;同时,他也给出了与众不同的哲学论断并对儒墨所言仁义等道德规范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二)“德”之规范意涵及特性。其实,圣人、贤人、君子等概念在庄子之前已有散论;与前人不同的是,庄子对此进行了独特的论证并提出了“真人”论,同时也给出了自己评价圣人的标准,他说:“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徐无鬼》)。在道德修养层面,庄子就“德”的逻辑性及层次性也给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例如真人之德、帝王之德、残人之德等。
何谓真人之德?在庄子那里,“真人”所具备的品质是以“德”为凭借的,他说:“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同上);“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同上)。这就是说,“真人”不违逆微少、不逞强求成、不谋虑俗事;“真人”睡觉时不会做梦,醒来时不会烦恼,饮食不觉甘美,其呼吸深沉绵长;“真人”不会乐生,不会怕死;生不欣喜,死不拒绝;无拘无束地死,无拘无束地生。在庄子看来,生死皆由命,若夜旦之常;“我”存在于自然中,面对自然规律,应该坦然自若。
何谓帝王之德?面对纷扰动荡的社会,庄子虽然多有批判但是却并没有完全否定统治者的作用,尤其是在对帝王的批判中,庄子多是从天道无为与自然本性的角度去否定人为的功用,多是从道德的高度去批判帝王的攻伐角力与文治武功;他说:“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天地》)。在庄子眼中,过去的诸多帝王既没有真正地领悟大道,也没有循德而治;因此庄子指出帝王应该具有帝王之德,他说:“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天道》)。在庄子看来,在现实的政治统治中,帝王们若能做到虚静恬淡、寂寞无为,那么就会“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同上)。进而,庄子指出:“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馀;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上)。由此观之,庄子认为帝王们应该以天地为宗,顺天地之道,崇尚道德,以无为为方策。唯有如此,方可达到“帝王无为而天下功”的局面。较之,庄子的这种思想和老子的“无为无不为”可谓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后人多不察,而且多批评庄子倡导无为思想、消极避世。
何谓残人之德?庄子在寓言故事中虚构出一批形残而德全之人,这些人的德之光掩盖了其形之残或曰其德足以弥补其形之残,因此他们多为世人所景仰与钦慕。当然,庄子的寓言故事并不是一般性的事实描述,而是寄其深意的;庄子意在借他们之口表达出自己对世俗的批判。例如,在《德充符》篇中,庄子虚构出申徒嘉并借其口论及德与形之关系,申徒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德充符》)。在此,庄子还虚拟出无趾与孔子对话,以致孔子自叹不如并告诫其弟子应该勉之。因此,我们解读《庄子》之文应该玩索其语言虚实的张力及其背后的隐意,应该透过文字发掘出庄子对世俗道德规范与价值观的批判。当然,初看起来,庄子是不走寻常路——褒扬形残而德全之人,贬斥形全而德缺之人;其论好像有些荒诞不经,然而细细玩索,便不难发觉庄子对徒有虚名、徒有其表的世俗功利化思想的精准批判与其论之高妙。
(三)“德”之实践意涵及特性。尽管庄子所言之“德”与儒家所言之“德”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庄子并非完全否定“德”之于道德实践与人格修养的作用。下面,我们从“立德”与“修德”的层面对庄子语境下的“德”之实践性略加讨论。
何谓立德?庄子认为:“德成之谓立”(《天地》)。这就是说,德不成无以言立,唯德有所成才能算是立德。在庄子看来,立德有内外两个维度与本末两个层次。从道德个体之内在方面来看,庄子认为外感官与内感官按照一定规律发生作用才能达到对“德”的体会与确认,进而做到“合于天地”、“游心于德”、“去德之累”、“退仁义、摒礼乐”。从道德的外在性来看,庄子认为:“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胠箧》)。也就是说,在庄子看来,史、杨、墨、师旷等人皆忙于外立其德,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扰乱天下。换言之,庄子强调的是内在的立德,而非外在的立德、立功。
何谓修德?在庄子的哲学语境下,道德个体不仅要注重“立德”,而且还应该注重“修德”。那么,如何做才能实现“修德”呢?庄子托喻“古之真人”,强调“以德为循”(《大宗师》);进而,他指出:“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在此,庄子肯定了“心有所定”对“修德”的重要性。在庄子看来,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个体还应该:“彻志之勃,解心之缪,去德之累,达道之塞。富、贵、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庚桑楚》)。这就是说,在庄子看来,外在的功名利禄、富贵显达、容色气意、喜怒哀乐、去就取与等世俗诱惑与人之欲求皆不利于修心修德,反而成为修德循道之障碍。因此,庄子主张应该摒弃诸种诱惑与烦扰,如是,才能修心修德、融通大道。
诚然,在庄子的哲学语境下,所谓“修德”其实质是“心修”,而不是“形修”,更不是按照儒墨所倡仁义礼智等规范去修炼出光风霁月的高大形象。因此,庄子强调“坐忘”与“心斋”,甚至提出“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天地》)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庄子看来,天下无道,与其进而抱薪救火、枉费心机尽做无益之举,不如退而着意修德、与世无刃、与人无隙,以就闲适,游心于德[8](P9~10)。
二、“形”之意涵及特性
何谓“形”呢?从语义学角度看,形者,物之象、人之表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史记·太史公自序》)[4](P3292)。诚如,《说文解字·彡部》云:“形:象形也。从彡幵声。”[5](P716)又如,《释名·释形体》云:“形,有形象之异也。”[6](P60)概之,“形”之本义,指象、画、物之表也。然而,上述解释似乎并没有完全道尽庄子道德哲学语境下的“形”之意涵。
在庄子道德哲学语境下,“形”作为与“德”相对应的哲学范畴也常被论及;分类论之,大抵如下:其一,人之形。在庄子的视域中,人之形乃是天与之,他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师》);“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德充符》)。由此可见,庄子认为天地阴阳四时之和谐与否与人之形有重要的关系,故而他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在宥》)此外,在庄子那里,人之形是可离的、可堕的,如此才能呈现内在纯性,实现逍遥游;诚如他说:“形固可使如槁木”(《齐物论》),“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在宥》)。尽管如此,庄子却没有完全否定“形”的存在,从顺乎大道、应乎自然的维度,庄子认为生命个体应该“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齐物论》),并提出“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人间世》)之高见。其二,物之形。从生成论的维度看,庄子认为:“物成生理谓之形”(《天地》);“……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同上);“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寓言》)。由此观之,庄子从生成论的角度不仅论证了“形”的客观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生物进化的逻辑路向。只不过,庄子眼中的“物成生理谓之形”、“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是表层的物物相异、是“始卒若环”的循环论。在庄子那里,物以形成,形以道成;物之形源于道,而道则是无形的。其三,天地之形。“有”是“无”之分,“形”是“道”之分。在庄子看来,“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则阳》);“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庚桑楚》)可以看出,庄子将作为感性认知与生存体验对象的天与地以形上性的“形”予以统而概括,完成了对天与地的另一种概念化的体认与建构;进而,他以“道分成形”的逻辑理路将作为客观存在的天与地纳入至概念化、形上化的“道”中。由此,“形”在庄子的道德哲学中被赋予了丰瞻的意涵及特性。
(一)“形”之形上意涵及特性。所谓“形”之形上性,只是相对而言,其实“形”原指具体之物的表象;但是在庄子那里,“形”与“道”、“德”之间确然存在一定的生成与依存关系,这使得“形”具有了某种形上性。诚如他说:“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天地》)从生成论的视角看,庄子对“形”也有明确的论述,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同上)。在《知北游》篇中,庄子托言于孔子与老聃关于“至道”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这一点;庄子借老聃之口说:“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知北游》);“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同上)也就是说,庄子认为道之无形、物之有形,物之有形源于道之无形,即万物以形而生。从认知的角度看,在庄子那里,“形”之形上性还体现在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的认知层面。在庄子看来,“太一形虚”(《列御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寓言》),“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则阳》)。凡此可见,在庄子眼中,“形”既是具体的、表象的,又是形上的、无定形的;同时,“形”又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它体现在万事万物中,能够为认知主体所认知。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形”呢?对此,庄子从“复通为一”的角度论证了“形”之于生死的意涵。据《至乐》篇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此时,惠子与庄子就有形、无形与生死展开了讨论,庄子认为:“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在庄子看来,生死之状与有无之形只是道与气的具体呈现——“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需要指出的是,庄子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拘泥于“形”、执著于“形”;他说:“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列御寇》)这就是说,如果过于执著于“形”,则会导致“形累不知太初”。当然,庄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对“以形造形”的,他曾寄言于徐无鬼说:“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变固外战。”(《徐无鬼》)由上观之,从生成论层面看,道本无形、物成于形,道为物根、物为道形。从认知论层面看,天地有形、万物诸形,所谓有形无形皆在气之变也。从生死观层面看,识得真“形”,方识大道;除却假“形”,不为所累;看破俗形,不为所造。
(二)“形”之道德意涵及特性。在庄子那里,尽管“形”是形上的、外在的、表象的,但是“形”之于道德个体而言却又具有一定的道德性与规范性。在此,庄子提出了“人之形”、“守形”、“形色”、“养形”、“成形”等哲学范畴。
在庄子那里,“人之形”是道之所成,是气之所聚,是自然和谐所至;反之,如果“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在宥》)如上所论,形之于道,其位相次;神若守形,形乃长生;诚如《在宥》篇所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复如《刻意》篇所云:“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也就是说,修身治世之要在于体认大道,如若能够“无视无听,抱神以静”,那么“形将自正”、“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从另一个角度看,庄子对“形”与“心”的关系也十分看重。在《在宥》篇中,庄子借鸿蒙之口论及“养心”,其曰:“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可见,在庄子那里,“形体”是个体入道的困累,若要达到“与道为一”就必须“堕其形体”,如此才能消解“形体”对心灵的困囿。在庄子看来,“形充空虚,乃至委蛇”(《天运》)。又,在谆芒与苑风讨论何谓“德人”与“神人”的对话中,庄子借苑风之口说:“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天地》)。由此可见,在庄子眼中,“形”作为某种具体的存在应该被消解或消亡,如此才有可能实现“照旷”,进而达到“混冥”之境。遗憾的是,在庄子看来,今人多重“形”,而不重“心”;他说:“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谓:遁其天,离其性,灭其情,亡其神,以众为。故卤莽其性者,欲恶之孽,为性萑苇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并溃漏发,不择所出,漂疽疥癕,内热溲膏是也。”(《则阳》)因此,庄子反复强调要“堕其形体”、“吾丧我”、“坐忘”,并试图以此来消解“形”对“心”的困累,进而实现“道通为一”、“逍遥而游”。另据《田子方》所载: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说:“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田子方》)。凡此可见,“遗形”之于“游心”的重要性。
此外,庄子还从“养形”与“成形”的层面论述了“形”之于“人”的道德意涵。在庄子看来,“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馀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达生》)又,在《田子方》篇中,庄子托言于颜渊与仲尼的对话,庄子借仲尼之口说:“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虽然,女奚患焉!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由此观之,在世人看来,“形”可以养,“养形足以存生”;但是庄子对此却是持批评态度的。在庄子看来,“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唯有顺大道、应自然、达其情、达其命;如是,人生可达生、至乐也。在庄子看来,“形”不必养,“形”成而受之即可矣;世间万物出存入亡、生死如气之聚散,生命个体一旦“形”成,理应顺乎天道自然,端然待尽,以此终年;犹如庄子在《应帝王》篇中所描绘的列子“块然独以其形立”之形象。
(三)“形”之实践意涵及特性。所谓“形”之实践性,本文主要是从“形”之形下性去剖析“形”之于道德主体的意涵。在庄子看来,“形”受于道,“形”成于天;任何雕琢皆是“有为”反倒是对“形”之自然本性的伤害。因此,庄子认为“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天道》);进而,庄子从历史哲学的维度论述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同上)。可见,“道德”、“形名”在庄子哲学进路中的逻辑位次与价值次序;较之,“道德”次于“大道”,“形名”次于“道德”。
从修身体道的层面,庄子认为道分形至,因之受之;如若复归大道、与道为一,则应“堕其形体”。也就是说,在庄子的逻辑进路中,“人”不应劳形伤神,更不应去做无谓的矫饰;因此庄子指出“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刻意》)。在庄子看来,“人”如果要达到与道为一的理想境界,应该“堕尔形体,吐尔聪明”(《天运》),“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在宥》);不应该“劳形怵心”(《应帝王》)、“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渔父》)。基此可见,在庄子那里,“形”对于“人”体认大道是一种困累,若要达到“与道为一”就必须“堕其形体”,如此才能消解“形体”对心灵的困囿。换言之,在庄子眼中,“形”作为某种具体的存在应该被消解与销亡,如此才有可能实现“照旷”(《天地》),进而达到“混冥”(同上)之境。从人性的层面,庄子认为世人常为形名所困,尤其是得利得势时更是得意忘形,如此皆造成对自身本性的戕害。在庄子眼中,世俗之人逐利若“螳蜋捕蝉”——得意忘形,而不知“黄鹊在后”;他说:“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蜋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山木》);如是,实可悲矣。因此,庄子强调说:“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达生》)同时,庄子通过举例的方式论证了自己对“形”的否定性观点;在鲁侯与梓庆的对话中,庄子托言于梓庆云:“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同上)由此可见,唯有返朴归真,方可识得大道;唯有摆脱功名利禄之困,方可静心、忘吾、观天性;如是,才能“以天合天”,识性达生。从政治的层面,庄子提醒为政者不应只重外在之形,他借市南子之口说:“吾愿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山木》)。在庄子看来,为政者尤其是人君若要实现天下大治,应该实行无为之法,使民自化;如果要实现个人的至乐与逍遥,则应该“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如此,方能实现治身与治国的至高境界。在庄子看来,治国之重不如治身之重,因此他借市南子之口说:“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山木》)。此外,在“形”、“志”、“利”、“道”的逻辑关系中,庄子进一步明确了其逻辑路向,他说:“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让王》)。
综上,庄子从形生于道、形成于物的维度赋予了“形”之形上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肯定了“形”的存在性与客观性。尽管庄子承认,“形”源于道、“形”根于天,理应受之、应之,但是庄子从“人”之道德实践的层面却又否定了“形”之于道、“形”之于性的地位。原因在于,倘若“人”只是被动地顺乎天道、应乎自然,那么“人”的内存纯性、自由与价值应该如何彰显呢,又何以实现自性逍遥与逍遥而游呢?因此,庄子反复提出要“堕形”、“坐忘”与“心斋”,其意或许就在于强调“人”应该通过自身内在的本性觉解与价值超越去消解外在诸物对生命本性的束缚与困累,进行实现“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与道为一、逍遥而游。
三、“德”“形”之间的逻辑及张力
如前所述,庄子认为,“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天地》);“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同上)。同时,“人”作为生命个体是“道与之貌,天与之形”(《德充符》)。既然“德”与“形”皆根源于“道”与“天”,那么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与内在张力呢?
(一)才全而德不形。庄子在《德充符》篇描绘了王骀、申徒嘉、哀骀它等皆是身残之人,其意在反复强调:其一,形残而可德全,其二,德全胜于形全,其三,才全而德不形。在庄子的笔下,哀骀它是个外表极其丑陋的人,但其内在的品质与才能却吸引众人愿意接近他。同时,庄子借孔子之口提出了“才全德不形”,又借鲁哀公之口解释了“才全德不形”。所谓“才全”,简单地说,不仅仅指知识的全备而是指精神上的达脱以及道与德的境界;或曰:氤氲化醇,谓之才全。在庄子的语境下,“才全”之人就是那种在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等诸事面前能保持自然本性之人,就是那种能够使心灵与自然万物同游于若春和之气中的人,就是那种游心万物与之和谐以应而不失其自然本性之人。所谓“德不形”,即指德似有象,德无定形;也就是说,至高之德或形上之德没有固定的表象与形式;或曰:若水内保而不荡,则物自取法而不可离也。这一观点犹如老子所言的“大音若希,大象无形”(《老子》第四十一章)[2](P171)。从道德形而上的角度看,庄子的“德不形”与孔子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7](P57),二者颇为相近。由此可见,他们大都认识到至高的德、君子的品质很难用固定的表象与形式加以描述与概括;若用形而下的定义强行概括形而上的品质,似乎也是极为困难的,更不要说用一种功用之能去定义了。
此外,在“才全”与“德”的关系中,庄子进一步否定了“才全”,肯定了“德”的重要性;并且他通过“德不形”这一形而上的论述,将“德”推上了至高的位置,当然他的论证或多或少也留有神秘主义之倾向。
(二)全德方有全形。庄子曾经通过子贡南游于楚“偶遇”某丈人的故事予以详论全德与全形之关系,并巧借子贡之口阐明了德全与形全的辩证关系;同时,庄子肯定了“全德之人”。诚如庄子笔下的子贡所言:“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天地》)在庄子看来,德为形之本,有德方有形,无德则无形,爱德非爱形。庄子从形而上的角度对此展开了论证,他借孔子之口说:“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豘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资,刖者之屦,无为爱之。皆失其本矣。为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乎!”(《德充符》)这就是说,就连小猪对其母之爱也是爱其主宰形貌的精神而不是单纯的外形,更何况人乎?换言之,如若一物失其本质便难有其形,即使有也是徒有其形。在庄子看来,全形尚且如此保之,更何况保持全德呢!此外,庄子通过闉跂支离无脤与卫灵公、瓮盎大瘿与齐桓公的对话提出了“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德充符》)的观点。庄子指出:“平易恬惔,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刻意》)。由上可见,在庄子那里,德全比形全更为重要,全德或德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完全弥补形体不全之不足。因此,在全德或德全的前提下,全德之人彰显出来的是道德层面的形而上的全形,而不是执著于身体上的全形。
(三)全形而非全德。在庄子的哲学语境下,无论是他在《人间世》篇中所描绘的支离疏,还是他在《德充符》篇中所塑造的王骀、申徒嘉、哀骀它等皆是身残之人,然而他们却是全德之人;相反,庄子寓言中的身体健全之人在他们面前或者说在道德面前却显得相形见绌。这也许正是庄子想要表达的全形并不一定有全德,残形亦可以有全德。据此,庄子对儒墨诸子所推崇的三皇五帝进行了道德层面的批判,他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盗跖》)可见,在庄子那里,帝王们的文治武功的评定也是要依据道德(即道家语境下的而非儒家语境下的“道德”)为基础的,即便是黄、尧、舜、禹、汤等人也皆只是全形之人而非全德之人。在庄子看来,普天之下的诋毁与赞美对其都毫无益处与损害,这样的人才是全德之人。概而言之,在庄子看来:全形未必有全德,全德胜于全形[8](P11~`12)。
(四)德内与形外。在庄子看来,人内含其德,德成而形立。例如,庄子塑造的列子之形象——“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应帝王》);这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庄子语境下的“德之于内”与“形之于外”的逻辑关系。当然,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庄子语境下的“德”与“形”和儒家语境下的“德”与“形”并不相同。具言之,在庄子的语境下,内有“德”与外有“形”并不一定是光辉的形象或“圣贤气象”,而是顺乎大道、应乎自然的自然而然的形象。换言之,在庄子的语境下,外在之“形”并不是那么重要,相反,内在之“德”倒是值得追寻;诚如申徒嘉批评郑子产时所说:“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德充符》)相对于“形”而言,庄子更强调“人”应内立其“德”,他说:“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胠箧》)。如前所论,在庄子看来,“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同上)。此外,在庄子眼中,“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其为形也亦远矣”(《至乐》)。较之,庄子是十分看重“德”的,他甚至批评追逐财富是劳神伤形;当然,这一点可能和庄子的财富观与人生旨趣有关。
综上所论,庄子以道为体、以德为本,从内与外、形上与形下论证了“德”的内在性与外在性、形上性与形下性,提出了至德之世、至德之人、圣人之德、帝王之德等伦理范式,并对当世帝王以及儒墨诸子所推崇的帝王圣人进行了批判。同时,庄子又以德为本,以形为末,给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并主张通过堕肢体、坠形体以及离形去智来打通通往自然之德与天地之道的道路。在“德”“形”关系层面,庄子不仅提出了“才全而德不形”,而且极具辩证性地提出了“全德方有全形”与“全形而非全德”,以及德立于内与形立于外的论见。进言之,庄子以游心于德和为基点,以德兼于道为理路,以辨德之本末,以论德之立修,以别德形关系;不仅表达了他对当时之世不满与批判,而且也揭露了当时世人的伪善与狡诈。概之,庄子视域中的“德”“形”关系与价值取向是:一,形残而德可全,德全胜于形全,才全而德不形;二,重“德”不重“形”,重内不重外;重自然与无为,不重雕饰与有为。
[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魏)王弼.王弼集校释(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汉)许慎.说文解字(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汉)刘熙,(清)毕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王传林.德与德不形——略论庄子道德哲学语境下的“德之内蕴”[J].武陵学刊,2014,(6).
〔责任编辑 张 伟〕
On the Meanings and Differences of “De” and “Shape” in Zhuang Zi’s Context
WANG Chuan-li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In Zhuang Zi’s philosophy,“De” is not only moral philosophical and metaphysical and internal, but also materialistic and practical. Relatively speaking, “Shape” is more materialistic and external although it was metaphysical. Between “De” and “Shape”, Zhuang Zi emphasizes the inherent virtue of “De” rather than the external “Shape”. Zhuang Zi not only expresses his dissatisfaction and criticism to the society, but also exposes the hypocrisy and the cunning of the people at the time, through a cardinal points wimming in the mind and a logic way of the unification of Mind and Way, to debate the fundamental and the incidental of Mind, to view the education of morality, to distingu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form. Certainly, in the natural and do-nothing philosophical context of Zhuang Zi’s, Zhuang Zi fills with the yearning to natural and simple world, and yearning for simpl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Although we may believe that the aspirations of Zhuang Zi’s is a appeal to the Utopian in the face the cruel reality, we cannot ignore the metaphysic of moral philosophy of Zhuang Zi’s. In a word, the relationship and value orienta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shape” in the view of Zhuang Zi’s is “De” to be perfect,“De” over “Shape” and “De” no seeing; and stressed “De” not emphasizing “Shape”, stressed inner not emphasizing outside, stressed natural and inaction not emphasizing carving and promising.
Zhuang Zi; Mind (Te/De); Shape; Meanings; Characteristics; Logical relationship
2014-11-18
王传林(1978-),男,安徽阜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研究。
B223.5
A
1004-1869(2015)02-00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