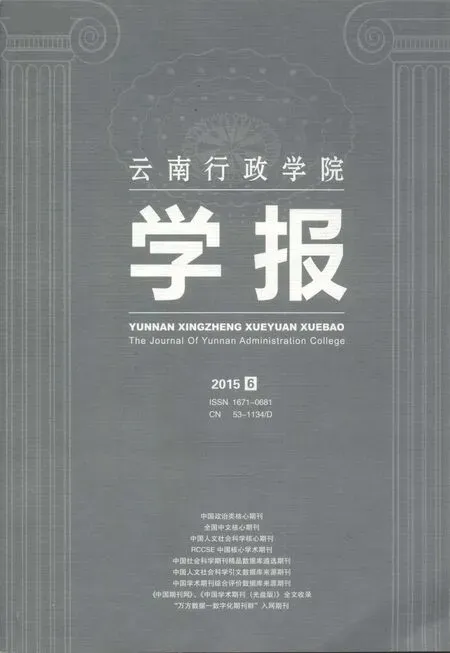城乡结合部“村改社区”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制研究*
于莉,崔金海,袁小波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城乡结合部“村改社区”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制研究*
于莉1,崔金海2,袁小波3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乡结合部产生了大量的“村改社区”,面临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城市化转制。本文对比了城乡基层管理体制的差异,探讨了“村改社区”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实质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这种转制是一场涉及利益分配、治理体系重组和社区秩序重构的社会改革。
城乡结合部;村改社区;基层管理体制;转制
在我国城乡存在着不同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城市的基层管理是街居体制,街道对基层社会实施社会管理,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在街道的指导下,对社区居民开展社会服务和群众自治。我国乡村基层管理为村镇(乡)体制,乡镇是具有独立经济和社会管理权力的一级政府,村委会作为村民组织,除了组织社会管理和村民自治外,还要管理和经营本村的集体经济,发挥经济管理的职能。两种基层管理体制在城与乡的不同空间中各自发挥功能,彼此相安无事。但在城乡结合部,两种体制出现了交叉和碰撞。这种碰撞起因于两个因素,其一,在土地征用与村落拆迁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在社会身份上将从村民转型为市民,必然同时带来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向居委会转型的问题;其二,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和部分中心市区的居民入住城乡结合部,使得以村民为管理与服务对象的村委会,无法满足人口多样性结构的需求,外来人口和入住居民需要服务范围更为广泛的基层治理组织提供的管理和服务。因此,城乡结合部面临基层治理体系的变迁,需要根据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特有性质和独特问题,进行创新和再造。
一、从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到城镇社区管理体制
200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其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1]。城市的膨胀扩张所伴随的征地拆迁、旧村改造、撤村并居等一系列过程,使中国村落数量迅速减少,同时也造就了新型社区类型——“村改社区”。
所谓“村改社区”是指在城市化背景下,原居住在农村村落中的农民在征地拆迁后,集中安置到新建的城镇化居住社区。这类新型社区的居民以被征地农民为主,他们可能来自一个或几个村委会,此外社区中还有大量租住农民富余房屋的外来人口,以及部分在社区中购买商品房的城市居民。可见,“村改社区”是将居住在传统农村社区的人口安置到现代城市化景观和环境中,并输入了新的人口元素之后,产生的新型社区。“村改社区”面临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和治理模式的城市化转型,这种转型首先表现为从以村民委员会为核心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到以居民委员会为核心的城镇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型。因此,探讨“村改社区”的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型,首先需要分析农村与城市基层社区管理的主体组织[2]——村民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所具有的共性和差异。
村民委员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是我国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两种基本组织类型。在我国宪法中,它们都是基层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二者性质相同,具有并列关系[3]。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建构和职权行使分别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比村委会和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可以发现两个基层自治组织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鲜明的差异:
第一,在组织职能上,村委会担负的治理职能包括农村生产、生活领域中有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而社区居委会只负责与城市居民生活领域和社区服务相关的事务。
第二,在自治性质上,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具有更强的自治性质,村委会的设立、调整和撤销除了由政府提出外,还需经过村民会议的讨论同意;而居委会的成立、撤销、规模调整则直接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
第三,在选举方面,《村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村委会直接选举和意见反馈的机制;《居委会组织法》并没有明确的直选规则,居委会可以由居民直接选举,也可以由居民代表间接选举。
第四,在经费来源上,村委会的办公经费和村干部的生活补助通常由村集体筹款解决;而居民委员会则由政府规定和拨付其办公用房、工作经费和人员补贴。
第五,在与居民的关系上,村民对村委会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许多与村民利益攸关的事务,如集体资产的经营处置、集体土地的分配、乡村事务的管理、乡村发展的决策等等,全部由村委会负责[4],除了村委会,农民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居委会外,他们还归属于自己的工作单位,以及各种可以满足需求的机构和团体。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可以为居民提供工作、社会和生活等各方面的服务,因此居民对居委会的依赖性较低,对其关注程度也不高[5]。
旅游者的需求不断更新,乡愁情怀需要不同的载体来跟踪并丰富旅游者的体验。不同地域的乡村旅游应结合各地的自然、历史、文化特色形成各具特色的旅游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避免过度商业化与经济利益的过度索取,还原真正的乡村环境。
第六,在管理模式上,村委会以属地所有者作为自己的管理对象,通常采用熟人管理的模式实现对村落的社会管理;居委会的管理对象是属地居民,其管理模式通常是单位人管理[6]。由于村民既是属地的居民,也是属地的所有者,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以及所有权关系建构熟人关系,因而村委会与村民在权力、义务和利益方面存在一致性;而城市居民作为单位人与所在单位的利益紧密相关,作为社会人与公共性、国家性利益密切关联,因此,社区组织与居民在权利义务关系上存在分歧[7]。
由于存在以上差异,决定了从村委会管理体制到居委会管理体制的转型,并不是组织换一块牌子这么简单,这个过程将涉及社区组织属性职能、基层管理体系和管理模式的全方位转换。
二、“村改社区”转型的实质
“村改社区”的转型实质上是一个由封闭的传统社区到开放的现代社区转型的过程。这种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并不是在破坏了村落社区的物质景观,甚至破坏了村落社会的网络结构之后就可以自然实现的。除了文化观念成为阻碍传统社区开放性发展的影响因素之外,村落内部的利益关联也成为难以打破村落结构的巨大阻碍。
传统村落在经历征地拆迁的非农化过程之后,获得了作为补偿的巨额集体资产,利用这些资产,村镇集体不仅可以获得集体经营的资产来源,也可以调动这些资源为被征地农民提供补贴、分红、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区设施。由于集体资产具有封闭性的边界,它是原村落居民的共同财产,并成为被征地农民重要的生活保障,因而强化了村落居民利益共同体的封闭化。具有村籍身份成为识别村落利益共同体的边界,村落成员可以在收入分配、就业、入学、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特殊待遇和权力。村制管理并不包括村籍之外的人口,也不允许村籍之外的人口分享村落的福利待遇。由于村落集体经济的管理和分配通常由村委会控制,这也导致了村民委员会的封闭性,非村籍成员不可能进入村民委员会,更不可能参与村落的管理和决策。
尽管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村落社区组织发生了新的变化,大部分村落建立了集体经济组织进行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但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和成员与村落社区组织经常重叠交叉,导致二者之间界限模糊,并逐渐出现集体经济组织替代村落社区组织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趋势。蓝宇蕴在探讨非农化村庄社区组织问题时,就指出非农化村庄社区组织的建构出现村庄单位化现象,即村落依托集体经济的发展办社会[8]。基于村落资源的独享性,这种村庄单位化的趋势加强了村落的封闭性以及村民对村落的依赖性。
当村落社区经历拆迁安置而转变为“村改社区”之后,村落社区的物质空间界限被打破,当“村改社区”有越来越多的外村村民和外来居民入住之后,村落社区的社会空间界限也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户籍改革和社区管理体系的改制,将可能危及被征地农民基于村籍待遇的利益共同体的边界,这必然会带来种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村改社区”转型困难重重。
三、“村改社区”基层管理体制的过渡性模式
第一种是村委会与社区居委会分而治之,即在新建社区内设立居民委员会,对社区内购买商品房的居民实行社区管理,而原有的村民委员会并未撤销,社区内的村民仍归原来所属村落的村委会管辖。这种村民与居民分而治之的形式强化了被征地农民与外来居民的隔离,既不利于社区整体的发展和协调,也不利于被征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由于很多社区内的服务不能惠及到村民,再加上村民通常并非整村安置,导致很多事务需要回到原村办理,也给村民造成了不便。
第二种形式是村委会与社区居委会同时存在。在一些整村安置的社区内同时存在村委会组织和居委会组织,两个社区组织在服务对象上并无区别,从服务内容上,居委会更侧重于社会服务。实行这种安排的社区通常是为了实现村委会向居委会的过渡。可见,村委会与居委会并行存在只是暂时之计,而且这种设置所导致的多头管理和资源浪费的弊端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种形式是经济组织办社区,这样的情况通常发生在集体经济经营比较好的村落,而且是整村安置的社区。社区中建立了集体经济的集团组织,组织的领导就是村委会的领导,由于村集体经济发展良好,能有更多的资源改善社区设施和购买社区服务,所以村委会对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实际上是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了更为实质的作用。这种经济组织办社区的模式比较类似蓝宇蕴提出的村庄单位化现象,其后果是加强了村落的封闭性和被征地农民对村落的依赖性,反而为村落社区的城镇化转型带来更大的阻碍。
第四种形式是目前我国“村改社区”中较为主流的转型方式,即“村改居”。所谓“村改居”是指在划入城市建设规划区域内的原农村地区,将原来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撤销,改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采用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对被城镇化的农村地区实施治理。[9]但许多研究者发现“村改居”后的社区居委会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原来的村委会管理模式,普遍存在转型不彻底的情况。
四、“村改居”转型模式的现存问题
“村改社区”是由传统村落社区转变为现代城镇社区的产物,作为社区转型的结果,必然带来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型,许多地方将这种转型看作是撤销农村村委会建立城市居委会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村改居”。然而,在实施“村改居”的社区中,可以看到社区组织的这种转型目前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村改居”后社区居委会的经费主要还是来自于集体经济。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管理职能是归属于村民委员会的,而社区居委会只具有办理居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务的社会职能,从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将意味着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职能需要转移给新的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然而在集体资本转移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后,“村改居”的社区组织面临着经费短缺、资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传统农村社区中社区组织和社区事务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于集体经济,改制后,“村改居”社区的经费除了上级拨付的补贴之外,工作经费仍主要来源于集体经济,从而导致社区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依赖。
其次,在管理体制上,很多“村改居”的社区组织仍然采用农村村委会的管理方式,依靠传统的宗族关系实现对社区的治理。“村改居”社区中村民的生活空间仍为原来村落所在的区域,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族关系和以地域为基础的邻里关系在社区生活中仍起重要作用,宗族意识和大族观念在社区选举和社区事务管理中的影响依然存在[10]。
再次,居委会组织通常是由原村委会班子简单组成,其成员大部分是原村委会干部。由于具有“村籍”身份的被征地农民与社区组织,特别是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关联最强,在集体经济与社区组织没有彻底分离之前,村民担心“非村籍”人员进入社区组织会导致集体资产被外来居民“共产”,因此“村改居”的社区组织成员仍然来自于本地村民。
此外,非村民群体的社区组织归属感弱,社区参与不足。“村改社区”中人口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成员的复杂性,即使是安置的村民也常常来自于几个村落。此外,还有购房的城市居民和租房的外来人口。由于社区组织成员通常来自原村落成员,导致其他人口群体没有代表在社区组织中任职,他们与社区组织的利益关联松散。这些“外来者”游离于社区组织之外,对社区组织缺乏归属感,社区参与在广度和程度上都存在不足。
最后,“村改居”漠视了村委会和居委会的法律地位,也漠视了被征地农民的意愿。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的成立、撤销和范围调整,应由本村村民会议决定,各级政府只有程序上的提出与批准的权力。而实际运作过程中,“村改居”过程往往实行行政主导,政府通常以行政公文形式公布并予以确认。在缺少村民认同基础上的社区转制要么会遭到抵制,要么导致新的建制形同虚设。
五、“村改社区”转制是一个复杂的建构过程
“村改社区”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是一个重新建构而非简单置换的过程,它将是一场涉及利益分配、治理体系重组和社区秩序重构的社会改革。
首先,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定位的日益突出,带来了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和城镇建设,这一过程涉及村镇集体收益和村民利益补偿的合理性分配问题。在传统村落社会中,村委会具有管理村集体资产的经济功能,而城市社会中的居委会并不具有经济功能,如果在“村改社区”将村委会简单变身为居委会,村集体经济管理职能如何转移,村委会与村民的利益关联如何割断,这将是“村改社区”中社区组织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
其次,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最大障碍是被征地农民对村镇体制的依赖,这不仅仅是社会管理和自治权利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它是关系村民长远利益的集体财产处置和集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如果实施“村转居”,集体资产的处置就会提上议事日程,关于集体资产如何核算和分配,触及各方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必将诱发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因此集体资产和集体经济是否能够处置妥当,决定了社区组织是否能够成功转型。
再次,由于被征地农民不愿放弃村民身份,由此形成“村改社区”中同时存在着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混居的状态,导致不同人口群体共同居住在一个社区,却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社会归属。由此使得“村改社区”的社区组织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代表和服务于这些界限分明的居民群体。如果能将村民的集体分红、利益补偿和社会保障与被征地农民户籍身份分开,被征地农民是以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身份获取集体经济收益,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身份获得社会保障服务,那么,农业户籍对被征地农民来说将不再具有特殊价值。由农业户籍变为非农户籍是被征地农民市民化迈出的第一步,在户籍制度没有彻底取消之前,非农户籍将为被征地农民身份转型提供合理性依据,同时,被征地农民的市民化转型也将对“村改社区”的城市化转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1]杨伟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的几个现实问题[J].经济纵横,2011,(4).
[2]卜万红.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结构的演变与重构[D].硕士研究生论文,2004.
[3]晋龙涛.试论村委会与居委会的差异[J].农业考古,2012,(3).
[4][5]罗伯特·贝涅威克、朱迪·豪威尔、伊伦娜·堂.社区自治:村委会与居委会的初步比较[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6][7]王圣诵.“城中村”土地开发、“村改居”和社区民主治理中的农民权益保护研究[J].法学论坛,2010,(6).
[8]蓝宇蕴.非农化村庄:一种缺乏社会延展性的社区组织[J].广东社会科学,2001,(6).
[9]梁慧、王琳.“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理论月刊,2008,(11).
[10]丁煌、黄立敏.从社会资本视角看“村改居”社区治理[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0,(3).
(责任编辑马光选)
D638
A
1671-0681(2015)06-0123-04
于莉(1976-),女,天津市人,讲师,博士;崔金海(1974-),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副教授,博士;袁小波(1982-),女,陕西咸阳人,讲师,博士。
2015-09-21
天津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村改社区’组织建设研究”(TJSR11-03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结构重组与功能调适: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体制创新研究”(10YJC84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