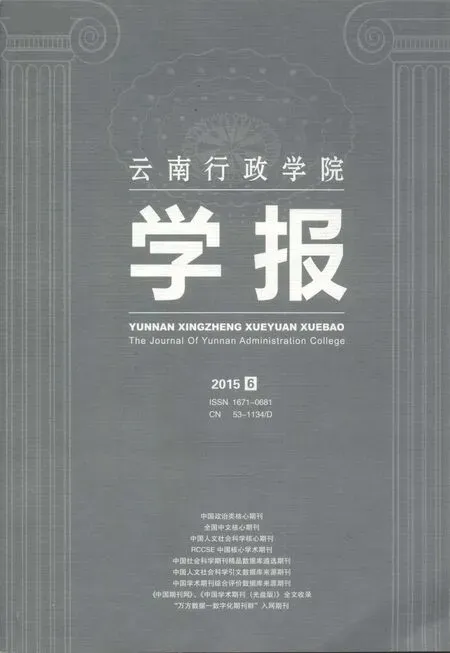新中国文化治理的结构转型
李世敏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武汉,430079)
新中国文化治理的结构转型
李世敏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武汉,430079)
文化治理,不同于治理文化,它是以文化的价值规训、政策引导等力量进行的国家(社会)治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治理会根据政治场域的变化而变换不同的面孔。新中国的文化治理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国家意识形态笼罩的文化治理、市场经济导向的文化治理、回应社会需求的文化治理。文化作为一种治理的工具,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政治场域的变化而不断调适,才能够成为有力的治理武器,文化治理也才能够实现公民对国家的认同,统治也才能够取得合法性和有效性。
文化治理;政治场域;意识形态;政策;合法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1],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
一、“文化治理”的提出
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作为复合词,是一个极具弹性的概念。一方面它与“文化”相连具有浓厚的艺术、价值、思想意涵,另一方面它又兼具“治理”所蕴含的权力、多元、沟通等理念。[2]从文化的角度,目前对文化治理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四个层面:一是从文化政策的角度研究文化治理,这类研究将文化治理仅仅局限在文化政策领域,其概念接近于治理文化,可以视为狭义的文化治理。郭灵凤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政策可以等同于文化治理,二者均是在统治或者治理的框架下探讨文化”[3]。安托尼·埃弗利特指出,由于文化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互不关联和各自为政,导致文化政策难以有效执行,只有用“整体性政府”观念实现“横向”跨部门的整合与合作,文化政策才能够顺利落地;二是从文化产业视角研究文化治理。国外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从批判的角度对文化产业(或者文化工业)进行审视。阿多诺(T.Adorno)与霍克海默(M.Horkheimer)等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文化日益沦为一种商品,并且随着工业化不断地被标准化、同质化,从而失去了文化本来丰富多彩的一面,同时文化的“物化”也使得精神层面的文化底蕴不断削弱[4](P194);国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是从一种积极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改变和完善国家治理模式[5];三是从价值认同的层面研究文化治理。安东尼奥·葛兰西(A.Gramsci)认为,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统治阶级通常会利用文化宣传与教育等工具来干预主流价值,并在骗取大众自发性认同的基础上取得政治社会的支配权[6](P12)。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将福柯的“治理术”引入文化研究之中,通过对博物馆等文化艺术的研究,揭露文化背后的国家规训等治理问题[7](P224)。这个层面的研究往往认为,文化治理的关键和落脚点在于核心文化认同的建构[8];四是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化治理。这类研究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研究色彩,它将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等纳入广义的文化政治范畴。比如,奥古·弗莱勒斯对加拿大多元文化治理的定义和分析,就是对后民族国家或者说移民国家中多民族认同的治理模式的探讨[9]。
从治理的角度,只有一小部分学者特意指出了“文化治理”与“文化管理”的区别,认为文化治理意在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其重心落在发展上,而文化管理是国家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人、社会的文化行为进行规范,其重心落在规范上[10]。大部分学者并未从治理与统治、管理区分意义上定义文化治理,恰恰相反,他们多是从统治、管理、管治等宽泛意义上对文化的“治理”展开讨论。台湾学者王志弘将文化治理的概念视为文化的政治场域,即透过再现、象征、表意作用而运作和争论的权力操作、资源分配,以及认识世界与自我认识之机制[11]。笔者认为文化治理,是通过文化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其中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既包括了文化政策等实践层面,也包含了价值认同等精神层面,而治理的领域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化上面,而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治理。
总体而言,国内对于文化治理的研究近几年在不同层面逐步展开,然而尚缺乏一个长时段历时性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治理转型做一个粗线条的分析。这里的“粗”,一方面是由于文化治理的历史节点跨度大,本文只是根据每个时代的不同主题做笼统的划分;另一方面是由于文化治理涉及方方面面,本文只对特定时期文化治理的核心主题做针对性的描述。
二、国家意识形态笼罩的文化治理
特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总是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治统治,因此文化治理往往具有政治面孔[12]。新中国是在冷战的夹缝中诞生的,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在意识形态的争斗十分激烈,中国稍微放松警惕,就有可能被西方渗透,发生颜色革命。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建国之初,非常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治理,以确保社会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中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旗帜和灵魂。王永贵认为,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成功之处在于,始终在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13]。因此,在思想宣传领域,新中国的文化治理一开始就从出版、新闻、文艺、教育等各个领域开展大规模、铺天盖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1951年8月,全国出版署署长胡乔木提出:“出版工作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斗争”[14]。当时,全国新华书店也号召增加出版政治类书籍,以满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1953年9月,《斯大林全集》中文版首先出版;1953年12月,《列宁全集》中文版出版;195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出版[15](P55)。除了政治类的图书出版之外,这类的图书销售也逐步达到高潮。以湖北省京山县为例,从1967年开始,当地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当年销售各种图书276万册,销售金额27万元。其中《毛泽东选集》、毛泽东相、毛泽东语录和著作单行本共208.6万本(张),合计销售金额22.5万元,占销售收入金额的83.3%[16](P586)。
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性观念,它起着一种“社会粘合剂”作用,能整合和巩固已有社会秩序,“而新闻传媒恰恰就是构筑和稳固意识形态合法性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17]。新中国的文化治理就很好地抓住了新闻传媒这个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成立了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报纸杂志。建国前夕,按照毛泽东关于创办大党报的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将《晋察冀日报》和原晋冀鲁豫解放区出版的《人民日报》合并,并于不久后成为党中央机关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突出政治性和党性,强调新闻舆论工具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作党的工具和人民的喉舌;1949年9月5日,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创刊。该刊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对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研究和探讨[18](P55)。
新中国文化治理初期也特别注重对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和重塑。为了全面领导电影事业,1949年4月,中央设立了专门的电影管理机构——电影事业管理局,归口中宣部领导。电影局主要负责政治性审查,以保证电影的导向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了意在全国展开新中国戏改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正式推出了后来称为“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方针。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的大会。会上胡乔木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重要讲话。随后,全国文艺界以及科学界都进行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
在学校教育方面,马克思主义课程逐步增加。1949年10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最早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反动课程,添设马列主义教育课程。同时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增加了一些《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宣扬共产主义价值的教学内容。
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宣传教育层面的灌输,还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渗透之中。由于中国农民天生缺乏阶级意识,为了将阶级观念“嵌入”到农民的头脑之中,共产党人便通过土改、四清等一系列运动来让农民心里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嵌入农民的头脑。通过动员农民进行“诉苦”、“揭发”、“批斗”来打破农民狭小的地域和宗族观念,从而激发农民的阶级观念与国家意识,进而树立党和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20]。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新中国的文化治理都被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所笼罩,国家通过各个系统全方位地宣传马克主义思想,塑造阶级斗争观念,成功将这种意识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形成了意识形态全面笼罩的文化治理模式。
三、市场经济导向的文化治理
意识形态的过度膨胀很容易导致极端,过度地渲染党内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威胁,导致中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时期。十年浩荡之后,文革熄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后中国步入注重实践时期,务实治理成为主旋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治理的重心相应地从“为政治服务”转向“为经济服务”。在文化治理的“政治面孔”转向“经济面孔”之间,还经过了一段“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淡化的过渡时期。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祝辞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周扬在大会上表示:“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
在过渡阶段,文化治理并未出现经济导向一边倒的情况。邓小平在多个场合也提到:“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1](P367)。然而,随着整个国家治理的经济中心转向,精神文明这只手逐渐软了下来。
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甚至出现了文化“服从”经济的状况。1995年10月19日,湖北省京山县一位领导在全县文化产业会上讲到:“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同时,文化还要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发展。”经济压倒一切,导致了文化系统“不务正业”地举办各种与文化无关的企业,也都纳入了文化产业的范畴。京山县文化系统1995年度工作总结中提到:“为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局党委报请县委、县政府同意在杨集乡召开了全县文化产业现场会,有力地推广了杨集乡文化站在短期内创办粉丝厂、酒厂、家具厂,实现年产值30万元,创纯利3.5万元,促进了全系统产业的发展;新华书店筹办新华工艺制衣加工厂;厂河文化站手套厂恢复生产……”
国外最早从产业角度剖析文化治理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基本上是从“大众”的视角关注它,主要论述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对“大众”主体性和批判性的消极影响作用[22](P174)。然而在国内,西方那种对文化工业的大肆批判现象并没有出现,国内学者更多是去讨论我国文化产业的成就以及如何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5123亿元,同比增长17.1%。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45%,文化产业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的6.4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0.36个百分点[23]。
一方面是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却是文化事业的举步维艰。随着以文补文、以文养文的改革措施,曾经财政支持的文化事业单位被当做包袱“甩”向市场,这导致了一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也难以运转。文化事业在增量上的“内卷化”,使得一些文化学者提出了“文化体制空转”的概念。这种现象和理念,使得文化工作在实践层面并不是把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作为逻辑起点,而是政绩导向,片面地追求各种形式主义的形象工程[24]。
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出现了经济压倒一切的观念,文化日益被边缘化。这导致一方面文化事业的发展徘徊不前,另一方面则是人们思想价值的日益扭曲。恰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所论述的那样:娱乐和信息工业(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令人难以抗拒的,它通过激发精神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将‘心甘情愿的’消费者和文化的生产者绑定在一起。这些文化产品向人们灌输着某种虚假意识,操纵着人们的思想,让大众无法看清其欺骗性……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25](63)。
四、回应社会需求的文化治理
2006年9月颁布的《“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正式提出“文化权益”的概念,要求“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文化权益”的概念,指出“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标志着我国文化治理开始回应社会发展的权利转向。
文化权利在国际上公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1948)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国家要满足公民的文化权利需求,就必须要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我国在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有学者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本身就是政府文化治理的制度设计和体制创新,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走向全新的服务型公共文化治理模式”[26]。
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之后,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才进入快车道。2011年1月,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要求全国切实把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的工作做好,并指出免费开放的重要意义在于,“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是政府举办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阵地。”
2011年,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启动,该项目旨在研究和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探索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保障机制。2014年3月19日,文化部牵头成立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该协调组由文化部、中宣部等20个相关单位组成,主要负责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大事项的协商和部署。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2015年5月,经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研究决定,将其牵头组织起草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共文化服务在立法层面的推进,标志着其前期的展示和象征意义逐步转入实质层面,公民的文化权益将会进一步得到有效保障。
文化治理的服务转向,跟新时期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紧密相连。它既回应了公民的文化权利,同时也是现代“治理术”的实际应用。所谓的“治理术”,就是使人误认为治理是维护他们的自由,通过自由来显示治理。或者更简洁地说,通过自由进行治理[27](P92)。福柯认为:“对人的治理,首先应当考虑的不再是人的恶习,而是人的自由,考虑他们想做什么,考虑他们的利益是什么,考虑他们之所想”[28](P91)。这种新式的软性文化治理所蕴含的规训,正如我国在“三馆一站”免费开放意见中指出的那样,“‘三馆一站’既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
当下文化治理既有回应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兴起的一面,同时又有回应社会价值多元的一面。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在论述文化部分时,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重要位置,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整合人们对社会主义、对基本公德的认同。尤其是在当下我国大量的“无公德”个人出现、路人倒地扶不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社会正能量缺失、精神信仰迷茫等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显得尤为必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精神力量,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29]。
五、余论
新中国文化治理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的是国家与社会一体化背景下的“统治-稳定”思维;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萌动背景下的“管理-发展”思维;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背景下的“治理-和谐”思维。因此,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才有了真正现代“治理”意义上的文化治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将文化治理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维度划分为三个阶段只是为了突出每个阶段的不同主题以及行文的方便,其实三个阶段之间并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也并非是简单的相互替代,而仅仅是文化治理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在各个阶段其实都存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不同面孔的文化治理。
文化总是无形中受到政治“场力”的影响,并根据政治场域的变化而不断地调适角色。这种政治场域既有宏观的国际视野,比如世界格局由冷战思维向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切换;也有中观的国家战略,比如国家发展重心的调整;还有微观的社会环境,文化治理的对象最终还是人,而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对治理中的文化“编码”会进行能动性地“解码”,人的思想改变了,社会环境就转变了。文化作为一种治理的工具,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政治场域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才能够永葆活力,成为有力的治理武器。文化治理也才能够实现公民对国家的认同,统治也才能够取得合法性和有效性。
[1]刘忱.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的关系[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10).
[2]刘俊裕.欧洲文化治理的脉络与网络:一种治理的文化转向与批判,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112/ 112-liu.pdf.
[3]郭灵凤.欧盟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J].欧洲研究,2007,(2).
[4]Theodor Adornoand Max Horkheimer,“The CultureIndustry:Enlightenmentas MassDeception”,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NewYork:Continuum,1993.
[5]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J].湖南社会科学,2014,(2).
[6]Antonio Gramsci,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and trans Quentin Hoare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NewYork,1971.
[7][英]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M].王杰,强东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张鸿雁.核心价值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文化治理——深化改革文化治理创新的模式与入径[J].南京社会科学,2015,(1).
[9][加]奥古·弗莱勒斯.加拿大多元文化治理模式在后民族国家时代的革新[J].常永才,吕桃,王佳馨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10]范玉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国家文化治理[J].湖南社会科学,2014,(2).
[11]王志弘.精神建设,艺文消费与文化政治:台北市政府文化治理的性质与转变(1967-2002)[J].台湾社会研究,2003,(1).
[12]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13]王永贵.新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J].江苏社会科学,2009,(5).
[14]胡乔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的报告[R],1951-8-2.
[15][18]吴建国,陈先奎,刘晓,杨凤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16]湖北省京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京山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17][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5).
[19]张星星.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确立[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1).
[20]朱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嵌入乡村日常生活探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为考察对象[J].学术论坛,2013,(12).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2][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M].林宏涛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9.
[23]王婧.中国文化产业经济贡献的影响因素[J].统计与决策,2008,(3).
[24]王列生.警惕文化体制空转与工具去功能化[J].探索与争鸣,2014,(5).
[25]Marcuse,Herbert.OneDimensionalMan.London:Sphere,1968.
[26]李少惠.转型期中国政府公共文化治理研究[J].学术论坛,2013,(1).
[27][美]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M].彭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8][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M].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9]胡宝荣,李强.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2).
(责任编辑刘强)
D0-05
A
1671-0681(2015)06-0038-05
李世敏,(1984-),男,河北省内丘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15-10-0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18);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及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编号:CCNU14Z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