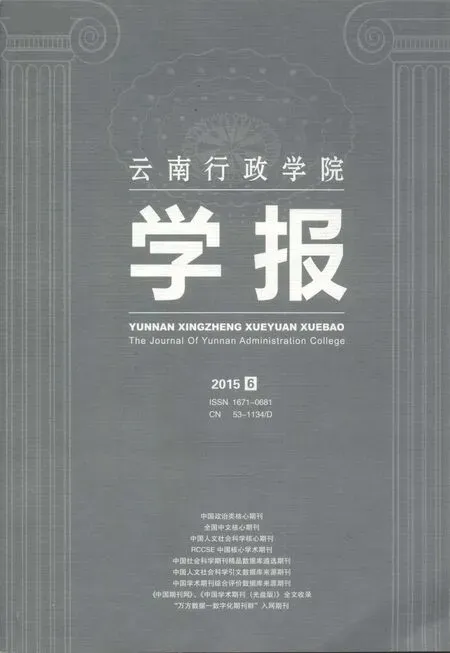主持人语:漫谈对文化的政治学研究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主持人语:漫谈对文化的政治学研究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栏目主持人: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入选者,著名三农学者。
吴理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入选者,著名三农学者。
作者通过自身对文化的研究,论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政治学研究主要内容。作者认为,将研究的视域转向当代中国,关于文化政策、文化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重大现实性和理论性问题,亟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文化进行政治学研究,而国内当前对此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呼吁政治学者共同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政治学研究。
文化研究;文化政治学;当代中国文化
一、研究文化的缘起
早在安徽省社科院工作期间,我就跟随辛秋水研究员做农村文化贫困问题的研究。文化贫困问题之所以引起辛老的关注,缘起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贫困农村的经验调查和蹲点扶贫的实践体验,他认为,这些农村贫困并不仅仅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经济、技术的落后,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地区社会文化的贫困。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些地区没有或不存在文化,只是他们的文化是一种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贫困文化”。因此,改变这些农村的贫困面貌,首要的任务是改造他们的“贫困文化”,为此辛老提出:改造贫困文化必须从“人”开始,因为人是文化的主体;而改造“人”的关键是开启民智,提高人的素质。这就是辛老的“以文扶贫、扶智扶人”的文化扶贫思想。在国内,文化扶贫最早是由辛老提出来的,后来上升为国家决策,成为国家一项重要扶贫工程。后来,我们对辛老的文化扶贫理论及实践进行了初步总结,出版了《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一书。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最早从贫困的视角从辛老那里触及农民文化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所理解的文化主要是人力资本和观念意义上的。
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工作一年后,2005年中宣部、文化部委托学校作一个关于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大型问卷调查,我又参与了这个重大调查项目。我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调研报告《游走在城乡之间——来自安徽、四川和湖北内陆省份农民工的报告》得到了俞正声同志的高度肯定,他批示道:“报告很好,用数据说明概念,事实产生结论,而不是反之。读后很有帮助和启发。此件发至省几大班子领导,各市州县区领导参阅。”这项研究成果后来分别获得武汉市第十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七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年湖北省社科联和湖北省文化厅,又让我做一个湖北省农村文化体制改革与农村文化发展的报告。2007年湖北省委宣传部委托我对农民工思想道德状况进行调查。2008年我又主持了一项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研究”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同年,我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为题参加了国家重大招标项目的申报,尽管这一次我没有获得重大项目,但最终获得了重点资助。正是因为前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2010年底,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最终获准立项。自此以后,我正式转向了文化研究,并努力尝试从政治学切入当代中国文化研究。
二、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
应该说,国内外有一大批顶尖学者和大家从事文化研究,他们主要是从文化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文化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成果。说实在的,要想在这些领域有所创新非常难。
而且,人们对于“文化”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的,比较难以把握文化这个研究对象。据说,现在世界上有关文化的定义已达200多种。但比较权威并系统归纳起来的定义源于《大英百科全书》引用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洛伯(A lfredL.K 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K luck hohn)在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Culture:ACriticalReviewofConceptsandDefinitions)一书中所列举的164条定义。克拉克洪在《人类之镜》[1]一书中论述文化概念时,他用了将近27页的篇幅将文化依次界定为:⑴“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⑵“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⑶“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⑷“一种对行为的抽象”;⑸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⑹“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⑺“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⑻“习得行为”;⑼“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⑽“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⑾“一种历史的积淀物”;最后,或许是出于绝望,他转而求助于比喻手法,把文化直接比作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2]。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对它进行研究。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域转向当代中国,从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等学科出发,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文化展开研究,仍然有许多重大现实性和理论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不可否认,在我国过去也有一些关于文化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要么将文化内涵仅仅局限于价值、精神层面,而难以进行实证研究;要么将文化外延无限扩大、与“文明”概念或“整个生活方式”相等同,抓不住文化的主要内容,失去了文化研究的本身特色和独特魅力。
我个人认为,当前至少有三个主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文化发展研究,二是文化政策研究,三是文化政治研究。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糙的划分,其实这三个主题是相互影响的,甚至存在一定的交叉或重叠。
关于文化发展研究,我后面还要进一步展开。先说说文化政策研究。最近几年,随着公共管理学科的兴起,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日益成为我国的一个显学。然而,在目前的公共政策研究之中,对文化政策的研究相对薄弱。
其实,文化政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在西方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正式开始的。他们主要讨论:文化政策的历史演变,文化政策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国家文化政策间的复杂纠葛,全球化对文化政策的影响,文化政策的反思与批判,作为公共政策的文化政策,文化政策与公民的文化权力,法律与文化政策,国际文化政策的比较研究,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我国台湾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界文化政策研究同样受到广泛关注,逐渐形成台湾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要焦点[3]。严格而言,我国大陆地区的文化政策研究才刚刚起步。
在我国,关于文化政策的研究被人为地区隔为两个领域,一是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另一个是文化事业政策研究。目前,研究前者的学者较多,而研究后者的人尤其较少。我被文化部聘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委员会委员,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从事公共文化服务乃至公共文化政策的研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学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我国从事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具有极大的创新空间。
接下来,我想简单地谈谈文化政治研究。
什么是“文化政治”呢?先得追溯一下这一概念的缘起。1991年,一位出生美国的非裔女作家贝尔·胡克斯(bellhooks)写了一本名为《向往: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学》(Yearning:Race,Gender,and-CulturalPolitics)的书,第一次提出“文化政治学”的概念,对于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社区、身份、电视、文学等问题予以关注。这可以视为文化政治研究的发端。此后同在1994年有两本以“文化政治学”为名的著作问世,一是格伦·乔丹(GlenJordan)和克里斯·威登(ChrisWeedon)的《文化政治学: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CulturalPolitics:Class,Gender,RaceandPostmodern-
World),二是艾伦·森费尔德(A lanSinfield)的《文化政治学——酷儿读本》(CulturalPolitics--Queer-Reading)。贝尔·胡克斯的观点揭晓了文化政治研究的宗旨:“清醒地坚持将文化研究与进步、激进的文化政治相联系,将会保证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使批判性介入成为可能的领域。”[4]贝尔·胡克斯等人从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出发,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等,形成研究所谓“非常规政治”或“非正式政治”的“文化政治学”。当今文化研究中大力推崇文化政治学并予以身体力行的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他们不仅以卓著的理论建树推进了文化政治学,而且在具体的文学、文化研究中采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在西方学术领域里,“文化政治”主要关注和研究种族、民族、族裔、身份、性别、年龄、地缘、生态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所关涉的对象一般是社会的边缘群体或受支配群体。以致詹姆逊认为,文化政治的任务就是“详细列出各种边缘群体、被压迫或受支配群体——所有所谓的新社会运动以及工人阶级——所忍受的种种‘束缚’结构,同时承认每一种苦难形式都产生出了它自己的特殊‘认识方式’(epistemology),它自己的特殊的由下而上的视野,以及它自己的特殊的真理”[5]。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仍然是权力,包括权力的界定、分配、使用、执行、生效、争夺、转移、巩固、延续等内容。正如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所说:“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每种事物在根本上都与权力有关。权力处于文化政治学的中心。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也就是说,所有带有意义的实践——都涉及到权力关系。”[6]
西方“文化政治”的研究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揭示社会边缘群体、亚群体或被压迫群体的“无意识”支配的隐秘权力机制为己任,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批判,甚至主张“迈向一种渐进的民主政治”。
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当代中国学者的主要任务,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政治”这个概念不仅比上述这些文化研究者要宽泛一些,而且更具(传统)政治学的特性,它主要关注国家政治或总体性政治。具体而言,它主要论述(国家)政治权力的定义、政治权力的展现(或再现)、政治权力的论证。因此,文化政治研究一般是由这些关键词构建的:意识形态、话语、文化霸权、合法性、(身份)认同(差异政治)、接合、文化权利、收编、文化整合、规训、定义、论述、表征(文化符号)、文化资本、公民文化。我们的研究旨趣与西方学者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自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不一样,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期发展阶段,而西方发达国家已普遍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各自面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尽管如此,西方学者的研究仍然有可资借鉴之处。
文化政治研究的核心,简洁而言,就是围绕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线索展开的,主要探讨“文化治理”的议题。
国内关于文化政治的研究,严格而言,才刚刚开始。为了开始这项研究,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梳理文化政治研究的主要关键词(为此,本栏目首先推出几篇文化政治关键词的文章),并尝试运用这些关键词来理解、阐释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现象和问题,从而逐步建构中国本土的文化政治学,服务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这项工作,无疑地需要包括政治学者、公共管理学者、社会学者等在内的社会科学学者的共同努力。
三、我对文化发展的研究
在我看来,文化不是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价值命题,只能作阳春白雪式研究,而是当下中国现实的一个核心问题。文化,尽管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在我看来它首先是一个公共性概念。
譬如,农村文化发展研究。透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我的主要结论是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性日渐消解——所有的农村文化之变几乎都是围绕着公共性的消解这根逻辑主线展开的:农民对自己的社区认同日益弱化,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衰微,村庄的公共舆论日趋瓦解,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那个曾经是农民生活的家园“村社共同体”也处在解体之中。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必须抓住其主要矛盾,即公共性的消解和再造这个核心问题来展开,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农民观念的变化上面。
如今,人们在行动之前,总是要问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人际关系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在许多地区,农民邻里之间传统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农民之间的劳动关系都变成即时性的金钱交易。
农民在日渐功利化的同时,也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使得传统社区公共生活走向瓦解;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农民的生活逻辑中来,其行为充满着越来越多的变数而无法有效预期。“农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写照。对于当下农民而言,个人利益远远超过了公共利益,公共事务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学陷阱之中。
公共精神是一个共同体或社会的灵魂。一个社会的公共精神越发达、越充分,这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就越好,每个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资源和公共福利就越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农村社会里,这种公共精神正在不断流失,农村的公共事业也因此而萎缩。虽然最近这些年国家逐年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但是即便是这样,农民考虑是否参与这些公共事业建设也是看他能否从中获取即时性利益——政府是否给予金钱报酬以及所给的报酬是否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而不是因为这项公共事业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
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的乡村社会里,村庄公共舆论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各种偏常或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诸如“那是人家的事”这样的村庄公共舆论,形式上似乎趋向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更加包容,实质则是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人们不再在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谈论、批评甚或指责社区内某个人的失范或败德行为;人们偶尔会讨论与自己社区无关的“大话题”,这些大话题不仅失却了在地性,也失却了公共规范的功能,总之,这些公共舆论不再以公共利益为旨归了。
没有了公共舆论的规约作用,也没有了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情,年轻人开始频繁地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可以毫无顾忌地贪污,甚至与乡村混混势力联合在一起。农村社区成为无规制之地,丛林原则肆虐横行,成为当下农村治理无可回避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抛弃“全能主义”[7]治理型式的同时,国家也逐步放松了对私人生活的控制;“市场”逐渐取代国家将其力量延伸到农民的私人生活世界,从而加速了对传统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解构作用。诚如阎云翔所观察的那样,这种私人生活的变革,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他们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无视应有的义务与责任,最终沦为“无公德的个人”[8]。
私人生活的变革总是跟公共领域的变革相互影响、交织作用,其中最坏的情形同时也在当下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正在泛滥的是:一方面是私欲的无限膨胀或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是互助精神的消解和公共意识的衰落。这种农民私人生活的异化,实际上是农村公共生活退化的一种表征和映射。
家庭生活是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基础,它既是农民私人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农村公共领域的基本组成单元。如今,原来视为农民日常生活最坚固的“堡垒”——在集体化时代,国家曾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摧毁农民小家庭利益,将它融入社会主义“大集体”之中,然而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也日益变得不堪一击了。近些年,农民的离婚率急剧上升,打破了农民婚姻家庭一贯的稳定型态,农民的性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农民对婚前性行为说三道四,如今外出打工农民婚外同居、农村女孩进城“做小姐”、农民婚丧的脱衣舞表演已屡见不鲜,农民对此也见怪不怪了。农民的家庭生活无论是在形态上还是在结构上乃至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量青壮年农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不仅仅使往昔其乐融融的农村失却了生机和活力……最初发生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层面的“空心化”也日渐蔓延到农民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之域。农村文化的“空心化”,不单表现在农民伦理道德的缺失和异化,更表现在年轻一代农民从骨子里瞧不起自己的农村文化——他们的行为取向抑或心理意识都是城市化的,他们不知晓也不愿意遵从传统农村社区的伦理道德规范;他们拼命地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抽身、逃离出来,纷纷拥抱五光十色的城市。
实际上,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性的消解跟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启的乡村社会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我认为,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是乡村社会个体化的一种反应。
如果旧的公共生活方式被消蚀,国家和农村社会自身又不能及时孕育新的公共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候,新兴的宗教成为农民日常公共交往的一种替代物而伺机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后,一个个个体不单从高度集中的、整齐划一的、无所不包的“总体性社会”中“脱嵌”出来,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人从家庭、亲属关系、单位或集体、社群(社区)和阶级等结构性藩篱中解脱出来,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 lrichBack)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个人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并不是像欧洲那样发生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架构中”[9],而日益成为“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个体,农民缺乏有效结合而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伴随乡村社会个体化,农村福利制度的缺失、互助互惠网络的消解、公共生活的式微和日益加剧的“流动的生活”,都为当下农村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理据。恰如马克思所言,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与人分离和疏远的表现[10]。
然而,为什么偏偏是基督教及其变种宗教发展得更快呢?因为这些新兴宗教的教会组织相对于其它宗教而言联结得更加紧密,并且形成了巨大的组织网络,遍布城乡社会,他们大多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更加方便那些年老体衰、行动不便的老人以及顾及家庭和照顾农业生产的留守妇女的经常性集会,通过这种集会不但可以排解他(她)们的孤独、愁闷,而且可以形成一定的互助模式,解决他们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经常出现的靠单个人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譬如老人照料、相互关照和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等);一个“家庭教会”的规模往往与村社共同体的范围具有极高的一致性,也较好地说明了它更容易满足信徒日常生活的需要。
即便是外出务工的农民,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也容易在教会网络中寻找到必要的帮助,得到类似于家的温暖。在那些政府公共服务缺位、村社共同体解体的地方,信仰基督教便成为个体化农民重新团结起来、重新“嵌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个体化在另一个方面也意味着传统的消失或者从传统的生活方式中脱嵌出来,换言之,个体化的乡村社会不再被传统规范所束缚,人们在形式上拥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因之,农民在宗教信仰上日益多元化和自由化。人们对于宗教信仰不再像过去那样干涉他人,认为这是别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非信教村民对信教村民的态度从一味排斥转向温和的“选择性认同”。即便如基督教这样与中国传统枘凿方圆、扞格不入的外来宗教,也不再被农民所排斥。
可是,在一个同样个体化的村庄里,为什么有些农民信教有些农民不信教呢?从诸多田野调查和笔者在农村的经验观察来看,当前信教的农民绝大多数是老人、妇女、疾病患者、残疾人和鳏寡孤独,尽管每个人的信教动机各不相同。也就是说,这些被新兴宗教所吸引的农民往往是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群体,与之相反,那些不信教的农民往往可以借助市场化机制来解决他们生活和生产上的合作问题,他们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些边缘或弱势农民未必(完全)是被宗教的教义所吸引,加入宗教组织或许是他们唯一可能的现实选择而已。并且,这些边缘群体还可以借助宗教来建构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意识形态),消解自身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劣势处境,或者建立属于他们的认同感(以与优势群体相区隔)、道德感(重新评价优势群体)、自尊感(自我意义建构)。市场经济本身包含着一种筛选机制,它往往将一个村庄分化为两大群体,一部分人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这些人往往被称为“能人”,另外一部分人则被市场经济所淘汰,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相对于前者,后者更容易被上帝所恩宠,成为祂的信众。
总之,正是因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和“公共性的消解”导致了农村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农村宗教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解读为农村公共生活衰落和亟待重构的一种变相反应。
这些发生在乡村社会的变化,其实已经弥漫于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了。重建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将成为目前中国文化建设最紧要的历史使命。可是,对此所进行的研究却严重不足。对于我们这些生逢当代、恰逢中国社会的学者而言,不但十分“幸运”,而且也有历史责任,去研究当代中国现实社会文化发展和建设问题——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甚至可以说,当下中国处在千年未有之变革时代,这给我们这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切身体验和思考的机遇,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理会它,因为我们的苦乐痛痒、愁闷与喜悦、激情与梦想无不跟这个时代、跟当下中国社会紧密关联着。
[1]ClydeKluckhohn(1944),MirrorforMan.NewYork:Fawcett。
[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4~5页。
[3]方彦富:《文化政策研究的兴起》,《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4]BellHooks(1991),Yearning:Race,Gender,and Cultural Politics,London:Turnaround,pp.9.
[5]Fredric Jameson(1988),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as an Unfinished Project.Rethingking Marxism,No.1,pp,71.转引自[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内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6]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7]“全能主义”一词由邹谠所创,他认为:“全能主义”(totalism)的概念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不同,它指的是一种指导思想,即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和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8]参阅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57~261页。
[9][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一格恩斯海姆:《前言:个体化的种类》,载[挪威]贺美德、鲁纳编著:《“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许烨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责任编辑刘强)
D0-05
A
1671-0681(2015)06-0004-06
吴理财,男,湖北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三农学者。
2015-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