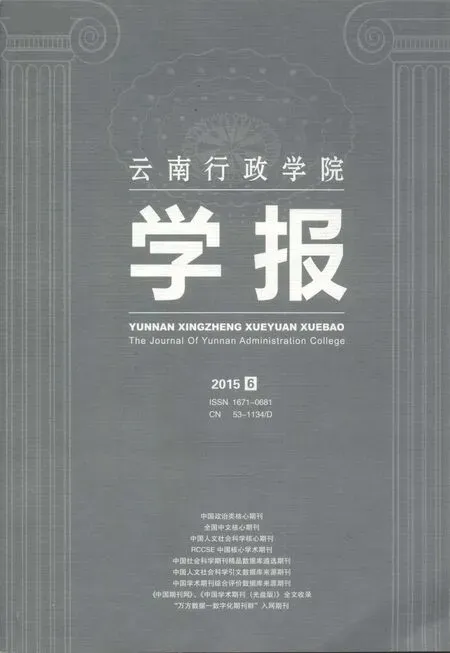论我国边疆的多重属性及其安全风险*
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论我国边疆的多重属性及其安全风险*
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边疆是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边缘性部分。在国家地理空间分布中,我国边疆处于国家政治体系的远端、经济中心的外围、文化辐射的末梢、信息传导的终端。我国的边疆作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又是与周边国家接壤或毗邻之地,不但是国家地缘政治博弈与文化角力的前沿阵地,而且也是军事安全风险的聚积之地。边疆独有的地理空间特质、地缘政治特质和民族文化特质,使其天然地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风险,并时常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诸多挑战。
边疆;边疆属性;边疆安全;安全风险
在当前民族国家组合而成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占有一定地理空间的疆域构成了民族国家最为基本的生存空间,疆域安全的建构乃是民族国家得以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安身立命的前提。边疆作为国家疆域中非常特殊的区域,是国家地缘政治博弈与文化角力的前沿阵地,也是军事安全风险的聚积之地。我国的边疆不仅是国家与国家疆域毗邻或交汇之地,而且还是政治偏远、经济边缘、文化异质、民族聚居和多元宗教文化聚汇之地,边疆独有的地理空间特质、地缘政治特质和民族文化特质,使其天然地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风险,并时常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诸多挑战。
一、边疆的地缘政治特点与安全风险
我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的多民族国家,海陆疆域俱为辽阔,毗邻国家众多,边界线漫长而且犬牙交错,地缘政治生态十分复杂。边疆作为国家与周边国家疆域的毗邻地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国家地缘政治角力的前沿阵地、国家军事安全风险的汇聚之地和地缘政治问题的多发之地。
(一)边疆是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前沿阵地
在当今国际政治体系中,民族国家以其清晰的主权意识和疆域概念成为了国际政治地理空间中最为基本的组成单位。在当前全球地表已经份属不同的民族国家或者被不同的民族国家控制之后,各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思量,为了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国家安全保障或者生存空间拓展,往往与其他国家开展各式各样的合作与竞争,并形成和平与战争、合作与博弈、联盟与冲突等各种国家关系形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直以来十分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重睦邻友好,然而,由于国家利益的歧异、地缘政治的思量和政治文化的异质,周边一些国家也不可避免地与我国展开各式各样的地缘政治博弈与竞争。边疆作为我国与周边国家毗邻的区域,周边国家与我国之间的博弈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又体现为围绕边疆展开的边疆争夺、边疆挤压和边疆较量。就边疆争夺而言,我国与周边一些国家还存在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和海上权益争端,东海,南海问题时时搅动相关国家敏感的神经。就边疆挤压而言,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大国崛起,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地缘政治格局的主导者和既得利益者在国家安全最大化的理性思量之下,担心中国的崛起挑战既有的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因而不断挤压和压缩我国的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试图通过战略围堵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就边疆较量而言,周边一些国家的整体实力虽然与我国无法抗衡,但他们善于通过边疆建设形成于相对我国边疆发展的区域性优势。周边国家边疆建设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一些久居贫困的边疆民众在生存境遇的跨境比较中产生了难以言说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
(二)边疆是国家军事安全风险的汇聚之地
不管是从人类有史以来国家征诸战争的历史来考察,还是从我国边疆的传统认知与定位来分析,边疆都是国家军事安全风险的汇聚之地。只要当今世界没有实现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和老子所谓的天下大同,边疆因为地缘位置而滋生的军事安全风险就不会消逝。从人类有史以来的国家历史来看,绝大多数的国家之战,不管是源起于国家利益的纷争,还是意识形态的隔阂,抑或是统治者扩大国家生存空间的政治野心,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和战争烽火莫不发端于边疆。边疆安全成为测度国家疆域安全最为基本的指标之一。为了维护国家疆域完整和政治安全,历来的国家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边疆的军事战略地位,孜孜以求地在边疆进行军事布防和建设,而一个国家在边疆进行的军事布防与建设往往又容易引起周边国家自身安全指数的降低和“霍布斯恐惧”的滋生,周边国家进一步又加强自身军事力量的边疆布防。周边国家军事力量的增长和边疆布防的变换,又反过来降低该国自身的安全感观,导致国际社会军备竞争现象的出现,并进一步刺激和放大国家安全尤其是边疆的军事安全风险。
就我国边疆传统认知与定位而言,在传统的国家认知与边疆想象中,核心区域往往被视为国家的腹心和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国家存续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边疆地区往往被视为国家核心区域的外围部分,是王朝国家“由治走向不治”的过渡性区域,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事使命和拱卫核心区域的政治重任。随着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启动与完成,边疆认知逐渐从传统王朝国家时期动态盈缩之地变成主权国家不可分割的固定之域,但由于晚清以来边疆危机的深重,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局势的并不太平,边疆的军事要冲地位和战略防卫地位依然十分突出,边疆也主要被视为拱卫国家安全的战略纵深和安全屏障。而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纵深和防御屏障的边疆也理所当然在承受了来自国际局势紧张和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种种安全挑战和地缘风险。
(三)边疆是国家地缘政治问题的多发之地
我国是一个边疆广袤,边界线漫长的国家,与我国接壤和毗邻的国家众多,边境地理形态十分复杂。边疆与生俱来的地缘政治特点天然地蕴藏和滋生着诸多安全风险。首先,边界线漫长使得边防难度和边防压力十分之大。长期以来,我国边境与周边国家的边民,相互之间走动频繁,声气相通,再加上许多边境线一带便道林立,边民互市或走亲访友等常常不办理出入境手续而取便道出入邻国。这一方面给非法跨境务工、非法跨境婚姻、非法移民等活动提供了先在的便捷条件,另一方面又为一些跨国犯罪事件(如走私、贩毒、宗教渗透、拐卖妇女儿童等)预留了地理空间[1]。其次,与我国边疆地区接壤和毗邻的国家十分众多,客观上也使得我国边疆成为周边国家治理绩效负向效应外溢的承担者。由于我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隔界相望,周边国家的治理绩效便与我国边疆地区产生了直接的关联性。如果周边国家出现治理失败等问题,那么我国边疆地区难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前周边国家治理中出现一些问题,如东南亚地区军火管制失控问题、缅甸难民问题、朝鲜核试验外溢效应问题,都是直接影响我国边疆安定祥和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最后,边疆作为国家对外交往交流的前沿阵地,其内部滋生的社会风险容易产生跨国性后果与影响。不管是艾滋病的跨境传播,还是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化,都与边疆地缘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
二、边疆的地理空间特点与安全风险
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来说,边疆处于国家政治格局的远端、经济中心的外围、文化传导的末梢和交通体系的边缘。边疆区域在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分布格局中的独特区位使得边疆区域容易遭受到诸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
(一)边疆的地理风貌与安全风险
在我国国家政治地理空间格局之中,边疆之所以被视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不仅在于文化的奇瑰,而且也在于地理的特异。按照李安宅先生的说法,边疆地区其所以不与内地相同之故,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就自然条件而论,不在方位,而在地形[2]。顾颉刚先生也曾言道:“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3]。边疆这种独特的地理风貌孕育了边疆与内地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社会形态、民族文化和民族秉性,却也使得边疆与内地的社会交流和文化互动存在诸多天然的阻滞,既影响中原文明向边疆地区辐射,也妨害边疆民族文化向中原地区的流动。具体而言,首先,边疆地理风貌对于边疆民众的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生活习惯和身心特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地缘政治学的相关解释,地理环境是形成民族文化复杂因果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也是制约社会存在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发展。我国西北、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各具情态的地理风貌孕育了不同的边疆文明,不但导致边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异质,而且边疆与边疆之间、边疆内部之间的文化异质性也很明显。其次,边疆独特的地理风貌还天然地影响甚至阻隔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的交流互动,导致了中原文化与边疆文明相互理解、交融与涵化的困境。我国的边疆区域主要以高山、大河、荒漠、戈壁、大海为标志,风景虽然壮美,地形却着实险峻。这种险峻的地貌,成为了王朝国家时期中原文明与边疆文明双向交流与沟通的最大障碍,也容易产生诸如族际政治信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二)边疆的政治区位及国家政治安全
“‘疆域’作为一种国家存在的物质载体和空间实现形式,产生于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人文地理条件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之中。”[4]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漫长的冲突与融合的历史中,我国古代先民以中原为观察和想象天下的原点,并按照王朝统治实力所能掌控和达到的区域将国家疆域划分为“中央属土”和“周缘边疆”。在古代先民的边疆想象中,边疆就是国家由“治走向不治”的过渡性区域。在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尤其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地区进行投射和释放,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我国通过“行政权力渗透”和“民族精英绥靖”将边疆地方政权整合进入国家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不过,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完成和国家政治一体化的建构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边疆居于国家政治格局远端的基本事实。而边疆处于国家政治格局的远端,直接导致边疆容易滋生领土和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认同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涉及政治安全的诸多问题。一方面,我国国家疆域广阔,边疆区域与中心区域存在显著差异,边疆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辐射与意识形态的感召,民族政治亚文化现象十分突出,国家整合的难度比较大,一些极端分裂势力往往也利用边疆的区位特点和文化特点,鼓噪和从事分裂国家疆域的违法活动;另一方面,边疆处于国家政治格局远端,在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过程中也容易成为其他国家制衡和迟滞中国崛起的抓手;此外,我国边疆地处国家政治格局远端,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大肆进行宗教渗透和文化侵略提供了上下其手的空间,他们利用边疆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异质的特点,大肆从事解构边疆民众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的勾当,严重挑战边疆区域的秩序建构和安全维护。
(三)边疆的经济区位及国家经济安全
我国的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处于经济中心的外围,远离国家经济增长极的辐射与驱动,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推进,我国边疆区域赢来跨越式发展的良机,但由于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在地理风貌、发展起点、传统文化、发展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一些边疆区域还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存在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特点。此外,在我国国民经济动态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用最大化倾向,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金、物质、能量、信息、人才等,不断向国家核心区域尤其是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市场经济本身蕴藏的“回波效应”使得边疆区域存在因为人力、物力、财力的减少而导致发展速度降低的风险,再加上边疆处于地缘政治博弈与角力的前台,国家在推进边疆发展方面持审慎的态度[5],从而使得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非均衡状态,尤其是边疆区域的贫困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我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是一个国家经济系统抵御国内外各种因素威胁、侵蚀、干扰与妨害能力,是国家经济独立、协调、稳定、健康运行的一种状态。经济安全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没有经济安全的建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都将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区域发展非均衡和边疆发展滞后的状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边疆安全与稳定的重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它不但降低边疆抵御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而且导致国家内部经济系统循环运转存在失衡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边疆在国家发展格局中边缘化的困境如果长期得不到改观,那么边疆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将有可能变异成政治共同体的巩固与统一的问题。
(四)边疆的文化区位及国家文化安全
在中国传统的边疆想象中,边疆往往被先民们想象成远离京畿的异域空间和化外之地,边疆也以其文化区位的殊远和文化表征的奇瑰称名于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文化互动日趋增强,但由于边疆远离国家主流文化的感召与辐射,边疆民族文化又具源远流长的延承性、封闭性与保守性,边疆民族文化的特质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边疆处于国家文化传导的末梢与边疆民族文化的相对完整性,使得国家文化在向边疆地区传播之时出现了多重阻滞。首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在向边疆地区传播之时,由于地理空间的遥远,容易出现认知深度与认同效力递减的问题。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边疆传播过程中,又容易与边疆传统民族文化产生一定程度的抵牾轩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统领、涵摄和引领边疆民族文化,将是关系到边疆稳定和安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再次,边疆发展的相对滞后和公共文化供给不足,又使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存在深层次的困境。很多边疆地区,国家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仍然非常有限,除了电视之外,大多数民众不能和国家主流政治文化进行密切的接触。在一些边境沿线地区,甚至还有很多自然村不通电,不能收看电视。很多少数民族还存在语言障碍,对主流政治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都非常有限[6]。还次,我国边疆地区往往也是当今世界几大文明折冲碰撞的重要地方。边疆社会的文化认同、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容易受到境外文化的冲激与影响,从而引发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问题。
三、边疆的民族宗教特点与安全风险
我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人口众多,规模庞大,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的历史流变中,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相互嵌入式的民族居住结构。以民族分布而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成份众多,而且诸多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俱有分布,如云南省的少数民族成分多达55个,内蒙古自治区为54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53个,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民族成分也分别达到了53、48和51个。以民族人口规模而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规模十分庞大,“据统计,至2007年末,分布在我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数约为6648.14万人,约占全国人数总数的5. 03%。其中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人口最多,为3735.41万人;西北边疆次之,为1271.26万人,东北边疆为1115.34万人;北部边疆为526.13万人”[7]。我国边疆地区不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而且也是宗教文化氛围十分浓郁的地方。在我国边疆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大多数都信仰宗教,如藏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傣族多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流行信仰伊斯兰教。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与落实,边疆地区出现了一场持续的宗教复兴运动,宗教场所得以恢复和重建,各种宗教团体纷纷成立,各类宗教教徒数量都有所增加。
我国边疆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以及由此产生的瑰丽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宗教文化,使得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构成更为丰富和多元,不过,边疆民族组成的多元和宗教文化氛围的浓郁,也使得边疆地区不得不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首先,边疆民族的多元组合潜藏各个民族利益博弈的问题。在当前我国民族事务的治理中,随着民族平等、团结、和谐和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的价值取向的确立,各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各个民族利益高度的一致性,并不能遮避当前各个民族在民族具体利益上依然存在博弈与摩擦的可能。在国家对稀缺性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中,各个民族基于自身利益维护与壮大的理性思量,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竞争与博弈。如果国家在稀缺性资源权威性分配过程中,不能实现利益分配的“实质性正义”,或者不能有效地满足各个民族的利益期待,那么就容易产生民族关系安全等问题,尤其是一些在族际分化中居于不利地位的民族更容易产生民族认同强化和民族离心等问题。
其次,边疆多元的宗教文化也潜藏着宗教的不容与纷争的问题。边疆地区宗教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是我国深入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结果。在当今世界,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信仰自由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因宗教差异引发的冲突仍然不断发生,宗教多元也带来了隔阂、不容乃至敌视”[8]。“由于各门教派都坚称自身的信仰就是最高真理,所以宗教与宗教之间没有构成‘一体’的可能。征诸历史,宗教事实上也只有宗派的分化,没有宗派与宗派、宗教与宗教的凝合。如果所谓‘一体’不能像历史经验所昭示的那样,明确并且富有建设性地指向礼乐文化和主体性,而只是以政治所维护的国家统一体为遁词,那么,宗教问题在当前就很难摆脱一个特殊尴尬处境,即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宗教问题都将演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极大地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社会认同和政治体制认同的难度;长远地看,心往各处想,劲往各处使的宗教,将很难向古代的‘社稷’那样发挥推动社会认同、凝聚的作用,甚至可能被各种政治企图、政治势力所利用,成为社会分裂的动员仪式。”[9]一些别有用人的组织和个人正是看中了宗教的这种特点,摒弃宗教的正信正传、正知正觉于不顾,极力煽动宗教偏执和宗教狂热,不遗余力地推动宗教问题政治化。一些国家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挑起地区冲突;一些极端组织利用宗教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还有一些人利用宗教从事违法犯罪活动[10]。
再次,边疆的多元民族与中华民族建构的问题。在我国各个民族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各族人民交相互动,不断磨合、吸纳与涵化,最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我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纵深推进,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更进一步地成长为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自发演进和理性自觉而不断长成的中华民族,为我国各个民族提供了共有的政治屋顶、历史体验和精神家园。它的纵深建构,“既是中国民族国家巩固的基本前提,也是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基本前提。中华民族越是巩固,越能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11]。随着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纵深推进,当前我国从国族历史的叙事、政治图腾的表意、民族利益的经营与精神家园的建设等诸多方面深入推进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然而,当前我国将各个民族整合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却因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与国族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异质性而遭遇到了诸多阻滞。边疆各个少数民族在民族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动力,它们共同筑就了气象万千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然而,勿庸讳言的是,各种异质性的民族在跨文化交流中也会存在文化敏感和文化冲突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潜在地构成了中华文化一体的整合困境,如中华民族始祖想象的困境、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的难题、文化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均衡悖论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善,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华民族建构和中华文化建设,也会威胁到边疆地区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和民族共识的形成。
最后,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博弈的问题。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而民族认同是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和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它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按照原生主义的解释[12],人类个体一出生就陷入了“婴儿民族陷阱”,在牙牙学语时期就浸淫在父母、亲属和社区所构建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天然地汲取自己所属族群的独特认同和集体记忆。在原生主义的理论视阈中,民族认同更近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生的认同”,而国家认同则是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权利保障、教育宣讲等方式在后天进行的“理性的建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交集,却又并不完全重合。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员在自我的认同体系中,将何种认同置于优先地位,是关涉到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影响国家巩固和民族和谐的一个基本问题。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界线上的非重合性,使得我国边疆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天然地存在认同失谐与认同错位的风险。由于边疆区域与中心区域地理区位上的遥远,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国家与边疆的互动,边疆少数民族与国家主体民族又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具有指向相异的民族认同和差异的文化价值观,导致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疏离感和主体民族文化的相异感;此外,边疆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性毗邻区域,与邻近国家的地理距离十分相近,边疆民族因同一民族跨境而居形成了与他国同族居民同文同种的社会文化网络,使以地缘为基础、以族缘为纽带的跨国流动十分便利,边疆民族重民族身份,轻国民身份的现象比较突出,其国家认同具有模糊性、摇摆性和选择性[13]。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模糊性、摇摆性和选择性,导致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在边疆贯彻和实施的阻力增大或者使其流于形式化,引发并加重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边疆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安全压力,增大了分裂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可能性,同时也为敌对势力借机分裂我国提供了可乘之机[14]。
[1][7]周平主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149,146.
[2]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M],北京:中华书局,1944:1.
[3]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164.
[4]黄毅.论“边疆观”及其空间表征的历史考察[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5]周平.论中国的边疆政治及边疆政治研究[J],思想战线,2014,(1).
[6]郑晓云.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11,(7).
[8]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9.
[9][10]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
[11]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41.
[12]James McKay,AnExploratory Synthesis of Primordialand Mobilizational Approaches to Ethnic Phenomena[J],Ethnicand Racial Studies,1982,(5).
[13]何明.国家认同的建构——从边疆民族跨国流动视角的讨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0,(4).
[14]李崇林.边疆治理视野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探析[J],新疆社会科学,2010,(4).
(责任编辑刘强)
D67
A
1671-0681(2015)06-0048-06
朱碧波(1981-),男,湖北潜江人,法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
2015-9-2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研究”(11&ZD12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CZZ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基于扩展的增长核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