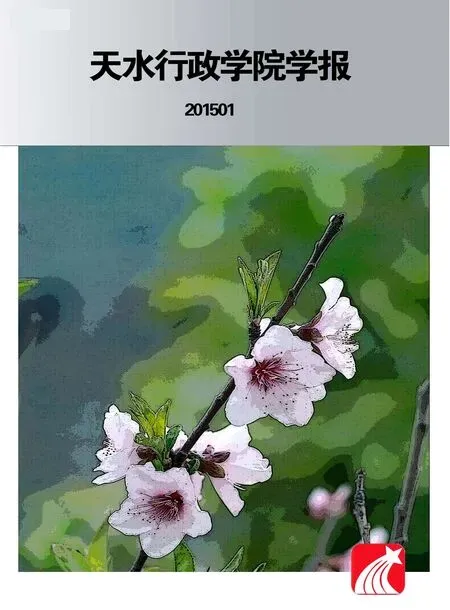论冯友兰才、力、命思想
马光耀
(中共天水市委党校,甘肃天水741000)
论冯友兰才、力、命思想
马光耀
(中共天水市委党校,甘肃天水741000)
冯友兰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新原人》一书中首次提出才、力、命思想,结合立言、立德、立功三个梯度阐述了对成功的独特见解。笔者通过对冯先生才、力、命范畴的具体分析,力图找出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并通过分析、归纳、对比、综合的方法揭示成功因素的异同,剖析才、力、命思想的不足,探究成功的科学含义,以期揭示出当代人成功的共同性因素。
冯友兰才;力;命;思想
人人都想成功,但真正成功的人却不多,这是因为理解成功因素的科学含义的人很少,即使理解到位不能付诸实践也是徒劳。冯友兰的才、力、命思想,强调在学问上才占主要地位,在事功上命占主要地位,在道德上力占主要地位,有明显的机械论倾向,笔者难以赞同,以下分析阐述之。
一、才与力
才,包括才学和天资两个部分。冯友兰对才的定义是:“一个人的天资,我们称之为才。一个人在某方面的才的极致,也就是他的力的效用的界限。到了这个界限,他在某方面的工作即只有量的增加,而不能有质的进益。”[1]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第一,才就是天资、天赋、先天具有的,冯先生是先验论者、天赋观念论者,当然这也属于遗传决定论的观点,不尽科学。第二,人的能力有限,人的潜力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这与当代科学中生理学所揭示的人的潜力是无限的观点相反。“才是天授,天授的才须人力以完成之。就此方面说,才靠力以完成。但人的力只能发展完成人的才,而不能增益人的才,就此方面说,力为才所限制。人于他的才的极致的界限之内,努力使之发展完成,此之谓尽才。与他的才的极致的界限之外,他虽努力亦不能有进益,此之谓才尽。”[2]在才与力的关系上,后天的努力只能发展才的方面,而不能增益人的才。这实际上是他不懂得人的才干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光是头脑里有才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人必须在实干中才能增长才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实践作为中介沟通了主客体,使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人,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
力是指人的努力程度。“一个人的努力,我们称之为力,以与才与命相对。力的效用,有所至而止,这是一个界限,是一个人的才与命所决定底。”[3]冯先生的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才与命决定力,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力决定才,而不是才决定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仍然是力。因为天资再好,不付诸行动仍然无济于事。在此意义上,冯与孔孟一样,是先验论者,也类似西方哲学的天赋先验论思想。“人的力常为人的才所限制,人的力又常为人的命所限制。”实际上这是他给人力主观地划定界限,使之服从于才与命,可见在知行关系上,冯是先知后行的代表人物。这也可以从他的《新理学》中最根本的“理”范畴类似于西方哲学中柏拉图的“理念”范畴得到映证。
二、命与才、力
命运是表示个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的范畴,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冯友兰给命下的定义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或不幸,没有理由可说。”[4]生活在哪个家庭,哪个时代,不由我们选择,也就是说个人出生的环境是既定的,这是人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对人的活动有巨大的制约或影响作用,所以无理由可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5]生在一个各方面好的家庭,人的遭遇会好点,即幸运;反之,连基本的健康卫生条件都不具备,则算不幸,这里各方面条件指的是经济条件,家长的智商、情商、教育背景、生活常识、健康卫生条件等综合因素。他又说:“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类不能战胜,否则就不称其为命运,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6]这里仔细分析起来,一方面,冯先生割裂了命运与环境的关系,才造成他最终得出不科学的结论。其实,命运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微妙。在孩童时期,环境决定命运,而在成人时期,是人改变创造环境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因此,实践是人的本质,人是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冯先生认为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也有其合理之处。冯先生又说:“这命不是一般迷信的命,就是机会,也可以说是环境。”在此,他将命解释为机会,或环境。但一般指的是儒家的命,类似于“天命”,“儒家所讲的命,乃指人在一生中所遭遇到的宇宙之事变,而又非一人之力所奈何的。”并且他重述,“创造环境,争取机会是属于努力那方面,与这里的命无关。”从这段话可知,冯友兰对命的解释相当矛盾,一会儿说命运就是机会,也可以指环境,一会又说命指儒家的命,但显然他侧重于儒家的命。这几种解释显然不同,如果说命是机会,那就要看你能否抓住它;但他又说,这属于个人努力方面,与这里的命无关。这同样割裂了命、环境、机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的儒家的命无非是对一些事的无可奈何,不可改变。其实人生有许多可以改变的命,而其中也有不可变的命,如先天遗传决定了人的眼睛、身体是否健康,而后天环境更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健康的眼睛在恶劣的环境下被损害就是例证。总之,命本身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但总的规律是变的,这也符合辩证法的规律。冯先生给人人为地划定一个界限“命”,让人自守本分,这在本质上与儒家孔孟的宿命论思想一脉相承。周国平教授说:“命运主要有两个因素决定:环境和性格。环境规定了一个人的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决定了他对遭遇的反应方式。”[7]笔者认为行为造就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在一定条件下决定命运;而正确的判断力和果断的行动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
冯友兰说:“一个人的命运的好坏,影响到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的贵贱。”“一个人命的好坏,影响到他所作事的成败。”[8]这是冯友兰的经验之谈,也是常识。人的命运不同,环境不同,起点也就不同,身份地位自然不同,同时,身份地位高的人能办成的事一般人却办不到。有些庸才成功了是命好,不是他的能力强。冯先生认为自然境界中的人对于其所做的事的成败,亦不必有某种情感,这实际上否认了人是一个知情意的统一体。他把道家所处的境界归为自然境界,而把儒家孔孟的境界尊奉为天地境界,确实有薄彼厚此之嫌疑,这说明他的立场是儒家一派的,他也以新儒家的代表人自居,企图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地步。他指出“贤”是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圣”是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显然,他的“圣”与“贤”和古代的圣与贤不同。他又提到求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主要功夫是致知用敬。用敬靠力,致知需才。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天地境界与自然境界的划分并不科学,有很强的主观性与机械性。范鹏教授说:“境界说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错误的。其实,没有社会哪有社会之理,脱离了社会哪有个人之理。境界说的方法是错误的,纯动机论的抽象继承法产生了以文害意的恶果,对境界的机械划分没能反映出正逆向两个方向发展的真实趋势。”[9]很明显,境界说理论与生活实践的脱节是根本缺陷;但同时他又给人们设定了道德理想,让人们明白精神价值尤其是道德价值的崇高地位,对于当代人的道德缺失似乎有所启示。
三、学问、事功、道德
冯友兰说“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10]笔者认为,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基本是科学的,已为大量事实所证实,但对于后面的说法不敢赞同。笔者仍以冯先生举的例子为证来说明理由。“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历史上最成功的例子是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成功。”项羽之所以输给刘邦是因为心机不够,不会用人,即才力没有充分发挥所致。对此毛主席有诗为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主席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而冯友兰却将项羽的失败归于命运,并引用了项羽的《垓下歌》为证,说“‘时不利兮’是项羽毫无办法,而有些庸才偏偏成功,史册上很多,不胜枚举。”[11]这样的论证显然不能成立。其实项羽的命运本来比刘邦要好的多。首先,项羽的叔父项燕是大将军;而刘邦只是一介亭长。其次,项羽的军事实力要远比刘邦强大。项羽之所以会落得“时不利兮”的下场是他自己没有抓住机会将刘邦置于死地,不会识人,不会用人,一再错过机会所致。项羽的命运由好变坏是他一次次痛失良机,没有正确的判断力所造成的恶果。厚黑学大师李宗吾先生则认为项羽的失败是因为脸皮不厚心不够黑。项羽曾经用“破釜沉舟”之计击败秦军,他也是有才的;所以不是项羽的命不好,而是项羽有才、力却不会用,即没有正确的判断力,这导致他最后的命运不好。由此可见,冯先生对命运的定义存在误解,有偏颇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有些道理,有些“庸才”能够成功的例子确实不少。这是由“命”即家庭环境好决定的。总之,不加分析地说“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有失偏颇,实际上这是他强调天命而轻视人力,叫人“安之若命”罢了。
冯友兰又说:“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这种说法未免失之简单。“普通人以为圣贤需要特别在事功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错误的,孔子和孟子成为圣贤和他们的才干没有关系。”[12]这种说法显然不对。众所周知,孔孟之所以成为圣贤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才学高,怎么能说才与德没有关系呢?至于孔孟的道德怎样,我们当然不能像冯先生那样不加分析地说是圣是贤,毕竟说是一回事做又另一回事,可能孔孟的道德并不怎么样,他们自己说得到却做不到,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道德起源于人们之间的需要,起源于民众的生活实践,它是历史的、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当然有继承性和民族性,具体的是说时代性和现实性。即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而谈道德,这样的道德是被抽空的,也是不现实的,是强加给人的东西。首先,它贬低人的情感、欲望以崇尚理性,暴露出极端理性的不足。其次,它完全忽视了人的意志自由,只让人选择善;但是恶人往往选择恶,并且以此为乐。由此可见,冯友兰受孔孟儒学、宋明理学影响之深,他把传统的道德抽空之后又想在新社会运用,即他所说的“旧瓶装新酒。”其实道德是具体的、历史的,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谈道德必然失之玄虚。冯先生主观地将道德架空意在以道德为目的,建构宗教式的哲学道德观,这是不现实、不科学的,目标太高就会不切实际,“道德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13]。笔者认为道德的本质是对人性善恶的反映,是对人心灵美丑的反映。“道德的本质是人格的呈现。”[14]首先,道德是主客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特殊意识形态,只靠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道德有其客观性,不是只有主观性。即不同的人道德层次不同,境界当然不同。其次,有些坏人也不会努力去成就道德,因为他们认为那样一文不值,并且他们喜欢做一些不道德的事,还以此为乐。最后,要求每个人都成圣贤的愿望虽好,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与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之所以会有这些缺陷是因为他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而缺乏科学性。
冯先生对命的认识有个生动的比喻:“人生如打牌,而不如下棋。与下棋时,对于一时所有之可能底举动,我均可先知;但于打牌时,则我心中将来打和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预测底。所以,对于下棋之输赢,无幸与不幸。而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与不幸。”[15]这段话中,“下棋对于一时所有之可能底举动,我均可先知”说法显然有问题。其实,棋力的高低主要决定于棋理与算路,棋力低的人往往不知棋力高的人下这步棋的意图。这当然是不可先知的。棋力相当的人,虽可先知,但下棋的输赢与运气密切相关,包括当时的身体、心理状态等因素,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简单的说“下棋之输赢,无幸与不幸。而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与不幸。”古人曾说过“人生一局棋。”这与冯友兰“人生如打牌”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其中的真意如何走好人生这盘棋中的关键几步,人如何设计、计算人生的棋路,也有启发意义。的确,人生由于个人遭遇不同,而不可能像一盘棋那样双方机会均等,在此意义上,冯先生的比喻比之更合理。
四、对成功的不同见解
季羡林先生认为,“成功=天资+勤奋+机遇”,并且认为“只有在勤奋努力上下功夫,天资、机遇都是天授的。”[16]王海明教授认为,“欲望与才力命德相一致,乃是幸福或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17]李金水认为,决定人生成败的十六种因素分别是:细节、心态、品格、选择、情绪、思考、时间、健康、诚信、目标、行动、说话、关系、自信、潜意识、眼光[18]。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对成功的理解都不全面。首先,成功是一个包含综合因素的概念,不是简单的套套公式就能付诸实践。因为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恋爱、婚姻、考试、工作、做事做人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就决定了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次,不同的人对成功有不同的理解。季羡林先生强调人力的作用;冯友兰先生强调,才、力、命在不同方面地位不同;王海明教授强调欲望在成功中的首要地位;李金水强调成功的综合因素,但至少缺少胆量这一因素。再次,其实成功是一门实践科学,需要不断地探索总结经验教训,需要经验的积累,需要胆量和智慧,需要自信作为根基,需要正确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落实在行动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它更接近行为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国外成功因素的研究中,早就有遗传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之分,其中行为主义属于环境决定论;而智商属于遗传决定论,情商属于环境决定论。最后,成功是一个综合学科的范畴,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解释。科学主义把成功理解为使用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人本主义把成功理解为满足人本身的生存利益或心理需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五种基本需求由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于需求层次的不同,成功的层次也就不同。实用主义把成功理解为有用,适应环境。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成功在于如何发挥人的潜能。现代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总结了十七条成功的法则,后来当代的潜能成功学大师安东尼奥·罗宾提出人人都有成功的潜能,就在于能否发现和开发这座金山;并提出成功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即想象成功、思考成功、相信成功、采取行动争取成功[19]。自我心像心理学的创始人马克斯威尔说:“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自我心像是个人精神上的观念,或者是他们的自我图像,是左右个性和行为的真正关键。”[20]综上所述,成功是一个包含主客观因素的范畴,实践沟通了主体的人与客体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内在统一了主体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两种观点。换言之,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下,人的成功主要由主体决定;而在不同的环境下,人的成功主要由客体制约所致。这个统一的基础是人的实践活动。
[1][2][3][4][8]冯友兰.新原人[M].北京: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周国平.人生圆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9]范鹏.论冯友兰的境界说[A].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C].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10][11][12][15]冯友兰.新原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3]肖群忠.伦理与传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余潇枫,张彦.人格之境—类伦理学引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16]季羡林.人生沉思录[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
[17]王海明.伦理学与人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8]李金水.成败不是偶然—决定人生成败的16件事[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5.
[19]安东尼奥·罗宾.激发无限的潜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0]马克斯威尔.你的潜能[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B261
A
1009-6566(2015)01-0121-04
2014-11-16
马光耀(1971—),男,甘肃天水人,中共天水市委党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