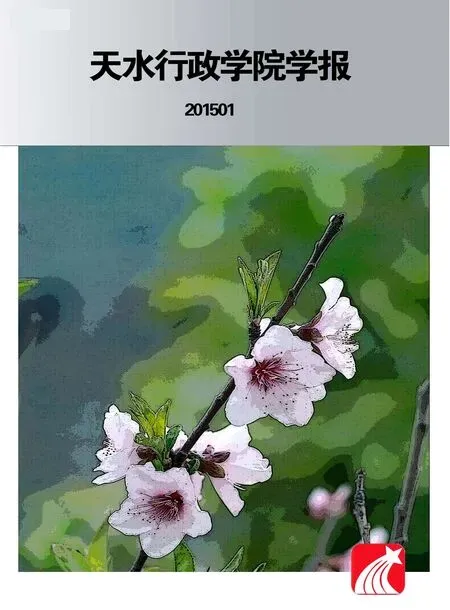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涵、特征与现实意义
李砚忠
(中共中央编译局战略发展研究部,北京100032)
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涵、特征与现实意义
李砚忠
(中共中央编译局战略发展研究部,北京100032)
“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交往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理论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存在着实践性与社会性、物质性与历史性、价值性与科学性原则等多向度性的统一。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表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交往过程中,既要体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又要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个体特色。正是在这个原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
交往;基本特征;现实意义
一、交往的概念与历史发生
(一)交往的概念界定
“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但是,对交往问题的研究并非始于马克思。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中就以“一个自我意识对另一个自我意识”[1]的方式把“交往”问题提了出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并反复提到“同别人的实际交往”,把“交往”视为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能力和成果的交换关系。马克思对“交往”问题的系统研究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七十多处使用了“交往”、“交往方式”、“交往关系”这类概念。
“交往”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劳动过程;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往”就是人与物、人与人双重关系的统一。它并不是静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动态地表现为主体间的互动,正是通过这种互动过程,人实现其在物质、能力、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交换和交流。在形形色色具体化了的“交往”活动中,有的侧重于物质层面,有的侧重于精神层面,不过,多数的交往活动是二者的合体。精神交往对物质交往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就其根源和两者作用的比较上,物质交往决定精神交往。“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其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环节。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活动中牵引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原理;又从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交往关系中牵引出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它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解决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他们能够具体而真实地解释生产与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形式的联系。
总之,从内涵来看,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给“交往”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根据马克思原初使用的意义域以及人作为一种能“思维”的情感动物的特性,我们可以把“交往”界定为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人们通过实物、信息及意义的传递和共享达到相互理解和彼此协调进而影响或改变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活动。从外延来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使用的“交往”含义则非常广泛,包括个人之间的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民族内部的交往和民族间的交往、普遍交往等等。
(二)交往的历史发生
人的存在和发展是一切历史当然也是生产和交往发展史的首要前提,而生产、交往对人的生存发展又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人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之必然发生的根由在于:个体创造能力和活动范围的有限性与其自身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历史环境中,单个个体且不说征服自然,即使凭借一己之力生存下去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生存的第一需要促使我们的祖先相互协作、共同团结起来。交往则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可以说,交往的最初形态就是在生存的压力下诞生出来的。因为交往主体无论选择何种活动,首先都要生产自己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人们首先必须从事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且这种生产活动是在活动者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中进行的。人的个体需求的无限性和自身力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依靠个体的人自身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只有借助于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换其活动和共同合作,才能满足个体自身不断发展的多重需要。离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个中介环节,任何改造外部自然界的生产活动都无法进行下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创造人类所需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从来就不纯粹是单个人的事情,只有在生产劳动中,个体才获得了社会性和各自特殊的规定性。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最初时期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催生了交往。
(三)交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交往是使个人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和重要途径。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以及与他人联系的需要,使人不仅必须了解、把握他人的信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且必须让他人了解自己的需要,以借助他人的活动来补充自身活动的不足和欠缺,与他人共同建构社会生活。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是人类社会的第一大进步,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没有人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没有相互之间力量和信息的传递,社会生产就不可能得以进行。
另一方面,从民族或地区而言,社会交往的不断拓展促使生产力的不断进步。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马克思并以腓尼基人和中世纪的玻璃绘画为例来说明。马克思还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后是在法兰德斯)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最好的例证就是:“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由此可见,“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度”。所以,交往的扩大,是生产扩大的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
生产力进步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分工的不断发展,发展了的生产力要求分工的不断进步,进而导致城乡之间的分离,“出现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2]。分工的专业化程度直接表征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3]。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分工的实现不仅仅是在一个部门内部,也不仅仅是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通过交往的发展,每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更好地了解到自身所独有的优势和所处的劣势,从而实现扬长避短。交往促进了分工的专业化发展,进而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进步。
(四)交往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
随着历史的进步,交往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得到强化。最初简单的协作不仅仅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并且还创造了些许的剩余生活资料,紧接着就“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4]。人们相互之间利益的不同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阶级”的产生。任何一个阶级都是从之前的家庭或利益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因为这可以“得天下之利”。“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5]。
出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个人利益的需要,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相互协调、相互让渡个人利益和权益,以社会契约的方式达成默契,从而建立国家。因为社会中的每个人不仅拥有属于自身独特的个人利益,同时又有着共同利益。在诸多问题上,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有时是矛盾的。不过,总的说来,这样的利益的冲突总是存在于一个小个体和其余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而且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问题上,某个矛盾中的小个体在别的矛盾中又处于跟别的大多数个体有着共同利益的大多数一方。“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而这种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6]。从古希腊的城邦到现代的民主国家,都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社会生活及国家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成为必须。
二、交往理论的基本特征
交往既是一种关系性范畴,也是一种活动性范畴。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存在着多向度性的统一。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统一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对交往现象考察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没有物质生产活动,交往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实践的基础形式,马克思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7]可见,生产和实践活动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同时“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交往也自然携带有这种“存在物”的社会属性。“社会交往过程其实是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过程,这种过程实质是人的本质之间的相互交换。”[8]在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实现着人的社会化,同时,也通过社会交往,人又不断实现着对原有的社会关系的改造,促进新的社会联系的产生。总之,社会交往的发展体现着人的社会化程度和社会性水平的发展,也意味着社会的一体化与相关性越来越强。
(二)物质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的统一
如果说实践原则和社会性原则的统一,为马克思考察交往现象奠定了正确的出发点,那么,由此出发点的深入,必然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物质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相统一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交往理论其物质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的统一主要表现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交往关系(物质交往),构成人类其他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基础;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交往方式,总是在生产力的不断推动下改变自身,从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因此,交往也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这种传承性表现为后代人既继承前人的生产力成果,也继承了前人的交往形式,当然对前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继承是建立在人们现实生活基础上的。人们现实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着前人积淀下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制约的。因此,交往和交往形式的发展是一种与人类历史发展同步的现象。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考察,无论是从经济形态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还是从人的发展形态即对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及个性自由的阶段亦或是从所有制关系出发的社会发展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考察和划分,其实质都与人们的交往形式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
(三)价值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统一
马克思交往理论所遵循的价值原则一方面是马克思对交往本身在价值运行中作用的考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原则还体现在马克思交往理论本身的价值取向上。众所周知,价值是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价值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及其扬弃。价值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生产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产生对象化和对象扬弃的价值运动。马克思说:“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在生产和消费中,交往起中介作用。对于人化自然物质价值来说,交往是价值的基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于对人们的交往活动的历史考察,通过交往形式的历史演变的审视,揭示了资本主义交往形式的历史暂时性,确立真正属人的交往形式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原则。因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归宿是人的本质的实现途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得以进行的方式方法。”[9]马克思交往理论所确立的价值原则是建立在其交往理论的科学性之上的。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在:第一,交往的主体首先是“现实中的个人”,而不是主观臆想的抽象的人或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第二,马克思交往理论所考察的社会交往现象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是感性的、具体的。第三,马克思交往理论把对人的考察放置到生产方式和交往活动的结构之中,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展现人的价值的发生发展过程,从人的价值发生的应然状态来把握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价值的应然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马克思“交往”范畴的多义性、交往形式的多样性和交往理论特征多向度的统一性,才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交往思想的理解出现歧义性和多样性。如在交往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就存在“雏形说”、“等同说”和“缺失说”[10];在“交往学转向”中,国内学者提出了“交往实践观”[11],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12]。如果说前者是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文本”的丰富性的话,那么,对“文本”理解的多样性就表征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价值意义的多元性,这恰恰从“外延”的角度再次表征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科学内涵的丰富性。
三、“交往”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当今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清朝末年,正是由于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才被帝国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而日本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的政治改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便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抓住机遇,走向遵循全球通则的“交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造就有利的国际环境。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表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交往过程中,既要体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又要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个体特色。正是在这个原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
随着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整体相关性越强,各个民族和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越应具有自己的“特色”。而对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贵的启示:民族特色是民族狭隘性的否定和超越,民族特色意味着一个民族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国情是特色形成的出发点,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看,一国国情既反映了一国在世界历史所处的地位,又反映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对该国的规定性,必须将它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的特定状况来把握。一国国情的形成离不开该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相互作用,一国特色的形成当然也离不开该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相互作用。因此,所谓“特色”,并不是离开世界历史整体联系的“特色”,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特色”,“特色”不等于孤立,不等于封闭。
人类文明史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与交往范围扩大同步的。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为发展社会的交往提供了变通工具和通讯条件,因而它能够不断地促进交往的发展;另一方面,交往的发展可能使本民族从其他民族之中获得先进的工具、工艺、管理方式、社会文化等。它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加速发展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越来越离不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只有在与世界各国的竞争中和交往中加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才能使自己不断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世界化。要使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当代世界的一切文明成果,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中国的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取决于中国加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水平和程度。
从当代的总格局看,在现代开放的世界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性质上对立的社会制度。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由于各自的利益和特点,必须相互开放,同时,在这种相互开放中又存在着冲突和对抗,这就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奇特矛盾,即社会主义必须向世界开放和在开放中如何不丧失“自我”。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因此,在向世界的开放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足点正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任何一条促动它发展的思想理论,一旦忽视了它的特殊性,都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历史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破产,新民主义道路的成功,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社会主义模式化建设的失误,是这一结论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验证。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他提醒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4]。以后他又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让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5],“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16]。这些精辟的论断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在实践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勇于创新,大胆探索,不断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总之,随着世界普遍交往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必须把立足中国与面向世界结合起来,既保持中国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要实行对外开放,又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世界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历史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未来同世界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只有在世界交往这个大背景中、在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检验中,才能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1.
[2[3][4][5][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艾福成.马克思社会哲学的当代阐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59.
[9]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3.
[10]姚纪纲.交往的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40.
[11]郑召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12][13][14][15][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The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about the Marxist Communication Theory
LI Yan-zhong
(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PC,Beijing 100032,China)
s: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it contains two dimensions:one is the exchange to occur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namely the labor process;another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Communication can promote the process on the mankind social civilization,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Communication theory exists the unified dimension of the practice and social nature,substance and historical nature,value and scientific principles.The marxist communication theory can indicat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world,but als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n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orld.The The CPC can put forward the great theory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this principle.
communication;basic characteristics;practical significance
A81
A
1009-6566(2015)01-0112-05
中共中央编译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灾害应对、风险分担与政府治理现代化”(项目编号:14C11)。
2014-12-28
李砚忠(1980—),男,山东潍坊人,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战略发展研究部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