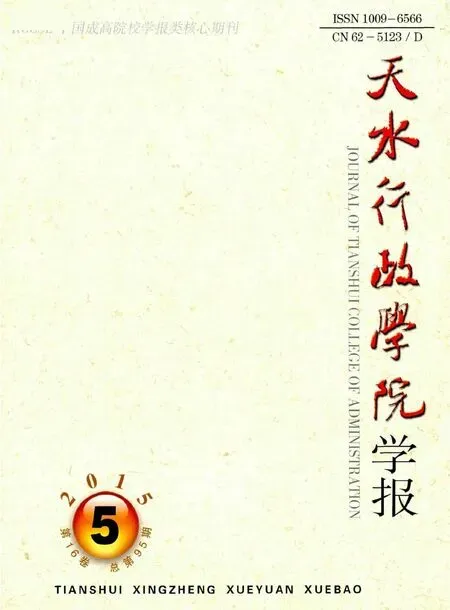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性质
陶奕安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性质
陶奕安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随着网络平台的不断发展,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造成的社会危害再次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中。2013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解释中的规定存在与刑法原理不相吻合、可能导致实践操作障碍等不足之处。实质上,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是可以用《刑法》中的其他罪名或者其他法律来规制的,最新公布的《刑法修正案(九)》中也将部分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纳入到刑事处罚的范畴,因此把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一律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是不合理的。
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性质
一、“虚假信息”的界定
(一)何为“虚假信息”
赵秉志教授认为,“虚假信息,是指不真实的信息,既包括虚构的不存在的信息,也包括对真实信息篡改、加工、隐瞒之后的信息。虚假信息一般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1]张明楷教授认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的“编造行为不仅包括完全凭空捏造的行为,而且包括对某些信息进行加工、修改的行为”[2]。笔者赞同以上学者对“虚假信息”的界定,“虚假信息”不仅包括虚构的不存在的信息,也包括对真实信息篡改、加工、隐瞒之后的信息。我国虽未规定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实质上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和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行为是同质的行为,只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内容不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中的“虚假信息”包含的内容更广,而其他两种行为只限于虚假恐怖信息和虚假证券、期货交易信息。由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和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中的“虚假信息”都是既包括虚构的不存在的信息,也包括对真实信息篡改、加工、隐瞒之后的信息。所以,根据刑法体系解释的要求,《解释》中的“虚假信息”应与《刑法》中的“虚假信息”保持一致,如果对其进行限制解释,则会造成刑法体系上的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虚假信息”中包括对真实信息篡改、加工、隐瞒之后的信息,但这里的对真实信息的篡改、加工、隐瞒必须是严重的篡改、加工、隐瞒,如果仅仅是对真实信息进行轻微的篡改、加工、隐瞒,就不属于编造虚假信息的行为,可以使用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出罪。比如,浙江上虞发生车祸,7人死亡,次日冯某在当地论坛发帖称“死亡9人”。这种情况就不属于编造虚假信息的行为,因为这种轻微的修改不会对一般公民对于这一信息的认识产生较大影响,社会危害性较小。如果本案中冯某发帖称死亡100人或更多,那么这种远远与真实情况不相吻合的篡改显然属于编造虚假信息。
(二)“谣言”与“虚假信息”
有学者认为,“谣言”和“虚假信息”在概念上是存在差异的,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而“虚假信息”是指与事实不符合的信息,这种信息既有可能有事实根据,也有可能没有事实根据。该学者认为“虚假信息”应做限制解释,仅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对于那些有事实根据但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的信息不应认定为虚假信息。对于这一观点,笔者并不认同。
事实上,在理论界,对于“谣言”一词该如何定义也存在着很多争议。有学者认为,“凡是谣言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凡是真实的或有事实根据的都不能称之为谣言。”[3]也有学者认为,“谣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有自发产生的,有人为制造的,但大多与一定的事实背景相联系。”[4]还有学者认为,“谣言就是真实的”[5],“谣言应该是中性词,谣言的确也可能事后被证明为真实陈述,是‘真实的谣言’。”[6]可见,“谣言”一词如何界定尚且存在诸多争议,该学者仅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上一个语言学上的定义就将其与我国刑法规范上的“虚假信息”相比较,显然不具有合理性。
“谣言”与“虚假信息”实际上并无差别。
首先,谣言有可能没有事实根据,完全是他人捏造的,但谣言也可能有事实根据,只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失真了。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往往经过多个个体的连续复述”[7]。当人们接收到某些信息时,由于对事物认识的偏差,也可能是记忆的出入,容易造成对信息的歪曲认识和理解,然后再将歪曲认识的信息传递出去,这样信息会越传越走样,最终可能造成有事实根据的消息却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甚至差别很大的情况,即“失真”的产生。
其次,谣言不是没有事实来源,而是来源不确定。谣言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谣言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来源不确定、事实不确定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谣言并非必然就是虚假捏造的谎言,而是在谣言传播之时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8],不是在谣言传播之初没有事实依据。“谣言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它包含了真实的事实碎片”[9]。
再次,谣言是只可描述,而不可定义的。谣言是生活用语,从一般人的理解上来看,“谣言”和“虚假信息”都是指不真实的信息,二者的含义是一样的。在这个网络谣言盛行,打击网络谣言行动此起彼伏的网络大环境下,一般公民对谣言的理解就是指不真实的信息,而不会去关注这个信息是否有事实根据。不管是新闻媒体的报道还是相关学者的文章,显然都是把“谣言”和“虚假信息”作为同一种概念来谈的。
最后,谣言的本质属性是虚假信息,也就是说不论是来源还是传播手段或者是传播渠道,都不是谣言最重要的要素,谣言最核心的要素只有一个——虚假信息。
二、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解释》中第五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可以看出,该《网络诽谤解释》将网络空间中的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以及编造虚假信息散布的行为纳入到《刑法》中寻衅滋事罪的第一款的二、四项之中,即“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和“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但是,笔者认为,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并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一)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并不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这就涉及到对“网络空间”和“公共场所”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区分问题。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公共场所”概念做符合信息社会变化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互联网各类网站、主页、留言板等网络空间具有“公共场所”属性[10]。还有学者认为,公共场所,是指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11]。网络空间不是虚构的,其与现实生活存在密切联系,但网络空间不是公共场所,它与三维空间存在一定区别[12]。在强调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相互影响,已经融为一体的同时,也应该承认二者存在显著差别,直接将“网络空间”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是不妥当的。
首先,对照《刑法》的全文,无法得出寻衅滋事罪的“公共场所”包括“网络空间”这一结论。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的四种情形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行为人在现实的空间,通过书面表达以外的形式,实施了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并且,二百九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的”中的“起哄闹事”,是指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目的,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法条中的“造成公共场所严重混乱”,则是指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受到破坏,引起群众惊慌、逃离等混乱局面。可见,该项规定中的“起哄闹事”,显然是一种发生在现实空间中的行为,并不包括网络上的表达行为。该项规定的“公共场所”,也必须是现实的空间,不包括虚拟的网络空间。如果把“公共场所”扩张到包括网络在内,显然超出了法条的文义,因而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按照体系解释的要求,解释者在解释一个刑法条文时,必须根据该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体系解释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在于避免断章取义、避免自相矛盾,以便刑法整体协调。”[13]我国《刑法》中有多个罪名均以“公共场所”作为构成要件要素或者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如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聚众斗殴罪等,上述犯罪中的“公共场所”皆是现实的物理性空间,不包括虚拟空间。举例来说,《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规定:“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可见,该条明确规定了“公共场所”的范围。虽然法条中有“其他公共场所”的表述,但是,这里的“其他公共场所”也应该限定为与法条列举的对象性质相同的现实领域的公共场所,并不包括网络空间。相反,如果认为刑法条文中的“公共场所”包括虚拟空间,会对整个刑法体系产生影响,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刑法》第一百三十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规定:“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或者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危及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如果说这里的“公共场所”包括“网络空间”,那么网络游戏就会涉嫌该罪了。有人可能会反驳,称这里的枪支、弹药等是指实际的武器,那么,既然“公共场所”可以包括虚拟空间,“枪支”、“弹药”等为何不能包括“虚拟武器”呢?因此,根据体系解释的要求,为了保证刑法用语含义的一致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中的“公共场所”并不包括“网络空间”。否则,必然导致解释的恣意性与刑法各条文之间的不协调。
其次,没有一部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把“网络空间”规定为“公共场所”。2013年颁布的《寻衅滋事解释》第五条采取列举的方式已经对“公共场所”的含义予以明确:“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在该条所列举的范围内,并未就互联网做出单独规定。即使“其他公共场所”也应该是与前边所列举的场所是同一类型的。前面所列举的类型均是实体空间,而不是虚拟空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真想突破“公共场所”的原有文义,把虚拟的网络世界也包括在内,那么它们一定会明确表明这一点,而不会故意把这么重要的问题留给人们去猜测。所以,“公共场所”应指实体空间,并不包括网络这样的虚拟空间。再如《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也采取列举的方式,对“公共场所”进行界定:“本条例适用于下列公共场所:(一)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二)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三)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四)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五)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六)商场(店)、书店;(七)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该条例对“公共场所”的界定比《寻衅滋事解释》所界定的范围宽一些,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所列举的公共场所都属于线下、实体的场所,都没有涉及到网络空间。
再次,从“公共场所”本身的词义上来看,其也不包括“网络空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公共场所是指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活动的处所。这一定义揭示出公共场所最基本的特征:公有公用性,是指公共场所对外开放,允许公众自由地进出。这一特征将那些封闭的、半封闭的地方排除在公共场所之外。然而,网络空间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网络空间其实并不都是对外开放的空间,还有隐秘空间,当交际的网民数量少而沟通的内容具有特定性、沟通的方式具有隐密性时,其交往空间就具有特定性、私密性,很难说是在公共场所进行沟通联络[14]。如微信就是朋友之间的即时通信工具,即使是具有公开转发功能的“朋友圈”,也只是限于私人之间的非开放圈子[15]。再如在新浪微博中,“粉丝”越多,则表明发表的微博可能会被越多人看到。如果“粉丝”很少,则其发表的内容就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并且,每个网民即使同时登录、使用同一网站,互相之间也处于一个看不见、听不到的隐秘空间[16]。并且,公共场所是允许公众自由进出的,这里的“自由出入”并不是指言论的自由出入,而是指身体的自由出入[17]。公众虽然可以在网络空间发表言论,但其身体不可能进人网络空间。如果说网络是“公共场所”,那么报纸、电视等传媒是不是公共场所?因为不特定的人都可以在报纸或电视等传媒上发表言论。那么将来是不是作者写文章、嘉宾上节目都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最后,将网络纳入“公共场所”的考量范围,是对现行法律的一个突破。不仅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也突破了法制底线。这种突破值得所有人警惕,它意味着1997年刑法中明确禁止的“类推”死灰复燃。互联网是现实社会在网络上的延伸,但是其在人们的观念中只是一个信息平台,将互联网解释为公共场所,明显超出了“一般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二)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并不会直接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网络诽谤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而《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中规定的是:“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显然,司法解释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场所”的实体性对于定罪的影响,将“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改为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但是,“公共秩序”与“公共场所秩序”并不是一回事。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公共秩序”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依据共同生活规则而有条不紊进行的状态,既包括公共场所的秩序,也包括非公共场所人们遵守公共生活规则所形成的秩序[18]。然而,“公共秩序”仍然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概念。只要进入公共领域的事务都存在一个公共秩序问题。譬如,宏观的秩序可以包括法律秩序、环境秩序、公共安全秩序,等等;具体的秩序可以包括公共场所秩序、特种器材生产秩序、无线电管理秩序,等等[19]。可见,“公共秩序”既包括公共场所的秩序,也包括非公共场所人们遵守公共生活规则所形成的秩序。“公共场所秩序”是“公共秩序”的一部分,“公共秩序”属于“公共场所秩序”的上位概念,二者并不等同。那么,寻衅滋事罪所侵犯的法益究竟是“公共秩序”还是“公共场所秩序”呢?张明楷老师认为:“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旨在保护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但是,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满足于将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概括为公共秩序或者社会秩序,不仅不利于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有损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因为分则条文都是为了保护具体的法益,而非保护抽象的法益;对保护法益的抽象程度越高,其所包含的内容就越宽泛,受刑罚处罚的范围就越广,从而具有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解释为犯罪的危险。换言之,保护法益的抽象化,必然导致对构成要件的解释缺乏实质的限制,从而使构成要件丧失应有的机能;导致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也被认为侵犯了过于抽象的法益,进而以犯罪论处。”[20]“公共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不应当作为寻衅滋事罪所侵犯的法益,否则会造成入罪范围的扩大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所以应根据寻衅滋事罪的具体类型确定其具体的保护法益。就“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类型而言,联系“破坏社会秩序”的规定,其保护法益显然是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在公共场所从事自由活动的安全与顺利[21],即现实中的“公共场所秩序”。
可见,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如前所述,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所保护的法益是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在公共场所从事自由活动的安全与顺利。刑法之所以规定起哄闹事型的寻衅滋事罪,是因为公共场所往往人员密集,而起哄闹事的语言和行为会直接地、即时地造成公共场所的现场混乱和失控,会直接对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人身安全产生威胁。而对于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它只是一种以信息网络为媒介的言论,其直接后果是引发虚拟网络世界的数据变化,继而也可能在受众的思想中,引发观念的变化,舆论的偏向。由于存在着空间上的距离,它并不会直接对公共场所的现场混乱、现场失控等秩序损害产生紧迫性,也不会直接威胁到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其危害性难以与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等同视之。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一样,会侵害社会秩序与公共秩序,也会侵犯一些其他的法益,如名誉权、商誉权等,但正如笔者之前所述,这里的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过于抽象,“在确定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时,应当以该罪在刑法典中的顺序与地位、刑法的旨趣、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为根据。但与此同时,必须考虑在判断犯罪的成立与否时,能否根据确定的保护法益,对具体案件得出妥当的结论。”[22]由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并未入罪,所以无法确定其具体侵犯了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下的哪一种具体秩序,但可以肯定的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侵犯了某种秩序,但这种秩序不一定是公共场所秩序,就算其确实是影响了现实中公共场所的秩序,但这种影响也仅仅是间接影响,其社会危害性远不及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社会危害性。并且,现实空间的行为产生现实的危害后果,其因果关系相对容易确定。但网络上的言论产生现实空间的危害后果,其因果关系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因为它具有间接性、转换性、随机性、多样性等特点[23]。如果不能确定因果关系,也就没有办法认定犯罪了。
三、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定性
事实上,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是可以用《刑法》中的其他罪名或者其他法律来规制的。
我国早就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惩治包括网络谣言在内的网络违法犯罪。2000年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就对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违法犯罪如何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作了系统规定,并对政府有关部门、网络经营主体及社会公众在维护网络安全上的责任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根据刑法和《决定》的有关规定,对利用网络造谣传谣,并对他人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造成特定程度损害的,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利用互联网造谣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可以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和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对于在网络上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以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对于利用网络编造或者故意传播虚假的恐怖信息,危害公共安全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对于利用互联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损坏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信誉罪定罪处罚;对于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定罪处罚;对于成立网络公司,专门以造谣传谣谋取非法利益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对于利用互联网进行敲诈勒索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此外,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可以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在民事法律方面,《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了名誉侵权:“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还规定了通知删除规则:“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在行政法律方面,主要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如果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或者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尚不构成犯罪的,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给予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也规定,通过互联网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谣言的,依法予以处罚。
可能有人会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不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行为方式呈现出新的类型,“虚假信息”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上述法律的规定并不能完全涵盖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笔者并不否认这点,上述罪名中确实存在对虚假信息的内容规定过窄的情况,无法解决实践当中产生的新问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立法适当扩充某些罪名中“虚假信息”的内容或者直接制定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来解决问题,而不能随意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当然,对于设立新罪,应严格界定其犯罪构成,避免其成为无所不包的口袋罪。其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已经对上述这一问题进行了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险情、疫情、警情、灾情信息的行为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畴中,这一规定在当下确实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经过分析可以看出,“险情、疫情、警情、灾情”实质上均可为虚假恐怖信息所部分涵盖。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法定刑要高于编造、传播虚假险情、疫情、警情、灾情信息,按照从重处断原则,容易造成编造、传播虚假险情、疫情、警情、灾情信息的部分虚置。笔者认为,如果选择通过立法适当扩充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虚假信息”的内容,那么和修正案九相比,这一“虚假信息”的内涵仍有待于进一步适当扩充,应将更多扰乱社会稳定、造成社会大众心理恐慌的虚假信息都包含在内[24],这样才能解决实践中的众多问题。
[1]赵秉志,徐文文.论我国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刑法规制[J].当代法学,2014,(5).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932.
[3]江万秀等.谣言透视[M].北京:中国群众出版社,1991.17.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9.
[5]胡泳.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9).
[6]周裕琼.谣言一定是洪水猛兽吗?——基于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09,(8).
[7]游雅.谣言的再定义——从一则网络谣言谈起[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10,(4).
[8][9]李大勇.谣言、言论自由与法律规制[J].法学,2014,(1).
[10]曲新久.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N].法制日报,2013-9-12(7).
[11][20][21][22]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上篇)[J].政治与法律,2008,(1).
[12]张明楷.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以刑法的谦抑性为中心[J].人民检察,2014,(9).
[13]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83.
[14][16]曾粤兴.网络寻衅滋事的理解与适用[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报,2014,(2).
[15]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以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的发布为背景[J].法学,2013,(10).
[17]张明楷.简评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解释[J].清华法学,2014,(8).
[18]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808.
[19]孙万怀,卢恒飞.刑法应该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造谣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J].法学,2013,(11).
[23]马长山.法律的空间“穿越”及其风险——从两高办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出发[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4).
[24]赵秉志,徐文文.论我国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刑法规制[J].当代法学,2014,(5).
D924.3
A
1009-6566(2015)05-0087-06
2015-07-11
陶奕安(1990—),女,甘肃白银人,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