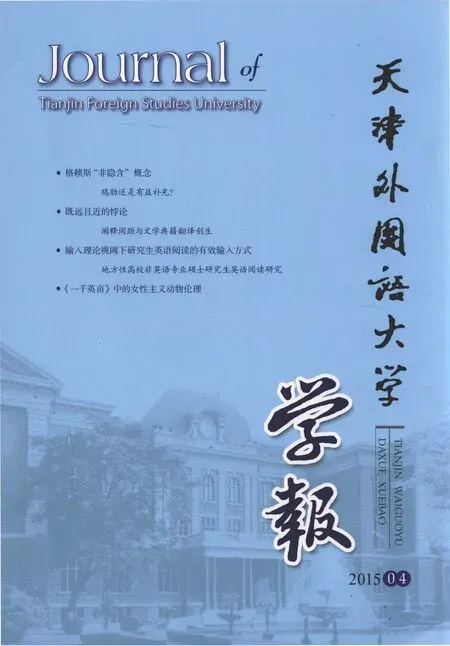既远且近的悖论——阐释间距与文学典籍翻译创生
刘晓晖
(大连外国语大学 应用英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化转向思潮使文学典籍翻译研究蓬勃发展,呈现出学科多元交叉之态势。忠实原文、回溯原意、作者至上、语言对等等传统研究取向终被打破,“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阐释学话题也在新时代视角的审视之下得以绽放异彩。由此文学典籍翻译的创生性问题引发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对于文学典籍翻译的创生性,不难从转世重生、借尸还魂、转世美人等主张中获得一些启示。而这些主张大都只回答了为何可能的问题,而对何以可能的问题却罕有见地。笔者认为,阐释间距的存在是解密文学典籍翻译创生为何可能和何以可能的关键因素。
翻译中的间距无处不在,这可在钱钟书先生(2009:775)那里得到有力的印证:“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钱先生所说的文字与文字之间、原作品与译者之间、译者与自身表达力之间的距离用阐释学术语来表述就是间距。文学典籍翻译中的间距更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文学典籍来自遥远的过去,跟当下译者之间的距离无论从时空还是语言文化而言,都可以用远在天边来形容;而另一方面,语言将文学典籍带到了当下译者的面前,又使其近在眼前,为译者提供了近距阐释和创生的契机。因此,对于文学典籍译者而言,翻译其实就是一种在历史的远距与当下的近距之间不断权衡最终实现创生文本的过程。不同译者的权衡方式会产生相异的译作文本,文学典籍的生命也会因此得以无限延续。文学典籍翻译中这种既远且近的间距悖论为文学典籍翻译研究提供了参考。本研究即以此为出发点,以伽达默尔的时间间距理论为主要依据,解析文学典籍翻译创生的潜在性和可行性,也即回答上述有关文学典籍创生的两大问题,以期为文学典籍翻译研究提供些许启示。
二、阐释间距与翻译创生
间距概念在阐释学领域由来已久,最初指的是久远的历史文本由于在当下的时代变得陌生难懂而成为疏远的流传物。随着阐释学的发展,间距的内涵日益丰富,对间距的理解呈多样态势,出现了心理间距、文化间距、语言间距、时间间距等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就是以间距为前提,狄尔泰心理移情的出发点是主体的心理间距。利科尔和伽达默尔对间距的阐述更为系统化,虽然二者各有侧重和偏颇之处。利科尔(1987:162)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一书中论述了间距化的问题,提出了本文的概念,即“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在他看来,话语的固定就意味着间距化,“表明了意义超越事件以及所表达的意义与言谈主体的分离……本文因脱离了作者而获得了自主性”,因此,“本文的世界是由读者的世界而表现出来的”(裘姬新,2009:16)。利科尔否定了作者的意图,而把文本完全开放在阐释者面前,增加了阐释的自由度。伽达默尔的间距理念与科利尔的观点判若云泥,着重强调了间距的功能和作用。他对时间间距的阐述发人深省,进一步拓展和凸显了阐释的创生功能。根据伽达默尔的时间间距理论,在阐释者与流传物之间及历史与当下之间形成了一种两极对立的间距,而这种对立性的间距正是创生之渠,充盈着意义的无限可能,是生命的缔造域。在伽达默尔看来,时间是间距形成的基本条件,时间将主客体之间疏远化或是异化。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既属于过去又存在于当下。由于来自历史,流传物对当下的阐释者而言具有陌生性,而语言的书写功能又让它在当下的语境中得以留存,使阐释者可见、可触、可考,具有一定的熟悉性。因此,间距就成了陌生性和熟悉性两极之间的重要联接,成为伽达默尔所说的历史与当下的中介。由此可见,伽达默尔间距概念的核心是时间间距,“一切解释首先是发生在时间之中的,理解其实是在时间过程中的理解,即在时间过程中对那些对理解造成阻碍的前见的区分的过程”(犹家仲,2004:29)。但是伽达默尔的时间观念不是单纯指机械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它借鉴了海德格尔时间性的概念,将空间性也纳入了间距思想当中,强调了“存在的时间、空间的同一性”(同上)。可见历史与当下之间、流传文本与阐释者之间也存在空间间距。空间的延展性为多元阐释提供了契机,同时也解构了权威论、绝对判断、原意为本等一元性论断。意义的创生是时间性和空间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时空的共同联接当然也包含了心理间距、文化间距、语言间距等相关内涵。
阐释学的间距概念,尤其是伽达默尔的时间间距思想,让我们看到了翻译创生的潜在性和可操作性,为文学典籍翻译为何可能和何以可能的诘问提供了参考。翻译需要考察时间与空间涉及的若干元素,如源语文本的历史性、时代性、文化性、译者的当下性、前见等。这些因素相互碰撞而产生的间距都会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一一呈现。如果译者能够妥当处理传统与当下、源语文本与译者、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等的间距问题,翻译就会产生相对满意的创生效果。如同阐释的前提是间距的存在一样,翻译的前提也是以间距为条件。但有别于传统阐释学的是,伽达默尔的间距理念强调的不是狄尔泰宣称的跨越鸿沟,或是简单的填沟平渠,而是利用这种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不断创生,翻译的操作范式也应如此。如果鸿沟被填平,源语文本的意义就会被永久固化,从而陷入一元论的误区,也就宣告了源语文本的死亡。事实上,间距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差异性,也意味着真正意义的不可企及。正因如此源语文本的创生才会不断持续下去。“对一文本或艺术品真正意义的发现是没有止境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不仅新的误解被不断克服,而使真理以从遮蔽它的那些事件中敞亮,而且新的理解也不断涌现,并揭示出全新的意义。”(伽达默尔,1999:382)文字的意义往往具有多指性,可以衍生出多种指向,可以从一种意义创生成另一种意义,这种动态的变化无时不为,新的意义也会随时产生并固化。因此,此在的译者总会以当下的眼光从看似远在天边的文学典籍中领悟出新的内涵并增添新的生命力。文学典籍所负载的远的元素虽然貌似制造了诸多鸿沟,让意义变得深不可测,但伽达默尔让我们意识到远并非不可逾越的绊脚石,相反却蕴含着更多的创生可能。
三、远在天边的文学典籍与翻译创生的潜在性
文学典籍翻译的历时性决定了历史间距的存在,也就意味着翻译必须在历史的维度中创生,其核心使命就是开拓典籍文本的生存和生长语境,使中国的文学精髓跨越疆域,在异域中扎根并流传。从表面上看,文学典籍的译者似乎与典籍文本间遥不可及,远古的文本与此在的译者间的时空间距为文本的阐释设置了巨大的鸿沟。译者似乎总在历史长河的对岸反复揣摩典籍的内外特质。文学典籍不仅在时间上离译者很远,而且在诸多方面都看似欲将译者拒之千里。
比起非文学典籍翻译,文学典籍翻译涉及到更多的介入因素,但最关键的是如何阐释和再现它的文学性的问题。文学性彰显了中国文化独有的艺术内涵,很多典籍经过历史传统的过滤和磨砺实现了经典化,被烙刻上了独特的艺术创造和文化差异的标签。如盛行于南北朝的骈文就尤其讲究对仗的工整和谐及声律的铿锵有力,在声韵方面注重平仄的运用,在修辞上则强调藻饰和用典,加上大量利用同形旁字,创造了联想丰富、节奏明快、抑扬顿挫、颇富艺术美感的卷帙。除了带有古汉语的特性外,中国文学典籍偏抒情轻叙事,重写意而淡写实,总体侧重表现。例如,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中虽不见描写幽州古台的字眼,但寥寥四行诗句却宣泄了诗人内心无比的惆怅与失落。诗人寓情于景,感喟人生苦短,抒发了不及见来者的悲怆之情,堪称千古绝唱。《唐诗快》曾大赞道:“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用苏珊·朗格(1986:300)的话来说“是一次情感的风暴,一次情绪的紧张感受”。中国文学典籍中远的因素还可见于宗白华(2009:118)所说的那种既淡又幻、“非无非有”的模糊美之中。模糊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至高追求之一。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及“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等都是对此种境界的捧赞。“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曲江》第二首),“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暮江吟》)等绝妙佳句都是老子所说的“神而不知”(《老子》)的妙笔。中国文学典籍中还蕴含着独到的想象因子。黑格尔(1997:357)曾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中国文学典籍中处处可见这样的艺术本领。中国志怪经典《聊斋志异》的想象性就可见一斑,有时空无界、上天入地、前世来生的穿越,有花化仙、人变鬼、鬼还魂的离奇变身,也有阴阳两隔的爱情或是仙凡之间的佳话等。文学典籍中倡导的道、气、玄、虚、阴阳、太极、天人合一等思想无不博大精深,深奥悠远,进行翻译转换时难免困难重重。
很多人可能会把这种远的特性等同于不可译性,因为这些独特的中国风着实设置了层层障碍。远是文本的历史性使然,而因为远而望而却步的译者实际上是被传统的忠实观念禁锢所致。虽然译者的责任和使命决定翻译应该忠于源语文本的文学性,但翻译的应然与实然往往充满了矛盾与冲突。译者越想原汁原味,就越会发现真正的忠实只是理想罢了。传统观念中理想的翻译是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但在伽达默尔看来只是个主观愿望而已,绝对的意义是不存在的。理想的翻译不是追求一种整齐划一,也不是一种静态的反思,更不是对历史原貌或者作者本意的一种单向还原,而是此在的阐释者在历史的前见和自身的前见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富有新的生命力的文本。“人所需要的不单单是坚定不移地追求终极问题,而是还需要知道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正确的。”(伽达默尔,1999:48)因此,远其实蕴含了丰富的翻译创生元素。唐宋诗歌的模糊之美、志怪小说的想象空间、古代儒释道哲学的博大幽深等都体现了远的不可穷尽的特质。这一方面否定了原意还原论,另一方面也为当下近距离的翻译创生提供了无限可能,译者的此在性正是创生的关键。中国文学典籍之所以能如此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每每流传到一个历史阶段都会跟当下的阐释者进行对话,寻求新生。远古的文本意义和价值是在间距中不断被当前化才得以流传。在进行文学典籍翻译时,为了传达对文本的理解,译者不仅会改变源语文本的语言模式,而且受前见的影响,对原意也会作出相应的改变。正如伽达默尔(1999:382)所说:“每个翻译者的任务就不只是重新给出他翻译的那位讨论对手所真正说过的东西,而是必须用一种在他看来对于目前谈话实际情况似乎是必要的方式去表现个人的意见。”文学文本中看似千头万绪的远的特质造就了理解的开放式,为翻译提供了创生的源泉。通过与文学典籍的近距离对话,当下的译者会创生出截然不同的译作文本,从而实现文学典籍生命的延续。
四、近在眼前的文学典籍与翻译创生的可行性
文学典籍的远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而近则提供了熟悉化的可能。承载着悠久传统底蕴的文学典籍借助语言的书写和传播功能在当下近在眼前,可以跟译者近距离展开对话。流传物的近包含了丰富的内涵,除了物理距离上的可观可感之外,近更多地意味着与译者在当下环境中心灵上的互动。走进当下时代的流传物避免不了要入乡随俗,必然要经历古今碰撞、协商、融合直至再生的过程。任何文学典籍的流传都无法回避过去和现代的交融。“在文字传承物中具有一种独特的过去与现代并存的形式,一切历史文本对于他的解释者来说都是同时代的。”(伽达默尔,1999:394)近在眼前的文学典籍如果想保持生机,就必须面临此在的译者以当下的观念和认知等进行新一轮的定位和阐释,同时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被同时代化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生命的无限延续,文学典籍既远且近的悖论即在于此。远是因为它的精髓和蕴涵遥不可及,朦胧幻化,好比王国维所说的隔,因而难达百分之百的忠实;近则在于它不仅流传于当下,而且因意义的无极限而向此在的译者无限敞开,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从而为新译本的不断诞生创造了条件。因此,每一份译文的诞生虽然不是完全的脱胎换骨,但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焕然一新。当然任何一个文学典籍的文本意义都不可能在一个时空中显露无疑,每一个时空只不过揭开了部分面纱,如伽达默尔(1999:386)所说:“对一个本文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
对于近在眼前的文学典籍,翻译创生又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呢?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答案。他将视域定义为“视力所及的区域,它囊括了理解者在开始理解之前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1999:265)。译者视域的形成既归因于个性化因素,也涉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包含当下传统、文化观念、审美修养、价值取向、认知结构、理想追求等。这些因素往往会深入骨髓,形成前见,在译者与源语文本近距离对话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时间间距的存在注定译者与源语文本之间必然存在视域差异。源语文本视域中所包含的语言特色、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历史文化和传统价值等很可能与译者的视域大为不同,而译者往往会从自己所经历和认可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和审美形态出发来与源语文本积极对话,并寻求一种翻译的路径。“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流传下来的本文……当某个本文对(使)理解者产生兴趣时,该本文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同上:380)目的语文本的生成过程也就是译者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需要不断协商,直至达成圆融,即视域融合的过程。译者首先会带着自己的视域进入典籍文本,在理解的过程中向源语文本发问,文本在作出回应的同时也向译者提问,在这种交流中译者会根据自己的视域作出价值和理解判断,经过深思权衡之后与源语文本形成视域融合。视域融合的结果是产生创生文本,从而为源语典籍文本增殖新意。因为翻译是跨语言的操作,从视域融合到翻译文本的生成要经历更为复杂的过程。朱建平(2006:74)就曾谈及翻译活动会出现两次视域融合,“先是译者视域与原作视域的融合,再是第一次融合后形成的新视域与目的语文化视域的融合”。但这种融合不是一对一的完整对等,视域之间毕竟存在间距,这也是创生能够持续不断的奥秘所在。
视域融合为近距离的翻译创生提供了必然条件,也回答了创生何以可能甚至是无限可能的问题。不同时代的译者,包括同代的译者,由于视域的差异往往拥有不同的翻译目的和需求,并在翻译过程中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从而对近在眼前的文本创造出各有千秋的译文,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就拿李白的《送友人》来说,中外十多位译者进行了英译,其中很多都是著作等身的翻译名家或诗人,如翟理斯、宾纳、庞德、韦利、小畑熏良、杨宪益、许渊冲等。他们来自于20世纪的不同年代,经历了不同的境遇,处于不同的审美境界,拥有不同的艺术追求。当他们与流传至他们所处当下的源语文本进行对话的时候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效应,创造的译文可用各尽其才、各显所需、各有侧重、各有创造来形容。20世纪初意象大师庞德翻译《送友人》时,美国诗歌界正面临改革的困境,而身为改革先锋的庞德从中国古诗中发现了灵感和希望。中国古诗意象丰盈,词简意浓,婉约含蓄,这些特点正好迎合了他探索新诗的方向。庞德在与原诗的近距离对话中把个人视域中的诗学理想和时代诉求放在了首位,也正是这样的视域造就了庞德式创造性误译的翻译特色。在翻译该诗的过程中他将原诗中符合新诗理想的特质进行了创造性改写,打造了与原文等效的艺术特色,利用浮云、落日、马鸣、挥手等意象凸显了惜别的愁绪。虽然庞德的翻译将原诗中的对仗、押韵及“东城”、“游子”等言辞舍弃,造成了严重的漏译现象,但他所创造的丰盈的意象和含蓄的意蕴为美国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引发了轰动效应。与庞德不同,对李白研究细致入微的许渊冲追求的是一种圆融的翻译效果。许老博古通今,横贯中西,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美学思想。他的译文追求中西合璧,既颂古风又传西韵,并将美作为翻译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与原文近距离对话的过程中,许老个人视域中的上述因素对他对诗歌的阐释和创生起到了关键作用。许译《送友人》大大不同于庞德和小畑熏良等倡导的散体意译风格,而是精于雕琢。尾韵(ababacac)既塑造了韵律美,又体现了古诗的典雅,颈联借助反复修辞法创造性地译为Like floating cloud you’d float away;/With parting day I’ll part from you(许渊冲,1995 :73),生动再现了原诗的对仗效果。他还将“孤蓬”创译为lonely thistledown,并未按常规选择英文对 应 词 bitter fleabane或 tumble-weed。thistle指蓟,素有苏格兰之花的美称,是勇敢的象征,许老借用此花与下文的“万里征”形成关联,表现出友人就要四处漂泊,勇闯天涯的深刻内涵。中国文学典籍浩如烟海,这种近距翻译创生产生的相异效应的例子不胜枚举,比比皆是。每个译者都对原意进行了一番探寻,但如冯友兰(1996:13)所说:“无论译得多好,译本也一定比原本贫乏”,因为原意是不可穷尽的。
五、结语
文学典籍文本的意义永远都是难以名状的,司空图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周易·系辞》中的“言不尽意”以及《庄子·外物》中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等都证明了文学文本中间距的存在。这种间距的存在不是障碍或是沟壑,而是绵延不息、繁衍生息的水渠,为文学典籍的译者提供了意义阐释的创生域。间距中流淌的涓涓细流孕育着翻译创生的无限可能,看似远在天边的中华文学典籍进入当下的视域就会近在眼前,并在不同的阐释中焕发异彩,从而实现文本生命的无限延展。正如季羡林(1997)所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保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中华文化精髓将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译者在既远且近的间距中不断创生而走向世界,发扬光大。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4] 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5] 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6] 季羡林.中国翻译词典序[A].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7]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8] 裘姬新.从独白走向对话——哲学诠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9] 许渊冲.唐诗宋词一百五十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0] 犹家仲.间距的阐释学意义[J].河池学院学报, 2004, (5): 28-33.
[11]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2] 朱建平.翻译即解释:对翻译的重新界定——哲学诠释学的翻译观[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2): 7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