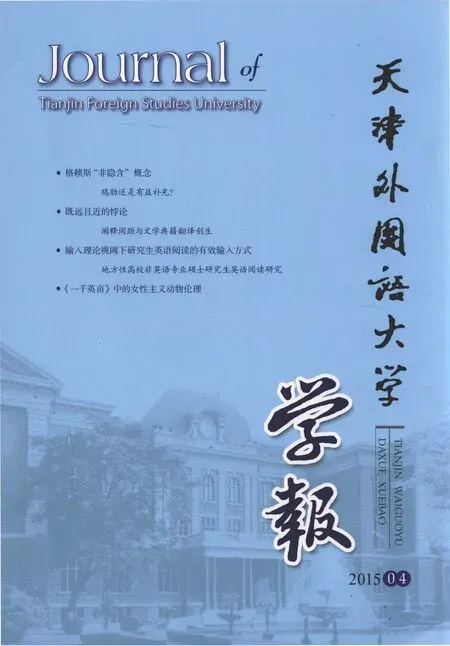谎言的语用学述评
陈 赢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一、引言
大多数人一天要遭遇将近两百个谎言(Meyer,2010:5),谎言的无处不在或已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人们说谎的动机至少有九种,概括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动机,如为自身谋求优势、保护隐私等 (ibid.:35)。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些动机背后是谎言的语用意义和效果,值得结合语用学理论进一步研究。就语用学本身而言,解读谎言亦是对现有语用学理论的检验,借由谎言能帮助我们认识现有理论的贡献和局限,以求对语言现象有更深刻的语用认识。本文对语用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梳理,重点探讨了每一个理论对谎言的认识或述评,并指出理论的长处与缺陷。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将宏观解释与微观描写结合,建构一个多层面研究谎言的语用分析框架。
二、语用视角下的谎言
1 言语行为理论
语言哲学家Austin是“语言使用论”的代表人物,提出“说什么就是做什么”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语言哲学的研究拓展至使用者层面(林玫,2009)。Austin认同“意义诞生于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即“日常语言学派”(温金海、李淑杰,2010)。Austin(1975)提出了施为句(performative)的概念,施为句无所谓真假,目的是“以言行事”。但施为句需要符合合适条件。违反这些条件的言语被分成两类:未能以言行事和滥用以言行事。Searle(1979)进一步系统化合适条件,其中之一为真诚条件。满足真诚条件,需要说话人的意愿、信念、情感等与言语行为的内容一致,比如,使用断定式言语的说话人须相信他所断言的内容(Cruse,2004)。换句话说,如果说话人的真实意图与说话人的施事行为不一致,就造成了Austin所谓的滥用以言行事。Austin和Searle都认为合适条件是构成一个言语行为的必要充分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弥补了真值条件语义学未能涉及的言语功能,然而,说谎这一语言行为,因不能满足真诚条件而遗落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之外。尽管人们在交流中通常默认真诚条件的实现,即所谓取真偏好,但这仅限于理想化的言语交流。Cicourel批评言语行为理论所举的例子是 “基于完全理想化的日常情形,剥离了任何实证意义的讨论”(Marmaridou,2000:196),现实的某些情形下,不遵循真诚条件亦能以言行事。例如,汉语中非真诚性邀请未能满足真诚条件,却能被受邀人理解并接受,交际目的依然实现(于秀成、张绍杰,2011)。不论善意、恶意,说谎是最典型的例子。一方面,言语行为理论认定,言外行为受制于一系列规则,因此,谎言不符合合适条件,也就不具有以言行事的言外之力;另一方面,如果谎言满足了真诚条件,在获得言外之力的同时,却又失去了以言取效的言后效果。Reboul(1993)通过上述悖论指出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在缺陷(何自然、张淑玲,2004)。尽管Austin创造了滥用以言行事的概念,却未能充分揭示类似说谎这样的语言行为本质。
2 合作原则理论
Grice(1989)提出话语意义的两分法: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自然意义是字面原义,具有真值条件,而非自然意义是非显见、依赖语境且可取消的。话语生成的不属于命题内容的非自然意义被Grice定义为会话含意。Grice看到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意图性本质:说话人带有特定意图,引导听话人识别他所要表达的信息,旨在实现最想实现的交际目的。Grice的推论模式是基于对上述两点的认识,即非自然意义和意图性。
Grice将会话交流放入原型会话模式中。原型会话中的对话者默认彼此具有合作性意图,“对话者的贡献被对方理解,与对方相关,也与交流的总体目标相关”(Cruse,2004:367),即对话者都会为实现交际目的而作出努力。Grice将理想化的原型会话模式概括为合作原则及四条准则。四条准则包括质量准则、数量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四条准则各包含几条细则,其中,质量准则包括一条总则:尽量说真实的话,以及两条细则:不说你相信是假的信息,不说你缺乏足够证据的信息(Grice,1989:45)。四条准则并不是僵固地限制交际,而是灵活的,在遵守合作原则的前提下,公然违反准则,就生成了深层的会话含意。
Grice对话语真实性也有过思考,Grice(1989:27)指出,从重要性来说,质量准则比其他准则所在的层次更高,“满足质量准则是其他准则运作的前提。尽管如此,就会话含意的生成而言,质量准则所起的作用似乎与其他准则没有完全不同,而且将它与其他准则放在一起,也更为方便”。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遵守合作原则前提下所产生的会话含意才是Grice合作原则理论的关切所在,而言语交际中的不合作情形,例如假装合作的说谎行为,则被边缘化,没有得到足够的考虑和研究。因其对人类言语交际过于理想化的合作偏好,Grice的理论受到了一些批评:Levinson将合作原则理论描述为“哲学家的天堂”(McCornack, 1992:5),Stich也质疑,人类交际中的真实性是否真那么有趣(Sperber& Wilson,2002:14)。
当然,合作原则之所以有合作偏好,缘于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将基于共同交际目的善意交际情形默认为人类言语交际的原型模式。与之相对应的是交际者彼此不共享对称信息和共同交际意图的非合作性情形。然而,这也使得合作原则理论易受来自语用社会视角的批驳,认为言语交际理论应当将社会因素考虑进去。另外,Grice本人也并没有将合作原则理论修正、应用到对非合作性交际情形的研究,而非合作性交际情形绝非鲜见的交际模式。相反,它同样蕴含着人类交际行为的本质和特点。事实上,谎言已引起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兴趣,诸如心理学、犯罪学、传播学、法律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语用认知等领域对谎言的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
Grice也曾表明,说话人也可以“悄悄地、不露声色地违反一条准则”(McCornack,1992:5)。这意味着,说话人可以隐蔽地违反质量准则来达到误导和欺骗的目的。一方面,说话人假装合作,另一方面,说话人利用听话人对交际合作原则的默认,实现说谎目的。前面提到Grice将质量准则设定为一条总则和两条细则,那么,谎言的形成究竟是违反包括总则和细则在内的质量准则,还是仅仅违反质量准则中的总则呢?Grice(1989:371)在解释质量准则时提到 “虚假信息并非低质量的信息,而是根本不能被视作信息”的观点,却没有明确解释上述问题。Sperber和Wilson (2002:3)也看到这一点,认为Grice没有明确表态,讨论的“究竟是质量准则的首条细则,还是质量准则的总则。而这并非一个次要的细节”。
Grice对质量准则的设定和模糊的解释容易限制谎言的范畴,造成彻底捏造的谎话才是谎言的误解。我们认为,谎言的实现,既可以通过违反总则“尽量说真实的话”和不说你相信是假的信息、不说你缺乏足够证据的信息,也可以通过不违反细则只违反总则。就后者而言,某些非虚假、证据充足的信息在特定语境的催化下,就足够误导听话人,或经说话人操纵,信息蕴含能误导听话人的深层会话含意,我们将之定义为“欺骗性会话含意”。看似为真的命题,在特定语境下却可能是虚假信息。
再者,谎言并不只局限于对质量准则的违反,也涉及对其余准则的违反。说话人可以通过多种策略对信息进行操控,达到欺骗目的。因此,McCornack(1992)提出了基于合作原则理论的信息操控理论,谎言被分为至少四种类型,分别是对信息质量、信息数量、信息相关度、信息表达方式的操控(1992:6),并且可能同时违反两条以上的准则。信息操控理论的贡献在于灵活运用Grice的语用理论,将现实里形形色色的谎言从信息组织角度作了有理有据的归纳,突破了谎言仅涉及违反质量准则的认识局限,表明了谎言信息组织形式是有系统、有规律可循的。
3 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的创立基于语言学家Sperber和Wilson对Grice语用理论的批评之上,与会话准则能确保有效言语交际的观点相左,关联理论认为,Grice提出的会话准则只是从经验出发的常识,是冗余的。关联理论的观点是,会话含意仅须通过“关联”就能被听话人识别,无须考虑合作原则下的种种准则。Sperber和Wilson是从认知机制和推论过程的角度研究会话含意,不赞同将言语交际限制在特定准则和规范框架内。他们着重从认知领域出发,研究听话人的释义过程,因而,关联理论不像言语行为理论与合作原则理论那样因过于理想化而受到质疑,基本避开了对该理论在社会文化层面思考过于天真的顾虑。
鉴于语言的不确定性,Sperber和Wilson提出,用听话人释义的两个步骤—明说和暗含来取代Grice提出的会话含意(Grundy,1995:105)。明说指明确表达出的假设,暗含指隐晦表达出的假设,即含意(Sperber &Wilson,1995:182)。关联的认知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两条假设:第一,或称认知关联原则,指人类认知系统倾向于处理最相关的信息输入;第二,或称交际关联原则,指每一条话语都传递了对最优关联的假定(Sperber &Wilson,2002:15-16)。
如上所述,关联原则本身就能够为听话人搭建桥梁,通向所有含义推断中最相关的那一个。这里存在“积极认知效果”和“加工努力”之 间的 权衡(Grundy,1995:107;Sperber &Wilson,2002:15),也就是说,最相关的信息意味着用最少的加工努力来最大化积极认知效果,这是在Grice理论中未涉及的一种心理过程。
就谎言而言,Sperber和 Wilson(2002:34)与Grice认为欺骗性信息根本就不是信息的观点一致,从关联角度来看,欺骗性信息几乎没有传递任何积极认知效果。他们的争论点在于,说话人对于有效信息的贡献能够“在一个没有真实准则的框架内更有效地实现”,因为质量准则的总则涉及“传递的是什么”,质量准则的细则涉及“说的是什么”,而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ibid:3)。这一说法与我们的观点一致,字面真实性既非交际真实性的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比如,字面真实的信息亦可构成谎话,而讽刺的字面信息与事实不符,表达的却是真实意图。Sperber和Wilson(1995:218)主张:“说话人必须对听话人的认知能力和语境资源作一些假设”,这一观点在谎言现象中可以得到具体例证,如说话人必须考虑听话人的认知能力来确定以何种方式操控信息,更好地达到欺骗目的。关联理论虽然消解了Grice的质量准则,提出一些有趣的观点,其兴趣却在于解释隐喻、讽刺、玩笑这类语言现象,对谎言并未深入探究。
批评话语分析的部分研究借鉴关联理论,将对语言操控与意识形态的研究置于认知学说之下。例如,Saussure(2005:14)作出假设,认为操控是通过阻碍听话人的认知推论过程得以实现的,即“阻碍人的理性机制”(Emeren,2005:XII)。借鉴关联理论的认知假设,可以较合理地提供谎言常不能被识破的认知理据。然而,该理论建构于抽象的语言心智活动、描述性不够,在语言使用的微观层面欠缺操作性的具体框架,至少目前来看,未能成为全面剖析谎言的有力工具。
4 礼貌理论
Leech(1983:11)提出“普通语用学”概念,重点讨论会话的语言学准则。他的模型是为“目标取向的言语情境”设计的,在这种言语情境中,“说话人用语言对听话人的思维形成特定效应”(ibid.:15)。Leech的语用学观点与Grice理论同源,提出如下礼貌原则并视作完善合作原则的必要补充: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同情准则(Leech,1983:132)。Leech的礼貌原则抓住了人际交往中一些默认的社会惯例,部分地解释了Grice合作原则理论未能触及的礼貌语言现象。在一些特定场合,人们觉得自己有义务说一些并不相信或同意的话,而这类谎言通常是无害的,是出于社会关系乃至听话人的利益而说的。这就是所谓社会谎言或善意的谎言。考虑到交际的礼貌惯例,人们遵守上述礼貌准则,如果礼貌的需求到达极致的程度,就会出现善意的谎言。但很显然,礼貌原则无法全面解释谎言,毕竟,很大一部分谎言出于恶意,并非利他。再者,礼貌原则过于具体,因而太过僵固,没有深究人们遵守礼貌原则现象背后的心理动因。
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理论(1987)不同于Leech的礼貌原则,因为他们的理论围绕的是由Goffman(1967)发展的面子概念。所谓面子,是一种“公众自我形象”,可以保持亦可失去,包含“负面面子”和“正面面子”。负面面子指“行动自由,不被强加意志束缚”,正面面子指我们“积极一致的公众自我形象”,并渴望自我形象“被他人欣赏和赞许”(Brown &Levinson,1987:61)。面子是 “基本需求,且每个成员都知道其他成员渴望拥有面子,部分地满足面子需求,符合每一个成员的利益”。基于对面子的需求,该理论假定人们为了避免面子威胁行为,求助于某些保全面子的策略(ibid.:65)。Brown和 Levinson对这些策略进行了详细说明。Brown和Levinson礼貌理论的一大贡献在于,该理论比Leech的礼貌原则更深入一步,掌握了言语交际背后的社会心理动机,即面子保全动机。相比Leech的礼貌原则,面子理论相对灵活得多,无须再制定刻板僵固的、容易招来社会语用学批评的言语交际准则,可以将面子理论经过修正,运用到跨文化的面子保全策略研究中去。另外,面子概念也使得该理论将社会权力和社会距离加入语用学的考察范畴。然而,面子理论与礼貌原则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尽管该理论能很好地对社会谎言作出解释,但局限于讨论言语交际的礼貌现象,因而也无法成为谎言研究的理论框架。
5 顺应理论
Verschueren作为欧洲语用学派代表人物,其语用观不同于上述提到的几位语用学家,他认为语用学不能仅限于对语言形式和意义的研究,更应该延伸至人类生存与语言使用的内在关系。语用学研究的是“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行为或社会行动的形式”,因此,“语用视角应当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维度就是语言与人类生活之间的联系”(Verschueren,1999:6)。根据他的观点,语用学不应被视作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应上升至一门独立的研究,探究与认知、社会与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语言使用,而这恰恰构成了“语言行为的全面复杂性”(Verschueren,1999:7)。Verschueren 认为,语用学应当关注的是“语言的有意义的功能”(ibid.:8)。
顺应的概念并非直接源自Verschueren,而是基于前人的思想积淀。Piaget思考了“同化”和“适应”两个概念,他的心理学理论将生命体看作解决问题者,不仅顺应生物环境,还顺应社会和文化环境,因此,知识的增长被视作人类进化的表现(Verschueren,1987:47)。早在1875年,Whitney便认为,语言的起源和演化应归因于人类对生存中交流需求的顺 应(ibid.:48)。Becker(1984),Foppa(1979)和Mahoney(1975)将语言习得与语用发展的模式相关联,将前者定义为一种连续的顺应过程。同样,在辅助孩子的语言习得过程中,母亲用语也可看作是一种顺应。此外,一些顺应论学者举出不少支持例证,如间接言语行为的使用就是为了避免自然界的竞争(Verschueren,1987:50)。在此基础上,终于出现了蕴含语言顺应性的语用学概念,如Searle(1976)以客观世界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作为区分言语行为的一个维度,提出了言语行为的适从性。
Verschueren顺应理论的一大主张是:语用的本质是一个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选择发生于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包括语音、词形、语义、句法和语篇。Verschueren(1999:56)将这一主张细化为七条要义:(1)选择发生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2)不仅选择语言形式,也选择语言策略;(3)选择过程可于任何程度的意识下发生;(4)选择在语言表达和理解过程都会发生,且对于意义生成方式具有同等重要性;(5)一旦使用语言,就不得不进行选择,不论选择范围是否足以满足交际需求;(6)选择一般不是等效的;(7)选择有对应的可替代选择。基于此,Verschueren(1999)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属性:变异性、协商性、顺应性。他认为,语言选择的范围是可变的;选择是可协商的,并不是机械的形式和功能的对等;语言选择的变异性和协商性是为了顺应交际需要。三个属性相互依存:顺应性是比前两个更高一级的概念,是语言选择的目的,变异性、协商性是顺应性的满足条件,是语言功能的基础。Verschueren(1999:69)还提出语言顺应性的四个研究角度:顺应的语境关联、顺应的结构对象、顺应的动态性、顺应过程的突显性。语境关联指交际语境中与语言选择相互顺应的成分,即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会世界(ibid.:76)。结构对象包括任何层面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原则。动态性指语境关联与结构对象交互的顺应过程。突显性与认知相关,指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上述顺应论的核心观点不仅揭示了言语交际的顺应性本质,也为语言行为的研究提供了较系统的理论框架和语用视角。Verschueren将语言结构、动机、过程和意识程度都纳入语用范畴,拓宽了语用学视野,其对言语交际的本质认识更复杂、更透彻,在现有的语用学理论中,具有较高的解释充分性。
顺应论旨在建构宏观理论框架,对谎言并无具体涉及。但我们认为,顺应论从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出发,将语言行为视作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对交际需求的顺应,那么,说谎行为自然也被包括在内,与其他语言行为并无本质区别。谎言是在语言结构层面和策略层面作出语言选择的结果,是语言顺应的一种。就突显性而言,说谎总体上是意识程度相当高的语言行为,同时,部分语言选择也可能是下意识发生的,如说谎需要虚构信息造成认知负荷太高,从而发生了认知泄露。说谎体现了对结构对象和语境关联成分的顺应,物理环境、社交关系和心智状态锚定了从语言形式到语言策略的选择,语言选择的顺应性体现出层层递进的关系,最终指向说谎者的真实交际意图。谎言有一定的语言特征和信息操控策略,反映出语言的变异性、协商性。不同于经典语用学理论将谎言视作非默认、边缘化的反常交际行为,顺应理论帮助我们透过语言纷杂的表面,从根本上认清谎言与其他语言行为的共有本质。
三、谎言的语用研究框架
对上述理论进行梳理,目的是建构谎言的语用理论框架。国内较早用顺应论解释谎言现象的是何自然和张淑玲(2004,2006),对谎言作为语用策略的顺应性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建构了多层面分析谎言的语用理论框架:将顺应论作为研究谎言的宏观框架,从语言的三大属性划分谎言研究的三个层面:变异性—谎言的语言表征、协商性—谎言的信息策略、顺应性—谎言的语用意义。顺应理论过于概括,虽然提供了研究的哲学途径,但要进行具体分析,仍需要借助微观的语用学理论。尽管Grice的理论受到批评,但合作原则广泛地被各类学者作为理论基础,运用到对语言使用的讨论中(Marmaridou,2000:233),例如前文提到的信息操控理论。我们将信息操控理论纳入宏观理论框架的第二个层面,探讨说话人如何通过对会话准则的操控对谎言进行信息设计。语言的变异性使得谎言会出现某些语言指征;语言的协商性保证了会话准则是可操控的,谎言信息设计是有规律的;语言的顺应性说明了谎言背后的动机。三个层面由表及里,从微观描述到宏观解释。Chomsky提出评价语法的三个平面:观察充分性、描写充分性、解释充分性(刘润清,1995:214-215)。推及语言研究亦如此,将擅长解释的顺应论和擅长描写的信息操控论结合,目的是确保对谎言的分析能兼具描述性和解释力。
四、结语
本文对现有语用学理论及其对谎言现象的讨论进行扼要述评,指出各理论的贡献与不足。语言顺应论能从宏观角度揭示谎言与其他语言行为的共有本质,而经典语用学的合作原则理论则能从微观角度描写谎言信息组织方式的“特异性”,因此需要建构多层面分析框架。至于谎言具体如何通过语言表征、信息操控和顺应动机体现变异、协商和顺应性,我们拟结合实例另文讨论。
[1]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 Brown, P. & S. C. Levin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Cruse, A. Meaning i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De Saussure, L. Manipulation and Cognitive Pragmatics: Preliminary Hypotheses[A]. In L. De Saussure. & P. Schulz (eds.) Manipulation and Ideolog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scourse, Language, Mind[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5] Goffman, E.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r[M]. New York: Garden City, 1967.
[6]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H. P. Grice (ed.)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9.
[7] Grundy, P. Doing Pragmatics[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1995.
[8]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New York: Longman, 1983.
[9] MaCornack, S. A.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Theory[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992, (59).
[10] Marmaridou, S. S. A. Pragmatic Meaning and Cogni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11] Meyer, P. Liespotting: Proven Techniques to Detect Deception[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0.
[12] Searle, J. R. A Classification of Illocutionary Acts[J]. Language in Society, 1976, (5).
[13] Searle, J. 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4]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15] Sperber, D. & D. Wilson. Truthfulness and Relevance[J]. Mind, 2002, (111).
[16] Van Emeren, F. Forward[A]. In L. De Saussure & P. Schulz (eds.) Manipulation and Ideolog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scourse,Language, Mind[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17] Verschueren, J. 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M]. Belgium: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1985.
[18]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何自然, 张淑玲. 非真实性话语作为语用策略的顺应性研究[J]. 外国语, 2004, (6).
[20] 林玫. 语言与语言哲学[J]. 兰州学刊, 2009, (12).
[21]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22] 温金海, 李淑杰. 语言研究范式的哲学底蕴释读[J]. 广西社会科学, 2010, (11).
[23] 于秀成, 张绍杰. 汉语非真诚邀请语用特征与言语行为适切条件[J]. 东北师大学报, 2011, (6).
[24] 张淑玲, 何自然. 非真实性话语研究述评[J]. 现代外语, 2006,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