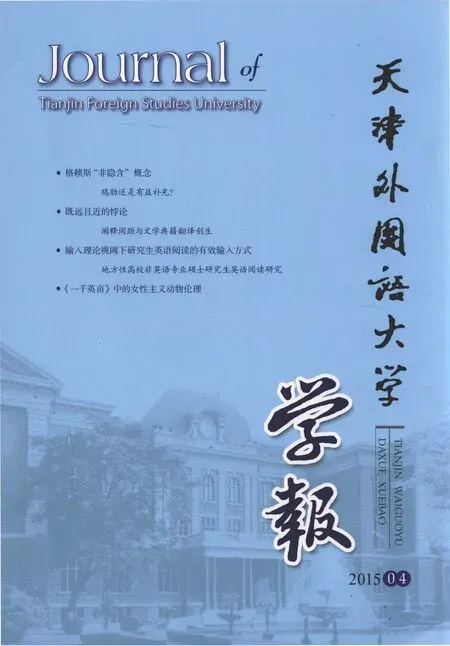格赖斯“非隐含”概念——鸡肋还是有益补充?
姚晓东,戴卫平
(北京林业大学 外语学院,北京100083;中国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2249)
一、引言
日常会话中话语有时包含或展现的意思比说话人想表达的内容要多或与字面内容有差别,说话人会随之去除或者希望听话人根据语境消去他没传递的那部分意义,进而使得话语传递的意义不同于语言表达式本身通常具有的隐含。格赖斯的“非隐含”(disimplicature)概念就属于这一现象:特定语境有时会舍弃、取消句中词句通常所具有的蕴涵或会话含义,即说话人U通过陈述(或明确传递)p,删除了q。这不等于说U没有进行隐含,而是随后删除或希望听者删除这一本已可能传递的内容。
非隐含概念并未引起语用学界重视。一方面,Chapman(2005:135)认为,这一概念存在问题可能是格赖斯没有回头深入讨论的原因,但她没有明示究竟问题何在。另外,会话含义理论的问世为话语理解提供了“意会大于言传”的推导机制,说话人意向介入意义分析既向真值条件语义学发起了挑战,也是对意义使用论的反动,这一强烈冲击分散了学界探究非隐含的注意力。再者,非隐含现象可借助已有的相似概念暂时得到解释可能是它遭受冷遇的另一原因:Chapman认为它与Cohen(1971)对“删除”概念的松散解释接近,同时与潜在含义、含义的可取消性有关联。
然而非隐含概念并非可有可无。它与含义的可取消性不同,也和Cohen的删除概念存在差异,其运作兼跨语义学和语用学两个领域,是格赖斯意义分析模式的必要补充,甚至可能成为会话理论比较有趣的延伸(Chapman ,2005:134),理应引起语用学界的足够重视,重新发掘很有必要(林允清,2007:106)。厘清非隐含与相关概念的共性与差异,明确其作用对象、范围及促成因素有助于全景透视格赖斯意义理论,进而为近年出现的新一轮关于会话含义到底可否取消的争论(Borge,2009;Capone,2011;Feng,2013;Jaszczcolt,2009;王晓飞,2012)提供些许思路。
二、非隐含概念的提出
在讨论意向的分类,回应和评价Davidson对意欲和想要(intending/wanting)的概念区分时,Grice(1974:3)提到了非隐含概念,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只是提到三个涉及非隐含的例子 :
(1)奖品要么在厨房里,要么在阁楼上;我知道把它放哪里了,但不告诉你。
(2)Hamlet看见他父亲在Elsinore的城堡上。
(3)你是我咖啡中的奶油。
例(1)前半句话中由“要么”引发的会话含义,说话人不知道奖品确切在哪儿,被后一个小句排除了,说话人有意取消了原本的惯常含义。另外寻宝游戏这一场景的特殊性也足以让听者自行排除上述隐含。例(2)中,由于剧情一开始就显示Hamlet的父亲被害,所以这句话中Hamlet看到的只能是父亲的亡魂。读者不会坚持 “看见”意谓 “所见确实存在”这一隐义,它已被现实语境知识删除。有时语境传递这样的信息:如果明说内容的某些蕴涵明显为假,正常的蕴涵就会被悬置。若借助合作原则考察这一现象,我们可以认为说话人没有遵守会话的质准则,即“尽量使你的话语为真”和“不说自认为虚假的话”。严格来说这里说话人违反了质准则的第二次则,并非对“看见”一词的严格使用,而是松散用法 。此时听话人不按常规在真值意义上解读其语义蕴涵。一定背景下,比如谈论或报告这一情况时说话人可采用词语的松散用法来指这种幻象。“幻象”、“亡魂”等附加语会使话语就显得冗长过于较真。这里删除的词语的语义蕴涵是句子明说内容的一部分。例(3)的隐喻不能按照句子的话面意思来解读。按照格赖斯的说法,说话人进行了非隐含操作。与例(2)不同,百科知识使话语的字面意义不合情理,全部明说内容均站不住脚,此时非隐含作用的范围不是话语明说或蕴涵意义的一部分而是全部,听者转而寻求不同的解读取代本来的话面意思 。
上述三种非隐含类型中,例(1)取消的是潜在的一般会话含义,例(2)删除了词语的语义蕴涵,例(3)否定了话语的字面意思,听者在非隐含基础上另辟蹊径获取不同解读。其中例(1)和(3)可由会话理论解释,前者体现了含义的可取消性,后者则基于对质准则的违反,源于句子论元之间范畴的不对称,听者要根据语境推断说话人含义。可见例(3)中非隐含与推导说话人意向或含义处于话语解释过程的不同阶段,听者在非隐含后的另一阶段重新解读说话人意义。就上述例子而言,非隐含包括去除部分语义内容、取消会话含义或超越字面意义转而寻求全新解读的理解过程。但对于非隐含的运作与“删除”概念、含义可取消性等邻近概念的差别,取消对象和范围的差异,以及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等仍需进一步阐释。
三、非隐含与“删除”概念辨析
Chapman (2005)认为非隐含与Cohen的“删除”概念相似。其实不然。我们在考察Cohen的概念后解析二者的异同。Cohen (1971)认为话语解释的语义论比较明晰,可以取代格赖斯的会话论。在讨论and一词时他发现句中一些原本由and传递的附加信息以某种方式被取消或删除了,and只起连接作用,丧失了表达时间先后或因果关系等语义特征的功能。实质上and有多种义项特征:表明连接成分是语义或功能上的同类,表达时间先后和句法上的连接并置等。词条解释足够详尽的字典就会包含上述特征,但具体语境下某一特征会被取消或删除。而以格赖斯为代表的会话论则坚持认为取消的是对人类话语的一般假设,一个不适于对某具体自然语言的描述中说出的假设(Cohen,1971:55)。下列例子“塑料花”、“石狮子”、“画得很精致的手”、“假声”、“他无意中羞辱了她”、“防尘罩上的女孩没穿衣服”等,就涉及语义删除。其中“花”中“作为植物的一部分”,“羞辱”一词中“故意”的语义特征被修饰语删除了。同样看到“防尘罩上的”这一限定语,我们也不会把“女孩”词义中原有的某些特征带入对句子的理解。这里删除的既有词语的蕴涵义(如“羞辱”所包含的故意性),也有义项特征。
另外,“删除”概念还适用于消除歧义。在讨论同形异义词和多义词时Cohen(1970:480)提到了green bank,fair price等短语。搭配抑制了bank可能释义中“不受颜色影响”、fair一词跟dark对立的“浅棕或灰白色”限制。有的搭配中词语的义项变体之间会产生冲突,可能解读之间相互影响制约个别义项特征的出现,这时词语的义项特征不一定全部被删除。有时相邻词汇能够抑制搭配对象的显性特征或者激活、凸显通常情况下的隐性或边缘特征。一些语义成分由此得以保留,其他成分特征则被语境抑制或删除。
这同样适用于隐喻用法。Cohen(1970:482)指出隐喻表达中的词语已经不怎么受义项特征或语义成分的限制,或者仅保留其中的一些特征成分。他认为在自然语言中,词或短语的比喻义全部包含在字面意义中,通过去除语义假设中一个或几个合适部分中的某些变量限制而得到比喻义。例如在baby airplane中,baby一词中的年龄、人类特性等变量几乎对意义理解没有任何限制,只保留了“个头小”的特征。至于哪些限制成分可以被去除,Cohen的看法是,变量按照重要性由弱到强排成一个等级序列,人们会期待那些不再发挥效力的限制变量位于靠近等级序列的最强一端。只有这样,通常凸显的意义特征由于受到特定语境限制而不可取,听话人会转向平时不被凸显的边缘义项,而这一被“放行”的意义特征和搭配语词之间有足够的距离,使解释者形成陌生感,隐喻才成为可能。即二者既要存在一定的疏离感或冲突,不然构不成隐喻,也要有相关性,否则无法解释。可见Cohen的语义论和格赖斯的含义观对隐喻分析的着眼点不同,前者从词语搭配入手,通过对语义特征的抑制与激活寻求可能的合理解释,后者源于句子论元间范畴错位引起的非隐含,进而转向含义解读 。
讨论了义项删除的功能后,我们来看“删除”的运作机制。词汇语义特征的抑制或删除遵循一定的要求。这首先体现在,词语的意义区别性特征集内特征的重要性有相对的层级次序。一般而言,字面用法中的次要特征最先被删除。如“塑料花”中修饰语删除了“花”义项中的生长概念而不是典型的外形特征。而当某重要语义特征被删除时,我们倾向于称其为隐喻用法,因为它偏离了词语所表达概念的典型特征。其次,不能删除逻辑小品词的意义真值功能内核,所以我们从不会赋予这些小品词隐喻用法。
Cohen与格赖斯对逻辑语词及其对应自然语言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法也不同。首先Cohen(1971:56)赞同格赖斯提出的修订版奥卡姆剃刀,坚持只赋予逻辑语词一项词典意义,若无必要,无需增加义项,但二者对它对应的自然语言做法不同。Cohen认为自然语言语词涵义丰富,从自然语言到逻辑语词,删除的是词条义项特征集中的某一特征,剔除了常态意义的一部分。而在格赖斯的非隐含过程中取消的是关于人类话语一般隐含的假设,相当于Cohen语义公设中词条的一个义项。此外会话理论主张逻辑语词和对应的自然语言语义相同;二者的差别在于具体语境中逻辑语词对应的自然语言能产生一定的会话含义。我们认为二人解读自然话语时采取的方法不同。语义假设论是在做减法,先赋予词语内容丰富的强式意义而不仅限于真值意义,之后根据语境剔除原有诸多词义中不合时宜的义项。而会话含义论是在做加法,主张只赋予词语真值意义,必要时根据语境增加隐含意义。如果语境不合适或者随后出现的语境与句子意义不协调,这种通常会出现的隐含意义被终止,有时甚至会删除词语原有蕴涵义的一部分,如删除see的松散用法中“眼见为实”的蕴涵。可见非隐含与删除概念的深层假设不同,语义论和会话论对这种取消的本质看法不一。Gazdar(1979)提醒我们,标准的语言学含义研究想当然地把意义解释为系统意义或逻辑式,然后用含义充实或者根据语境削弱它,剔除或取消话语原本可能携带的隐含义。这一说法跟格赖斯的非隐含思路假设异曲同工,都不同于Cohen的删除概念。
综合来看,Cohen对删除概念的论述更多地聚焦词语意义,根据搭配和修饰语剔除词语的某些义项特征,消除歧义,删减说话人不想宣认的意义成分,或者淡化中心义项和常规用法,激活凸显一些边缘特征。另外Cohen提到的语境更多的是由语言形式标示的语境。比较而言,格赖斯的非隐含概念则面向句子层面,涉及的语境不限于词语搭配,会话含义可以被取消。再者,另一种意义的取消来自随意言谈。人们使用语言并不那么严格,用词松散随意。格赖斯给出的另一个例子是两个人在不同光线下选领带,他们事先都知道(且彼此也知道对方知道)领带是中绿色的,却依然会说:“现在是浅绿色”或“这种光线下它有点儿发蓝”。严格来说这一意思应当表达为领带“看起来”是浅绿色的或“似乎”有点儿蓝的暗影。而现实中双方都知道不存在变色的问题,没必要进行修饰限制,随意说法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这时言辞中原本具有的蕴涵义就被取消,却不是会话含义(姜望琪,2003:72)。类似的例子还包括see的松散使用。我们知道Macbeth产生了幻觉也完全可以说“Macbeth看见Banquo了”。这句话中see原本的部分规约意义或蕴涵被取消,即便Banquo没有出现,读者也不能根据这句话就否认这一隐涵是其规约意义的一部分,同样也不能否认其义项中存在这一隐涵。这种松散说法类似于Sperber和Wilson(1995)的随意言谈(loose talk),是说话人根据语境在衡量可行性之后的说辞。虽说眼见为实,但生活中人们确实会这样说,即便知道是幻象也会说看到了实物本身 。随意言谈在日常会话中很普遍,除了合乎语境,还要得到会话另一方的认可,否则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受欢迎的后果(Grice,1989:45)。具体语境下很多话语都会导致非隐含。上文提到的挑选领带和Hamlet的例子,删除或抑制的是语言形式通常具有的蕴涵而不是语用含义;藏宝游戏中删除的是会话含义而非规约意义。这与Cohen的删除概念不同。概言之,删除概念和非隐含概念在语境、删除范围、运作层面和载体方面均存在差异。
四、非隐含的运作过程
1 非隐含过程及其作用范围
格赖斯没有深入探讨非隐含的运作机制,但Chapman(2005)指出我们可以根据会话准则来解释它,即假定说话人遵守会话准则尤其是质准则的第一次则,不说自知虚假的话。如果明说内容的一个或所有蕴含明显为假,就可以认定当下这些蕴含没有产生,进而取消话语原本的隐义;如果非隐含涉及明说的全部,则听话人转而寻求不同的解释。前一种情况可以解释格赖斯给出第二个非隐含的例子“Hamlet看见他父亲在Elsinore的城堡上”。这里“看见”蕴涵了“所见之物真实存在”,但背景知识阻止听话人做出这一隐义解读,或者说话人利用听说二者的共享知识取消了“眼见为实”隐义。后一种情况适用于例(3)“你是我咖啡中的奶油”这类隐喻话语,由于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范畴错位,此时非隐含的作用范围涵盖全部明说内容,听话人会放弃明说内容转而寻求非字面解读。例 (1)则是典型的说话人借助上下文语境自行取消根据荷恩等级推导出的一般会话含义的例子。
但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格赖斯的话语解读基于两类机制:一是语言编码机制,获得字面意义;二是合作原则,获得附加的会话含义。对上述三例的解释显示非隐含既不是原始编码的意义,也不是能整齐划一地借助合作原则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这一意义既非“明说”也非“暗含”,这就对其范畴归属与推导提出了疑问。另外格赖斯把隐喻话语归为“仿佛在说”的内容,听话人从字面意义理解开始发现其与现实世界不对应或无法满足交际需求,就认定理性的说话人虽违反了质准则但在深层依然遵守合作原则,随即放弃字面意义转而寻求非字面解读。这一“两步走”的非隐含理解过程符合格赖斯的含义解读顺序,似乎在明说、暗含之间增加了一个过渡阶段,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即表明格赖斯的明说、暗含无法穷尽意义的全部,间接证明了关联理论“显义”(explicature)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显示暗含阶段之前的意义解读中语用介入不可避免,即存在所谓的“格赖斯循环”(Levinson,2000:187)。
结合第三节的分析不难看出Cohen对删除概念的分析虽涉及语言使用和语类 ,但更多集中在词语搭配对彼此义项隐现的相互作用:激活凸显边缘特征,压制、削弱中心特征,消解歧义。而格赖斯提到的随意言谈能删除蕴涵等规约意义;藏宝游戏的例子则是上下文语境导致含义被取消,说话人放弃或不宣认特定会话含义;隐喻用法中话语的明说内容不合时宜,百科知识触发非隐含过程导致重新解读话语。归纳而言,语言语境(包括词语和分句)、情景语境(语言使用及其场合)和社会文化语境(包括百科知识)都能引起非隐含,删除部分意义成分。这是我们对非隐含运作过程、促成因素及其涉及范围的初步归纳。
另外说话人意向是格赖斯会话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意向识别对于会话含义推导和言说效果的生成不可或缺,说话人意向及其在听话人身上的效应决定了说话人意义,进而决定句子和语词意义。格赖斯也因此被指责为心灵主义者,其理论被称为意向意义论(Schiffer,1982;Chapman,2005:3)。那么在非隐含中说话人的意向处于何种地位,是否也“传递信息、影响或指导他人的行动”(Grice,1989:28)?格赖斯的例子显示说话人并没指望所有的非隐含都在听者身上产生反应:有时非隐含是说话人无意识传递的(如随意言谈中取消语义蕴涵),有时则随之明确取消某种含义(如寻宝游戏中删除一般会话含义),而对隐喻的解读则需识别说话人意向。第一种情况下说话人意向的作用并不明显。这也显示非隐含和“没有暗含”不同:人们表达非隐含时有时是有意的,甚至是想暂时误导对方(如寻宝游戏中),有时则是由于言说能力不足或者出于省力考虑(如随意言谈)。
2 非隐含、潜在含义与含义的可取消性
非隐含是会话理论的延伸但又不同于会话含义。含义理论是在坚持理性会话主体假设下,听话人利用合作原则及会话准则,结合语境对明说内容进行增容或调整,解析出大于言传的附加意义或抛弃说话人字面意义,对反语、隐喻等“仿佛在说”的内容不进行字面解释,转而寻求话语可能的会话含义。而在非隐含中,某些语言形式的语义内容或蕴涵被取消或中止。诚然有些情况下合作原则会使部分明说内容析取出去或被替代,在这一点上会话含义理论和非隐含具有共性,在对隐喻解释上也有交叉:此时含义推导是在非隐含基础上进行的,二者所处的阶段不同,非隐含作用在先,即听话人发现对话语字面解释的结果不够明晰或与常识相违背(如隐喻中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明显的范畴错位)时,就会放弃明说的内容进行非隐含,然后寻求可能的含义解读。
此外,我们很容易把非隐含与潜在含义关联起来。Gazdar(1979)区分了句子的潜在含义和实际含义。由于跟实际语境冲突,原本可能出现的潜在含义未能实现,而满足话境条件的部分才实现为话语的实际含义或意欲隐 含(Burton-Roberts,2006;Gazdar,1979:55,132;Jaszczolt,2009)。蕴涵、含义都会导致某些含义被过滤、删除或中止 。会话含义的可取消性测试基于如下观点:含义不是话语常规语力的一部分而是在语境中运算出来的(Gazdar,1979 :292)。Grice(1978 :114-115)把可取消性视为会话含义的最重要特征,虽非充分条件却是必要特性,如随意言谈中的一些意义可以被取消但不是会话含义。他并未把含义的特性作为测定会话含义的定义标准而只是参照指标,其中一些特性至少可以为确定是否存在会话含义提供初步证据。格赖斯的论述显示非隐含概念与潜在含义概念不同,前者可删除的意义范围广,不限于含义还包括语义蕴含、语义特征等;后者的作用对象只限于含义。不可否认目前学界对含义的可取消性存在争议:一方认为说话人意向/意义不可取消只能纠正或澄清,另一方则强调区分含义取消的潜在可能性与实际发生。非隐含概念可为这一争论提供参照。Chapman(2005:134)给出一个非隐含例子:假如某人说“Bill下周想要(intend)去攀登珠穆朗玛峰”,而当时的语境明确显示这具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时他实际上非隐含了“Bill确定会去登山”这一Bill宣认的意向。可见现实情形对意向的限制也属于非隐含的关注范围,这契合格赖斯对意向的严格限定(姚晓东,2012)。格赖斯藏宝游戏的例子也显示说话人意向以及含义被取消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研究的关注点不应该只落在个别含义触发语上,要在整体把握整个句子甚至是话语的情况下才能决定到底是意向/含义被取消,还是说说话人一开始就没有这一意向。
五、非隐含概念的存在价值
非隐含概念未引起语用学界的足够重视,但在格赖斯意义理论体系中当占有一席之地。会话理论是格赖斯意义分析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话参与者根据理性主体假设,借助合作原则,结合语境生成和理解话语。听者识别言者意向,对明说部分进行调整或增容进而获得说话人意义,而后者又用来界定句子和词语意义。非隐含机制是言者借助语境对意义有意无意的删减和把控,听者也随之调整相应解读,这构成了格赖斯意义理论的一部分。有时发话人收回话语传达的一些意思,这与含义的可取消性不无关系,有时听者根据语境去除听到话语的部分意义,这从另一方面凸显了语境的削容作用。同时如上文所示,非隐含概念显示我们能根据现实语境判断说话人是否具有某一特定意向,这均为对语用学的有益补充。
另外,非隐含机制在解读明说和获取暗含过程中也发挥作用。含义是在明说基础上推导出的附加意义,而非隐含是根据语境,有时从对明说的解读中去除不合语境的部分,如取消一般会话含义,有时则去除话语的语义内容,中止词语语义蕴涵或部分义项特征使话语传递的意义小于语言形式包含的内容,这是部分取消。再者听话人发现句子意思与自己的认识冲突进而非隐含或放弃话语字面语义寻求其他解释。说话双方还认为彼此遵守着会话准则,尤其是质的准则(Chapman,2005:134-135)。这一动态的分析过程契合会话是动态的实时行为,因而对会话含义的解读也必须是动态的随语境而变的(姜望琪,2012),这些都对语用学研究不无启发。
第三节的讨论显示会话含义和非隐含在删除内容范围、运作机制上存在差异:前者是在做加法,后者在做减法。尤其是在对隐喻的解读中,当听话人意识到字面解读明显为假,非隐含会促使她取消话语的字面解读,此时非隐含已完成使命。听话人随后根据合作原则进行含义推导则是在另一层面上的操作。发生阶段不同也是保留非隐含概念的原因之一。与含义可取消性相比,非隐含作用对象的范围广,涵盖语词的语义蕴涵,这是含义可取消性无法囊括的。这在提醒我们不能对随意言谈的真值内容当真的同时,也对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彰显了语用学界提出的格赖斯循环。格赖斯对明说与暗含的区分表明二者遵循先后顺序,含义推导建立在对话语字面意义解读的基础上,对编码意义的解读不涉及语用介入。格赖斯对非隐含的探讨似乎对自己的明说与暗含二分构成了挑战,印证了关联理论对其批评属实:明说与暗含无法囊括意义的全部,即使在对明说的解读中也有语用介入,格赖斯忽视了显义在话语解读中的作用。这是格赖斯始料未及的,也可能是他未继续深入讨论这非隐含这一概念运作机制的真正原因。
上述讨论都表明非隐含概念并非可有可无,作为含义理论的有益补充,非隐含与之一道丰富了格赖斯意义理论的图景,在明晰语用学的动态性和语境的作用的同时,使我们更加客观地审视经典格赖斯语用学理论的成败得失。
六、结语
作为一个曾被忽视的概念,非隐含尽管可能存在问题却是拓展格赖斯会话理论的增长点和对语用学的丰富与发展。尽管存在交叉和关联,非隐含概念与Cohen的 “删除”概念不同,也不能完全用含义的可取消性来解释,更不能与潜在含义概念混淆。上述概念无论是在运作机制、作用对象和范围,还是对语境的认识方面都存在差异。重新发掘这一概念不仅可以更丰满地呈现格赖斯意义分析模式的全貌,厘清各类意义之间的关系,为含义可取消性的争论提供参照,也能深化我们对语用学理论的认识,比较各理论派别在含义解读推导方面的得失。作为会话理论的有益补充和格赖斯意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非隐含概念既丰富了经典格赖斯语用学思想,也对其意义分析模式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值得挖掘。
*感谢胡壮麟、姜望琪教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 例(1)是在玩寻宝游戏时说的话。在讨论会话含义的可取消性时,Grice(1989:45)再次提及这一例子。
②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这里“父亲”是松散用法,实指“父亲的亡魂”这一语义充实,关联论的显义(explicature)也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③ 这里我们也应当考虑到成语(idiom)的解读,成语的字面意义与整体凝固意义不同,听话人会直接获取成语的意义,却并不属于Grice所谓的非隐含范围。
④ 关联理论认为隐喻表达源于交际者对语言的创造性松散使用,字面意义只是激活相关百科知识的入口,听话人会利用语言和当前语境两方面线索直接解读话语进而获得临时性的满足最佳关联假定的解读,这需要听话人具有“读心”能力,而非Grice更多侧重语言语境和认知映射进行的话语解读过程。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地化解格赖斯循环。
⑤ 特征集相当于Cohen(1970:474-475)提到的语义范畴或区别特征分类,比Aristotle的范畴概念更广泛丰富。这一语义假设的基本结构在不同场合下有不同变体,称为相关变量概念的局部表现。这里场合不包括社会—物理场景。
⑥ 这并不意味着see有两种意义,一个表事实性的而另一个为非事实性的。
⑦ 场景会删除或取消某些意义成分(Cohen,1971:60)。如果一个人指着油画的一角说“这儿有只手”。显然这不是指有血有肉的手。
⑧ Horn(1972)认为中止与取消不同。
[1] Borge, S.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and Cancellability[J]. Acta Analytica, 2009, (2).
[2] Burton-Roberts, N. Cancellation and Intention[J]. Newcastle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06, (12/13).
[3] Capone, A. Knowing How and Pragmatic Intrusion[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11, (4).
[4] Chapman, S. Paul Grice: Philosopher and Linguist[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5] Cohen, L. Some Remarks on Grice’s Views about the Logical Particles of Natural Language [A]. In Y. Bar-Hillel (ed.) Pragmatics of Natural Language[C].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1971.
[6] Cohen, L. & A. Margalit. The Role of Inductive Reasoning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 [J]. Synthese, 1970, (3/4).
[7] Feng, G. W. Speaker’s Meaning and Cancellablility[J]. Pragmatics & Cognition, 2013, (1).
[8] Gazdar, G. Pragmatics: Implicature, Presupposition and Logical Form[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9] Grice, P. Further Notes on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P. Cole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9: Pragmatic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10] Grice, P. Reply to Davidson on ‘Intending’. H. P. Grice Papers, BANC MSS 90/135c, 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74.
[11] Grice, P.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 Horn, L. On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of Logical Operators in English[M]. LA: UCLA, 1972.
[13] Jaszczcolt, K. Cancellability and the Primary/Secondary Meaning Distinction[J].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09, (2).
[14] Levinson, S. Presumptive Meanings: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15] Schiffer, S. Intention-based Semantics[J]. Notre Dame Journal of Formal Logic, 1982, (2).
[16]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Cambridge: Blackwell, 1995.
[17] 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8] 姜望琪. 会话含义新解[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 (3).
[19] 林允清.《Paul Grice——哲学家及语言学家》评介[J]. 现代外语, 2007, (2).
[20] 王晓飞. 论取消会话含义的潜在可能与实际发生[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 (3).
[21] 姚晓东. Grice意义理论中的意向与规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