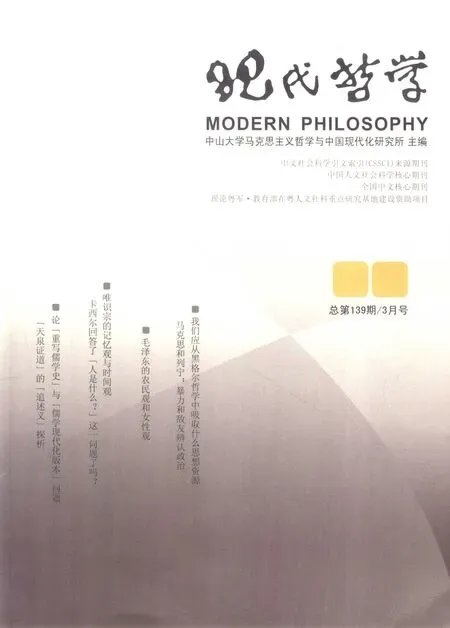仁爱的友谊观——论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的扬弃*
赵 琦
在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论述中,友谊主要是一种基于双方价值或善的亲密关系。①血缘亲情在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那里属于友谊讨论的对象,不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先天联系,因而构成对这句概述唯一的例外。参见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页。它不仅存在于我们今天称为朋友的那些人之间,也存在于任何互爱的人之间,父子、兄妹、夫妻之间的亲厚关系都属于友谊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阐发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友谊”范本之一,直到当代,哲学家们对友谊的讨论仍然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在亚里士多德的众多后继者中,阿奎那或许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位,不同于西塞罗等思想家,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独到的友谊观,使亚里士多德那里基于特殊价值的、少数人之间的亲密的爱成为一种以他人本身为目的的“仁爱”。然而,他的仁爱的友谊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包容并完善世俗友谊的主要特质的基础上对它的积极扬弃。阿奎那对世俗友谊的扬弃是否成功,不仅仅关系到他的友谊理论是否能够用于一般的人际交往,也关系到“仁爱的友谊”对现代人的道德实践和理论建树的价值。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第二部分从理论和思想史两个角度,展现阿奎那“仁爱的友谊”对亚里士多德友谊理论的否定,以及这一否定给阿奎那带来的挑战;第三部分证明仁爱的友谊是对世俗友谊的积极扬弃;最后,笔者将说明仁爱的友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是现代探讨友谊理论不可或缺的财富。
一、仁爱② “仁爱”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仁”,尽管两者的内涵具有想通之处。它在希腊语中为agape,在拉丁语中为caritas,英文中则是charity,可见该基督教术语具有漫长的历史,至今被人们广泛使用。——阿奎那友谊观的核心
阿奎那通过仁爱阐释友谊,他说“仁爱就是友谊”③ST IIaIIae.23.1.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标准我以ST代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IIaIIae是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对《神学大全》的注释法之一,这种注释法来自拉丁文的second a second ae,意思是第二部分的第二部分。取两个单词各自的含义,按其顺序用罗马数字表示,并与它们表示格的结尾-a和-ae结合,构成IaIIae。,其核心是神与人的友谊,该意涵也扩展到人与人的友谊。简而言之,阿奎那认为友谊是一种互爱关系,它始于一方以仁爱爱对方,让对方分享善的活动。因此理解阿奎那的仁爱,就能理解这种互爱关系,从而理解其友谊观。什么是“仁爱”呢?仁爱是一种以被爱者为目的的完善的爱,它不考虑被爱者已有的价值,是一种力图在被爱者身上创造价值或善的爱。因此,无论人们怎样偏爱朋友具有的诸种善 (美貌、才干、财富、德性),它们都不足以构成友谊的正当理由,只有对朋友自身的爱才是友谊得以可能的真正基础,对仁爱的结构性分析能清晰地阐明这点。
对仁爱的结构分析显示,每个仁爱的活动都是由两类不同的“爱”构成——“友爱”与“欲爱”。作为某种“爱” (amor),友爱与欲爱都是“那动向所爱的目的之运动的根本”①ST IaIIae.26.1.。也就是说,它们是在受到外物的刺激之后,在主动者内产生的趋向外物的“欲望”。“爱”作为一种“欲望”,以被欲望的东西为目的,不过对于人这样兼有理智和欲望的存在者,“爱”不仅仅是对目的的欲望,也因为目的的缘故,欲望达到目的的手段。阿奎那称对目的的爱为“友爱”(love of friendship),即“愿望一个人好”②ST IaIIae.26.4.;对手段的爱为“欲爱” (love of desire),这可以表达为“愿望让他 (她)分享自己的善”③ST IIaIIae.23.1.。只有同时具备两者,才构成仁爱。譬如,子女爱父母,他们以友爱所爱的是父母自身,出于对父母的友爱,他们会欲望 (爱)对父母好的事物,诸如健康的饮食、宽敞的居所,并以自己的能力让父母获得这些善,这就是“让父母分享自己的善”。综合仁爱的双重结构,对父母的仁爱是以他们自身为目的,尽力帮助他们获得各种善。由于目的因其本身为人所爱,友爱更加根本;手段由于目的的价值才为人所爱,因此欲爱必然依附友爱存在,是相对的爱。④ST IaIIae.26.4.
对于友谊而言,阿奎那认为对朋友的爱必须是以友爱为主导的“仁爱”,以欲爱爱他人不是真的爱对方,这样的人之间也不存在友谊。例如,为了小张的利益,我表现的和王冰亲厚,因为通过王冰,我能帮助小张。根据爱的结构,我以友爱所爱的对象是小张,因为该活动的目的是小张本身,为了小张的缘故,我以欲爱所爱的是小张可能获得的利益,那样无论我和小张是否互爱或具有友谊,我都不爱王冰。任何知道我的动机和目的的人也不会认为我爱王冰。王冰做为二阶手段成为我的欲爱的对象,他只是作为“小张可能获得的利益”这个“手段的手段”而被我欲望。因此,如果一个人因为利益的驱动而和另一个人亲厚,说他们是朋友,在阿奎那看来就好比说人和酒是朋友一样荒唐,因为正如人爱酒并不是为了酒本身,而是为了自己或他人能享用它,为了利益和他人亲厚也根本不是对对方自身的爱。
尽管在仁爱的友谊中,对朋友的友爱必须占据主导,但是缺少对朋友好的事物的欲爱,仁爱将不复存在,友谊也不复存在。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说明:第一,欲爱必然伴随仁爱。真的爱他人的人不可能不愿望他获得具体的善,只要能力允许,他会以自身具有的善为途径,帮助被爱者获得善。例如,父母爱孩子,也必然愿望孩子过得好,获得各种善,诸如身体健康、学业有成。而且只要能力允许,爱孩子的父母都会不辞辛劳地以自己的善 (诸如勤劳、财力、关爱)帮助孩子获得对他们好的事物。即使对于不太深厚的友谊,在对方需要帮助而自己的确有能力时,也多少愿意让对方分享自己的善,至少愿意为朋友献计献策。第二,如果没有欲爱,友爱不复存在,进一步而言仁爱也不复存在。如果对他人的爱没有欲求他人的善的实际维度,友爱就蜕变为一种抽象的愿望,一种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善意”(希腊语eunoia)的东西。“善意”尽管看似和仁爱具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善意是不动感情的。亚里士多德说:“善意也不是爱,因为它不包含倾向与欲求。”⑤N E 1166b32-33.此注释法是国际通用的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注释,NE代表《尼各马可伦理学》,不论该著作以哪种译本出现,均可以此法引用。只对他人具有“善意”的人不会愿望并帮助他获得善。在能力许可的条件下,不为他人谋求善的人不是真的以仁爱爱这个人。譬如对于某些完全具有工作能力的啃老族,无论他们如何甜言蜜语哄骗老人开心,在阿奎那看来他们都不是真的爱父母,因为他们不愿望父母获得基本的善——安度晚年。这样的子女对父母没有仁爱,也不可能和父母具有友谊。
综上所述,仁爱就是以被爱者为目的的爱,它不仅包含“愿望一个人好”⑥ST IaIIae.26.4.,还包含以自己的善为途径,以欲爱趋向对被爱者好的东西,即“愿望让他 (她)分享自己的善”①ST IIaIIae.23.1.。这两个愿望共同构成仁爱,缺一不可。在完善的友谊中,双方都以仁爱爱对方;如果一方完全以仁爱爱对方,对对方具有这两个愿望,另一方只要接受他,友谊就能发生,尽管只是不完善的友谊。这是因为虽然双方的付出不等,爱的意愿也有强弱之分,只要被动的一方接受对方的仁爱,就是不反对互享善的交往,而互享善正是友谊的活动本身。②这 个判断是符合常识的,但是阿奎那承认这种友谊的最初动机或许是神学的,在人神关系中,神以仁爱爱人,并给予人各种恩典 (即以欲爱爱对人是善的东西),人只要接受仁爱就是神的朋友。据此,人与人之间也能具有这种不对等的友谊。如果被爱者也能够以仁爱回报爱者,对爱者具有这两个愿望,那么以完善的仁爱互爱,就产生完善的友谊。
二、否定与挑战:两种友谊观的对峙
当代学界深受亚里士多德的世俗友谊观的影响,不少学者以其“世俗的友谊”作为现实中朋友关系的理论范本。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在根本观念与产生的思想背景方面,都与亚里士多德的友谊观截然不同。一方面,通过提出独辟蹊径的友谊观,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世俗友谊的否定;另一方面,对亚里士多德的友谊观深信不疑的学者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论对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两种友谊观似乎处于非此即彼的对峙地位。
(一)仁爱的友谊VS.世俗的友谊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友谊作为一种互爱其根基在于对价值或善的爱。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三类让人爱的具有价值的事物:道德的善、快乐和有用。他说:“只有可爱的事物,即善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的事物,才为人们所爱。”③NE 1155b18.基于这三种可爱的事物,相应的存在三种友谊——基于德性之善的好人之间的友谊、有用的友谊与快乐的友谊。可见,对价值的欲求是友谊的基础,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完善的友谊即以德性为基础的友谊中,朋友因对方自身之故爱对方,但是即便是这种几乎无私的爱,也以他人在道德方面的价值为前提。④最 直接的文本证据来自NE 1155b34-1156a5,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这种善意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 (对三类善的事物的爱)之一产生的”。
阿奎那反对以某种特殊的价值作为友谊的前提,主张以仁爱无条件地爱他人。因此,基于快乐与有用的交往不是友谊。阿奎那认为,人不能因为被爱者以外的原因爱朋友,不然就是以欲爱爱朋友,以欲爱爱人不是真的爱他人。他说:“利益及喜好的友谊,受到欲爱的牵动,有失真友谊的意义。”⑤ST IaIIae.26.4.因为对自己有用而和人交往是把他人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不符合仁爱,也背离仁爱的友谊。以快乐为目的和人交往不属于友谊,因为它不是为了他人自身之故“愿望一个人的善”,而主要是为了自己获得快乐愿望他人的善,如果自己无法从交往中获得快乐,就会中止友谊。
即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完善的友谊即基于德性的友谊,就其本质而言也不成其为友谊。因为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德性的爱让人爱对方自身,但是仍然是德性而不是他人的存在本身成为爱的首要对象和目的。仁爱的友谊能以坏人为友,让他分享自己的善,例如帮助坏人获得美德,而亚里士多德的世俗友谊却不承认好人和坏人之间可能具有友谊。亚里士多德这样解释“爱朋友”,根据这种解释,好人可以为了朋友自身的缘故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生命,因为好人爱真正的善或价值,为了获得真正的善,他们甚至可以以生命为代价去爱他人。⑥NE 1169a35-1169b37.由此不难看出,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自身的道德完善是最重要的,它比对他人本身的爱具有更基础的地位。但根据阿奎那的爱的结构,在这种“爱朋友”的行为中,好人真正爱的是自己,以欲爱所爱的是自己的善,朋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爱的目的,但是在根本上无法摆脱它相对于自我德性的从属地位。不然,就无需以德性作为友谊的前提。因此,就本质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好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阿奎那的友谊标准。
其次,除对价值的欲求和对他人无私的仁爱这一本质区别外,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朋友的亲密程度也具有不同的主张。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友谊必然是少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如果友谊基于价值,人们需要足够多的时间相互了解,确认对方具有自己重视的价值,从而决定是否与对方为友。①NE 1171a1-10,NE 1158a12-14.另一方面,就完善的友谊而言,一个人不可能与许多人相爱。亚里士多德说:“正如一个人不能同时与许多人相爱,因为爱是一种感情上的过度,由于其本性,它只能为一个人享有。”②NE 1158a9-12.而且,每个人的时间有限,如果将爱分给过多的人,会减少与每个人的交往时间,与他人的亲密友谊难以维持。
与少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相对立,仁爱从来不是只以少数人为对象的爱。仁爱面向所有人,我们可能同时愿望不同的人过得好,并且帮助他们获得对他们好的东西。如果对方不拒绝我们的仁爱和帮助,友谊就会产生。仁爱本身没有规定交往必须如何深入,朋友的关系必须如何亲密,而只是规定要以对方为目的愿望他们获得善。由于两种友谊观念在对价值的爱与亲密关系方面相互对立,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似乎完全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世俗友谊。
(二)思想史的维度
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与仁爱的友谊具有截然不同的思想史背景。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理论产生于希腊的古典时期,城邦已经出现并成为公民生活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讨论部分来自对公民友谊的观察,这种关系多少带有契约的性质,人们因为共同的目的和需要走到一起。另一方面,高尚的公民在因城邦事务交往的时候,会为其他公民的德性所打动,在共同的事业中培养出高尚的友谊。
虽然身处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讨论仍然受到更早的传统社会友谊模式的影响。在希腊传统社会中,氏族或部落成员之间具有更为牢固的友谊。亚里士多德屡次提到“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它是希腊的古老谚语,具有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内涵。部落成员之间会把他人看作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他人因此成为“自我”,爱他人就是爱自己的身体。以《伊利亚特》为例,当阿基里斯听闻好友帕特罗克洛斯战死的消息时,悲痛地将自己的朋友称为“自我” (ison emēi kephalēi),其字面意思是“等同于我的头颅”。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讨论受到古典希腊社会的公民友谊和传统社会友谊典范的双重影响,前者使他对友谊的理解具有政治化的维度,后者让他赞同友谊的排他特质,肯定友谊是极少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阿奎那以仁爱诠释友谊,其核心“仁爱”来自基督教的传统。在阿奎那之前,西方世界早已存在将基督教的仁爱等同于友谊的做法。《圣经》记载基督用朋友来称呼他的门徒:“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③《约翰福音》15:15他告诉门徒要像他爱门徒那样互爱,然后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④《约翰福音》15:14。根据这些记载,“朋友”被用在以仁爱互爱的基督与信众,以及信众与信众之间。
然而,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而言,《约翰福音》中提到的“朋友”不是在描述一般意义上的友谊,它描述的是与世俗友谊相区别的另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只可能在信徒中发生。正因此,尽管中世纪的神学家能通过西塞罗接触到亚里士多德式的“世俗的友谊”⑤这 里指的是西塞罗的De Amicitia(《论友谊》),他的友谊观念虽然和亚里士多德不完全相同,但是继承了其中的核心思想——基于德性的好人间的友谊。该著作的中文译本可以参考[古罗马]西塞罗:《论友谊》,王焕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他们并没有将仁爱与世俗的友谊联系起来,而是努力避免把西塞罗的“友谊”和基督徒的仁爱混为一谈。譬如,被誉为大师的伦巴第(Petrus Lombardus,约1096-1164)在谈论仁爱时就小心避免用“友谊”这个词。⑥相关历史参阅Francini I.,“‘Vivere Insieme’,un aspetto della‘koinonia’aristotelica nella teologia della carità secondo san Tommaso”,Ephemerides Carmeliticase 1974(25),pp.275 - 278.以及 S chmitt,Ch.B.,“The Rise of the Philosophical Textbook”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792 -804.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约1200-1280)非常熟悉《尼各马可伦理学》,他是该书完整拉丁译文面世后的第一批具有基督教信仰的评注者,但即便如此熟悉占据该书五分之一篇幅的世俗友谊观,阿尔伯特也没有把它与仁爱联系起来。①该段历史参考Francini,1974。根据他的看法,《尼各马可伦理学》由英国林肯地区的主教格罗斯泰斯特 (Robert Grossateste)于1246-1247年翻译成拉丁文,在这之前一位无名氏曾经在十二世纪末第一次将该著作翻译为拉丁文,只是后来散落只留下了前三卷,叫做《伦理之书》(Liber Ethicorum)。读者或许还需知道中世纪的神学家大多不会希腊语,阿奎那本人也应该不懂希腊语,至少无法阅读希腊语的哲学著作,他主要依赖其好友穆尔伯克的威廉 (Willem van Moerbeke)为其翻译。
由于“仁爱”与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在理论及思想背景上的巨大差异,在阿奎那之前,很少有人将“仁爱”用到世俗的友谊中。阿奎那大胆地提出“仁爱就是友谊”,其意图并不是以仁爱的友谊简单否认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而是让仁爱的友谊成为扬弃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的一般意义上的友谊。
三、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的积极扬弃
仁爱的友谊同世俗的友谊存在不小的差异,但是它并不是对世俗友谊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其主要特质的包容与完善,从而赋予友谊更牢靠的基础。一方面,尽管以被爱者本身为目的,仁爱完善基于特殊价值 (德性、有用和快乐)的友谊;另一方面,面向所有人的仁爱让亲密的友谊更为持久。
(一)“仁爱”完善追求特殊价值的“友谊”
仁爱完善世俗友谊对特殊价值的追求,可以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论证。首先,尽管仁爱的友谊以朋友的存在本身为目的,但是它并不完全否定对特殊价值的欲求,而是主张不可本末倒置,忽略各种特殊价值的来源——人本身。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都赞同人的存在是德性、有用等一切属性的前提。因为人是实体,德性是属性,属性只能依附实体存在。如果离开存在本身,任何属性都不复存在。因此,人本身比包括德性在内的任何特殊价值更为根本,即使一个坏人的存在在原则上也比各种属性(包括德性)具有更高的价值。
其次,在本末顺位的情况下,仁爱的友谊能包容人们对特殊价值的欲求。阿奎那不反对享受朋友具有的各种特殊的价值,他反对的是只以这些价值为交友的动机和最终目的。人可以在仁爱的前提下爱他人的特殊价值——无论是较高的价值道德的善,还是较低的价值,诸如快乐或有用。既然友谊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么顺理成章“人”应当成为友谊的对象和目的,以他人的价值为爱的目的是和某个价值为友。就像“人和酒做朋友”是荒唐的,人也无法和某个价值做朋友。既然人只能和人做朋友,那么以人本身为目的的仁爱就应该成为欲求特殊价值的前提。在仁爱的友谊中,人可以享受朋友带来的利益和快乐,也能通过分享朋友的高尚人品,促进自我的道德完善。
以基于德性的友谊为例,很容易说明在两种不同的友谊模式下,人们欲求特殊价值的区别。人们都愿意和好人做朋友,但是这可以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动机,它们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一种情况是我觉得和好人在一起自在,因为好人会对我好,更能包容我的缺点,不需要小心维持,友谊也能持续。而且从好人身上,我能了解到获得德性的方法,从而帮助我获得道德完善。这种情况不是出于对具体利益的欲求,而是笼统地愿望通过他人的德性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帮助。这种关系尽管具有友谊的表象,却和阿奎那认同的友谊相去甚远。阿奎那认同的友谊是另外一种情况:爱对方,愿望在与他的相处中帮助他获得善,并为他获得善感到真心的愉悦。在爱和帮助朋友的过程中,爱者的道德自然而然得到提升,因为没有什么比以无私的仁爱爱他人更属于完善的德性。然而,道德的提升是仁爱的友谊自然产生的效果,而不是友谊的目的。
最后,以仁爱为“友谊”的内涵让世俗的友谊理论更加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无论爱者爱朋友哪种特殊的价值,仁爱都可能让人更好地获得这个价值;第二,仁爱可能使各种不完善的友谊成为真正的友谊。这可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类友谊的分类综合来解释。首先,对于有德性的好人朋友,以仁爱爱他让自己更容易获得价值。仁爱要求人将关注从自我转到被爱者身上,发现对方真正需要什么,找到帮助他获得善的途径。阿奎那认为这是深入他人内心的过程,它让爱者在知觉层面进入被爱者中。他说:“爱者在被爱者中,是由于对被爱者不只有表面的知觉,并设法探究属于被爱者的每件事情的内情,这样进入他的内部。”①ST IaIIae.28.2.对于自我品质的提升而言,很少有比深入一个高尚的内心更为有效,它给予人活生生的道德体验,就好像自己经历了这些事情。显然爱者能从这样的友谊中更好地分享好人朋友的德性。
对于亚里士多德那里不完善的友谊 (以有用和快乐为基础的友谊),阿奎那是否主张将它们彻底排除出友谊呢?答案是否定的。仁爱完善任何友谊,哪怕它们只是基于快乐和有用的友谊。对于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利益的伙伴,愿望他们获得善,就会更尽心地为对方的利益考虑,向双赢的局面努力,这样的人更容易获得信任,交易也可能会更加顺利。进一步而言,无私的爱他人也可能激发他人对自己的仁爱之心,从而获得真正的友谊。对于那些说话风趣、常常给我们带来轻松愉悦的伙伴也是如此。无论他们的道德如何,以仁爱爱他们,可能让彼此之间产生真正的友谊。一个风趣的人如果把我们当作朋友,会更愿意让我们分享他的风趣,因为他愿望我们快乐。因此,仁爱可能让重视快乐的人获得更多的快乐。
有些学者或许会质疑仁爱如何在生意伙伴,甚至一切朋友中作用。他们会问,如果无条件地爱对方,岂不是要放弃一切应得的利益?若是遵循这样的原则,还怎么做生意?即使对于非生意上的朋友,也不可能一味满足对方。这种质疑来自对仁爱的误解。仁爱虽然是不计回报的愿望他人的善,但是这并不等于无原则地满足对方的要求,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首先,仁爱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质利益,所以无条件地爱的对象也只是人。尽管对他人的善的欲求附属于对人的爱,而他人的“善”在一定程度上包括物质利益,但是这不等于无条件地给予其物质利益。其次,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善,最重要的是帮助朋友获得最高的善、幸福。在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传统中,幸福主要来自道德的善。如果为了满足对方的物质要求,而让他们丧失磨炼意志、提升道德品质的机会,这不是真的愿望他人的善。在阿奎那看来,只有当人愿望他人获得的善符合最高善的时候,才是仁爱,不然即使自以为为他人牺牲一切,也根本不是仁爱。第三,仁爱不排斥公正,它也不排斥某个具体角色对责任或义务的要求。即使朋友之间也可能有交易,当他们代表各自的公司接触的时候,必须遵守基本的商业道德,没有理由无条件地向对方退让。而且,真正的朋友会愿望对方好,这也包括愿望对方对工作尽忠职守,做一个有职业道德的人。因此,以仁爱爱朋友的人不会对朋友提出有损其道德的要求。
(二)仁爱让友谊更持久
既然仁爱的友谊不要求他人具有任何特殊的价值,它就是一种面向所有人的友谊。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完善的友谊只能存在于少数人之间,他甚至说“常为人们歌颂的友谊都只存在于两个人之间。与许多人交朋友,对什么人都称朋友的人,就似乎与任何人都不是朋友”。②NE 1171a14事实上,仁爱的友谊不排斥亲密的关系,而且还能加强友谊的亲密程度,可以通过三步加以论证。
首先,“仁爱的友谊”虽然面向所有人,但是这不是说事实上与所有人为友。面向所有人突出的是仁爱的无条件的特质,由于这个特质,对对象没有特殊的规定。因此,就潜在性而言,人可能以仁爱爱任何人。具有仁爱这一美德的人准备让他人分享自己的善,因为他愿望别人好,也愿望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善。但是就现实性而言,仁爱的友谊只能在少数人之间实现,任何人都不可能让无穷多的人分享自己的善。但是这不是仁爱者的意愿所致,而是客观条件所致。友谊是双方的事情,既受到爱者的时间和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被爱者意愿的限制。即使爱者具有与所有人交友的愿望,仁爱的友谊也只可能在少数人之间实现。对于大多数从未谋面的人,仁爱只能停留在愿望的层面,在潜在的意义上向陌生人敞开。因此以“和所有人的友谊根本不是友谊”为理由,无法驳倒仁爱的友谊。
第二步,仁爱的友谊并不削弱友谊的亲密程度。正如廖申白所言,亚里士多德使用的“亲密”是彼此对对方具有深厚的感情或爱。③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4页。无论历史上思想家们如何理解仁爱,在阿奎那那里仁爱确有亲疏之别,因为仁爱作为友谊不仅是人的内心感受,也受到对方与自身关系的影响。阿奎那认为,根据仁爱,人应当更爱那些与自己关系更近的人。他以十三节 (文章)①《神学大全》由三部分组成,每部分下由许多“问题”Quaestio组成,每个问题由“节”articulus组成。每一节讨论一个小问题,由“质疑”,“反之”,“正解”和“释疑”构成。这个“节”不是汉语中所说的“小节”,其篇幅远远大于小节。的篇幅详细讨论仁爱的次序,例如是否应该最爱和自己具有血统关系的人、是否应该爱父亲胜于子女、应该更爱施恩者还是受恩者等等。他主张,“仁爱应该先是对于那些与我们更为亲近的人,然后才是对于那些更善的人”②ST IIaIIae.26.7.。“更为亲近的人”就是一般意义上与人具有先天或后天联系的那些人,而“更善的人”是那些不太熟悉或交往不多的好人。在这里,人对不同的对象都具有以对方为目的的仁爱,差别在于强度。阿奎那认为对自己的父母、兄妹、好友应该具有更强烈的爱,与他们的友谊也应该更亲密。可见,根据仁爱,人能够也应该和某些人具有更为亲密的友谊。
在这里,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常识中一直被看作“一视同仁”的仁爱居然也有亲疏之别!这是阿奎那向世俗友谊观妥协的结果,还是仁爱的应有之意?阿奎那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仁爱不仅仅遵循被爱者与其对象即至善天主的远近,也遵循被爱者与爱者的远近,恰恰是后者决定了仁爱的强弱,从而决定友谊的亲疏。他说:“一个人对待那些外人,和对待那些与之有着特殊友谊里联系的人,所有的亲和方式并不一样。”③ST IIaIIae.114.1.仁爱者愿望每个人得到善,但是其愿望的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爱者与被爱者的关系,人可能因为先天或后天的“特殊联系”和某些人具有更亲密的友谊。阿奎那所说的“特殊联系”包括亲属关系,也包括朋友关系。例如,对于政治家而言,这种特殊联系可能就是政见一致;对于学者而言,或许是志同道合;对于商人而言,可能是互利互惠。对于和自己具有这些联系的朋友,友谊会更紧密。可见,阿奎那对仁爱次序的论述不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妥协的结果,而是考察爱的活动本身得出的结论。
第三步,仁爱的友谊能让友情更加牢靠,让亲密的友谊更持久。这是因为仁爱让朋友更能经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个问题的根本是友谊的持存性。亚里士多德的三种世俗的友谊中都存在亲密的关系,因利而合的朋友会在得到预期回报的时候关系亲密,由于快乐结合的人会享受对方的陪伴。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种友谊中的亲密很难持续,只要双方的所得不再相当,友谊就会很快中止。他说:“在快乐的友爱与有用的友爱中,也只有在双方都得到了同样的东西,如快乐,并且在同样的事物上得到同样的东西——如两个机智的人的友爱的情形——时,友爱才能保持。”④NE 1157a1-5.即使在完善的友谊中,只要双方的德性不再相当,例如一方变得很好,友谊很可能无法继续。⑤NE 1165b12-24.而且即使是好人朋友也不会愿望自己的朋友变的太好,因为友谊无法抵御过大的差距。⑥NE 1159a1-10.
仁爱的友谊不要求彼此的所得或德性具有任何一种“相当性”,这些“相当性”包括对方与自己的德性相当,得到的利益或快乐与付出相当,甚至在同样的事物上获得快乐。因为仁爱的根本是让对方分享自己的善,如果条件允许也分享对方的善。不过建立在仁爱之上的友谊,注重的是共享善,尤其是共享真正的善,不太可能只因为物质利益或快乐就变的过于亲密;但是对于自己的密友,当他犯下错误的时候,不会轻易放弃他。无论朋友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仁爱的友谊都要求尽可能帮助他克服,如果他没有勇气就要让他产生勇气。母亲对待孩子的形象是仁爱的友谊的典型⑦在古希腊与欧洲中世纪的学者看来,母亲与孩子的互爱也属于友谊,本文篇首就说明了这点。,她不求回报,不因子女的过失或错误放弃对子女的爱。对于母亲而言,孩子的存在具有最高的价值,丧失任何特殊价值,哪怕是德性都无法抹去孩子的存在本身的意义。以仁爱爱朋友的人不可能不愿望朋友好,也绝不会嫉妒朋友变得过于高尚,而是会为他的成长感到真心的愉悦。鉴于以上三步论证,仁爱不会破坏朋友之间的亲密,相反,它让亲密的友谊更持久。
综上所述,虽然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与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但是以仁爱为核心的友谊理论能够经受世俗友谊观的挑战,而且以仁爱诠释友谊的做法使得友谊更加完善,让亲密的关系更加持久。在这种意义上,阿奎那完成了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的积极扬弃。
四、跨时代的友谊观及其当代意义
尽管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阿奎那的友谊观得益于基督教信仰和天主教教义传统,但是阿奎那的探讨是以一般的友谊为对象,其友谊观因而能够承受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世俗友谊理论在内的各种挑战。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严密的理论论证,阿奎那将中世纪特别注重的德性“仁爱”建筑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并以此说明人的友谊应该具有的样态。尽管仁爱的友谊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却是任何社会和人种的人之间都存在的情感,为任何时代的人所向往,也值得所有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强调的无私奉献精神就是仁爱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以仁爱诠释友谊,但是他也曾颂扬朋友之间无私的爱。他欣赏古代希腊社会将友人看作分离的自我的做法,屡次提到“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在《欧台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以这句脍炙人口的谚语说明人应该像爱自己那样爱朋友。①如果深究,这种爱尽管与仁爱有些相似,但是仍然是不完善的,因为它需要以对自己的爱为中介,才能达到对朋友的爱。这部分的讨论,受到古典学者 Stern-Gillet的影响。参考Stern-Gillet,S.,Aristotle's Philosophy of Friendship,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12.因此,尽管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传统和理论径路,亚里士多德对仁爱的友谊具有超越时代的渴望。
作为超越其时代的友谊理论,“仁爱的友谊”也对当代的理论探讨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目前英美学术界普遍受到亚里士多德友谊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从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论获得灵感,将友谊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以价值作为友谊合理性 (Justification)的标准,笔者称之为“友谊价值论”。②类似的著作和论文很多。例如 A nnis,D.B.,“The Meaning,Value,and Duties of Friendship”,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87(24),pp.349 -56;Whiting,J.E.,“Impersonal Friends”,Monist,1991(74),pp.3 -29;Sherman,N.,“Aristotle on Friendship and the Shared Life”,Philosophy& P 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87(47),pp.589-613.这种观点固然揭示了友谊的某些方面,但是正如另一些学者指出的,它无法解释友谊的不可替代性。③例如,见 Stump,E.,2006,“Love,by all Accounts”,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2006(80),pp.25-43.对此,笔者撰写论文系统地批驳以价值作为友谊的基础。参见赵琦:《论友谊的正当性——一个托马斯主义的回答》,《哲学分析》2014年第5期。在现实生活中,友谊的变化常常不伴随价值的变化。即使人们发现一个陌生人具有自己更重视的品质,甚至他在各个方面都好过自己的朋友,人们可能还是更爱自己的朋友。以父母与子女的友谊为例,别人的孩子即使比自己的孩子更礼貌、更温和、更聪明,人们还是愿意与自己的孩子具有更亲密的友谊关系。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话,“他(她)的确没什么缺点,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他(她)”;我们也时不时遇到这样的情况,说不出一个人好在哪里,却很享受与他的交往。这些实例都说明对价值的欲求与友谊的互爱并不完全等同,价值也不足以解释友谊的动机。这是亚里士多德友谊理论隐含的问题,它被当代哲学家以更突出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当代探讨友谊最棘手的理论困境。
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将基督教的仁爱观念用于“友谊”。弗里德曼认为对价值的爱不是对人本身的爱,友爱是要赋予被爱者价值。④Friedman,M.A.,“Friendship and Moral Growth”,Journal of Value Inquiry,1989(23),pp.3 -13.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友谊自身就具有价值,例如,舒曼强调被人疏忽的友谊活动本身的价值。⑤Schoeman,F.,“Aristotle on the Good of Friendship”,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5(63),pp.269 -282.但是,他们都只是受到基督教仁爱观念的影响,没有系统地考察仁爱和世俗友谊的关系,尤其是无私的仁爱与追求特殊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足以解决当代学界陷入的困境。然而,当代学者努力挣扎的问题,阿奎那早就给出过答复。由于对中世纪哲学的忽视,以及对阿奎那解读的偏差等一系列原因,阿奎那的仁爱的友谊始终没有引起当代哲学家的充分重视。如果继续阿奎那的道路,阐发仁爱如何扬弃“世俗的友谊”,就可能调和无私的爱与友谊价值论,提出让友谊走向德性的更完善的友谊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