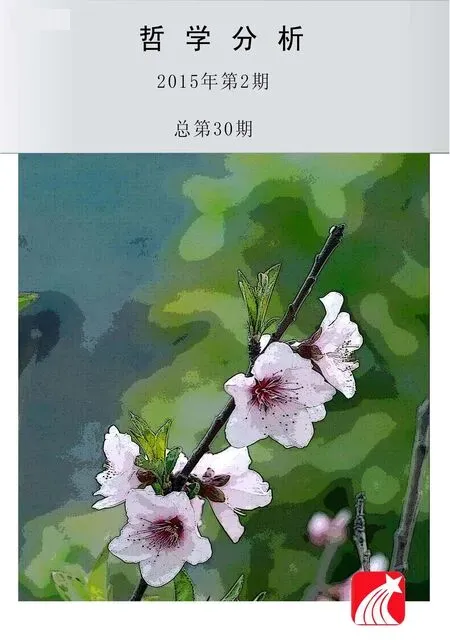我们怎样才能幸福:康德与今天的中国
——艾伦·伍德教授访谈录①
李明洁 [美]艾伦·伍德
我们怎样才能幸福:康德与今天的中国
——艾伦·伍德教授访谈录①
李明洁 [美]艾伦·伍德
编者按:当代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价值系统却遭遇了迷惑乃至混乱。对于很多已经不同程度上富裕起来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今天我们怎样才能感觉到幸福?或者问得更直接一些:有了钱以后为什么还是感觉不到幸福?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道德?我们该有怎样的信仰?两百多年前(后世称之为“理性时代”),德国哲学家康德针对当时欧洲遭遇的信仰迷局予以了系统的哲学反思。重温康德关于幸福、道德和理性的论述,对于遭受类似精神危机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无疑是适切的而且及时的。就此,华东师范大学李明洁教授采访了康德专家艾伦·伍德(Allen W.W ood)教授。
伍德教授是欧美德国形上哲学和康德研究的一流学者。曾先后任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和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是剑桥版《康德全集》的编辑和其中多卷英文版的译者。代表作包括《康德的道德宗教》(1970)、《康德的理性神学》(1978)、《卡尔·马克思》(1981,2004年第2版)、《黑格尔伦理学思想》(1990)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2014)等。
李明洁(以下简称“李”):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本能。康德说:“一切希望都是指向幸福的”,“幸福是对我们一切偏好的满足”。但是康德又指出:“人们不能按照确定的原则行动来成为幸福的。”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幸福感却没有如期而至。在康德看来,为什么实现幸福是非常困难的呢?
艾伦·伍德(以下简称AW):依据康德的观点,幸福是我们对所希望的生活的一种理想,是依据理性和想象创造出来的。它基于经验性的期待或者偏好。这种理想部分源于我们的自然本性,但是也受制于社会属性,尤其是我们对于名誉、财富和权力的需要,因为这些会让我们有优越感。康德认为天性并不是有意识的作为,但是天性的形成却是与之相符的自觉的结果。动植物的器官都适合它们的生存和繁衍。一般而言,每类物种都尽力将它们的自然素质发展到极致。人类也是一类自然物种,但却是“理性”的物种。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才智和活动不为其本能所限,而是能更远地发展自己的才智,创造自己的天性,并把这些才能传递给下一代。物种尽力发展的自然准则使得人性最终包含了不同的价值。这就是说,人类依据不同的目的来发展各自的天性,代代扩展相传,以致人类的天性没有终点可言,而是永远在发展的过程中。
天性为这种无止尽的发展提供了两种途径。第一,它让我们感到不满足。我们无法形成关于幸福的最终和一致的概念。因为如果我们一旦有了这样的概念,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它,就失去了进一步完善物种属性的动力。作为一类理性的物种,幸福是我们自我设定和向往的终点,但是天性却让我们永远无法达到这一目标。你可以这样想:我们之所以有形成自我幸福观念的能力,就是为了确保我们将永远“不幸福”。天性让我们总有“部分的不幸福”,这样我们才能在与其他同类竞争的时候保持较高的地位。第二,我们都有“非社会性的社会性”(这是康德从蒙田那里借来的说法)。我们是社会性的,所以我们需要他人。但是我们的社会性却是非社会性的,因为我们需要他人的那些部分正是他们优于我们的,而且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我想优于你,而你又想优于我。我们部分的幸福感正是来源于这样的优越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的某个人是幸福的,其他的人就会不幸福。而且,造化如此就是为了人类的才智能得到无限的发展。我努力进步以便优于你,你努力发展以便优于我,并传给下一代。没有人达到了他所追寻的幸福,然而人类却丰富了才干,一代超越了一代。
李:由此看来,“不幸福”本是人生常态。显然,在康德眼里,“我们的幸福观念终其一生都在变化之中,当我们改变自身需求的意念时,就会产生新的欲求,因此,真正的幸福,即完全的满足,总是无法达到的”。那么,就幸福的特质而言,我们是否可以说,直接以幸福为目标或指向的追求,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呢?
AW:恐怕不能完全这么说。幸福并不是那么绝不可能,难以实现。尽管天性如此,但天性也发展我们的道德能力,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真的比其他人高级,每个人都有尊严,有各自将要到达的不可比较的目的。因此我们会发现“非社会性的社会性”是一种不道德的倾向:我们不应该追求优于他人,而应该独立地因而平等地评估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价值。社会习俗给予某些人更大的权力或者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荣誉,从根本上讲这是不道德的。人类的道德进步包含着对这类旧习的抗争。
康德认为,我们应该追求的不应是最大的幸福,而应是康德所称为的“理性的幸福”,即:我们理想中的幸福应该是与道德相匹配的,能使我们值得幸福,能将自我和他人都作为目的,能有人的尊严。这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幸福(如果他人能被允许和我们拥有同等的幸福的话),恐怕这才是我们任何人至少可以指望的最大的幸福。
李:按照康德的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偏好的满足而获得幸福,应该追求符合道德的“理性的幸福”。然而,他又明确指出:道德与幸福是完全不同质的范畴。这似乎正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困惑:经济突进,价值多元,人员流动;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当下性和功利性。道德及其规约系统正在面临挑战或者已然崩溃。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道德?也就是说,实施道德行为的“意志”从何而来呢?
AW: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愿望成真,因为我们的愿望很可能都不能自洽。我希望这个,得到了,可能另外的一些我就不可能得到了。我也许希望得到所有人的敬重,又希望他们能爱我。但是,如果他们敬重我,他们就会高看我;反之,他们就会觉得我可以被利用,从而看轻我。所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同时,在人类竞争的情形下,如果我从他人那里得我所愿,他人也就无法同时得到我的敬重和爱。
道德准则告诉我去行动,也告诉我去感知和希望,我愿意他人也都能够按照天理去行动、感知和希望。天理要我们将每一个理性存在者视作有内在尊严的目的,并追寻“目的王国”——那将是理性人类的理想的共同体,在那里所有的目的是建成一个和谐的社区。没有人的目的建立在他人的损失之上,而是大家分享各自的目标。最终我们将有一致的追求,我们将只追求“理性的幸福”,并帮助他人去追求他们的“理性的幸福”。
很清楚,我们将幸福的实现建立在他人的损失之上是不“需要”道德的。但是,将幸福建立在他人的损失之上的做法,从整体而言,将是无人可以幸福的毒药。如果我们只追求“理性的幸福”,那么我们需要道德来告诉我们哪些幸福属于“目的王国”,哪些则不在此列。通过追求“理性的幸福”,我们才可能实现属于“目的王国”的幸福。
李:在您看来,道德的必要性是针对“目的王国”而言的,它与人的尊严相关联。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确实反复提到这个“目的”:“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但是,您也指出,幸福与道德并没有内在的因果性,有时甚至不能两全。如果人们置“目的王国”于不顾,只是想以幸福和快乐作为自己的目的呢?当前很多人似乎就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呀。
AW:让我现在从另一个进路来谈谈幸福的观念和如何快乐。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歌剧《三便士》中有这样一首歌,翻译成英文是这样的:“不要在幸福的后面追得太快,因为幸福追在你的后面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在幸福的后面跑得太快,幸福就离你更远,永远追不上你了。所以,为了快乐,不要追逐你自己的幸福。要有一些其他的追求——做好事,做有意义的事,谋求他人的幸福,等等。如果你不追逐幸福,你就会幸运地被幸福追上。你也许都没有留意,因为你忙于更重要的事情呢。但是你最终获得了快乐。
你听说过“长勺子”的寓言吗?这是个关于来世的故事,说的是天堂与地狱。据说它的作者是罗姆斯朔克(Romshishok)的哈姆拉比(Rabbi Haim),立陶宛的一位犹太游走传教士。不过,在亚洲和西方的不同文化中都有相似的寓言。
寓言是这样的:天堂和地狱是一样的。人们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桌子中间是美味佳肴,仙境美食,每个人分有一把勺子。(我想在中国的版本里应该换成筷子。)但是勺子太长了,都到桌子对面去了,而且折不回来。所以,没有人能替自己拿到食物。天堂和地狱的唯一差别是:地狱里的人都很自私,他们挨饿,悲惨极了。他们唯一的快乐是对他人的厌恶、仇视和看到别人受苦。天堂里的人们不自私,他们喂对方吃饭,每个人都很快乐。他们之所以快乐是因为吃到了仙境美食吗?还是因为他们看到别人开心地吃到了他们喂的美食呢?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无所谓了。
事实上,我根本就不认为这个寓言是关于来世的。我认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哪里的人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哪里就是地狱。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特别是美国,强大和有实力的少数人是自私的(我不认为是大多数人),贪婪卑鄙的,敌视不同于自己的人。他们认为人都应该自私自利,当有人提出谋求公益时,这些恶人就会想:“他们就是一撮儿想从我这里骗东西的乞丐。”中国的将来也会是这样的吗?
但是哪里的人们助人为乐,也乐于接受他人的帮助,哪里就是天堂。这样的世界,人类就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或者如费希特所言,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自私的人只为自己谋幸福。但是自私的幸福是没有价值的。自私的人不配得到快乐,而终将付出代价。人们只有在自己的幸福之上,还顾念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才有机会成就一个快乐的世界。
幸运的是,确实存在很多高于一己之幸福的更重要的事情。康德认为,以一己之幸福(哪怕是“理性的幸福”)为参照的生活将使理性存在者遗漏生活中更重要、更有价值之处。康德认为人生在世不是为了享乐的。我对这一看法没有把握,但是我很肯定的是,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不仅仅是为了追逐一己之幸福。如果你只索要幸福,那么你将不配有你已经得到的幸福,你的生活将失去你本已经得到的最大的价值。本性并没有让我们只追欢逐乐,而是注定要我们去找寻那些远好于一己之幸福的事情。
李:看来,您认为仅仅追求一己之幸福,于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是非理性的,都有生命价值的贬值之虞。那么,人生在世的最大价值应该是什么呢?
AW:我们最大的价值在于锻炼自我理性自治的能力。这种能力给我们尊严,这种锻炼将使我们配得幸福。成为有德之人将使我的“自我(我是谁)”获得价值和意义,即:幸福是我的境况或境遇的唯一意义,我的快乐与否皆源于此;而不是对自我渴望的满足,也不是与他人去比较财富、权力的大小和荣誉的高低。
当我能认可作为理性存在者的真实价值时,就会发现作为人的价值无疑将高于境况或者境遇带来的价值。人生在世只追求享乐是可怜虫的借口。道德不是“为了幸福”才去追求的。道德有其自身的理由,因为它无疑比幸福更有价值;而你遇见幸福的唯一机会只会存在于实践道德行为的过程中。
在我们身边看到的大多数人都在追逐自己的幸福,都在损人利己,都把他人当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这样的社会必将不快乐。从根本上来看,这类社会中人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并没有领会到自己最大的价值所在。他们没有价值地活着,因为他们没有为自己的道德属性赋值,而这是唯一能给他们的生命以意义的东西。
美国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曾经说过:“乌合之众都生活在无声的绝望中。”他是说:比不快乐的生活更糟糕的,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生活。当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无意义的,他们心无旁骛地追名逐利,而这正导致了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而且如此绝望。
李:中国目前有一个特异的现象:一方面道德迷惘,另一方面各种所谓的宗教活动却或明或暗地盛行。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里说:“道德不需要以宗教为前件,宗教却要以道德为基础”。相比起来,后一句话更难理解。康德认为宗教是建立在道德的废墟上的吗?或者说,宗教是出于道德的需要而建立的吗?
AW:康德,在他的时代,曾力图将道德理性与从欧洲继承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结合到一起。今天的康德哲学往往忽视这一点,而且与康德思想中的以下方面也鲜有关联。康德告诉我们必须以至善为宗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相信上帝。但是康德强调,道德的价值以其自身为目的,不只是取悦上帝的手段,不是顾忌到有人会奖善惩恶。上帝的奖惩观和信仰是康德继承的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他的目的是改造它,从而使人们能够看到道德自身的内部价值,而不仅仅是取悦上帝并获得奖励的手段。
康德看到,即使在教义的内部,奖惩观也具有自我消解性。因为如果上帝真的会因为我们道德良好而表彰我们,他就没有理由去表彰那些仅仅为了得到表扬而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的人,因为这些人并不是好人,也不值得表扬。因此,道德不能被连带着想象为取悦上帝之道。上帝自己必须看到道德行为本身的良善,它能自我取悦并且值得去做。当你这么去看待事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宗教(也就是康德所谓“将所有的义务认作是神的旨意”)必须以道德为基础,而不是道德以宗教为基础。
李:就康德宗教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而言,有彼此对立的两种立场:传统性的诠释(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与肯定性的诠释(affirmative interpretation)。传统性的诠释主张:康德的宗教哲学摧毁了人们心目中的上帝,其代表人物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砍掉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但是,肯定性诠释认为,康德宗教哲学与传统神学及其教义是相当契合的。您作为后者的代表人物,如何看待“传统性的诠释”派的观点呢?
AW:也许我可以谈谈康德自己与宗教的关系,以便帮助大家理解。康德在严格的基督路德教虔信派的家庭中长大。18世纪常被称作欧洲的“理性年代”,但是也是宗教狂热复活的时期,如英国的遁道派与贵格派、德国的虔信派和中欧犹太人的哈西德派。“理性年代”也是当时的智者反抗身边这些宗教运动的时代,他们反对以宗教狂热取代生活中的理性。
康德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他的壮年时期,康德表面上看并不是一个教徒。他从来没有说过虔信派是好的。甚至当大学的教职要求他参加科尼斯堡天主教堂(K觟nigsberg Cathedral)的宗教活动时,他也拒绝那么做。在那些场合,他总是“不舒服”(通常,这个词的意思是“生病”,但是也许是“我不愿意”)。
康德认为宗教礼拜、赞美上帝、匍匐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在神职人员面前宣誓信仰,这些都是对上帝的“虚情假意”。在康德看来,对上帝的真正崇拜,是你尽到为人的义务并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是他拒绝参与宗教活动的道理。
虔信派认为,为了得救,你必须经历“重生”,必须感受到神的恩泽清除了你的罪恶并将你变成新人。我想,康德小时候肯定见过很多虔信派教徒哭喊着表达他们的忏悔和喜悦,声明他们感受到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上帝之手,经历在基督里的重生。但是第二天他们又变回了从前的有罪之人,照样贪婪、吝啬、下流,尽管他们确信他们已经“得救了”并且“重生了”。这样,在原有的恶习之外,他们又多了自大和自负的恶习,他们的“重生”使他们变得更坏。康德成熟的哲学思想否认我们可以对超验的事物有经验性的意识,他把宣称这样意识的人称作“狂热分子”(Schw覿rmerei)。
康德特别反对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当你公开宣布如此这般的时候,有多少机会真是这样的呢?你真的相信吗?不少教条的内容难以让人相信甚至理解。这样说甚至是中肯的。你要去相信你不能理解的东西;或者你不仅不理解,甚至对自己是否相信也不确认。那么,当你在宣称信仰的时候,你近乎是在撒谎——对你的教友、你自己,甚至是上帝。所以教义在教人们撒谎,或者说是,你并不理解你该去相信的东西。也许当你懂得更多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完全不相信了。所以,教义和信条在鼓励你不去思考你之所信。安全的做法是让那些被要求死记硬背的教条“变成”你所相信的。你不让自己去想在这些“话语”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信仰,尽管你都不理解它们。但是你不能容忍自己和他人对那些信条有任何的怀疑,只能接受那些愿意那么说的人,说他们相信的那些话。任何人怀疑、甚至思考这些教义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有口无心地背诵教义与信条将使你变得惯于撒谎,又教条、又不宽容并且轻率。
李:您对康德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的介绍,似乎证明了“传统性的诠释”派观点的部分合理性。但是您认为,正是经由康德的分析,我们才能理性地赋予上帝这一道德理念以传统神学的所有特征。那么在您看来,康德所说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AW:康德观点认为,信仰的目的是让我变成更好的人。他很清楚情形有时候并不是这样,而是相反。但是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他又坚决主张,人类不能仅仅依靠自我来完成德性的进步。我们需要一个自愿的伦理共同体(ethical community),在那里人们尝试与他人分享爱与目的,在现实的心灵生活的共同体中探索“目的王国”。康德认为教堂是这样一种共同体的模型——“上帝的子民”,像家人一样集合在看不见的“天父”门下。他希望,就像政治机构会越来越进化得对个人自由更为公开、公正和保护一样,宗教机构也应如此,而少些武断、狂热,少些对上帝的“虚情假意”,多些对上帝的真正的崇拜。这样才能成为更好的人,充盈你的也帮助他人充盈他们的道德使命。
如果康德是对的,那么我们的道德使命就会要求我们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我在前面讲到“长勺子”的寓言时描述过这样的社会)而奋斗,并终得正果(即康德所说的“至善”,the highest good),这也就是德性之人要之为奋斗的目标。正是因为他们关注这个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多远才能到来,所以他们注定要形成信仰,来思考有无达到目标的可能,并理性地期待至善的实现。康德感觉这里面存在着类似传统中对上帝的忠诚。因为“至善”于凡夫俗子而言,总归是力所不逮的。我们发现人世间有些变好了,有些却似乎更坏了。如果我们感觉向着至善即更美好世界的努力是无望的,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就会放弃奋斗。但是“至善”是我们道德使命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我们作为德性之人的义务,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为至善而奋斗并不能放弃信心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相信有上帝,有这样一位道德完善的最强大的造物主和大自然的统治者,相信他也有至善的愿望并能帮助我们达到它,那么,我们的期待就可以是长久的。“忠诚”可以是我们对应信之信念的内心坚持和实际行动,但是我们也处在放弃信仰的危险中,因为尽管我们应该相信,但是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并放弃努力。“为至善而奋斗”与“对上帝的忠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生关联。“对上帝的信仰将帮助我们实现至善”包含在我们追求至善的坚持中。
李:您的这些话阐释了康德所说的,“道德原理惟有在预设一个具有最高完善性的世界创造者的情况下才允许这个概念是可能的”。看来,康德反对的是教条式的宗教和没有反思的上帝概念。您提到,康德晚年的著作《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和“伦理共同体”的概念,是否都是基于一种隐喻?康德把教会分为“有形的”与“无形的”两种,其中“有形的”教会就是指现实世界中的教会;而在伦理共同体(或者称为“无形的教会”)中,人们的联合是自愿的而非强制的,它与由法律所构建的、具有外在约束的社会不同,“无形的教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具有内在的自觉性。您前面多次提到“爱”与“心灵生活”,也应该与这个隐喻有关吧?由此看来,康德宗教哲学是以道德为前提的,就是说康德主张道德宗教,而不是宗教道德。您认为这样的信仰在今天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AW:我想,尽管我们甚至都不再从字面上接受康德与上帝相关的道德宗教,但是在世俗生活中,仍然找得到与康德对上帝的道德忠诚类似的,能帮助我们实现其价值的对应物。如果我们放弃为一个没有阶级、废除了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社会而奋斗的话,我们也就很容易放弃对人类进步的期待,也将不愿意为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或者也不愿意为更美好的世界付出必要的牺牲。哪怕我们发现对上帝的信仰仍然不是一种足以表达我们的忠诚和希望的动人方式,我们仍然可以为了与我们自己一样的下一代,为了终有一天消除剥削和压迫,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而奋斗,并以这样的方式保有我们的忠诚和期待。这就是康德主义道德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尽管它并不是建立在对上帝信仰的基础上的。
如前所述,当信念是件好事时,就不是超验的信条。在出现反例而容易诱导放弃时,在信仰该被信仰的东西时感受到有所要求因而觉得可能放弃信仰更舒服一些时,信念将给你坚定内心信仰的勇气。如果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话,我们就应该为之奋斗、做出牺牲、经受冒险,哪怕无法保证我们肯定成功。因此,放弃对美好世界的希望可能更容易也更舒适一些,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偷懒、自私、只为自己谋幸福、不必操心他人以及下一代的未来和没有阶级的社会。现实证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信念,只要我们关注、操心,为之奋斗,做出牺牲,经历险阻,它就有可能实现。我们应该有勇气去坚信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应该去相信的,哪怕相信它已经不容易,实践它也会更难;而放弃和自私自利却会更容易一些。我们该有的信念是会让生活更为艰难的。
(责任编辑:张琳)
李明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艾伦·伍德(Allen W.Wood),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哲学系荣休讲席教授。
本访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2&ZD012)支持。
①在撰写采访提纲和翻译的过程中,得到南京农业大学马彪老师(外国哲学博士)和印第安纳大学维布卡·德宁(Wiebke Deimling)女士(哲学史博士后)认真的专业帮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