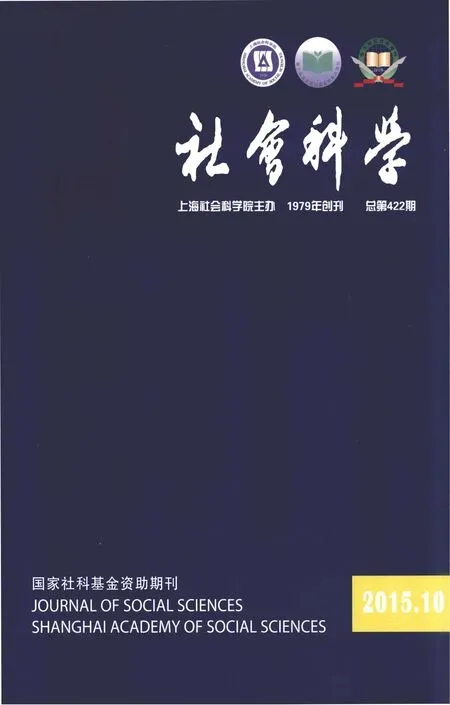日本对华认知与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张 云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很不平坦,近年来更是跌至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对此,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主流解读为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保守化日益严重,中日力量对比迅速变化让中国成为日本民族主义高扬的牺牲品,这导致日本对华关系上日益偏离友好路线并采取防范、遏制甚至敌对的对华政策。从国内政治角度的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如何确认国内政治与外交决策的联系从来就是国际政治学中的难题。力量对比变化角度的解释有说服力,但过度局限于双边框架,忽视了日本对华认知和政策是其整体对外关系一部分的大背景。日本对华政策不可能仅依靠对中国本身或者中日关系影响的认知来制定,而是受制于日本整体外交。在关心中国的发展是否对日本构成威胁的同时,日本的战略家们有理由更关心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体系带来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离开整体国际形势的分析会让中日关系的研究处于狭隘和短视的困境。从对外战略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在战略和外交上同美国紧密结盟的国家,日本天然地关心中国的发展对于日美同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如果国际体系和日美同盟将发生变化,日本的整体外交就必须随之变化,对中国外交也就相应地需要变化。离开美国因素,讨论中日关系就可能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从而无法为准确决策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这也是研究三边关系重要性所在。现有的日本对华认知和政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日本对外关系认知和决策中的核心变量——美国因素,笔者认为日本对于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认知才是影响日本对华认知和政策变化的首要因素,本文将新世纪以来日本对华认知和政策分为五个阶段,试图系统地考察并证明美国因素是如何在新世纪以来日本对华认知与政策中起关键作用。
第一阶段:“间接稳定论”(2001—2005)
与所有的同盟关系一样,日美同盟也不能摆脱“同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即“被抛弃”的恐惧(The Fear of Abandonment)和“被卷入”(The Fear of Entrapment)的恐惧①Glenn H.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6,No.4,July,1984.pp.461-495;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p.180-186.。特别是作为同盟中较弱一方的日本,从日美同盟建立那一刻开始就始终在这两种恐惧中寻找平衡。冷战时期,日本的大战略逻辑非常清楚,即只要保证日美同盟稳定,日本就可以获得美国的市场、资金、技术从而发展经济,只要有美国的支持,日本就可以顺利地利用亚洲国家的原料和市场发展经济,而日本付出的代价是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后方支持,这是双方之间的“战略交易”,如何管理日美同盟也就成为日本战略的核心问题。冷战中,由于美国面临着苏联这个巨大的战略对手,因而日本可能被美国抛弃的恐惧并不强烈,日本在管理同盟关系中更加担心可能卷入同自身安全和利益没有太大关系的美国“战争”和“冲突”。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日共同战略对手苏联事实上退出了本地区,日美同盟的存在意义一时受到了双方的怀疑,双边关系出现了“漂流”②Yoichi Funabash,i“Tokyo's Depression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8.p.35;INSS Special Report,“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October 11,2000.p.2.。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回到了原有的认识,即日本的大战略“成本和风险最小”仍然是坚持日美同盟的基轴,管理日美同盟关系照旧是日本战略和外交的中心问题。中美关系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发展迅速,美国对日外交的相对冷淡则让日本感到不安③Morton I.Abramowitz,“The State of East Asia and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Morton I.Abramowitz,Funabashi Yoichi and Wang Jisi,“China-Japan-U.S.Relations:Meeting New Challenge”,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02.p.41;Akihiko Tanaka,“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EAN +3 Framework”;Melissa G.Curley and Nicholas Thomas,Advanc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London:Routledge,2007.p.63.。2001年,小泉纯一郎当选日本首相时候,日本对于日美同盟的未来有不确定感(即“被抛弃”的恐惧)④Yun Zhang,“Multilateral Means for Bilateral Ends:Japan,Regionalism and China-Japan-US Trilateral Dynamism”,The Pacific Review,Vol.27,No.1,March,2014.pp.5-25;INSS Special Report,“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October 11,2000.。尽管“中国威胁论”在这个时期首次在政府文书中出现,但是中日之间的力量差距仍然悬殊,日本并没有真正感到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和日本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日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认知美国和世界,而不是中国。
“9·11 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开始的全球反恐战争(The Global War on Terror)成为结束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对于冷战后世界认知分歧的重要转折点⑤冷战后到“9·11”前,日本存在着对于世界体系将会更多是美国单极独霸还是多极化的争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胜利让日本的战略家们坚信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世界国际体系将持续⑥藤原帰一:「帝国と大国のあいだ—日本にとってのアメリカ·中国にとってのアメリカ」;毛里和子、張蘊嶺編:『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アジアの共生と協力をめざして』,岩波書店2004年版,第193 页。。甚至还有些专家学者提出了美国可能变成世界帝国,世界将成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⑦毛里和子、張蘊嶺編:『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アジアの共生と協力をめざして』,岩波書店2004年版,第210页。。对于美国超级独大霸权的深信不疑构成了日本战略精英们思考的智力基础。按照这样的逻辑,选择“搭车”(向美国一边倒)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聪明的选择⑧事实上,这种倾向不仅仅存在于日本,加拿大等美国的盟国在这一时期同样显示出“搭车”的强烈倾向。参见Jerome Klassen and Greg Albo,Empire's Ally:Canada and the War in Afghanista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3。。美国作为日本外交中最主要变量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地加强,当然也包括日本对华外交的考量。东京大学国际政治专家藤原归一教授认为,中国与日本的政策外交前提深深地受制于美国的选择⑨藤原帰一:「帝国と大国のあいだ—日本にとってのアメリカ·中国にとってのアメリカ」;毛里和子、張蘊嶺編:『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アジアの共生と協力をめざして』,岩波書店2004年版,第211 页。。基于同样的逻辑前提,另一位东京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则通过权力平衡理论来解释中美日三边关系,其认为“美中、日美关系如果为正,日中关系就必然为正。2001年‘9·11 事件’后中日关系的稳定可以用‘预设稳定论’(Stability by Default)来解释而不是来源于双方的积极努力(笔者将其称为‘间接稳定论’)”①关于“间接稳定论”的简单说明,参见毛里和子、張蘊嶺編『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アジアの共生と協力をめざして』,岩波書店2004年版,第175 页。。换句话说,日中双方不怎么努力,日中关系也会稳定,现在日中关系的稳定(该文的发表时间为2004年3月)有间接形成的一面。换言之,稳定的中日关系可以由稳定的日美关系与中美关系结构性地创造出来。从政策层面来看,上述逻辑正好同小泉纯一郎在外交上“赋予日美关系以特殊重要性的单一外交”②[日]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 页。相呼应。日本对美国予以全方位的支持(Unstinting Support),并将加强美日同盟作为日本与世界交往中的核心③The Edwin O.Reischauer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The Paul H.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Global Context:2008”,Introduction,The Japan Times,2008.。
“间接稳定论”中认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可以从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中自动获得的逻辑同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对华政策上几乎是无视态度相吻合④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知识精英虽然主张“间接稳定论”的作用,但是中日关系需要从间接稳定走向自律稳定,然而这方面的论述很少。参见山本吉宣「グローバル·システムの中の日中」;毛里和子、張蘊嶺編『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アジアの共生と協力をめざして』,岩波書店2004年版,第166—167 页。。正如前面所述,日本知识精英对于国际体系的认知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将会在很长时间内持续,那样中国崛起的影响就会在美国独霸的框架内消化。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国内民族主义的抬头,日本首相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了无视中国的做法。尽管小泉首相接连参拜靖国神社,但2001年—2004年中日关系并没有出现极度的恶化,虽然中日首脑双边互访从2002年后停滞,但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多边场合同日本首相进行了会见。日本知识精英认为不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变量的“间接稳定论”的解释有效性获得了“证明”⑤日本的战略专家可能较好地解释了日本外交逻辑中的美国因素,但是可能过度估计了中国外交中美国因素的作用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日本决策者来说,无视或者忽视中国的代价并不大,这体现了在日美同盟巩固的情况下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牺牲部分中日关系也没有关系的暗含逻辑。2005年11月,小泉纯一郎在同布什总统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说,“日美关系越是好,日本同中国、韩国、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关系就会好”⑥《朝日新闻》,2005年11月17日。。
第二阶段:转向“积极稳定论”(2005—2009)
这一时期,日本知识界对于世界形势的判断以及日美同盟的认知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沼、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主流的日本战略专家认为,全球力量正在发生转移。他们对于国际体系的基本看法是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体系正在趋向结束,尽管美国相对于其他大国仍将享有明显的优势⑦植木(川勝)千可子:「世界の構造変動と日米中関係―リベラル抑止政策の重要性」,『国際問題』,No.586,2009年11月,第15—28 页。,世界正在从美国独霸向多极化体系转变,尽管这个过程将会漫长⑧田中明彦:「日本の外交戦略と日米同盟」,『国際問題』,No.594,2010年9月,第39—40 页。。美国也不再被认为将会成为现代版的罗马帝国。2005年,发生在中国主要城市的反日游行对于上述“间接稳定论”的逻辑构成直接挑战,强化了的日美关系和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很明显并没有自动带来中日关系的稳定。
基于上述认知,日本主流正常国家民族主义知识精英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已经逐渐成为日本对外政策中不可无视的变量,但是在如何应对方面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第一类是某种意义上坚持在原有“间接稳定论”的基础上强调通过日本自身的自主努力来应对。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东京大学国际政治专家北冈伸一教授,在批评美国反恐战争失败的基础上①北岡伸一:「新たな世界秩序の模索」,『アステイオン』,No.70,2009年,第54—55 页。,指出美国在后危机时代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②北岡伸一:「新たな世界秩序の模索」,『アステイオン』,No.70,2009年,第63 页。。在这个巨大的国际体系的变化进程中,日本在对外战略上不能够像以前在美国的单极世界国际体系中那样“消极地等待”,而应当努力成为新兴国际体系中的“积极的全球行为者”,采取更为积极的安全政策包括重新解释集团自卫权③北岡伸一:『グローバルプレイヤーとしての日本』,NTT2010年版;Shinichi Kitaoka,“Japan's Turning Point:Proactive Pacifism and Global Diplomacy”,Gaiko Forum,No.244,Nov.,2008.pp.8-15。。北冈伸一认为判断中美关系会紧密尚为时过早,因此日本的作用依然很重要,日本不应当总是预测中国和美国的想法,而应当积极地引导”④北岡伸一:「2010年代の日本外交」,『国際問題』,No.588,2010年1/2月,第2 页。,“日本如果是可以依赖的话,自然会成为美国的伙伴,否则美国就会和中国协调处理问题,这就会对中国有利”⑤北岡伸一:「新たな世界秩序の模索」,『アステイオン』,No.70,2009年,第63 页。。另一位战略专家冈崎久彦认为,“美国越感到中国军事崛起的重要性,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就会增加,这是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原理”⑥「日はまた沈むのか――米中「同盟」の狭間に消える日本」,『中央公論』2009年7月,第37 页。。中国崛起,美国重视中国,中美接近,这是正常的发展,这本身并不直接构成美国抛弃日本的原因,只要日本对美国有价值,美国就不会抛弃日本。只有日本自主强化战略意图和能力才能够巩固日美同盟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这事实上体现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实力和日美同盟的有效性存在着怀疑。
第二类则认为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由于国力的相对减弱以及从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向奥巴马时期的多边协调方向转变,对于日美同盟的稳定和有效性显示了信心⑦田中明彦:『ポスト·クライシスの世界:新多極時代を動かすパワー原理』,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尽管强调坚持日美同盟基轴,他们认为在后经济危机时代“日本对外政策的最大课题是中国的软着陆”(今后10—30年中国能否实现安定的寻求国际合作的繁荣国家是日本对外活动的首要目标)⑧田中明彦:『ポスト·クライシスの世界:新多極時代を動かすパワー原理』,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12 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田中建议在避免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对中国采取“深度接触”政策⑨田中明彦:『ポスト·クライシスの世界:新多極時代を動かすパワー原理』,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16 页。。植木认为,尽管中国有核武器并且持续20年增强军力,但无论从能力还是意图方面来看,中国对日本采取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低10植木(川勝)千可子:「世界の構造変動と日米中関係―リベラル抑止政策の重要性」,『国際問題』,No.586,2009年11月,第22 页。。就算中国对日采取敌对行动,日美同盟的可靠性使得双方会共同行动,中国对日美同盟的威慑力不会存在误认11植木(川勝)千可子:「世界の構造変動と日米中関係―リベラル抑止政策の重要性」,『国際問題』,No.586,2009年11月,第22 页。。但是,美国在经济危机和反恐战争后正在变得内向(Inward-looking)12植木(川勝)千可子:「世界の構造変動と日米中関係―リベラル抑止政策の重要性」,『国際問題』,No.586,2009年11月,第24 页。,为了促使中国发挥合作和建设性的作用,日美今后需要采取的方向应当把重点放在建立中美日三边对话和协调机制上13植木(川勝)千可子:「世界の構造変動と日米中関係―リベラル抑止政策の重要性」,『国際問題』,No.586,2009年11月,第25 页。。
正常国家民族主义知识精英们在判断国际体系趋势方面并没有大的失误,在中国崛起的认识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都认为构成有限挑战,对于坚持日美同盟也没有分歧,然而在日美同盟的有效性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提出的政策处方也就有所不同。对日美同盟有效性持相对悲观观点的知识精英认为要继续让同盟有效,让美国的承诺变得可靠需要加强日本自主的努力,在亚洲展现日本的价值,同价值观相近的国家以及东盟国家加强关系从而为日美同盟作补充,认为同中国直接接触需要有一个牢固的基础,在准备不充足情况下的接触会适得其反。对日美同盟的基础性威慑功能持相对乐观的知识精英认为仅依靠日美同盟是不够的,日本需要做的是主动加强同中国建立互相信任,最终推动三边框架的形成,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日本同中国建立互信从而为将来在新体系中能够占领有利地位做准备的机会。从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开始到民主党上台前的几届内阁,实际上的政策反映了正常国家民族主义中相对乐观主义派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对于小泉的中国和亚洲外交反思过程中,日本知识界中的中等国家国际主义派也显示了一定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国际体系的权力转移以及中国独立变量的重要性,他们比上述知识精英有更强烈的认知。
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批评小泉外交失衡,认为其没有看到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重要性的增加①中西寛:「改革から構築へ:小泉外交の経験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No.550,2006年4月,第4 页。,认为小泉首相所说的“日美关系越是紧密,日本与亚洲关系越好”是时代错误,日美关系和亚洲外交需要同时实现②中西寛:「改革から構築へ:小泉外交の経験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No.550,2006年4月,第10 页。。他还以日本要求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失败为例,批评了对美一边倒的外交对于日本全球外交的不利点③中西寛:「改革から構築へ:小泉外交の経験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No.550,2006年4月,第10—12页。。他同时指出亚洲政治经济正在经历重大变动,认为经济相互依存深化就会自动带来关系和谐的想法是危险的,需要有意识地选择抑制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政策④中西寛:「改革から構築へ:小泉外交の経験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No.550,2006年4月,第10 页。。他还强调了日本外交应当在推动东亚地区主义和全球多边体制中发挥积极作用⑤中西寛:「改革から構築へ:小泉外交の経験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No.550,2006年4月,第9—10、12 页。。
日本庆应大学添谷芳秀教授认为,东亚地区的安全主要是由中美战略关系决定的,因此,日本只有走东亚外交的道路才能发挥自身的长处⑥添谷芳秀:「アジア外交60年―敗戦から東アジア共同体へ」,『外交フォーラム』2005年8月,第33 页。。添谷认为,日本应当首先将自身定义为同加拿大和德国那样的中等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等国家的大战略和外交,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与日美同盟并重,这样不仅可以将中国包容在该机制内,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美国包容进来⑦添谷芳秀:『日本のミドル·パワー外交:戦後日本の選択と構想』,ちくま新書2005年版。。添谷芳秀教授认为,小泉时期日本外交被过度的“反中”意识所左右,结果自我束缚了外交空间。他认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积极外交的根本动因是担心美国利用中国周边国家鼓励反对中国,因此日本没有必要将中国的动作放在对立面来看待,而应当努力准备好系统地包容中国的构想,并努力让其他亚洲国家共有这些构想,这才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关键⑧添谷芳秀:「アジア外交の再編:官邸外交を機能させるために」,『国際問題』,No.558,2007年1/2月,第31—32页。。然而,从政策层面来看,东亚地区主义并没有在小泉后的自民党内阁中占据多大的地位。
正因为日本主流认为日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也相对稳定,积极主动开展中国外交就比较可能成为决策者的选项。安倍晋三首相在第一次当选后,对中国采取了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积极外交,并且在对美外交上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基本上继承了上述路线。这也被大多数日本国际关系和战略专家们所认可⑨Makoto Iokibe,“America and Asia:Synergy of the Two Arenas and Japan's Diplomacy”,Gaiko Forum,No.245,Dec.,2008.p.8-10;中西寛:「改革から構築へ:小泉外交の経験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No.550,2006年4月,第4—6页;北岡伸一:「新たな世界秩序の模索」,『アステイオン』,No.70,2009年,第46—67 页。。
第三阶段:非常规时期(2009—2010)
2009年,日本民主党以压倒优势在日本战后首次完全击败自民党实现单独执政,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的“55年体制”。在鸠山由纪夫就任日本首相期间,正常国家民族主义者在政策决定过程中被边缘化①例如田中名彦与北冈伸一都没有进入首相关于安全政策的咨询会议。。鸠山一方面提出了“对等的日美关系”,另一方面提出在中日合作基础上建立东亚共同体。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因为鸠山亲华,所以希望对日本战后外交做出历史性的改革。然而,作为政治家的鸠山,其判断依据主要还是建立在对经济危机后美国势力相对下降与中国实力上升造成的国际力量变化的认识上。鸠山的政策明显带有“搭车”(Bandwagoning)中国和“离美”的倾向。
从长远来看,鸠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并没有错误,坚持日美同盟但保持适当距离、加强中日合作发展多边框架这些政策倾向无疑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但问题在于鸠山的剧烈政策变化严重挑战了战后一直积累起来的正常国家民族主义者大战略的共同智力基础:一个牢固的日美同盟。他们担心日中关系的快速接近会以牺牲日美同盟为代价。田中明彦尽管认为,“从世界趋势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多中心化深化是没有疑问的事情,中国和印度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的经济规模会相对缩小。挑战美国军事实力的国家还不会出现,但是在经济领域则相对影响力下降”②田中明彦:「日本の外交戦略と日米同盟」,『国際問題』,No.594,第39—40 页。。在一个体现了权力弥散(The Diffusion of Power)和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新国际体系中,日美同盟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积极的安全政策③田中明彦:「日本の外交戦略と日米同盟」,『国際問題』,No.594,第40—41 页。。田中认为,日美同盟应当超越美国向日本提供安全的层面而为更大范围的日本外交发挥作用,把强化的日美同盟变成促使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采取“自制的装置”来保证日本的安全④田中明彦:「日本の外交戦略と日米同盟」,『国際問題』,No.594,第41 页。。其中暗含的意味是鉴于美国势力的相对下降,为了实现日美同盟的强化,日本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为此,田中提出日本需要成为一个美国的“普通的同盟国家”,重新对集体自卫权提出宪法解释,放宽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武器使用限制、武器全面禁止出口等来消除和减少日美同盟中的“非对称性”问题⑤田中明彦:「日本の外交戦略と日米同盟」,『国際問題』,No.594,第40 页。。他指出了同中国加强直接接触和通过多边主义来包容中国崛起的挑战,但是强调这些努力都应该建立在一个巩固的日美同盟和日本更加积极的安全政策基础上⑥田中明彦:「日本の外交戦略と日米同盟」,『国際問題』,No.594,第41 页。。对日美同盟可靠性更有信心的正常国家民族主义知识精英则对鸠山的外交再平衡政策表示了赞同。植木认为,“在美国表现出内向的倾向,如何才能让中国发挥合作的建设性作用,今后日美需要做的是在经济、安保、危机管理等方面尽快建立中美日三边框架”⑦植木(川勝)千可子:「世界の構造変動と日米中関係―リベラル抑止政策の重要性」,『国際問題』,No.586,2009年11月,第24—25 页。。他们对鸠山由纪夫内阁同中国积极推进建立信任关系给予高度评价⑧植木(川勝)千可子:「世界の構造変動と日米中関係―リベラル抑止政策の重要性」,『国際問題』,No.586,2009年11月,第25 页。。然而,大部分正常国家民族主义者在鸠山执政期间认为日美同盟受到了损害。
美国对于鸠山的离美倾向也高度戒备。奥巴马政府东亚事务高级官员贝德在回忆录中写到,“日本民主党的一些立场和在竞选运动中的口号让华盛顿忧虑”⑨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2.p.42.。贝德还写到,“他们(民主党议员)还暗示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减少对于美国的依赖。还有一些对于美军在冲绳的存在表示怀疑态度,并且提到了在选举承诺中提及的重新考虑普天间代替设施”10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2.p.42.。2009年10月,盖茨国防部长访问日本,他在私下对日本政府官员相当严厉,不允许在普天间问题上有进一步的变更11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2.p.44.。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问日本的时候,对鸠山外交上的离美自主倾向表示了警戒,这也加强了日本民众的不安①「重い注文と見るべきだオバマ演説」,『毎日新聞』2009年11月15日。。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让日本媒体和民众对于鸠山由纪夫离美倾向的担心进一步增加。2010年5月,鸠山突然宣布辞职,最终证明了他的外交思维过于超前,日本无论主流精英层还是民众对如此重大的转变还没有准备好,这是一个非寻常的时期。
第四阶段:回归“间接稳定论”(2010—现在)
2010年5月,鸠山由纪夫内阁辞职后,正常国家民族主义知识精英中坚持日美同等基础上加强自主积极努力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仍然认为国际力量转移过程中美国实力相对降低,美国单极世界的国际体系行将结束,世界在向多极化或者“无极化”(No Polar)②Ian Bremmer,Every Nation for Itself: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London:The Penguin Group,2012.的方向发展。在新形势下,日本需要更加能动地设定“自身的坐标轴”,以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姿态来主动强化日美同盟③谷内正太郎:『日本の外交と総合的安全保障』,ウェッジ2011年版,第7—9 页。。他们对于在鸠山内阁执政时期被“破坏”的日美同盟感到担心,认为日美同盟的修复要建立在日本积极主动努力的基础上。
日本知识精英对中国的主流认知发生变化,主要有两个动因。第一是日本对于美国对华认知和政策的变化;第二是2010年9月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美国在2010年初实质上开始“亚洲再平衡”政策,在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直接介入南海问题④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2.p.104-105;清水美和:「中国との外交政策をどう更新するか」,『世界』2011年3月,別冊「日中関係 私たちはこう考える」,第124 页。。日本开始认为,美国已经放弃奥巴马第一任期开始时候的对华“绥靖政策”⑤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2.p.104-105;清水美和:「中国との外交政策をどう更新するか」,『世界』2011年3月,別冊「日中関係 私たちはこう考える」,第124 页。,批评中国外交“强硬”(Assertiveness)的声音越来越强⑥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2.p.104-105;清水美和:「中国との外交政策をどう更新するか」,『世界』2011年3月,別冊「日中関係私たちはこう考える」,第124 页。美国对于中国主张自我强化的文章评论回顾,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2013.pp.7-48。。美国的变化给日本知识界和决策者的对华认知和政策选择提供了认知基础和框架,事实上在2010年以后,日本国内关于中国的认知变化很多都能够在美国的知识界中找到原型。尽管美国的变化为日本的认知变化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但是,直接促成变化的是“撞船事件”⑦“撞船事件”发生前,日本知识精英和政策人士尽管开始认为中国外交姿态的变化引起了美国的政策变化,但对于中国的认知和政策选择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例如曾经担任外务次官的薮中三十二在2010年出版的书籍中仅提到了“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的傲慢,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变化”。他并没有涉及到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也没有提出对中国的新的政策建议。参见薮中三十二『国家の運命』,新潮新書2010年版,第43 页。。“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知识界首先对于美国的新姿态以及对日本的影响很快进行了新的解读。北冈伸一认为,“美国回归亚洲在日本被解读为向中国传递坚决的信号,中美两国集团论(G2)的幻灭以及日本对美的战略价值提升”⑧北岡伸一:「日本外交の座標軸―外交三原則再考」,『外交』,Vol.6,2011年2月,第15 页。虽然日本的战略家们不断强调日本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对外战略而不是经常性地猜测美国战略或者中美关系如何,但事实上都没有摆脱在判断美国战略基础上设定日本政策的框架。。中国的问题是急速大国化导致的大国意识抬头,特别是解放军的主张强化⑨薮中三十二:「今後の日本の外交·安全保障はいあにあるべきか外交」,Vol.6,2011年2月,第34 页。。还有对于中国是否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对外合作政策提出了严重质疑10伊藤憲一:「膨張する中国と日本の対応」,『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第35 政策提言』,2012年1月,第1 页。。还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已经从负责任的大国向建立中国秩序的方向发展11北野充:「中国の対外戦略·4つの潮流·からみる大国化と中国的秩序への志向」,『国際問題』,No.604,2011年9月,第47—62 页。。
尽管日本的战略专家们认为中国变得比以前更加自我主张(Assertive),但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三边关系和国际体系上而不是中国。田中明彦认为,中国的崛起带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国际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很大①田中明彦:「パワー·トランジッションと国際政治の変容:中国台頭の影響」,『国際問題』,No.604,2011年9月,第11 页。。在权力转移的漫长过程中,他认为依靠美国和盟国的合力能够包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他认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过大评估自己的力量和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应对不够灵活。从这个意义来说,一个巩固的日美同盟可以成为一个让中国不至于高估的装置,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被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②田中明彦:「パワー·トランジッションと国際政治の変容:中国台頭の影響」,『国際問題』,No.604,2011年9月,第11 页。。很有意思的是,同之前不同,他没有提及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日本要积极开展对中国的直接接触的努力。相反,田中指出了外部刺激可能会造成内部不稳定情绪的危险③田中明彦:「パワー·トランジッションと国際政治の変容:中国台頭の影響」,『国際問題』,No.604,2011年9月,第10 页。。这似乎在提醒日本,如果不够精致的对华接触可能会适得其反。同日本的中国专家不同,日本的战略专家们对于中国外交方向变化与否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关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着原来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即有限挑战而且稳固的日美同盟可以对应。尽管中国的崛起正在引起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但主要的参与者就是中国和美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暗示对于日本来说,聪明的办法是强化同盟关系,积极推进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外交而不是加深同中国的直接接触。这个背后的逻辑在于,首先日本不是力量结构变化的主角;第二,对华积极接触政策也不一定有效。北冈伸一在2011年指出,同中国的接触政策必须建立在强化了的日美同盟和日本同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基础上④北岡伸一:「日本外交の座標軸―外交三原則再考」,『外交』,Vol.6,2011年2月,第15 页。。这些说明日本对华认知的逻辑又回到了21世纪初第一个十年前半期的“间接稳定论”。但是,这个逻辑的智力基础同以往既有相同也有区别。10年前,日本认为没有必要同中国进行积极外交,其主要建立在相信美国单极帝国的世界体系和日本在经济实力上也比中国具有明显优势的基础上。当时,日本没有很强的对华积极外交的动力,日本对华还处于从上向下看的姿态。而进入第二个十年,日本开始担心由于实力变化和直接接触不成功的成本让其在单独面对中国的时候信心减少,同时又认为日美同盟以及强化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再加上自身努力尚足以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考虑到如果积极接触不成功可能引起的负效应,追求“政治安全的思维方式”就合乎情理地比开展有创新性的外交占了上风。强调日美同盟的加强也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减少由于缺乏同中国的实质性关系而带来的不安心理。同时为了平衡日本过于依存美国可能引起的国内反弹,日本采取了同其他地区加强关系的态度。从战略角度来说,日本试图避免直接面对中国。因为一个强化了的日美同盟和更加积极的安全政策调整起来似乎不那么困难,政治上也安全(中国的对日政策决策中是否也存在类似逻辑的可能性值得探讨)。然而,这样的政策结果是牺牲了更加主动积极的对华政策可能性和灵活度。从政策层面来看,鸠山内阁倒台后,菅直人首相立即改变了前任的离美倾向,日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基轴的定位被重新强调,几乎不再能够听到谈及东亚共同体的话题。上述思维逻辑构成了从菅直人到安倍晋三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智力基础,即仍然延续小泉时期的“间接稳定”而不是“自律稳定”(鸠山的失败让后来的内阁也感到对中外交的国内政治风险)。安倍晋三在第二次当选首相后不久,在接受采访时候说,“外交首先是强化日美同盟,然后在将同东南亚和印度的关系提高到更高水平的基础上再来同中国搞好关系”⑤『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1月11日。。
结论
日美为正式的同盟关系、中美属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战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美国因素在中日相互认知和决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因素和中美日三边关系是全面理解日本对华认知和决策的关键。美国因素对日本外交整体有决定性影响,日本的对华外交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对华外交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日美同盟关系。
当日美关系不稳定的时候,日本外交就面临结构性困难,如何拉住美国变得头等重要,对中国就很难采取积极政策,因为这可能会加深日美关系的风险,日美关系的稳定是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前提。与此同时,即使日本对日美同盟有信心而中美关系呈现对抗,日本在中美之间面临选择,为了保持同盟的安全,对华关系的政策选择自由受到限制,结果导致中日关系下滑,这就是我们在民主党执政时期看到的情景。当日本对于日美同盟有信心的时候,中美关系也稳定的情况下,日本外交的自由度增加,日本比较容易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这就是我们从安倍、福田、麻生到鸠山时期看到的对中国的接近政策。而鸠山时期由于对中国的急速接近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反过来日本国内对于日美同盟的信心减少,维护同盟的要求显得突出,中日关系就不得不被牺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对于日美同盟信心的判断是决定其对中国政策的首要变量,而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是从变量。换言之,日本对于中国本身的认知还没有成为其对外战略中的决定性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