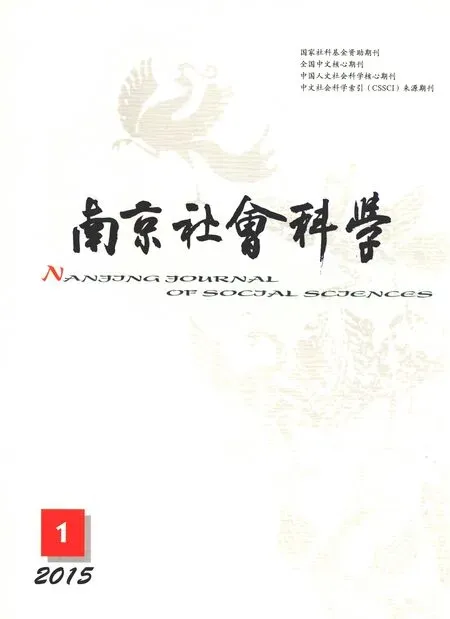核心价值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文化治理*——深化改革文化治理创新的模式与入径
核心价值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文化治理*——深化改革文化治理创新的模式与入径
张鸿雁
摘要在全球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交流、冲突、碰撞和整合中,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正在受到外来文化的挑战,文化的“混杂性”为强势经济体的文化传播创造了前提和文化场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以文化自觉的积极态度迎接挑战,以全新的文化治理模式建构时代的核心价值。对此,本文提出了三个层面新的思考:一是核心价值的文化认同是现代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文化治理;二是文化认同需要重构民族的“文化根柢”和“日常生活的自我价值体系”;三是文化治理的入径之一是市民主体精神的再造和职业伦理精神的现代重构。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化治理;核心价值;文化根柢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特色文化城市研究”( 12&ZD029)的阶段性成果。
全球化浪潮和现代网络技术带来的文化空间扩展和整合,出现了文化混杂性——“克里奥尔化”①的文化现象,且已在全世界漫延,人们被“混置”于不同的制度、文化、思想和信仰的交织环境之下,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激烈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原有的民族文化认同正在被整合,国家的文化向心力面临多样化发展的考验。英国学者汤林森曾认为:“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使经济上强势的国家,亦不能幸免于此”②。同时,全球化更使得文化逐渐成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战略资源,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全球战略格局都具有深刻的意涵,甚至有学者证言:“21世纪的竞争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③。全球化在带来了对传统文化认同解构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化价值和文化认同因过快的文化更替、变迁而缺少生长的稳定条件,导致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文化认同的“结构性缺失”和“合理性危机”④等现象的发生。
一、“文化认同”的现代性与“文化身份自我识别”
文化认同既是社会发展“现代性”的一种文化结晶,也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文化凝聚力所在。城市化过程作为“现代性”的表征,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社会系统的内在结构变迁,而且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全面而深刻的变革,由于经济与文化转型的动力因不同,社会变革必然产生相对的“社会与文化堕距”。加之,改革的实质是对不同利益集团的结构性调整,必然产生新的社会文化要素和“异质性”社会差异,进而必然引发文化价值的某种对立和冲突。经济基础领域出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转向”甚至是某种文化危机会被诱发出来,如信仰危机、核心文化价值丧失等,而其文化认同则成为突出的时代问题,全世界后发现代化国家无不如此。全球范围的现代化竞争,已将中国抛入了一个新的“混杂型”的文化参照背景之中,正处于“文化转向( Culture Turn)”关键时期。如何形成独有的民族文化认同,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特有的“文化价值识别”和“身份自我识别”,则需要明确中国的“世界文化身份”,包括建立民众从文化心理结构所表现的“文化自我识别”能力。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及文化领域正在出现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化危机”与“合理性危机”,即社会文化系统不能为社会整合提供足够的合法性以确保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信任。⑤具体而言,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中,这种文化认同危机表现为三重文化特征:
一是“文化自觉”与“我们感”( we-ness)⑥自我意识的缺失。核心价值缺乏文化认同,必然使文化失范现象的层出不穷,价值观新旧交替、社会多元文化并存、社会角色多重错位——复杂的社会状态可以说是现阶段国人文化价值观缺失的集中表现,这是地方性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向整合和冲突带来的一种特性——“文化价值颠覆”,“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人对于自身这样的困惑不解”⑦,表现为普遍意义上的“消极公民”现象——即对现实的社会变迁与改革抱有一种“不关心、不参与”的态度,缺乏共有的“价值认同”,特别是“我们感”( we-ness)的某种丧失。《政治参与蓝皮书:中国政治参与报告( 2013)》⑧的一份调查说:在体制认同、政党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发展认同六种认同中,以5分为满分计算⑨,文化认同和体制认同的得分最低(均为3.44分) ;同时,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得分略低,显示出了“参与水平低”的基本态势。以上数据说明: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广大居民的整合与引导能力尚未形成,尚未成为现代公民意义之上的各阶层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居民对于“文化认同”共识和重要性呈现漠视态度,由此也导致了国家文化认同感低下问题的发生。
西方学者在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也清楚地认识到:“以文化为基础的认同似乎随‘现代性’,即随文明的扩展而反向地进行变化。”⑩世界共同的规律是:文化共识的模式在宏观领域造成了社会群体文化认同感的低下,在微观领域则表现为一种“失范”,⑪这是在认同传统制度的基础上所表现的对以往制度和文化不认同所形成的违背社会多数人意愿的行为和结果。帕森斯的回答是:社会中有一种规范秩序( normative order)“它是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一致性理解,通过内化(主要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化)的过程,使成员得以共享这种规范秩序;当社会成员按照它规定的规则行事时,就避免了‘失范’或‘战争’从而产生了社会稳定的社会秩序( factual order)。”⑫以此类推,“文化失范”也是如此,针对“失范”的文化治理就是要建立新的“规范和秩序”,我们并不认为以往的“范式”都是合理的,但是,对于现实的文化失范现象的社会标准也是清晰的,正如有学者论及的那样: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的转型期,原先用于维系微观社区互动的地方性知识被挤压、被破坏,新的文化共识又尚未建立,一系列文化“规范真空”导致的“文化失范”现象不断滋生。⑬
二是“国民性”式微与传统人文价值碎片化。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文化身份”的迷茫。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某种断裂已不言而喻,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进行的一项居民生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普遍具有较强的传统文化优越感,但同时,与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感和优越感并存的还有对传统文化流失的危机感。⑭这种传统“国民性”文化的日渐式微,使得居民对于“我们从哪里来”的国民身份认同产生了认知错乱,更无法确立“现处何地?”“去往何方?”的问题。因此,这种传统人文价值的危机更多时候表现为在全球化世界的“个性迷失”,“一种伴随现代全球化运动而产生的文化传统的失落感和追忆情绪,它是‘现代性’文明和文化的副产品,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来说,有着‘家’的意识形态的性质”。⑮从表象上看,全球化对不同国家传统文化的整合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以传统文化“被碎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多人虽然会仍然感觉到传统文化价值的存在,但却无法在整体辨识、自我认同和自我识别。正因为如此,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进行重拾、重缀、重构和创新已经时代的主课题。零点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等8城市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是: 61.7%的城市居民认为我们正在失去传统文化,⑯而在事实上,我们不仅正在失去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我们更没有明确如何建构当代文化甚至不知道如何“建构过去”。⑰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的:文化自觉“首先表现在从艺术到文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对人、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肯定。”⑱而且这种文化觉醒也创造了知识和道德的解放,创造了这个时代的“再生人”( the man of the Renaissance),他们有两个主要的特质:“知识和道德上的勇气。”⑲
三是“自我无意识的文化本位”与“被边缘化”。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去理解,“文化认同”程度代表着民族共同价值体系的文化凝聚力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所构成民族生存力,这是跟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的文化身份识别和规范求同的民族归属感的核心。但是,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强势介入,因内忧外患的中国失去了自我身份文化的建构机会,甚至某些领域出现了“自我无意识的文化本位”。或有,当论及自我的时候,妄自尊大躺在过去荣誉上;当反观世界潮流的时候,妄自菲薄找不到自我,导致社会核心文化认同感的模糊,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缺乏内聚力和竞争力,“集体无意识”地被边缘化。导致了两种文化异化现象:“中国文化边缘化”和“中国文化威胁论”的双重滥觞。需要进一步认识的是:被人们所认同的现代化发展的样板国家,与外界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冲突,亨廷顿把这种“冲突被称为”一种文化“认同战争”。⑳由于宗教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阶段等原因,文化认同的融合是一个具有本质差异的、或者称是有异质性差异的文化悖论,融合的社会前提十分复杂,甚至可以理解是一种人类文明整体的存在方式。如果不能形成文化自觉意义上的文化认同的内在文化动力因,其文化被边缘化只是个时间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文化认同感关系到中国如何打破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边缘化境地,更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重任。
二、传统“文化根柢”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㉑价值再造
文化认同的依据是民族的“文化根柢”,这是建立在对“中国文脉”延续与继承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的。早在20世纪胡适在美国演讲时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变成一种现实。这一复兴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着西方色彩。但剥开它的表层,你就可以看出,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可以看得更为明白的中国根底——正是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和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㉒中国传统“文化根柢”的重拾与重构,是中国文化价值认同的原动力。面对西方文化东进的冲击,维持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必要的张力”需要一种国家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根柢”重构的文化新启蒙运动。弗里德曼认为,“更大的社会认同的分裂伴随着中心的现代主义的衰落,”而民族文化在这义上被激发,主要的表现就是寻根。“文化认同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并不仅仅只是游戏,而是精神上和社会生存上生死攸关的严肃的策略问题。㉓从“中国文化根柢”寻根的意义上来培植文化认同感,其诉求本质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为全体大众所共享的“核心价值”,这也是文化认同的土壤。从文化治理的角度强调重构文化认同不是对全球化文化取向的反叛,而是强调通过对民族性和世界性文化的双向选择,从人类文化整体进化的角度创造“人类大同”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而非简单地“复兴”、“回忆”与“回归”传统文化。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基于现代性而再造的“文化认同”应该从微观文化行为入手,创造从内心深处形成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需从两个层上入手:
一是建设文化认同的“常人生活体系”,让优秀文化传统成为中国人的日常认知与行为逻辑。帕森斯曾强调:“文化含义的结构构筑成了所有行为体系的‘基础’”。㉔文化治理不只单纯地建构宏大理想,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与日常行为文化价值取向的建构,只有让文化传统内化为日常行为和日常习惯才能形成社会整体和谐的基石。社会学“常人方法”的核心问题是强调“秩序”,而“秩序”必然寓于“日常生活的结构”、“日常生活态度”㉕之中,并形成一种长期的群体、个体习得的一种自然行为,包括尊重与被尊重和遵守秩序等,最终上升为一种社会的高尚理性和“集体良知”㉖。格奥尔格.齐美尔则认为:“‘即使是最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㉗而我们以往的文化治理多是以宏大叙事理想类型开始,而不能从“常人生活”的具体事实出发导致形成空旷的理想而无实际行为,往往是大而无当或者不能实践的“理想类型”。相反,发达国家比较大多将教育体制作为渗透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渠道,文化认同的建构具体而有行动逻辑。如在英国,强调学校要树立和落实“英国核心价值观”,2007年1月25日英国教育提出了全国中小学教授英国传统价值观的教育计划,规定11-16岁的中小学生学习有关英国言论自由、多元文化、尊重法治等核心价值观以及英国不同群体对英国社会的贡献等内容。㉘1981年和1988年,新加坡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价值观讨论。1991年政府将讨论结果以《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的形式公布,为摆脱“现代新加坡人没有根、也没有文化”的危险,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还开展了“文化再生运动”。㉙有学者很清楚的指出:仅仅社会结构、社会机制与日常生活联系是不够的。“没有哪个人类社会能够脱离具有一定观念、价值观、规范以及思考方式的人而存在的。换在种方式来说,每一个社会都由文化构成,并且在其基础之上运行,并且每个人都需要文化。”㉚同时还强调:“一个群体的观念、价值、信仰深刻影响并共同促进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㉛对于中国而言,则必须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教育渗透于日常生活规范和日常生活教育体系之中,通过日常生活的规范和课程的内容设置、经典文本的阅读等方式,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文化规范”和日常行为。而其深层次的解释是:“文化由较为普通的价值观组成,并由此产了具体行为规范,这引起规范反过来指导人们,以期与更为宽泛的社会结构的‘需求’相谐调的方式行动。”㉜显然这也是当代中国最缺乏而急需建构的“底层文化——基础文化”。
二是“荣誉感内化”与“生活仪式内化”的双重建构。在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文明的整合创新中,国家荣誉感和日常生活伦理及生活礼仪秩序的双重建构是一种必须选择。“构筑崇高”是英雄主义文化的集中体现,与日常生活礼仪的高雅文明化是不可分割的结构体,也是“治世”与“成德”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日常生活个体与集体的日常生活在社会学家眼中是一种社会存在的“表演”,在欧文.戈夫曼看来是“表现了他所在社会普遍、正式的价值标准,我们可以用涂尔干( Durkheim)和拉德克立夫—布朗的办法,把它看成是一种仪式——看成是对共同体道德价值表达性复原和重申。”㉝日常生活行为礼仪作为实现个体生活价值的表现与手段,自外作用于人,约束人的“心”与“行”,自内又是生活品质的象征。(《论语·雍也》。㉞国家荣誉感则是核心价值的“文化内核”,在文化认同感模糊、文化失范现象泛滥的当下,这种双重建构是在理想与现实生活中建构一个彩虹——桥梁,在依托中国传统文化重建当代中国人文核心价值的时候,让文化认同落实到具体行动上㉟是一种经验过程。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实现礼仪教化的制度化,使其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行为伦理秩序。
中国式的文化符号不仅仅是物化的要素,更多要体现在行为伦理和日常生活之中,让远大的理想类型建构、落实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形成典型的有序、有礼、恭让、利他的“常人生活体系”,在主动融入世界文化主潮的格局中,让优秀文化行为成为中国人可识别的“文化身份象征”。“人文特质”和“国人文化身份”必须在一定的文化治理模式下加以规范才能实现。
三、文化认同——市民精神建构的基石:职业伦理的现代性面向
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㊱从个体视角来解读文化治理和文化改革的人本导向,则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使个体自身得到全面的发展——从“常人生活”视角出发就可以理解本文提出“文化治理”的“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及职业伦理面向的深刻意涵。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契约型”社会是历史真正的出发点。西方有关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的讨论证明了伦理文化对公民社会发展的导向作用。㊲如西方学界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强调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注重它的社会整合和文化保存与传播功能,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帕森斯、哈贝马斯、阿拉托等人㊳。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市民社会”文明深化过程“不是整个物质关系,而是思想文化关系,不是整个商业、工业关系,而是整个知识精神生活”㊴,因此,“市民社会”、“文化认同”和文化治理是一种内在结构体,只有从现代意义建构“市民精神主体人格”,才能践行现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市民精神和市民文化的培育是“文化治理”的应有之义;市民社会主体人格的培育应构成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面向。
中国的市民社会仍然不成熟,㊵虽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激发下中国开始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但是其文化条件不足以致发育缓慢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遥观西方历史,从古罗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开始,公民意识源远流长。中国虽有上千年的道德伦理文化,但在历史上曾长期与市民法制文化无缘,因而也产生不了公民道德。文化的缺失既有制度方面的,也有非制度亦即观念方面的。㊶费孝通指出,“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体系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是没有的”。㊷同时,中国特定历史事件造成的文化断裂对市民文化和民族文化认同造成创伤十分深刻的。借鉴历史,我们应该认识到市民社会的建立不能仅仅依赖“自上而下”的制度路径,更应该强调市民社会“底层文化”的文化自觉和智慧,形成“自下而上”的“市民文化内核式”路径,这也是“文化治理模式”创新的精髓所在。
社会学家韦伯和涂尔干都提出时代意义的“我们的文化使命”问题。韦伯则把“职业伦理学说”解释为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有序化的核心,作为“在一个由作为主体的公民个人之间的互动领域的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何以可能?”这一世界历史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涂尔干则将职业伦理和道德自由视为公民文化身份的基础。韦伯认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也确实感到了这种义务”。㊸我们再一次强调职业伦理构建是现代公民道德建构主要基础。
而反观中国的当下,职业伦理的普遍低下已经成为国人愤慨与无奈的事实。“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早在2009年的一项调查说:在全国对“哪些职业失去操守的现象最严重?”,共调查12575名公众,结果排名依次为:医生( 74.2%)、公安干警( 57.8%)、教师( 51.5%)、法律工作者( 48.4%)、公务员( 47.8%)、新闻工作者( 37.6%)、会计师( 30.7%)、学者( 20.3%)、社会工作者( 10.9%)。㊹以“教师”为例,2009年教师节,人民网做了一个网上调查,问“教师节,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在由50772名网友参加的投票中,竟有高达62.9%的网民选择最期待“加强师德教育,提高教师素质”,而“强化尊师重教,延续中华传统”仅仅得到了3.9%的投票率。㊺以上的数据虽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民众,但却以反应出职业伦理和道德领域正在出现的各类问题,而其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文化领域一个真正的市民文化难以建立,更将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造成连带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职业伦理的丧失不再是学术文本中的危言耸听,更会当下中国文化改革不得不面临的“社会事实”。《决定》在“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方面明确提出“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从官方话语到本次的学理性讨论,我们应该将落脚点放在更高层次的“职业伦理”( Professional Ethics)层面上来。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合理稳定积极的职业伦理必然带来市民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如美国“自由、责任、诚实、平等、公证、守法”就是职业伦理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它借由职业团体而内化于个人,进而构成所谓的“美国精神”。无论是实践证明还是理论观照,都启示中国:以职业伦理、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市民文化、市民精神的生成是文化认同与“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而在其中,职业伦理是其支点。
如马克思所言,随着人们生产实践发生变化,“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㊻职业伦理的主体性文化价值是时代文化认同的写照。职业(“profession”)和工作职位( officium)最早就是“从古老的市民团体强制性的义务(中)派生出来的”。㊼当代哲学家埃米特指出,“一种职业……伴随它的是对其履行的标准的观念,……实践者处于这种职业中,对于维持一定的标准,就有一种信用上的真诚”。㊽在中国介入全球国家化竞争的过程中,必须汲取西方职业伦理的优秀要素并进行内化——即强调有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中国市民新伦理文化,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和“天职”价值。一些发达社会的实践证明了职业伦理建设在文化治理中的中心性地位。有研究成果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职业伦理规范,并将职业道德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化。如: 1958年7月美国第85届过会通过了共同决议《美国政府部门伦理准则》,并在此基础上先后以立法形式通过了《政府官员和雇员伦理行为准则》) ( 1965年)、《美国政府伦理改革法案》( 1989年)等等诸多法律与制度条文。㊾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工商职业伦理教育发展迅猛,有近90%的商学院开展有关工商职业伦理方面的实践教学。1984年全美274个新闻及传播课程中有117个与新闻道德有关,到了90年代初,美国高校新闻院系有一半以上开设了新闻伦理学课程,㊿形成了以学校为基地的美国“职业教育”模式职业伦理的公民教育体系,应该是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一种强迫型教育,强调职业伦理教授的终身“连续性”,为从“学校”走向“职场”,再从“职场”迈向“市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核心文化价值观的文化认同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构成了人们组织经济活动和成长土壤,关键是因为价值观影响着人类的进步方式与进程。注重文化和文化改革的思潮并不新鲜事物,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政治学者爱德华·班菲尔德、经济学者约翰·康芒斯都曾经从不同的方面论述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甚至是明确说明文化改革是制度变迁和社会改革的幕后推手和发生土壤。相较于社会改革中的其他力量,文化所需要扮演的角色更加复杂而多变,它可能是改革的对象,也可能是改革的动力,更可能是改革的工具或最终的成果形式——它甚至随时随地表现为改革的方方面面。这不意味着文化因此(至少在逻辑上应然的成次)只能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的工具、策略与功能性论述,而是将文化治理视为一个政治、经济行为、策略与措施的价值诠释、意义赋予与内在逻辑思维的理性论述对话领域或空间。“文化治理”若要成为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手段,就必须从人文价值的高度创造国家治理的典范和范式,并从“伟大荣誉的理想”到“常人生活形态”双重建构。如有西方学者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更像是对文化和政治互动关系的形象描述。
改革由现实问题倒逼而产生。过去社会上发生的是——传统伦理被破坏、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后果——文化掌握了倡导变革的主动权,经济则不断调试自己来满足这些新需求。正如非洲研究、开发和管理协会创办人和会长埃通加·曼格尔在研究非洲文化改革时提出的基本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
注:
①“全球本地化”、地方文化的混合性,是这个时代的表征:“全球本地化的另一个同义词就是克里奥耳化,克里奥耳这个术语一般指的混种的人,但它已被延伸到‘语言的克里奥耳化’这一概念……克里奥尔化与混合化经常可以相互交换使用。”乔治·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王云桥、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②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③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2,No.3 ( Summer),1993.
④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页。
⑤张鸿雁:《“合法化危机”:中国城市化社会问题论》,《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期。
⑥Mael,F.,Ashforth,B.E.Alumni and their alma mater: A partial test of the reformulat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2( 13).pp.103 -123.
⑦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7页。
⑧房宁主编:《政治参与蓝皮书:中国政治参与报告( 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⑨身份认同的得分最高(4.19分),其次是发展认同(3.74分),第三是政党认同(3.63分),第四是政策认同(3.59分)。
⑩⑰㉓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4、366页。
⑪⑫㉕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63、63页。
⑬杨晓民:《全球化时代的地域文化》,《读书》2010年第11期。
⑭⑯零点指标数据:《传统流失,文化设防并非妄谈》,2008年3 月19日,网址: http://www.horizonkey.com/c/cn/news/2008 -03/19/news_720.html。
⑮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⑱欧金尼奥·加林主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⑲威尔·杜兰:《文艺复兴》,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页。
⑳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㉑㉝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9页。
㉒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㉔㉗㉚㉛㉜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周书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6、12页。
㉖Talcott.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New York: Free Press.1937.p.319-320.
㉘陈静、郝一峰:《国外核心价值观建设路径的经验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㉙吴玉军、吴玉玲:《新加坡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及其启示》,《外国中小学教育》2008年第7期。
㉞任强:《在理念与礼仪之间——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义与礼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5期。
㉟山西太原、河北行唐等有关地区已在“儒学”领域进行了近七年的实践。
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㊲余玉花:《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伦理文化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5年第1期。
㊳武经伟、陈炳生:《公民、权利、道德及范式转换》,《思想战线》2006年第6期。
㊴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黄华光、徐力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㊵张鸿雁:《论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㊶肖雪慧:《公民社会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3页。
㊷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㊸㊼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168—169页。
㊹李颖、王冲:《哪些职业失去操守现象最严重?调查:医生公安居前》,《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8日。
㊺《超6成网友教师节最期待加强师德教育、提高教师素质》,人民网2009年9月11日。来源: http://rexian.people.com.cn/GB/56029/10031943.html。
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㊽龚群:《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及其伦理》,《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
㊾㊿王正平:《美国职业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特点》,《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1期。
〔责任编辑:秦川〕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Core Value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An Innovative Model and Approach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Cultural Governance
Zhang Hongyan
Abstract:In the global age,different kinds of 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are faced with communication,impact,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In this process,local culture tradition and core value are definitely stuck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y are forced to meet challenges brought out by foreign cultures,therefore,this“culture mixing process”has created a base and a cultural field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During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in China,we should f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of“cultural consciousness”,and meanwhile,we should try to construct the core value system of the current age with brand of new cultural governance model.This paper comes up with new thoughts from three different levels: the first is to realize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ization is cultural identity,and cultural governance model of social structure is in badly need to achieve that goal.The second is that we should use the reconstruction of”cultural roots”and“self-value system within daily life”to achieve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the third one is that one way of achieving cultural governance model is to rebuild the principal spirit of citizens and construct the modern ethical spirit of professionals.
Key words: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governance; core value; cultural roots
作者简介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南京210046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 2015) 01-007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