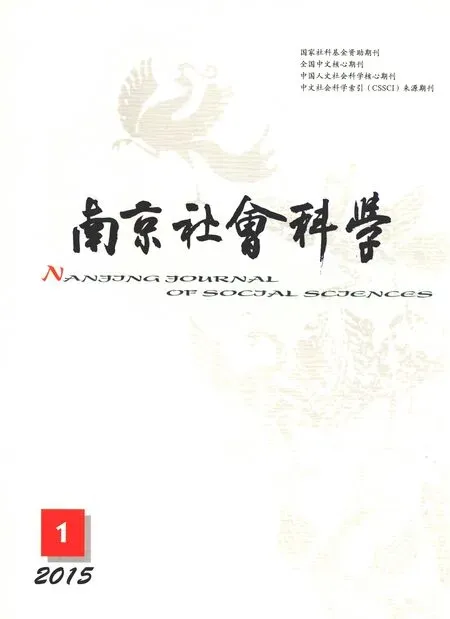桑德尔对罗尔斯道义论自由主义的元伦理学批评*
石敦国
罗尔斯的《正义论》划时代地打破了西方政治社会和伦理道德研究领域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一统天下的理论格局,为实质性的价值和规范研究重新赢得了地位,推动了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繁荣发展。与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图景。在桑德尔看来,能够引起如此深入持久的争论,正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伟大标志所在。由于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判是针对其正义理论的元伦理学基础的批判,所以,桑德尔的批判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及一般道义论自由主义构成了最根本性的挑战。
一、道义论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和理论困境
1.道义论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
道义论自由主义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正义的首要性。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①桑德尔把正义的首要性进一步解释为:“正义不仅仅是作为偶然的因素被权衡和考虑的许多价值中最重要的一种价值,而且更是权衡和估量各种价值的定律。正义是诸价值的价值,并不将自身看作是它所规划之诸多价值的同类物。诸多价值冲突时,正义就是彼此赖以和解和调节的标准。”②对于人类的本质多样性基础上的多元价值来说,正义是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价值,正义是前提性和基础性的价值,只有在正义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其他的价值目的才是有意义的。罗尔斯说:“那些需要违反正义才能获得的利益本事毫无价值。”③
第二,权利(正当)优先于善。桑德尔说:“同正义的首要性一样,正当对善的优先性是原始的、第一层次的道德要求,被终极地假定具有某种元伦理的地位。”④关于正当的优先性,罗尔斯说:“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由正义所确保的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计算。”⑤正当对善的优先性还表现在,正义原则不以任何善观念为前提,而是独立地得出的。“用以推导第一原则的证明形式,不以任何终极人类意图或目的为先决前提,也不以任何决定性的人类善观念为先决前提。”⑥
可见,罗尔斯以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的优先性为核心的道义论自由主义,不仅和康德一样反对功利主义,而且尤其反对目的论,力图为个人的平等自由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在罗尔斯看来,平等的公民自由不能仅仅意味着功利主义的满足的最大化,也不能服从于某种普遍性的目标的实现。功利主义的利益原则和目的论的宰制性目的都不可避免地要侵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2.阿基米德点的困难
既然正义的首要性意味着正义是“权衡和估量各种价值的定律”,那么,正义原则就是一种权威性的评价标准,用以评价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各种善观念。这个作为评价标准的正义原则被罗尔斯称为阿基米德点,罗尔斯把寻求阿基米德点看作是其理论的核心问题。
作为评价标准的正义原则有两种可能的来源。一是正义原则直接得自于社会中流行的各种价值和善观念,桑德尔把它称为经验性来源。二是正义原则外在于社会诸价值和善观念,这就是先验性来源。可见,阿基米德点问题实际上是正义原则与社会诸价值和善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评价标准和评价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正义原则的经验性来源存在如下的问题:首先,如果正义原则来源于社会诸价值和善观念,就是说如果正义原则的来源完全是经验性的,那么,就不能保证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因为为正义原则提供内容的不过是社会中的一种或几种价值和善观念,即使这些价值和善观念为整个社会的人们所认同,也不能改变其仅仅是所有价值和善观念中的一种的地位。在价值和善观念多元且彼此不可通约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和善观念都不能充当评价其他价值的尺度和标准,否则就是一种强制和武断。其次,这种经验性来源将导致正义原则的任意性和偶然性,而不能保证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这与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的本性是不相符的。
正义原则的先验来源则完全排除社会中流行的各种价值和善观念,而依赖于一种先验的假设。正义原则的先验来源似乎可以避免经验来源的偶然性和任意性,达到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因为正义原则是排除了社会中各种价值和善观念的影响而独立地获得的。正义原则的这种先验来源能够确保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的优先性。但是,正义原则也仅仅是在不依赖于各种价值和善观念这种意义上具有首要性和优先性。这种先验来源却不能说明正义原则是如何与各种价值和善观念相联系的,因而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的优先性依然是一种武断的假定。如果说经验性来源是由于偶然性而显得任意和武断,那么先验性来源则由于缺乏与各种价值和善观念的联系也仍然是任意和武断的。
可见,正义原则的来源问题,即正义原则与各种价值和善观念的关系问题,使道义论自由主义陷入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先验主义,都难以为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的优先性这一道义论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提供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支持。这种困难将会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正义原则以及道义论自由主义的其他观点的正当合理性难以在理论上得到证明,另一方面,道义论自由主义在制度和社会基本结构中的规导性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罗尔斯无疑正确地看到了道义论自由主义这种根本性的困境,甚至可以说这种困境构成了罗尔斯整个正义理论的出发点。罗尔斯寻找阿基米德点的方案就是力图克服这种困难。按照罗尔斯的要求,这个点“不是一个从世界之外的某处产生的视景,也不是一个超验存在者的观点,而是在世界之内的有理性的个人能够接受的某种思想与感情形式。”⑦。寻找阿基米德点是罗尔斯对道义论自由主义的元伦理学谋划。而桑德尔却证明,只要罗尔斯坚持道义论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相对于善的优先性,其谋划就不会成功。
3.道义论主体理论的困境
在桑德尔看来,一方面,正义的首要性、正当的优先性涉及到正义原则与社会诸价值和善观念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涉及到自我与其目的之间的关系。与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的优先性相一致的是自我相对于其目的的优先性。道义论反对目的论。对道义论来说,最为根本的并非我所选择的目的,而是我选择目的的能力,一个具有选择能力的“我”。罗尔斯说:“由于自我优先于目的,目的由自我确认,甚至一种支配性目的也是由我在大量的可能性中选择的。”⑧自我相对于其目的的优先性又是道义论自由主义一个元伦理层面的核心观点。
与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的优先性一样,自我对于目的的优先性符合理性存在者的自律理念,即人是有选择能力的主体,是独立于他所追求的目的之外的有尊严者。罗尔斯说:“这就是把人类主体作为一个具有选择能力的主权行为者的概念,作为一个其目的经过选择而非既定,其目标和追求经过意志行为而非认知行为才获得的生物的概念。”⑨
在桑德尔看来,自我优先于目的,我不是所有经验的目标、属性和追求的被动容器,而是一个不可还原的、积极的、有意志的行为者,我能把自己从环境中区分出来,我把那些目标、属性、欲望等都看做是“我的”,而不是我由他们构成。正义的首要性产生于有必要区分评价标准与被评价的社会,而自我的优先性产生于有必要区分主体与其处境。可见,道义论的自我就是一个独立于其偶然需求和偶然目的的主体。
就像正义原则具有经验性和先验性两个来源一样,自我也具有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两个自我观念。如果组成自我的只是各种偶然的欲望、需要和目的的聚合,这种自我就是经验的自我。经验的自我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属性以及自己所处的情景区分开来,自我就等于自己的属性之和,自我没有对于自己所处的情景的独立性,而是被情景所决定的,这就是情景化的自我。经验的、情景化的自我被桑德尔描述为“我是X、Y、Z”,这种自我不能形成统一性的自我概念,因为属性和情景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自我也就处于流变之中,并消失于流变之中。情景化的自我缺乏统一性,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自我。
能够用来代替经验的和情景化的自我观念的,看来只有诉诸超越于经验的先验原则,以便于确保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的优先性。先验自我具有相对于其目的、属性和情景等等的独立性和优先性,因而具有先在的自我统一性。桑德尔把先验自我描述为“我拥有X、Y、Z”,以区别经验自我的“我是X、Y、Z”。如果说经验的情景化的自我缺乏统一性和相对于其目的的优先性,那么,先验自我的困难在于,一个完全与其经验特征分离的自我,只不过是一种抽象。这种自我的统一性、优先性和独立性同样是一种任意和武断的结果。
二、罗尔斯道义论自由主义的重建
对罗尔斯来说,重建道义论自由主义,坚持道义论立场,即坚持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优先于善的基本观点,以便坚持自律的基本理念,捍卫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的尊严,就必须与康德的先验论的道义论分道扬镳,为道义论自由主义寻找新的基础,以便论证道义论自由主义的正当合理性。道义论自由主义的基础性重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定正义原则这个用以评价各种善观念和社会基本结构的阿基米德点,二是重建道义论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念或主体理论。
1.原初状态的设置
原初状态的设置是罗尔斯不同于康德先验路线的一个新的论证方案,是罗尔斯面对道义论自由主义的困难所提出的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康德是通过先验的演绎方法来克服经验主义的偶然性和任意性,达到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先验演绎方法能够确保正义原则或道德法则的优先性,因为原则和法则是不依赖于任何善观念而独立地得出的。罗尔斯要通过原初状态的设置以不同于康德的方式论证正义原则的正当合理性。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使我们能从远处设想我们的目标,但是又不会远到从超验王国的角度去设想。”⑩所谓从远处设想我们的目标,就是保持正义原则与各种价值和善观念的距离,确保道义论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和独立性,我们的目标即正义原则是不依赖于任何善观念而独立地得出的。但是这个距离又不能太遥远,不能像康德那样到超验王国去寻找正义原则。正义原则不能与社会中各种价值和善观念毫无关系。原初状态使正义原则与各种善观念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从而消解正义与善、先验与经验以及道义论与目的论之间的对立。
罗尔斯不是像康德那样从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的理性本质出发,把正义原则或道德法则推导出来。罗尔斯也从人的理性本质出发,但是正义原则是理性的人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选择。一边是理性的先验演绎,一边是理性的合理选择。所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理论,是一种关于选择条件的理论,原初状态就是罗尔斯所设置的正义原则的选择条件。罗尔斯要证明,正义原则是一切理性的个人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这既能避免经验主义的偶然性和任意性,继承先验主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又能避免先验主义的抽象性和超验性。
2.无知之幕
在桑德尔看来,罗尔斯原初状态中有两个关键性的成分似乎可以满足道义论自由主义重建的要求。一是参与选择或缔结契约的各方所不知道的东西,一是各方所知道的东西。设置不知道的东西是为了与各种价值和善观念保持距离,确保正义的优先性和独立性;而设置各方知道的东西则是为了不至于与各种善观念离得太远,以保持一定程度的经验性。他们不知道的是任何可能将他们中的每个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信息,这就是无知之幕的假设。具体地讲,他们既不知道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种族、性别、阶级、财产或机会、知识、力量或其他一些天赋能力等方面的信息,也不知道他们的善观念、价值、目的或生活追求。
设置无知之幕所要达到的结果,一是使得正义原则不依赖于任何善观念而独立地得出,确保正义的首要性和正当对于善的优先性。因为无知之幕能够“防止正义原则的选择受到自然和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各种偏见的影响。”⑪如果说先验方法是直接从人的经验处境中超脱出来,在本体的目的王国中寻求正义原则,那么,罗尔斯则是把选择者的经验处境的相关信息,以及在经验处境基础上的善观念括置起来,以免在正义原则的选择中受其影响。二是避免正义原则来源的偶然性和任意性,达到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如果选择者或缔约者知道自己的地位、财产、知识、机会以及由此决定的善观念、价值和追求,那么他们对正义原则的选择就不过是由他们的特殊善观念决定的,至少是受其善观念影响的。不仅他们的善观念对其他人来说是特殊的和偶然的,而且他们的善观念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偶然的,因为他们的地位、财产、知识等信息是会经常改变的。被选择者的特殊信息决定和影响的选择是不能达到全体一致同意的。罗尔斯是用选择条件的共同性来保证选择结果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不是从人的某种普遍本性出发推导出普遍的正义原则,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不是基于人性的普遍性。第三,无知之幕保证人们在公正平等的条件下选择正义原则,公正的选择条件保证公正的选择结果。只有正义原则得到全体一致的认同,才能保证正义原则对社会基本结构和善观念的权威性。
3.首要善和善的弱理论
罗尔斯在原初状态中设置了首要善。首要善是指那些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想要的东西,包括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一类的善。无论人们具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追求和善观念以及相应的生活计划,首要善肯定是他们的偏爱,因为首要善为人们其他善的追求和生活计划的实现提供条件。如果说无知之幕即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的设置是为了拉开与人们的经验处境和特殊善观念的距离,以避免正义原则的偶然性、任意性和武断性,确保选择的公正性、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那么,罗尔斯设置首要善则是为了使人们离开自己的经验处境不至于太远,不至于落入超验的、虚幻的境地。首要善的设置使得正义原则不是来源于先验的演绎,而是来源于人们的现存需求和真实而普遍的人类意欲。
罗尔斯始终强调,首要善必须是弱的而不能是强的,否则就离开道义论而与目的论接近了。罗尔斯善的弱理论要求,首要善并不提供判断和选择特殊价值和目的的基础,“他的目的在于保障论证正义原则所必须的首要善前提。”⑫首要善是实现人们的价值和追求的基本条件,因而是一切人都意欲的,以首要善为基础的正义原则是人们的共同选择,这足以保证在首要善基础上的正义原则的首要性、优先性、普遍性和必然性。即使人们各自有自己的特殊善观念以及相应的生活计划,但是首要善却是先在的、前提性的选择。首要善可以满足正义优先于和独立于善的道义论要求。首要善理论是善的弱理论,其弱性在于,首要善不是与人们的各种特殊善观念并列的,严格地说首要善不是一种善(强的),而是为了正义原则的选择而必须的前提。一旦正义原则通过首要善产生出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各种善观念就由正义原则来评价和规导,首要善自始至终都不能充当评价标准和规范原则。
4.主体理论:自我统一性的重建
桑德尔认为,自我优先于其所追求的目的,是道义论自由主义主体理论的核心观点,罗尔斯的主体理论的重建必须围绕这种优先性解释而展开,必须排除那种先验的解释方案,这种主体不是因为居住在本体王国中而获得优先性的自我,但也不能是一个彻底情景化的自我。桑德尔说:“对自我及其目的的解释,必须告诉我们两件而非一件事情:自我如何与其目的区分开来,以及自我如何与其目的联系起来。”⑬
“在互无利益关涉的假设中,我们发现了罗尔斯主体观念的关键,发现了我们必将成为的、将正义作为首要美德的主体图像。”⑭桑德尔认为,在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中蕴含着一种占有性主体的自我观念。这种主体观念存在于互无利益关涉的假设之中。这种假设关系到自我的本性,这种自我关注的是利益和目的的主体,而不是那些利益和目的的内容。在桑德尔看来,罗尔斯的占有性主体,即一个先在的个体化的主体与占有观念的结合,符合道义论自我的基本要求,即自我独立于和优先于其目的,自我独立于和优先于其拥有的事物,自我优先于利益、目的以及与别人的关系。这种独立性和优先性又不是通过与利益、目的等相分离,在一个超验的本体王国中获得的。占有性自我与其目的既是分离的又是联系的。
桑德尔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占有性自我概念的这一特殊功能。他说:“就我占有某物而言,我立刻既与之相关又与之相别。”⑮占有概念是一个间距性概念,它意味着我与某一事物相关,又与某一事物相别。由于与事物相关,占有性自我就不是抽象的先验主体;而由于与事物相别,占有性自我又是连续的和统一的主体,而不是彻底情景化的主体。即使我失去了事物,我依然是占有事物时的那一个我,外部事物的变化不会影响自我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三、对罗尔斯道义论自由主义的批评
总的批评观点是,罗尔斯能否走出道义论自由主义的困境,避免经验主义的情景化和先验主义的抽象化问题,正义的首要性、正当的优先性能否通过罗尔斯的方案得到正当合理性证明。
1.无知之幕问题
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常常引起人们的批评,这种批评认为,“原初状态太脱离人类环境,其描述的原始情景太过抽象,以至于无法得出罗尔斯所期望的原则;或者,就此而言不能得出任何决定性的原则。”⑯无知之幕的设置,人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财产、天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善观念一概不知,是为了人们在选择过程中不受特殊善观念的影响,确保道义论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正义的首要性、正当的优先性和独立性,保证选择的公正性和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无知之幕下既不存在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也不存在对选择有规导性的东西,因而人们根本得不出任何确定性的原则来。无知之幕不但不能保证正义原则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独立性,反而使得正义原则的选择成为一种纯粹的任意和武断。
2.首要善的问题
罗尔斯在原初状态中设置了首要善,为正义原则的选择提供前提。为了确保正义的优先性和独立性,罗尔斯区分了善的强理论和弱理论,强调首要善的弱性。但是,人们仍然对罗尔斯的首要善提出了批评。对罗尔斯首要善的批评与对无知之幕的批评正好相反。如果说无知之幕使得正义原则的选择条件太抽象,大有陷入先验论之嫌,那么,人们对首要善的批评则是质疑原初状态是否真正独立于现存的各种需求和意欲,正义原则是否不依赖于各种价值和善观念而独立地得出,正义原则的选择条件是否足够抽象以便确保其首要性、优先性和独立性。同时,虽然罗尔斯认为首要善是处于原初状态中的人们都意欲的,因而在首要善的前提下选择的正义原则是普遍的和必然的,但是批评者们认为首要善依然是一些特殊的善观念。“首要善的设置不过反应了对西方自由的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的偶然偏好,所得出的原则只是流行价值产品。”⑰因此,首要善的设置使得正义原则不过是社会中现存的价值和善观念的产物,根本没有所谓的优先性和独立性,首要善与道义论的基本立场是相矛盾的。
3.对正义美德的批评
针对正义的首要性即正义是第一美德的批评,主要是从罗尔斯所阐述的正义的环境方面进行的。与休谟一样,罗尔斯的正义环境包括两方面:客观环境和主观环境。“只要互无利益关涉的个人对适度稀缺条件下的社会利益划分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要求,就可以形成正义的环境。除非存在这些环境因素,否则就不会有任何适合于正义美德的机会。”罗尔斯强调指出:“正义的环境是人类社会的特征。”⑱批评者对正义美德的批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正义不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美德。罗尔斯的正义环境是一些经验条件,只是在某些类型的社会或社会的某些特定的阶段才具备的一些特征。罗尔斯一方面对正义的环境进行经验主义的解释,另一方面又说正义的环境是人类社会的特征,因而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验的东西就不是普遍的。既然只有在某些社会或者社会的某些阶段才会出现正义的环境,那就不能说正义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美德。显然,只有在人们之间互无利益关涉和相互冲突的社会里,在被大量分歧和矛盾所困扰的社会里,正义才是首要的。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上和政治上压倒一切的考虑就是调解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目标,以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桑德尔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并非像真理之于理论那样绝对,而是有条件的。”⑲在包括部落、邻居、城市、乡镇、大学,以及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中,由于这些共同体具有共同的情感和共享的追求,在这些共同体中正义不是首要的美德。
其次,正义只是一种补救性的美德,正义甚至不是美德。正义美德的补救性在于,当一个社会陷入道德堕落时,用正义来做修理的工作。既然正义只是补救性的美德,那就说明正义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美德。休谟也认为正义是补救性的,一个社会的人们越仁慈越慷慨,正义的作用就愈发微小,甚至根本没有作用,而那些更高尚的美德将被置于首要的地位。同时,不能说正义的增进意味着社会道德的进步。实际上,当社会更多地需要正义原则来调节时,说明真正的美德已经衰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充分的正义也根本无法弥补道德的缺陷。因此,“如果正义的增长并不必然隐含着一种绝对的道德进步,那么,可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正义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恰好与之相反。”⑳
4.对罗尔斯主体理论的批评
对罗尔斯主体理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先在个体化的主体观念进行的。在桑德尔看来,虽然罗尔斯通过占有性主体概念,把自我与目的既区分开来又联系起来,既避免先验主体的抽象性,又防止成为经验主义的彻底情景化的自我。但是,罗尔斯的主体理论中明显地存在着先在个体化的观念,以及主体的多元性优先于统一性的观念,这是罗尔斯主体理论的基本悬设。“多样性相对于统一性的优先性,或者说主体在先的个体化观念,所描述的是首要的正义必须获得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条件。”21罗尔斯表达了一种个人主义偏见,排除了或者说贬低了诸如仁爱、利他主义和共同体情感等方面的价值。“原初状态所预设的恰恰不是一种中立的善理论,而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观念。”22
桑德尔认为,正是这种先在个体化的主体观念使得罗尔斯占有性主体的理论不能获得成功,即一方面要坚持自我优先于目的的道义论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又要与其目的相联系,不能成为一个本体王国的超验主体。因为这种先在个体化的主体观念,预设了与其所拥有的目的和利益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将自我置于超越经验极限的地位,一次性地也是永久性地将其身份固定下来。”23显然,先在个体化主体的预设与占有性主体观念处于相互矛盾之中,一方面预设了具有先验性质的主体以捍卫其道义论原则,另一方面又阐述一种占有性主体概念,以避免完全与目的和利益分离的超验主体观念。
在桑德尔看来,这种先在个体化的主体观念的重要后果是,人与人的关系、统一性和共同体不能从这种主体理论得到理解。因为这种主体观念认为,道德主体的基本特征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需求和欲望、目标和属性、追求和目的,来刻画人类的特殊性。每个人都被独一无二地嵌入时空之中。”24不能因为罗尔斯的占有性主体观念,就认为统一性和多样性都具有同等的优先性。在罗尔斯那里,人类主体的统一性必须以其多样性为前提,却不能反过来认为统一性是多样性的前提。
罗尔斯的主体理论,那种先在个体化的观念以及多样性对于统一性的优先性,“排除了主体间的或主体内的形式的可能性。”25因为这种主体间或主体内的自我并不预设一个先在个体化的自我。主体间观念对自我的解释不是侧重于单一的、个体的人。另一方面,罗尔斯的主体理论也完全排除了主体内观念,不能理解单个的个体人内部自我的多元性。按照内在主体的观念,在一个自我之内存在着多个自我。正因为罗尔斯的主体理论排除了主体间性和内在主体观念,所以它就把人们的公共生活,以及以共同的追求和目的为基础的构成性的共同体排除了。在罗尔斯那里,我们首先是不同的个体,然后我们才与他人建立关系并作出合作安排。但是,在桑德尔那里,我们已经先在地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我们的自我完全是由共同体内的公共生活的参与构造出来的。
注:
①③⑤⑦⑧⑨⑫⑱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1、3、587、560、28、396、129—130 页。
②④⑥⑩⑪⑬⑭⑮⑯⑰⑲⑳ 21 22 23 24 25 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 20、22、4、31、31、67、68、69、34、34、39、42、66、75、77、6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