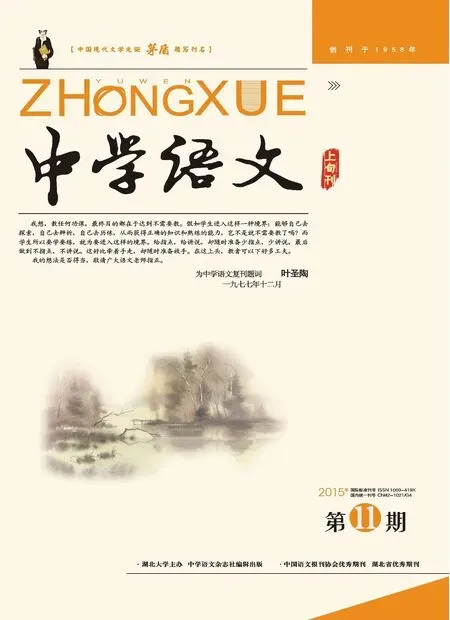文字彩衣下的陷溺心灵
——陆蠡《囚绿记》细读(上)
苏宁峰
文字彩衣下的陷溺心灵
——陆蠡《囚绿记》细读(上)
苏宁峰
《囚绿记》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散文家陆蠡的代表作,同时,陆蠡也以之冠名自己最后一本散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其编选在现行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第二册第一单元中。我相信,这是对这位诚悫忠直的、牺牲于抗日年代的年轻作家最好的纪念与致敬。
有意思的是,苏教版与沪教版也将此文选编入初中语文教材。能同时入选三种教材,可谓名篇,然其篇章虽名,其旨却未必昭明。罔顾全篇而断章取义,不及细读却袭用陈说,讲“政治正确”,贴政治标签,将文学教育庸俗与狭窄化为政治教育,这种现象至今仍时时出没于深具教学权威性的教参之中,其流毒之深可见一斑。今不揣简陋,以人教版的《教师教学用书(必修二)》的解读为据,对《囚绿记》作批判性的解读,以期就正于方家。
一、教参:政治主题的预设与粗疏的阅读态度
众所周知,陆蠡的《囚绿记》大致写于卢沟桥事变的后一年。其文在篇末有一处叙述:“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担心我的朋友电催我赶速南归。……离开北平一年了。我怀念着我的圆窗和绿友。”文章以“囚绿”为题,其情节则以叙述“我”与“绿”的关系为主:寓居在北平的“我”因为孤寂,也为了排遣孤寂而选择了一间窗外长有常春藤的屋子。“我”为了装点过于抑郁的心情,将窗外的常春藤拉进屋来“囚禁”,让这“绿”“为我作无声的歌唱”。案前蓬勃生长的常春藤让“我”发现了“生的欢喜”,但常春藤却因为被囚禁而日渐憔悴。我自觉“自私”,却有了“魔念”而不放走它,直到卢沟桥事件发生。临行前,我开释了“这位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并在离开一年后还怀念它。人教版教参编者为它整理出了简要的情节线索:“我”寻绿、观绿、囚绿、放绿和怀绿。
在主题认知上,编者驾轻就熟地将它预判成是一桩政治历史事件的反映。其先入为主的思维痕迹很清晰地留存在“整体把握”一栏中。编者说:“时值日寇入侵,华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作者是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作家,国难当头,不能不愤怒、忧烦,不能不生出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这也应该是作者写作本文的直接原因,但这种心绪表现得非常隐蔽,文章之‘巧’由此而来。”①
这“不能不”与“应该是”的结果便是编者将那主观先验的、政治主题的预设很深地楔入到解读之中——这正是庸俗政治解读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其贫乏僵化的思维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一种先声夺人不容辩驳的专制霸气。政治高于艺术,臆测先于文本,编者甚至不是失误,而是有意地将创作背景当作创作主题,将背景对于文本的可能影响当作必然影响与实然影响,也就是将“可然”读成了“必然”与“实然”。——至于文本中明显缺乏支持编者主题的证据,那也无妨,因为“这种心绪表现得非常隐蔽”,因为“非常隐蔽”所以“文章之‘巧’由此而来”。
这种专制粗疏的态度只好与支离破败的逻辑结婚,诞生出许多脆弱的结论。我们撷取编者在教参中有关文本主题的相关表述来简析。
在“整体把握”栏目中,编者说:“(本文)含蓄地揭示了华北地区人民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命运,象征着作者和广大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在这里干脆脱掉“含蓄”,直接挑明就好,编者的逻辑比附是:被“囚”的“绿”,象征着“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华北地区人民”;既然是被“囚”,那么命运是“苦难命运”;既然是作者情感上赞美“绿”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那么,自然就“象征着作者和广大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问题是:“囚绿”这施虐动作的发出者是“我”啊,如果说被“囚”之“绿”可以象征“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的话,那么,“我”就应当是那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象征啊!“我”怎么可能也成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的象征!难道是作恶者与受害者共同站在道德精神的神坛上深情相拥接受祝福?
在“问题探究”栏目中,编者说:“‘囚绿’写绿枝条最艰难的状况,这暗示着艰难的国运家运;‘囚绿’表明作者复杂的心情,这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领土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内心极度痛苦和精神上坚决反抗的反映。”
先吹毛求疵一下:“‘囚绿’写绿枝条最艰难的状况”应当是“‘被囚之绿’写绿枝条最艰难的状况”,编者表述时,主客体颠倒了。
在这里“绿”象征义变动成为“国运家运”了。而将“绿”囚禁起来的“我”“内心极度痛苦和精神上坚决反抗”。
问题是:作为施虐主体的“我”囚禁“绿”时有过道德上的自我审视,说自己是“自私”与“魔念”,但在行为上却坚决明确,一直将“绿”囚禁到“我”离开北平时。对此,“我”不仅并无忏悔与羞惶,而且“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超过了任何种的喜悦”。可见,教参中所说的“内心极度痛苦”并非由“囚绿”而起。再有,是“我”施虐于“绿”,那么要进行“精神上坚决反抗”的主体也应当是“绿”啊,有谁能够理解:“我”一边喜悦地施虐于“绿”,一边又痛苦地在精神上自我反抗施虐?这是陆蠡的变态还是解读的错乱?因此,“精神上坚决反抗”的判断也是逻辑倒错。
在“关于练习”栏目中,编者说:“作者最后怀绿,其实也是在怀念苦难中的北平人民。这是暗示的写法。”
在这里“绿”像钟摆一样,又摆回来象征着“苦难中的北平人民”。其义大体接近于“华北地区人民”了。
可也就在“关于练习”栏目中,编者又说:“‘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可见作者把绿色当作希望、幸福和快乐的象征。”
在这里编者又承认作者在文中的说法。但若是将以上几种说法摆列在一起,划个等号,那逻辑上该是何等的混乱!
但这些矛盾含混的乱象还仅是一角,我们不妨再深入一步,撷取教参中有关文本的基本关系与结构的表述来简析。
众所周知,“我”和“绿”的关系是横贯全文的大脉络,也是解读的关键所在。
在“整体把握”栏目中,编者说:“‘绿’是全文描写的客观对象,作者围绕‘绿’展开思路,铺设线索。”
在 “关于练习”栏目中,编者说:“作者紧紧围绕‘绿’做文章,那么读者就应该抓住‘绿’来理解文章,抓住‘绿’就抓住了文章的中心。”
在这里编者认为在“我”与“绿”的关系中,“我”为宾,“绿”为主,甚至于见“绿”不见“我”,“绿”才是叙述的侧重点与解读的关键点。——这个认识很重要,因为它正是编者众多逻辑结论的推断起点,也是文章“筋骨肯綮”的聚结之处。编者紧扣“绿”推演概括出本文的结构思路是:“文章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 ‘寻绿’‘观绿’‘囚绿’‘放绿’和‘怀绿’。”
应该说,在这粗放的结构线条里有着粗砺的迷惑力:“我”与“绿”的关系一以贯之。紧扣“绿”则处处有“绿”,而动作中又处处有“我”。但编者的认知与概括是否稳惬周圆,则还需要与文本本身作逻辑形态上的梳理、检视与比对。
依照编者的判断:“绿”是关系中的主体,“绿”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象征着“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坚强高尚的精神品格”。那么顺此逻辑推演的结论应当是:“绿”是写作的重点,是正面表现的对象。那么,“囚绿”的“我”自然是作为“绿”的反对面——将苦难加诸于“绿”的象征体而出现,结合编者那“不得不”和“应该是”的创作背景理解,那“我”就应当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象征。另外,“我”是作为突出“绿”的精神气节品格的衬托体而存在,那么,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象征的“我”的形象与情感应当是猥琐、阴险和恶毒的,或者在开始时是负面的,然后受“绿”的精神感化而发生忏悔与改变。依此推演,则本文合乎逻辑的结构思路应是:寻绿——囚绿——放绿。
陆蠡原作中那深切表达“我”对“绿”的渴恋之意的“观绿”与“怀绿”部分是大可以删掉或简写的。重点情节应当是“囚绿”,且在具体写作中应当突出“绿”,应当详细地叙写它在被囚受虐时的坚强与反抗,尽写“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是如何“永不屈服”的。至于“我”,则应当突出叙写囚虐“绿”时的变态心理和行为,以及随后释放“绿”时的忏悔心理。而且,在写到对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的敬意时,就应当写“我”因感动而立即放了它,而不是“仍旧不放走它”直到我离开北平。
但不幸的是,这样的逻辑推演与写作重点在许多方面与陆蠡原作之间都有着巨大的差异。陆蠡的原文里,“我”与“绿”的关系中,“我”是真正的主角。“我”是以两种方式在两个层面上存在的:行为反应与心理情感。二者关系中,“我”对“绿”的心理情感是原因,“我”对“绿”的行为反应则是结果。心理与行为既构成完整的“我”,又结成因果关系,推动情节的展开。而编者分明只是从“我”表层的行为反应来概括,而忽略了“我”的心理情感的层面,这种概括的失真失准度也大可想见。
二、还原:真实背景的梳理还原
对于散文《囚绿记》而言,“我”与“绿”的关系以及对“绿”的象征义的理解,是事关根本的问题;而对根本性问题的理解失误将会导致全局性系统性的错误。可以看出,人教版教参在解读《囚绿记》中“绿”的含义时,是将“绿”从与“我”构成的关系中剥离出来单独解读的。但问题恰在于:“绿”的含义无法只通过自己而获得全面准确的诠释,因为“绿”处在一定的关系中。
关系即是解读的背景与定位。原型理论家弗莱说:“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构成了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②推原其理,则作家的任何一篇作品也都是置于一系列关联域及其关系之中的。因此,对《囚绿记》散文意蕴的探讨,若能置放于其散文集的文字经纬背景前,则不仅有利于定位,也更有助于相互比较阐发。
真实的陆蠡一直存活在他所有的文字里。如果我们不是懒怠地自我囚禁在《囚绿记》的文字监狱里,那么只须走出一步,便可看见他的《〈囚绿记〉序》,便可听到他的心灵告白:“我是感情的奴役,也是理智的仆隶。我没有达到感情和理智的谐和,却身受二者的冲突。”③“在这矛盾和中,我听到我内心抱怨的声音。有时我想把它记录下来,这心灵起伏的痕迹。”④
序言里,他所确定的是《囚绿记》这整部散文集的主题基调。他说得明白,他想写的就是自己的心灵故事与生命事件。但是有些论者却不想让他就这么被人明白,他们说:只叙写自己的心灵事件,这能有多大的文学价值?这部散文集既然是编成于1940年那火热的抗战年代,怎么能不带有抗战的影子?只有跃进到时代精神与民族气节的主题天空,作品才能在思想与艺术上保持高度!但是,这种思想臆造出的只是政治标签,却永远无法是文学评论。
既然篡改与附会是这种评论最大的武器,那么,我们只需要还原真实就能击溃它。在散文集《囚绿记》的序言中,陆蠡无一字涉及他所在的抗战时代与民族精神,他只说此文集记录下的是他在感情和理智方面冲突的“吞吐的内心的呼声”。在其文集辑录的九篇文章里,按照内容大体可分三辑:心灵情愫;故园的昆虫鸟兽与乡间往事;生命故事。在此逐篇简提,罗列其下:
《囚绿记》:寓居北平期间与离开后,“我”寂寞的心灵对“绿”的渴恋与怀念。
《光阴》:秋郊散步,“我”假想与自己“思想”开展的关于“光阴”的心灵对话。其间穿插着对父祖“珍惜光阴”往事的回忆。
《寂寞》:真实地假想“我”与寂寞相习相处相安的生命故事。
《门与叩者》:一个因为过分的寂寞而催生出的假想的故事,它透露着寂寞地生活在门内的主人(“我”)被寂寞拜访的渴望。
《乞丐和病者》:假想“我”是乞者与病者。乞者虽一无所有,却拥有美丽的幻想、珍贵的空闲与宝贵的祝福;“我”因一时惜己之心而“病”,而病是人生“乐曲的休止符”。
《昆虫鸟兽》:故乡杂忆。分篇写自己童年乡居时有关“白蚁”“鹤”“虎”的家庭与村居往事。
《私塾师》:“我”幼年时的私塾老师在时代转型期的艰难生活。
《独居者》:“我”无意中发现了独居者C君生命秘密的故事。
最后剩下的一篇《池影》也最有意思。因为他一开篇就提到抗战,这让那些预备贴政治标签的论者血脉贲张:
“我来这池塘边畔了。我是来作什么的?我天天被愤怒所袭击,天天受新闻纸上消息的磨折:异族的侵陵,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正义在强权下屈服,理性被残暴所替代……我天天受着无情的鞭挞,我变成暴躁,易怒,态度失检,我暴露了我的弱点……”
但紧接着,文字便迅速转折了,转到了陆蠡最熟悉也最喜爱的主题“生命的自我审视”上,这将让此类论者因预期的完全落空而陷入荒诞与绝望——这不是因为忠厚憨直的陆蠡在耍人,但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是陆蠡给他们的诚实评论的忠告。
“我所以特地来偷一刻的安闲,来这池塘边散一回步。我要暂时忘却那些不愉的念头,借这一泓清水来照一照我自己,瞧一瞧我原来是怎么样的。”
于是此后,陆蠡就写自己逡巡池边,在“我”和“我的影子”的假想的心灵对话中回忆自己的生命往事:婶母的故事、祖父的故事、池塘的故事,最终仍旧绾结到“我”的感慨上,“我是怎么了?我是坐在这池水旁边,我原是为了来看我自己的影,而我想起了它,忘了我自己。……”在这篇故事中,“抗战”只是缘起,陆蠡对自己的心灵审视与生命回忆才是此文的主旋律。
其实,陆蠡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即时政治题材的疏离、淡然与超越并不让人诧异。他生前出版的三部散文集《海星》《竹刀》(又名《溪山集》)与《囚绿记》,论时间大都在抗战期间,可真正表现抗战的篇章,严格来说,并无一篇。《海星》是他的处女作,出版于1936年,其中大量短章,有着美的旋律与诗的素描,文字则有着“月下,这白玉般的石桥”的“古典的和谐”之美韵,整部文集处处流溢着“爱与美的青春幻想”的清澈情思;《竹刀》则出版于“淞沪会战”后的1938年,他评说:“这集子,可作为我生命的里程碑。往事如坠甑,我颇懒于一顾。倘不幸遗下一丝感喟,那不过是凡人之情而已。”也就是说,他文集中所写的依然是“凡人之情”的“一丝感喟”:列于文集篇首的《溪》写的是“故乡的山水乃如蛇啮于心萦回于我的记忆中了”“我如怀恋母亲似的惦记起故乡的山水了”;而其后的篇章中则基本无不是故乡风物和由此生发的生命感喟的了。而写于1938—1940年间的散文集《囚绿记》,其主题依然是对自己的生命审视与感喟,用他在序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在理智与情感“将失未失的平衡中,在这矛盾和中,我听到我内心抱怨的声音”的“心灵起伏的痕迹”。
这些背景的梳理还原将有助于我们确立真实判断的基础:我们的鉴赏解读应当立足于每一位作家在他所有文字中所存留下的生命真实,或者至少说,我们鉴赏解读的第一步应当是由此而迈出的。我们无法通过机械的政治历史的预设而预定了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创作主题。当时代的政治性宏大命题并没有内化并进入一位作家的心灵真实与能愿范围的时候,它们就始终像是陆蠡在《门与叩者》中所写道的那样:文字门外短暂叩门就匆匆消失的访客。作家的“门又轻轻地掩上。这样轻轻地,连停在门上的蝇虎都不曾惊动。”
①文中所引教参的内容,均来自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二)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版。
②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惠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③④袁振声编:《陆蠡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第2版。
[作者通联:福建厦门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