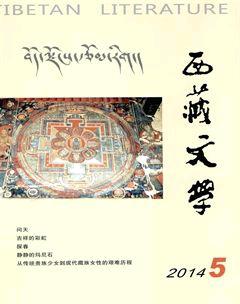回归:洼西文学创作的一种倾向
马传江 朱霞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四川藏族作家洼西彭错的《雪崩》等作品,归纳出其文学创作的一种倾向:回归。这种回归,体现在叙述上,是向故事回归;体现在修辞上,则是以互文的手法回归世界丰饶的本相;在精神指向上,则体现为其向“家园”回归的努力。
【关键词】回归;故事;互文性;家园
“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不无留恋地哀叹。在网络不断渗入生活,面对面的交流经验被日益剥夺的当下,我们听到好故事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些故事总是长着相似的面孔,以难以辨认的模样伫立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四川藏族作家洼西彭错的作品显得别有意义。
一叙述:回归故事
《乡城》是洼西彭错近几年发表的小说,散文等作品的结集,我们重点说小说。洼西彭错的小说,重新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向故事本体。花样翻新的叙述手段,相较于故事本身的跌宕起伏而言,他选择后者。如此一来,他的小说叙事便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底本时间的长度增加。底本时间与述本时问,是四川大学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提出来的概念吲。大略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在当代中短篇小说中,由于写作者对于生活片段的愈加重视,小说对于生活横截面的书写愈来愈多,相应地,就导致小说底本时间在不断缩减,在极致之处,几秒钟发生的故事也可能构成一部中篇小说的描述对象,西方意识流小说可以推为代表。
而洼西的小说就呈现了一种回归。一种重新回归故事的讲述,回归故事本身的波澜起伏,而不是叙述手段的花样翻新。这种讲述的一个首要特征,即在于底本时间的长度增加。《雪崩》讲述了泽仁顿巴从一个17岁的小僧人到成长为乡城上游头人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底本时间从1919年开始,1930年泽仁顿巴死亡截止,长达11年。在这11年间,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都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讲述——如泽仁顿巴母亲卓嘎的寻仇者的到来,这直接导致了泽仁顿巴命运轨迹的改变:从此刻开始,他舍弃掉一个小僧人的身份,向一个乡城头人的目标进发。
2、情节的链状形态。讲一个有“空缺”的故事,自从格非开始,似乎成了一种时尚。在格非的小说《青黄》中,青黄到底是什么,文本没有回答。而“空缺”的设置,就让人物的行动链自行散开,难以为继。洼西小说回归故事的另一个标志即是这种链状情节的设置:一个序列的结尾,同时是下一个序列的开头。仍以《雪崩》为例,泽仁顿巴的身世之谜,在小说开篇就被提了出来,这不仅是卓嘎的困惑,亦是我们的困惑。有了困惑,便要解开。随后布根随从的寻仇,卓嘎的自尽,泽仁顿巴的还俗以及随后成为乡城上游头人的继位者,到重修桑披岭寺,以及桑珠来信身世之谜揭开,泽仁顿巴死亡。情节链环环相扣,次第展开。
3、编年史的手法。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历史叙事手法,有利于读者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了解历史事件,便于了解历史事件间的互相联系。这种编年史的手法,在当代小说中被大多数人舍弃的原因之一,恐怕在于,这样一来讲好一个故事的难度颇大。再加上人们的阅读经验日趋复杂,顺叙的时间安排可能很难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洼西重新拾起了古老的手艺,将中国人写史的手法运用在了小说之中,以编年史的形式讲起了故事,并讲得有声有色。如《1901年的三个冬天》,这篇小说以人的欲望为叙述核心,展现了1901年冬天由“乡城民兵统领”布根登真之死所引起的喧哗与骚动。小说的第一部分标题为“1901年11月27日,夜”,第二部分“1901年11月28日,晴”,第三部分“1901年11月29日,晴”,第四部分“1901年11月29日之后,阴晴不定”。
而在《雪崩》中,章节的小标题“1919年,折曲寨小僧人泽仁顿巴”,“1920—1924年,乡城上游地区头人的继位者”,“1925年,甲日烟道借道求和亲之旅”,“1930年夏,亚丁神山脚下的约瑟夫·洛克”,依年份排列,脉络清晰。
二修辞:通过“互文”回归世界的丰饶本相
“互文性”理论自确立至今,尚不足五十年,但已成为当今文学研究与批评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它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当代法国文学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而这另一文本,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文本。这个互文本,可以是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也可指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
如果我们将“互文”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当然,这里的修辞,并不是指语言的措辞、用法等问题,而是韦恩·布斯所说的,作者的叙述技巧、文学的阅读效果等问题——那么,几乎可以说,互文是洼西小说的一个重要修辞手段,在小说文本对历史文本的吸收与改编之中,洼西揭示了色彩斑斓蕴涵丰富的虚构世界如何成为可能。
在小说《1901年的三个冬日》和《雪崩》中,作者都提到了《乡城县志》、《乡城大事记》等地方史志,尽管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判定小说中的这些史志是否真实存在,而其引文又是否与地方史志完全一致,不过莫言已经用《红高粱》中的县志告诉我们,小说家言,岂可尽信?好在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并非至为重要。
重要之处在于:历史,只是洼西小说的凭借,借由历史或者虚构的历史——它们无一例外地显得色彩单调——作者试图复活一个曾经存在的人物或者世界,一个曾经存在于历史,或者存在于作者头脑的人物或者世界。而这个世界,业已展现出远比历史叙述更为斑斓的色彩,并作为一个丰饶而广阔的地带存在。以泽仁顿巴来说,那些地方史志的简略叙述所勾勒的是一个扁平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人物形象:乡城土匪头子。而小说则不然,它以长达三万字的篇幅使得泽仁顿巴立体可感:他天资聪颖,体形彪悍,富有政治头脑,他儿女情长,又胸怀壮志,他心狠手辣抢掠财务又修葺寺庙广种善缘,这样的一种圆型人物,才是作者欣赏的人物,而这种互文的手法,便体现出了作者努力的方向:让世界回归其丰饶的本相。
洼西小说中还存在另一种互文的情况,即,此一小说和彼一小说的相关性。如《雪崩》和《1901年的三个冬日》的互文。两个文本的相互指涉,几乎可以将《雪崩》看做是《1901年的三个冬日》的接续。《雪崩》中泽仁顿巴报仇的因由正是《1901年的三个冬日》中卓嘎受沙雅指使对布根登真的杀害。如此以来,我们或许可以推测,作者试图以一部长篇小说,建构一长段时期的历史,使这一段时期回归其丰富本相的雄心隐隐可见。
三精神指向:回归“家园”
“家园”,在某种程度上,和“故乡”、“家乡”等词同义,但除了一种亲切、依恋、舒适的情感蕴涵之外,相较于“故乡”等词,“家园”又多了一种形而上的意味。这种意味是由海德格尔赋予的——他在解读荷尔德林的诗作《返乡——致亲人》时,认为“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并在随后的诗学论文里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使之上升到存在主义的哲学高度。
海德格尔的诗学传人中国后,“家园”的形而上内涵得到普遍认同,它的使用也相应由经验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雪崩》中泽仁顿巴为母亲报仇,可以解读为一种回归以母亲为代表的家园的努力,而其自杀,则是在得知其错认父亲、错杀兄弟之后,精神家园的瞬间崩塌所致。至于《祖父之死》中“我”念兹在兹的对于祖父故事的还原,无外乎是一种对于精神家园回归的努力。
而在洼西的诗作中,我们发现其家园的精神指向的表达是通过对自然的编码来实现的。
生活在远离家园的城市/我像一柱炊烟/轻轻散在风里——《家园》(见《民族文学》,2003年第2期,39页)在这首题为《家园》的诗里,洼西表达了一种无家的窘境:“烟”的意像,意味着无根,漂泊,意味着对城市文化的不认同。而“风”则是漫无边际、不可触摸、无可归依的心理状态的象征。这样的时刻,他只能在回忆中,通过对自然的编码复活关于故乡,关于家园的记忆:荞麦花流成了海/一段当年的情歌/隐隐约约在耳边唤归
而那些在故乡的老朋友也随之一一鲜活起来:那时在乡下/阳光很温暖/老朋友们一起/说说笑笑唱唱——《阳光下的老朋友》(见《民族文学》2006年6期,87页)
那个悬挂在空中的月亮,也同时被重新编码,携带了精神意涵:月亮不在天上/在我的家园/白发的娘亲和孤灯下的爱人/把满月熬成新月/又把新月守成满月/家园的方向/从来月光如水——《月亮不在天上》(见《民族文学》2006年6期,88页)
“现代人已经处于无家可归状态”,这是海德格尔以深刻的历史感,深入到人类特别是现代人类生存的历史中思考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正因如此,现代人对“家园”的找寻在情理之中。具体到洼西,我们看到,在家园的声声召唤之下,他已经在诗中启程。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