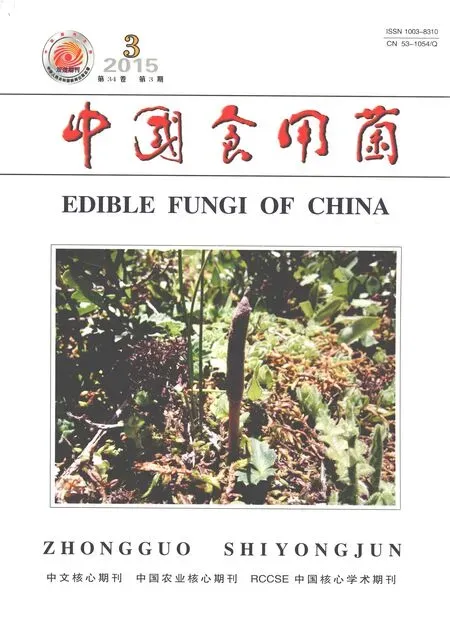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的菌文化
王 强,刘盛荣
(1.宁德师范学院思政部,福建 宁德 352100;2.宁德师范学院生物系,福建 宁德 352100)
〈菌蕈文化〉
论中国古代的菌文化
王 强1,刘盛荣2
(1.宁德师范学院思政部,福建 宁德 352100;2.宁德师范学院生物系,福建 宁德 352100)
中国古代人很早就认识到菌类生物的食用与药用价值;并在与菌类的长期接触中,通过对它们外形特征、生活习性的了解,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菌文化。一方面,许多人因芝菌类生物的稀缺难觅以及奇异的外形,称其为仙草,将其视作祥瑞;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因菌类生物寄生或腐生的异养生活习性,以及某些菌类生物看似短暂的生命周期,而将菌类生物视为不祥之物。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对于相同的客观事物,不同背景的观察者会给出不同的主观解释,进而赋予事物不同的意义。
菌文化;祥瑞;凶兆;主观解释
中国古代对于菌类生物的了解很早,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对菌类生物习性认识的逐步加深,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菌类文化。在古代,除了食用与药用功能外,菌类生物还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但有趣的是,古代有关菌类生物比较主流的象征意义有两种,一种将菌类生物视作祥瑞,另一种则将其视作凶兆,寓意截然相反。
1 中国古代对于菌类生物的总体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菌类生物的称呼主要有“菌”、“芝”、“蕈”等。
《说文解字》对于菌的解释是“地蕈也。从艸囷声。渠殒切”[1],对于芝的解释则是“神艸也。从艸从之。止而切。[1]”至于蕈,《说文》的解释是“从艸覃聲。慈衽切。[1]”而《康熙字典》引《唐韵》的说法,蕈乃是“菌生木上”而《玉篇》的说法则是“地菌也”。
从对于菌、芝、蕈等字的释义可以看出,在古代,人们已经注意到菌类这一生物类别,但限于生物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多将菌类生物视作草的一种或者说认为菌类生物与草本植物相近。当然对于菌类生物的一些独特性状,古人亦有一定的认识。应劭曾言:“芝,芝草也,其叶相连。[2]”很直接地点明菌类生物外形结构简单,没有根茎叶区别的特点。而《列子》一书中曾言“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说明古人对于菌类生物异养的特性已经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颜师古在注《汉书·东方朔传》时,曾对“寄生”一词时有过考释,他认为“寄生者,芝菌之类,淋潦之日,著树而生,形有周圜象寠数者,今关中俗亦呼为寄生。非为茑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叶者也。故朔云‘著树为寄生,盆下为寠数’。[3]”而司马彪在注释《庄子》中“朝菌不知晦朔”一句时,解释到“大芝也,天阴生粪土上,见日则落。”[4]可见,在唐代以前,古人们对于菌类生物乃是依靠腐生或是寄生才能存活的异养生物这一特征的认识已经进一步深入。
另外古人们也很早就开始尝试采摘菌类进行食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黄帝杂子芝菌》一书,颜师古的注文解释其书乃是“服饵芝菌之法也。[3]”可见在汉代以前,食用菌类生物的现象就已经极其普遍,以及有专书介绍服用之法。另外根据陈士瑜《中国食用菌栽培历史初探》一文介绍:
早在二千多年前,菌类即已成为珍贵的食品,《礼记·内则》说:‘食所加庶,羞有芝栭’;《吕氏春秋》也说:‘味之美者,骆越之菌’;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内,还有‘蒸菌法’、‘木耳菹’等食菌加工方法,也反映出人们对菌类的爱好而促进了加工技术的发展。《神农本草经》内还多次谈到,经常食用某些菇类,可使人‘轻身不老延年’[5]。
另外对于菌类生物的药用保健功能,古人亦多有认识,明代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收录了大量的菌类药材,其中特别在菜部介绍了芝、木耳、杉菌、皂荚蕈、香蕈、天花蕈、蘑菰蕈、鸡、舵菜、土菌、竹蓐、雚菌、地耳、石耳等十五种菌类生物(详见《本草纲目》菜部第二十八卷,菜之五),李时珍将这些菌类归入菜部,乃是认识到了这些菌类生物作为食材与药材的双重属性。另外,古人们已然注意到了菌类生物味道鲜美,但某些种类含有致命毒素这一性状。《康熙字典》在对菌字进行释义时,注引了张华《博物志》的说法,“菌,食之有味,而常毒杀人”,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里记载生于苦竹边的竹蓐有毒,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是对各种可做药材或是食材的菌类生物是否有毒,以及毒性的大小进行了标注。
相较于食用、药用等具体实际用途之外,探讨中国古人对于菌类生物文化象征意义的分歧与差异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与通常所见的先扎根土壤,再逐渐抽枝发芽,进而开枝散叶,最终花果繁茂的草木植物不同,通过孢子方式在自然界进行传播繁殖的菌类生物,给古人们一种从天而降的神秘感,因此在古代,人们经常将菌类生物的出现视作一种上天对于人们的启示。但有趣的是,有些人将之视为祥瑞之兆,而有些人则将之视为凶兆。
2 象征祥瑞的仙草
菌类生物,特别是其中的芝类,在中国古代多被视为祥瑞之征兆。据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转引的《神农经》上的记载称:“山川云雨、四时五行、阴阳昼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为圣王休祥。[6]”
菌类生物与普通的植物相比较,有着较为独特的奇异外形。菌类生物没有明确的根茎叶区分,其中野生的芝菌类生物更是数量稀少,又多生长于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难以采摘,因此常被古人们称为仙草,自先秦时代起,芝草等菌类生物便被视为是修仙者食用的好食材。在《汉书·艺文志》中记有《黄帝杂子芝菌》一书,而班固对其的介绍乃是“服饵芝菌之法也”的书籍,并将其归类为神仙家之列。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转述:“生于刚处曰菌,生于柔处曰芝。昔四皓采芝,群仙服食,则芝亦菌属可食者,故移入菜部。[6]”
秦汉时代诸多帝王人物亦对于芝草颇为痴迷。秦代方士卢生就曾向秦始皇吹嘘芝类的奇效,他说:“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2]”始皇帝对此信以为真,并还因自己行踪遭泄露,而大开杀戒。
而另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汉武帝,同样对于求仙之事也同样颇为热衷;相较于秦皇,汉武在这方面花费的人力物力可谓不遑多让。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听信方式公孙卿之言,“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2]”不过相比于始皇,汉武帝似乎要更“幸运”点,史载“(元封二年)夏,有芝生殿房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有光云,乃下诏曰:‘甘泉房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2]”另外据班固《汉书》对此事的记载,汉武帝因为此事,还专门下令“作芝房之歌。[3]”如淳的注释引用《瑞应图》的说法认为“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旧故,则芝草生。[2]”而《瑞命记》则认为:“王者仁慈,则芝草生。[6]”而这株令汉武帝兴奋不已的“仙草”,其最为“祥瑞”的特征乃是“九茎连叶”[3]。而古人眼中的这种茎叶相连,无疑是菌类生物子实体的一种外形。晋代的葛洪曾有记载“木渠芝,寄生大木上,状如莲花,九茎一丛,味甘而辛,[6]”汉武帝时期的这株芝草生长于巍峨的甘泉房中,而宫殿之内不缺的就是大型的木材,因此这株芝草是葛洪所说的“木渠芝”的可能性极大。
另外由于菌类生物多生长于腐朽潮湿之地亦或枯木石缝之间,而在古人看来,这些地方并不适合生物生长,但菌类却能立足,因此许多人将其归结为统治者的德行高尚,从而使得腐地生物。柳宗元的说法便是:“使受天泽余润,虽朽枿败腐不能生植,犹足蒸出芝菌,以为瑞物。[7]”
汉宣帝时期,曾因为祥瑞频现而改元康年号为神爵,而这些祥瑞中便有菌类生物的踪迹。在宣布更改年号的诏书中提及:“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厥理。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惧不能任。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所振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3]”汉武帝时期曾出现于甘泉房的九茎芝草再次出现于函德殿中,这令宣帝感到十分的惊喜。可见,在西汉之时,诸多君臣将菌类生于宫殿视作祥瑞之兆,乃是上天对于西汉诸帝德政的感应。
而在东汉,芝草现世同样也被比附成了大汉德被苍生的象征;班固与王充这两位东汉时代的大学者也均对芝草青睐有加,班固在《白虎通》中认为“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芝实茂。”王充则在其《论衡》中认为“芝生于土,土气和,故芝草生。[6]”可以说,在他们看来,芝草现世,乃是统治者德被天下的表现,是一种吉兆。而在正史的记载中,东汉统治者对于芝草这一祥瑞亦极为重视。明帝时,“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而汉明帝本人亦将“芝草生于殿前”这些自然现象视为祥瑞之迹,并将随之而来发生一系列事件视作乃是感应祥瑞而生,因此认为: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觞,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由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从官视事十岁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奉赎,在去年以来皆还赎[8]。
而汉章帝时期,又因“凤皇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8]等祥瑞,改元和年号为章和。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菌芝的喜爱热情不曾减退,张华在为西晋朝廷所造的《大豫舞歌》里写到“潜龙跃,雕虎仁。仪凤鸟,届游麟。枯蠹荣,竭泉流。菌芝茂,枳棘柔。和气应,休征滋。协灵符,彰帝期。绥宇宙,万国和。昊天成命,赉皇家,赉皇家”[9],可见其将菌芝茂视为祥瑞之兆。同时,这一时期亦是道教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而被誉为“仙草”的芝类生物在这一时期亦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葛洪《抱朴子》一书对于芝草的各种分类,各类芝草的颜色、性状以及如何采摘芝草、如何服食芝草都有详细的记述。在葛洪的时代,人们已经确认了: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凡数百种也”,同时对于这些菌芝的形状亦多有详细了解,“石芝石象,生于海隅石山岛屿之涯。肉芝状如肉,附于大石,头尾具有,乃生物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大者十余斤,小者三、四斤[6]。
而除了对于这些菌芝外形的记述外,还对菌芝的生活习性、生长环境有所记载:
曰木威喜芝,乃松脂沦地,千年化为茯苓,万岁其上生小木,状似莲花,夜视有光,持之甚滑,烧之不焦,带之辟兵,服之神仙。曰飞节芝,三千岁老松上,皮中有脂,状如龙形,服之长生。曰木渠芝,寄生大木上,状如莲花,九茎一丛,味甘而辛。曰黄柏芝,生于千岁黄柏根下,有细根如缕,服之地仙。曰建木芝……曰石脑芝、石中黄,皆石芝类也。千岁燕、千岁蝙蝠、千岁龟、万岁蟾蜍、山中见小人,皆肉芝类也。凡百二十种[6]。
而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时候,人们通常也将芝草这些菌类生物视作天降祥瑞。在浩瀚的中国古代史籍典册中,有关这类祥瑞现世的记载屡见不鲜,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另外,由于芝类的菌盖外形亦与古时候帝王使用的车盖与伞盖相似,因此亦有芝车、芝盖这些名称流传下来;而这种与帝王用器外形上的相似,又促使人们对于芝菌更加喜爱,视其为祥瑞之物。
3 预示不吉的凶物
但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亦有许多人将菌类生物的出现视作不吉之兆。之所以将菌类生物视作不吉之物,同样也与古时候人们对于菌类生物性状习性的认识有关。主要来看,一是困为某些菌类生物生命周期短暂,给人以负面的寓意;二是因为菌类生物乃是异养生物,其生存方式或为腐生或为寄生,而这在古人看来,乃是一种破败凋敝之象,而这也是古人视菌类为不祥的主要因素。
庄子在其名篇《逍遥游》中有“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一语,用来指代那些短暂的生命;而同是生活于战国时期的雍门周则有“夫以秦、楚之强而报弱薛,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一语[10],用来比喻那些弱小的事物。“朝菌”一词,后代学者存有争议,较为普遍的三种解释分别是以司马彪为代表的“大芝”说、以潘尼为代表的“木槿”说以及王引之等人的“蜉蝣”说;现代有学者以“‘大芝’并不以日之朝暮为生长周期,亦不以月之始终为生命极限”[4],来否定“大芝”一说,笔者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例如常见的食用菌竹荪,其原基形成菌蕾后,多在晴天的早晨开始生长菌盖、菌柄与菌裙,继而向下展开菌群,一般到下午时,菌盖上的担孢子成熟并开始自溶,滴向地面,同时整个子实体萎缩倒下。另外南华菇,鬼头伞等菌类生物亦为出菇之后一天内便逐渐凋落。
在科学尚不发达,对于菌类生物的了解还停留在外部形态观察层面的古代人看来,这样的情况无疑便是典型的“朝生暮死”。因此庄子“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一语中的“朝菌”指的是某种菌类生物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另外结合雍门周那句“磨萧斧而伐朝菌也”来看,先秦时期人们所说的朝菌,在“大芝”、“木槿”以及“蜉蝣”似乎也更应该是“大芝”这样的菌类生物。首先,斧子多是用来砍伐植物的,去砍伐蜉蝣明显太过牵强,虽然菌类生物在现代生物学分类体系中属于微生物,但在古代,人们是将其视作植物的;而木槿,虽然并不是特别高大的植物,但作为一种能长到二到四米高的落叶灌木,砍伐时使用斧子,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夸张的事情;而使用斧子砍伐柔弱的菌类“植物”当是对于“磨萧斧而伐朝菌也”的合理解释。
另外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无论《逍遥游》中的“朝菌”究竟实指为何,并不妨碍在中国古代,许多人将“朝菌”理解成某种菌类生物,并以菌类生物来喻指生命周期短暂且生命力脆弱的事物。
谢灵运在其绝命诗中感叹:“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9]”在诗里,他以脆弱易逝的菌类来喻指自己多舛而又短暂的一生。
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大臣崔光上表曰:
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极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按其形,即《庄子》所谓‘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终晦朔’,雍门周所称‘磨萧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气郁长,非有根种,柔脆之质,凋殒速易,不延旬月,无拟斧斤。又多生墟落秽湿之地,罕起殿堂高华之所。今极宇崇丽,墙筑工密,粪朽弗加,沾濡不及,而兹菌欻构,厥状扶疏,诚足异也。夫野木生朝,野鸟入庙,古人以为败亡之象。然惧灾修德者,咸致休庆。所谓家利而怪先,国兴而妖豫。是故桑谷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鸱鹊巢于庙殿,枭鹏鸣于宫寝,菌生宾阶轩坐之正,准诸往记,信可为诫。且南西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跨时,民劳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愿陛下追殷二宗感变之意,侧躬耸诚,惟新圣道。节夜饮之忻,强朝御之膳,养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则魏祚可以永隆,皇寿等于山岳[11]。
结合上下文,可知崔光表文内的“朝菌”明显是指菌类生物,因为“非有根种”一语,明确点明了他所指之物乃是通过孢子方式繁殖的菌类。他认为菌类生物“柔脆之质,凋殒速易,不延旬月,无拟斧斤”,而这些认识也都源自于古人对于菌类生物外在性状的了解;同时,崔光认为菌类“多生墟落秽湿之地”,而在“墙筑工密,粪朽弗加,沾濡不及”的宫殿之内出现“兹菌欻构,厥状扶疏”的景象,无疑是上天预示国家将要面临破败境况的凶兆,值得北魏统治者注意,进而改善朝政,避免朝廷沦亡。古人“菌生宾阶轩坐之正”乃是凶兆的这一看法,与菌类生物的生活习性亦紧密相连。作为异养生物的菌类,只能通过寄生或是腐生等方式生长,因此其生长之地多为“墟落秽湿之地”,宫殿住宅内出现菌类生物,无疑会让人联想到此处将会沦为废墟,故而将之视为不吉之兆。
中晚唐时期的名臣郑注在与宦官的斗争中失败,家破人亡,而据《新唐书·郑注传》记载,“注败前,菌生所服带上,褚中药化为蝇数万飞去。[7]”同时,这一情况还被收录到该书的《五行志》中,在志中,史家们郑重记下“大和九年冬,郑注之金带有菌生”一事[7]。可见,在许多人眼中,生命周期短暂,且多生长于墟落秽湿之地的菌类生物若无故出现于人的周围,可不都是什么吉兆,相反却有可能是凶兆。同样生活于晚唐时代的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中便一反之前秦汉魏晋时期众多士人追捧芝草的态度,认为“屋柱无故生芝者,白主丧,赤主血,黑主贼,黄主喜;形如人面者亡财,如牛马者远役,如龟蛇者蚕耗”,而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对此亦颇为赞同,认为段成式的看法乃是“先得我所欲言,其揆一也。[6]”另外作为一名医学家,李时珍虽然对于菌芝类生物的药用价值进行了肯定,但对于方士们将其吹捧为仙草的做法却并不赞同,相比于段成式,李时珍对于菌芝类生物的分析更为理性,结合菌类生物的生长环境,他认为“芝乃腐朽余气所生,正如人生瘤赘,而古今皆以为瑞草,又云服食可仙,诚为迂谬”,至于方士们所言的五色芝,他分析其成因乃是“方士以木积湿处,用药敷之,即生五色芝。[6]”
李时珍之所以将视菌芝为仙草这一观点批评为迂谬之说,亦与明代的社会现实环境相关。在《本草纲目·菜部》中,李时珍专门提到嘉靖年间曾有方士王金向明世宗献五色芝草,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他对这一社会风气并不赞同,故专门在书中予以解释与驳斥。
4 结论
纵观中国古代对于菌类生物的看法,可以发现,人们因为思考角度的不同,在基于对菌类生物性状特征以及生活习性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其中一方认为菌类生物能存活于其它生物难以生长之地,乃是上天对于统治者德被苍生的感应;同时限于古代生物知识的缺乏,通过孢子繁殖没有根须的菌芝,其突然出现又被解释成乃是精气所化,于是一方将其视为仙草,认为服食可得神效,因此将菌芝类生物视为祥瑞之兆。而另一方则认为菌类生物生命短暂,且多生于墟落秽湿之地,本身乃腐朽余气所生,人生活的周围若出现菌类生物,乃是将要破败的凶兆。
而这种对于菌类认识存在分歧的现象本身亦是一种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菌类生物的特征与习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会因观察者不同而产生变化。但是由于诸多观察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环境以及职业身份的不同,对于相同的客观事实做出了不相同的主观解释,并藉此赋予菌类生物以不同的意义,进而使得菌类生物在中国古代同时拥有了吉兆与凶征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寓意。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邱尚仁,蒋骥骋.“朝菌”训诂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9(1):50.
[5]陈士瑜.中国食用菌栽培历史初探[J].微生物学通报,1983,10(5):224.
[6]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7]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Ancient China Mushroom Culture
WANG Qiang,LIU Sheng-rong
(1.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Ningde Normal University,Ningde 352100,China;2.Department of Biology,Ningde Normal University,Ningde 352100,China)
The Chinese ancients know the fungi have edible and medicinal value in the early age.The ancients build special cultural concept of fungi.On the one hand,a lot of people consider the fungus are the symbol of auspicious,becaus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fungus.But also many people consider the fungus are the forebode of disaster,also for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fungus.From this phenomenon,we can learn that,different observers will give different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s to the same objective thing,and give it different meanings.
cultural concept of fungi;the symbol of auspicious;the forebode of disaster;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s
S646.9
A
1003-8310(2015)03-0088-05
10.13629/j.cnki.53-1054.2015.03.024
王强(1984-),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传统学术与史学。E-mail:wangqiang2822@126.com
2015-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