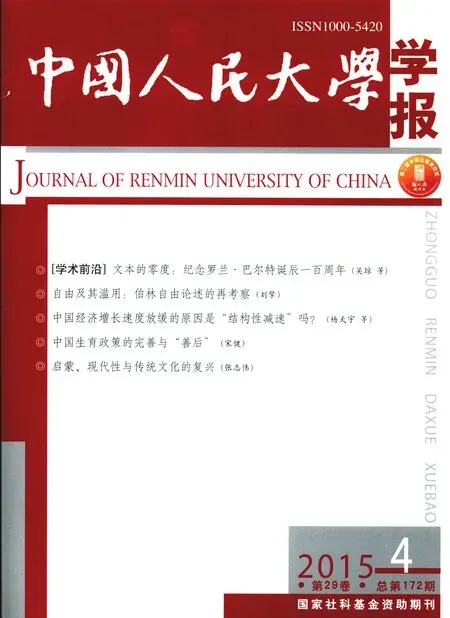编年体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创拓之作
——评袁济喜教授新著《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
杨青芝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编年体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创拓之作
——评袁济喜教授新著《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
杨青芝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尽管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年史,但是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年史编修,依然是一个较难涉足的领域。因为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相比,批评史的著论很少,因此,要在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提炼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年系列,确实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与大胆的探索。袁济喜教授的《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是迄今第一部编年体文学批评史著作。此书将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有机融为一体。该书较之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以及民国学者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可谓是汉末三国两晋方面文学批评范围的专论。该书昭示了“中国文学批评编年”这一宏伟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为之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对于其他各朝文学批评编年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在文学理论批评史及文艺学史编撰成果丰硕的今天,学术编年是否还有必要呢?
作者认为,采用学术编年体例,还原汉晋文学批评的历史情境,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文学批评的生成路径,以及与社会现实、士人活动、学术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天然血脉关系,看到生生不息的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的走向与生命力来源。同时,也可以为长期以来争论不息的“魏晋文学自觉论起于何时?”等问题找到答案。这个答案是:文学自觉是一个过程,汉晋之间只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直到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在清末民初与西方文学观念接轨,才形成今天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概念和现代文学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认为,既要吸收西方文学批评学科的思想,更要顾及中国文学批评的既有范畴与特色,二者不可偏废。应当按照汉晋文学批评的固有面貌来进行编年,这一看法颇具识见。纵览民国以来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一直注重“提纯”,即按照狭义文学概念来甄选历代诗文评及经、史、子、集中的一切论文之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史,既要调和前三十年狭隘、武断的政治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将文学审美性转化为贯穿批评史的文学自觉主线,又要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历代诗文评和论文之说进行现代阐释,因此,论的成分往往大于史的成分,不大注重历史脉络的清晰,尤其在前后朝代之间存在大幅度跳跃。采取学术编年体例,不仅呈现了汉晋学术的清晰脉络,也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过度阐释。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编年是一个不容掺杂水分的实打实的工程,不可能如有些史著那样材料不够就大量展开论述。作者编修此书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无疑是文献甄选。他在导论中指出,如果以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概念去衡量,这一时期严格符合标准的著述并不多,要从事编年工作自然是无从着手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一直包含在先秦诸子以来的各种文化典籍中,通过政治批评、思想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等形式得以展现,这种种著作,如王符的《潜夫论》、徐干的《中论》、应劭的《风俗通义》等,都包含了文学批评内容。曹丕的《典论·论文》在今天被公认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宣言,实则是从属于整个社会时政批评风潮中的产物,《典论》本非一本文学批评专书,而是一部子书。当代学人没必要作茧自缚,以现代文学概念划界,将那些深具人文价值、将文学问题与文化研究关联起来的文献排除在外。即便是民国以来一直被视为文学理论的《文心雕龙》,也是一个大文学理论的体系,与现代所言之“文学批评”并非一致。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诗文评”,不能看做是西方文学观念体系中文学批评的代名词。蒋寅认为《文心雕龙》是包含传统文学理论于其中的文章学理论体系,以此类推,一切包含了文学批评的政治批评、思想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类著述,都可以、也应该纳入文学批评编年的文献范围。
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是以日本学者铃木虎雄1920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为标志开始建构的,这说明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批评有赖于西方现代学术文化的整合,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建构是中西文化综合的产物。不过,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西方文艺学所说的狭义的文学批评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范畴,更能体现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化特征,更能彰显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过文学评论来阐释原理的特点,是中国文学批评既具形上人文关怀也具有形下现实关怀品格的生动体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内涵,远非以文学自觉、彰显文学之艺术属性和审美特性为基点的现代文学观念所能包容。因此,该书不局限于今人所云之“文学批评”范畴,而是从更广泛的视野去收集与评论。
确立文献甄选原则是文学批评编年如何进行的根本,具体的研究方法也很重要,作者在这方面体现出了自己的用心和学术智慧。
首先,该书以三国两晋取代更为常见魏晋之称,并纳入汉末桓、灵二朝,是摆脱官方正史魏晋相继的观念,也摆脱学术自成因果和文学观念自行演进的认识,指出桓帝与灵帝时期以来的士人问题与魏晋文学自觉有着密切联系,魏晋文学与文论的精神蕴涵,是汉末乱世士人阶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产物。同时指出,三国时代不唯魏国文学事业兴盛,吴国与蜀国也涌现了一些相关的文学理论批评人物与著论,两晋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人物如陆机,其活动也与吴国相关,《文赋》很可能是在吴地撰写,陆机入洛后,思想文化还保留着鲜明的吴国贵族特征。于魏晋合称中突出三国的区分,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西晋与东晋文学批评的不同,前者承袭北方文化因素,而后者多受江南文化影响。该书对吴国、蜀国文学理论资源的开掘与考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其次,该书将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和现代的学术方法融合起来,先借助前人研究,从原始资料做起,以年代为经,以人物、事件、著论、学说为纬,将二者之间互相印证,融会贯通。对于胶着一体的文学批评与哲学思想、文学创作,努力理清人物、事件、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三,该书除了和其他文学编年、学术编年一样完成了这一时期重大文学人物、事件、观点的系年,具有索引功能,还增加了资料长编的内容,并将史料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连接起来,说明了每一时期文论思想、批评观念与政治、学风的关系,也纵向说明了不同时期各种思想的关系,时有作者的精到评论。
当然,此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虽然汉末三国两晋乃至南朝的文学批评与当时的文化思潮、哲学观念有着密切关联,但是毕竟当时已经有了文学观念的自觉与独立表达方式,因此,应当注重彼此之间的分野,即使是夹杂在哲学与史学等领域中的文学观念、范畴,也要加以区分与提炼。但是本书在有些界定上较为模糊,例如对于汉末与东晋某些时期的文学与哲学、宗教之间的关系界定,就分析得不是很清晰,这或许是需要加以指出的。
(责任编辑 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