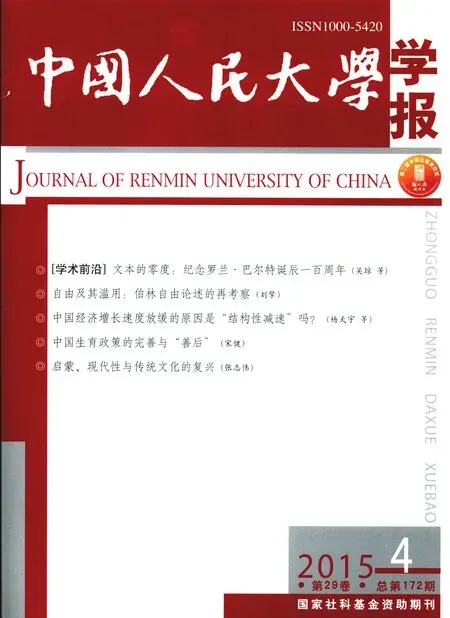整合式还是多元化?
——劳动关系研究范式的争辩与研究发展趋向
吴清军
整合式还是多元化?
——劳动关系研究范式的争辩与研究发展趋向
吴清军
劳动关系学科是多学科交融的产物。在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各学科关于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分析框架,因此,对于劳动关系的学科基础、研究对象、核心主题、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等与研究范式有关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辩。对西方劳动关系学界的有关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后可以做出如下预判:劳动关系学科未来仍将沿着多学科的方向发展,并不需要单一整合式的研究范式,但作为学科的统一标识,学术界应在核心研究主题上取得一定共识。
劳动关系;研究范式;制度研究;系统论;多元主义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劳动关系作为一门社会公认的独立科目,就已经出现在美国教育体系当中。[1]但该学科自建立之初,就是多学科交融的产物,其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政府—工团主义、德国历史—社会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甚至基督教的教义。[2]劳动关系学科思想来源多元化的结果是,一方面可以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视角以及理论资源,也使得劳动关系在研究与教学上很难成为一门大家所共同认可的独立学科。尽管劳动关系学科自建立之初就一直努力打造成一门跨越多个学科的独立学科,但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劳动关系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学科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核心主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视角等基本研究范式问题,一直都存在着分歧和争辩。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劳动关系研究在欧美国家整体衰落,虽然劳动关系学者更加注重对学科基本范式和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的探讨和研究,但其结果却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与争辩更加激烈。
中国的劳动关系研究和学科建设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真正出现。当西方劳动关系研究经历了起源、发展、兴盛以及衰落整个过程时,中国劳动关系研究则刚开始兴起。因此,厘清西方劳动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经验教训,对推动中国劳动关系研究和学科发展非常重要。本文将立足于中国劳动关系研究的现状,对西方劳动关系学界有关研究范式的争辩与研究发展趋向进行梳理。在对文献的梳理过程中,本文将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学界在争论哪些劳动关系研究范式问题?第二,劳动关系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在哪里?
一、劳动关系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根据已有文献梳理,我们把劳动关系学科争辩的主要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劳动关系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二,劳动关系的研究对象如何界定?其三,劳动关系研究的视角是什么?其四,劳动关系研究的核心主题是什么?我们将依次探讨这四个争辩的议题。
在19世纪的欧美国家,社会越来越关注工人的工资过低、工作条件恶劣以及工作时间过长等“劳工问题”。到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劳工和资本之间阶级对立加剧、工会运动高涨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蔓延,英国、美国及日本等国家都意识到,劳工问题不仅是劳动领域的问题,而且是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存亡的“社会问题”。[3]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首先在美国,国家公共政策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以“资本—劳工”关系为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经验研究。1920年,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教授约翰·康芒斯开设了一门劳动关系学课程。课程包含四方面内容:劳工立法、劳工史与产业政治学、劳动管理、失业原因与救助。这门课程的开设,标志着劳动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教育体系中诞生了。从康芒斯开设的课程内容来看,劳动关系的研究既包含制度经济学、劳动法学的内容,同时也包含劳工史、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的知识,所以从一开始,劳动关系就是一门多学科交融的产物。那么,劳动关系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呢?这一问题直至今天仍然是劳动关系领域中争辩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学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劳动关系并非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劳动关系是一门有着自己独特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独立学科。
持“研究领域说”的观点认为:研究者以劳动关系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可以使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这个领域中并没有一种综合性的劳动关系研究范式。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认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可以使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没有必要发展出一种超越单一学科的综合性分析方法。劳动关系的优势也就在于它是一个研究领域,可以吸纳多种不同的学科共同进行研究。[4]“研究领域说”的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学者们认为,劳动关系从建立之初就是个交叉学科,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当时公共政策和一批多个学科的学者为解决作为社会问题的劳工问题,开始共同研究劳动关系问题。他们研究劳动关系,选择了一条既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同时又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中间道路。在学术研究上,无论是制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还是管理学等学科,都反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把劳动力界定为自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的学术规范。他们并不认为劳动力仅仅是生产要素,反对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自由”和“契约精神”的学术假定。[5]
学者们认为,尽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劳动关系研究未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但学科之间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资源上互相借鉴,形成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领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劳动关系作为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及管理学的学者都开始回归到自己的本学科,仅从单一的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出发进行研究。劳动关系学科不仅无法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甚至连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向也受到了巨大影响。[6]
与“研究领域说”的观点相反,还有一批劳动关系学者坚持认为劳动关系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认为,如果以是否拥有统一的、独特的方法论作为评判一个学科是否成立的标准的话,那么,大家都公认的经济学的统一的、独特的方法论又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只知道经济学有逻辑的、数理的或是统计的方法论,并没有听说过经济学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方法论。既然可以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为什么不能认为劳动关系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呢?[7]所以,这些学者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包含三方面要素:第一,有明确的或可观察的研究客体,并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研究;第二,有由客体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现象,且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第三,有能够解释现象或预测现象发展的规则。如果以这三个标准进行判断,劳动关系既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又有相应的学术规则,劳动关系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认为,劳动关系的学科特性之所以不被认为是一门独立学科,是因为劳动关系并非像经济学那样是一门单一的学科,而是交叉学科。所以我们需要区别交叉学科与综合学科、多元化学科、跨学科与超学科之间的差异。劳动关系的学科特性之所以被人误解,核心原因在于:劳动关系在大学课程中,绝大部分都是多元化的教学与研究,包含了劳动经济学、工会运动史、劳工社会学、产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课程,很少有人致力于发展作为交叉学科特有的方法和课程体系。劳动关系作为交叉学科,要求研究者成为劳动关系的“专家”,他们需要懂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其他学科与劳动关系相关的知识,但无需像经济学家那样,对货币理论、金融模型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得那么深入。[8]
上述两种观点一直未达成共识。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欧美一些大学是按照劳动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来设立学院、系或研究中心的,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大学纷纷撤销劳动关系院系,把劳动关系的教学与研究融入了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劳动关系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越来越多,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特征也愈发明显。
二、劳动关系的研究对象如何界定?
毋庸置疑,劳动关系研究的对象是劳动关系,那么,劳动关系到底又是什么?劳动关系学科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按照学科的一般发展规律,这一涉及学科立足的根本性问题早就应该得到解决,但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模糊不清,那么它的研究边界也就无法确定。如果什么都可以研究,那么学科的特性又如何体现出来?研究对象界定不清晰,一直影响着劳动关系的学科发展。劳动关系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学者们意见纷呈,给出了不同的界定。[9]根据已有的文献,可以把不同的界定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最宽泛的界定,认为劳动关系包含所有与劳动和生产相关的现象。尼尔·张伯伦(Neil Chamberlain)就把劳动关系等同于与劳动相关的所有方面[10],认为凡是与劳动相关的现象都是劳动关系的研究对象。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同样也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界定劳动关系的,认为劳动关系是与生产相关的社会关系。[11]赫伯特·赫尼曼(Herbert Jr.Heneman)做出了更为宽泛的界定,他认为劳动关系就是产业经济中所有与雇佣相关的关系。[12]从宽泛的角度界定劳动关系,自然可以把许多与劳动或生产相关的研究领域都包含进来,扩充劳动关系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的知识体系,但与此同时,也使得劳动关系的研究边界和研究主题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很难把劳动关系研究与经济学或社会学对工作和劳动的研究区分开来。[13]所以,劳动关系的广义界定在学界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只有部分学者在特定的背景下使用这种界定。
第二类是最狭义的界定。这种界定以劳动关系研究的某些主题作为边界来定义劳动关系。金斯利·拉弗(Kingsley Laffer)就以劳动关系的核心主题来界定劳动关系,认为劳动关系研究的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谈判关系。[14]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流行同时也是最狭义的界定是把劳动关系研究局限于工会和集体谈判,把劳动关系研究等同于工会—管理雇佣关系的研究。理查德·马斯登(Richard Marsden)认为:“劳动关系就是关于工会、管理方和集体谈判的研究”。[15]这种界定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并成为当时经验研究的主流。关于工会和集体谈判的研究,也成为划定劳动关系研究边界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集体谈判制度衰落以及工会入会率急剧下降,劳动关系学者开始寻求新的突破,不仅在研究主题上发生变化,而且关于劳动关系的定义也开始有所改变。[16][17]
第三类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中间层面进行界定。中间层面的界定也是按照劳动关系的研究主题来定义的,与狭义的界定不同的是,他们设定的都是一些抽象层次较高的主题。杰克·巴巴什(Jack Barbash)认为,劳动关系是解决雇佣关系中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研究。[18]而理查德·海曼(Richard Hyman)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进行定义,认为劳动关系就是对市场力量进行社会规范的研究。[19]休·克雷格(Hugh Clegg)认为,劳动关系可以简化成对工作规范(job-regulation)的研究。[20]斯蒂芬·希尔斯(Stephen Hills)做出了类似的界定,认为劳动关系是对企业和工人组织之间关于控制雇佣关系的谈判研究。[21]中间层面的界定以研究的抽象主题来定义劳动关系,实际上在定义的同时,也是对劳动关系研究进行抽象的理论概括。
劳动关系到底是什么?如何界定劳动关系?如何确定劳动关系的研究范围?上述三个层面的界定自始至终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布鲁斯·考夫曼(Bruce E.Kaufman)给出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认为既然我们今天无法在劳动关系定义和研究范围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还不如回顾一下历史,去看看最早提出劳动关系研究的学者们是如何界定的。[22]他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认为最早提出劳动关系研究的文献有四个:第一,1919年由罗素·赛奇图书出版社(Russell Sage Library)出版的《劳动关系:选编目录》(IndustrialRelations:ASelectedBibliography)。这本小册子把已有的目录分成了两部分:雇佣管理和管理参与。雇佣管理部分包含所有涉及劳动和人事管理主题的内容,同时还包含工厂治理方法的内容;管理参与部分包含工会、工厂委员会、战时联合劳动管理委员会等相关内容。第二,赫曼·费尔德曼(Herman Feldman)在1928年为社会科学研究委员撰写的劳动关系领域的调查报告。他认为,就雇主—雇员关系而言,劳动关系要研究五个基本主题:工厂(从人类行为的角度进行研究)、工人与工作的关系、工人与同事的关系、工人与雇主的关系以及工人与社会公众的关系。第三,威斯康星大学1920年最早建立劳动关系教学科目,包括劳动立法、劳动管理(人事管理)、劳工史与产业政治学以及失业原因与救助四门课程。这个课程模式后来被其他大学所模仿并不断改变,1930年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课程改为包括劳动法、劳动管理、劳动争议处理及人事管理四门课程。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一半课程是关于雇主的劳动管理政策(包括人事管理、员工参与、薪酬福利等),另一半是关于工会主义和劳工政策的课程。第四,美国国家产业协商委员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1931年提交的《劳动关系:政策和规划管理报告》。该报告提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劳动关系包含了所有从雇佣中产生的事件与现象”。
从考夫曼总结的劳动关系研究内容四种来源来看,20世纪20年代,劳动关系包含有关工作、劳动、雇佣关系的所有主题。它所强调的是工作世界的所有关系,既从雇主的角度去研究工作组织、人事管理以及雇员对雇主的反应等主题,同时也从雇员和工会的角度去研究罢工、集体谈判、工会主义等主题。这时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综合学科的研究,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管理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那么什么是劳动关系呢?近些年大家比较认同的是保罗·爱德华兹给出的界定。他认为,原来我们一直用“industrial relations”这个概念,但是“industry”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制造业(manufacturing),虽然我们在使用产业关系时,也包含了公共部门的劳动关系,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业关系的含义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最突出的变化表现为服务行业在欧美国家已成为主导产业,所以服务行业私营部门的劳动关系就不能再用“industrial relations”来表述,使用雇佣关系“employment relations”来表述更为确切。[23]那么如何界定雇佣关系呢?他认为界定这个概念,关键是要对雇佣的概念做出定义。他认为:“雇佣是指雇员在雇主权威管理下进行工作,并作为劳动的回报获得劳动报酬的所有经济行为”。[24]这个定义把雇佣与家务劳动、自我雇佣(self-employed)等劳动形式进行了区分。所以,他把雇佣关系界定为:有偿雇佣下雇主和雇员形成的关系。[25]考夫曼在2004年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应该用雇佣关系来替代产业关系的概念,因此,劳动关系是一个研究雇佣关系以及与雇佣关系相关联的行为、结果、实践和制度的研究领域。[26]
三、劳动关系的研究视角是什么?
劳动关系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呢?近百年的发展历史证明,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劳动关系都没有形成大家所公认的独一研究视角。那么,劳动关系的研究视角到底有哪些?也就是说,不同学科是如何来看待劳方—资方所形成的雇佣关系的本质的?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假设、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存在很大的差异,当把研究对象集中到劳动关系上时,他们看待雇佣关系的本质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学者们对目前劳动关系研究视角的概括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瓦尔特·穆勒耶恩奇(Walther Muller-Jentsch)把其概括为五大类,即系统论、马克思主义方法、制度主义、行动理论、经济学方法。[27]布莱汉姆·达巴斯查克(Braham Dabscheck)也把劳动关系研究的视角概括为五类:系统论、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合作主义和规范理论。[28]考夫曼从劳动关系研究核心主题的角度把劳动关系研究视角区别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研究雇佣关系为中心的、传统的较为宽泛的研究视角,另一类是现代集中于工会、劳工管理关系的较为狭窄的研究视角。[29]
在学术界,大家比较认同迈克尔·撒拉芒(Michael Salamon)的总结。他认为,劳动关系的三种研究视角源于不同学科对雇佣组织本质的三种不同认识,即一元主义、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一元主义假设雇佣组织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管理者和雇员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利益和目标;组织内部是和谐一致的,没有必要制造矛盾。从一元主义视角出发,形成对雇佣关系本质的四点基本假设:第一,劳资双方组成的是一个工作团队,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团队中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第二,劳资双方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组织内部的矛盾只是工作过程中因个人性格不同、决策计划和信息传递不通畅、部分雇员对管理者的决策和行为不理解等造成的,并非是实质性的利益冲突;第三,管理和被管理是因工作分工需要而形成的,管理者拥有绝对的权威,管理者的决策和管理是合法的、合理的,被管理者必须接受,并保持对管理者的忠诚与服从;第四,工会是来自雇佣组织外部的势力,工会的实质是与管理方争夺管理权,工会进入雇佣组织,将会在组织内部制造矛盾。[30]
多元主义视角则将雇佣组织中的资本所有者、管理者和雇员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认为集团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利益矛盾是天然存在的,但是可以通过制度和程序来解决和调整矛盾。从多元主义视角出发,他们对劳资关系的实质形成了几点基本的判断:第一,雇佣双方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第二,雇佣双方的矛盾是可以通过一套包括集体谈判、调解和仲裁以及民主参与等制度予以限制和解决的;第三,多元主义接受工会在一个雇佣组织中存在的事实,承认工会的正面作用。[31]
马克思主义视角与前面两种不同,认为雇佣组织内的雇佣关系就是阶级关系,是一种资本与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劳资双方对立和对抗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劳资关系的本质有着几点基本假设:第一,劳资关系是阶级关系;第二,劳资关系是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三,劳资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可以解决;第四,工会是工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的必然反应,但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需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解决。[32]
在许多学者看来,一元主义代表了管理学研究劳动关系的基本视角,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评主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只有多元主义才是劳动关系学科应有的研究视角。亨利·卡茨(Herry Katz)和托马斯·寇肯(Thomas Kochan)等人对此进行了较好的概括。他们认为,劳动关系研究有五个基本假设:第一,劳动力不是商品;第二,劳资双方利益多元化;第三,冲突和利益分歧是劳动关系本质特征;第四,劳资双方存在着共同利益;第五,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制度和程序进行调和。[33]
四、劳动关系研究的核心主题是什么?
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社会学家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以及德国历史—社会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被认为是现代劳动关系研究的三大奠基人。[34]德国历史—社会经济学思想被制度经济学吸纳之后,在劳动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中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在美国以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关系研究;二是在英国以社会学、史学为代表的劳动关系研究。但不管是康芒斯还是韦伯夫妇,他们对劳动关系的研究都比较宽泛,他们研究劳动力市场、工会主义、劳工组织谈判、劳工政策以及产业民主等,并没有确定单一的劳动关系核心主题。
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才得以改变,新一代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在美国,以艾伦·弗兰德斯(Allan Flanders)、休·克莱格(Hugh Clegg)和阿兰·福克斯(Alan Fox)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在英国,确定了劳动关系的研究核心主题,即劳动关系制度与规范。
1958年,邓洛普在《劳动关系系统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系统论”的观点。邓洛普认为,劳动关系理论的核心任务是要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劳动关系系统中会产生出特定的规则,并且,劳动关系系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对这些规则产生影响的。[35]根据这一核心问题,他建构了一个劳动关系的框架图谱,认为某一特定时期的劳动关系系统包含了特定的主体、特定的背景、维系系统的共同意识形态以及规范行动者在工作场所与工作社区的规则。[36]具体来说,在劳动关系系统中有三个主体,即政府、雇员与雇员组织、雇主与雇主组织;这三个主体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共同的信念;这些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以及信念维系着整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运转。三个主体在技术、市场以及权力三个主要的外部环境下互动,从而形成劳动关系系统中工作场所和工作社区的“规则网络”。[37]如果按照一个模型来理解的话,在劳动关系系统中,规则是因变量,而主体、外部背景和意识形态则是因变量,系统论可以用以下公式进行表述:
R=f(A,T,M,P,I)*引自Blain,A.N.J.,and John Gennard.“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A Critial Review”.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1970,8(3):394.其中,R为规则(Rules),A为行动者(Actors),T为技术(Technology),M为市场(Market),P为权力(Power),I为意识形态(Ideology)。
在邓洛普的系统论模型中,他把劳动关系的规则和规范置于整个分析框架的中心,这不同于以往把产业冲突或集体谈判等作为劳动关系研究的核心。[38]
虽然牛津学派没有提出统一的理论,也没有统一的分析框架,但是他们把研究的核心都界定为“工作规范”,并采用了共同的“多元主义”研究范式。在具体研究中,他们借鉴了邓洛普的观点,认为劳动关系的核心议题是研究工作规范。与邓洛普不同的是,他们区分了内部工作规范和外部工作规范,并且认为工作场所的内部工作规范可以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而由内部的雇主与雇员自主确定,并可以不断进行调整。牛津学派强调规范制定的过程,其核心过程就是集体谈判;同时他们承认工会的价值,反对政府和法律过多地介入劳动关系的改革,认为集体谈判才是规范劳动关系最好的方法和手段。劳动关系系统规范是由集体谈判的规则制定过程所决定的,在集体谈判过程中,劳资双方显示了彼此力量的对比与博弈。牛津学派的观点可以简单地用公式进行概括,即
r=f(b)或r=f(c)*其中,r(rules)是指劳动关系的一系列规则,b(collective bargaining)是指集体谈判,c(conflict resolved through collective bargaining)是指通过集体谈判的冲突解决。
与邓洛普的系统论模型相比,牛津学派和系统论有着共同的产出,即规则,但是他们的投入不同。系统论强调决定规则的有多种因素,而牛津学派只强调通过集体谈判的规则制定。尽管与邓洛普的系统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牛津学派研究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工会、集体谈判和与之相关的劳动关系制度。[39]
系统论和牛津学派把研究核心主题确定为对规则、规范的研究,这已成为劳动关系研究的传统。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成为整个劳动关系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有些学者甚至将劳动关系研究等同于对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的研究。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反思这一研究传统,其中强调研究劳资力量对比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强调主体行动的“策略选择模型”以及强调研究劳动关系社会目标的“劳动关系平衡理论”较为突出。
海曼在《劳动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关系做出重新的界定,他认为“劳动关系是对工作关系控制过程的研究”。[40]系统论和牛津学派对规则和规范的研究,往往会陷入非人格化、结构化的社会秩序的解释中。邓洛普和弗兰德斯看到的是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正式的制度和有序的社会规范,但是劳动剥削、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社会贫困、阶级冲突与矛盾、社会动乱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讨论的阶级划分现象仍然存在。在此,海曼并未直接借用马克思的剥削、阶级斗争等核心概念,而是把这些不平等和冲突矛盾现象概括为另外一个概念:权力斗争。海曼认为,永不停止的权力斗争是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所以,海曼认为劳动关系研究的核心主题应该是劳动关系中的权力较量。
托马斯·寇肯、哈瑞·卡兹(Harry C.Katz)和罗伯特·麦克西(Robert B.McKersie)1986年在《美国产业关系的转型》(TheTransforma ̄tionofAmericanIndustrialRelations)一书中提出了“策略选择模型”。他们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关系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正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劳工政策和二战后集体谈判制度规范的劳动关系转向劳动关系模式多元化、无工会企业越来越多的“新产业关系”。面对美国劳动关系的转型,邓洛普的系统理论难以给出满意的解释。他们在批评邓洛普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策略选择模型理论,将管理者的战略与价值理念引入劳动关系系统当中,并把它放在理论分析框架的核心地位,而并非是劳动关系的制度和规则。他们强调了劳动关系主体中雇主的行动与策略,否定了结构化的角色和行动。[41]
巴德在2004年的《人性化的雇佣关系》(Employment with a Human Face)和2005年的《劳动关系:寻求平衡》(Labor Relations:Stri ̄king a Balance)中提出了“劳动关系平衡理论”,这是近20多年来在劳动关系理论构建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理论分析框架。[42]巴德认为,美国传统劳动关系研究专注于劳动关系过程的研究,包括如何组建工会、如何进行合同谈判、如何解决争议和申诉等;并且,美国工会一直习惯于将这些劳动关系过程细化为工作规制,因而学界形成将劳动关系研究等同于工作规则研究的传统。[43]但是,劳动关系研究并不是工作规则的研究,工作规则只是为了达到更重要的目标的一种手段。劳动关系研究需要一种根植于雇佣关系目标的理论分析框架。[44]巴德的研究从雇佣关系目标入手,雇佣关系的社会目标是:效率、公平和发言权。[45]如果能够实现这三个雇佣关系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状态,那就是一种人性化的雇佣关系。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的衰落,学者们开始反思劳动关系研究局限于规则、规范等制度研究的传统。上面介绍的三种理论分析框架,就给劳动关系未来研究提供了选择。制度研究的传统被打破了,但劳动关系的核心议题到底是什么呢?直到今天,我们也未看到一个学界共同认可的答案,学者之间的分歧和争辩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未停止。
五、劳动关系研究发展趋向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劳动关系学科已发展了近百年,但劳动关系的一些核心问题仍然处在争辩之中。那么,劳动关系研究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另外,如果要发展劳动关系理论和研究,又如何去跨越目前劳动关系研究的多元主义、一元主义和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一种典型的做法是类似于考夫曼,他尝试去构建一个整合式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产生整合式的劳动关系研究范式和理论。[46]巴德并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构建一个宏大的、单一的、整合式理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劳动关系的研究内容界定清楚。他认为劳动关系既不需要宏大的、纯粹逻辑思辨的理论,也不能仅停留于经验研究,劳动关系学科应该发展“元研究范式”(meta-paradigm)。[4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劳动关系研究领域并不需要单一的、整合性的高度抽象理论,但需要对核心研究主题存在一定的共识,劳动关系也需要一个统一的标识[48],或者需要一个凝聚的核心。
劳动关系应该是多学科的研究,不排斥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观点,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和马克思主义批判研究都应该包括进来,并且还可以包含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社会科学的学科通常并不是以某一种单独的理论为特征的,事实上学科都是通过其内容与社会标准两个方面来定义的,核心和焦点在于学科研究的内容。并且,一个学科的内容并不要求避免与其他学科相重叠,也不排斥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49]所以,巴德把劳动关系学科要研究的内容概括为“人力资源—劳动关系”(HRIR),认为在人力资源—劳动关系研究领域中,可以把多元主义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批判性劳动关系研究三种研究范式都包含进来。虽然目前这三种研究范式互不相容,在一些基本假设和分析逻辑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在人力资源—劳动关系的研究领域中,并不需要一种研究范式,而是需要一种元范式,即一张定义一个研究领域的指标参数的组织结构图。[50]
不管是考夫曼的整合式理论分析框架,还是巴德的元研究范式,我们都可以看出,目前劳动关系学界特别重视对涉及影响劳动关系走向的核心问题的研究,不管未来发展方向如何,至少学界已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与努力。中国劳动关系学科建立时间较短,通过学习和借鉴欧美国家劳动关系发展的历史,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中国劳动关系的独特经验,提炼和抽象中国的经验研究,为劳动关系研究提供全新的知识来源。
[1][2][5] Kaufman,Bruce.TheGlobalEvolutionofIndustrialRelations:Events,IdeasandtheIIRA.Geneva: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04.
[3] Morrison,Charles.AnEssayontheRelationsbetweenLaborandCapital.New York:Aron Press,1972.
[4][13][23][24][25] Edwards,Paul.“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P.Edwards (ed.).IndustrialRelations,TheoryandPractice(2nd ed.).Oxford:Blackwell,2003.
[6] Strauss,George.“Comment on: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Industrial Relations”.IndustrialandLaborRelationsReview,1988,41(3):449-452.
[7][8][14] Laffer,Kingsley.“Is Industrial Relations an Academic Discipline?”.JournalofIndustrialRelations,1974,16(2).
[9]Strauss,George & Peter Feuille.“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A Critical Analysis”.IndustrialRelations, 1978,17(3):259-277.
[10] Chamberlain,Neil.“Issues for the Future”.InProceedingsoftheThirteenthAnnualMeeting.Madison,WI.: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1960.
[11] Cox,Robert.“Approach to the Futurology of Industri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LaborStudies,Bulletin,1971,8:139-164.
[12] Heneman,Herbert Jr.“Toward a General Conceptual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How do We Get There?”.In G.Somers(ed.).EssaysinIndustrialRelationsTheory.Ames:Iwo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9.
[15] Marsden,Richard.“Industrial Relations:A Critical of Empiricism”.Sociology, 1982,16(3):232-250.
[16] 托马斯·寇肯、哈瑞·卡兹、罗伯特·麦克西:《美国产业关系的转型》,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17][43][45][46][49][50] 约翰·巴德:《人性化的雇佣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8] Barbash,Jack.“The Founder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as a Field of Study”.In R.J.Adams & N.M.Meltz (eds.).IndustrialRelationsTheory:ItsScope,Nature,andPedagogy.Metuchen,NJ.:Scarecrow,1993.
[19][40] 理查德·海:《劳动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20] Clegg,Hugh.“Pluralism in Industrial Relations”.BritishJournalofIndustrialRelations,1975,13 (3):309-316.
[21] Hills,Stephen.“Integrating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Social Science”.In R.J.Adams & N.M.Meltz (eds.).IndustrialRelationsTheory:ItsScope,Nature,andPedagogy.Metuchen,NJ.:Scarecrow,1993.
[22][26] Kaufman,Bruce.“Employment Relations and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 System:A Guide to Theorizing”.In Bruce E.Kaufman(ed.).TheoreticalPerspectivesonWorkandtheEmploymentRelation ̄ship.Champaign,IL.: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2004.
[27][38] Muller-Jentsch,Walther.“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ndustrial Relations”.In Bruce E.Kaufman(ed.).TheoreticalPerspectivesonWorkandtheEmploymentRelationship.Champaign,IL.: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2004.
[28] Dabscheck,Braham.“Of Mountains and Routes Over Them:A Survey of Theorie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JournalofIndustrialRelations,1983,25(4):485-506.
[29] Kaufman,Bruce.“Paradigm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Original,Modern and VersionsIn-between”.BritishJournalofIndustrialRelations,2008,46 (2):314-339.
[30][31][32] Salamon,Michael.IndustrialRelations:TheoryandPractice.London:Prentice Hall,1998.
[33] Katz,Harry C.,Thomas A.Kochan,Alexander J.S.Colvin.AnIntroductiontoCollectiveBargaining&IndustrialRelations(4thed.).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8.
[34] 布鲁斯·考夫曼:《产业关系的理论基础及其对劳动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3(17)。
[35][36][37] Dunlop,John.IndustrialRelationsSystems(rev.ed.).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3/1958.
[39] Ackers,Peter & Adrian Wilkinson.“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Paradigm:A Critical Outline History and Prognosis”.JournalofIndustrialRelations,2005,47(4):443-456.
[41] Kochan,Thomas A.,Robert B.McKersie & Peter Cappelli.“Strategic Choice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IndustrialRelations,1984,23(1):16-39.
[42] Hunter,Laurie.“Book Review:Employment with Human Face:Balancing Efficiency,Equity,and Voice”.BritishJournalofIndustrialRelations,2005,43(2):321-344.
[44] 约翰·巴德:《劳动关系:寻求平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47] Budd,John.“A Meta-Paradigm for Revitalizing Industrial Relations”.In Charles J.Whalen (ed.).NewDirectionsintheStudyofWorkandEmployment:RevitalizingIndustrialRelationsasanAcademicEnterprise.Northampton,MA.: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8.
[48] Adams,Roy.“Theory Construction and a Checklist”.In R.J.Adams & Noch M.Meltz (eds.).Indu ̄strialRelationsTheory:ItsScope,Nature,andPedagogy.Metuchen,NJ.:IMLR Press,1993.
(责任编辑 武京闽)
Integration or Pluralism?——Debates on the Paradigm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WU Qing-jun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Industrial relations as an inter-discipline has been short of integrated paradigm and theory between disciplines over the nearly 100 years in its development course. There are four sorts of debates on paradigm. Firstly,is industrial relation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Secondly,what is industrial relations? Thirdly,what are the viewpoint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Fourthly,what is the key subjec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re has not been consensus on these debates among scholar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industrial relations should develop the meta-paradigm in the future. Industrial relations,as a research field,does not need an integrated paradigm,however,it needs a consensus on the key subject.
industrial relations;paradigm;institutional research;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pluralism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4XNJ012);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
吴清军: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