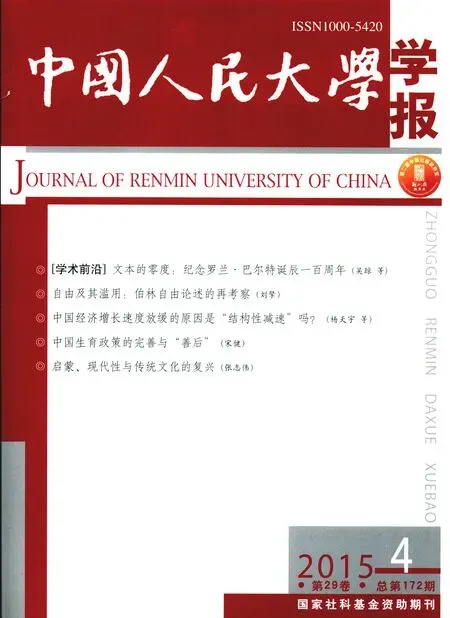晚期罗兰·巴尔特与怀疑论哲学
金松林
晚期罗兰·巴尔特与怀疑论哲学
金松林
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罗兰·巴尔特认为权力无处不在:它在这里被耗尽,在别的地方又会重新萌生。权力寄附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语言常见的表达形式:语言结构。为了瓦解隐藏在语言结构中的权力,他从特鲁别茨柯伊、叶姆斯列夫等人的音位学著作中挪用了“中性”概念,并且将它和怀疑论哲学结合起来。事实证明,这种错误的理论嫁接不但削弱了其思想解构的锋芒,而且使他逐渐蜕变为一个遭人厌弃的寂静主义者。巴尔特晚期的这一形象既动摇了我们的固有观念,也促使我们对他以及他的理论展开更加全面、有效的新评估。
罗兰·巴尔特;中性;怀疑论;权力
时至今日,罗兰·巴尔特研究已基本模式化了。人们总是习惯以《S/Z》为界,将巴尔特的理论生涯划分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个阶段。在一本小书的前言中,英国学者里克·李朗斯就将这一转变形象地表述为从“冷的巴尔特”转向“热的巴尔特”。[1](Pix)“冷”和“热”这两个形容词巧妙地传达出类似信息,即与前期相比,转向之后的巴尔特更富有魅力。因为在这一时期,巴尔特喊出了一系列口号:“作者死了”、“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文本的愉悦”,等等。通过这些,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富有挑战性、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形象。迄今为止,这一形象不仅影响到我们的阅读和阐释,而且僵化了我们的认知。
这就是最后的巴尔特吗?当我们翻开他在法兰西学院连续数年的讲稿(1977—1980年),就会发现那个富有挑战性、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不见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他者——一个丧失了行动意志、思想消极、缺乏创造力的学究式的人物。有人指责他说:“在借助于巧妙地混合南腔北调与无聊之谈来糊弄傻瓜的艺术中,大师级的人物无可争辩地就是罗兰·巴尔特。”[2](P123)拉道尔弗斯·梯尤文也公开批评巴尔特的讲座是“令人厌倦的乌托邦”[3](P2)。作为近友,安东尼·孔帕尼翁显然也不满意巴尔特的表现,说“他让前来听课的朋友们失望”[4](P25)。传记作家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更是斥责此时的巴尔特已经“活着进入了死亡”[5](P238)。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转变?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即归因于他母亲的去世①罗兰·巴尔特的母亲埃里昂特于1977年10月去世。,因为在《明室》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没有母亲,我可以活着(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失去母亲)。但是,接下来的生活将绝对是坏得无法形容的(毫无品质可言)”[6](P75)。
其实,这一看似合理的解释所遮蔽的恰好是巴尔特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进入法兰西学院以后,他主动将自己的解构主义与怀疑论哲学结合起来,这种错误的理论嫁接不但削弱了其思想解构的锋芒,更为严重的是,使他由一个知识界的理论先锋逐渐蜕变为一个主张“隐退”、“无为”的寂静主义者。他的学生埃里克·马尔蒂形容此时的巴尔特“就像一个蜗牛壳那样,他谨慎无比地蜷缩在这个壳里以逃避外部的世界”[7](P27)。
由此可见,我们对巴尔特的认知是存在问题的。其实,那个富有挑战性、思想激进的巴尔特在他进入法兰西学院不久就终结了。大约从1977年开始,他向我们呈现的就已经是另一副面孔。茨维坦·托多洛夫在一篇简短的文章中称这一时期的巴尔特为“晚期巴尔特”[8](P259)。接下来,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巴尔特晚期的转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他是怎样接纳了怀疑论哲学并且使自己在理论上逐步退却?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他1977年1月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说起。
一、语言结构与权力
对于巴尔特晚期思想的发展,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因为在这篇演讲中,巴尔特不仅提出了未来课程的设想,而且阐明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他说:“实际上,我们间接但持续关注的是权力。”[9](P459)过去,我们以为权力仅仅是一种政治现象,如今我们也相信权力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几乎无处不在。权力在这里被驱赶耗尽,在别的地方又会重新萌生。巴尔特认为:“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力所寄附的对象就是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语言必要的表达:语言结构……作为语言系统之表现的语言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完完全全是法西斯主义的。”[10](P460-461)
我们要知道,巴尔特说这番话的时候台下就座的有福柯、德勒兹、格雷马斯、索莱尔斯、埃德加·莫兰、罗伯-格里耶等法国知识界巨擘。一位在场者回忆:“此时福柯眼睛看着天。这意味着:罗兰最终没有达到高度。”[11](P15)路易-让·卡尔韦事后也评论说:“即使语言是法西斯主义的提法被人们记住了,这也许是作为笑料,也许是觉得可悲。一个如此聪明的人竟然说出这番毫无意义的话。”[12](P217)然而,巴尔特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中开始了他为期三年并因意外死亡而结束的讲座。
怎样瓦解语言结构中的权力?巴尔特想做的工作是釜底抽薪,他回到了索绪尔。在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在由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太凯尔阵营中,借助于索绪尔所提供的语言学工具,这基本是一种理论共识。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强调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使一个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一切,就构成该符号”[13](P168)。如英语中的bad和bed,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它们,两者都不拥有自身的含义。它们的意义就产生于音位(//和/e/)之间的对立。索绪尔将这种模式概括为a/b,即聚合关系,有时我们也称之为“二项对立”。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有聚合关系的地方,就有意义;凡是有意义的地方,就必然存在聚合关系。在这种意义生成的机制中,巴尔特意识到:“意义依靠冲突(选择其中一项而舍弃另一项),所有冲突都会产生意义:选择其中一项而拒绝另一项,总是意味着作出意义的牺牲”[14](P7)。他将这种意义生成的机制简单概括为“是/否(+/-)”,意思是:“一个词项的实现排除了其他词项同时出现的可能性”[15](P222)。由此表明,语言天生就是独断论的。
要想瓦解语言中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巴尔特认为必须破除聚合关系。从特鲁别茨柯伊、叶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的著作中,他找到了问题的破解之道——“中性”。在音位学研究的过程中,特鲁别茨柯伊发现在某些比较特殊的音位上语音之间的对立会消失,如英语摩擦音[s]后面的p和b,t和d,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语音中和”。随后,叶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在语言学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因此,他们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种新的概括:a/b/既非a也非b,但同时既是a也是b。在这个表达式中,a和b是存在对立关系的两项,“既是a也是b”是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的复杂操作或者说复杂项,而“既非a也非b”属于“零项”或“中性项”。巴尔特认为这个中性的项次不但能够破除聚合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免除意义。其实从《写作的零度》开始,巴尔特就一直梦想着一个免除意义的世界,这种观念一直延伸到后来他对音乐、绘画、摄影、法国新小说以及日本俳句的肯定。*在《符号帝国》和《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这两本书中,均有“免除意义”的条目。参见Roland Barthes.Empire of Signs.New York:Hill and Wang,1982:73-76;Roland Barthes.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Hampshier 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1977:87.
在符号学中,语言只是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理论模型。作为一个符号学家,巴尔特不可能局限于此,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种解构的策略拓展到更广的领域。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上,他强调:“思考中性,对于我来说,它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自由的方法——目的是要在时代的竞争中展现我自己的风格”[16](P8)。譬如,在话语领域,当我们采用中性的策略,就能够避开言语冲突,以免遭到攫取意志的胁迫。在生存领域,当我们采用中性的策略,就可以远离意识形态和权力,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实际上,我们真的能够如此吗?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它不过是巴尔特的一种设想,一项带有怀疑论色彩的“伦理学计划”[17](P11)。
二、中性与怀疑论
在功能上,中性是破除聚合关系之物。在语义层面,何谓中性(neuter)呢?根据哈杜默德·布斯曼《语言学词典》的解释,它是由拉丁词根ne(不)和uter(两者之一)组成,意为“不是两者之一”,“既非此,亦非彼”。[18](P361-362)如果联系到意义生成的机制“是/否(+/-)”,“既非此,亦非彼”也就意味着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必须悬置判断、不做取舍。否则,我们就会成为独断论者。巴尔特认为这种人总是通过自己的攫取意志滥施权力。
在《夏吕斯的话语》中,巴尔特举了《追忆似水年华》第三部“盖尔芒特家那边”里面的一个例子:叙述者在结束盖尔芒特夫人举办的家宴之后匆匆赶赴同德·夏吕斯男爵的约会,后者让他坐在路易十四式的椅子上,因为就近,他却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这一行为立即遭到德·夏吕斯男爵的嘲讽:“哼!这叫路易十四式椅子啊!亏您还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19](P536)为了分析该场景,巴尔特将独断论的语言模式拓展到了符号领域:路易十四式椅子(是)/扶手椅(否)。表面上,这是一种文化编码(座椅的形式风格),实际上,它是企图通过话语来实现个体支配的欲望。因此,巴尔特说:“德·夏吕斯所操持的是警察的语言”[20](P165)。然而,类似场景和判断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们就生活在一个断言的世界里。
巴尔特伦理学计划的核心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循着自己的细微差异去生活。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求我们在各种是与非之间悬置判断。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拒绝同一,在面对独断论时小心地逃避,巴尔特认为这种温和的态度最接近于古代怀疑论哲学。皮埃尔·奥邦格说:“在古代,怀疑论者,或者不如说后来被称为怀疑论者的人们,都自称是‘艾菲克蒂柯伊’(Ephektikoi),这个名称是指让判断暂且悬而不决,而使用独特思考方式的一类人。”[21](P20)让·保罗·杜蒙进一步认为,“当某位怀疑论者采取沉默的态度时,他并非在怀疑中寻找一个舒适的避难所或者是避免犯错。刚好相反,在面对一些不确定的、受制于等量矛盾的对象时,他仅仅在描述自己灵魂的平衡状态。”[22](P25)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搜集整理的皮浪的言论中,怀疑论者的怀疑不仅被视为最高的善,而且被认定为一种崇高的品格。为了将自己的思想和古代怀疑论会通,巴尔特建立了一个关系式:“中性=设想沉默的权利——一种沉默的可能性”[23](P23)。由于对一切事物都无所取舍,主动放弃任何判断,所以人们就不会陷入各种矛盾冲突或者被权力所捕获。
为了把“沉默”上升为一种智慧,巴尔特还在东方哲学中不断寻找资源。如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五十二章》)让·葛罗涅在《道家精义》中将这句话完全解释为怀疑论的:“首先不判断,不说话;然后内心不判断,不说话。”[24](P29)[25](P110)因为巴尔特恰巧通过这部著作接触到道家哲学,所以他认为道家主张彻底的沉默。至于后来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在巴尔特看来,这种彻底的沉默已经不是缄口不言,而是充满诗意的万籁俱寂了。*在1978年2月25日的演讲中,巴尔特对“缄口不言”(tacere)和“万籁俱寂”(silere)两个词进行了区分。参见Roland Barthes.The Neutra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21-22.在题为“中性”的研讨班上,他还列举了佛祖妙传心印的例子。据《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记载,佛祖于灵山法会上拈金色钵罗花示众,众僧悉皆罔措,唯有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佛祖于是将心印付传于他。巴尔特认为这是沉默的最高境界,它不仅跳出了语言的罗网,而且开启了最高层面的“悟”。在《符号帝国》中,巴尔特认为全部禅宗的实践就是要制止语言,远离各种攫取意志,从而避免意识形态符码对我们的统治。[26](P74-75)
从学理的角度看,这些解释完全是牵强附会,因为无论是古希腊的怀疑论哲学还是东方的禅道哲学,均与权力无涉。巴尔特为了解构权力,而将这些资源与中性关联起来不过是为自己的理论张本。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上,也有人出面纠正他的错误,而巴尔特却说:“对于佛教、道家、否定神学以及怀疑论哲学,我都一无所知,也不假装知晓。如同人们在思想史或宗教史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对象是教义的、系统的、历史的本体——它们根本就不在我的话语里。说到极点,当我引用佛教或者怀疑论的时候,千万别相信我。它们不在我的掌握之中,对于它们,我一点也不精通。更明确地说,我别无选择,不得不‘对其整体失敬’(尼采语)。因为教师应该完整地(这种完整,依照他自己的安排)授课,而我却不能这样讲述(佛教,怀疑论)。我的目标是:既不当导师,也不做信徒,而是扮演尼采意义上(无需获得好评)的‘艺术家’。”[27](P64)这番话充分体现了巴尔特的真实意图。然而,他将东方的禅道哲学理解为怀疑论的,并且将它们和古希腊的怀疑论哲学一起嫁接到自己的理论之中,这一做法不仅削弱了其思想解构的锋芒,而且使他逐渐蜕变为一个寂静主义者。
三、寂静主义的哲学
巴尔特晚期非常喜欢日本僧人东阳英朝所编的《禅林句集》中的一句诗:“静坐无事,春至草生。”在《小说的准备》、《中性》以及《新生》的提纲中,他都多次引用过。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这句诗写的精美,而是因为它所展现出的行为方式(坐禅)和生存境界。巴尔特评价说:“此处没有语言的惊扰,见证着纯净的生活”,“这里没有本我,只有一个姿势与大自然同在”,“静坐无事=实际上意味着彻底摆脱了谬误的世界”。[28](P185)如果联系到传记作家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和埃里克·马尔蒂对巴尔特的晚期记录,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此,巴尔特已经从理论上退却了,他开始在哲学中构建一种宁静的生活。这一变化刚好也印证了黑格尔的观点:“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真正愿意做一个怀疑论者,那他就是无法说服的,也就是说,根本不能使他变成一个抱持积极的哲学的人——正如一个四肢麻木不仁的人是无法使他站起来的一样。”[29](P116)
在不断搅扰的现实生活中,怎样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呢?巴尔特所设计的一种方案是“无为”。这是中国道家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原意是:遵循事物自身的规律,不强作妄为。法国汉学家亨利·马伯乐在其著作《道教与中国宗教》中却将老子的这一观念误解为“不行动”、“不作为”,不过他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消极退避的哲学观念,而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其核心是“贤者不争”[30](P152)。巴尔特通过马伯乐的著作接触到这一观念,并对它作了新的阐释:“无为”就是“无所事事”、“无动于衷”、“免除意志”、“弃绝”、“休眠”,总而言之,就是要让自己处于一种零度的状态。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中,巴尔特读到了这样的句子:“那就是,不要再追求什么事业,只要平安度过此生;不要再自寻烦恼,不要还有什么欲望”[31](P178)。这是安德烈公爵在某次旅行中的所思所想。按照西方的传统观念,这是一种悲观主义,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在巴尔特看来,这就是无为的境界——一种很难被西方人所理解的生存智慧。
巴尔特所设计的另一种方案是“Xéniteia”。这是他从希腊语中撷取的词汇,该词的原意为“远离家乡”、“流浪到国外去”、“在国外居住”。巴尔特引申为一种特殊的流放形式——自愿流放或者对自己的就地流放,即虽然身处现实之中却主动成为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局外人。他举了卢梭的例子。在莫蒂埃投石事件之后,卢梭便逃到位于碧茵湖中央的圣皮埃尔岛上避难。不久,他就产生了一种自我流放的冲动:“我心中惴惴不安,真巴不得人们把我这个安身的地方建成一座永久的监狱,把我在这里关一辈子,剥夺我的一切权利,断绝我走出这个监狱的念头,切断我与陆地的联系,使我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忘记岛外的人们,也让岛外的人们忘记我。”[32](P139)[33](P60)在世人眼里,这可能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巴尔特却认为这是一种藏而不露的生活,一种罕为人知的智慧,它不仅能够免除社会责任,而且可以实现内心安宁。尼采说:“人与人之间,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沟壑众多。成为自我的意志,即我称之为距离感人法的东西,是所有强大时代的本质。”[34](P132)[35](P70)巴尔特认为尼采所提出的“距离感人法”的主要原则是既不支配别人,也不被别人所支配。既然现实生活充满了各种权力和斗争,那么成为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局外人就是必需的。
除了以上两种之外,巴尔特还设计了另一种方案:“idiorrythmie”。这是他根据希腊语的idios(“本人的”、“个人的”)和rhuthmos(“节奏”、“节奏性”)杜撰的一个词汇,我们不妨把它翻译为“个人节奏性”。为了说明这个词语的含义,巴尔特列举西方宗教史上两种不同的隐修体系:一是安托万体系。安托万是古代埃及著名的修士,据阿塔那修的记载,他三十五岁左右进入卡拉尼斯沙漠苦修,在那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后来,他又遁入深山。安托万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迎来了大批的追随者。这些人隐居在他周围,彼此独立,互不干扰。二是帕科姆体系。与安托万体系相比,这是一种聚集修道的方式。在帕科姆修道院,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严格的管理制度生活,他们在公共餐厅吃饭,在集体宿舍就寝,在教堂里聚会祷告。巴尔特认为,这是一种最不值得推广的隐修方式,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不但要遭受各种权力的干预,还必须保持共同的节奏。而安托万体系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自我禁闭,这些修士隐居在窝棚或洞穴里,绝大部分时间不与外界打交道,只有在特殊的宗教节日才聚集在一起。巴尔特后来在阅读雅克·拉卡里埃的作品《希腊之夏》时发现,公元10世纪前后在马其顿南部的阿索斯山上生活着一群修士,他们虽然聚集在一起,但是每个人又都拥有自己的空间,既可以独自隐修,也可以相互交流。巴尔特将这群人进退自如的隐修方式称为“阿索斯山体系”。该体系最突出的特征是“个人节奏性”,即每一个个体在共同体中却又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由此可见,这些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是自由的,他们的生活与权力无涉。巴尔特认为,如果说安托万体系和帕科姆体系是两种极端的隐修方式,那么阿索斯山体系就是“一种居间的、乌托邦式的、伊甸园式的、田园诗般的形式”[36](P9)。
以上这些方案非但不够科学,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许多难以自洽的矛盾。比如个人节奏性的生活对于自我流放来说,还保存着对群体的迷恋;宗教的生活和日常俗务之间毕竟殊途异轨。不过,它们在一点上是相通的,即这些方案都集中反映了巴尔特晚期因信靠怀疑论而导致的寂静主义心理。因此,有学者评论说:“巴尔特远不只是学者理论家,其内心蕴涵着(不合时宜的)诗学怀乡病,而其表面的主张不过是另一种生存愿望的变相表白,这种向往文学乌托邦境界的分析性表白,遂可成为我们再次反思人类一般伦理学情境和文学伦理学情境的一面镜子。”[37](P355)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巴尔特及其理论进行新的、更加全面、更为有效的评估。
[1] Rick Rylance.RolandBarthes.New York&London&Toronto&Sydney&Tokyo&Singapore:Harvester Whea ̄tsheaf,1994.
[2][5][11] 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Rudolphus Teeuven.“An Epoch of Rest:Roland Barthes’s ‘Neutral’and the Utopia of Weariness”.CulturalCritique,2012 (80).
[4] Antoine Companon.“Roland Barthes’s Novel”.October,2005 (112).
[6] Roland Barthes.CameraLucida:ReflectiononPhotography.London:Vintage,1993.
[7] 埃里克·马尔蒂:《罗兰·巴特:写作的职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 Tzvetan Todorov.“The Last Roland Barthes”.In Neil Badmington (ed.).RolandBarthes:CriticalEvaluationsinCulturalTheory. Vol.IV.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10.
[9] [10] Susan Sontag (ed.).ABarthesReader.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82.
[12] Louis-Jean Calvet.RolandBarthes:ABiograph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4.
[13]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4][15][16][17][22][23][24][27][28][31][32][36] Roland Barthes.TheNeut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18] 哈杜默德·布斯曼:《语言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9]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Ⅲ),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0][34] Roland Barthes.HowtoLiveTogeth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21] 雅克·施兰格等:《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5] Jean Grenier.L’espritduTao.Flammation:Paris,1973.
[26] Roland Barthes.EmpireofSigns. New York:Hill and Wang,1982.
[2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0] Henri Maspero.TaoismandChineseReligion.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1.
[33] 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5] Friedrich Nietzche.TheTwilightoftheIdo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7] 李幼蒸:《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载罗兰·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张 静)
Late Roland Barthes and Skeptical Philosophy
JIN Song-lin
(School of Philosophy,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School of Literature,Anqing Normal College,Anqing 246001)
In the inaugural lecture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Roland Barthes claimed that power is everywhere.Exhausted,defeated here,it will reappear there.The object which power is inscribed is language or its necessary expression:language structures.He borrowed the notion “neuter” from phonology of N.S.Trubetzkoy,Louis Hjelmslev,etc.,and connected it with the philosophy of skepticism to deconstruct the power lurking in language structures.It’s proved that the false connection not only weakened the strength of deconstruction,but also made him a quietist being accused.The image of late Roland Barthes challenges our inherent idea,and urges us to reevaluate him and his theory in a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effective way.
Roland Barthes;neuter;skepticism;power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罗兰·巴尔特的晚期研讨班理论研究”(SK2014A296)
金松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安徽 安庆 24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