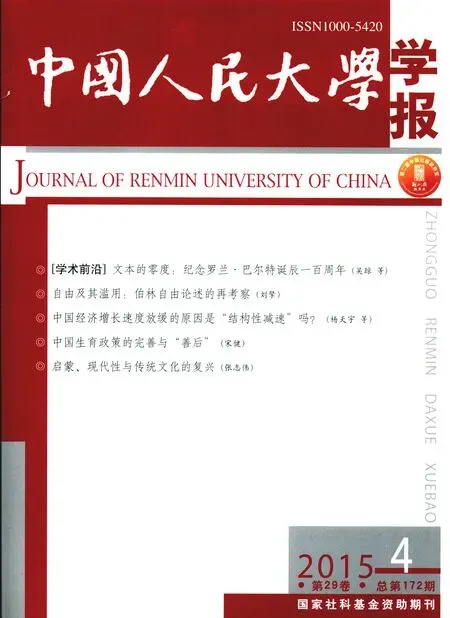环境法视野中的环境义务研究述评
李艳芳 王春磊
环境法视野中的环境义务研究述评
李艳芳 王春磊
关于环境义务的研究缘起于环境权的困境。环境义务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针对环境法的本位问题与环境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一直延续到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过程中。义务本位论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已有的环境义务研究多从主体角度展开,并集中于政府环境义务。关于企业环境义务的研究突破不大,关于公民环境义务的研究则集中于消费者角色。无论何种立场,国家在环境义务中承担主要角色是普遍的呼声。相对而言,关于环境义务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更多的理论深化。
环境义务;权利本位;义务本位
环境法学界对环境义务的研究缘起于环境权在立法、司法领域里遭受的困境。对环境权的理论研究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开始,但是经过30多年的探索,学界至今仍然对环境权主体、客体、内容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甚至对环境权本身的意义也存有质疑。受此影响,环境法学研究难以沿着“利益—权利—救济”这一主流的法学研究范式进行理论建构,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也备受传统部门法的诟病。环境法理论研究的滞后,也传导至环境法律制度的有效建立和环境立法的质量提升。有人讥讽中国虽然有数量庞大的环境立法,但却同时拥有最恶劣的生态环境。痛定思痛,学者们开始反思,将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环境立法、环境司法救济中心所带来的问题,进而跳出环境权的困境寻求新的研究范式。自2003年起,徐祥民教授发表了一系列质疑环境权本位的文章,成为国内环境法从环境权到环境义务思维转变的节点。近十年来,有关环境义务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并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虽然体现了环境法义务本位思想,但尚未形成自觉的理论指导。本文希望通过对环境法义务理论的梳理,厘清环境法义务理论的主要内容,为未来的中国环境法治提供较为明晰的理论发展方向。
一、环境义务本位
重构环境法理论体系的努力,其起点就是环境法本位问题。因此,环境义务研究兴起之初矛头就直指环境权,从而引发了环境法本位之争,即中国环境立法应以环境权利还是环境义务为本位。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争论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关于环境权的主体、理论依据以及路径选择合理性的论辩最为激烈。[1]限于本文主题,以下仅涉及关于环境义务本位的相关争论。
(一)环境义务本位论的基本观点
环境法的义务本位,是指通过普遍设定环境义务、限制所有主体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的方式来设计环境保护的实现模式。[2]虽然义务本位论也有不同的观点(如义务重心论[3]),但总体上都主张通过设定义务性规范来实现环境法的目的。
义务本位论的首倡者徐祥民教授认为,环境资源有限而人类欲求无限,因此,解决环境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分配,这种分配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义务,义务本位是环境法的唯一选择。[4]他认为,人类在各种环境极限和环境危机面前必须自我限制。[5]义务本位要求法律为维护或实现整体利益而对个体设定义务,将个体义务作为个人与整体之间法律关系的主导方面,按照个体义务履行的需要配备其他法律制度。在义务本位的法理下,个体对整体的义务是一种普遍的义务,同时,政府也是义务主体。[6]
一方面,义务本位论者采用立证方式,从正面论证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他们认为,环境保护法的任务就是把过去认为是合法的做法宣布为非法,把过去曾作为权利予以肯定的一些行为宣布为不是权利,或者还承认其为权利但要求其行使必须附加某种条件,或不得超过某种限度。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保护法就是权利限制法,是以义务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现代环境法。[7]环境利益不是人们行使权利带来的好处,而是人们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必然结果。只要所有人都履行了保护环境的义务,环境利益就能自然实现。如果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的,某一行为即使从表面上看是个体行使权利的行为,但其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权利行为了,而是对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环境法是一种义务本位法,是义务配置法。[8]有研究认为,义务本位是顺应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选择,它为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也是推进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文明飞跃的重要思想武器。[9]也有研究分别从实然规范角度分析了能源法、海洋资源法、流域立法、循环经济法等的义务本位。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看,这些研究无疑是对环境法义务本位的有力论证。
另一方面,义务本位论者通过强烈质疑和批评权利本位论来反证自身。他们认为,全球性环境危机至少在危机应对领域已经打破了权利话语,使权利面对环境危机而无能为力,取代它的应是人们的责任意识,是人们共同保护环境的义务。只有从个体出发,努力合作保护环境,以实现人类整体的环境利益才是切实可行的途径,而对于个体来说唯一的方式就是付出或限制,这种付出或限制,在权利义务中的体现就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所以,与环境结合的应该是义务,而不是权利。[10]义务本位论者认为以环境权为本位不适合环境法,因为环境权“设定—主张—救济”之路不足以达致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而环境义务“设定—执行—履行”的方法更有利于实现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1]环境权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不是靠主张、请求权利来实现,而是靠环境义务的履行来实现,靠义务主体的主动积极履行来实现。[12](P22)与权利本位论相比,一方面,义务具有不可放弃性、不可违背性的特点,只要义务被履行,义务规范所意图保护的利益就必然实现;另一方面,义务规范可以指向更为广泛的利益保护。因此,以义务为本位的立法更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13]
(二)对义务本位论的反驳和批评
针对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义务本位论也遭到了权利本位论者的反驳。权利本位论者认为,环境立法的失败不是权利本位导致的,而是由于权利本位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是权利本位缺乏实现的客观条件——公共机关支持和监管的缺位等外在因素造成的。[14]权利本位论者还认为,义务是权利本位的当然内容,权利本位解决的是权利义务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忽视义务,在这点上义务本位论者存在误解。[15]
权利本位论对义务本位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法律规范的外在形式谈论本位问题过于浅表。权利本位论认为,本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具体法律中采用何种法律规范,则与其所依附的法律部门的性质相关,即使通篇都是义务性规范,也并不代表具体环境法律就是义务本位型的。[16]权利本位在法律规范上也可以以义务的面目出现,这是一个法律规范的设置策略问题。[17]义务本位论主张以义务性规范为主进行立法,实际上仅从法技术层面论述本位问题,即仅在实在法层面探讨义务规范的价值,属于对本位的浅层认识。[18](2)将公共利益的保护交与政府依旧存在问题。权利本位论者指出,义务本位论在强调自我限制原则的同时忽视了相互限制原则,混淆了政府利益与公共环境利益,走向了整体主义的极端——公民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主张的权利[19];而且将执行法律的主体交给政府,难以避免政府失灵的问题。[20](3)批判权利本位的论据之一——环境实践/环境立法的失败,同样可以用来批判义务本位。权利本位论者认为,义务本位论的批判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因为当前中国环境立法的主要形式就是义务性规范,所以实践方面的缺陷同样也指向了义务本位论。[21]换句话说,当前环境立法从形式上看就是“义务本位”的,而现实是环境立法不成功、污染日益严重,所以用这一理由批驳权利本位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4)义务本位在正当性与时代性上存在欠缺。权利本位论者认为,义务本位论的研究浅尝辄止,缺乏义务设置和配置的正当性研究[22],而且以义务为本位也不符合时代潮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就是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文化体系,而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是法治主义与人治主义的重要分水岭之一。[23]以义务为本位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是逆立法潮流而动。[24]
也有学者从评论环境法本位之争的角度对环境法本位之争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些学者认为,环境法的本位之争是对法学理论提出的权利本位论的“直觉式反驳和全盘式接受”,没有提供审视环境法的内在基准。他们认为,在这场争论中,权利本位论缺乏现实性研究,义务本位论缺乏哲学正当性研究,二者在根本上有五个共同倾向:(1)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环境公共利益的共同善和个体善的特质;(2)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利己倾向和合作倾向在维护、增进环境公共利益中所具有的功能;(3)都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主观权利(主观法)和客观法,因而都没有洞见环境法是维护、增进环境公共利益的客观法;(4)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或夸大了中国社会复杂文化传统的某个方面,因而都没有充分运用这种复杂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来担当维护、增进环境公共利益的历史使命;(5)都忽视了环境公共利益制度化为个体权利的可能性。[25]有学者认为,这种纯思维式的“先验的概念思维”辩论急于建立自己的“本位帝国”,却忽略了环境法的真实目的——解决环境问题。[26]也有一些学者跳出两者之争,就环境法本位问题提出了环境权利义务并重模式、环境行为指向等不同研究路径。
二、环境义务的内容与主体
(一)环境义务的内容
环境义务从不同角度可有不同的分类。从义务内容角度看,有基本环境义务与具体环境义务之分。蔡守秋教授指出,基本环境义务是指为了保障基本环境权利实现并且在各种具体义务中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的保护环境的义务。这里的“保护”是指起码的、力所能及的、合乎常情的保护。基本环境义务是内含于基本环境权利中的义务,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既是行使基本环境权利的内在要求,也是对行使基本环境权利的内部限制。基本环境义务的基础性,是指该义务是对一切单位和个人的起码要求、起码约束,是一切单位和个人在其能力范围内能做得到或能履行的义务。基本环境义务的普遍性,是指对行使基本环境权的一切单位和个人普遍适用的义务。[27]不过,由于对基本环境权利即公民环境权的质疑,关于对应的基本环境义务的探讨比较少。关于具体环境义务的研究占据了环境义务研究文献的主体,但这些研究多从主体角度出发,并以现有法律规范为依据,研究深度和理论性都不足,缺乏对某类具体环境义务的共性研究。在众多文献中,只有唐忠辉对某一具体环境义务——环境强制检测义务,从其正当性、主体、内容、作用、实现途径等方面展开了系统深入研究。[28]
关于环境义务的特征,普遍性、绝对性、客体隐蔽性(一称对物性)得到一致认同。普遍性指所有受法律约束和调整的社会主体都毫无例外地负有环境义务,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国家;绝对性指承担环境义务不附带任何的免除条件,且不以权利人提出的履行要求为前提;客体隐蔽性指环境义务从表面上看直接指向环境,实质保护的是人类整体利益——环境利益。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了优先性、有最低限度而无最高程度限制、自益性与共益性同在,以及义务标准确定上的科技依赖性等特征。[29][30]很多研究环境义务的文献都指出环境义务与环境权具有不对称性,前者指向的环境是局部的、单项的,后者指向的环境是整体的、综合的。这种不对称表现在范围、强度、时间向度以及整体与要素对比等方面。[31]
(二)环境义务的主体
从主体角度研究环境义务是当前的热点。现有研究一致认为环境义务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包括国家/政府、法人/企业、公民个人,但对不同主体承担环境义务的范围及限度仍有不同认识。有研究指出,确定环境义务主体应依据污染者负担原则、集体负担原则和共同负担原则的顺序进行分配,只有在穷尽前面原则的基础上才可以适用后面的原则。[32](P156-157)
1.政府环境义务
关于政府环境义务存在不同称呼,如国家环境义务、国家环境职责或政府环境职责。[33]这些不同称谓源于不同的理论基础。有研究表明,关于政府环境义务的理论基础有公民环境权论、国家环境权论、公共职能论、福利行政论、善治论、环境安全保护义务论、公众环境利益论不同学说。[34]还有研究认为,政府环境义务不能简单根据“基本权利—国家义务”的演绎方式论证,而应从国家任务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归纳推理,政府环境义务基于“国家目标条款”生成。[35]
一般认为,政府环境义务是第一性义务,违反此义务会导致第二性义务——政府环境责任。但也有学者不加区分地将两者统称为政府环境责任。[36]还有一些研究并不严格区分政府环境(管理)权和政府的环境义务,而统称为政府环境职责。政府环境义务的早期研究一直与政府的环境管理权相交叉。有观点认为,政府的环境义务与政府的环境权利是并生的,不正确行使政府环境权就是对环境义务的违背。反对的观点则认为,政府没有环境权利,其所具有的环境管理权是基于公民环境权的一种让渡。将政府环境义务包含于政府环境职责之中,也源自行政法上关于行政职责的解读。在行政法上,职责是职务与责任的合称,前者指职权,后者指义务。对政府部门而言,行使职权同时也是履行义务,行使职权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义务包含在“职权”或“职责”之中,政府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或履行职责既是其权利,又是其义务。[37]
对政府环境义务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有研究从权利义务对应的角度出发,认为度量政府环境义务的标准是基本环境权,而基本环境权的度量依据则是环境质量标准。[38](P194)有研究认为,政府环境义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预防人为环境风险的伦理义务;二是制定环境标准,以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39]也有研究将政府的义务具体化为指引、教育义务,预防、规划义务,监督、管理义务,评价、强制义务。[40]有的研究则将政府环境义务进行体系化的梳理,区分为规划决策类、实施执行类、保障措施类、监督机制类、责任追究类。[41]还有研究认为政府环境义务包括现状保持义务、危险防御义务、风险预防义务。[42]可以看出,环境法上的政府环境义务与传统行政法关于政府职责相比,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事先预防的义务在政府环境义务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是环境法调整机制与其他部门法的明显区别所致。环境法调整机制的变革,促使政府环境义务产生了由物文主义到人文主义、由消极义务到积极义务、由保护义务到给付义务、由一元型到多元分散型的嬗变。[43]
尽管有环境权利本位和环境义务本位的争论,但争论双方对强化政府承担环境义务持普遍支持的观点。普遍认为,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其提供者应当是政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府追求GDP的增长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生态破坏等问题的主要原因,只有规范和控制好政府影响环境的行为,才能有效遏制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保护和改善环境。[44]因此,在环境义务的承担上,政府应发挥主导的作用。更极端的观点认为,公民的环境权就是政府的环境义务,而不应成为人人的环境义务。[45](P151-152)
政府环境义务也是《环境保护法》修改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环境法律施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环境保护法》修改应强化政府环境责任。[46]张梓太教授在1995年就指出,完善环境立法应当实现政府部门由“权力主体”向“义务主体”的转变,政府在违反环境义务时应承担相应责任。[47]蔡守秋教授也指出,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和不足,是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失灵、环境法律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的实质是缺乏完整性、有效性和正当性。他归纳了政府环境责任的八大缺陷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对策。这八大缺陷是“重政府经济责任,轻政府环境责任”、“重企业环境义务和追究企业环境责任,轻政府环境义务和追究政府环境责任”、“重政府第一性环境责任,轻政府第二性环境责任”、“重政府环境权力,轻政府环境义务”、“重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轻中央政府的环境责任”、“重政府机关的环境责任,轻其他国家机关的环境责任”、“重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责任,轻政府负责人的环境责任”、“重政府环境责任中的行政调整机制,轻政府环境责任中的其他调整机制”。他指出,健全政府环境责任的重点和方向,是不断提高政府环境责任的可操作性,实现政府环境责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48]完善政府环境责任,既要拓展政府环境第一性义务即政府环境职责,提升政府公信力,也要强化政府环境第二性义务即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建立全面的问责机制。[49]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则主张,政府应当在保护环境上有积极的作为,要求国家以积极的姿态向公民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以使得个人能够在舒适安宁的环境中生活,主要是提供适当的环境公共产品和搭建有关制度性平台,以充分保障公民环境权益。[50]
2.企业环境义务
与政府环境义务一样,企业环境义务的界定也要面对义务与责任的区别问题。一些研究认为,企业环境责任包括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只有企业环境法律责任才与环境义务相关。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应将企业环境责任定位为企业的环境义务。根据本文研究主题,以下所称的企业环境责任将只限于法律意义。在这一语境下,企业环境责任等同于企业环境义务。
企业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造者。要想从根本上治理环境,企业必须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限制。然而,企业是理性营利者,要想让企业主动自觉地以一定的成本承担治理污染的成本或者放弃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治理污染就是限制企业的排污行为,约束其生产经营活动可能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各国环境法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赋予政府职责对企业排污行为进行约束监管,另一方面则对企业施加环境义务,要求企业在行使自己的财产权、经营权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排放,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在我国,企业环境义务是每部环境法律/法规的规范重点,占据了大量的条文篇幅;数量众多而细致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几乎也将企业环境义务进行了全方位的细化和具体化。在这一背景下,当前较为通行的“对策法”或“立法论”式的研究模式用武之地显然有限。这也是当前关于企业环境义务的研究文献非常少且理论价值十分有限的主要原因。
早期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研究集中于环境侵权责任,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理论建构。这也反映在环境立法上。有研究认为,我国现有法律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存在主体单一、环节单一、责任内容欠缺、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企业环境责任的真正革新应是使企业环境责任从传统的侵权责任中走出。[51]近些年关于企业排污权的研究较多,排污权的设计让企业环境义务有了更多的理论创新空间。有观点认为,《京都议定书》的制度设计促进了环境义务与经济权利之间的互换性,而排污权首次以法定的正当权利形式出现,则体现了环境义务与环境权利之间的意念转换。[52]正是因为环境容量资源的准公用品的特性,使得排污权具有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的双重法律性质,结合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防治环境污染的初衷,现阶段还是应该更多地强调排污权的义务属性。[53]
3.公民环境义务
在环境义务主体的研究中,关于公民环境义务研究的文献数量是最少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十分有限。台湾学者陈慈阳认为,人民(意即公民)的环境义务可区分为实体义务和与程序相关联的义务两类,实体义务是人民的自主义务,包含不污染环境(消极义务)和美化环境、监控污染行为(积极义务)两个方面;与程序相关联的义务包含登记、告知、参与及容忍等。[54](P355)对公民环境义务的具体研究目前只限于公民作为消费者和生活垃圾制造者时所承担的环境义务。
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出发,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人类在享有对自然的权利的同时,应该也必须履行对自然的相应义务。人对自然的义务主要包括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义务、可持续发展的义务、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义务这三个方面的内容。[55]不同领域中公民应承担的环境义务的性质也不同(强制性的、约定性的或其他),因此,政府与居民的环境义务应合理界分和适度平衡,设置公民强制性环境义务应以政府相应配套义务的前置履行为基础。[56]
对公民环境义务研究较多的是消费者环境责任。有研究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现时代的异化消费观给予了关注,认为这种异化消费的蔓延应当引起环境法对自身规制对象和权利义务配置等方面的反思和调整,包括将消费者和企业一样明确视为环境法的规制对象、均衡配置环境法上的企业环境权利和义务、消费者环境义务的法律化。该研究提出,可根据消费过程的不同环节,对消费者的义务进行分解。(1)购买环节:负担真实的环境成本的义务;减少或消除基于虚假需求的消费的义务;选择环境友好型产品的义务。(2)使用和消费环节:一是在购买环节没有承担该当的环境义务时,消费者在消费和使用相应的产品或服务时将受到替代性的环境义务的约束;二是无论消费者在购买环节是否已经承担了该当的环境义务,在使用和消费环节仍要承担特定的环境义务,即应当确保自身的消费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或破坏在环境可承载的范围之内。(3)处置环节:承担便利废弃物品回收的义务、减少进入处置环节的废弃物品。[57]另有研究认为,近代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因此,在法律上承担环境义务的公民应限于消费者,即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应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消费者环境义务主要包括适度消费、循环消费、妥善处置消费废弃物等义务规范。[58]
已有的研究也探讨了公民环境义务与企业环境义务的关系问题。有观点认为,就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消费者不应当承担主要的环境义务。[59](P159-162)也有观点认为,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义务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的。消费者能承担的真实环境义务决定了企业环境义务的边界。消费者环境义务的设定和完善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环境义务的实现。[60]
三、环境义务的法律表达
环境立法应如何展现和反映环境义务?换句话说,环境义务在法律规范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这既关涉环境义务理论能否落在实处,也关涉环境保护目标能否实现。
(一)关于环境义务的宪法表达
环境义务的法律表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环境义务在宪法中如何规定。我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学术界将这一规定界定为我国宪法上的基本国策条款。由于只涉及“国家”这一主体,有研究认为,我国当前宪法中缺乏关于企业和个人环境义务的规定,并建议采用“义责结合型”的设计予以完善。[61]有研究认为,宪法第26条是客观法性质的基本权利,它赋予了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不具有可请求性。[62]有研究则认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是国家环境保护的宪法规范形态,是对所有国家权力进行约束的“国家目标条款”,现行《宪法》第26条和第9条第2款共同表述了环境基本国策,并具有“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效力。[63]有研究认为,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义务。在配置环境义务时应当区分消极的环境义务和积极的环境义务,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分别进行配置。[64]
(二)关于《环境保护法》的环境义务规范及立法模式
环境义务在法律规范上的具体表现,更重要也更为切实的是《环境保护法》中对环境义务的规定。有研究认为,现行环境法对环境义务的规定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和宣示性,是一种消极义务,它强调事先预防和事后治理的模式,缺乏事中控制,在义务的架构上缺少积极进行环境投入的义务机制。环境义务应走向一种积极性的、生态法域的义务——环境回馈义务,具体指人类对环境负有的回报和补偿责任,具体表现为涵养水源、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等对环境进行积极投入的行为。[65]有研究将这种积极、主动保护环境的行为机制称为环境责任。[66]相反的观点认为,《环境保护法》中关于“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的规定不是空洞的摆设,而是具有丰富内容的条款,它暗含了环境权、明示了环境义务,可作为处理环境纠纷的依据,是加强环境管理的武器。[67]另有研究论证,“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应从义务视角解释为对公民和其他主体环境义务的规定。[68]
有学者对《环境保护法》仅规定义务不规定权利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和逻辑是一种典型的从国家权力出发到公民义务、从公民义务出发强化政府权力的立法思路,它违背了从公民权利出发到政府义务(职责) 、从公民权利出发强化政府责任的法治原则。仅仅从规定公民的基本环境义务出发,无法确立与该义务相联系的政府义务或职责,只能确立和促成与该义务相联系的政府权力或职权。[69]
(三)关于政府环境责任的立法完善
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关于环境义务的规定将影响整体环境法体系和制度设计。尽管对《环境保护法》中环境义务的规定方式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其中环境义务的配置,所有的研究都认为应加强政府环境义务(责任),并采取激励措施促进企业和个人环境义务的履行。有研究提出,《环境保护法》立法应强化政府环境责任以提高环境行政执行力,包括健全环境管理责任、加强环境服务责任、兼顾其他环境责任。[70]政府环境责任的立法完善,还需要改变现有的政府主导的环境立法体制,突出立法机关主导,并加强公众参与。[71]有研究提出,实现政府环境责任的保障是健全的问责机制,这单靠《环境保护法》是无法完成的,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的支持。[72]有研究进一步提出,完善政府环境问责机制应从内部与外部、权力与非权力等多方面着手:在立法机关问责方面,在全国人大内部确立专门的机构对政府进行问责;在司法机关问责方面,强化和完善环境行政审判,扩大受案范围,增设诉讼类型;在社会公众问责方面,加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通过政府环境审计、强化环保部门对政府其他部门的监督等方式深化行政机关问责。[73]
(四)关于企业环境义务的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环境立法中关于企业环境义务的规定数量众多,涵盖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清洁生产等几大方面。当前关于企业环境义务的规范性研究涉及企业环境义务的细化、拓展两个层面。细化指在已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企业环境义务的具体落实进行细化研究。例如有研究提出,完善企业环境义务法律制度需要细化环境准入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细化环境准入制度“不仅要求建设项目符合环境标准,也需要评价企业作为经营主体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即“还应当考虑该企业的股权情况、资金能力、技术手段和发展规划等主体评价”,“对某些承担环境责任能力有限的企业,要求其在申请环境准入时提供一定形式的担保”。细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包括细化披露对象和披露内容等。[74]“拓展”指在现有企业环境义务法律规范体系中,增加新的企业环境义务法律规定或突破实在法渊源边界,将企业环境义务推进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外领域。例如,有研究提出应增加环境责任主体延伸制度,即规定企业主体资格终止后环境责任延伸承担主体,包括股东、高管、利益相关人等。[75]有研究则以具体实例对环境污染责任承担中的母子公司关系进行了研究。[76] [77]更多的研究关注《公司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以此拓展企业环境义务的法律渊源。此外,绿色税收、绿色证券等相关立法研究,也体现了企业环境义务研究的拓展。
(五)关于公民环境义务的法律表达
针对学界担忧的环境义务尤其是公民环境义务履行难问题,有研究提出了公众共用物标准,认为判断或评价一切单位和个人是否履行其基本环境义务的主要标准,是该单位或个人的行为是否使环境保持在公众共用物这种状态,或是否独占独用环境这种公众共用物,或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排除其他不特定多数人享用环境这种公众共用物。[78]有研究以具体立法为例,认为在为公民设置环境义务时应合理界定政府与公民的环境义务边界,法律为公民设置强制性环境义务应谨慎为之,要充分考虑其实现的外部资源依赖,并注意与社区自治等民主形态之间的冲突与协调。[79]
四、环境义务研究的评价及展望
相对于环境权研究,国内关于环境义务的研究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在经过本位之争和《环境保护法》修改理念之争后,尤其是在环境污染频发、雾霾日益严重的现状下,环境义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明确支持义务本位的学者也逐渐增多。但是,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相比于环境权研究,环境义务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深化研究。
第一,关于环境义务内涵的研究流于表面。现有环境义务的定义套用了传统关于义务的界定。就法理而言,权利和义务尽管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主体上,但有主次之分,所以仍能有明显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分,且权利主体所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其他人。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领域,义务主体所负义务的绝对性特征明显,这种绝对性的义务也能现实履行。然而,在环境法领域,当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存在于同一主体(尤其是公民个人)上时,权利与义务的主次之分并不明显,因此,该主体既是环境权利主体也是环境义务主体,且权利主体所对应的义务主体不仅包含其他人,还包括自己。公民要保护自身的环境权利,就要承担相应的环境义务。例如,想要得到清洁的水源,不仅要求他人不排污,公民本人也不能排污。从这一角度说,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具有并生性特征。与其他部门法中的义务相比,在环境法领域,要求企业或者个人承担不排污的绝对性义务显然是不可能的。环境义务与传统法上的义务有明显不同的特质,单纯套用传统法理上对义务的理解来界定环境义务,显然缺乏对环境法内在基准的考量。
第二,关于不同主体环境义务的研究轻重不均。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承认,公民和企业环境义务的充分履行是实现保护环境目标最根本的途径。然而,公民环境义务和企业环境义务的履行,无论是在法律设计上还是现实考量上,都面临诸多困难。就法律设计而言,公民保护环境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界限区分较难,作为营利性经济人的企业,所承担的环境义务也只能是法律的单纯附加,没有内驱动力。从现实考量,一方面,环境问题产生于近代工业发展之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此过程中,政府承担首要责任;另一方面,环境具有生态整体性,作为公共物品,整体环境质量的保持和提高,已超出公民个体、社会组织或企业的能力范围,因此,将政府设定为环境义务的主要承担者,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目的的实现。出于这些原因,政府在所有环境义务主体中被推向主导地位。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应承担主要的环境义务。基于此,已有关于环境保护义务主体的研究集中在政府环境义务上,对其他主体环境义务的则关注较少。
第三,在有关政府环境义务的研究中,预防性环境义务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未来关于政府环境义务的研究,在此方向上有较大的深化空间。关于政府环境义务的理论基础,现有研究仍从行政法角度进行论证,缺乏其他角度的研究。只有从环境法角度界定、认识和明晰政府的环境义务,才能真正实现提倡者所期望的环境保护的目标。
政府是环境义务的主要主体,公民和企业次之,这种选择有其现实必要性和法律可行性,但这并不是理论上淡化甚至回避对公民和企业环境义务研究的理由,而恰恰应当成为理论奋进的方向。当前环境法学界对企业环境义务的研究虽有一些思想的火花,但仍局限于履行行政义务和环境侵权责任的范围,而对公民个人环境义务的研究则只集中于消费者一个角度,缺乏全方位、系统性的研究。对于企业环境义务和公民环境义务的内涵、外延、特征、法律表征、制度运行等层面更缺乏研究。将义务与环境法特性相结合,有针对性地从环境义务中提炼、升华并反哺传统法义务理论,是环境法作为现代法值得期待的贡献。
第四,现有关于环境义务的研究集中于环境义务现状的描述,对环境法义务本位的深层原因的理论挖掘与实证研究明显不足。环境法义务本位论的现有研究局限于与权利本位论的争论,尽管提出了理论基础,但反证多于立论,且对实在法规范中大量存在的法律义务条款缺乏有力的理论论证和支撑。从法解释学和实证研究的角度论证环境法义务本位是未来值得深入拓展的领域。
第五,义务本位论指导下的环境义务立法研究逻辑尚需要进一步理清。以环境义务为本位的环境义务法律体系应遵循清晰的逻辑进行立法表达,方能便于立法、守法、执法与司法。具体而言,在规范形式上,应遵循“宪法中环境义务相关规范—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义务规范—环境单行法中的环境义务规范—其他法律中的环境义务规范”的层级逻辑;在规范内容上,应遵循“政府环境义务—企业/组织环境义务—公民环境义务”的主体次序逻辑;在规范性质上,应遵循“环境权利(存在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体系中)—第一性环境义务—第二性环境义务(环境法律责任)”的内在逻辑。当前,我国实在法中的环境义务法律规范在逻辑体系上并不十分明晰,导致条文设计与安排上笔墨不均,如政府环境责任等重要逻辑板块内容过于笼统。相应理论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未来关于环境义务的研究应以明晰化的逻辑理路进行,以使环境义务的法律表达更为顺畅。
[1] [21][26] 张祥伟:《环境法研究的未来指向:环境行为——以本位之争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14(3)。
[2][13][30] 顾爱平:《权利本位抑或义务本位——环境保护立法理念之重构》,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3] 周玉华、郭永长:《环境法“义务重心论”》,载《环境法治与建设和谐社会———2007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第四册),2007。
[4] 徐祥民:《极限与分配——再论环境法的本位》,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4)。
[5] 徐祥民:《从全球视野看环境法的本位》,载吕忠梅、徐祥民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三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 徐祥民:《生态文明时代的法理》,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春)。
[7] 刘晗:《环境资源相关权初探》,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8] 刘卫先:《从“环境权”的司法实践看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以菲律宾儿童案为例》,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4)。
[9] 陈南岳、陈西岳:《可持续发展·义务本位·文明的飞跃》,载《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10] 刘卫先:《环境人权的本质探析》,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2)。
[11] 徐祥民:《告别传统 厚筑环境义务之堤》,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12] 徐祥民:《环境权论——从人权发展的历史分期谈起》,载《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论文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
[14][15][17][22] 钱大军:《环境法应当以权利为本位——以义务本位论对权利本位论的批评为讨论对象》,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
[16][20][24] 张一粟:《环境法的权利本位论》,载《东南学术》,2007(3)。
[18] 王彬辉:《论环境法的逻辑嬗变》,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
[19][25] 王小钢:《义务本位论、权利本位论和环境公共利益——以乌托邦现实主义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10(2)。
[23] 公丕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义务本位》,载《学习与探索》,1991(6)。
[27][33][44][69][78] 蔡守秋:《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载《现代法学》,2013(6)。
[28] 唐忠辉:《论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强制监测义务》,载《政治与法律》,2009(12)。
[29][64] 刘卫先:《环境义务初探》,载《兰州学刊》,2009(2)。
[31][66] 陈晨:《对环境责任的几点思考——从“权利—义务”到群体利益》,载《法学论坛》,2006(4)。
[32][38][59] 胡静:《环境法的正当性与制度选择》,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34] 巩固:《政府环境责任理论基础探析》,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35][42][63] 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法学研究》,2014(3)。
[36][71] 张建伟:《完善政府环境责任的若干思考》,载《河北法学》,2008(3)。
[37] 黄振中、谭柏平:《试论能源法的义务性规范》,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1)。
[39] 冯庆旭:《论政府的环境义务》,载《学理论》,2012(34)。
[40] 孔云峰、李曦:《浅析法律视角下的政府环境义务分类》,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5)。
[41] 徐安住、佘芮:《政府环境责任形式研究》,载《唯实》,2011(10)。
[43] 刘耀辉、龚向和:《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中之政府环境义务嬗变》,载《法学杂志》,2011(5)。
[45] 周训芳:《环境权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6][72] 钱水苗:《政府环境责任与〈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47] 张梓太:《我国环境立法的误区及对策研究》,载《环境导报》,1995(1)。
[48] 蔡守秋:《论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与健全》,载《河北法学》,2008(3)。
[49] [70] 张建伟:《完善政府环境责任——〈环境保护法〉修改的重点》,载《贵州社会科学》,2008(5)。
[50] 钭晓东、肖雪珍:《国家环境给付义务》,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51] 吴真:《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体系之重建——以循环经济为视角》,载《当代法学》,2008(5)。
[52] 周林军:《环境规则与经济权利——〈京都议定书〉中的法律经济学理念》,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3] 刘鹏崇:《“排污权”权利主体论》,载《内蒙古环境科学》,2009(6)。
[54] 陈慈阳:《环境法总论》,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
[55] 王莹、秦碧霞:《论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载《道德与文明》,2006(1)。
[56] [79] 焦艳鹏:《公民环境义务配置的依据与边界——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为例》,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57][60] 陈贻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观与环境法的反思》,载《行政与法》,2009(12)。
[58] 秦鹏:《消费者环境义务的法律确立》,载《法学论坛》,2010(1)。
[61] 金明明:《环境义务入宪的路径分析》,载《唯实》,2009(12)。
[62] 王锴、李泽东:《作为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宪法环境权》,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4)。
[65] 刘明明:《从“保护”到“回馈”——论环境法义务观的逻辑嬗变》,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3)。
[67] 蔡守秋:《论环保法中关于单位和个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义务和权利》,载《环境科学》,1991(2)。
[68] 刘卫先:《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 条新释》,载《行政与法》,2008(9)。
[73] 张建伟:《完善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的若干思考》,载《环境保护》,2008(8)。
[74][75] 郑佳宁:《新形势下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规制——以我国的特殊防治主体为研究视角》,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4)。
[76] 冯汝:《母子公司人格否认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的运用——由信宜紫金矿业溃坝事件引发的思考》,载《河北法学》,2014(2)。
[77] 杨继:《公司环境责任之再思考——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启示》,载《法学评论》,2007(1)。
(责任编辑 李 理)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Legal Obligation
LI Yan-fang,WANG Chun-lei
(School of Law,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It was because of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dilemma that environmental legal obligation theory emerged. From the beginning,obligation theory argues with the right theory about the base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That debate continues when the environmental law is revised. Although the “obligation base” is gaining more and more support nowadays,the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legal oblig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s,especially the government than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individuals. Comparatively speaking,studies on the environmental legal obligation are still at an initial stage,and therefore more theoretical deepening is needed.
environmental legal obligation;right base;obligation base
李艳芳: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春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