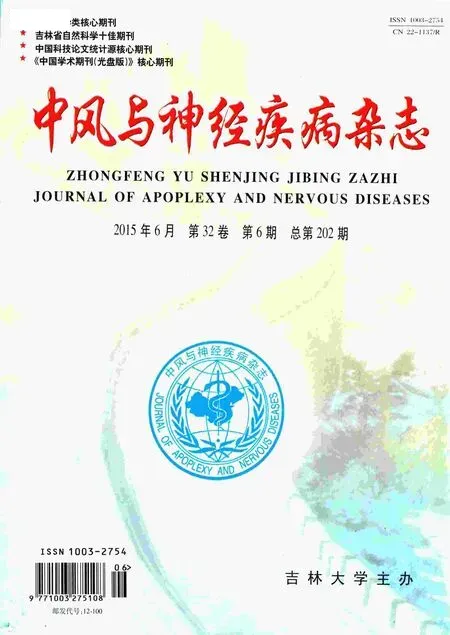神经梅毒的研究进展
张耀文,林京京,孙玉冰,韩玉亮,黄 娇,杨 薇
神经梅毒(Neurosyphilis)是指由苍白密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TP)感染所致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过去被认为是梅毒(syphilis)的晚期表现,现在已被证实可发生于梅毒的各个阶段。由于青霉素的出现,梅毒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近年来随着艾滋病的传播和同性恋人群的增多,梅毒发病率又开始上升,神经梅毒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就神经梅毒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梅毒的流行现状
梅毒是苍白密螺旋体(也称为梅毒螺旋体)感染人体引起的一种系统性、慢性的性传播疾病,可引起人体多系统多脏器的损害,产生多种多样的临床表现,导致组织破坏、功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1]。梅毒历史有数个世纪之久,首次报道见于15 世纪末的意大利[2]。目前人类是梅毒螺旋体唯一已知的自然宿主。梅毒以性传播为主,母婴传播和输血也是重要的感染途径。少数患者可经接吻、握手、哺乳或接触污染衣物、用具而感染[3]。此外,器官移植也可以感染梅毒,但比较罕见[2]。在前青霉素时代,梅毒的发病率相对较高。20世纪50 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发达国家,梅毒的发病率显著下降。在美国,梅毒的年发病率从1943 年的峰值72/10 万下降到1956 年的4/10 万,降低了18 倍。当时,无论是梅毒还是它的神经系统并发症都完全消失了,与梅毒相关的出版物也显著减少[4]。就在人们以为梅毒早已成为过去时,它又伴随艾滋病的传播和同性恋人群尤其是男同性恋的增多再次流行起来[5]。目前全球有2500 万梅毒感染者,年发病率1200 万。在过去20 y,全球众多地区的梅毒发病率都在持续上升。在美国,梅毒的感染率从2000 年开始增加,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男-男性行为感染,而且大多同时伴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在英属哥伦比亚和加拿大地区,2012 年梅毒发病率达到了近30 y 来的最高纪录[2]。在中国,梅毒的重新流行始于上个世纪80 年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报道显示,梅毒发病率由2000 年的6.43/10 万增至2013 年的32.86/10 万,年均增长13.37%。从2009 年开始至今,梅毒一直居于全国甲乙类传染病发病排序的第3 位,仅次于乙型肝炎和肺结核[6]。
2 梅毒“神经浸润”
神经梅毒是梅毒螺旋体感染所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过去它被认为是3 期梅毒才有的表现,现已被证实可发生于梅毒的各个时期[1]。实际上,梅毒螺旋体感染初期就可以累及到脑脊膜。研究证实在一期梅毒患者出现临床症状之前,就可以在其脑脊液中检测到梅毒螺旋体[7],这种情况称为“神经浸润”。通常情况下,脑脊液中的梅毒螺旋体会被机体清除,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曾经发生过“神经浸润”。但是某些特殊情况,如同时合并HIV 感染,机体无法彻底清除脑脊液中的梅毒螺旋体时,脑膜炎、听力减退、葡萄膜炎等症状会在梅毒感染后几周或几个月陆续发生[8]。2010 版的美国性传播疾病治疗指南就明确指出,神经梅毒可以发生在梅毒的任何阶段,脑脊液异常在早期梅毒患者中很常见,甚至在未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的梅毒患者中也很常见[1]。神经梅毒早期主要影响脑脊膜、脑脊液、脑和脊髓的血管,晚期主要影响脑和脊髓的实质,只有出现神经梅毒晚期的临床表现才应该诊断为3 期梅毒[8]。
3 神经梅毒的临床表现
梅毒因其复杂且不典型的临床表现被称为“杰出的模仿者”(The Great Imitator),神经梅毒表现更是如此[9]。神经梅毒的主要临床表现有神经浸润、脑膜炎、血管炎、麻痹性痴呆、脊髓痨等[8]。这些传统的临床表现对神经梅毒具有诊断价值,但是,目前神经梅毒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部分患者同时合并有HIV 感染,晚期典型的梅毒越来越罕见。神经梅毒的临床表现形式变得多种多样,更加复杂[8]。下面介绍几种非传统神经梅毒的表现形式。
3.1 帕金森综合征 患者表现为双侧不对称的静止性震颤、写字过小征、构音障碍和流涎,步态以摆臂减少、行走拖拽为特点,出现了阿罗瞳孔。经过一个疗程的青霉素治疗后,构音障碍和流涎好转,震颤的幅度和频率减小,写字也基本恢复到正常大小。其面具脸、步态拖拽和摆臂减少虽然持续存在,但是没有再进展[9]。
3.2 舞蹈症 患者为70 岁男性,全身性舞蹈症病史10 y。症状开始于右侧肢体,3 y 以后扩展到左侧。神经系统检查未见异常,也没有明显的精神症状。患者经青霉素G 治疗后其舞蹈症症状得到缓解,整个病程中未使用过任何专门治疗舞蹈症的药物。6 个月后随访,其舞蹈症症状减低到了最小程度,未遗留明显的残疾[10]。
3.3 皮质基底节变性 患者为53 岁女性,以性冷淡和焦虑起病,随后2 y 精神障碍进行性加重,频繁跌倒。检查显示表情呆板、右侧肌强直、运动迟缓、姿势不稳、肌阵挛。在青霉素G 治疗后6 个月随访,MRI 显示额顶叶皮质高信号消失,认知功能有轻度改善。3 y 后结构性失用、病觉缺失消失,帕金森的体征仍然保留,左旋多巴治疗无效[9]。见于文献报道的非传统神经梅毒的其他表现形式还有海绵窦综合征[11]、进行性核上性麻痹、肌阵挛、肌张力障碍[9]等等,不胜枚举。虽然我们之前叙述过在当今时代晚期的、实质型的神经梅毒变得罕见,但很多患者直接以实质损害起病,这一点值得关注。另一方面,这些不同于5 个传统综合征的案例只是神经梅毒千变万化的临床表现的冰山一角[9],提醒我们应在神经系统疾病的鉴别诊断中考虑神经梅毒。
4 神经梅毒的诊断
梅毒螺旋体病原体复杂、培养困难,为实验室生产螺旋体菌株设置了障碍,限制了梅毒病理生理学研究和诊断“金标准”的确定。因此,我们在现行实践中是通过临床和血清学改变来判断疗效,而不是从微生物学角度去评价,很难将梅毒复发和再感染区别开来[12]。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梅毒诊断标准,确诊神经梅毒包括:(1)处于梅毒的任何时期;(2)脑脊液VDRL 试验阳性。疑似神经梅毒包括:(1)处于梅毒的任何时期;(2)脑脊液VDRL 试验阴性;(3)脑脊液蛋白定量检测异常或白细胞数升高,并排除了其他已知的可以造成上述异常的疾病;(4)临床症状或体征与神经梅毒相关,并除外了其他引起这些临床异常的疾病[8]。
在上述标准中,VDRL 试验作为脑脊液的标准血清学试验,在排除血液污染的情况下其结果阳性可诊断为神经梅毒,但仅凭这一点来诊断神经梅毒尚有不足之处。虽然VDRL 试验具有高度的特异性,但其敏感性低,即使患者有神经梅毒,试验结果也可能是阴性的[7,13]。其他多数试验既不敏感也不特异,需要与其他试验结果和临床评估结合到一起来进行判断。因此,神经梅毒的实验室诊断通常是梅毒血清学检查阳性、脑脊液蛋白定量检测或细胞计数异常、脑脊液VDRL 试验阳性伴或不伴临床表现等多项指标的组合[8]。在HIV 感染者中,脑脊液白细胞计数通常是升高的(WBC>5/μl),提高临界值(WBC>20/μl)将有助于提高神经梅毒诊断的特异性[14]。由于VDRL 试验敏感性低,因此可以考虑行脑脊液荧光梅毒螺旋体抗体吸收试验(Fluorescent treponemal antibody absorption,FTA-ABS)进行额外评价。多项研究表明,脑脊液FTA-ABS 试验诊断神经梅毒特异性低于VDRL 试验,但敏感性很高,该试验阴性可以用来排除神经梅毒[8]。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研究发现对于神经梅毒的诊断来讲脑脊液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PR)和VDRL 试验具有同样的敏感性和特异性[8]。有人将VDRL 试验和RPR 试验做过比较,前者使用时需要临时配制、操作不便、不宜保存,且试剂缺乏、价格昂贵[15];而后者宜存放、操作简单易行、有商品化的试剂盒购买方便[16]。前者不能靠肉眼观察到凝集反应,需借助光学显微镜进行观察[15],后者在30 min 内仅靠肉眼就可以观察到试验结果[16]。基于这些优势,脑脊液RPR 试验被广泛地应用于神经梅毒的实验室诊断中,尤其是在那些无法开展VDRL 试验的医院,并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不过在我们确信脑脊液RPR 试验能够替代VDRL 试验之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8]。最近,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进行梅毒螺旋体DNA 扩增来检测病原体被认为是神经梅毒最有希望的诊断方法。目前该技术主要选取具有特异性的基因靶点合成引物和探针来检测梅毒螺旋体的基因片段,常用的有polA 基因、TPN17 基因、TPN47 基因,它们在梅毒螺旋体中相对保守、特异性好[17]。但由于青霉素类药物的广泛使用和其他原因,临床中出现了很多变异菌株,这些基因可能已经不再“保守”了。另外,该技术在不同组织来源样品中的检出率不同,目前仍停留在实验研究阶段,尚不能满足临床对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的需求[18]。因此,神经梅毒的诊断应该同时兼顾临床线索和实验室检查,因为没有单独一组实验室指标能够以最佳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充分地预测神经梅毒的存在。
5 腰穿检查的时机选择
对可能从腰穿中获益的梅毒患者的识别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在梅毒的整个病程当中,梅毒螺旋体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侵犯发生的早而频繁,并且很多梅毒患者发生神经系统侵犯以后仍是无症状的。因此,研究者们最近在试图寻求一些能够用以确证和评价神经梅毒的临床线索和生物学标记[12]。多数研究用脑脊液VDRL 试验阳性或者脑脊液白细胞计数>20/μl 来定义神经梅毒。基于这一标准,研究者们发现血清RPR 滴度≥1∶32 与神经梅毒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不论患者处于梅毒的任何时期,不论是否伴有HIV感染,也不论有无神经系统症状[8]。用这一滴度标准来判断神经梅毒的存在具有100%敏感性和40%特异性[12]。另外,如果HIV 感染者CD4 细胞计数≤350/μl,神经梅毒的风险也会增高[19]。由此,一些学者得出结论:血清RPR 滴度≥1∶32 者,尤其是CD4 细胞计数≤350 μl 的HIV 感染者需要进行腰穿[8]。一些专家推荐在同时感染HIV 和梅毒的患者中常规行腰穿检查,但对于那些没有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由于缺少支持腰穿检查能够改善临床预后的相关证据,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20]。目前多数关于腰穿对神经梅毒预后的影响的研究都是对有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行腰穿检查,仅有的一些对无症状性神经梅毒的研究也是回顾性的。并且,这些研究都未强调对无症状性患者行脑脊液检查的远期获益。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神经梅毒的诊断尚缺乏一个“金标准”[12]。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讨论梅毒患者行腰穿检查的指征时,神经梅毒的病史、出现了累及神经系统或眼科系统的症状或体征应该成为主要的关注点[19]。在无神经系统症状的情况下,脑脊液检查与临床预后的改善是否相关还缺乏证据,有待进一步研究。
6 神经梅毒的治疗
自从青霉素发明以后,它一直是治疗各阶段梅毒的首选药物,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它对梅毒螺旋体仍然有效[8]。另外,青霉素作为主要的治疗药物,它成本低,有多种衍生产品。这些都大大限制了制药公司想要投资于梅毒研究的想法[12]。然而必须重视的是,随着抗生素的滥用、耐药菌株的增多和越来越高的发病率,梅毒治疗新药的开发已经迫在眉睫。还有一点常被忽略,美国性传播疾病治疗指南指出神经梅毒的治疗应该回归到性传播疾病治疗的范畴,提出要对神经梅毒患者的性伴侣进行管理和协同治疗[1]。
7 结论和展望
神经梅毒可能仅有脑脊液的改变而无任何症状,可以发生于梅毒的任何时期。它也可以表现为无数的神经系统的、耳部的、眼部的症状,只有高度怀疑时才能确保患者不会被漏诊。任何时候不能依靠单一指标诊断神经梅毒。鉴于梅毒不断上升的发病率,尤其是神经梅毒在初级阶段可以治愈,知道神经梅毒多种多样的表现和保持对神经梅毒的高度警觉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类社会的面貌不断更新,疾病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方法手段的改进,对古老疾病的重新研究也会焕发出新的青春。
[1]Workowski KA,Berman S.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treatment guidelines,2010[J].MMWR Recomm Rep,2010,59(RR-12):1-110.
[2]Morshed MG.Current trend on syphilis diagnosis:issues and challenges[J].Adv Exp Med Biol,2014,808:51-64.
[3]Lafond RE,Lukehart SA.Biological basis for syphilis[J].Clin Microbiol Rev,2006,19(1):29-49.
[4]Berger JR.Neurosyphilis and the spinal cord:then and now[J].J Nerv Ment Dis,2011,199(12):912-913.
[5]Ghanem KG,Workowski KA.Management of adult syphilis[J].Clin Infect Dis,2011,53(Suppl 3):S110-128.
[6]龚向东,岳晓丽,滕 菲,等.2000-2013 年中国梅毒流行特征与趋势分析[J].中华皮肤科杂志,2014,47(5):310-315.
[7]Lukehart SA,Hook EW,Baker-Zander SA,et al.Invasion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by Treponema pallidum:implications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J].Ann Intern Med,1988,109(11):855-862.
[8]Marra CM.Update on neurosyphilis[J].Curr Infect Dis Rep,2009,11(2):127-134.
[9]Shah BB,Lang AE.Acquired neurosyphilis presenting as movement disorders[J].Mov Disord,2012,27(6):690-695.
[10]Ozben S,Erol C,Ozer F,et al.Chorea as the presenting feature of neurosyphilis[J].Neurol India,2009,57(3):347-349.
[11]Noel CB,Moeketsi K,Kies B.Cavernous sinus syndrome,an atypical presentation of tertiary syphilis: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Clin Neurol Neurosurg,2011,113(1):65-67.
[12]Farhi D,Dupin N.Origins of syphilis and management in the immunocompetent patient:facts and controversies[J].Clin Dermatol,2010,28(5):533-538.
[13]Timmermans M,Carr J.Neurosyphilis in the modern era[J].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2004,75(12):1727-1730.
[14]Marra CM,Maxwell CL,Collier AC,et al.Interpreting cerebrospinal fluid pleocytosis in HIV in the era of potent antiretroviral therapy[J].BMC Infect Dis,2007,7:37.
[15]Marra CM,Tantalo LC,Maxwell CL,et al.The rapid plasma reagin test cannot replace the venereal disease research laboratory test for neurosyphilis diagnosis[J].Sex Transm Dis,2012,39(6):453-457.
[16]Castro R,Prieto ES,da LMPF.Nontreponemal tests in the diagnosis of neurosyphilis:an evaluation of the Venereal Disease Research Laboratory(VDRL)and the Rapid Plasma Reagin(RPR)tests[J].J Clin Lab Anal,2008,22(4):257-261.
[17]Gayet-Ageron A,Ninet B,Toutous-Trellu L,et al.Assessment of a real-time PCR test to diagnose syphilis from diverse biological samples[J].Sex Transm Infect,2009,85(4):264-269.
[18]吴静宜,童曼莉,李淑莲.神经梅毒的实验诊断研究进展[J].41-43+46.
[19]Janier M,Hegyi V,Dupin N,et al.2014 European guideline on the management of syphilis[J].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2014,28(12):1581-1593.
[20]Libois A,De Wit S,Poll B,et al.HIV and syphilis:when to perform a lumbar puncture[J].Sex Transm Dis,2007,34(3):141-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