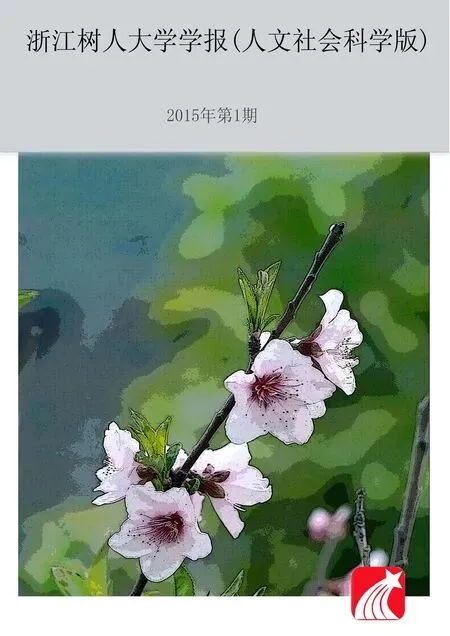从农村公社到现代国家的社会形态演进分析
黄 冠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365105)
从农村公社到现代国家的社会形态演进分析
黄 冠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365105)
以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证明了农村公社作为相对原始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同现代国家存在的根本性差别。研究明确生产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论证村舍生产方式同集体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通过比较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论证个人主义同现代西方国家的天然契合性,同时也指明了地区环境对生产组织形态和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影响。
村社;现代国家;集体主义;个人主义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再次成为学界的热门论题,在新的国家经济发展态势和国际形势下,在城镇化全面铺开的当下,中国政府是否应该作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时刻,从理论上和历史上理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之间规律性的发展变革关系,就兼具了理论、实际和实效上的必要性。要理清现代国家的变革规律,就不得不从诞生现代国家的农村公社讲起。
一、村社特征及成因
原始社会中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公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引发了氏族间的融合,而这种融合最终破坏了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血缘的纯洁,在此情况下,新的以生产组合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逐渐成形,农村公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作为研究的起点,农村公社(村社)这一概念工具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加以详细解说。
(一)村社的概念
农村公社,又称“农民公社”“毗邻公社”“地域公社”“农民村社”,简称“村社”。村社广义为农业公社、游牧公社与狩猎公社等不同类型公社的总称;狭义专指农业公社。它是原始社会解体时期形成的、以地域性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二重性为特征的社会组织。①甄修钰、张新丽:《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的动机和方法论——兼论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困境》,《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43-155页。世界各地普遍经历了农村公社发展阶段。虽然早期农村公社明显地保留着起源于家庭公社的痕迹,但是阶级社会的某些因素,互相对立的阶级集团,都是在农村公社阶段逐步形成的。农村公社由父系家庭公社发展而来。由于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冶金业,开始了金属工具的使用。新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公社成员间的流动,同时有了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所组成的杂居村落,于是出现了基于地域联系的农村公社,又进一步巩固了村社内部的关系,并扩大了与其他村社的联系。村社的发展经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解体三个阶段。*付世明:《论帝俄时期村社的发展变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25-129页。虽然农村公社生产资料所有制二重性曾为公社经济的发展赋予强大的生命力,但到了农村公社晚期,这种二重性就成为公社解体的决定因素。*甄修钰、张新丽:《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的动机和方法论——兼论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困境》,《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43-155页。在晚期的公社里,耕地虽按传统实行定期重新分配,但土地所有权已被奴隶主或封建领主篡夺,社员以承担各种贡赋或劳役为代价,耕种公社的“份地”。*甄修钰、张新丽:《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的动机和方法论——兼论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困境》,《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43-155页。后来,农村公社从内容到形式都逐步消亡。
(二)村社的实质
村社是适应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人类个体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以地域为基础联系起来的,实行基本生产资料(如农田和大型水利设施)公有,小型生产资料私有,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集体劳作的人群集合。*陈其人:《农村公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的论述》,《复旦学报》1999年第6期,第52-59页。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以“均分”为特征的土地公有制。土地由全体成员共有,并将其使用权平均分给全体成员,同时对各块土地的耕种权力进行轮替。第二,成员集体劳作。第三,社员个人在向村社缴纳一定量的产品后,对在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上,所收获的产品拥有所有权。
在当今社会,以我国为例,许多地区依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而其分配原则也和传统村社主义一样,“社员个人在向公社缴纳一定量的产品后,对在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上,所收获的产品拥有所有权。”那么现代农村和传统村舍是不是同样的社会存在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现代农村中,农村的全体成员,不会再像曾经的村社社员一样,进行义务性的集体劳作。而这种义务性的集体劳作正是产生于村社主义息息相关的集体主义的土壤,如果不能产生和培养集体主义,那村社就不再是村社。因此是否采取义务性的集体劳作作为生产组织形式,就成为区分现代农村和传统村社的关键。至于为什么集体主义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将在下文中予以论述。
二、村社主义与集体主义专制
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原理,特定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必然衍生出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亚洲村社是以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和大规模农田水利为基础,以集体劳作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涂成林:《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21-37页。这种生产方式衍生出的与其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就必然是集体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从村社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必然,一方面是由于大规模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非个人可以独立完成,而这些水利灌溉设施的使用价值,也非个人可消耗穷尽,就是说,这种水利灌溉设施从一开始就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消费使得非排他性)。建造时工程的大规模以及消费时的公用性质,客观上决定了这种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只能通过集体劳动来建造;另一方面,由于大规模水利灌溉设施的使用,使得土地的可耕种面积大大超出了个体劳动者的劳作范围,这就形成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可耕地面积同相对缩小的劳动者个体劳动能力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关系,作为个体存在的劳动者不得不采取与其他劳动者合作的方式,即共同劳作,以使得潜在的可耕土地成为实在的收获。
这两方面的生产特征,客观上就决定了亚细亚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同时,在水利设施共用的前提下,在集体劳作的过程中,寻找可以用来对生产收获进行公平分配的标准也越来越困难。生产所得的模糊,进而导致了土地归属上的模糊,最终在经过不断的重复博弈后,出现了以“平均”为表现形式的土地公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特点是,在人群集体占有某片土地后,将这片土地尽可能均等地分给其群体成员,共用“无主”(无主之物即为公有)的水利设施,集体劳作,一个人所分得的土地上的产品为劳动所得。土地公有制主要包括:国家土地公有制、村社土地公有制和家族土地公有制,至于其具体的划分和运作,前面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述。与这种“均分”土地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产生了集体主义和亚细亚专制政体两个上层建筑。
(一)集体主义的社会演进
在土地公有制产生的同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集体主义也产生了。经过长期的集体协作劳动的锻炼,在土地公有制产生后,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以集体利益,即大多数人利益为优先考量的意识形态,成为亚细亚地区的主流价值取向。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一切行动以集体的存活为优先考量,集体中绝大多数成员的生存权利受到保障,在确保集体存在的前提下,个人可以追求和保有其个人收益,但一旦取得集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则可以不受任何谴责的,剥夺某个或某些成员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讲,集体主义的这种特征可以概括为多数人的暴政。
与个人主义不同,在这种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统治下,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就是人力资源。因为在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个人与个人之间可以通过占有不同的资源和彼此间的交换与博弈,实现和保护其个人利益。但是在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引导下,个人只能通过集体对其身份的认同,才有可能获得和保有其个人利益,就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集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地位是以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实际上就是社会成员,即人力资源,所以在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人力资源成为首要资源,占有人力资源越多的人,也同样可以占有包括物质和精神资源在内的尽可能多的各种其他资源。这种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也可以理解为对人力资源的迷信,正如“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对人力资源的迷信,又必然产生与其相适应的统治方式——人治,而人治的下一步,只能是专制。
(二)亚细亚专制
以“均分”为特色的国家土地公有制,客观上要求一个集权的强大政府,以实现和维持土地均分的利益格局。*涂成林:《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21-37页。这样在生产力层面上就产生了对专制政权的需要。在社会意识层面,由于受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统治,人力资源相对其他资源的优势地位,客观上都在呼唤着专制政权的诞生。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作为社会构架的各种法律和道德标准,实际上又是由人治定并取得社会成员认同的共同意识。所以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社会中,那个最受认同的社会成员,其实就占有了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源。这种对人力资源的占有,就使得其在这一社会中,可以合理合法地为所欲为。而可以为所欲为的领导者,也正是人治的首要标志。当然此时这名占有最多人力资源的社会成员还不能被称为统治者,虽然他获得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并未取得任何的物质保障,其任意妄为的权利,也要在取得社会成员的首肯后才能够行使。这就使得每次以集体名义采取的行动,都要通过人与人之间不断的博弈,才可能成行。早期的希腊雅典政体,就具有这种典型的人治特征。由于社会成员对人力资源的占有,并未以确定的形式被固定下来,形成稳定的社会共识,所以这个时期虽然有各种各样通过取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认同而任意妄为的人,但是他们充其量都还只能被称为煽动社会成员采取其倡导的行动的领导者,而不是一个已经占有了社会权利的统治者。是否形成了稳定的、对人力资源占有者身份的认同,正是人治和专制的根本区别。
在人治情况下,领导者可以任意妄为,但这种可以任意妄为的权利,由于缺乏确定下来的社会认同,因而没有保障。那么这种没有保障的权利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呢?当然是拜战争所赐。战争和生产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战争是突发性事件,因而不像生产劳作,有无数的机会可以“熟能生巧”。战争更多的是一时的领悟和指挥的天赋,无论这种战场上的指挥能力是来自天赋还是平日的积累,它都不似生产活动的组织能力那般容易模仿,一个沙场老兵未必能够指挥军队迎敌,但是一个工厂的老工人,却绝对可以组织有效的生产。由于战争的这种特性,使得人类社会中具有军事活动指挥者身份的人,基本上是最早稳定在少数人身上。而这种稳定的身份认同,在经过多次的征战后,会从稳定的认同,进化成确定的认可,似乎军队的领袖只能是这些人,或者这些人的族人。就如土地上收获分配的模糊,引发了土地所有权的模糊一样,对军事领袖身份的确定认可,引发了其对军队所有权的认可。或者说这是某一种形式的对象性关系,即军队和领袖,离开了彼此,则彼此都不存在。这样,本来由社会公有的军队,渐渐变成了军事将领的私人物品。而作为人类社会中组织化程度最高,行动效率最好的人力资源集合——军队的所有者,军事将领就成了人治社会中最早的、稳定下来的领导者,或者应该改口称此时的他们为统治者。正如人类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人类社会最早的统治者,都是军事将领,当军事将领对军队的占有确定下来,人治社会也就进入了专制社会。
总之,在村社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下,必然产生与之孪生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则必然导致对人力资源的迷信,对人力资源的迷信则导致人治的产生,人治之后,进一步出现与之相呼应的统治形式——专制。
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前面已经论述了村社主义和集体主义及专制的关系,下面将概括叙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总体和细节上的区别。同时,在解述之前必须说明,所谓集体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统治地位,并非指社会成员所实际采用的价值取向,而是指在一个社会集团中,被主流舆论所认同的和宣扬的,被作为“正确”而加以鼓吹的价值衡量标准。就好像明明是要牟取私利,却一定要打着民族大义的旗号,如同民族大义是可以把卑劣伪装成正义的煽动口号,集体主义也是一般。
(一)集体主义
顾名思义是以人群的集合为考量起点的价值评判标准,其应用基于一个重要假设,即集体利益是可以明确限定的。但什么是集体利益,又由谁来界定集体利益?如果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出现了冲突,作为集体的成员应该怎样抉择?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人把它鉴定为组成集体的各个成员的个人利益中的共同部分;对于第二个问题,它的答案至今还在争论之中,但现实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仍然是精英政治在起作用。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倒是有了确定的答案——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二)个人主义
以个人收益为衡量基准的价值评判标准,一种以个人为中心完全主观的价值标准,其基于的假设是:个人是最了解其自身需要的人。*方春龙:《经济学发展脉络及趋势——个人效用与社会效益的新视角分析》,《宜春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第33-36页。那么同样的问题,什么是个人利益,由谁来界定个人利益,如果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那么应该如何取舍?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非常明确的,个人认为对其有效用的事物,都可界定为其个人利益。对于第二个问题,在启蒙运动后,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盛行,对个人选择权利(包括选择犯错的权利)的尊重,已经成为当今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所以无可置疑的,个人是其个人利益的确定主体。至于第三个问题,从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代历史中,比如帝国大厦边的“钉子户”、德国皇宫边的破旧豆腐坊,不难看出,只要是个人通过正当手段获取的利益,即使这种个人利益站到了集体利益的对立面,它也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
(三)两者对生产运作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影响
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各自的特性相适应,计划和市场两种具有不同特性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就与其相伴而生。集体主义本来产生于村社的集体劳作,作为集体劳作的一个重要特征,计划无处不在,从最初对公有土地的“均分”,到生产的组织,以致最后产品分配,无处不渗透着以集体名义而推行的计划。这些计划以集体利益为名,名义上由集体制定,以人力资源为基础,对整个集体中所有的成员都具有强制力。集体的成员只能服从计划的安排,任何“自作主张”的行动都将受到集体的惩罚(比如云贵地区曾经出现的强制种植某种烟草,对不服从者的田地进行破坏的现象)。在这种以计划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方式下,任何的利益都只有在得到其他成员认同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保存,任何不被多数人认同的所得,都将遭到以集体为名的剥夺,实际上个人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
由于这种情况的盛行,个人必然将其主要精力用于维持其在集体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生产经营。为了避免集体其他成员对自己的嫉恨以及成员之间的过度竞争,集体成员会自觉地将自己的产出维持在一个相对中庸的水平上,既不比别人多,惹人嫉妒;也不比别人少,遭人耻笑。而如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缺乏竞争,生产力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后,长期停滞不前。
专制主义是集体主义必然出现的统治方式,所以推行于集体的计划,实际上是由少数统治者及其附庸制定的,而这就必然造成另一个现象,即由全体社会成员创造的社会财富,以集体的名义,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由其支配使用,集体名下的财富会不断积累,但集体成员无法进入富裕社会。甚至,在长期如此后,就会出现和军队归属权同样的变化,即集体名下的财富,长期由少数人支配,最终变成只有这些少数人对财富拥有使用权,进一步发展,使用权变成了所有权。
由上可知,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其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一切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现实中这种多数人的意志,常常被少数人窃取或左右,但仍然是以多数人同意的形式出现),缺乏相对客观和稳定的评判标准。而与集体主义相对,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其主要的优势就在于社会成员通过长期的重复博弈后,形成了相对稳定,甚至不容侵犯的评价原则。在个人主义条件下,个人以其掌握的全部资源为其自身牟利。为了避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极端的对抗出现,而损害自身利益,个人以其掌握的资源为基础,通过不断的重复博弈,以满足他人需要的方式来获取个人利益。当这种重复的博弈以确定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后,市场就应运而生了。
市场作为一种与计划相区别的生产组织和产品分配的方式,其有效性是以个人为牟取私利而进行生产劳作,以及个人无法满足其全部需要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市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出现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后,才能成行。同时作为长期重复博弈的结果,形成了一系列对个人利益进行保障的措施,任何通过非市场方式对他人利益的剥夺,都为社会所不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作为重复博弈后,彼此妥协结果的法律,其最基本的目标就是保障个人权益不受侵害。作为人与人之间博弈制度化的集中表现——市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场各参与者基本权利(如财产的保障权)平等。第二,未经个人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对其合法所得进行剥夺。第三,个人自主决定其行动,并对其行为负责。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强制无过错人员,对其采取任何特定的行动。第四,个人的所得来自于其对固有资源的经营,任何合法所得,都必然受到保护。
与市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相适应,其必然出现的统治形式,就是民主制政体。其实现代民主制政体,就是市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在国家生活领域的扩张。如果说在经济市场中,人力物力各种资源可以公平竞争,那么在政治市场中,人力资源依旧是决定性的关键资源。不同的政党,或同一政党中的不同派系,通过定期选举这种“竞价”的政治制度,通过对民众的利益承诺,换取尽可能多的选票,从而获得一定时期内的对行政权的使用权。但是与专制政体不同的是,这种对行政权的使用权,由于业已制定的作为社会成员博弈结果而确定下来的、制度化的定期选举,而使得这种使用权无法发展成所有权。无论是如何获得民众认同的领导者,都无法再次把这种认同固定化(如委内瑞拉的查维斯修宪事件)。究其原因,这依旧是市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带来的结果,由于市场中的个人,都以其个人利益为优先考量,虽然也存在这种“利他源于利己”*赵永宏、王冬放:《论“国富论”中的经济发展理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102-106页。的现象,但是个人在选择某些人来行使公共权力时,优先考量的依旧是个人利益,这就造成了“任何个人利益中的共同部分,一旦以公共利益的形式确定下来,就马上脱离个人利益,并与个人利益对立”这种现象的出现。即是说,公共利益是民选政府所要谋求的利益,个人不但没有义务为此牺牲其个人利益,而且其为了保护其个人利益而采取的任何合法手段都是受到鼓励和认同的,正是这种政府与个人间的博弈,使得政府无法把公共权力的使用权所有权化,也正是这种博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以集体名义出现的对个人权益的剥夺。
四、从村社到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是指以市场为生产组织基础,以个人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以民主和分权制衡为政权组织原则的,个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相互制衡、相互推进的国家形式。按照马克思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原理,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制度和发展模式,也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出现的结果。如前所述,最初在村社主义下产生的是与其相适应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采用的是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与此相适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是专制主义的政体。那么集体主义是如何转向个人主义、计划是如何被市场所取代、专制主义又是如何发展到民主制?
(一)前现代社会的特征
在村社主义盛行的封建社会,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巩固和保护自己统治权,为此需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力不受内部臣民的挑战;第二,保证自己所统治群体的存活;第三,保证自己的统治不受来自外部的威胁。对于前两件事情,只要这个专制统治者不是孤独昏庸,把臣民逼到求生不得的绝境,作为被统治者的臣民是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反抗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集体行动的问题难以解决;另一方面,统治者掌握着社会中组织最优良的人力资源——暴力机关。正如盛邦和教授的“人——土地”原理所显示的那样,只有当普通百姓“活不下去”时,才会出现改朝换代。*盛邦和、井上聪:《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5页。由此不难看出,专制统治者在主观上是没有改变业已存在的村社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而对于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专制统治者不但不会改变,更会大肆宣扬,因为“朕即国家”。
既然内因上村社主义的封建国家内部,没有产生市场的迫切需要,更不要说用个人主义来取代集体主义商品经济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补充,而作为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就更加不可能出现了。虽然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当时低效的运输和通讯水平有分不开的关系,但是维持国家稳定的政治考量则是更主要的原因,这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本应停滞的村社主义下的集体主义盛行的封建专制国家,转向市场和个人主义的民主制现代国家呢?
(二)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特征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从现代国家最先产生的欧洲说起。中世纪的欧洲,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林立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之间兼并战争不断,间或伴有外族入侵。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统一整个欧洲,这样在欧洲大陆就形成了一个持续的军事竞争系统。各个王国之间为了占有更多的领土、获取更多的财富而彼此征战。甚至在一国内部,由于通讯和交通技术低下,虽然国王是国家中最大的暴力资源所有者,可以在短时间内集合数量庞大的军队进行征战,但受制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根本无法长期维持数量庞大的军队,所以实际上国王能够有效控制的领土范围十分有限,各地的领主贵族之间也常常发生战争。
这种混乱的情况就给商人这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群体生存的空间,他们通过往来于各个相互对立的王室贵族之间,提供这些王室贵族领地内无法生产或稀缺的商品,积累了财富,又使他们成为各王室贵族不可或缺的“朋友”。混乱即给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空间,但也限制了其发展的可能。割据的政权,造成了分裂的市场,不同的关税标准,使得商品经济发展被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对商人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各国国王,在集体主义的专制国家中,国王作为国家的代表,可以合理合法地剥夺商人的财富。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通过这种对本国商人财产的剥夺,短期内聚集起巨大的国家财富,崛起成为称霸一时的列强。但是这种掠夺性的发展无法长期维持,所以依靠掠夺发迹的列强也通常迅速衰亡。从某种程度来说,所谓的“霸权衰亡的定律”*张东亮:《论霸权》,《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第32-36页。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而与专制国家相反,在商人聚集的所谓城市国家中,虽然商品经济发达,社会成员财富不断增加,但是作为整体的国家积贫积弱,从不曾崛起成为欧洲强国,只能作为一个繁华的“配角”,最终也逃不过被吞并的命运。既然集体主义的专制国家和个人主义的城市都不能解决社会成员和国家的长期发展问题,那到底出路在哪里?最初是国王选择了“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以保护集体利益为第一原则,兼顾个人利益。如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在欧洲持续的军事竞争系统中崛起并长期称霸,几乎统一欧洲大陆,但随着国家的强大,国王专制权力膨胀,集体主义再次吞没了个人主义,法兰西帝国随着路易十四的去世,也在两代后的路易十六时期灭亡。
通过不断的重复博弈,最终作为国家集体意志代表的国王们终于意识到,集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都不能真正保住他们的政权,而当保住政权成为第一要务时,专制就成了不再必需的东西,最终作为武力所有者的国王选择与资本的所有者商人媾和,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开始逐渐成为主流价值评判标准。这种价值评价标准的根本特征是,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任何集体行动,都应当以保障其成员的个人利益为第一前提,任何损害其成员个人合法利益的集体行为,都必须马上停止,并对该成员利益进行赔偿。虽然其间作为集体主义的另外两个支持者——贵族和教会,都对这种新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是面对财富和武力的联盟,他们也和集体主义及孕育它的村社主义一样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至此,现代国家诞生。
五、结论:从比较的视点看现代国家诞生
依据北京大学朱天彪(2006)*朱天彪:《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93页。的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将欧洲的情况同其他地区进行如下的比较。
(一)古印度洋与东南亚群岛地区
这个地区与早期欧洲地区相似,也有繁荣发达的互补性贸易,而且由于水路交通发达,所以大多是远程贸易。但是与中世纪欧洲不同,当时在这个地区虽然存在着各类政治实体,由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保护国——古代中国,所以它们彼此之间并未形成一个持续的军事竞争系统,因此其本国的统治者,就缺乏转变村社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动力。如前所述,作为村社主义的最大受益者,这些王公贵族根本没有主观意愿去改变现状,甚至于其国内的普通民众,在既得利益集团的煽动下,早已产生了对集体主义的迷信,会主动反对任何动摇集体主义专制的改革措施。
(二)古印度地区
古印度地区也和欧洲相似,也是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历史上只出现过三次短暂的统一,但是,古印度地区也未出现欧洲那种持续的军事竞争局面。一方面,由于古印度地区高原面积大,可航行河流少,各地间联系少,不利于政治实体间保持长期持续的军事互动;另一方面,婆罗门教以种姓制控制社会,众所周知,在村社主义中产生的宗教是集体主义专制最为盛行的领域,多的是“党同伐异”。而种姓制度又使这种集体主义专制固定化,把整个社会都囊括入集体主义的宗教价值体系,结果形成了价值衡量标准上的“超稳定结构”,所以古印度地区虽然各国政治上分裂,但是在价值衡量标准,甚至政权组织方面高度统一,都是集体主义的种姓制专制。在这种国际和国内情况下,古印度国家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能是停滞甚至逐渐倒退,而现代国家也不可能产生。
(三)古伊斯兰地区
与古印度地区相似,伊斯兰教对政治也有很强的控制力,对政府并不重视。但不一样的是,阿拉伯人把宗教和军事力量结合起来,积极对外扩张,四处征战。与古印度洋及东南亚地区相似,古伊斯兰地区贸易也比较繁荣。那么为什么古伊斯兰地区没有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呢?这是由于,一方面,古伊斯兰地区的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武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外的部落中,而每逢战乱,城市中伊斯兰教的忠实者,就会通过引入城外的部落,来实现政权更迭,霍尔和艾肯贝里把这种国家叫做“周期性”国家,②朱天彪:《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93页。国家的统治者没有机会和被统治者进行长期的重复博弈,以改变其集体主义的专制统治;更重要的原因是,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完全控制了古伊斯兰地区居民的精神生活,和古印度地区相似,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被以宗教的形式绝对固定了下来,同时由于该地区主要的军事活动是“对外”的侵略,而不是“对内”的争夺,所以实现向现代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任务。
(四)古代中国
与上述相比,古代中国也曾经经济贸易繁荣,同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也不深刻,而且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也受到过不少外族的侵略,那为什么也没转向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呢?这是因为古代中国长期“大一统”,没有形成持续的军事竞争系统,同时古代中国幅员辽阔,比整个欧洲还要大,因此统治者对外族入侵的威胁并不敏感,必要时甚至可以暨天险而偏安一隅,对政权的危机感十分缺乏。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会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实现国富民强,反而会通过宣传集体主义的“爱国”思想,愚民教化,从而达到国富民弱,以便于统治。
总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神州大地就形成了持续的军事竞争系统,结果这个时期是古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时期。同时,村社主义的井田制被废除,铁器取代青铜器,实现生产工具的飞跃,生产力大发展,最后终结这个时代的更是一个因商人(吕不韦)而强盛的国家——秦。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如果把世界历史分为传统和现代两部分,那么传统就是属于村社的、集体主义的、专制的;而现代就是属于市场的(发达的商品经济)、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民主的。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外部威胁存在,停滞的村社主义在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统治下就会一直停止下去,商品经济不可能发展,现代国家也不可能出现。
[1] [美]卡尔·A·魏.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 [德]恩格斯,刘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导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3]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 盛邦和,井上聪.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5]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陈汉轮)
Analysis on the Social Evolution fromVillage Communes to Western Modern State
HUANG Guan
(TanKahKeeCollegeofXiamenUniversity,Zhangzhou,Fujian, 363105,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Western sta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Marxist theory as the guidance to prove that rural communes as primitive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hav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to modern stat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ideology, and demonstrates the necessary connections between rural production and collectivism. By comparison between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t proves the natural fit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Western modern states. It also indicate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local environment on the changes of social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al forms.
village commune; modern state; collectivism; individualism
2014-11-10
黄冠,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保障。
10.3969/j.issn.1671-2714.2015.01.012
——以《文化偏至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