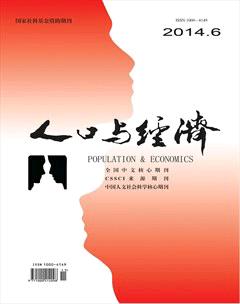中国人口红利真的结束了吗?
原新+刘厚莲
摘要:文章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辨析了两种对人口红利的认识,并从劳动力资源变化判断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性。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12年达到峰值9.4亿,直到21世纪40年代中期还保持在8亿以上,21世纪30年代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保持在60%以上,劳动年龄人口缓慢老化,劳动力资源的人力资本积累不断增加。由此判断,目前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正由聚集转向减少,并逐渐转入收获结构性人口红利阶段。但是未来收获人口红利的难度加大,将更多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化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制度改革。
关键词: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035-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4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Really Ending in China?
YUAN Xin, LIU Houl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ai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is two kind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based on literature, then judge the existen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by the trend of labor resource. The results show: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China reached the peak of 940 millions in 2012, and will keep above 800 millions until the mid 2040s, and the percent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will hold above 60 before 2030s.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s ageing, and the human capital of it gradually increases. Thus, Chinas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turning from agglomeration to reducing, and we gradually gain the structural demographic dividend. However, i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o gai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which depends on human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Keywords:demographic dividend; workingage population; human capital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的人口转变。人口死亡率从20‰下降到1970 年的7.6‰,之后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从1970年的5.81快速下降至1992年的2.05,2000年为1.22,2010年为1.18
2000年和2010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尽管许多研究一致认为近年总和生育率存在低估,但是他们所估计的总和生育率(1.5~1.6)仍远低于更替水平[1~5]。这标志着中国已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发展阶段。死亡率和生育率相继下降,并稳定在较低水平,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这促使许多学者由关注人口规模(人口增速)对经济的影响逐渐转向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被称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概念从提出至今历时十余年,然而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存在性的判断见解不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于2015年前后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人口抚养比转为上升,人口红利结束;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随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而进入减少的阶段,并将于2030年左右结束。本文将在梳理“人口红利”概念演进的基础上,针对两种不同的人口红利认识观展开分析,并从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与存量、比重与结构和劳动力资源的素质几个方面,综合判断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性。
一、“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等东亚国家开始进入人口转变阶段。与此同时,对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开始摆脱只关注人口规模(人口增速)的局限,进而转向关注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和人口素质等各类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迅速增长,创造了“东亚奇迹”。布鲁姆(Bloom)等人研究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并将其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Gift);他们通过增长核算法和计量实证方法测算发现,东亚经济奇迹约1/3是由人口红利所贡献的,如果将东亚奇迹定义为超过潜在经济增长部分,那么人口红利的贡献达到50%[6]。人口红利只是潜在的经济增长优势,梅森(Mason)认为正是东亚各国良好的政策和制度,如有效的劳动力市场、高储蓄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才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源泉[7]。布鲁姆和坎宁(Canning)等人论述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实现的机制和制度保障,通过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储蓄和人力资本三个途径来提高经济产出,并且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健康、教育、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制度保障[8],这是实现“人口红利”的逻辑架构。
梅森等人认为基于人口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陷,并提出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框架,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转化为标准消费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转化为标准生产人口,来测算人口红利规模,经测算,东亚奇迹约有1/4为人口红利所贡献;其研究的创新还在于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认为为预期进入老年而进行的储蓄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9]。对比两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大于总人口增速而出现的潜在经济增长条件,侧重于人口指标的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是由储蓄、人力资本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源泉,它可以是持续的动力,侧重于经济指标的分析。若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积累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将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另外,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结束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生并不一定存在先后顺序关系,两者可能存在时间上的交叠,而且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依赖于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建立的良好制度。
随后,国外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上,主要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储蓄、妇女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等。布鲁姆和坎宁的研究发现,爱尔兰主要依赖于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实现人口红利,而中国台湾的人口红利则主要依赖于高储蓄率[10]。罗纳德(Ronald)等人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依赖于储蓄,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受公共政策和制度所影响[11]。布鲁姆和坎宁等人利用1960~2000年9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生育率下降对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每当妇女少生育一个小孩,将会增加两年的劳动参与时间,这有利于提高家庭收入[12]。阿什拉夫(Quamrul H. Ashraf)等人分析了生育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生育与经济增长存在内生性,将生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马尔萨斯效应、索罗效应和人口年龄结构效应等,而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又可细分为储蓄、小孩照看与质量、保斯珀效应(Boserup Effect)
保斯珀效应(Boserup Effect)是指人口增长而形成的集聚效应和创新效应。等,并最终测算出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对尼日利亚未来15年经济发展的贡献高达70%[13]。布鲁姆和坎宁等人利用DHS调查数据建立微观面板模型,考察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人口红利实现基础,即死亡率下降、家庭的生育数量减少、抚养比下降、更高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妇女参与劳动时间增加,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家庭收入[14]。
国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始于21世纪之初,而且对人口红利的讨论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升温。在人口红利的概念认识方面,很多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随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而存在的[15~20];也有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这一人口条件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21~28]。在实证研究中,普遍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是衡量人口红利较好的代理变量。王丰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修正得到有效消费人口和有效生产人口,把两者比值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29]。
学者们基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抚养比变化趋势,对目前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性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前者认为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至2015年前后;而后者则认为人口红利开始于1990年左右,并将持续至2030年左右。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的各类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如较低的12.1%[30]、15%[31],较高的27.23%[32]、26.8%[33]。对于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孟令国等人实证考察了由人力资本、储蓄等形成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将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与增长方式的转变[34]。
二、对于两种“人口红利”认识的辨析
上述两种人口红利的认识分别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和人口学的视角。
索罗模型(Solow Model)研究经济增长时没有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其假定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无差异。人口红利概念基于人口转变理论,抛弃了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无差异的假设,通过增长核算法发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大于总人口增速时所带来的额外增长源泉。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时间差带来的人口结果是少儿人口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即经济发展处于人口红利期。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上升转为下降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小于总人口增速,人口红利消失。这种对人口红利认识的形成主要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增长核算理论。
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轻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从微观层面而言,家庭拥有更少的小孩和老年人,将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从宏观层面而言,整个社会拥有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越少,即人口抚养负担越小,也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当人口红利期处于人口抚养比较轻的阶段时(如低于50%),它包括小于一定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与上升阶段。
经济学视角与人口学视角的人口红利认识尽管都强调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差异在于前者认为人口红利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增加、抚养负担持续下降的阶段,后者认为人口红利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负担较轻的阶段。显然,两者所描述的人口红利期既有重叠,也有相异,且前者所认为的人口红利先出现先结束,后者认为的人口红利后出现后结束。
对人口红利认识的差异,导致国内学者对中国人口红利存在性的判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口红利就出现了,目前随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而结束;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红利出现的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并在2030年左右消失。
本文抛开两种认识的差异,考察2012年中国各个省份总人口抚养比变化情况(详见图1)。2012年17个省份总人口抚养比都介于30~40(15~64岁人口=100,下同)之间,8个省份低于30,6个省份高于40,其中12个省份的总人口抚养比处于下降的态势。目前的总人口抚养比现状说明,大部分省份的人口抚养负担较轻,总人口抚养比变化有增有减,并且减少的省份超过1/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有11个西部省区GDP增速超过10%,其中贵州省最高,达到12.7%
数据来源:中西部红利:多省市GDP增速超10%.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314/11884205_0.shtml。为此,不管从哪一种对人口红利的认识出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衡量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当然,人口红利存在性的大趋势是由集聚转为减少。
图12012年中国各省份总抚养比水平值与变化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2、2013)。
注:变化值根据2013年和2012年数据相减而得。
无论是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人口学角度,人口红利的核心都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只要劳动力供给充足,能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它还是属于较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2001~2011年平均增速为10.4%,2012年、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都为7.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02-24。。这既有我国主动调整结构的内因,也有国际经济周期的外因。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外需由于欧美经济走低乏力,投资由于上一轮的刺激作用接近尾声而减缓步伐,因此,经济增速转为中高速也属正常。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数据,2014~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达7.4%以上数据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cp_prop。这足以说明在未来这段时间中国劳动力供给仍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为进一步说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下面对2050年之前的劳动年龄人口存量与增量、比重与结构以及劳动力资源素质进行细致分析。
三、2050年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分析
1.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与增量分析
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与增量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红利期存在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规模开始下降,未来是否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决定了人口红利的存续性。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了三次生育高峰,分别在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早期至70年代中期、80年代(详见图2)。生育高峰期人口促成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快速增加,这同时影响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和增量的变化。
从图2可见,在劳动年龄人口存量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增加。
图21950~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变化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R].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2013。其中,2013年以后的数据取自中方案预测数据。
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规模接近6亿,1998年超过8亿,2005年超过了9亿,2012年达到峰值9.4亿,从2013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缓慢减少。图2显示,根据2013年世界人口预测报告,21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继续保持在9亿以上,21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保持在8亿以上,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仍大于7亿。从时间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在9亿以上的情况至少还要持续13年,劳动力资源供给保持在8亿以上的情况还要维持30年。另外,单独二孩生育调整政策于2014年在全国各地全面实施,这在2030年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部分劳动力,减缓劳动力人口的下降速度。同时,未来还将逐步延迟退休年龄,这也将释放一部分人力资本积累较多的低龄老年劳动力(如科研行业、教育行业、医疗卫生行业等的劳动力)。因此,从人口角度来看,劳动力资源规模的存量依然庞大。
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量方面,2013年之前,中国人口增量一直保持为正增长,其中有两个阶段处于较大规模的增量,即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和21世纪的头五年;2013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量转为负增长,但是减少速度缓慢,21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年均减少不到500万,21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期年均减少不到700万。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由正转为负,只能判断人口红利正进入由聚集开始趋向减少的阶段,但并不能否定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的存量依然存在的事实,即由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主导的人口红利将依然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经济发展城乡差异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东部发达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正在逐渐削弱,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二元经济特征依然显著。对“民工荒”、工资上涨等现象直接的判断是刘易斯拐点迹象显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出现普遍短缺。目前所谓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35],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因此,若简单以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开始变为负值来判断二元经济体的人口红利结束,会存在较大的偏差。尽管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处于负增长的态势,但是未来中国劳动力资源规模依然庞大,劳动力总量供给充足,劳动就业压力将继续存在。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补充城镇部门低端劳动力市场供给,缓解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的矛盾。若能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效解决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问题,将能调节人口红利的空间余缺,促进人口红利的均衡发挥。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结构分析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结构的变化能够说明人口红利规模的大小和发展所处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大,生产性人口越多,抚养负担越小,人口红利的潜力就越大。依据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可以定性判断第一次人口红利发展所处的阶段,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最大时,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也将达到最大。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衡量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中青年的比例,若当劳动年龄人口以青年为主,此时处于第一次人口红利期;当劳动年龄人口快速转变为以中年为主,此时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潜力将不断壮大。
图31950~2050年中日韩劳动年龄人口
(15~59岁)占总人口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同图2。
下面从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比较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结构。从图3可见,首先,1950~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现先降低后上升再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于1985年突破60%,2010年达到最大值,接近70%,并于2030年后低于60%,超过60%的时期为1985~2030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超过60%的年份为1960~2005年,最高约为65%。日本实现人口红利期为1960~1990年,并将1972年前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1973年之后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由于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遭受美国的打击,日元大幅升值,随后资产股市地产泡沫化和泡沫破裂,经济进入低迷发展阶段,因此1990~2010年这20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36]。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60%的年份为1980~2025年,最高约为68%,目前韩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通过对比中国和日本、韩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比重远高于日本人口红利期的比重,与2010~2015年的韩国相当,且2020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速度低于韩国。因此,中国的生产性人口比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能支撑经济快速增长。
图41950~2050年中日韩劳动年龄人口
(15~59岁)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同图2。
其次,将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指数界定为大龄劳动人口(40~59岁)与低龄劳动人口(15~39岁)的比值,从而对比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化。图4显示1950~199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呈轻微的年轻化,1990~2035年呈现不断的老化趋势,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指数约为0.8,最大为21世纪30年代,约为1.02,随后劳动力资源又呈轻微年轻化。日本在人口红利期末(1990年前后)时,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指数约为0.8,至2010年后开始上升,2025年前后达到最大值,约为1.1。韩国2010年该数值达到0.8,之后也基本一直高于中国,劳动力资源老化程度高于中国。中国劳动力资源老化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老化程度和速度弱于日本和韩国。此外,郝东阳等人的研究表明,家庭储蓄随着户主年龄增加而呈现倒“U”型变动趋势,当户主年龄处于40岁以下,家庭储蓄率缓慢增加;当户主年龄处于40~60岁之间,家庭储蓄率迅速上升[37],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指数越大,其储蓄能力将越大。相比处于1990~2012年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集聚期(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指数达0.4~0.8)而言,中国未来劳动力资源相对老化,说明中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将可能会形成为养老而进行准备的储蓄动机。这再次说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规模正逐渐减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将可能壮大。
3.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不断增加
如果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推行了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等政策制度,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它将由于人力资本的特殊性而成为未来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根本。目前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趋于减少,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且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包括“三驾马车”依赖程度的转换、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源结构的转变、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等,这些都将依赖于前期积累的人力资本。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制度不断完善,教育经费支出不断增加,大学持续扩大招生规模,人口受教育水平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提升。从出生队列来看,“六普”数据显示,“50后”至“90后”的各个年代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7.86年、9.01年、9.63年、10.74年、9.70年,即随着代际转换,人力资本积累迅速增加。从就业人口来看,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0年的6.8年增加至2000年的8.0年,2010年进一步提升至9.1年,预计2020年和2030年将分别达到10年和12年,接近美国目前的水平(12.5年)[38]。另外,《中国统计年鉴2013》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10年达到74.83岁,比1990年提高了6.28岁。这些都表明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不断提升,为壮大第二次人口红利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我国逐渐积累了规模庞大的人才资源,农民工培训也在不断加强,从而助力新时期经济发展。人才资源是高级的人力资源,2010年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21亿,占全国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11.1%;各类人才资源规模庞大,其中高技能人才资源达到2863.3万人,专业技术人才资源达到5550.4万人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2-06-05].www.gov.cn/g2dt/2012-06/05/content_2153635.htm。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略有上升,2013年达到32.7%,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者的比例为9.3%,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者的比例为29.9%。
四、人口红利机会仍存在但收获难度增加
快速的人口转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即人口红利,它通过劳动力投入、储蓄和人力资本等作用于经济增长。虽然对人口红利的认识视角不同,导致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存续性的判断,但无论基于哪一种视角,人口红利都是指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是21世纪40年代中期前规模保持在8亿以上、21世纪30年代前比重保持在60%以上。尽管目前出现民工荒、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但这主要是就业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规模问题,是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的结果。劳动力人口趋于老化,但也可能随着良好的制度实施而形成较强的储蓄动机。另外,未来劳动力人力资本仍将处于快速积累的阶段。由此判断,中国人口红利仍将存在于未来一段时间。第一次人口红利正由集聚转向减少,未来步入收获结构性人口红利阶段,因而收获难度将加大,更多需要依靠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以及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
为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一,要充分把握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带来的结构性人口红利机会。由于人口转变进度差异和存在大量流迁人口等因素,仍有十余个省份的人口抚养比处于下降的态势,如贵州、辽宁、吉林、广东等地,人口红利还处于集聚状态。第二,完善劳动力市场培训制度,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参与率。民工荒与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并存,充分说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较为严重。应通过相关就业培训制度,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锻炼,提升农民工技能水平,契合产业发展所需,努力缓解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矛盾,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就业水平。运用人才吸引等办法促进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努力化解东中西部地区和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难题。在我国,虽然刘易斯所界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由无限剩余转变为有限剩余,但是仍存在大量的隐形劳动力,需通过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缝合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健全养老保障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要继续深化改革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寻求政府、工作单位和个人养老责任的均衡。若能形成老年人口储蓄动机,营造良好的个人和家庭投资环境,并能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将为经济发展赢得增长动力。第四,投资于人力资本积累,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正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将来要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历经十余年的高等教育扩招为我国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但这部分人力资本在释放潜能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困难,如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导致人力资本积累虚化,与社会需求存在偏差等。从长期来看,应继续加大教育和培训、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减少贫困地区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参考文献:
[1] 陈卫. 2000年以来中国生育水平估计[J]. 学海,2014,(1).
[2] 崔红艳,徐岚,李睿. 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J]. 人口研究,2013,(1).
[3] 杨凡,赵梦晗. 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J]. 人口研究,2013,(2).
[4] 李汉东,李流. 中国2000年以来生育水平估计[J]. 中国人口科学,2012,(5).
[5] 郭志刚. 六普结果表明我国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J]. 中国人口科学,2011,(6).
[6] Bloom, D.E., J.G.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3).
[7] Mason , A.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 [M] // A. Mason.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Challenges Met, Opportunities Seiz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1-30.
[8] Bloom, D.E., D. Canning, S. Jaypee.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2003.
[9] Mason , A. and L. Ronald.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J]. GENUS LXII, 2006, (2).
[10] Bloom, D.E., D. Canning. Global Demographic Change: Dimension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8, 34(S1).
[11] Ronald, L. and A. Mason. Population Aging, Wealth, and Economic Growth: Demographic Dividends and Public Policy[R]. WESS Background Paper, No.23, 2007.
[12] Bloom, D.E., D. Canning, Günther Fink, E.F. Jocelyn. Fertility,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9, 14(2).
[13] Quamrul H. Ashraf, David N. Weil, Joshua Wilde. The Effect of Fertility Redu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3, 39(1).
[14] Bloom D.E., D. Canning, Günther Fink, E.F. Jocelyn.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R]. PGDA Working Paper, No.93, 2012.
[15] 蔡昉. 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6] 蔡昉.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
[17]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2010,(4).
[18] 蔡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 中国社会科学,2013,(1).
[19] 王德文. 人口低生育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 中国人口科学,2007,(1).
[20] 孟令国,王清.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6).
[21] 于学军.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 中国人口科学,2003,(1).
[22] 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2005,(6).
[23] 马瀛通.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 中国人口科学,2007,(1).
[24] 陈卫,都阳,侯东民. 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 [J].人口研究,2007,(2).
[25]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 人口研究,2007,(1).
[26] 穆光宗.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27] 王桂新,陈冠春. 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J]. 人口学刊,2010,(3).
[28] 钟水映,李魁. 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10,(4).
[29] 王丰. 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 [J]. 人口研究,2007,(6).
[30] 车士义,郭琳.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2013,(3).
[31] 同[29].
[32]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 人口研究,2004,(5).
[33] 王金营,杨磊.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 人口学刊,2010,(5).
[34] 同[20].
[35] 田雪原. “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老龄化视角[J]. 中州学刊,2012,(6).
[36] 梁颖,陈佳鹏.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的比较的视角[J]. 人口学刊,2013,(4).
[37] 郝东阳,张世伟.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年龄分布[J]. 消费经济,2011,(5).
[38] 胡鞍钢,才利民. 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4).
[责任编辑冯乐]
[15] 蔡昉. 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6] 蔡昉.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
[17]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2010,(4).
[18] 蔡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 中国社会科学,2013,(1).
[19] 王德文. 人口低生育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 中国人口科学,2007,(1).
[20] 孟令国,王清.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6).
[21] 于学军.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 中国人口科学,2003,(1).
[22] 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2005,(6).
[23] 马瀛通.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 中国人口科学,2007,(1).
[24] 陈卫,都阳,侯东民. 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 [J].人口研究,2007,(2).
[25]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 人口研究,2007,(1).
[26] 穆光宗.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27] 王桂新,陈冠春. 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J]. 人口学刊,2010,(3).
[28] 钟水映,李魁. 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10,(4).
[29] 王丰. 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 [J]. 人口研究,2007,(6).
[30] 车士义,郭琳.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2013,(3).
[31] 同[29].
[32]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 人口研究,2004,(5).
[33] 王金营,杨磊.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 人口学刊,2010,(5).
[34] 同[20].
[35] 田雪原. “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老龄化视角[J]. 中州学刊,2012,(6).
[36] 梁颖,陈佳鹏.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的比较的视角[J]. 人口学刊,2013,(4).
[37] 郝东阳,张世伟.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年龄分布[J]. 消费经济,2011,(5).
[38] 胡鞍钢,才利民. 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4).
[责任编辑冯乐]
[15] 蔡昉. 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6] 蔡昉.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
[17]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2010,(4).
[18] 蔡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 中国社会科学,2013,(1).
[19] 王德文. 人口低生育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 中国人口科学,2007,(1).
[20] 孟令国,王清.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6).
[21] 于学军.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 中国人口科学,2003,(1).
[22] 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2005,(6).
[23] 马瀛通.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 中国人口科学,2007,(1).
[24] 陈卫,都阳,侯东民. 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 [J].人口研究,2007,(2).
[25]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 人口研究,2007,(1).
[26] 穆光宗.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27] 王桂新,陈冠春. 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J]. 人口学刊,2010,(3).
[28] 钟水映,李魁. 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10,(4).
[29] 王丰. 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 [J]. 人口研究,2007,(6).
[30] 车士义,郭琳.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2013,(3).
[31] 同[29].
[32]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 人口研究,2004,(5).
[33] 王金营,杨磊.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 人口学刊,2010,(5).
[34] 同[20].
[35] 田雪原. “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老龄化视角[J]. 中州学刊,2012,(6).
[36] 梁颖,陈佳鹏.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的比较的视角[J]. 人口学刊,2013,(4).
[37] 郝东阳,张世伟.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年龄分布[J]. 消费经济,2011,(5).
[38] 胡鞍钢,才利民. 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4).
[责任编辑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