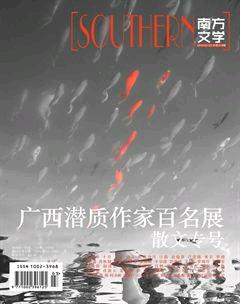美 人
饶珍珠
小镇不大,三条青石板老街呈K形交错,沿驮娘江的叫立新街,依清水河的叫东新街,靠后龙山的是红新街,大部分是雕檐画梁的百年古建筑。即便时光动了无情刀,剥蚀了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但斑驳陈黯中仍隐约可见当年的繁华。
她家在东新街的深处,我去上小学和初中,都要经过她家门前。
她叫什么名字?我一直不知道,只知道她夫家姓李,就姑且叫她李氏美人吧。老一辈的人都说她年轻时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人。
“她呀,也说不出怎么个美法,可就是左看右看都顺眼,而且让人觉得不敢靠近。”奶奶正纳布鞋,头都不抬。
“那您不是说民国时土匪很多,经常下来抢姑娘吗?她是怎么逃得这劫的?”
“土匪要抢的主要是黄花大姑娘,那时她已经嫁人生孩子了。而且她很少出门,不得已出门也是拿锅底黑烟抹脸,乡亲们也帮遮掩,这才逃过呢。”
我读初中时,她已年过四旬,但还是美得让人叹服: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让人想起西湖的水光,潋滟波动,涟涟一片,瞧不出一点杂质、一点烟火气;黛眉如画,白皙细腻的鹅蛋脸,挺直的鼻梁、自然红润的樱桃小嘴。在南方这种小地方,女子一般矮小,但美人长得很修长,1米7左右,在小镇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她不爱笑,神色清冷,街边扎堆闲聊的女人中很少有她的身影。
她不仅脸蛋漂亮,更胜在气质风华。有林黛玉的弱柳脱俗之姿,也有宝钗的高贵优雅之气,但我觉得她更像妙玉,有种淡定入禅的出尘之美。
这世上就有这么一种人,老天爷在造她的时候费了不少心思。她不仅天生丽质,而且尽享岁月的宽容,时光风霜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痕迹。
她家在巷尾的转角,房子比别家还简陋,别家都是雕龙画栋的明清古民居,就她家是泥巴房。屋后是河岸悬崖,别具匠心的用横木和竹子在峭壁上撑起一个大大的竹阳台。阳台旁边是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巷道和阳台只隔十米宽的距离。
春暖秋凉,来回总能看见李氏躺在阳台的藤椅上,有时翻看一本厚厚的书,有时什么都不做,安静躺着。阳光洒落在她身上,感觉有落寞静静滴下来,她形影清瘦,眉目在光影中清凉出尘,整个人有一种烟寺晚钟的清寂,仿若淡远空幽的水墨画。
虽然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出身,但我认为她必是大户人家。她与我所熟悉的奶奶、母亲那一类小镇女人很不同。奶奶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赶牛耕田、上屋揭瓦,风风火火,身上的衣服从没有熨帖、干净利索的时候,她们往街头这么一叉腰一站,一扯嗓子,保准鸡飞狗跳。
可她不,她品茶、看书,种一园子的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李氏是寡妇。二三十岁就守寡了,独自带着一对儿女生活,一直没有再嫁。她的丈夫听说也是有文化的人,好像是教书先生,听这消息时我松了口气,庆幸她嫁的不是什么屠户之类。
她民国出生,经历了动乱、匪患、饥荒、“文革”等世间跌宕。我一直揣测:作为一个美人,又是寡妇,想来是非多,“文革”时,她被挂鞋游街吗?被人泼脏水吗?自然灾害那几年,有人饿死了,她一个纤弱的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熬过艰难的岁月,李氏的儿子却在十五岁时突然疯了,有种说法是去县里读高中回来路过山神庙,吐了口水,被山神弄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反正书是不能读了,整天在家关着。
他不太像疯子,衣着干净,除了狂躁时激昂地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在阳台走来走去以外,更多的时候是安静的,在那个危崖的阳台上,握着一杯茶静静坐着,忧郁而清癯,四周洒满阳光。
有一次,我放学路过老教堂,刚好碰见李氏挑着一挑水,手上还提着一篮子红米菜,很吃力的样子。我鼓起勇气上前,说我帮您拿那篮菜吧?她抬头看我,她的瞳仁是一种通透的墨,注视人时清淡却掩不住夺人的光华。
她点头致谢把篮子递给我,一路上问我是哪家的孩子,我报上了祖父的名字。祖父在小镇也算是知名人士,她打量我,说,怪不得呢,书香门第,气质很不一样,生在那种家庭你有福了。
十四岁的小孩能有什么气质呢?何况我穿着土气,性格内向。但她这么一说,我还是高兴得眉开眼笑。
“您长那么美,怎么还那么辛苦呢?”我傻乎乎问道。
她轻轻笑起来,笑如芳草,目光澄澈,实在让人心动。
“长相和苦不苦有关系吗? 而且,我不觉得苦啊,靠自己双手吃饭,腰杆直。”她放下水桶,俯下身,温柔地说,“记住,不管有没有男人可以依靠,女人都要自强自立,不要像它一样。”她指着一旁古榕上那缠缠绕绕的黄色藤萝。
我点点头,虽然这些话对小女孩来讲还是深奥,但我相信她讲的肯定是对的。
李氏穿的是黑色唐装,上衣小立领斜襟,下身宽脚裤,很合体,女性的曲线一览无遗,好像那衣服就是从她身里长出来的。老一辈的妇女都穿这种壮族服饰,不是黑就是灰。但奶奶和母亲包括很多女人她们的唐装很宽大,根本看不见腰身,女性风格模糊。
奶奶曾说,衣服紧,该露的露了,不该露的也露了,难看,伤风败俗。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合身衣服很难看,不该突的都突了,人家看见了很丑?而您穿的是合身衣服,您不怕丑吗?”我问道。
她又笑了,看来她不爱笑只是我以前的错觉。她转个圈后对着我说,“那你看我这样子,丑吗?你认为穿合身好看,还是宽宽大大没腰身好看?”
我看了看,歪头想想,老老实实说:“您这样穿好看,衣服还是合身的好。”
“这就对了。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女人的身子要是没有这些线条就不成女人了,既然有了,干吗要遮着掩着呢?这是老天爷给的礼物,很美的,美的东西就要展现出来,懂吗?”
从来没有谁对我说过这样“大逆不道”的话。那时的我正为自己身体的发育烦恼,觉得自己丑极了,她的话我似懂非懂,但起码对自己身体的发育变化不再深恶痛绝。
三变花谢了,霜白鹭飞,冬天来了。
傍晚,我去学校上自修,走到老榕树前,随意瞟了一眼路下方的百年码头,看见李氏正挑着一担满满的喂猪的红薯叶上台阶,大冷的天她高高挽着裤脚,可能担子太重,她每走几步就停下来歇歇脚、擦擦汗。
我停下脚步,想去帮忙,可我是挑不动的。明白了这个道理,顿生怅惘之意。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古老而宁静的小镇应该也不乏好男人,怎么就没有人肯站出来与她并肩,为她遮风挡雨呢?生平第一次,我叹息自己不是男儿身,不与她同一时代,不能为她揽下所有沧桑。
她是那般不染烟火的凉玉,应该是在开满荷花的院子里,凭栏斜阳、闲看宋词,而不是现在这副模样。
几年后,我外出求学,后又回到小镇初中当老师。住在家里,每天步行去学校,还是走原来的路线,还是穿行在东新街古老斑驳的房子。那三两石榴,艳丽的花在春天暖风中探出严谨高耸的女墙。
那一年,美人的儿子去世。来来往往中,再也看不到那个英俊的疯子在斜阳中如浮雕般沉静的身影了。
美人迟暮,只有那一剪秋瞳依然天高云淡。
她已不认识我,更不知道她曾经宛如一道幽光,投影在这个沉静的女孩心灵深处。
喝茶的时候,我跟女友感慨:“这么美好的女人怎么就没有男人呢?”
“也许就是过于美好,让男人望而生畏了吧?”
我哑然,的确有几分道理。
没两年,我离开小镇去进修后来又到外乡工作,偶回老家也很少走东新街了。有一次回家过中秋,去表姐家吃饭,突然很想看看李氏,就拐过她家门口。
原来的花园,那个危崖上的竹阳台,已经坍塌,在原来的位置,新起了一幢小楼。我正寻找李氏的身影,却看见她坐在地上,手抓着亮闪闪的铁门向外张望。我大惊,急忙走过去,问她怎么了,伸手从铁门探进去,想把她扶起来。她摇摇头,“不用,我站不起来,腿废了。”
我不敢看她那曾经修长的腿,小心地问:“那我进去帮您拿个凳子坐着吧?地上凉。”
“你进不来的,铁门锁着呢。”我望过去,果然,一个黑亮的铁将军把着。
“那您怎么不好好在屋里呆着,到门口干吗呢?是不是有什么事呀?”
“没事,只是在屋里呆久了,发霉了,想出来闻点人气。”还是那样波澜不惊的语气。她的裤子沾满了灰尘,想必是一路从房里爬出来的。
她家人丁单薄,女儿女婿都忙,外孙在外求学,看来白天家里就经常只剩她一人。
“你走吧,不用可怜我,我觉得自己挺好的,人活一世,哪能事事圆满呢?都七十多岁了还能喘气,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开恩了。”她露出笑容,淡淡的。
没多久,这个清冷的美人就去世了。
今年,我去贵州的安龙看荷花,一池一池洁白或粉红的莲花, 遗世清幽,在霏霏细雨中,那般的静好、那般的寂美。
那个刹那,我想到了李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