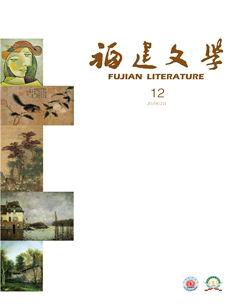论“闽派批评”
“闽派批评”的称谓一度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为数众多的闽籍批评家同时跻身于文坛,登高而呼,雄辩滔滔,许多重大命题的确立隐含了他们的思想贡献。强烈的理论兴趣无形造就了一个醒目的群体,“闽派批评”即是对于这个群体的命名。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文学史上许多命名并非精心策划或者深思熟虑的产物,相当一部分美学潮流或者学术派别的命名由于不无偶然的历史机缘,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朦胧诗”,或者“形式主义学派”、“达达主义”、“耶鲁四君子”,如此等等。“闽派批评”之称并非来自学术特征的严谨概括,这个命名毋宁说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闽籍批评家的人数明显超过了各个省份的平均数。
可以列举的闽籍批评家名单洋洋大观。一部分批评家长期身在京沪,例如谢冕、张炯、刘再复、陈骏涛、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张陵、李子云、潘旭澜、朱大可等。他们多半是年轻时外出求学,毕业之后就职于京沪的学院或者研究机构。另一部分批评家长期活跃在闽地,例如孙绍振、许怀中、刘登翰、林兴宅、王光明、俞兆平、朱水涌、杨健民、谭华孚、南帆等。个别批评家的活动轨迹相对复杂。陈晓明当年已经在闽地崭露头角,继而求学、定居北京;谢有顺求学于闽地,登上文坛的时候已经栖身于粤地。
如此多元的成长背景显明,闽籍批评家并未承传某种共同认可的文学观念。因此,“闽派批评”并非一个彼此师承或者同声相应的学派。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到主体论、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闽籍批评家活动在跨度巨大的理论场域,分别充当不同主题的领衔主角,譬如谢冕、孙绍振之于新诗论争,刘再复之于文学主体性,陈晓明之于后现代主义。
为什么闽籍批评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论兴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朱熹、李贽、严复不仅是闽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他们的文学观点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应。闽地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他们在诗论方面尤有建树,譬如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负盛名,“以禅喻诗”之说在诗歌批评史上影响久远。至于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均为文化大师,他们分别具有独到的文学理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判。总之,历史上的闽籍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以至于坊间有“闽人好论”的戏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考证,20世纪80年代集体崛起的闽籍批评家具体地受惠于哪些思想线索。他们相对一致的认识是,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无非是一个遥远的背景,“闽派批评”的浮现更多地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机遇。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解放的叙事逐渐成为主旋律。作为解放叙事的先锋,文学承担了摧枯拉朽的使命。文学批评的意义是扩大战果,开拓理论纵深。闽籍批评家接手的第一个理论战役是“朦胧诗”之争。70年代末期开始,一批风格迥异的诗人开始集结。他们的诗作充满了象征、意象和反讽,情绪忧郁、悲愤、孤寂,音调嘶哑。80年代初期,这些诗作陆续出现在刊物之上,立即引爆了激烈的争论。对于习惯颂歌与战歌的批评家说来,这些诗作古怪艰涩,主题朦胧——令人气闷的“朦胧”是当时的著名评语,也是“朦胧诗”之称的来源。这些诗人的中坚之一舒婷居于闽地,她的诗作被视为尖锐的挑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福建文学》率先发起争论。一时之间,应者云集,诸多批评家见仁见智,蔚为大观。这一场争论成为许多闽籍批评家的发轫之处。
《福建文学》策动的论争延续到1980年的南宁诗会,掀起了一次新的波澜。闽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勇敢地为“朦胧诗”辩护,张炯担任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会议之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继而又在《诗刊》刊登《失去平静之后》。如果说,谢冕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沉住气,保持宽容,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历数文学史上成功的变革,那么,孙绍振力图阐发的是新诗背后的美学原则——“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的论文标题即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异于颂歌与战歌的传统,新诗追求的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在孙绍振看来,这种美学原则的深刻根源是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在当时,这些观点惊世骇俗,以至于谢冕、孙绍振不得不承受学术之外的巨大压力。时至如今,“朦胧诗”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的认可,谢冕、孙绍振的“崛起”之说酿成了新的理论话题。王光明、陈仲义等闽籍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对于新诗进行卓有成效的后续研究,他们的开疆拓土功不可没。
“朦胧诗”争论之后,众多闽籍批评家共同卷入的另一个理论事件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争。由于解放的叙事纵深扩展,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读文学?是不是仅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唯一视角?各种零星的尝试和实验之后,理论的总结势在必行——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于1986年的春天在厦门召开。当时,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或者接受美学等诸多西方批评学派尚未登陆,打动批评界的毋宁是以自然为范本的科学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奉为时髦,不少文学研究论文以列举图表、数据与数学公式标榜科学精神。厦门会议的论辩之中,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诗与数学的统一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不过,过度的科学主义引起了另一些闽籍批评家的非议。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仅仅提供各种描述真实的视角。如果无法确认文学批评力图阐述何种价值观念,批评家又怎么知道选择哪一种描述视角?因此,没有理由用貌似客观精确的科学话语覆盖人文情怀。
几乎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同时,闽籍批评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这种观点是文学对于主体哲学的致敬。刘再复分别阐述了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尽管现代哲学对于主体概念的种种质疑不可避免地波及文学主体性命题,但是,多数人深切地体会到隐藏于这个命题背后的苦心: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这个意义上,闽籍批评家的理论工作显示了一脉相承连续性。众多闽籍批评家的知识谱系相距甚远,可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围绕相近的问题持续地思考,这只能解释为历史的迫切性。endprint
“闽派批评”的出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年,王蒙曾经对文学批评发表过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闽派批评”堪与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势。籍贯、地域文化渊源、历史机遇——“闽派批评”命名的依据显然是三种因素的相加,尽管三者的意义并不相等。然而,这个命名之所以普遍流行,显然得益于几次影响广泛的批评实践。没有批评实践的支持,种种人为的舆论吹嘘走不了多远。必须补充的一个事实是,福建省文联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一个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为“闽派批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尽管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京、沪、闽三地众多闽籍批评家担任这个刊物的编委,刊物发表了“闽派批评”的许多重要论文。因此,谈论“闽派批评”的组成范围,通常会提到《当代文艺探索》的主编魏世英,副主编王炳根、林建法、林焱和编辑王欣。
20世纪90年代,“闽派批评”之称逐渐淡隐。当然,这不等于闽籍批评家销声匿迹。一些批评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老骥伏枥,他们仍然密切注视文坛的动向,不时发表真知灼见。更多的批评家精思不辍,开拓不已:谢冕对于诗歌一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终聚焦于诗歌领域;王光明与陈仲义与谢冕相近,诗歌的信徒是他们从未放弃的身份;相对地说,孙绍振的学术战线辗转不定,他曾经涉入普遍的美学问题,继而转向了微观的文学写作、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学语文教育;刘再复移居海外多年,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沉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重大课题。如果言及闽籍批评家转身幅度之大,刘登翰或许是一个特殊的例证。他于90年代逐渐转向了海外华文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形成了学术梯队,其中佼佼者如刘小新、朱立立。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将性别研究推向前台,闽籍批评家林丹娅积极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至于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俱已卓尔成家,他们广泛涉及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由于学院造就的良好学术环境,许多出生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闽籍批评家正在迅速地成熟……相对闽籍批评家二十多年的工作状况,这些描述无疑挂一漏万,我企图借助这些描述提出的问题是:面对如此之多的学术资源,是否到了重提“闽派批评”的时候了?
重提“闽派批评”,制造乡贤的学术聚会或者地域文化表彰仅仅是次要目的。重要的是发现新型的话语平台,召回曾经活跃的批评精神。闽籍批评家是不是可以如同当年一般犀利骁勇,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文学话题,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很大程度上,这同时是文化环境的迫切要求。
现今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学批评正在滑向边缘。娱乐新闻、明星八卦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节目占据了大部分传媒的版面;许多人心目中,网络文学几乎等同于文学的范本。与此同时,经典文学体系的声望急剧下降,严肃正在某些人心目中演变为令人厌倦的品质。这时,文学批评何为?文学批评将在这个时代文化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愈来愈多的批评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分量。20世纪曾经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繁盛的理论生产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种考察文学、考察世界的视角。批评家可以发现各种文学话题,还可以借助文学话题阐述对于世界的各种观点。“闽派批评”的历史证明,由于批评家不懈的呐喊、辩驳、阐发和倡导,某些显赫一时的声音消失了,另一些大逆不道的观念逐渐成为共识。作为文化空间的开拓,文学批评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果说,“闽派批评”的称谓曾经贮存了丰盛的文学记忆,那么,许多闽籍批评家即将开始面对另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称谓如何内在地织入文学的未来?
责任编辑 石华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