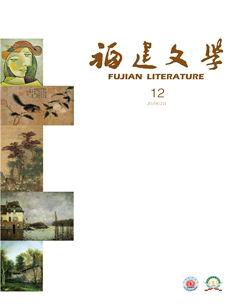汀水谣
“天下水皆东,唯汀独南。”汀江,源于汀州庵杰龙门,流经闽西诸客家县,水流湍急,多险滩,入粤东三河坝后称韩江,八百里水路到潮汕入海。江岸乡间行走多日,得采风故事若干,叙农耕社会乡土侠义传奇。岁月流逝,武风隐伏,金戈铁马不再。念及故乡昔日浮光片羽,毋使湮没,作“汀水谣”。
隔山浇
来到大沽滩,正是细雨霏霏的时节,原本汹涌澎湃的江水此时甚是平缓。今日千里汀江“七十二险滩”,多半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曾经南来北往的“鸭嫲船”不见了踪影,俗谚说“上河三千,下河八百”的繁忙景象已然成为历史陈迹。
江面上,挖沙船缓缓移动,隆隆的马达声连同不远处的一座水泥公路大桥强烈地提醒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时代了。
文清学弟有篇考据博文,引注明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翁万达《汀郡守华山陈君平两滩碑》说:“故舟行甚艰,逆焉如登,沿焉如崩。……盖诸滩皆然,而龙漈为甚。”龙,即龙滩,在今闽西上杭县官庄乡回龙村,淹没为水库区;漈,为漈滩,在长汀、上杭交界处,今羊牯乡白头漈。博文附图,两山对峙处,斜向急弯。河床长草,江石光滑圆润,花纹多变,一如我书案上的奇石。
我来此地,是试图揭开家族历史的一个谜团,同行者是当地作家李应春兄。我们站在大沽滩岸边,默默无语。
家族的一代武林高手八叔公太是在大沽滩失踪的。中都镇“和记”饭铺唐有德掌柜对当时的李神捕说:“在俺这里吃了一壶米酒、一盘油炸花生米,转脚往大沽滩那边去了。”
李神捕乃汀州府“六扇门”第一高手,百案百破。他的名头就栽倒在“老关刀失踪案”上。
老关刀是闻名闽粤赣边的客家把戏师,功夫好,行走江湖,全凭一个“义”字。说他德艺双馨,是有据可考的。民国《武邑志·义行传》载:“捐建茶亭、石桥各一,乡人称善。”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三月初五日辰时,上杭中都墟,老关刀从河头城逆行至此,扯圆圈子,立马耍了一阵大关刀。这关刀,有讲究,又唤作青龙刀、偃月刀、青龙偃月刀,还有叫冷艳锯的,重八十二斤。关刀在一个六旬老汉手中亮光闪闪、呼呼生风。不服不行,满场叫好。有人就说了,没有真功夫,咋敢叫老关刀呢?
此时,老关刀敲响了铜锣,说:“走江湖,闯江湖,哪州哪县俺不熟?卖钱不卖钱,圈子先扯圆。老夫来到贵码头,一不卖膏药,二不卖打药,只是卖点中草药。 常言说得好啊,腰杆痛,吃杜仲;夜尿多,吃蜂糖;四肢无力呢,吃点五加皮。老夫今晡不卖老药,卖点新药,新药名叫隔山浇。诸位乡亲听好啦,撒尿撒不高,就吃隔山浇;吃了隔山浇,撒尿撒上八丈高;站在地上,撒在床上;站在床上,撒在蚊帐顶上;站到蚊帐顶上,撒到屋顶上;站在屋顶上,撒到高山上;站在高山上,汀江都撒浇。”
围观者一听,乐了,有人问:“老关刀师傅,你这隔山浇怎么吃哪?”老关刀笑了,当当两声,贴近他的耳朵却提高嗓门说:“小哥,你莫讲给别人听哦。有酒泡酒,无酒泡尿。无酒无尿,可以干嚼。”围观者全听清了,哈哈大笑。氛围好,其乐融融,隔山浇很快就卖光了。老关刀收拾家伙什,乐呵呵地走向了“和记”饭铺。
墟场情境复原,得益于“客家通”网站邱博士的博文《客家江湖顺口溜》。特此鸣谢。
老关刀来到“和记”饭铺,入里屋,靠墙迎门而坐。老熟人了,唐掌柜立马端来了一壶客家米酒和一盘油炸花生米。老关刀笑眯眯的,慢悠悠地吃喝,直到日头偏西。
结账,老关刀叠脚就走。唐掌柜说:“老关刀师傅,不歇歇脚?”老关刀说:“不了,明日是上杭墟哦。”唐掌柜说:“样般敢扎手(干嘛这样勤快)?”老关刀说:“桥该修喽。”
唐掌柜明白,上月暴雨,冲塌了汀江支流溪流的许多桥梁。一大把年纪了,做把戏赚点钱不容易。唐掌柜暗忖,早知如此,这次老关刀的开销,他就不收了。唐掌柜想不到的是,老关刀茕茕远去,留给他的是最后的背影。
当时的大沽滩风高浪急,修不了桥梁。过江,须搭船。码头两岸,都有凉亭。现在,老关刀就在西凉亭里头等候。旁边有三五个壮实挑夫,他们挑盐路过歇息。看到那把大关刀,一位说:“您是老关刀师傅吗?”老关刀说:“正是老夫。”挑夫说:“好功夫啊,打倒了西洋大力士。”老关刀笑了:“老皇历喽,三脚猫功夫,侥幸侥幸。”挑夫说:“天快黑了,明日过江吧,武婆寨的土匪是有洋枪的。”老关刀说:“多谢小阿哥,俺一个做把戏的,有几个小钱哪?”挑夫想想也是,说:“有空来千家村做把戏哦。”老关刀说:“好,好,会来,会来。”
挑夫走后不久,一只鸭嫲船靠岸了,摇船的是一个白脸后生。说好十文铜钱,老关刀上了船。船到江心,白脸后生停下了双桨。他问老关刀:“师傅是老关刀吗?”老关刀瞳孔收缩,按刀柄。白脸后生一翻掌,亮出了洋家伙,说:“这叫盒子炮,你没用的。”老关刀说:“好汉,看中什么,都拿去。” 白脸后生说:“痛快!你老了,不要卖隔山浇啦。”老关刀说:“好好的草药,干嘛不卖?”白脸后生说:“俺叫隔山虎,你骂人哪。”
一声枪响,在大沽滩上空回荡,一直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
时日久远,我们注定解不开这个历史悬案。上述,是我个人的想象。老关刀是我家族史上的善者、仁者、勇武者;李神探当然是李作家的曾祖父,著有《闽西吟草》。这个擅长文墨者,没有留下关于“奇案”的片言只语。
回城路上,我想起了大沽滩的一副对联:“白水漈头,白屋白鸡啼白昼;黄泥垄口,黄家黄犬吠黄昏。”
七里滩
在古汀州客家博物馆的草坪上,我又看到了那只鸭嫲船,在两棵大唐柏树的浓荫之下。
古柏大有来历,清乾隆年间纪晓岚大学士在此夜遇红衣人,冉冉而没,遂写下了“参天黛色常如此,点首朱衣或是君”的楹联。
这鸭嫲船是昔日航行于汀江的主要水上交通工具,类似于浙江绍兴一带的乌篷船。鸭嫲船要大一些,蓬似大箬笠,土灰色,晒干的竹叶经过风吹雨打的颜色。
遥想当年,千里汀江之上,鸭嫲船夹杂于浩浩荡荡的竹木排之间来往穿梭,“上河三千,下河八百”。
我来此地,是打捞我们客家族群那些遥远的记忆。
清光绪三年,八月既望。清晨,霞光初露,一些在汀州古城过夜的船只就陆陆续续解缆起航了。
汀州往潮汕,是顺流,八百里水路,俗称千里汀江或千里韩江,有七十二险滩,以龙滩、漈滩、大沽滩为最。我想,“大沽”或许是“大哭”的转音。我家乡与大沽滩一山之隔,我熟悉那里的客家话。
话说彼时社会动荡,闽粤赣边山高路遥,时有强人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上下行船只多结伴而行。
这一只鸭嫲船,约莫有八成新,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船头船尾,一老一少。老的精干。少的粗壮,却眯着一只眼睛,嘴角歪斜,有些木讷。老者叫他愕牯子。愕牯子即呆子,客家话。他叫老者三伯公。
船上的乘客,是一位堪舆师,俗称地理先生。客家地区盛行风水术。行地理者,多师承赣南三僚村杨公先师,观砂察水,以“形势”论。这些人行走江湖,见识高,人缘广。水路强人,盗亦有道,传言从不抢妇孺及先生。
此地理先生姓李,年逾不惑,三绺长髯飘飘,显见仙风道骨,一把长剑斜背,剑不离身。李先生云,此剑不是凡剑,乃飞剑,可千里取人首级,杀敌于无形。
昨日,李先生以十两银子高价包船,要求九月初一辰时,准时抵达粤东松口镇。汀州经上杭县城,顺流往峰市、三河坝,转松口镇,时间足足有余。
李先生此时正端坐在船舱内,靠窗,手持一本连城四堡文渊堂版练大侠著《梁野散记》,念念有词。他的心情很好,松口镇的“赛百万”李大先生是他的本家,悬赏千两银子,要踏勘一处好风水。
李先生出道以来,即名动诸边。他的成名之战,却是在梁野山麓的武所古镇。话说彼时,几位大名鼎鼎的同行对一处风水格局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李先生飘然来到,手持罗盘转了一圈,断然道:“此乃雄牛牴角形,好斗,妨主家,横蛮不显文星,富贵难求。”众大哗。李先生淡淡道:“若不信,东七步,南九步,西三步,挖地一尺三寸,便知分晓。”主人将信将疑,令人在指定位置下挖,果然挖得一块枕头大小的白石头,还热乎乎的。李先生出剑,剑光一闪。这只雄牛就算是阉了。从此,武所家族和睦相处,文风兴盛,接连中了几个秀才、举人。传说有危姓举人正待上京赶考,志在必得。
李先生的风水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此打住。
船行汀江,秋水清澈,鸭嫲船顺风顺水、渡险如夷。日落时分,抵达晒禾滩留宿。
日出三竿,李先生睡醒了,踱步船头,拉开架子,舞了一套二仪四象八卦剑法,徐徐收势。此时,他瞧见了愕牯子弯腰弓背站在船尾,手持竹篙,一动也不动。
这呆子要干什么?
这呆子啊,客家人称为愕牯子。传说某年大年初二,随媳妇转娘家。媳妇知他愕,临行前交代说,吃饭夹菜要讲规矩,我会在你的脚上牵一条丝线,我动一下,你就夹一下,切记切记。来到老丈人家,开饭了,愕牯子偶尔动动筷子,规规矩矩。老丈人真高兴啊,都说这女婿是愕牯子,俺瞧着像是个秀才郎嘛。正要夸奖几句,不料,这女婿突然筷子飞舞,尽往菜碗招呼。忙不过来啦,他就端起菜碗倒进自己的饭碗里,弄得饭菜狼藉。原来,饭桌下两只小狗抢食肉骨头,牵乱了丝线。满堂愕然,媳妇欲哭无泪。又传说愕牯子出门,挎了一竹篮煎粄,路见山间水车,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愕牯子想,你饿了吧,怎么一直叫唤“俺吃俺吃”呢?遂投入一块煎粄。水车响声依旧。愕牯子投了一块又一块,水车还在叫。愕牯子说,都给你吃好了。连竹篮带煎粄一同扔了进去。水车卡住了,不响了。愕牯子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就在昨天租船之后,歇客店的老掌柜有意无意地向李先生说起了那些笑话。李先生一笑了之,没有说什么。
“刷”“刷”“刷”……一连串的闷响,但见愕牯子快速挥动竹篙,点击水面,一堆麦穗鱼就直挺挺地躺在了船板上。
麦穗鱼,又叫罗汉鱼,头尖无须,凶狠好斗,杂食。这个时节,成群的麦穗鱼从潮汕水底上溯千里,游到了这片水域。
愕牯子扔下竹篙,双手掩面,蹲在船板上呜呜大哭。
三伯公跳出船舱,指着愕牯子厉声道:“大清早的,哭什么哭?乌鸦嘴!”
愕牯子吞吞吐吐说:“铁钉公子……跑……跑掉了……一只。”
三伯公嘲笑道:“什么铁钉公子?禾摆子!晓腚毋晓朘。不是看你有几把笨力气,学撑船,垫钱都没人要。”
愕牯子不敢哭了,嗫嚅道:“三伯公,俺要……跟您……学撑船。”
三伯公说:“上午走七里滩,不用力气,你就不要吃早饭了。”
愕牯子说:“不吃,俺不吃。”
说完,三伯公进了船舱。李先生走了过来,掏出一块千层甜糕,递给愕牯子,说,张家老店的,甜哪。
愕牯子一把抓过,三下两下吞入肚,噎得双眼暴突。
船行七里滩,风平浪静。行三里许,就看到岸上有一群客商模样者,夺路狂奔。中有一人,停了停,说,快逃啊,黄拉虎下山啦。
杭武一带客家人叫老虎,通常发音成拉虎。这黄拉虎,是千里汀江之上鹞婆寨的著匪,传说三个月前被陈捕头率百名兵勇一举剿灭。黄拉虎不知所终。怎么又回来了?三伯公犹豫了。李先生笑了:“船家,焉得不知是抢生意的?故弄玄虚?又焉得不知是乡人开玩笑?俺一个杨公弟子,行善积德,黄拉虎何必为难?这样吧,俺加一倍酬金,你尽快行船。”
三伯公吆喝一声,船行甚速。七里滩尽处,夹岸高山,收束江水,形似穿针,人称穿针峡。
转眼就要驶过七里滩了。忽见前头有一大堆横七竖八的竹木挡道,三五只鸭嫲船随意飘荡。三伯公暗暗叫苦。忽闻岸上铜锣鼓点乱敲乱打,噪杂一片。又听啪啪两声暴响,两把铁钩飞落船舷,将鸭嫲船拖到了岸边。
岸上,一个铁塔似的蒙面人立在前头,手中是一把玄铁开山刀。
三伯公趋上前来,说:“俺就是叫铁艄公的,给个面子,这三两银子,留给弟兄们喝口酒。”
蒙面人一刀劈下,三伯公就滚落河边。
李先生踱出船舱,手持书卷,伸了个懒腰,说:“好汉,俺就是个行地理的,俗姓李,道上朋友谬称李半仙的。脚跟上安灶头。交个朋友好吗?”
蒙面人哼哼冷笑。
李先生快速滑步退后,瞬间抽出了宝剑。
李先生舞动宝剑,剑光四射,寒气逼人。蒙面人又是一刀劈下,李先生就栽倒在船头了。
愕牯子拖着竹篙,呜呜哭喊:“你赔俺三伯公,你赔俺李先生。”
蒙面人极不耐烦,不待他在船头站定,猛力挥出了一刀。
愕牯子提起竹篙,碰向开山刀。
竹篙斜断,成尖刺,直插蒙面人前胸,破膛而出。
绒家变
欢快的锣鼓声过后,是长串鞭炮炸响,声震四邻。
偶染风寒的阿贵,挣扎着从床上爬起,趴在窗沿上,瞧着房长叔公率族人肩扛“乐善好施”金字牌匾,热热闹闹地往隔壁邻居院子里去了。
“昌哥真是威风哟!”阿贵咂咂嘴,伸长了脖子。
“躺下,躺下,喝药啦。”八妹,阿贵的生媚,端来了大碗头浓黑的“狗咬草”药汤,侍候他喝了下去。
八妹扯过棉被,蒙住了他的头脸。这叫“发汗”。
昌哥,也就是一个挑担的。船到汀江河头城,下行粤东石市,有十里险滩,水流湍急咆哮,浪花飞溅似棉花,遂得名棉花滩。此处为行船禁区,上下游货物全靠挑夫的铁肩膀铁脚板驳转。汀江流域“盐山米下”。盐包是牛头包,每包司马老秤计三十斤。一般人挑四包,阿昌挑六包,长年如此。
阿贵也是挑夫,和阿昌同伙。他们还一块习练南拳朱家教,敲门师傅就是闽粤赣边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老关刀。他们也学南狮,阿昌舞狮头,阿贵牵狮尾。他们的打狮功夫,也有了些名气。年初五,均庆寺庙会,他们的青狮,缩上了三张层叠的八仙桌。
客家地区重冈复岭,山路弯弯十里八里则有亭翼然,形似廊桥。中置茶桶,常年有人施茶。茶桶里一柄小竹筒,千人万人用过,却无肚疼病患者。故里相传,大唐罗隐秀才说过:“路亭茶,驱病邪。” 这是“圣旨口”,一说就灵。
阿昌得“乐善好施”牌匾,源于一家三代为“甘露亭”长年施茶,风雨无阻。众乡绅联名上书。曾知县大为感动,亲笔题字,鼓乐送来,期在淳厚民风。
五月初九日,芒种。老皇历说:“一候螳螂生;二候鹏始鸣;三候反舌无声。”客家民谚说:“芒种雨涟涟,行路要人牵。”这个时节挑担辛苦,异于平常。山间石砌路光滑,不能稍有闪失。
阿昌和阿贵他们趁大雨停歇的间隙,一路奔走如风,将盐包从石市挑到了河头城。盐行检货的,是一个洋派后生,见到阿昌,就说:“你就系昌哥?”阿昌点头称是。洋派后生就让他挑来的牛头包先过秤了,还破例递给了他一根香烟。
天晚收工,阿昌和阿贵分享了那根洋烟。阿贵猛吸了三五口,说:“呸!怪味,跟俺村金丝烟比,差远啦。”
阿昌再忙再累,次日一大早,总要挑担热茶上甘露亭。甘露亭在村外的半山腰处。路人上岭下坡困倦了,多在此地歇脚。
来到甘露亭,阿昌惊讶地发现,茶缸不见了。哪只死贼牯啊。上百年的大茶缸,也算是古董了。怪就怪自家粗心大意哦。这一天,阿昌没有出工,买来了新茶缸补上。第三天,他挑茶上山,更为吃惊,新茶缸被砸烂了。当第三口茶缸被砸烂时,阿昌忍无可忍了。施茶行善积德,与人无怨无仇,恶人是谁呢?阿昌发誓要抓住他,游街示众。
就在阿昌频繁而痛苦地更换茶缸的同时,村子里风传来了绒家。绒家半夜闯入村庄,咬死了三头肥猪、两条看家狗和数十只鸡鸭。张三哥生媚的花衣裳晾在屋外,也被偷走啦。甘露亭打烂茶缸的,不是绒家又会是谁呢?
旧时,闽粤赣边崇山峻岭之间,活跃着一种大型的类人猿动物,浑身长毛,体格强壮且奔走如飞。传说,绒家神出鬼没,喜欢掳掠上山砍柴的妇女交媾。好些年头了,过山的乡民双手都套有竹筒。绒家突然出现,则紧紧抓住行人的双手仰天哈哈大笑。乡民趁机抽出双手逃逸。绒家,或说为野人,或说是山魈,是一个恐怖的传说。提及绒家,哇哇哭闹的孩童,立即吓得乖乖收声。
这天早上,阿昌又扛着一口新茶缸上山了。茶缸里,藏有两把八斩刀。多年前,阿昌在三河坝救助了一位落难的咏春拳师。临别,咏春拳师赠送了这对八斩刀。八斩刀便于隐藏携带,威猛,锋利,削铁如泥。
阿昌放置好茶缸,藏匿了兵刃,又挑担去了。傍晚,伙伴们都回去了。阿昌破例在河头城吃了两大盘“肉甲哩”和三海碗牛筋丸,一抹嘴角,径奔甘露亭。
“十七十八,岭背剟鸭。”五月十七日夜晚,月亮在太阳落山后,花费了剟一头鸭的时辰,露出了东山。月光如水,群山朦胧,汀江隐隐约约,蜿蜒南去。
阿昌潜伏在茶亭西侧的草丛里,双手握刀,随时准备和传说中的绒家决一死战。
月过中天,西移,绒家始终无影无踪。阿昌悄悄返回,就在他猫着腰走出百来步的时候,他听到了茶亭里传来哗啦一声巨响。阿昌义愤填膺,提刀狂奔。不远处,他看到一个庞大的黑影从茶亭窜出,隐没山林深处。
茶缸又破了。阿昌再次扛来一口新的。白天,他还是和阿贵他们一起挑担。晚上,继续潜伏在荒山野岭。这次,他更换了方位。月出,移动,西落。就在月亮阴暗的一阵子,阿昌抽身下山。
噗哒哒,茶亭的瓦屋上爆起一阵奇怪的响声。
风吹树梢,野虫唧唧。
一团黑影闪入了茶亭,举起大石块,砸向茶缸。
一把刀,砍杀在石块上,迸射出一溜亮光。另一把刀直抵黑影胸膛。
“俺就晓得是你。为什么?”
黑影掀落野兽皮,扯下面罩,跺脚哭喊:“为什么?你都有,俺都没有。力气,你大;好名声,你的;舞狮子,你当头,俺当尾巴。连洋奴的一根臭烟,都要送给你吃。从小一块光屁股长大,凭什么好事都是你的?老天爷啊,你偏心眼哪!”
阿昌收刀,说:“俺看到的是绒家变身,你不是俺阿贵兄弟。”
九月半
大雨,倾盆大雨,闽粤赣边客家话所言竹篙雨,密密匝匝直插山坡。丰乐亭瓦片嘭嘭作响,一会儿工夫,茶亭的屋檐就挂起了一道断断续续的珠帘。
丰乐亭在汀江边。汀江流域多雨,是以该茶亭的楹联写道:“行路最难,试遥看雨暴风狂,少安毋躁;入乡不远,莫忙逐车驰马骤,且住为佳。”此联如老友相逢,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丰乐亭外,有一把棠棣树枝探入了窗内,一嘟噜一嘟噜的金黄棠棣,滚动水珠。
“棠棣子,酸吗?”说话的是一位壮年汉子,敞开黑毛浓密的胸膛,手持酒葫芦,蹲踞在一条板凳上,剥吃花生。他身后的墙壁上,靠着一大梆刀枪剑戟家伙什。看来,他是做把戏行走江湖的。
“没落霜,样般有甜?呆子的婿郎。”说话的是花白胡子老人,干瘦干瘦的,山下千家村人氏,几个儿子都在千里汀江上当排头师傅赚钱。老人闲不住,时常挑一些花生糖果来茶亭售卖。
他那花生是自制的,加配料水煮花生晒干,入陶罐拌石灰储藏多日,这就是糠酥花生了。张记糠酥花生是很有名的。客家茶亭,有人施茶,行人至此饥渴,解下数文,买来三二两糠酥花生配酒配茶喝,正好。
“老伯,您这糠酥花生地道,再来半斤!”汉子将最后一把花生壳碾碎,摊开手心,恰好吹来了一阵山风,粉末就纷纷扬扬飘出了茶亭之外。
竹篙雨稀落了下来,东两点、西三点的,淅淅沥沥。远处的山峰,有云雾往来。
丰乐亭外石砌路上,一行人匆匆忙忙地闯了进来,他们是打狮班的,为千家村的张禄贵老太爷八秩诞辰祝寿,赢得了满堂彩。几封银子的赏钱,使他们难以抑制兴奋,他们不顾乌云密布,执意要当日返回枫岭寨。
半途,大雨就来了。闽西山地多草寮,他们齐齐窝在一个路边山寮躲雨,伏着雨空子,猛跑一阵,就来到了这丰乐亭。
进得茶亭,他们一个个拳花撸天,大声嚷嚷,重复着舞狮夺魁的豪勇。有几个,还蹦跶着舞步,意犹未尽。
“花生,糠酥花生哦。”花白胡子拖腔拖调地叫卖。这群汉子咽着口水,捂紧口袋,竟然没有一个人过来“交关”。
“花生,糠酥花生哦。又香又脆的张记糠酥花生哦。”花白胡子又吆喝了一声。
就有一个汉子说话了:“老人家,您老就别吆喝了,俺们不是猴吃牯。”
花白胡子自讨没趣,悻悻然,道:“没有钱,就莫充好汉。”
汉子说:“好,好,俺们没有钱,不是好汉,可也不是猴吃牯哟。”说着,有意无意地摆弄着钱袋子,哗哗响。大家都呵呵笑了。
花白胡子的脸,当场就黑了下来,把头扭到了一边。那个做把戏的,也有些不高兴了,什么猴吃牯猴吃牯的,难听。
客家人把那些个贪吃而又不顾体面的人,叫做猴吃牯。比如,村落里头,谁家飘出了食物的香味,此人就会适时地出现在这一家门口,借故入内,分一杯羹。猴吃,乃像猴子一样贪吃。其后缀,牯,男性;嫲,女性。
做把戏的站了起来,虎背熊腰,天暗了大半。他好像有些醉意了,大声说:“什么猴吃猴吃的,不买,就行开去,莫耽误人家做生意。”
“噫?俺们又没有撩拨你,你出什么头?这又风又雨的,荒山野岭,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做什么生意?”汉子也不高兴了。
“俺也没有撩拨你们哪,你们人多,俺也打不过,乡里乡亲,没得打。就讲啊,俺老马刀可以把话撂在这里,单挑,你们的狮头增发,也搬不动俺这小半条腿。”做把戏的原来是闻名江广福三省的老马刀。他放出了狠话。
汉子说:“俺就是增发。”
老马刀说:“试试看?”
增发说:“俺不是牛,干嘛要相斗?”
老马刀又问:“搬得动吗?”
增发说:“搬不动。”
老马刀说:“没有试,怎么晓得?”
增发说:“还要试吗?你脚下的麻石都开裂了。”
老马刀说:“原本就是开裂的。”
增发说:“客气了,昨晡俺也试过。”
老马刀说:“得罪了!”
增发说:“还说不准谁得罪了谁。十年后,俺来找你。”
老马刀说:“九月半,俺不走,三河坝等你来。”
雨停歇了。增发一招手,兄弟们鱼贯而出,很快消失在山坳边。
花白胡子下山,就把丰乐亭的故事讲开了,免不得添油加醋。他说,增发上前抱住了老马刀的大腿,老马刀一发力,增发就飞了出去,还摔断了两颗门牙。巧的是,那日山路湿滑,增发摔了一跤,刚好跌坏了两颗门牙。增发那是百口莫辩啊。
这十年,增发时常忍受着人前人后的指指点点,辛苦做工,厚脸过活。有人说,他拜了癞痢僧人为师,苦练一种常人忍受不了的功夫。可是,谁也没有见他露过一手半手的。增发变了,正月大头的狮子庙会也不凑热闹了。他沉默寡言,看上去有些呆。
这一天,是第十年的九月十三日,增发从上杭县城搭船下行百八十里,抵达河头城。河头城下行,沿棉花滩岸上过,到茶阳,再有半日行程,就是三河坝了。
增发在河头城街上行走,过木纲行,门前大石狮突然倾倒,增发飞起一脚,将大石狮踢回原处,位置分毫不差。其快如闪电,门子疑在梦中。
还是有人看出了名堂,增发功夫了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三河坝。有人就劝老马刀外出躲一躲,老马刀断然谢绝。徒弟们群情激昂,要拼了。老马刀摆摆手,叫他们都退下,没事,自有办法。
九月半,是决斗的日子。九月半,诸事不宜。
这日早上,老马刀独自一人在汇城东南角的一个老旧庭院里,生火熬稀饭。稻米在砂锅里翻腾着,清香四溢。老马刀忍不住一阵咳嗽,浓痰中夹杂血块。前年赣州圩场比武,伤了人,自家也落下了内症。他突然感到很孤独,很悲伤,很失落。他有些艰难地站了起来。这时,他看到了一个人,他等了十年的人。
增发右手握刀,左手提大包裹。
老马刀说:“来了。”
增发说:“来了。”
老马刀说:“晓得你一定会来的。”
增发说:“俺一天也没有忘记你。”
老马刀说:“是你的,就该还给你。”
增发放下大包裹:“这是你的。”
老马刀疑惑不解:“脉介(什么)?”
增发说:“利息。”
老马刀低头打开包裹,是梁野山金线莲。他想说些什么,却说不出来,呆呆地望着增发的背影慢慢消失在汇城墙角拐弯的地方。
责任编辑 林东涵
练建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现任职于冰心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