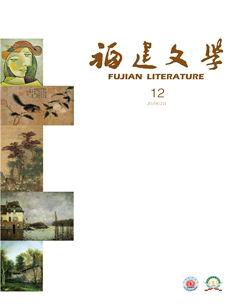一个人的村庄
钟红英
一
到景宁,是在夜里。
也似乎只有夜,才能够足以抵达心中对畲族先人的想象。他们是宁静朴素的,不杂一丝邪念的,纯洁得就像现在景宁静谧无声的夜。
也未必完全是准确的。自从进入景宁县城,这一路之上,除了我们一部车在浓荫的街巷滑行的声音外,分明还有湍急的水流声从身边清脆地响起。就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陌生,却不约而同在夜的黑中支起双耳、相互倾听对方的行动。
直到下榻山哈酒店,从霓虹灯闪烁的夜光中转醒,才突然明白,这一路如影随形的水,便是赫赫有名的鹤溪水了;也才与人不经意的交谈中醒悟,何以一座城的夜能如此宁静,只因至今,它穿行于街头巷尾最多的,是人力车,除了人力车。
心中蓦然升腾起一种感动,恍惚我果真来到了前世的鹤溪,那几百年前我的畲族先人从福建迁徙而来,在景宁最先落地生根的所在。
二
已很难想象我的畲族先人是如何“食尽一山则它徙”来到鹤溪的,这一年,有较明确史志记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那时的鹤溪有着与它的名字相称的外部形貌,它天然、美丽、悠远、宁静,还有一丝神秘的仙气散逸其间。卵石、土墙、木架围砌的山寨散落在溪畔山野间,日出日落的人们除山歌之外,都在口耳相传着一些来自先祖的先祖留下的故事,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将故事的真相讲述得清楚,就像那个传说中的汉代隐士浮丘伯,在土墙瓦寮下聊着说着的人们,有谁会去在意他是秦汉年间从旧儒学到新儒学发展历史中发挥着承前启后关键作用的大人物呢?又有谁会去想象,当年他曾当着朝中群臣的面,痛斥秦始皇“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而令秦始皇口舌无词呢?说到底,浮丘伯他只是一介隐士,抑或本身便是神仙呢,他从东海翩翩而来,与他左右相伴的还有两只神鹤。这是多么适合汉初崇尚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人生境界的一处胜地呀:四野青山环绕,林木何其葱郁,有清泉从敕木山汩汩而来,向西北汇而成溪,又将此山坳平畴处切割为南北两片,果然“两山夹一水,众壑闹飞流”之奇峰秀逸之所啊!既然有仙鹤沐于溪流,那就叫溪为鹤溪吧;既然有了鹤溪,那就以溪为名,不妨就将此地命名为鹤溪村吧!
古老的故事一直就这样传说着,直到明万历年间我的畲族先人的到来,才让鹤溪从汉之仙境归于人寰之喧卑:
他为雷进裕。是年,灾荒连连。雷太祖进裕公万般无奈,挑起祖担,携同四个儿子从福建罗源出发,踏上时为艰难的迁徙之路。已是第多少次这样说走就走的日子了?雷太祖显然不太在意,身上流淌的畲族血脉告诉他,当一个地方的土地贫瘠不足以再耕种,当这个地方官府的赋税沉重到不堪以负担,便是“只望青山而去”的离日了:“自耕林土无粮纳,做得何食是清闲。山上人多难作良……走出山头受苦辛”。
于是除农具之外,在祖担之内慎重地装进宗房支系的祖宗香炉、祖图、祖杖和族谱等。祖图是从龙麒出生、平番、受封、招亲、生育三子一女,到辞官、打猎殉身等彩绘成连环画的长轴画卷,它是畲家人的灵魂呀,无论身处何方,有了祖图便就有了自己的根;祖杖亦是畲族人的圣物呀,自从一根原木在法师的手里被雕刻成龙头,饰以金箔,垩以朱漆,系上一层层代表传师学师的红布,它便成为畲民心中一个无比圣洁的图腾了。
就是带着这样的情感这样的信念,雷进裕携同四个儿子踏上了前往浙江的道路。出发的时辰和往去的方向,他该有过卜卦的,只是他从罗源一路循着弯弯的古驿道终于到达浙江省境时,是否也曾有过预知,他将路遇一个和尚,并与他结下深厚的情谊,从此一再被后世子孙提起呢?
故事又是这样一代代传说下来的呀:他与和尚一路同行到了浙江,分手后,雷太祖在景宁一个叫大赤坑的荒凉深山坞里搭起了茅棚,父子五人靠垦荒种地度日。后来豪强侵占了他的土地,把他全家赶下了山,只好到处流浪。恰有一天,他们在鹤溪流浪拾荒的时候,不期然与和尚相遇了,和尚非常同情雷太祖,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寺院中,这个寺院,雄踞在敕木山的山腰之上,它在今天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惠明寺。
三
我在惠明寺前徘徊良久。寺门紧闭。空容无音。烈日下,高高的山墙与屋脊之上,正倾泻下一片耀眼的明黄,与四野层层茶林的碧绿相映,衬出油画般的景。《景宁县志》说,该寺建于唐咸通二年即公元861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那时寺院的规模大概也是不大的,一座观音,一个僧人,一口铁钟,两座香炉,便构成了寺院生活的全部,千余年来,它们与门前弯曲的石道、破落的残墙一道,几经起落,却始终未能阻断当地畲民对开山始祖惠明和尚的想象。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心中亦一度固执地认为,他或便是明万历年间,与雷太祖一同从罗源过来的那位和尚?岁月更替,几经变迁,几百年的时空在当地畲民心中似有若无,他们把这个和尚混名为惠明和尚,心中唯一牵系唯一感念的,是先人雷太祖在和尚的帮助下,从此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并由此惠及一座山、及山之四野零星散落的村庄。
故事就是这样串联起来的。确切地说,自从雷太祖来到这儿,和尚心中便多了一份牵挂。当漫山吐绿,雾岚飘渺的春天终于来到山门的时候,他抖抖索索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红布包,小心翼翼地揭开,出现在眼前的是他从福建带来的唯剩的三粒小小的白茶籽。他慎重地把茶籽撒在了敕木山的山腰上,并亲自教导雷太祖一家亦在敕木山上种植白茶,烘焙茶叶,由是便有了这一树一树漫山漫坡的茶——人们便又因寺而名,称它为惠明茶。
一座山最初只有一个人,一座庙,日子久了,又加了一个家,于是人气便开始旺了起来。便又多了一些草寮,便又多了一些茶园,便在茶园与茶园之间,又有了此起彼落的山歌。油坊、豆腐坊、织布坊、染坊、银匠铺、铁匠铺……,在这个山落出现,又在那个山坳散布,于是村庄就有了越来越浓厚的人间烟火的气息,于是漫长的历史就有了越来越丰润的细节。蓝姓、雷姓、钟姓,他们一些从福建而来,一些从江西而来,还有一些从广东而来,最后都聚集在了这座名叫敕木山的山麓田野间,惠民寺、敕木山、周湖、东弄、双后岗、旱塔……,“大分散,小聚集”的畲族村落分布格局,再次在浙江这块丰饶的土地,散发出勃勃的生气。
四
作为一个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畲族从未远离过大山的怀抱,这是始祖忠勇王为畲族子孙划下的一个“圈”呀,千百年来,不管迁居何处,它始终是山哈子孙的衣食所在和精神皈依。他们是这样敬重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呀,每当炊烟在这片山坳成为一个日起日落的温暖的存在,每当鸡鸭成群在房前屋后欢快地叽叽喳喳叫唤,他们便会请来风水先生,在村子的吉地立起一座自己族氏的祠堂,同时虔诚地在村子水口的某一处“请”来自己的土地公神,一年四季,从此香火不断。他们都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呀,祠堂内的先人既是祖先,亦是家神;土地公神上管风调雨顺,下管人畜平安,五谷丰登。唯如此,当一座祠堂、一座小庙在这个村寨立了起来,畲族人漂泊不定的心,才算真正安定了下来。
我不知道敕木山是如何成为畲族人心中的另一座“圣山”的,他们都称它是畲族的“小凤凰山”。那座矗立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是畲族的祖山呀,山上有畲族人共同的祖祠和祖墓。《高皇歌》是这样告诉世世代代畲族子孙的:当初高辛帝依从忠勇王的心愿,把他与三公主送到了凤凰大山宫中。山里的田场是多么肥沃啊,山上的鸟兽又是何其多啊!勤劳勇猛的忠勇王在农闲时节,最爱上山去打猎了,他祭拜过畲族的猎神,带上心爱的弓弩,大踏步走进了凤凰山的深山茂林中。在山顶,他与一只大山羊遭遇,在追杀的过程中,忠勇王不幸被山羊角顶撞,跌落下山崖,高高挂在了一棵大树上……
这是一个惨烈的关于畲族先祖忠勇王的死亡记忆。从此,畲族人把凤凰山当成自己的开山祖地,同时也把凤凰山当作畲族人灵魂的最终归宿地。
而敕木山——这座高高耸立在浙江景宁县域的大山,它同样是这一方土地畲族人的精神归宿地。从一个人、一个家,一座村庄,到现今浙江省境近20万的畲族人口,几百年来,畲族子孙绵延不尽的血脉之河在这里得到丰润的滋长,仍至逐渐壮大起来的畲族,为感念雷太祖进裕公开山立业的祖功,亦将他长子的座像,高高供奉在了敕木山腰惠明寺的神坛之上。
这是一个对先祖深怀感恩的民族,也是对赐予高山、良田,并给予五谷丰收的山神深怀敬意的民族。同治朝《景宁县志》是这样记载这座畲民心中的“小凤凰山”的,曰:“敕木山,县东南十里,高接云霄,为邑之镇山,远望可数百里。”其冬景之“敕峦霁雪”,时人叹为观止,赞“云宿必雨,土人常以占候,至新雨初霁,半山云雾翕然而起,隆冬积雪经月不散,尤为奇观”;而敕峦峰顶更有“直可低头看落日,真堪垂手数飞鸿”之奇景。
那么这是一个有意为之的选址?还是潜意识的文化遗传密码让畲族先人带上了祖地“凤凰山”的记忆而作的选择?无数个日子,散落在大山里的畲族先人,面对莽莽林海和层层叠叠的梯田,想起一年四季的辛苦劳作,口里心里念着的,都是对于这座大山的深深敬畏与感恩。于是,他们在敕木山顶建造起了一座自己心中的神庙——汤夫人庙,于是,他们在村口的山脚立起了自己的土地公神——汤三公庙,庙里供奉着只有刀耕火种的民族才能深深体悟的带有强烈农耕色彩的神祇汤夫人和她的父亲汤三公,他们是环敕木山畲族村庄保护神呵!听说,每到冬季,春节来临之际,敕木山上都会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这些庙宇矗立在皑皑白雪中,一片圣光,默默地护佑山脚下那些静静的村庄。
五
我常想,一个人与一个人村庄的缘分,是要有缘起的。就像我来到敕木山村,多半是因为民国年间同济大学生理学教授、德国学者哈·史图博(H.Stiibei)的提醒。
1885年,如果生命能够足够地延续,史图博该130岁了。他是有一点仙风道骨之气的:身材壮实,个儿高高,须髯飘飘。他喜欢穿中式长袍,也喜欢穿农人手编的布鞋,就是口里说着的普通话,也与农人一样,多少显得有点儿蹩脚。但他却永远显得那样阳光、健朗,无论走到哪里,遇见老乡就远远地打招呼,一有空儿,就钻进老乡家里神侃,若是刚好在吃饭的当儿,也便遇见什么吃什么了,一点儿也不见外,难怪住在敕木山的6天6夜内,他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素材,写下堪称畲族文化研究历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
《景宁畲族自治县志》如此记载:“民国18年(1929)夏,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上海同济大学教师李化民到景宁畲乡考察,撰写了《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对景宁畲族的族称、姓氏、风土人情等作了介绍,也是研究民族学的史料。”
这条记录十分简要,但我的整个敕木山之行,却是携同史图博和他的调查记一起前来的。敕木山村高高驻扎在大山的山腰之上。
已无法完全复原史图博当年所见之景。“道路是陡峭的,几乎像阶梯那样上升,偶尔形成盘旋的山路。路面规则地铺着大块光滑鹅卵石,专供徒步者往来之用。”而我来到这儿时,虽村道陡峭依旧,却有平整而干净的石板路贯通全村;那些低矮的泥屋也依然稀稀落落散布在悬崖峭壁之上,但可以明显看到,一些墙面新抹上了统一的白灰,一些围墙之上,还装饰上了畲族特色鲜明的绚丽彩带。
我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找到了那座老宅——当年留宿了史图博6天6夜的蓝日成村长的家。
1929年,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中国内战频乃,世界亦不太平。年末,一场发生在闽西上杭的“古田会议”曾经是那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未来时局;而始发于美国,进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又从此让全球进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然如此时局,对一个深处浙江南部深山老林里的畲族小山村来说,它的影响却远不如一个外国人的意外闯进引起的骚动来得巨大:“这个居住地的住户在外人面前特别胆怯。他一走近,妇女和孩子便突然消失了,只是偶然会见到一个好奇而胆怯的男人站在角落里或走道旁,假装在干什么活,以此作为一种借口,以便能在一旁不受阻挡地观察这位罕见的客人。”
敕木山的畲民几乎没有走出过大山,他们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来自于这座大山赐予的恩泽,即便偶尔要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也仅与汉人做些十分原始的以货换货的交易。因此,当史图博出现在村民面前时,他们显然深感意外而又羞怯好奇。两年后的1931年,史图博曾以类似的方式“闯”进海南岛探寻“黎族原生态图”,并出版了他著名的《海南岛民族志》,透过他的文字,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在少数民族村庄遭遇的麻烦、尴尬甚至“仓皇出逃”的狼狈,比如汉族向导为了让当地少数民族能够接受这位红头发白脸庞勾鼻子的域外来客,对他们声称史图博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外国国王,甚至经常不得不“被医生”给当地患流行疾病的村民看病;更多的时候,因着少数民族对外来陌生人的恐惧心情与警惕心理,他还被当作会使妖术能把村子的“宝物”带走的神职人员而被驱逐出村。
在敕木山村,史图博显然有过类似的遭遇,尤其对于畲族视为“宝物”的祖图,他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得到;而关于畲族的先祖“盘瓠”的故事,他更是在汉族向导的严格禁止下几次欲言又止。幸而村长蓝日成热情地接纳了他,用畲族人对待贵宾的礼仪来安排好他在村里的一切的方便,才有了后来对畲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调查记的产生,也才有了如今作为敕木山畲族文化印记的百年老宅留在了村子里。
从史图博的文字来看,显然,蓝村长家这座大院居住着不止村长一家,他的大哥和大侄子也住在这里,还有从外村请来的泥瓦匠,这会再加上史图博和李化民,宅院顿时热闹了起来。
史图博喜欢这样的热闹,他很开心地品味村长为他精心准备的一日三餐,也很“享受”地喝了畲民自酿的黄酒,还饶有兴致地观察村民们来家闲聊的一应举止,他发现在畲民中间,村长与占卜者、驱邪者、教师和在祭祖仪式中献过祭品的人以及出过远门的手艺人,都是受人尊敬的体面人,因此,只要是他们中的哪一个人进来,村长都会热情地向他们敬烟敬酒,并都十分自觉地把上座让给体面人坐。
余时,在家里的大多数时间,史图博都会细心地观察、静静地思考家中其他一应的细节。他发现,这家院子四周走道屋顶的那些木柱子,都雕有精细的图案花纹,这是要汉族大户人家才有这样的实力来装饰这样一幢房子的呵。现在这些图案花纹仍然清晰地保存着,除了汉族人家常见的吉祥鸟兽和四季花卉外,一些如凤凰、麒麟的雕刻明显带着畲族人独特的图腾信仰痕迹。
还有一些史图博记录下来的东西,曾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如那盏“可以反映西方文明已深入到中国内部角落里的极少数事物中的一种”的煤油挂灯、旧时畲族人用来作室内照明用及室外当火把用的老式火篾、挂在房门前据说可以带来幸福的五色布块,以及那个放在屋顶上据说具有保护房屋免受风灾的两把锄头,现在,它们都不见了踪影。
但史图博所说的汉式炉灶、炉灶边上从悬崖上流下的汩汩清泉,以及通往楼上的木楼梯仍在。我在楼梯口将头探进他当年住的客房,它是真小呢,窄窄的,黑乎乎的,几乎看不到任何光线,至于当年村长为他准备的用木板和稻草布置的简陋床铺,现在也都不见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厅堂楼上的后壁之上,史图博当年所见之畲家祖先神位仍在,神位上题写着畲族独特的“题词”,中间是“癸本家奉祀香火汝南郡历代宗亲位”,左右各有一列“日时进宝郎君”和“年月招财童子”字样。
据说院子左边一侧的房间曾经很久一段时间倒塌在那里,直到近年才重新修建了起来。它是村长自己的房间?还是他大哥曾经的住宅?当我独自一人站在这个祖先神位面前时,一位畲族风水先生的身影总在脑中挥之不去——他是村长的大哥。是的,在史图博的文字里,我已无法去揣测这位风水先生曾经有过怎样的人生变故,只知道在某种因素的作用下,他把自己的村长位置让给了弟弟蓝日成,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也过继给了没有子女的弟弟,然后弟弟再把他的女婿招上门来,当作自己的儿子,从此,弟弟一家热闹了起来,哥哥一家则慢慢清落了下去。
也许畲族对于同宗血亲之间的关系原本就是这样,能够将收养的孩子视同己出,何况他们还是一对亲兄弟;也许哥哥更多的是受了“神”的旨意,从此一门心思把精力投放在了“仙道”之上?似乎他是决意了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宗教的,“他在自己家里设了个小小的祭台,供奉阿弥陀佛小塑像,一有空便在祭台前烧香念经。据说有一次他在梦里见到敕木山的山门自行打开了,山的内部挤满了神的塑像,那时他就明白了,他已被召唤去做一名隐士,于是他就在敕木山山坡的高处盖了一个小小的茅舍,有时到那里去退隐几个月。”
如今,在蓝村长家的祖先神位上,应该有他的一个神位罢?
想着出神的当儿,我听到有山歌从院子后面的敕木山深处响起,这是畲族人的祖歌呵,苍凉、厚重,说尽畲族辗转迁徙的沧桑与无奈:
“当初出朝在广东,盘蓝雷钟共祖宗……福建官差欺侮多,搬掌景宁和云和,景宁云和浙江管,也是掌在山头多。景宁云和来开基,官府合老也来欺,又搬泰顺平阳掌,丽水宣平也搬去。蓝雷钟姓分遂昌,松阳也是好田场,龙游兰溪都可掌,大细男女都安康。盘蓝雷钟一宗亲,都是广东一路人,今下分出各县掌,何事照顾莫退身……”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