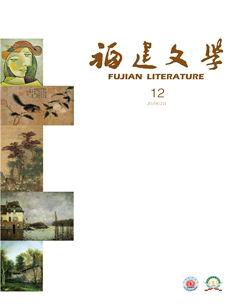原色的牧歌
云鼎
一
普罗旺斯显然是色彩的故都,行走其间,看到的色彩有的单纯明亮,有的优雅沉静,有的繁复厚重,使得无数艺术家为此如醉如痴。
或许是高大的阿尔卑斯山脉挡住了北来的浮尘,或许是地中海蒸腾的水雾滋润了山野,也或是通透的阳光晒出了万物的本色,所以,不论是海水、花田,还是山脉、村舍,所有物体的色彩,无不纯净润泽、纤尘不染,又自然晕化,组成了一部部色彩交响曲,无论你心中如何地烦烦扰扰,来到此地,会感到目不暇给,神清气爽,定会被这里清新的原色所浸染,想坐,想卧,想做一次长长的深呼吸。
普罗旺斯曾经是罗马帝国贵族们的休闲地,被称为“骑士之都”。虽然这一块膏腴之地多逢战乱、几易其主,乡野之间始终保持着宁静、纯朴的风格。正是普罗旺斯的明亮而丰富的色彩,大大激荡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的灵感,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塞尚、梵高、莫奈、毕加索、马蒂斯、夏加尔等人,均在普罗旺斯展开艺术生命的新篇章。随着英国人彼得·梅尔的《山居岁月》一书的问世,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个幽静而色彩丰富的地方。
二
蓝色,无疑是普罗旺斯的长笛,明净而优雅。
从热那亚西行不久便进入普罗旺斯,车子在山地穿行,时而涵洞时而桥梁,山色俊美,林木葱茏,偶有米墙红瓦的村落隐现于半山或空谷之间,地中海则像帘珑背后的美人,时不时露出令人惊艳的脸庞。当车子爬上高坡,你不禁会倒抽一口凉气:地中海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蓝得让人心醉;海的蓝与高天的蓝幻化在一起,若不是几朵轻盈的白云,谁也难以分清哪里是蓝天、哪里是大海,使人陡增贴近大海的期待。
尼斯,无疑是欣赏地中海最好的地方。站在尼斯海滨城堡公园的小山上看地中海,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蔚蓝海岸”。 细看蓝海由近而远,蓝色渐次深沉,直至海天一色。天使湾像一个半弯的月牙,环抱着这片大海。没有浩瀚的波涛,没有过往的巨轮,飞艇在海水里划出的几缕白浪,蓝天上鲜艳的彩色气球,更衬托出海的碧蓝纯净。海岸上两行高大的棕榈树隔开英国人大道和滨海步道,数公里的海滩上尽是享受阳光的半裸胴体。
有人问,为什么尼斯天使湾的海水特别的蓝?
那是因为这里出了一个克莱因。这个二十世纪最为独特的现代艺术家,发明了一种蓝色颜料,被他自己命名为“克莱因蓝”,并申请了专利。那天,他将一瓶“克莱因蓝”郑重地倒进地中海,并当众宣布,从此以后地中海比大西洋更蓝!
克莱因认为,“克莱因蓝”是这个世界上理想的蓝、绝对的蓝,其明净空旷,往往使人迷失其中。
克莱因的父亲是具象画家,而母亲却是个抽象画家,父母的基因共同创造出了这个另类艺术家。少年时代的克莱因常常与三个同伴一起,整天睡在天使湾海滩上晒太阳。三个人在这里瓜分了世界:阿尔曼选择了陆地,帕斯卡尔选择了空气,克莱因则选择了大海和天空,并在蓝天的一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认为,空气、海水和天空都是蓝色,是深度和无限极,是自由和生命,蓝,是宇宙中最本质的颜色。
为此,他极力推崇蓝色单色画。他认为一幅画的质量不仅仅是丰富的色彩,画的美感存在于它的视觉之外——这与印象派画家的观点何其相似。他还在巴黎当代艺术画廊创作了一个名为《蓝色时代的人体测量》的表演艺术作品,请来三个美丽的裸体女模特儿,在她们身上涂上深浅不同的“克莱因蓝”,然后让她们在地面的画布上翻滚拖拉,或在墙上的画布上贴靠按压,将身体形态和姿势的痕迹留在画布上。同时,邀请交响乐队为这些蓝色的美女们伴奏,交响乐演奏家们演奏克莱因自己创作的《单调交响曲》,这个交响曲由单独一个音符持续演奏十分钟,然后,留下十分钟的沉默,如此交替而成。单调的交响乐与单色的蓝精灵们共同表演,时空、影像、画作形成了一个蓝调的世界。此举一时间在世界艺术界传为美谈。
克莱因以独特的表现形式,诠释了他对地中海、对蓝色的挚爱。
三
普罗旺斯的黄色, 更像嘹亮的小号,壮丽而高远。
不论是山野和平畴,八月的普罗旺斯遍地都是盛开的向日葵。一行行、一块块,从平地蔓延到山坡上,抬眼望去,金灿灿一片,让人目眩心动。这时的向日葵已近成熟的季节,不论太阳如何转动,它都只把脸朝向东方,全不像青涩时期的“小圆盘儿”,时时刻刻把脸庞朝着太阳。
普罗旺斯的阳光十分鲜亮,花田的葵黄在阳光照耀下,知觉度却大大降低,一点也不刺眼,更没有给人烦躁之感,倒显得十分的温馨,让人心境辽阔旷远。站在花田下,黄色成了这里的主角,而那些谷地和山巅上的翠绿山林,那些开得蓬蓬勃勃、色彩缤纷的花草倒成了配角。
其实,人们认识普罗旺斯的向日葵是从梵高开始的。
这位印象派艺术巨匠在普罗旺斯生活了将近两年,这期间正是梵高创作的鼎盛时期。在这里,他被普罗旺斯明媚的阳光和遍地温暖的葵花所感染,创作了二百多幅以向日葵为题材的油画。其中,《向日葵》成为梵高的代表作。
他从二十七岁开始学画画,到三十七岁自杀,短短十年间画了八百幅油画、九百幅素描。然而,在他有生之年只卖出过一幅画,而在他死后,画作价格不断飙升,一幅小不盈尺的油画,售价竟然高达数千万美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个荷兰牧师的子弟,在短短的三十七年生命里,穷困潦倒、爱情伤怀、心中苦闷、一生坎坷,最终走向自杀。
他十六岁时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尤金妮亚,被其拒绝;二十八岁时又爱上了寡居的表姐凯,再次被拒绝。当他把所有精力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绘画时,梵高认识了曾做过妓女的克里斯蒂娜,逐渐产生了感情。克里斯蒂娜每天下班之后,就给梵高当模特儿,为他做菜、烧饭、洗衣服。这些举动让梵高体会到家的温暖,两个需要互相安慰的人同居了。对梵高而言,克里斯蒂娜有着令人崇敬的品质,和克里斯蒂娜在一起,使他增加了生活和事业的信心。梵高不希望只把克里斯蒂娜当作情妇,他要和她结婚,建立一个和睦幸福的家。于是,二人义无反顾地决定:当梵高每月能赚到一百五十法郎时就结婚。克里斯蒂娜当妓女时把身体弄垮了,虚弱的身子需要大量的营养品。然而,对绘画近乎痴迷的梵高,始终没有挣够每月一百五十法郎,却把微薄收入都花在了买颜料和雇模特上,这一切使克里斯蒂娜心疼不已,两人的矛盾日渐加深。梵高不得不结束第三次爱情。
梵高的爱情经历是悲剧式的,这与毕加索三次婚姻、数十个情妇的花团锦簇的爱情生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令人不得不抱怨上帝的不公。
经历了数次情感的波折,梵高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刺激,以至于狂躁不安、精神失常。于是,在朋友们的推荐下,他来到了阳光饱和的普罗旺斯,希望这里温暖的阳光能晒掉他心底的阴郁。
梵高一下子爱上了这个金灿灿的世界,于是,他用极大的热情和超人的勤奋描绘这里的的景色和风物。《星空》、《在阿尔的卧室》、《夜晚的咖啡馆》、《圣雷米》、《麦田里的乌鸦》等名作应运而生。
梵高在油画里使用最多的是黄色调子,他对黄色似乎情有独钟,即使他笔下的夜空,也有大块的橘黄色。这种黄色调子与他忧郁的心境和坎坷困顿的人生似乎相去甚远,以常人的理解,心理有创伤的人,作品的调子也是灰暗的。而梵高却不同,生活虽然给了他许多痛苦,他的内心却是炽热的,他的画作是明快的,色彩是动感的。
他曾说,“我越是年老丑陋、令人讨厌、贫病交加,越要用鲜艳华丽、精心设计的色彩,为自己雪耻……”
他喜欢画向日葵,与他欣赏葵花的向阳是分不开的。他崇拜太阳,因为太阳是一切色彩的本源,没有太阳就没有色彩;他崇拜黄颜色,因为黄色最能表现出太阳的明亮和温暖,代表着希望和未来。在他眼里,向日葵是不同寻常的花朵,是太阳的忠臣,是光和热的象征,是他内心翻腾的感情烈火的写照。
热爱温暖却屡遭冷遇,热爱阳光却贫寒灰暗,梵高是那个时代的矛盾复合体。
所以,他的精神才屡屡崩溃,以至于拿起刀片,追杀好友高更未遂,却割掉自己的耳朵,送给自己所爱的妓女。
他说:我把自己的心灵与魂魄融入了绘画,结果丧失了理智。
他不仅喜爱向日葵的黄,对一切黄色都非常迷恋,那一望无际的成熟的麦田,那落日余晖里的村庄和城堡,那金色迷离的晚秋,都留下了梵高的浓情蜜意。
他曾说,我喜欢漫无边际的大海,因为它与蔚蓝色的天空合二为一,形成海天的壮阔。巧的是离海边有一块看不到边际的金黄色的麦田,我想这就是现实和浪漫的比较,海天固然壮阔,但没有麦田的随和……金色的麦田在海风的抚慰下变得让人感到欣慰,我要把它画在纸上留在人间……
还是让我们再看看他的《向日葵》吧。这是一幅黄色调子的静物画,画面上十几朵向日葵或昂首,或低头,或弯腰,形态各异。这些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田野的葵花瓣,却被无情地折断插在花瓶里,失去了扎根的土壤,美好的阳光也晒不活它,它只能渐渐地走向枯萎。
花瓶中的每一朵向日葵似乎都在经受着无望痛苦的折磨,这一个个即将枯萎的生命之花,分明就是画家本人生活窘境的真实写照。画家在描绘它时该作何感想?原来自然界也有许多不公,那本是可以在灿烂的阳光中顺利走完一生的葵花,却无端地死在花瓶里。画家似乎是以此来安慰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
梵高用非常阳光的黄色调子,掩盖了自己的灰暗人生。
四
在普罗旺斯色彩的牧歌中,紫色的薰衣草无疑扮演了低音萨克斯的角色,宁静、温婉、雅致、高尚,像在欣赏一场雅尼音乐会。
罗曼·罗兰说:法国是因为薰衣草而浪漫。
其实,法国有四大浪漫元素,香水、红酒、服装、薰衣草。而普罗旺斯就占了两大元素:香水和薰衣草。
来到普罗旺斯,最吸引人的色彩当然是温文尔雅的紫色薰衣草,它几乎成了普罗旺斯的代名词。不论是谷地还是山坡,随处可见的是大片的紫色花田;有时这些紫色花田与葵黄的花田相比邻,一亮一暗、一暖一冷,一阳刚一温柔,使普罗旺斯更显得多姿多彩。未及走进紫色花田,一缕缕似有似无、淡淡的幽香随风而来,疑似美人在侧,不觉左顾右盼起来。
香水之都格拉斯,不仅田野里尽是紫色花田,就连小城的道路旁,高高的窗台上,精致的小院落,随处可见薰衣草的倩影。在小城里行走,简直就是在香雾里沐浴,那些衣着时尚的女郎从你身旁飘过,留下一阵浓烈的雅香,久久不愿散去。
小城依山而建,面朝大海。地中海的潮湿温暖的海风,一年四季都吹拂着格拉斯,再加上充足而明媚的阳光,自然孕育出了这片鲜花生长的乐土。山坡上的花田里,不仅有紫色的薰衣草,而且有玫瑰花、金合欢、茉莉花等,成了取之不尽的芬芳源泉。格拉斯理所当然地成了香水之都,成了法国香水的原产地,占据着全法百分之八十的市场,兰蔻、CD、香奈儿等多种名牌香水都是产自这里。
晚上,格拉斯旅馆的经理特意交代,诸位尽可开窗睡觉,让那馥郁的香味来到你的枕边,一定会有一个好梦在等待着你。
身处紫色的田野里,被馥郁的幽香所包围,再平凡的人也自觉高尚起来,再浮躁的人也会沉静下来,这就是薰衣草的魅力所在。
离格拉斯不远的圣保罗·德旺斯也是一座小山城,孤悬于高高山顶上,四周都是深不可测的山谷和森林,只有一条窄窄的山路通向城堡。站在城头望去,周围群山环抱,林木蕴秀,透过南面绵延的山岭,可以望见蔚蓝色的地中海。在北面的山岭上,一重重紫色的薰衣草花田铺在缓坡上。
小城被石头城墙包围着,城墙内侧的小路正好环绕小镇一圈。因为它太小,与其说它是小城不如说是一个小村更准确。在这个“鸟巢”般小城中心有一所建于十二世纪的圣保罗教堂,教堂的钟楼是古城的最高点。古城的街道如迷宫一样弯弯曲曲,厚重的石头建筑造型各异,依山就势,高低错落,散发着古朴的气息。
圣保罗·德旺斯还是名副其实的艺术殿堂。顺着曲折的街道行走,几乎每个门店经营的都是各种艺术品,青铜雕塑、木雕、剪纸、抽象画、水彩画、油画等等,在油画中最多的还是紫色的薰衣草油画。这里艺术品种类齐全,其前卫程度,不亚于大都会的现代艺术展览水平。流连其间,你绝不相信这只是一座深山小村。
小村从十九世纪开始名声慢慢大了起来,许多知名的画家来到这里不愿离去,安静地住下来,在这秀美的山村周边寻找灵感,有的甚至在此终老。毕加索曾频频光顾,马蒂斯在这里居住过五年,特别是夏加尔则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五年,一九八五年去世后,就安葬在圣保罗·德旺斯的公墓里,躺在一片紫色的薰衣草花丛中。
在圣保罗·德旺斯城门旁边,有一间紧靠山崖的饭店,入口处极其狭窄,似乎只是普通民宅,走进去却豁然开朗,露天的餐桌能容纳百人同时进餐,花园墙壁、游泳池畔和厅堂内有毕加索、米罗、夏加尔、布哈克以及其他伟大艺术家的创作真品。原来,当年这群艺术家们大都还没有成名,囊中羞涩的他们就跟饭店老板用画作交换吃喝。后来,画家们有的出了名,留下的作品已可以卖出天价,主人并没有把画作卖掉,而更希望人们认可他沙中捡金的眼光。
艺术家们为什么对这小小的山村情有独钟?他们不为别的,为的是寻找一份难得的宁静,因为宁静是艺术家最奢侈的享受;他们是为了这里遍地的花田,为了这些能让人沉静下来的紫色薰衣草。
不仅在德旺斯,在普罗旺斯任何一个地方行走,一不小心就踩在艺术大师们的脚印上。尼斯的马蒂斯、克莱因,圣雷米的梵高,埃克斯的塞尚,奥维纳格堡的毕加索等等,他们各具特色的传奇故事就是普罗旺斯的最大资本。
毕加索,这个二十世纪艺术界第一情圣,最早住在清净圣地戛纳。后来戛纳成了南法最喧嚣的地方,毕加索不堪其扰,搬到了维克多山上。这里是他最崇拜的老师、现代艺术之父塞尚出生并长眠之地。毕加索买下了塞尚的沃维那格城堡,并欣喜地告诉友人自己买下了老师“塞尚的山”,朋友以为他说的是塞尚的作品,便问他是哪一幅。他自豪地说:“原版!”毕加索一直居住在此,死后葬在维克多城堡——这里离老师塞尚的墓地很近。
当地人说,每当春夏之间,人们时常看见有两位老人赤足携手漫步于山野的紫色花田里,和煦的风吹拂着他们蓬松的白发,他们指指点点,时而互相争吵,时而互相搀扶,笑谈云天紫雾。他们的身边就盛开着一片片紫色的浪漫,点点碎碎的紫,缓缓汇成一道道紫色的河流。花田里穿着蓝裙的女人们在侍弄花畦,有轻轻的山歌和着芬芳依稀传来,偶尔飘来一朵白云悬浮在蔚蓝的天空,整个山脉染上了紫色的云霞。这是何等的浪漫诗意、何等宁静适闲、何等的神秘悠远的梦境?不是别的,是熏衣草点燃的童话故事,这个故事可以穿越时空,让后人深深地向往。
五
梅尔笔下迷人的山村在哪里?
只要你信步走去,在普罗旺斯的深山更深处随处可听可见。所有的色彩似乎都有了生命,都有了迷人的声音。那和着花香的微风的习习声,海边那规律而甜蜜的波浪声,树林鸟儿的嘀啾声,枝头叶子的沙沙声,田野里野兔和松鼠的索索声,峡谷和山峰的回应声,这些低回的单音调组合在一起,不是普罗旺斯的牧歌!
为什么这原色的普罗旺斯,会引燃那么多的艺术巨匠的超常灵感,留下了那么多常人难以读懂的现代艺术传世之作?
请听听他们的解释吧。
塞尚说:绘画不是追随自然,而是和自然平等地存在。
毕加索也十分坦诚地说,每次在街上看到孩子们在胡涂乱画,我都会停下脚步观看,孩子们的图画使人感到意外,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东西……所以艺术不是真理,艺术是谎言,然而这种谎言能教育我们去认识真理。
……
他们这些近乎哲学般的语言,只道出了一部分原因。然而,这些艺术主张与文学家的意识流,有异曲同工之妙。
走过普罗旺斯,我似乎明白了,是这里的原色和光影点燃了艺术家们的灵感。这里的色彩使人迷幻,这里的光影改变了人的直觉,潜意识的东西激荡、碰撞起来,或变成袅袅青烟,或变成魔幻的色块,或变成一片空白。于是,谎言和真理、平等和追随、抽象和真实,交融互换,使人迷幻起来,艺术家们的笔下自然流露出不同凡响的色彩。
在这原色和光影的牧歌里,常人对此尚且迷恋不已,何况那些艺术家们?他们自然乖乖地做了普罗旺斯的俘虏。
责任编辑 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