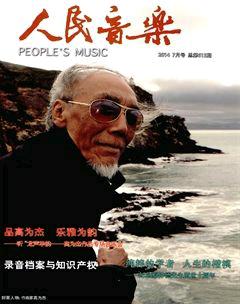博特乐图和他的《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
乔建中
我与玉成以师生关系来往,已逾十载矣!此一期间,我亲历了他从硕士到博士,从普通教师到教授,从青年学子到颇具影响的蒙古族音乐学者的成长过程。他的硕士论文《胡仁·乌力格尔概论》(2001)、博士论文《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2005)、他的《蒙古族经典民歌鉴赏》(蒙文,2007)、《安代词曲集成》(蒙文,2010年),他主持策划的“内蒙古民族音乐典藏·大师系列”(2010—)以及这篇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报告《表演、文本、语境、传承一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2008)、近三十篇文论、近一千五百个小时的音像资料等等,又清晰而分明地留下他求索进取的每一个足迹。《管子》云: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玉成通过这十年间的奋力拼搏,已经长成为一棵大家公认的研究蒙古族音乐文化的优质之材了。
然而,作为亲历者,我却深知其中的甘苦……
2001年秋,蒙古族音乐学家、我的学长扎木苏教授带着玉成来见我。老扎先介绍他此前的学业,再替他表明要继续研读博士的心意。他在一旁听,话不多。我当然给予肯定的回应,因为我完全相信扎木苏学长对他的所有评介,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此前有十余次到草原考察的经历。特别是1996年1月到过他的家乡一哲里木盟库伦旗,在那里采录过多位说书艺人表演的乌力格尔、故事民歌、安代舞等,当年夏天和后来,又在锡盟、阿盟、伊盟、呼盟等聆听了大量长调、短调、佛教音乐以及马头琴、萨满音乐,假如没有这些感性经验以及我自幼对蒙古族音乐的迷醉,我肯定不敢轻易接受一位蒙古族学生于自己门下读书。当然,答应的同时也心存犹豫。第一是他当时的学业背景和汉语水平是否会影响他的考试成绩以及他入学后能否阅读大量汉文文献;第二是他未来一定会、也一定要选择蒙古族传统音乐的研究题目,那我采用何种方式指导他,他又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我的指导,等等。可喜者,这些疑虑都随着我们两人以一种不予“约定”却默契“配合”的方式在后来的教学、交流中悄然消失了。
2002年,他与李莘同时考入中国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班学习,由我担任导师。幸获这一极为难得的学习条件和机会,玉成自知,除了苦读苦学、勤思勤跑外,别无它途。为此,除了各门必修课以及后来的田野考察,他选择了“足不出户”的生活方式,将大量时间花在阅读、摘录、分析、消化汉蒙文献上。他究竟读了多少书,我无法回答,但至少可以由他的博士论文、出站报告“附录”的“参考文献”作证。我相信他写进去的,一定都是他读过的。至于“勤跑”,主要是指他前期“跑”资料馆和图书馆,后期“跑”田野。三年间,前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他都在哲里木盟、兴安盟各旗采访说书艺人。这又可以用他三年间录下二百多个小时的音响作证。
俗话说:一个好汉要三个帮。考虑到玉成的民族文化背景,我从一开始就决定邀请扎木苏学长和萧梅研究员组成一个三人指导小组。我的目的是,老扎深邃的蒙古族音乐文化学养,一定能使玉成在这一领域有新的积累和提升;萧梅对西方民族音乐学和一些前沿成果的关注和学术敏感,也会进一步扩展玉成的学术见识,我自己则会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领域给他提供某些新视域,如此,他的成长也就会变得全面而健康。最终的结果证明了这种“联合指导”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杜甫诗曰:转益多师是吾师。对于玉成来说,三年间从三位导师身上获取了相互补益的营养:对我们来说,则因为能把自己的某些学术优长教授给最需要的学生而欣慰。我还想说,在今天的教育中过分要求学生“独尊一师”的风气,未必就好。现代的教育家应该以开放的情怀,鼓励学生多方求教、广泛吸纳。
以我个人观察,玉成从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班到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站,六七年间,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宗旨。概括地说,就是:立足传统、坚持两“勤”。玉成多次告诉我,他自幼就爱听胡尔奇们说书,他是通过胡仁·乌力格尔进入蒙古族传统音乐世界的,这样的感性经验对于他来说具有生命般的意义。而进入专业院校以后,他又从理性方面去逐步理解博大精深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二十余年间的感性—理性进进出出的交织,最终确立了他与蒙古族文化传统、音乐传统的那种相互融入又相互依托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从未显山露水,而总是很自然平实地见诸于他的各种文论中,或者潜隐于他将民间音乐传人请进学校以推进传承和建立“传统音乐驿站”、“内蒙古民族音乐典藏系列”以保护民间音乐遗产的默默行为中。总之,重视传统、善待传统、体认传统,已经成为玉成治学的一个不变的信条,这对于一个青年学者而言,我以为是十分可贵的。
所谓“两勤”者,一是勤“跑”,即跑田野;一是“勤思”,即勤于求索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作为民族音乐学家,这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两极,通过“两极”,不断强化自己的学术张力。我个人的感受是,跑田野是每个真诚的民族音乐学家的天职,是他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根基和出发点。对此,玉成也很认同。这十余年,他已经跑遍整个内蒙古草原,有些地方甚至去过多次。数百小时的音响就是在田野中录下的,这是他跑田野之“广”。同时,他也很注意与传人交流的“深”。去年,我们一同到东乌珠穆沁旗听赏“长调”,返程时,顺便探望并接长调大师莫德格老人回呼市。一路上,他几乎没有中断与老人用蒙语交谈,有时也跟她学唱。事后他告诉我,这次谈话收获非常大,老人讲了很多关于苏尼特草原上古老长调歌曲的传播、传承掌故和演唱方法,这是以往从未听过的。我想,这样亲近的深度访谈,绝不是第一次。草原既广袤,又深邃,不用十年二十年功夫,不与民间艺术家有如此亲近的交往,不可能踏到草原的“边”,也不可能探到草原的“底”。而只有以扎实的“边”、“底”考察为基础,才能真正挖出蒙古族传统音乐的精粹。
自然,“勤跑”也不是绝对的。它可以给我们提供直接面对表演现场,直接感受民间歌手、乐手声音的机会,让我们采撷到许多最生动、最真实的音像资料,以及在大脑中保留下珍贵而不可复制的声音记忆。但在“跑”完之后,我们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环节,那就是进一步整理、分析这些资料的方法以及通过整理、分析从中提炼出某种音乐的构成规律、表演特征及其与相关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这就是“思”。在这方面,每个学者都会因为背景、经验、学养、习惯而形成不同的思考方法和深度。从而,也就会影响到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把握水准及阐释的深度。大约从撰写博士论文起,我就注意到玉成对方法论和某些新的学术思潮比较关注。特别是因为他的对象是蒙古族口传音乐乌力格尔,因此他对当时刚刚翻译出版不久的《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约翰·迈尔斯·弗里著,朝戈金译,2000年版)和《故事歌手》(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2004年版)两本西方学术名著的兴趣尤为浓烈,而且反复阅读,将其与草原上的“故事歌手”们的表演、传承联为一体,进行深层思考,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可见“勤跑”与“勤思”不可偏废,只“跑”而少思、不思,则可“罔”之,或造成资料的堆积。珍贵的资料进入不了有序的叙述逻辑之中,或者不能被深刻的思想所统摄,必然会丧失它的价值。相反,只“思”而不“跑”、少跑,则可“殆”之,或如在沙滩上建起的楼阁。恰如《中庸》所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缺一不可以为学。所以“跑”“思”相兼,“知行统一”,才是学术的正道。只有找到二者之间的“历史的关联”,才能使二者在学术的层面上达到较高的统一。可喜的是,玉成不仅在读书期间坚持这一古代学术的优秀传统,在他毕业以后的六七年中,这个“知行统一观”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体现得更加充分。endprint
说到这一点,我就要讲讲他的这份“出站报告”了。
玉成说,《表演、文本、语境、传承——蒙古族音乐的口传性研究》是他博士论文的延伸。很对,他的对象仍然是他一向热爱并极度关注的蒙古传统音乐。但我们注意到,不变的是整体对象,变的是他的视域、视角、观念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他集中讨论的是“胡尔奇”及其音乐,即由“人”而乐,全面剖析这一草原文化“持有者”群体所创造的音乐。而在“出站报告”中,他把视域扩大到蒙古族传统音乐品种的几种重要体裁上,即长调、英雄史诗、潮尔道、胡仁·乌力格尔、叙事民歌、好来宝、诵经调、萨满仪式音乐及乃曰与乃曰道。直观地看,面面俱到、战线颇长。而认真阅读后,才了然作者“报告”的真正旨趣。他并不是要分别论证这些体裁品种的形态或本体,而是抓住它们的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征:口传。他说:“口传性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基本特征,蒙古族传统音乐便是口传音乐。”这样,他就首先把自己的研究与以往主要建筑在书面文本上的诸多研究区分开来。在这个前提下,他建构了本报告的理论框架或者如他所说的“研究模式”。即口传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它们的“表演”,有了“表演”,才有了“文本”,才有了“传承”,而在“表演”之前和表演之中,还有一个微观与宏观的“语境”。对此,他在“结语”中有一段自己的解释,他说,本报告的“整个研究思路以表演为中心,以纵横双向作整体关照:一方面,口传世界里一切来自传统,这些传统的因素通过艺人个体的表演得以选择和组合,生成文本。因此,表演的前置是传统,表演的产品是文本。另一方面,民俗社会中的表演,不是孤立的行为,它是在艺人与受众共同建立的语境当中进行,同时它存在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语境当中。因此,我们把‘表演前——表演——表演后全过程的观察思考,贯穿于整个论述,并将这一过程放置在微观民俗语境以及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进行动态关照。”有了这样清晰的研究取向,他又做了方法论的选择。如果说,在博士论文中,“帕里一洛德”的口头诗学理论仅仅是初步尝试的话,这次在“报告”中则是一次全面的贯穿性实践。因此,他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地宣布:他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口传史诗研究中所提炼出来的口头诗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蒙古族口传音乐的思考和研究当中”。同时他又把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早年提出的“概念一声音一行为”三重模式吸纳进来,使它与口头诗学理论相互“映照与补正”,用以支撑自己针对蒙古族口传音乐而提炼出的“传统——表演——文本”研究模式。有了这些缜密的理论准备和方法论的设置,他才以自己多年来在田野考察中亲自采集的各类体裁为对象,以表演、文本、语境、传承为视角,探讨每一种音乐背后的思维、认知、规则、行为、技法,并最终回答:世世代代的蒙古族民间音乐家是“如何选择、创造、运用音乐的”这一具有终极性质的诘问。他在多大程度上回答了这样的设问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一研究中提供了多少真实、可靠的资料?他梳理这些资料时采用了何种系统和方法?他在各类资料基础上设置了什么样的研究模式和目标?他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怎样的阐释?他的这一研究具有怎样的学术见识和认识深度?等等。总之,以我个人之见,这份出站报告,在学术上至少有如下几个价值:1.选择“口传性”音乐为题,既抓住蒙古族音乐的根本特性,又改变了以往以音乐文本研究为主流的学术方向,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2.通过扎实、丰富的田野资料和明确的学术取向,为口头诗学理论与中国音乐学研究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新的经验;3.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提出口传性音乐的“表演——文本——语境”三层次,并进行剥离式分析研究,其方法对于口传音乐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欣闻,该报告油印稿打出后,就在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专业博士生中广为传阅,并被多次引用,足见其文其论之实际价值。
最后我想说,玉成十年来的磨砺,是每个与他同龄人都经历过的。这是一个现代的社会,一个中国的现代社会,中国的现代学术环境。与古代社会与古代学术环境相比,早已有天壤之异。但为学术研究,作为学者,仍然有某些亘古不变的传统规矩。玉成以“立足传统,坚持两‘勤”为学术人生的第一要旨,既有对现代人文环境的适应,又有对传统经典的追随,他坚信这样的选择一定会让自己在现代人文环境中健康成长。
以我与他十年间持续不断的相识相知,我当然也相信这是他的一个明智选择!为此,我为他祝福,愿他在草原文化的探索中,一路前行!(责任编辑 刘晓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