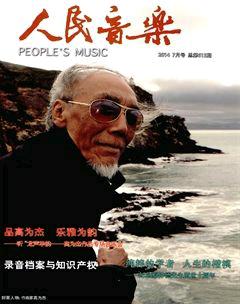“得意忘形”、“文质彬彬”:论当代音乐创作中的现代技法
田彬华
《人民音乐》2013年5月刊载了作曲家施万春先生的文章《现代主义不应成为学院作曲教学的主流——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引发的思考》,作曲家以自己多年来的切身体会为依据,有感于此次比赛中和音乐学院教学中出现的唯现代技法现象进行了批评。指出所谓现代风格“似乎已成为各大音乐院校作曲系的主流”,用传统技法创作备受冷落,认为“一个作曲家对任何风格和流派,都应该包容、研究、学习和吸收。”而作为学生“必须既要学好传统。又要学好现代,但要学好现代,首先要学好传统,因为它是造就任何流派作曲家的基石”。
凑巧的是,7月21日鲍元恺先生在中国音乐学网站个人空间发布博文:“黄安伦、陈其钢和我的三篇文章”。文章分别是:黄安伦《无调性与曲作的个性及其它》、陈其钢《关于对现代音乐的一封信》、鲍元恺《<中国风)的理想与实践》。博文开头尖锐地指出:“音乐学院作曲师生的作曲活动,现在很多不是为了给人听的”,对于这种现状,“我们有着同样的忧虑,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观点不尽相同。”三篇文章指出使用无调性音乐的巨大风险(黄)、无调性现代音乐的衰败事实(黄、陈),同时大力提倡民族传统音乐的学习(黄、鲍),认为应该走自己的道路(陈)。文章都是旧文(分别发表于1995、2000、2004年),但讨论的主题却有意无意和施文形成了一种呼应。
当代音乐创作中如何对待现代技法是老生常谈的争论议题了,似乎不能简单地用“保守”与“激进”来衡量。而是关乎到整个音乐创作中形式与内容的重大艺术命题,其中又掺杂了如何处理民族传统的问题,不可谓不复杂。笔者在阐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借用了两个成语:“得意忘形”、“文质彬彬”,假古人之语来重新审视这一当代话题,试图有所发现。
一、“得意忘形”:直面现代技法
几位作曲家切身感受到了学院派音乐创作中一边倒的倾向,与改革开放初作曲家们纷纷补课现代技法不同的是,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的“现代作曲技法”一家独大,其话语权统治了整个专业音乐界,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技法已经成为如今国内专业音乐院校的“新约圣经”——当然,目前可能也仅仅局限于专业音乐界。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让我们先追溯一下历史,施文的观点其实从国立音专的先辈肖友梅、黄自那里开始就形成了,“他们提出了同一个奋斗目标:吸收德国传统的作曲技术,以我国的国乐为本,建立中国的强力集团(国民乐派)。”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近百年来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思路在进行。而就在这一模式刚刚起步的时候,美藉俄裔作曲家齐尔品来华做了几件对中国音乐史影响深远的事情(如征集中国钢琴风格作品)。鲜为人知的是,他在给国立音专的教学建议中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在专业音乐教育中不应大量采用欧洲18、19世纪的音乐作品为教材;中国音乐发展也不必步欧洲音乐的脚印,古典、浪漫、印象主义等一步步地走。而应该直接步入20世纪音乐!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观点今天看起来依然十分超前:“他们(指中国人)没有任何西方音乐的传统(因此没有迷信)……你难道会要他们背负西方过去的古典乐曲这个深重的包袱吗?”
由此看来,施文所推崇的“传统技法”,实则是我们在过去的百余年“西化”过程中自己主动背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可惜,我们的音乐先行者们并没有听从齐尔品这位大师的建议。还是帮我们主动地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包袱”。到如今,“迷信”已经根深蒂固、习以为常:“不仅一般爱乐者,就是专业圈子里的众多从乐人,耳朵的审美定式依然囿于18、19世纪,因而很不习惯接受不谐和的音响组合与奇异的音乐思维。”由此可见,传统与现代,皆是西方外来文化的当代中国呈现,而国入作为“他者”却似乎毫不知情,将他人老传统作为自己传统进行守护——在国人日益文化“自觉”的当下,是否该卸下这一不知不觉间背上的“包袱”?
几位作曲家都看到了西方现代无调性音乐背离传统、背离听众、背离审美的一面。毫无疑问,这是西方现代技法的“顽疾”,但是,直面现代技法如今已是不争的事实,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更何况西方现代技法所开辟的音响新天地以及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创造性,对于任何一个作曲家来讲都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对于喜欢追求新事物的作曲学生们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对于整个音乐创作倾向和专业教育导向而言,不是现代技法该不该成为主流的问题,而是如何来直面现代技法的问题。
对于新潮技法的主动学习和追求并不是一件坏事。作为高度发达的技术体系,音乐创作技法问题的研究和学习无疑是重中之重。作为作曲学生掌握现代技法的练习性创作,有目的地、严格而系统地运用某个或某一些现代技法进行创作练习是必不可少的,教师对此要求和引导是极为正常的教学手段,不必因此而大惊小怪。但是如果仅限于此,则永远只能做“西方”的蹩脚学生。
而作为一个真正成熟的作曲家,如果对20世纪的音乐一窍不通或者持抵触态度,无疑会大大缩小他的创作能力,更不能奢望他能够创作出当代能够“不可覆盖的个性作品”(韩)。以两位老一辈作曲家为例:朱践耳和王西麟,他们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便以《唱支山歌给党听》、《翻身的日子》、《云南音诗》等作品崭露头角,但如果他们就此而停步不前,难以想象会产生他们80年代以来创作的十几部交响乐等重要作品——对各种现代技法的认真补课和虚心接受、融会贯通.无疑是他们赖以成功的重要技术支撑。
对西方传统和现代各种创作技法的娴熟掌握是一个当代中国作曲家的必备之技。但若拘泥于一招一式、受制于一家一派。终归小家子气,难成气候。朱践耳先生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后提出“合一法”,即灵活运用“古、今、中、外”这四种因素进行创作,这是一种相当辩证而又极具智慧的做法。如何才能将如此不同的四个元素有机统一地“合一”?无疑首先是“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晋书·阮籍传》),方能够进行更高层次上的“合一”。这从朱践耳的众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这一技术特征。
因此。直面现代技法,我们应该勇于迎头赶上,得其创新无限的内在之“意”,超其特定技法的外显之“形”——“得意忘形”,才是我们直面现代技法的不二法门。二、“文质彬彬”:文化身份显现与深度阐释endprint
“得意忘形”解决了技术问题,是否就能创作出称得上“经典”的优秀作品呢?佛日:不可说。
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何意?“文”是就形式而论,是指文饰,即华美、有文采:“质”是就内容而论,是指质朴,指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质美而无文”或“文美而无质”都是不够完美的,只有将“文”和“质”统一起来,才能成为理想中的“君子”。先哲的论述弥久沉香,历代儒学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去阐发、引释这一重要美学思想论述,论域亦延伸至文艺创作和评论上。在音乐领域,用来阐释音乐创作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亦是一个绝佳的中国式论述。
几位作曲家对学生们热衷于现代技法忧心忡忡,的确,如果在创作中只是一味追求创作技法的新颖与独创,则犹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赚足人们眼球之后可能很快就会让人们失望而去。更何况,这个“外包装”还是舶来品,与国人来讲尤其感觉“水土不服”,这也就是为何许多作品被作曲家们津津乐道而观众并不认可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如陈其钢所言:“无调性音乐的写作充其量是在20世纪为音乐创作增加了一种可能性”@。西方现代音乐无调性的道路只是其中一条,它打开了现代音乐的大门,但是其作用不能无限制地被夸大。回顾国人学习西方现代技法的历史,从改革开放前的严禁学习各种“资产阶级腐朽音乐”,到如今一窝蜂好坏皆收、唯西方新潮马首是瞻,变化不可谓不大,以至于“文胜质则史”已变成一种典型的倾向,至于接地气的音乐“可听性”早被抛至九霄云外。难怪黄安伦文章中提到,长期致力于普及交响乐的指挥家郑小瑛对一位作曲家说:“我们长期辛辛苦苦努力,好容易带进音乐厅一大批听众,你的一次音乐会就全赶走了。”⑦无奈之意溢于言表。
问题在哪里?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就是说精良的技术唯有与内在的艺术品质相结合,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佳作。反观当下的音乐创作,往往是作曲家们的技法游戏抑或生存需要——“文胜质则史”。当然,反之“质胜文则野”亦是废物一个,笔者亦多次观看当代作品音乐会,看节目单介绍似是立意悠远、哲思遐想,听完音乐后发现其实就是假大空的标题配以毫无意趣的技法堆砌,抑或是中西音乐的生硬嫁接……如有作曲家作品名日《虎虎生风》,究其缘由为“虎沪申风”谐音;亦有乐曲名为《离·骚》,实则与屈原诗作无半点关系——无论作品如何,如此这般随意的冠名,怎么可能产生出“立意高远”的深度作品呢?凡此种种,不一一类举。
如何来做?
现代技法占据主流不可怕,甚至是必然的,真正可怕的是作为中国自己的专业音乐教育和创作中,本国的文化传统被抛之脑后、弃之不理(注意:此处为文化,不单指中国传统音乐),这无疑就是现代版的“邯郸学步”。对于系统完整的西方音乐技术,作曲家可以有所偏好、有所取舍、有所创新,但是渗入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是他的自足之根本。这其中,有吹拉弹唱,亦有琴棋书画、诗词赋曲,既有民间小调,亦有文人古琴……总之是一个大的中华文化的滋润养育。只有传统文化的“学养”丰厚,才会“腹有诗书气自华”,才能在举手投足间“出口成章”。如果说西方作曲技法是“形”,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意”,换一个时髦的学术话语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体现是整个华裔作曲家面对西方话语体系作为“他者”的文化身份体现。
韩国学者刘贞银在博士论文中对中日韩三位代表性的作曲家武满彻、尹伊桑、朱践耳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后认为:“这三位作曲家作品中的传统都没有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转向“他者”,也即不是在追求“异国性”,而是在追求传统的本质,用自己独创的见解对传统进行再解释。他们使用了现代音乐技法,同时也超越了它”。这三位作曲家的创作方法给我们以不同的创作启发:不论采取哪种处理,作品的音乐语言可以完全是西方的,但是内在的审美特质却是地道的本族文化传统。
鲍元恺与黄安伦在文章中均大力提倡要重视本土传统音乐的学习,但过去那种流于表面的学习民歌、戏曲,弄一点五声旋律、配几个色彩和声的“新瓶装旧酒”的简单嫁接,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人们的审美要求和傲立世界的文化渴望了,绝不能让其成为作曲家们裹足不前的温床——没有深度的简单嫁接阐释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了。
有了“文化身份”显现之后,如何更进一步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呢?李诗原提出音乐批评要走向“深度阐释”,认为批评家要有人文关怀、深度阐释,指出在分崩离析的后现代状况之下:“当下音乐批评中那种丧失超越性、元叙事、整体性的‘叙事危机”,无疑也成为人文知识分子危机及人文精神萎缩的一种表现。“若其中的将“音乐批评”换做“音乐创作”这一论断依然透彻:当下音乐创作的苍白无力,无疑是“人文知识分子危机及人文精神萎缩的一种表现”。立意高远、深度阐释方能占领文化制高点,而个性阐释才具有人文永恒魅力。
作曲家中具有极大才具、极富人文关怀的那一小部分人,他们怀有“终极的人文关怀”,作品中有极具个性的“深度阐释”,最终所产生的音乐作品才真正堪称“经典”作品。如朱践耳第十交响曲《江雪》,京剧的咏唱和古琴的加入与西方现代技法的融会贯通只是其外在“文”,其中蕴含之先秦汉魏以来文人的高古气息、不与污浊世俗同流合污的隐士风骨才是其真正令人动容之处。另如瞿小松的作品《寂II》中,作曲家的题解为:“云飘云散,音生音逝,惟寂静永在”,这种浓郁的禅意和哲思是典型的中国智慧,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段休止一方面是对标题的映照,另一方面则与中国画中的“留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让我们在真切地感受到民族脉搏的跳动之时,又体悟到作曲家内心的追求。以上佳作,非心有天地者不能构建之,亦非肤浅之辈能得其神韵啊!
韩锺恩在“中华乐派学术论坛”提出,国人欲建设中华乐派,“中国应提供不可覆盖的个性作品。核心竞争力在于建构独一无二的中国学统”,窃以为,“中国学统”之建构,不仅要学习借鉴西方传统与现代技法:“得意忘形”,更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有所独创和推进;不仅要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获得身份认可,更要在人文高度上“深度阐释”、“个性表达”,方有可能企及“伟大”。二者若能齐头并进,“文质彬彬”,才有可能为世界贡献“不可覆盖”的作品。若果如此,“中华乐派”指日可待也!(特约编辑 于庆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