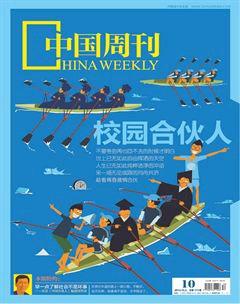客栈圈:回不去的心灵乌托邦
熊菂
一路迁徙,不同的房间像蜗牛的壳,给旅人提供暂时庇护。相比起酒店提供有保障然而千篇一律的服务,客栈如同“百变星君”,呈现无穷可能性。
对国人而言,客栈是这些年才在丽江、拉萨等地兴起的“新事物”。就拿我熟悉的丽江来说吧,最初的所谓客栈,不比招待所好多少,不过是当地人挪挪地方,腾出几间空房开门迎客。起码的被褥,简单装修的公共卫生间、淋浴间,就是设施的全部。渐渐地,外来人不仅仅安于游客的角色,有先行者租了院子,停下生活,顺势盘下一份悠闲的营生。
其时标间寥寥,多人间设施简朴,公共活动区也散乱杂陈,倒自成一番旁若无人孤高的野趣,而客人也不挑剔。客栈与投宿的客人间,达成一种类似恋爱的默契:合则聚,不合则散。
这是记忆中的乌托邦时代,我以为也是丽江最好的时代。外来者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拓宽了本地人的眼界;本地人宽容地接纳,给外来者落实自己的理想,提供了可能性——双方都不徐不疾从容淡定,互利互惠。
许多朋友都是在那时候结识的。每个人背后都有故事,而什么样的机缘造就他们上路,之后又停下来,云山雾罩,没有特别去打听,只是莫名相互体恤。他们显然是秉持安稳传统价值观的叛逆者,然而他们又有足够的行动力承担了改变自己生活的代价,他们在浪游嬉皮与精明商人之间,找到了一条折中的路。
然而时移世易,当资本的大军高歌猛进,原本的“散仙”们被迫打起精神应对,纷纷投入到客栈改造的“大跃进”中。世界变了,客人变了,客栈无论从外在到内核,也都变了。
而我陆续写下一些文字,追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乌托邦时代。
【丽江篇】
张文波:心里藏着《小王子》
张文波,2003年到2006年在丽江开“牌坊过落”客栈。2010年与女友一起开“颐和文苑”,如今已成遍布古城与束河的连锁店。2011年又开设“禅玺”茶庄。
迄今为止,就我所知,在丽江,没有哪个客栈,如“牌坊过落”那般得到过如此多的人们如此不由分说的青睐。
人的一生也许会走过万水千山,但只有一个地方,像你前世的乡愁,没来由地让你眷恋。你不断地回去一次又一次,怎么都不够。对我来说,这地方的名字确切无疑,它叫作云南。
1996年开始,去过多少次呢,数不清了。但我的完美旅行,始终没有到来。2004年,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一段邂逅之旅由此展开:那么多的人和事,亲切感和神秘感同时卷裹而来,带我走进云南深处,走进所有故事发生的腹地,也成了故事中人。
好友知道我有去丽江小住的想法,向我推荐了“牌坊过落”。
牌坊过落,我并不陌生。“非典”那年的丽江行,在它隔壁的“今生有约”客栈住过一阵。其实之前我钻进科贡坊的门洞,沿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往上,同时看到了“牌坊过落”和“今生有约”的店招,向左走向右走的问题在我心中瞬间闪现,惯性地右拐了一下,于是与“过落”擦肩而过。这遗憾在心中留下浅浅的回响,我以为和它,没有缘分。
丽江的客栈太多,各有特色。住进一家,往往就懒下来,不想挪动。即便这样,几年下来也住过不少客栈。那时候,《丽江的柔软时光》刚出第一版,闲暇时按图索骥去寻找书中所列客栈,一家家参观,以这样的游戏打发我在丽江水波轻漾的光阴。很偏远的巷子都寻去了,隔壁的牌坊,却永远是路过。有时我伫立片刻,默读它门口的大段说明,知道“过落”是纳西语“小巷子”的意思,按下快门记录我无端犹疑的心情。
那一年,我和它都远远端详。
回到加拿大,有时乡愁发作,便上网寻觅有关云南的文章,惊奇地发现,不知从何时开始,牌坊过落在天涯旅游版竟暴得大名。住过的深切怀念着,没住过的殷切期盼着,一篇“阳光爱人”呼唤爱的帖子更是将这股风潮推波助澜,上升为一种情结。
迄今为止,就我所知,在丽江,没有哪个客栈,如它那般得到过如此多的人们如此不由分说的青睐。还没住进牌坊,就对牌坊的各色人物如数家珍;住进来,自然而然成了半个主人——过落使每一个过客心中的喧嚣都暂时落下。
在这里,看似无序的人和事,以各自的轨迹兀自转动,聚散离合都成寻常。有的人走了,有的人正来;这边还说着路上听来的传奇,那边就有人漫不经心插嘴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某处曾跟此兄把酒言欢。这样的人群很有点蛊惑性,让人误以为放弃生活是很容易的一桩事,随波逐流又是那样令人向往的诗意。
为什么来丽江?各有说辞,打着理想的旗号或采取逃避的姿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有遗漏于时光之外的一段时光,这里有出离于世界之外的一方世界。
也许,这只是牌坊过落客栈给我的错觉。也许,这正是店主文波独有气质造成的假象。对于过落,朋友们与我有相同的看法。“别的客栈都是主人忽悠客人请饭,末了还偷偷折返拿回扣。过落可倒好,客人放下包,迎面碰上一位怪店主的邀请,走,出去吃饭,吃完还抢着付账!”
是的,文波就是这样。他心细如发沉默低调;他随和宽容古道热肠;他总在店里忙前忙后,规整这摆弄那,只顾着高谈阔论的人们曲终人散才发现:院子不知何时又从杂乱变为整洁;几位荷包羞涩的长住客也才发觉,不知从何时起,文波再没收过住宿费,相反自己身穿的衣裳脚蹬的鞋,都是打文波的衣柜“搜刮”而来……牌坊过落之所以提前进入“共产时代”,文波的“孟尝君”性格功不可没。
对许多人而言,文波是一个谜。而我个人最接近“谜底”的一次是在他的书架上发现一本《小王子》:印象里文波只爱看汽车和旅行方面的书籍杂志,和一本写给“心中藏有一个孩子的成人”的童话故事毫不搭界。可他书架上就放着这么一本我也极喜欢的——《小王子》。
忽然之间有些明白了。
文波与《小王子》一书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真有着某种程度的相象呢!都是那样地热爱机械,热爱一种接近极限的冒险和自由;心中都藏有一个黑洞,这黑洞迫使他们连自己也无法解释自己,在感情上常年彷徨,只有孤独上路,心头那纠结缠绕的欲望才得以释放宣泄。endprint
2006年,一切戛然而止。牌坊过落转让,阳光离开,朋友星散,文波从此开始一段落拓而浪荡的混沌期。
这以后,许多消息传来,文波的形象千变万化,与我们熟知的那个毫不搭界。但是,不知从哪儿得来的笃信,我们等待着无常变幻耍尽百宝、耗尽元气,等待月华重新朗照。
2010年年初,兴之所至,与好友重返丽江,听说文波筹备的新客栈快开业了。沿五一街一直走到文明村,远远望见一个身影在院外打扫,眼眶顿时有些湿润。文波看见我们,指指院门:“快进去坐着烤火,我忙完了这些就进来。”
一切都回来了,或者说一只无形大手按下了恢复键,停滞的时光复又向前。文波还是那个文波,无论他名下的客栈叫牌坊过落还是颐和文苑。
闭上双眼,让我回想多年前过落院子的人来人往,如电影镜头的随机叠加,繁华过后,一片空寂。
我知道你在这里长时间望天,云朵盛开和繁星满天都使你发呆。
我知道你在楼上的摇椅有一搭没一搭翻一本没头没尾无主的书。
我知道你们聚在一起大声说笑,邀约去巷底喧哗的酒吧街喝酒。
我知道有时候那把破吉他会发出动听的声音,你们围着它唱出心中忧伤的蓝调。
我知道院子里有隐秘的激情一触即发,明日又将远隔天涯,可今晚,你遇见了她。
我知道飞短流长,悲欢离合,一切人间的剧目在不动声色地上演又落幕,周而复始,永不歇止。
我知道一颗心在哪里被碰得生疼,在哪里得到抚慰,又在哪里再度失落。
我知道每一次欢笑的原由,每一滴泪的归宿,每一场缠绵背后的失去与付出。
是的,我可能不知道你,但我知道你的故事。你先走了,我才来。我来了,你却已经离开。我们在过落院子的潮涨潮落中,遇见又失散。
遇见又失散,一次又一次,所以我从不端详新来者的面庞,从不跟离别说再见。何必再见?总会再见。如果说丽江是被施了障眼法的一场浮华虚幻,那么不得其门而入的,至少享用了一番感官盛宴。而那些有幸获得秘匙的,也各有路径。
对牌坊过落的老友而言,仅需一句:文波,开门!
阳光:梦想与现实配比合理
阳光,2003年至2006年,在丽江与文波合作,开设“牌坊过落”客栈。2006年至今,转战大理,与女友小花一起,开设“天涯驿站”。
来了、乱了、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天没塌下来,自己没堕落,相反倒交了几个知情见性的朋友,一场“豁出去”的丽江之旅于是皆大欢喜。
大理博爱路的公车站,一位高瘦青年在街边晃悠。哦,晃悠仅指身形的一派悠闲,实际上他忙得很,先送完一拨客人,又顺道接上一位,就是我。远远地彼此看见,他大步流星向我走来,劈头道:
“我操,你……你还是那样!”
“你也还是那样!”
老友就这样完成了睽违几年的见面礼。
多年前,古都南京一个安分朴实的知识分子家庭迎来儿子的毕业礼。对这个家庭而言,儿子进学校当历史老师,留在父母身边,努力工作、娶妻生子,岁月静好唾手可得。
然而,一场兴之所至的云南之行改变了一切。
一向以慢性子著称的青年第一次发现并惊异于自己的决断力和行动力:偶然的旅行,偶然与网友见面,偶然投宿网友推荐的“过落客栈”,偶然与文波觉得投缘……这么多偶然叠加起来,某种必然成形了——科贡坊进去的小巷深处,从此多了一位来回晃悠的高瘦青年,而一名深受学生爱戴文质彬彬的青年历史老师,从此隐没。
阳光何时以何种机缘扬名网上,已被各种段子渲染得面目全非。对丽江而言,“考据”是个不必要的傻词。成为传奇比怎样成为更重要。当你急于追问为什么,便是传奇消散时。
聚到阳光麾下的粉丝们,多是不管不顾的相信者。来丽江的理由千千万,能不管不顾、任性一回,对一些人而言,是其中致命诱惑的一个。来了、乱了、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天没塌下来,自己没堕落,相反倒交了几个知情见性的朋友,一场“豁出去”的丽江之旅于是皆大欢喜。
毋庸讳言,阳光声名的七色光谱里是有几分旖旎的,从循迹而至多是女生这点便可见一斑。阳光走过酒吧街,也总挂着既无奈又有些自得的微笑在此起彼伏“光哥哥”的叫唤声中穿行。
在丽江度过了“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四年后,阳光去了大理。按说阳光是最不该离开丽江的,有谁比他更得丽江“白日梦”的真传?比起遍布丽江酒吧客栈的假嬉皮、假行者、假艺人、假感情,阳光无处不在又无所用心的真尤其可贵。
年轻的热情与年轻的真,混成一股鲁莽力道,勾勒出丽江阳光的基本轮廓,使阳光的种种轶事被提及被流传,使牌坊过落这个小客栈,在朋友们心中停驻不去,成为一抹思之怅然的温暖。
然而阳光毕竟还是选择了离开。当我再见到阳光,他已不是丽江阳光,而是大理阳光。他已不是当年那个粉丝无数、迷倒小女孩的有名帅哥,而是一位与女友携手创业、相濡以沫的成熟男人。
在大理,除了从丽江撤下来开的“天涯驿站”外,阳光和小花小两口又开了“天涯驿站博爱店”,据说,第三家分店正在洽谈中。未来,“天涯驿站”会分三个梯次,分别针对预算秉性偏好各不相同的客人,将客栈这项从丽江发仞的事业红红火火进行到底。
看着阳光,看着阳光的小院,阳光的变与不变,一目了然。井然有序、郁郁葱葱的小院,处处皆见小两口的用心贴心;而院子里的谈笑戏谑、呼朋唤友又此情此景似曾相识——是的,不管丽江还是大理,阳光还是那个阳光:永远热情、永远是中心、永远让你没好气,也永远不让你失望。
我问阳光当初离开丽江的理由。阳光说,为生活。“生活”二字从与生活南辕北辙耽于梦想的青年嘴里吐出,乍一听,很荒谬。可细想想,很真实。是的,生活。这就是阳光想要的生活:梦想与现实配比合理——而真正的配方秘而不宣,深藏于心,引导他的脚步,走向梦想与现实接壤的理想之地。endprint
阳光最后这样总结:去丽江,是放飞;来大理,是沉淀。
陈欣、周妍:建造“可能”生活
陈欣,2003年起,在泸沽湖里格岛开“光阴”酒吧、客栈。
周妍,丽江的资深游客。2007年至今,与陈欣一起开设“人和春天”客栈。
“我们对坐在山顶的草坝上/身后是核桃树、河谷、雪山和旋风/我们晒太阳,看星辰从江水里上升/我们喝啤酒,卷纸烟,臧否不在场的人/我说:晴朗的天气宛如我们的内心/你说:这样的生活是否有过,是否可能?”
一对恋人用四年时间、一个属于他们的“王国”回答:可能。
认识周妍和陈欣是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徒步旅行中。到丽江第二天,我稀里糊涂地加入一支队伍往泸沽湖进发,以那里为起点,妄图征服“泸沽湖——稻城”的徒步路线。
最终,八天八夜的同甘共苦使我们从此天下一家,成为每年必聚的老友。
那时,他俩的“基地”在泸沽湖畔,陈欣在里格面朝湖水开了一家叫“光阴”的酒吧兼客栈,丽江则作为他们的补给“大后方”不时造访、不时停留。
这是一对奇特的情侣——经历的迥异、年龄的差距、性格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痛苦着他们,让身边朋友悬起一颗心,可他们又总能安然度过,笑意吟吟携手现身。
周妍是学画的科班出身,陈欣是吉他业余高手。周妍任性的同时执着,陈欣果决的同时包容,他们时时在交战刻刻在悔悟,每一次冲撞的“后果”只不过把他们连接得更紧。
朋友们都知道周妍心底藏有一个“客栈梦”。那些一起蛰居小院晃悠古城的时光,周妍跟我说了她梦想的缘起:从2000年学校组织的写生活动第一次来丽江,第一次感受个性化小院,第一次认识到心中那些懵懂憧憬有成行的可能,这个梦想一直未灭。
虽说在朋友们眼中,因着男友陈欣的关系,她也算半个老板娘,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一个声音总在固执地提醒她:不是,不是这样。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人们往往莫衷一是;不想要什么,却清晰无比。周妍正是在这样的清晰与混沌交错中耽搁着、迷惘着,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从黄山公园望去,整个丽江古城呈现令人震撼的煌煌规模:屋顶,放眼望去全是屋顶——丽江究竟有多少院落,至今无明确的统计数字。这么多位置不同形态各异的院子,为什么就找不到自己可心的那一个?
2006年夏天,看院子,看院子,成了周妍每天的必修课。究竟要个什么样的院子,她也说不清,她所做的只是否定。朋友们议论起她旷日持久的寻觅过程,都颇有微词。
当周妍终于选定她理想中的院子,大家不免目瞪口呆。从位置上考量,七一街崇仁巷往外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太过偏远,几乎人迹罕至;从格局上斟酌,这个所谓的院子实际是个袒露的“工地”,上院只有一些零落的房架,下院倒有一个硕大无朋、泳池般的方正水塘;从价格上比较,也令人乍舌。
如今回想这些往事,只能说,我们都是一群只知夸夸其谈的鼠目寸光之辈,而周妍,倒有着异乎寻常的胆识和毅力。事实证明:不是周妍当初的选择没错,而是她的执着和努力没错。同样的地方,换一个人来经营,也许早已功败垂成,应验了我们所谓的“先见之明”。
其实无论我们的否定还是周妍的肯定,都不无道理。这个院子的长处短处都显而易见:长处是场地大、没什么限制;短处是相应的投入也大,一高一低两个院落、下院的水塘占据绝大部分面积不好布局,一不留神就被拖死。
周妍的幸运在于,不但有决心有信心,还有支持她的好伴侣好帮手——男友陈欣。陈欣有丰富的职场历练,又有在泸沽湖开店的心得和教训,还有之前在大理丽江两地帮朋友装修酒吧的经验累积。
最终,这对情侣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上院全部留作公共活动和辅助设施,下院用作客房。这样下院临水上院看山,住宿与休闲娱乐的区域完全分开,互不影响。更重要的是,为将来二次发展预留了空间:若有需要,上院可随时再改建出几个套房。
如今的庭院,错落有致花木扶苏;如今的周妍,是巧笑倩兮赏花品茶养狗画画、丽江美好生活的理想范本;如今的陈欣,是有条不紊忙里忙外客栈的操持人;如今的客栈,是服务周到口碑上佳携程网上排名靠前的优质保证;如今的日子,如客栈的名字“人和春天”一般:天人合一,春风拂面。
在分享朋友成功的喜悦的同时,我还留有一分“挑刺”心思:怎么说也一直在路上,一直漂泊的同时也存积大量住宿经验。一家客栈的好坏单凭光鲜的外表无法断言,要亲身体会,才真正了然于心。
周妍陈欣通过了测试。不但意料之中地通过了,其用心、其热忱、其坚持,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首先是细节上的用心,这大概与他们多年的驴友身份有关,懂得旅人的细小需求。比如说,每位客人入住,办完相关手续后,都会得到一系列温馨提示,其中便包括床头柜的抽屉里有插线板、灭蚊器的“喜出望外”。之所以大书特书这个小小的细节,是因为从中能窥见经营者可贵的换位思考。
其次是服务上的热忱。来云南的旅客,除享受标准化服务之外,或多或少都存有体验当地民风民俗的心思。而云南的茶文化,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项。因天性好茶,推己及人,周妍推出免费提供普洱茶服务,每个房间都备有一套茶具,也可叮嘱服务员把泡好的茶送至房间……
回想起当初,一片反对声中,有位朋友一语中的:你们做客栈,要守住出入口。边缘的位置,如今看来倒方便了客人接送。昔日冷清的深巷,也被热度不退的“丽江高烧”渐渐捂热。说起2007年元旦开业后长达半年罕见客源的坚守,陈欣和周妍有“劫后余生”的欣喜,更多是因坚持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淡然笃定。
按陈欣的话说,不能单方面迎合客人,那你永远处于被动,永远疲于奔命——言下之意,不是主客双方简单的较劲,而是客栈要有为客人着想诚恳的心,更要有自己明确的理念和清晰的原则。
的确,没有明确的理念,周围都卖几十块一个标间自己却敢定价上百的超前不可能坚持;没有清晰的原则,如今是个客栈随便一装修便标价几百的泛滥时代,也不可能维持原价的同时执行既有的服务标准,一丝不苟。endprint
随澜沧江水永逝的诗人马骅曾留下这样的诗句:
我们对坐在山顶的草坝上
身后是核桃树、河谷、雪山和旋风。
我们晒太阳,看星辰从江水里上升。
我们喝啤酒,卷纸烟,臧否不在场的人。
我说:晴朗的天气宛如我们的内心。
你说:这样的生活是否有过,是否可能?
一对恋人用四年时间、一个属于他们的“王国”回答:可能。
湘薇:周而复始,就是修行
湘薇,台湾花莲人,在美国大学里攻读宗教学,多次进藏学习藏语。在拉萨开有“卓尔巴”餐吧。2008年后到丽江束河开设“卓尔巴小院”。
院落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带来了一整个世界,热闹的时候,这里活象个小联合国,仿佛泰戈尔诗句的写照:“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素不相识。醒来,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
2007年的拉萨行,朋友托我带些东西过去,于是,我第一次在电话那头听到了一个柔和的女声:有台湾女孩特有的长长尾音,却并不因此感觉嗲和黏,相反倒有一股清新的真诚。就这样认识了湘薇,走进了位于藏医院路的卓尔巴。
虽说每位卓尔巴的客人都会被告知“卓尔巴”三个字,是藏语“牧民”的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心中仍坚持“望文生义”的第一印象,因为湘薇和她的朋友们开设的这家餐吧加咖啡吧,在拉萨众多同类店铺中,实在太卓尔不群了。
首先,这是拉萨第一家素食餐吧;其次,这是拉萨少有不卖酒的餐吧;最后,这是拉萨唯一一家“No Smoking”餐吧。许多拉萨朋友得知湘薇她们成功坚持了这点,都很惊异地问:你们怎么做到的?
来拉萨开卓尔巴之前,湘薇对烹饪一窍不通,其生命历程至简至纯,寺庙和学校两个词汇就能全面概括她近三十年的人生轨迹。然而,机缘加责任,使这位在美国大学里攻读宗教学、之前八次进藏都是为了学习藏语及田野调查的女孩,成了一位餐吧的主人。
从书斋到厨房、从与书本纸笔为伴到摆弄刀叉碗盏,这一过程中,湘薇吃了多少苦,从她那双伤痕累累的手可见一斑。边摸索边学习,人生重大转折不为赚钱只为慈善,卓尔巴的卓尔不群应该加上最重要的一条:它或许是拉萨唯一一家把营业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用于供养青朴山上苦修者的餐吧。
来自台湾花莲的湘薇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由于阿姨和舅舅都是出家人,耳濡目染,她自小便懂得出家不是逃避,不是弃绝,而是扛起众生更大责任的道理。
没有烟酒喧嚣,却有沁人心脾的宁静,卓尔巴因其宾至如归的服务、健康优质的饭菜而渐渐有了名气。尤其于一些国外的素食者和骑行者而言,卓尔巴简直成了他们抵达拉萨后最舒适贴心的休憩驿站。
他们经常光顾,难免“反客为主”,成了义工。这里面,“义”得最长久彻底的,大概要属Peter——原本想骑自行车环球旅行的他,从祖国荷兰出发,横穿整个欧洲、中亚,从新疆进入中国。来到拉萨,他的脚步停了下来,以前从未接触过佛教的他感召于卓尔巴一众的奉献精神,成了前台接待员、洗碗工,及去青朴时的背伕……
2008年,深爱西藏的湘薇和Peter不得不离开拉萨,来到云南,在束河重建他们的卓尔巴。这一次,不但有了咖啡吧,还有了一个宽敞方正的卓尔巴小院。
湘薇与云南结缘,始于上大学期间。在美国攻读学位时,湘薇曾有机会跟随牛津大学的一位梵文教授进藏寻找贝叶经。当他们在北京办理相关手续时,中国佛教协会的一位高僧问道,为何不去云南的西双版纳试试,那里南传佛教的传统一直未断,民间应该还保存着不少贝叶经。
就这样,湘薇来到云南,认识了版纳曼听佛塔寺的都罕听师傅。南传佛教盛行于东南亚一带,版纳的许多僧人都有去泰国等地禅修的心愿,无奈语言关是一大障碍,湘薇于是成为他们的义务英文老师。
彼时,都罕听师傅说,湘薇,毕业后干脆过来给我们做义工,教英语吧。湘薇随口答应。转眼间美国的学业完成,湘薇回到台湾,打算申请英国大学的有关博士学位。期间,她接到了都罕听师傅的电话。
英国的学校申请暂停,湘薇再一次回到了云南。除了在佛学院做义工,也多次重返拉萨,为的是给自己提供一个语境。
湘薇中断学业不是没有过挣扎,但正如师傅所言,哪怕博士读出来仍要面对这个社会,要做事。既然自己的缘法在大陆,那就愉快地接受它。
西双版纳无论气候特点还是佛教氛围都跟湘薇的故乡类似,令她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可相比起东南亚源远流长、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精神殿堂,当地对“文革”中被破坏传统的恢复才刚刚起步,尤其缺少像泰国那样的禅修中心。
在西双版纳建一所禅修中心,逐渐发展壮大成泰国那些著名禅修中心的规模,成为湘薇等一批为弘法而努力的僧众们的共同心愿。
湘薇用一位哥哥提供的资金,陆续在版纳买了些地,整合起来建禅修中心。后来哥哥无法再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幸得其他僧团的接续,才把这件事坚持下来。如今,西双版纳的禅修中心已初具规模,开始正常运作。
当我来到束河的卓尔巴小院,湘薇正独自忙里忙外。事业上的好搭档、精神上的默契伴侣Peter又去泰国禅修了,店里的厨师小妹也都下版纳的禅修中心帮忙,湘薇用瘦小身躯承担下一切责任。
不是没有过软弱和抱怨,可周而复始的日子其实就是修行。慈善事业在继续,跟拉萨的卓尔巴一样,束河这间卓尔巴的营业收入的一部分,也用于支持版纳的禅修中心。
院落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带来了一整个世界,热闹的时候,这里活像个小联合国,仿佛泰戈尔诗句的写照:“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素不相识。醒来,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
丽江是个江湖,乌托邦的外表之下其实盘根错节着各种利益各种矛盾。我也曾为她担忧,而她却以自身的纯良一一避过。在她口中夸赞着的,全是自己碰到的好人——房东是,邻居是,客人也是。而我知道,是她本身的质地,吸引了世间这么多好的东西。就好比一块磁铁,它所需要做的是把自己磁化,而不是跑到别的地方去找钉子。
大研古城与束河古镇的无数院落繁花过眼,卓尔巴是一径清幽的小溪,院子沉静,但毫不衰败,像有什么无形的美好之物在自足生长着。经湘薇介绍才知道,房东家世代是风水师,这院子正正地坐北朝南,整个束河找不到第二座。真是这样?或者说仅仅是这样,才成就了小院的妥贴安适?我想还有更多,人淡如菊的精神气息脉脉发散,才是每一位过路人都不由自主放慢脚步,被深深吸引的原因。
从拉萨“游牧”至此的湘薇简直把拉萨的卓尔巴都“搬”到了束河以慰“乡愁”,这里因此成为束河最具藏族特色的咖啡吧。“卓尔巴小院”不但像拉萨时那样坚持“三不”,还提供有机健康的素食餐点、100%的新鲜果汁、现磨咖啡及自己亲手做的面包、蛋糕和饼干。
我到的那天,湘薇刚从泸沽湖回来,不辞辛劳背回一百斤没施任何化肥农药、当地人留着自己吃的高原红米。
由于有了小院,卓尔巴也增设了住宿服务,其客房设施简洁耐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厕卫设施超级干净,几乎可说是一尘不染。以上句式怎么看怎么像广告词,却是我旅行世界各地发出的真挚赞叹。
在国内,能坚持这样不花哨却实在认真的服务标准,在客栈业里太难得了。而这里一切都纯出自然:因为他们没把你当客人,因为每个房间都应该是暂时的家,因为每颗游牧的心都有疲惫的时候。
因为,世界其实很小,是个家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