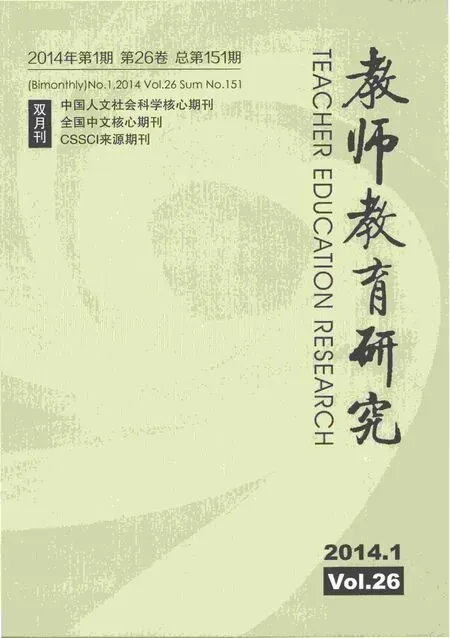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与教师的道德主体性
李义胜,叶牡丹
(安庆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优良的学校伦理是教育得以有效展开的精神背景,它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人文条件。在当前的社会情势下,教育改革向“深水区”的顺利推进,除了教育理念的陆续更新、制度及资金的有效保障外,学校伦理的优化是最为根本的精神保证。学校伦理的优化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优良师德的引领。然而,当前师德状况与社会对教师的期望值存有较大的差距。犹太裔法国哲学家埃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伦理,全面颠覆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存在论)传统,对“主体性”提出了全新的理解,进而构建了风格迥异的伦理学。对列维纳斯“他者”伦理的深刻解读,可以为教师对于伦理的本质及学校伦理的优化,提供新的思考向度,并进而涵养教师的精神气质,促使教师的道德主体性持续提升。
一、道德主体:教师的道德使命
人的道德主体性是人道德活动的内在依据,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譬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的“为仁由己”这一命题充分概括了其道德主体性思想。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言:“客观上高扬了人类的能创精神。”[1]而道家也以“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表达,通过天人相应的体验、见素抱朴的取向、德养相长的追求,描述了一种清新独立的道德主体性。那么,什么是道德主体性?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道德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在道德领域中的具体显现,也即人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自主性、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主体性建构主体,人在道德活动方面的主体性不断使人成为道德主体。
在传统社会中,教师的道德使命主要是充当社会主流价值的“代言人”,通过自身的道德践履来实现对社会大众的道德引领。而在价值多元的当今时代,教师肩负着多重道德使命,他(她)应当以道德主体的形象出现于教育场域以及社会的广泛领域。在相互异质且不可公度的诸种道德价值面前,教师首先是道德价值的“叙述者”和“阐释者”。“叙述”需要教师对“他者”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同时,“叙述”和“阐释”过程中教师不可能、也不应当做到价值无涉,它要求教师必须表达鲜明的价值立场:是传统的立场、现代的立场、还是对传统合理转化的立场?……这一切的实现必须以教师高度的道德主体性为保证。他(她)必须有高度开放、包容的文化视野及文化胸襟,并且对诸种价值能够自主、能动、创造性地选择。其次,当前社会中,传统中的一些优良价值正日益式微,甚至消失殆尽,而相对主义、自由主义、物质主义等价值观念正日渐流行……多元价值之间的互竞与冲突造成了我国当前社会某种程度的“道德无序”。因此,当前教师不仅仅是既定价值的“受动者”、“承载者”,还应当是优良道德价值的“创造者”。正如王海明先生所言:“道德都是人制定的……所制定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之优劣,完全取决于对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与道德目的的认识之真假。”[2]教师对优良道德价值的创造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真切感知,基于对道德终极价值以及道德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
二、“为他者负责”:他者伦理中的主体
列维纳斯伦理思想中的主体虽然与现象学、后现代主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理论关联,但列维纳斯所言的“主体”又与它们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列维纳斯“他者”伦理中的“主体”不仅具有现代哲学中“主体”的一般内涵,即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同时还具有“为他性”、“伦理性”等特征。
首先,列维纳斯所言的“主体”是一个伦理主体,而非认知主体。近代哲学侧重于从理性和自我意识的角度来理解主体,人的主体性也即意识的能动性。但当把理性局限于认识范围之后,就把理性从生活和历史中剥离出来,从而也就消解了理性应有的价值内涵。因为客观性的认识要求价值中立,理性的职责就被定位于以归纳推理或演绎推理等逻辑方式去把握客观的必然性。伴随着理性的认知化和逻辑化,理性就日益向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转化。这就使近代文化精神的两大支柱——理性和个体自由发生了内在的分裂和冲突。列维纳斯的核心思想就是“面对他者”,因此伦理学是第一哲学。“面对他者”不仅仅是与他者“面对面”的相遇,更是精神上的“面对他者”。列维纳斯认为,“我”与“他者”的关系不仅仅是主客体的认知关系,更不是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伦理关系。他认为,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与他人相遇,这种相遇具有伦理性。戴维斯梳理了列维纳斯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当我面对他者时,我与他是脸对脸、面对面;面孔对面孔是一种交流,而且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他人的存在以面孔显示,面孔的在场就预示着他人无法被我占有;他人的面孔一直在抵制我的占有企图,突破我的同一化;我注视着他人之“面孔”,不仅仅是一种“注视”,也是对他人的“回应”;对他人之“面孔”的“回应”具有原初的伦理性。[3]
其次,列维纳斯所言的“主体”是一个“为他”性主体。列维纳斯认为西方哲学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对“同一”的追求,无论是存在论还是自我学。从古希腊到海德格尔有着根本的一致性。从“同一”到“自我”的发展不过是一种逻辑的展开。追求“同一”意味着“他者”是我的一种变异,是他我(alter ego)。“他者”被认为是与“同一”的分离,最终要复归于“同一”。这就造成了“自我”对“他者”的控制与占有。列维纳斯确立了生存中“为他”的向度,“面对他者”意味着自觉放弃我对世界的占有性关系;意味着我必须对“他者”作出回应,从而肩负起“责任”,从而“他者”奠定了我作为主体的伦理本质。
再次,列维纳斯所言的“主体”是有着高度创造性的伦理主体。美国著名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Williamk Frankena)曾深刻指出:“……道德的产生是有助于个人好的生活,但不是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存在。”[4]可见,伦理的终极目的是让人过上一种“好”(或“善”)的生活。道德规范和标准虽然对伦理的构建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意义毕竟是有限度的,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能会变成阻碍社会和个体发展的消极因素。列维纳斯所言的“主体”并不注重道德行为规范和标准的确立,以及对道德语言本质的检验,更不去关心如何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这种“主体”采取的是超自然、超历史、超世界的视野,以建立“自我”与“他者”真正的“相遇关系”。“他者”是我所遇到的,是我所面对的,是同伴,是对话的对象。在“相遇”中呈现的“他者”是“我所不是”,这个“他”终究是不能还原到“我”的。在我与他者的相遇、对话中,“我”与“他者”都能不断超越存在,从而走向无限。因此,列维纳斯所言的“主体”并不是通过道德规范到达“好”的生活,而是在“相遇”中体验“好”的生活。主体的一切实践都是为了“相遇”,这种实践由于没有外在伦理规则的制约,因而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实践。
三、“面对他者”:教师道德主体性的表现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的伦理准则及实践方式,但它为我们揭示了伦理的基础——对“他者”的真爱和责任;它还为我们的伦理实践提供了宏观的目标和开放的路径,那就是与“他者”相遇。当前教师的道德主体性就体现在根据列维纳斯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自主、能动、创造性地选择具体的实践方式和伦理策略。
(一)与他者相遇
相遇是在某一时刻的某一地点,两个或几个人相互同时看见对方。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相遇是公共场合人们之间持续性的相互注意。列维纳斯所言的“相遇”与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颇为相似。马丁·布伯区分了两种关系“我-它”与“我-你”,并且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关系。“我-你”关系强调“直接性”,“我”与“你”的关系直接无间,没有任何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横亘于“我”与“你”之间。在“相遇”中,异在的东西与我相遇,这就使我超越自身,而非固定内在的“自我”,而是向世界敞开,接受生命中所遇之物,遂形成一个无限的关系世界。但列维纳斯与马丁·布伯又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列维纳斯所言的“相遇”关系中,“我”与“他者”并非是对等的关系,“他者”的地位要高于自己:“他人的存在权比我自己的更为重要。”[5]列维纳斯引用阿瑟兰波(Arthur Rimbaud)的诗“真实人生不在”来表达“相遇”是永恒的欲望。他试图分析并保持这样一种可能性:彬彬有礼地、富有回报地与他者相遇。它也致力于在这样一种相遇中去辨识一个仁慈与公正社会的各种源泉。[6]可见, “相遇”是优良学校伦理产生的“源泉”。教师与学生在道德上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教师道德主体性也只有在师生的“相遇”中才能得以提升。在当前,有两个因素严重阻滞了师生的相遇。一是功利主义的强力统治。教师和学生所重视的往往是“知识”的工具价值,也即知识所能带来的实际功利,而知识本身所蕴含的目的价值(人文价值)被严重遮蔽和消解。另外,师生交往时常受到功利的影响从而庸俗化,或者可以说师生交往为的是对各自利益的追逐,而不是建立于“真、善、美”这三个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尺度。二是科学主义对人文世界的僭越。科学主义遵循的是因果联系,依赖的是纯机械的因果解说方法;而人文世界是一个有理性、有激情、有目的的精神—历史世界,它遵循的是“理解”,也就是教师要不断通过“重新体验”来理解促使一个行动者或一组行动者去行动的内在理性。教育的世界既是一个科学世界,同时又是一个人文世界。而当前的学校教育,教师往往远离了学生,站在学生的“生活世界”之外,中断了与学生的情意交流与互动,把学生当成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情意、没有历史和目的的“物体”,用貌似科学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和建构学生的人文世界。因此,学校师生间的真正相遇取决于教师自觉抵制功利主义对自身的侵蚀,取决于教师自觉摆脱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强力统治。唯有此,教师才会产生对“他者”的尊重、敬畏和关怀,他(她)才能真正地与学生相遇,师生的人文世界也在这种相遇中得以不断建构。
(二)倾听与言说
列维纳斯在《别样于存在》中对“所说”(the said)和“言说”(the saying)作了区分。他认为,“言说”的意义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对“他者”的一种姿态。“所说”的重点在于它所传递的内容和信息。传统哲学中只重视“所说”的内容,世界、存在、真理、在场的秩序都是“所说”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所说就是传统哲学的居所。列维纳斯还着重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到“所说”在日常生活中的优先地位,但也要注意到传统哲学没有认识到语言另外的重要向度,也就是指向“别样于存在”的向度或者说“存在之他者”的向度。列维纳斯实质上强调了“言说”之于“所说”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说,“言说”先于语言中所有的动词变位、语言的系统,先于所有的语法……一言以蔽之,它先于我们所说的语言,它是人之与他人的“亲近”。列维纳斯的“言说”强调了诸如“坦露”、“亲近”、“谦卑”等与他者语言交流的姿态。“这种对他人的意义发生于亲近中。亲近非常不同于别的任何一种关系,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对他人的回应能力,它可以被称作人性,或主体性。”“去言说就是去亲近邻人。”[7]“言说是一种交流,确切地说,作为‘坦露’,是作有交流的条件”。[8]“坦露”像是一种裸露,是一种彻底被动性。
在教育的场景中,师生间的“相遇”实质上是精神上的一种相遇,而达到精神上的相遇就必须相互倾听和言说。校园伦理的建构,除了教师的行为引领之外,教师的伦理性语言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伦理性的语言具有描述性、规范性及情感性这三个特征。描述性是指教师语言中所包含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有大量可靠的日常事实作为支撑,使之有可靠的认知内涵;规范性是指教师的语言能够发挥应有的道德规范作用:情感性是指教师在运用语言来表述规则时,要有相应的情感,也必须激发出听众的情感。根据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我们可知教师与学生间的言说活动,除了要关注语言内容的描术性和规范性,更要关注语言表达的方式。对于教师来说,作为“他者”的学生,来自于一个高的维度,一个超越的维度。因此,学生作为“他者”,他的地位高于作为“我”的教师。因此,教师对学生的言说姿态上首先是一种真诚的“谦卑”,而不应该是居高临下的“政治灌输”和“道德说教”。这种“谦卑”源于对“他者”所具有的“他性”的尊重、敬畏和感恩——正是由于这种“他性”,“自我”才能向外在世界敞开,从而得以不断建构,从而走向无限……其次,师生在知识上虽然是一种授受关系,但在伦理上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学校是师生相遇的场景,在这个相遇的场景中,每个作为“他者”的学生都是教师的同伴和对话的对象。因此,教师与学生的言说是一种亲密伙伴间的对话,是心灵的彻底坦露和相互呈现。
(三)为他者负责
列维纳斯强调自我对他者的责任,而没有对他者提出任何要求。这种责任是对他者面貌发出的命令的回应。“是先于自由、超出本质的,它作为根源的根源、基础的基础突现出来的。‘对他人负责’的要求不断的在我身上出没,使我永远不得安宁。……”[9]教师对作为“他者”的学生负责,是基于教师对学生的“爱”。在列维纳斯那里,“爱”是其伦理的核心。有了爱,就会产生康德所言的“内在责任”,即由人的善良意志而产生的责任,而不是那种由社会角色所产生的“外在责任。”现代社会中“单子”式的存在方式已取代了传统社会中那种稳定的、充满温情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因此,囚徒困境成为陌生人社会的常态, “都市病”是城市普遍的情况。当前的儿童和青少年学生,他们更是特别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家庭中虽处于“中心”的地位,但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当他们走出家庭结构进入学校或其他社会结构时,他们体验的可能是更多的“孤独”和“不确定”。
列维纳斯并未指明“我”对“他者”负什么责任,但提供了无限开放的向度。他认为,他者的外在性是伦理的源头,外在性的进入使得主体自身性被打破,爱才得以可能。同时,真正的爱是一种自我的让位,是以“自我为中心”走向“以他人为中心”,是“成为他人的人质。”爱始于差异性,而非同一性,而为他者负责也旨在对差异性的尊重与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学生都是一个个差异性的个体,并且有着无限的成长方式和成长方向。因此,教师对作为“他者”的学生负责,并不是从预设的目标及自我的想象出发,因为这样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身上,这是对他人的“暴力”而不是关怀。教师对学生的真正负责就是放弃对学生的任何主观判断,不带任何自我的偏见与学生发生关系,在具体的关系情境中由学生来决定去需要回应什么。
四、结语:从道德代言人、立法者到道德完美主义者
著名的列维纳斯研究专家西蒙·克里奇认为有两种伦理哲学家:立法者和伦理完美主义者。前者提供系统的概念、规则,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后者就像列维纳斯。
列维纳斯展现了一个道德完美主义者形象。从自我到他人、从主体性(内在性)到外在性、从同一性到异质性。从这系列的转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列维纳斯所欲构建的是伦理最初的那种美好根基,即由“外在性”而产生的真爱和责任。列维纳斯的伦理是现代社会原始情感和责任缺失背景下的一种伦理诉求。但我们同时也感受到列维纳斯的伦理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在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大肆张扬、无孔不入的当今时代,这种以主体性的让位和对他者无条件地负无限责任为出发点的伦理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仍然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虽然列维纳斯并未给我们提供任何伦理的准则和体系,但他找到了真正的伦理的根基——即在他者面前无限的谦卑和责任,这是作为伦理人应具有的最为根本的内涵。在这意义上,这种伦理就是德里达所说的“伦理的伦理。”
在现实的意义上,教师应当是何种层次的道德主体?我们认为对教师的道德主体性应当有“道德代言人”、“立法者”、“道德完美主义者”这三个不同程度的要求。首先,当前传统德性伦理的式微似乎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社会对教师德性的提升似乎也难以寄予厚望。因此,对个体及社会组织的行为规范,更多地是依赖于种种强制性的规范和准则,而不是人的德性。因此教师的道德主体性就应当体现于自觉充当社会的“道德代言人”,他(她)是社会现有道德的“载体”,特别是他(她)应当做到对各种规则的遵从,这是底线要求;其次,从较高的要求来看,在价值多元甚至“道德无序”的当今时代,教师还应当是道德上的“立法者”,他(她)能根据道德的终极目的、社会的需要及个体发展的需要,自主、能动、创造性地创造道德价值;大多教师很难成为列维纳斯式的“道德完美主义者”,但它从方向上引领着广大教师自觉提升道德主体性。这种引领体现在,教师作为“道德立法者”,他(她)必须首先涵养自身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对“他者”差异性的应有尊重与敬畏,具有“真爱”的品质,这些是“立法者”工作的前提。
[1]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M].文凤书局,1944:56.
[2]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作者题记.
[3]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lnfinity[M].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9:42.
[4]威廉·W·弗兰克纳.善的求索——道德哲学导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7.
[5][7][8]孙向晨.面向他者一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53.205.205.
[6](英)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
[9]杜小真.列维纳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