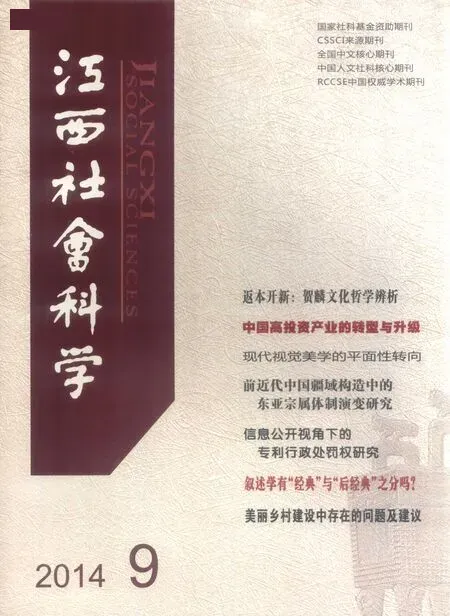叙述学有“经典”与“后经典”之分吗?
■乔国强
众所周知,大约出现在20 世纪60 年代西方的叙述学是结构主义思潮“催生”的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介绍到国内前后,已出现许多种不同的称谓,比如说“结构主义叙述学”、“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新叙事学”以及“广义叙述学”等。1997 年,现在英国杜伦大学英语系任教的戴维·赫尔曼教授曾发表了一篇题为《行动计划、顺序以及故事:后经典叙述学的因素》的文章,首次提到“后经典叙述学”这一概念。1999 年,他在编辑一本旨在讨论近期叙述学出现的许多新话题的一书中,再次提到“后经典叙述学”。①2005 年,他在与他人合编的《劳特里奇叙述理论百科全书》中,对“后经典叙述学”做出了界定。他的界定主要依据的就是他在1999 年出版的那本书。②2010 年,申丹和王丽亚合著了一本旨在介绍西方叙述理论的书,即《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在该书中,她们直接运用“后经典”一词并将其作为该书的书名。
这种将叙述学分为“经典”与“后经典”的说法缺乏学理依据,甚或说没有正确理解结构主义的原义或实质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叙述学的发展与变化。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即,梳理“经典”与“后经典”说的主要观点,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来看这种区分的非合理性,辨析赫尔曼提出的“经典叙述学”的四宗“罪”,来讨论叙述学是否应该分为“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
一、“后经典”说的主要观点
戴维·赫尔曼对所谓“后经典叙述学”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他在《行动计划、顺序以及故事:后经典叙述学的因素》一文中,提出了分析叙事文学的一些所谓“后经典”的模式。这些“后经典”的模式主要是围绕着行动计划、顺序以及故事这三个方面展开的。用他的话说,他所做的这些工作并非要把“经典叙述诗学当成一种过时的分析框架,而是论述它带有某些局限的有用性”[1](P1047 -1048)。他为此争辩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后经典叙述学的发展”[1](P1048)。需要注意的是,他在提出“后经典叙述学”这一称谓时特别强调“后经典”未必是“后结构主义的”,而是一种“吸纳了经典叙述学所未能吸纳的观念和方法”[1](P1049)的叙述学,或曰,一种被各式各样“理论模式和视角——女性主义、修辞学、语言学、计算机,所激活了”[1](P1049)的叙述学。这种“后经典叙述学”要做的工作就是去“组装某些,特别是认知方法中的因素”[1](P1049),并以此用来分析叙事话语。他认为,这样做能够“将读者反应理论重新语境化,并对共享和具有个人特点的阅读策略进行对比,这样一来,就可以将聚焦点从阐释的传统转向普通和基本的操作机制,赋予过去的阐释传统以力量并使其能够决定自己的适用范围”[1](P1049)。总之,依赫尔曼的意思,这种非结构主义的“后经典叙述学”并不是完全脱离了“经典叙述学”③的一种全新的叙述学,而是一种吸纳了一些“后经典”因素的叙述学。
第二,赫尔曼在1999 年出版的《新叙事学》④一书的引言中,对他在1997 年文章中所提到的有关“后经典叙述学”的说法,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他说:
叙述学在过去十多年来发生了惊人的嬗变,到今天似乎完全可以谈叙述学的“复兴”。换言之,叙述学已经从经典的结构主义阶段——相对远离当代文学和语言理论蓬勃发展的索绪尔阶段——走向后经典的阶段。后经典叙述学(不要将它与后结构主义的叙述理论相混淆)只是把经典叙述学视为自身的“重要时刻”之一,因为它还吸纳了大量的方法论和研究假设,打开了审视叙述形式和功能的诸多新视角。其次,后经典阶段的叙述研究不仅揭示结构主义旧模式的局限性,而且也充分利用它们的可能性;正如后经典物理学也不是把牛顿模式简单地抛在一边,而是重新思考它们的潜在思想,重新评估它们的适用范围。⑤
在这段话中,赫尔曼首次提到“经典叙述学”的局限性,不过,他并未对此进行详细论述,而是在后来编写叙述理论百科全书时具体说明了这个局限性,在此暂且不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再次重申了他以前所提出的“后经典叙述学”与后结构主义叙述理论不相干的观点。这一意在撇清与后结构主义关系的重申,再一次明确地表明了他对“后经典叙述学”的认识,即“后经典叙述学”是“经典叙述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个“重要时刻”,“后经典叙述学”与“经典叙述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承继的关系。到此为止,赫尔曼心目中的“后”似乎还是在表达时间先后这个意义上使用“后”这个词缀。
不过,从他为这段话所作的注释来看,他的真实观点与他所重申的上述内容并不一致。他在注释里解释说自己对经典与后经典之间关系的认识,主要是在一次会议上受阿卡迪·普劳特尼茨基(Arkady Plotnitsky)和巴巴拉·海恩斯坦(Babara Herrnstein)的启发。普劳特尼茨基和海恩斯坦将“后经典”界定为一种“激进思潮”、“几乎全新的解说”。他们还进一步解释说:“后经典的不确定性逻辑也许适用于经典与后经典之对立本身,因为这种对立也不是截然分明的,只是理论的对立或历史的对立,而且对立成分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等级差别。”⑥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除了具有“激进”、“几乎全新”这些品质之外,“后经典”还应与“经典”形成“对立”,只是这种“对立”不是“截然分明”的,其范围限定在“理论的对立”或“历史的对立”之中,并且“对立成分”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等级差别。在行文中,赫尔曼承认自己受到普劳特尼茨基和海恩斯坦的启发,并说将他们对“后经典”的有关认识用到了对现阶段叙述学发展趋势的讨论中来。从这样一个论证逻辑来看,他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普劳特尼茨基和海恩斯坦的观点,即把“后经典”看成是“激进”、“全新”以及“对立”的——他把自己所编辑这个原本是对不同叙述学问题进行讨论的论文集,就看成是“后经典的概念大反思工程”[2]。抑或说,依照上面的推论,赫尔曼心目中的“后经典叙述学”与“经典叙述学”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种“承继”关系,而是一种对立或决裂的关系。然而,综合起来看,他的前后说法有些自相矛盾。这种矛盾性透露出他在这一时期对“后经典”这一术语用到“叙述学”研究上还不是很有把握。
第三,赫尔曼在与他人合编的《劳特里奇叙述理论百科全书》中,对“后经典叙述学”又进一步做出了明确的界定。[3]
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该书编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赫尔曼以前的观点,即再次强调了“后经典叙述学”与“经典叙述学”之间存有一定的关系和“后经典叙述学”不应与后结构主义叙述研究相混淆这两点。与赫尔曼以前的观点相比,该处只是点出了结构主义叙述学所犯的四个错误,即“科学性、拟人观、漠视语境以及无视性别”。在随后的文字里,编者还列出了赫尔曼提出的六个新的研究叙述的角度(即女性主义、语言学、认知、可能世界理论所涉及的哲学、修辞学以及后现代)和安斯加·纽宁提出的八个方面(即把女性叙述学纳入到语境主义、主题与意识形态研究,另外还增加了基因转移和跨媒介研究这一个新的门类,并拓展了赫尔曼提出的其他几个研究范围)。赫尔曼和纽宁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语境研究的重要性;后者则详细指出如何从文本研究转换到语境研究。用他们的话来说:“结构主义是想提出一个广义叙述理论,后经典叙述学则更多考虑那个使每次阅读行为都有所不同的环境。”⑦从这个界定来看,赫尔曼和纽宁对后经典叙述学的理解和界定主要是基于研究的内涵和角度。
在很大程度上说,国内学者基本上重述了国外学者对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的看法。比如说,申丹、王丽亚在她们合著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一书中不仅很大部分地重述了国外学者对经典与后经典所做出的区别,而且还为其划出了一个大致的时间界限。[4](P5-6)
综上所述,国内外叙述研究领域里的一些主要学者对“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的界定和使用基本上是采用了赫尔曼等人的观点:(1)“后经典叙述学”不应与后结构主义叙述研究相混淆;(2)女性主义、认知、修辞等类别的叙述学属于“后经典叙述学”,抑或说,“后经典叙述学”也正是因这些类别的叙述学的出现而诞生;(3)结构主义叙述学的错误是“科学性、拟人观、漠视语境以及无视性别”。然而,从“催生”叙述学的结构主义的角度看,他们的区别是不合理的,既没有正确地理解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也没有正确地使用“后”(post-)这个词缀。
二、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分析这种区分的非合理性
自结构主义在20 世纪之初应运而生之后,讨论结构主义的学术专著不少,形式繁多。不过,依我之愚见,最为全面阐述结构主义思想的应该是瑞士学者让·皮亚杰。他那本在结构主义走向衰微时期撰写的小册子《结构主义》,不仅检验了“各个研究领域里出现的一些结构主义”,而且还“找出了结构主义的一般特点”。[5](P2)我对“后经典叙述学”非合理性的讨论,主要依据这本书对结构主义所进行的阐释。
皮亚杰认为,所谓结构,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或一个集合。这个结构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这样三个特性,其界限是由这个结构的那些转换规律所确定的;其共同点是要找出不需寻求外面帮助就能够自己说明自己的规律。找出这个规律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把找出来的结构规律形式化,并把这一形式化的东西作为公式加以运用。从皮亚杰的整体论述来看,他提出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这三个特性构成了一种贯通、联动的结构机制。“整体性”既不是“一个诸先决成分的简单总合”,也不是某个静止的“形式”[5](P5 -6);而是由“从最初级的数学‘群’结构,到规定亲属关系的结构”构成,并且是“由组成程序或过程产生”[5](P5 -8)的一个整体。抑或说,这个整体实际上不是一些以散在的形式而孤立、静止存在的个体,或因预设而存在的某个整体,而是一个因内部“转换体系”的运作而生成和不断完善的整体——这个整体因不断发生“转换活动”而存在。如果某个结构不具备这样的转换机制的话,“它们就会跟随便什么静止的形式混同起来,也就失去一切解释事物的作用了”[5](P8)。
皮亚杰提出的结构的自身调整性说白了就是指它“能自己调整”[5](P10)。这种自身调整性质能带来“结构的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这里所说的守恒性是“以结构的自身调整性为前提的”,即能使这个结构“所固有的各种转换不会越出结构的边界之外,只会产生总是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的规律的成分”[5](P10);而“封闭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闭性”,比如说,不是语言学所指的“通常情况下无法加入新条目进入其中的词性,并且这类词性通常含有较少数量的条目”[6],而是指结构自身转换调整的某种规律,是“按照不同的程序或过程才能实现的”和一个“复杂性逐渐增长的级次考虑”[5](P10)。这种自身调整性具有三个主要程序,即“节奏、调节作用和运算”[5](P12)。它们既可以是时间性的也可以是非时间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有一些调节作用,仍然留在已经构成或差不多构造完成了的机构内部,成为在平衡状态下完成导致结构自身调整的自身调节的作用。另一些调节作用却参与构造新的结构,把早先的一个或多个结构合并构成新结构,并把这些结构以在更大结构里的子结构的形式,整合在新结构里面。”[5](P12)
从叙述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几乎完全契合了皮亚杰对结构主义所作的界定和阐释。叙述学从产生的那天起,就不是或不应该是类似于孤立存在的“原子论式的联想图式”或预先形成的“涌现论的整体性图式”[5](P5),而是像皮亚杰所说的那样,存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转换的体系”。而且,无论是从叙述学研究这个体系内含的结构因素,还是从这个体系因转换而衍化出来的新的结构来看,都有一个“复杂性逐渐增长的级次考虑”。比如说,在这个体系内部有处于不同层面的若干不同成分,如故事、人物、场景、叙述者、受叙者、时间、视角等,这些不同的成分一直处在交互构成关系和不断转换生成新的关系之中;有独白、蒙太奇、基调等;还有空间、时空体、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嵌入等。在叙述学学科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有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最初提出的结构上的“语法分析”,即把人物、人物的特征、人物的行为分别类比为句子中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并借此构建成一些不同的关系;有西莫尔·查特曼提出的一个表示结构关系的图式(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叙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7](P151),还有M.J.图兰提出的与简化了的结构关系图(作者→叙述者→(受叙者)→真实读者)[8](P77)。这些发展变化正是一种如皮亚杰所言的“在平衡状态下完成导致结构自身调整的自身调节的作用”。
近二三十年间,叙述研究内部的关系结构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转换和调整,叙述学家们的关注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些叙述学家热衷于探讨事件的功能、结构规律、发展逻辑等;另有一些叙述学家则对叙述者在以口头或笔头表达的叙事作品中的功能或作用及他们在话语层次上表达事件的各种方法感兴趣;还有一些叙述学家兼顾各方,他们既关注故事层面又关注话语层面。⑧乃至发展至今,又出现了女性主义、认知、心理等多种叙述学的分支。综合这些变化来看,叙述学发展至今的整体结构及其构建模式,既反映了上面所说“复杂性逐渐增长的级次考虑”,也表现为一个类似于皮亚杰所说的“群”的模式,即“由一种组合运算(例如加法)汇合而成的一个若干成分(例如正负数)的集合”或曰一种“转换的体系”。[5](P13 -16)叙述学这个“群”在“组合运算”或“转换”的过程中,首先抽象出一些构成各分支叙述学核心部分的内容。这些核心内容既是从所谓的“结构主义”那里抽象出来的,也是从各叙述学分支在与其他学科(如女性主义、认知语言学、修辞学、心理学等)进行“协调”互动的构建中抽象出来的。这些抽象出来的核心内容形成了一些高一级的成分,超越了它们在各自体系内原有的一些成分,即“抽绎出我们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成分都能受其支配的某些共同的转换规则”[5](P18)。这些转换规则在叙述学各分支进行学科“组合运算”中找到了各自的对应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些如“女性主义叙述学”、“认知叙述学”、“心理学叙述学”、“修辞叙述学”等各种不同的“子群”即叙述学的分支。换句话说,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一些新的叙述学研究分支,并非是什么所谓的“后”,而是这个学科在自我转换中“调整”出来的结果。
另外,在皮亚杰那里,这个“群”还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具有“回到出发点的可能性”;其二是具有“经由不同途径而达到同一目的、但到达点不因为所经过的途径不同而改变的这种可能性”[5](P15)。“群”的这两个特点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这许多年来叙述学的发展脉络和走向:虽说叙述学发展出现了多种分支,但是它们既没有离开甚或常常回到最初研究的一些基本因素和基本理念,也没有脱离叙述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更没有改变叙述研究的总体方向。从那些被称之为“后经典”叙述学家的研究情况来看,他们尽管提出了一些有别于“经典”叙述学家关注的话题,比如说,他们对叙述结构的认识、叙述文本内部成分的划分、故事和话语层面的区别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话题等,但是,他们大体上还是围绕着“经典叙述学”有关叙述者、叙述视角等一些基点展开的;他们提出的那些所谓“后经典叙述学”的研究关系也还勾连着早期“经典叙述学”所构建起来的关系;甚或所使用的术语大都还是“经典叙述学”时期所构建的。说到底,所谓“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叙述学这个整体内部的一种“次序结构”关系。抑或说,它们所呈现的是一种具有“上界”和“下界”特性的“网”的模式,用“后于”和“先于”的关系把它们的所谓“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各成分联系了起来。⑨这或许就是赫尔曼强调的“‘后’这个前缀并非完全指与结构主义决裂,结构主义的许多成果常被用到一些新的分析之中”的根本原因吧。
再者说来,赫尔曼一直坚持说“经典叙述学”不是“后结构主义”的,也就是说,他认识到叙述学发展至今还没外溢出“结构主义”的框架,其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既然这样,那么他为何还要提出“后经典叙述学”这一称谓呢?依我之见,问题似乎并不在于他不懂得“后”(post-)这个词缀的意思(因为时间的先后顺序或因出现了一些与最初研究的不同侧重面,而不是不同性质,称之为“后”是不妥的),而在于他确实没有弄懂建构在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叙述学,特别是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叙述学的内部构建模式、规律、发展趋势等。所谓“后经典叙述学”与“经典叙述学”的诸多差异,其实都是这个学科整体自身所进行的一些转换和调整的结果,而并不是一个什么全新的学科——赫尔曼本人在《新叙述学》一书的引言中也承认所谓“后经典叙述学”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随着经典模式向后经典模式转移而发生的叙述理论转换”[2](P13)。这些转换和调整的过程(比如说,出现女性主义叙述学、认知叙述学等一些跨学科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形成一些“次序结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转换和调整并没有离开叙述学这个学科整体——它们不管“跨”到哪里或与谁“联姻”,都还是在这个整体之中。抑或说,由于叙述学结构内部具有“群”和“网”的性质,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就是要与其他学科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和整合,从而形成叙述学这个具有某种“次序结构”的一个整体。
皮亚杰在阐述结构主义的主要结论时也说过:“结构的研究不能是排他性的,特别是在人文科学和一般生命科学范围内,结构主义并不取消任何其他方面的研究。”[5](P118)对构建在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叙述学而言,这种“非排他性”就意味着可以与任何有益于这一学科构建的其他学科或研究领域相关联,并利用自身的转换和调整机制将这些相关联学科或研究领域整合到这个学科整体中来。
三、对“经典叙述学”的四宗“罪”的辨析
赫尔曼所批判的“经典叙述学”的四个错误,即“科学性、拟人观、漠视语境以及无视性别”,也是他将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以来的叙述学称为“后经典叙述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我的有限阅读所知,赫尔曼没有在任何场合里详细论述“经典叙述学”的这四个错误,而只是在与他人合编的那本《劳特里奇叙述理论百科全书》一书中,有七处提到“拟人观”(anthropomorphism)这一词语和两次提到“无视性别”(gender-blindness)这两个错误⑩,对另外两个错误则根本没有提及。鉴于此,我们也就只能从他在其他场合提到与此相关的话题或词语来展开讨论。
先说“科学性”。赫尔曼在为《新叙述学》所作的引言中,谈及关于叙述学的历史和沿革这一话题时,间接地提到所谓的叙述学的“科学性”。他说:“术语森严且热衷于严格分类法的叙述学是正宗结构主义的科学诉求的根本标志……当初以叙事的科学自命的叙事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落得一个‘陈旧过时’的评语。”[2](P2)从这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以得出赫尔曼所说的所谓“经典叙述学”的“科学性”的一个大致情况,即有以下三个要点:第一,术语森严;第二,分类严格;第三,以叙事的科学自命。这三点相互关联密切,具有共同的品性,不便分割。所以,下面需要综合起来讨论。
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叙述学是建立在像语言学这类具有科学品质的一些学科基础之上的。这些具有科学品质的学科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和成分及其结构关系的分类,其目的就是想以一种科学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叙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构建者在初始阶段就考虑到自己的话语体系并对自己研究的领域进行分类。他们这样做,既是这门学科的本质使然,也体现了早期构建者的严谨之处。或从学科构建的策略上来看,所谓“经典叙事学”在构建术语和进行分类方面即如赫尔曼所说的“森严”和“严格”,既是因为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小说叙事)是统一而明确的,也是出于对构建研究基点,即那些具有原型意义“母结构”而做的通盘考虑。唯此,叙述学才能够有一个作为一门学科统一的研究话题、统一的分析工具以及统一的表达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叙述学在构建初期也会考虑其理论实际运用的准确性、可行性和有效性问题。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找出能够将表达结构规律的形式,并运用“群”这个转换体系和守恒功能,从众多叙事作品、叙述方法等中抽绎出“可以使任何一种成分都能受其支配的某些共同的转换规则”或使之成为“各种结构的原型”。[5](P18 -37)今日叙述学出现多学科的“跨界”发展,所仰仗的也正是如上所例举的叙述学初建时期所构建的这种“科学性”——它所具有的转换规律和自我调整功能的科学性让跨学科发展成为可能。
再谈“拟人观”。赫尔曼等人在《劳特里奇叙述理论百科全书》一书中,七次提到“anthropomorphism”这一词语时,分别使用这个词语的名词、形容词或分词,其中有两处是名词性“anthropomorphism”,其余均为形容词性或分词性。他们在这仅两次提到名词性“拟人观”时,也均未做出任何的界定。不过,从他们唯一一次将“anthropomorphism”与“personification”的并置中⑪可以推断,他们所说的这个“anthropomorphism”(“拟人观”),其实就是“personification”(“拟人化”或“人格化”)的意思。“拟人化”或“人格化”应该不难理解,可是即便如此,他们可能出于某种考虑,在这部叙述理论百科全书中也没有界定“personification”这个词语⑫。另外,他们在使用“anthropomorphism”这一词语的形容词或分词形式时,有下列组合词语,即anthropomorphic being,anthropomorphic entities,anthropomorphic nature,anthropomorphic creature,anthropomorphized entities 等。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anthropomorphism”这个词语还可以用来表示“性质”(anthropomorphic)或“状态”(anthropomorphized),起到一种限定性作用。
可是,上面那些由表示“性质”或“状态”组合而成的词语并非都是所谓“经典叙述学”所讨论的话题,相反,更多的是所谓“后经典叙述学”要讨论的话题。比如说,anthropomorphic being 这一组合词语出现在对“照片”(photographs)这个词语的解释中:“曾有人认为,任何对某一孤立瞬间所作的视觉呈现,只要这一呈现暗示了某人或拟人物象的现在、此前或随后的现在,都可以当作一个‘压缩了的话语’。”[3](P429)其他与“拟人的”这一词语组合词的用法也属于类似情况。也就是说,对赫尔曼等人而言,“拟人的”(anthropomorphic)这个词语在他们所编写的叙述理论百科全书中,其实并不是一个指向叙述研究的特殊词语。
赫尔曼等人还指责“经典叙述学”犯了“漠视语境”(disregard for context)的错误。按理说,“经典叙述学”所犯的错误不应该在“后经典叙述学”中再次出现。可是,奇怪的是,“漠视语境”这一错误却在“后经典叙述学”中屡见不鲜。比如说,在后经典叙述学家詹姆斯·费伦与彼得·拉比诺维茨合编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2005)的一书中,只有布赖恩·麦克黑尔在《鬼魂和妖怪:论讲述叙事理论史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这篇文章中提到“语境论”[9](P63-68);在赫尔曼等人合编的《劳特里奇叙述理论百科全书》中,也没有把“语境”当作一个特别的术语来界定;在赫尔曼编辑的《新叙述学》(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1999)和《剑桥叙事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2007)两书中,同样也没有一处单独讨论甚或提到“语境”。须知,这些著作中的文章多由“后经典”叙述学家们撰写。我们虽不能绝对地说没有讨论或提到“语境”就是“漠视语境”,但是,不讨论或不触及这个问题也决不能说多么重视这个问题。从上面那些粗略的统计情况来看,在对待“语境”这个问题上,“经典”叙述学家和“后经典”叙述学家其实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只有“漠视”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是否“漠视”的区别。相反,倒是被赫尔曼称为“经典”叙述学家的施洛米斯·里蒙-凯南[3](P240)在她那部“经典叙述学”代表作之一《叙事小说:当代诗学》(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1983)的绪论中,坦承自己的论述首先“吸取了英美新批评”[10](P5)等学说的营养。我们知道,英美新批评的重要话题之一就是谈“语境”。除非另有所指,比如说,文化视域下的文学研究强调文学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3](P90-92),一般说来,“语境”指的就是新批评话语体系里的那个术语。
具体地说,“语境”最早是由新批评的前驱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1883-1917)在写于1915年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⑬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一首诗中,每个词都与其他词语相关联,“各个部分不可以称之为成分,因为每一个部分是因另一个部分的存在而受到影响,而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部分又是这个整体”[11](P22)。这一观点后来被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发展为“语境”理论。瑞恰慈在1936年出版的《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一书围绕着词语的意义来进行,提出了与休姆“语境”说相类似的看法。他说:“每一个词语对独特的语境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并从诗的语境中获得自己所在之处的确切意义。”[12](P26)这句话表明了新批评关注文本内的词语与整部作品语境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这种对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的观点不仅影响了“经典叙述学”基本理念的构建,而且也影响了“后经典叙述学”进行跨学科的拓展。虽然这“两派”都绝少明确说明自己如何运用“语境”说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或讨论具体问题(历史学研究中的“语境主义”例外),但是,他们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语境”说的基本理念,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至于赫尔曼批评“经典叙述学”所犯的第四个错误“无视性别”则不应该归罪于“经典叙述学”。叙述学作为一个学科,它自身的构建、转换、调整有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周期,不可能把所有问题一下子考虑透彻,并且把它们完全纳入整体的构建之中。“后经典叙述学”把性别问题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实在是因为所谓“经典”时期的叙述学为自己打下了这样一个具有外延属性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那么所谓的性别研究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即一个并不属于叙述学研究范畴内的性别研究。我们不能因为“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讨论话题的不同而用所谓的“后”来区分它们。
总而言之,尽管近二三十年间叙述研究内部的关系结构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转换和调整,叙述学家们的关注点也随之发生了很多变化,甚或还进行了一些“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但是,叙述学始终是在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转换和调整。那些新出现的发展方向或研究领域其实不过是由叙述学的“母结构”衍化、发展而来的,而并不带有表示不同性质的“后”的意蕴。当然,话又说回来,说叙述学始终是在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转换和调整,并不是“袒护”所谓“经典叙述学”中的一些局限性,更不是否定所谓“后经典叙述学”为克服所谓“经典叙述学”的局限性所做出的努力,而是指出叙述学这种基于形式研究的独立学科无论发展到何种田地或向何处发展,它都还是寄寓于“结构主义”的框架之内,至少无法摒弃“结构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
注释:
①参见戴卫·赫尔曼的《新叙述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
③赫尔曼虽然对叙述学做出“经典”与“后经典”之分,但是他常用“结构主义叙述学”,而很少用甚或不用“经典叙述学”这一称谓。除特殊情况外,本文不同时使用“经典叙述学”和“结构主义叙述学”这两个术语,以与“后经典叙述学”形成比照,并避免可能出现的术语使用混乱。
④为引用方便,引文使用马海良给赫尔曼主编的Narratologies 这本书的译名。
⑤戴卫·赫尔曼:《新叙述学》“引言”,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 -3页。引用时将原译文中“叙事学”一词语改为“叙述学”。下同。
⑥赫尔曼在注释中写道:普劳特尼茨基和海恩斯坦为这次会议的论文专刊作序时说:“‘后经典理论’这一术语可以表示与数学和科学以及当代文化和文学理论的激进思潮相联系的广泛含义,譬如量子物理学的实验和理论发展或当代理论生物学关于进化动力学的几乎全新的解说……后经典的不确定性逻辑也许适用于经典与后经典之对立本身。”见戴卫·赫尔曼的《新叙述学》“引言”,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⑦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450.
⑧Cf.Gerald Prince,“Narratology,”in 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 Kreiswirth (eds.),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524 -527.另见申丹、王丽亚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⑨有关结构主义的“次序结构”和“网”,参见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22页。
⑩根据该书的检索,书中有八次提到这个词语(Cf.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p.59,120,240,325,346,394,429,450;197,450)。不过,据查该书第325页中并没有出现这一词语。
⑪ 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 an,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59.Cf.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11.
⑫他们只是在界定“allegory”(寓言;讽喻)时提及personification 这一词语。
⑬1924年,英国文论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整理休姆部分遗稿并出版了《意度集》(Speculations)时,该文得以面世。
[1]David Herman.Scripts,Sequences,and Stories:E lements of a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PMLA,1997a.
[2](美)戴卫·赫尔曼.新叙述学[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
[4]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瑞士)让·皮亚杰.结构主义[M].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封闭性[EB/OL].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1%E9%97%AD%E6%80%A7.
[7]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
[8]Michael J.Toolan.Narrative: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8.
[9]James Phelan and Peter Rabinowitz (eds.).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Malden an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
[10]Shlomith 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3.
[11](英)T.E.休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A].刘若端,译.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Vincent B.Leitch.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Eigh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